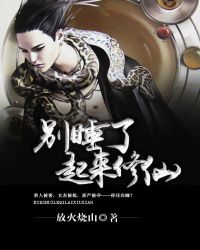第一节 柳宗元三教观对宋代儒学的影响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观新论--中国诗学研究专刊 (精)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第六章
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观的影响
柳宗元是唐代“三教融合”思潮中的儒家代表,其基于“辅时及物”立场之上的“三教融合”观,对宋代事功儒学家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反“天命论”以及以儒学为本融合三教的学术思路对宋明理学的影响也不可低估。柳宗元不但是宋代事功儒学薪火的点燃者,而且是宋明理学理性之种的播撒者。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观也极大地推动了宋以后“三教融合”思想的发展,在宋明一些有代表性的“三教融合”论者身上始终能看到柳宗元的影子。
/第一节/
柳宗元三教观对宋代儒学的影响
柳宗元在儒学发展史上的地位有待重估。有两大原因直接影响了对柳宗元儒学贡献的客观评价:一是宋代理学家对柳宗元的态度。重“名分”和大张旗鼓反佛的理学家们,对“名分不正”“助释氏之说”的柳宗元大加批判,致使其在儒学复兴运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被贬抑,甚至抹煞。二是现代学者往往把理学作为中唐儒学复兴运动的唯一“正果”。宋代儒学是沿两条线发展的,一条是以道德性命为主题的理学,一条是以经世致用为主题的事功儒学。这两大学派都是在中唐儒学复兴运动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理学是沿着韩愈偏重“内圣”方向发展而来的,事功儒学则是沿着柳宗元偏重“外王”方向发展而来,韩、柳两人对宋代儒学的影响各有侧重,而以往学界常常把宋儒学等同于理学,在突出韩愈对儒学复兴所做贡献的同时,却忽略了柳宗元的功绩。事实上,柳宗元不但是宋代事功儒学薪火的点燃者,而且是宋明理学理性之种的播撒者。
一、被“名分”和“佞佛”埋没的宋代儒学先驱
柳宗元最为宋儒所诟病的有两点:一是参与王叔文领导的“永贞革新”,“名分”不正;二是“佞佛”。这两点使他不断遭到后人的攻击,以致在复兴儒学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也被大打折扣。
有必要先对“永贞革新”作一简单介绍。一般认为,导致“永贞革新”最直接的政治原因,一是藩镇割据,二是宦官专权。永贞元年(805),唐顺宗李诵即位,他的东宫旧臣王叔文、王伾居翰林用事,又引用韦执谊为宰相。他们与柳宗元、刘禹锡等人结成政治上的革新派,共谋打击宦官势力。针对唐德宗末年的诸多弊政,“永贞革新”集团提出了许多革新建议和措施,均被唐顺宗采纳。永贞革新的主要内容是:夺取宦官兵权、集中财政大权、禁止地方官于常贡之外别进钱物、禁止盐铁使进献“月进”钱、禁止随意增加赋税、蠲免百姓积欠、降低盐价、罢宫市和五坊小儿、释放宫女及教坊女妓等。这些改革措施引起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集团及与之相勾结的节度使的强烈反对。俱文珍等人发动政变,幽禁顺宗,拥立太子李纯。最后,王叔文被贬后赐死,王伾外贬后不久病死,柳宗元、刘禹锡、韩泰、陈谏、韩晔、凌准、程异及韦执谊八人均被贬为外州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至此,持续百余日的“永贞革新”运动彻底失败。
奉诏对“永贞革新”做盖棺论定者是柳宗元的托孤诤友韩愈。其撰写的《顺宗实录》,是对“永贞革新”最早的记载与评价。韩愈虽然对王叔文等人的才能及政绩做了部分肯定,但对“永贞革新”的最后定性是“小人乘时偷国柄”,王叔文集团的拔擢人才是“狐鸣枭噪争署置” 。对柳宗元,韩愈在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为其撰写《墓志铭》的时候,仍批评他“不自贵重顾藉”、不能自持其身 。后世修两《唐书》及《资治通鉴》,关于“永贞革新”的内容,基本照抄《顺宗实录》,对其定性也是沿袭韩愈的观点。《旧唐书》评柳宗元曰:“蹈道不谨,昵比小人,自致流离,遂隳素业。” 宋代,随着韩愈名望的攀升及理学观念的成熟,柳宗元地位日趋下降。《新唐书》本着“明名分”的修史原则对《旧唐书》进行了较大改动,对柳宗元的评价更低:“叔文沾沾小人,窃天下柄,与阳虎取大弓,《春秋》书为盗无以异。宗元等桡节从之,徼幸一时,贪帝病昏,抑太子之明,规权逐私。故贤者疾,不肖者媢,一偾而不复,宜哉!彼若不傅匪人,自励材猷,不失为名卿才大夫。惜哉!” 这篇代表着官方态度的史评,敲定了柳宗元在宋代的人格基调。就连十分喜爱柳文的苏轼也对其人品大加鞭挞,认为柳宗元作《伊尹五就桀赞》“意欲以此自解其从王叔文之罪” ,并认为柳宗元“以礼乐为虚器,以天人为不相知”之思想是“小人无忌惮” 。朱熹也讽刺说:“柳子厚虽无状,却又占便宜,如致君泽民事,也说要做。”
柳宗元在宋代大受贬仰的另一原因是崇信佛教。北宋理学先驱们在中唐古文运动的基础上,继续高举复兴儒学的大旗,在道路上他们义无反顾地选择了韩愈指引的方向,视佛道二教为儒学复兴道路上的障碍,竭力主张扫除之。“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都是著名的排佛者。孙复写《儒辱》,把儒佛道三教鼎立看作“儒者之辱”,号召儒者对佛道“鸣鼓而攻之” 。石介写《怪说》,称佛道二教为“妖妄怪诞之教”,斥其“坏乱破碎我圣人之道” 。欧阳修提出“修其本以胜之”,号召儒学加强自身“礼义”建设,从而战胜佛教 。接着,张载、两程、朱熹等理学家,一边大张旗鼓地排斥佛道,一边暗暗吸收其理论精华,终于实现了儒学的复兴。在复兴儒学的整个过程之中,始终贯穿着排斥佛道的思潮,且为思想的主流。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以佞佛著称的柳宗元的地位是可想而知的。
在宋代排佛浪潮中,儒士们往往以“佞佛”作为扬韩抑柳的主要依据。如欧阳修:“自唐以来,言文章者惟韩、柳,柳岂韩之徒哉?真韩门之罪人也。” 朱熹也认为子厚不如退之,因为前者“反助释氏之说,因言异端之教” 。李涂也说:“退之辟浮图,子厚佞浮图,子厚不及退之。” 王令还翻出新花样,写《代韩退之答柳子厚示浩初序书》,代韩愈批驳柳宗元 。南宋朱子后学黄震(1213—1281),喜读柳文,但对其涉佛作品大加鞭挞。他说:“(柳集)六卷、七卷皆浮屠家碑铭,其理荡而不可究诘,其辞遁而不可明喻。” 又评《送僧浩初序》曰:“专辟退之之辟佛。愚谓退之言仁义,而子厚异端;退之行忠直,而子厚邪党,尚不知愧,而反操戈焉。子厚自以为智不遂,当矫名曰愚。吾见其真愚耳。”
众所周知,宋代儒学是在中唐儒学复兴运动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南宋以后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在思想上占据绝对优势,甚至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对柳宗元来说,理学家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在儒学史上的地位。重“名分”和大张旗鼓反佛的理学家对“名分”不正和“助释氏之说”的柳宗元大加批判,致使柳宗元在儒学复兴运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被贬抑,甚至抹煞。有研究者说:“柳宗元则很少得到理学家的肯定。这不仅有政治上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思想原因,事实上柳宗元的思想对理学产生之影响远远不及韩愈。从这一角度说,柳宗元在儒学发展史中的地位也远不如韩愈。” 柳宗元因政治原因很少得到理学家的肯定,这是事实;柳对理学之影响,即使真如作者所说“远远不及韩愈”,但由此而得出“柳宗元在儒学发展史中的地位也远不如韩愈”这样的结论也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宋代儒学并不仅仅只有理学,还有以经世致用为宗旨的事功儒学,这种儒学形态在北宋的影响远大于理学,从事功儒学来看,柳宗元在儒学史上的地位又是另一番景象。
二、柳宗元三教观对宋代事功儒学的影响
宋代儒学大致是沿两条线发展的,一条是以道德性命为主题的理学,一条是以经世致用为主题的事功儒学。这两大学派都是在中唐儒学复兴运动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中唐时期,面对儒佛道三足鼎立的局面,韩愈、柳宗元共同举起复兴儒学的大旗,试图建立儒学的“道统”,但韩柳对儒“道”内涵的理解是有很大差异的,造成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对儒佛道三教关系的理解。出于打击佛、老的需要,韩愈强调儒“道”的“仁义”道德内涵,以此把儒与佛、道区别开来;出于融合三教的需要,柳宗元强调儒“道”的经世致用内涵,认为三教可以在“佐世”功能上得到统一,因此他主张三教之间相互融合、取长补短。理学一脉受韩愈影响较深,而事功儒学一脉则受柳宗元影响较深。以往学界在评价韩、柳在儒学史上的地位时,总有扬韩抑柳的倾向,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们以宋明理学作为唐宋儒学复兴运动的唯一“正果”,然后以理学为标准来衡量韩、柳两人的贡献,从而得出韩愈为宋代儒学复兴运动的先驱之结论,而同样为儒学复兴做出重大贡献的柳宗元却被忽视了。直到今天,柳宗元对宋代事功学派的影响还没得到足够的重视。
翻检一下宋代事功派儒学家的言论,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他们大都对柳宗元抱着同情与赞扬的态度,对佛、道两教抱着宽容的态度。
1.范仲淹
范仲淹(989—1052),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一生积极倡导儒学,锐意改革除弊,领导了“庆历新政”。范仲淹是第一个公开为“永贞革新”辩护、为柳宗元等革新派鸣不平的人。他说:“刘与柳宗元、吕温数人,坐王叔文党,贬废不用。览数君子之述,而礼意精密,涉道非浅。……《唐书》芜驳,因其成败而书之,无所裁正。……吾闻夫子褒贬,不以一疵而废人之业也。” 他认为《旧唐书》对“永贞革新”的定性是以成败论是非,对柳宗元等人“以一疵而废人之业”是不符合孔子论人原则的。
南宋赵彦卫对范仲淹的观点作了进一步申述。他说:“唐八司马皆天下奇才,岂皆见识卑下而附于叔文?盖叔文虽小人,欲诛宦官,强王室,特计出下下,反为所胜被祸;而善良皆不免。当时有所拘忌,不得不深诛而力诋之。后人修书,尚循其说,似终不与为善者,非《春秋》之意也。惟范文正公尝略及之,八司马庶乎气稍伸矣。” 赵彦卫肯定了范仲淹对柳宗元等“八司马”的态度。
2.李觏
李觏(1009—1059),北宋著名儒家学者,其重经世致用的思想为范仲淹“庆历新政”提供了理论支持,也成为王安石“熙宁变法”的思想渊源。与范仲淹一样,李觏对柳宗元也抱着理解与同情的态度。在《答李观书》中,他说:“子厚得韩之奇,于正则劣矣。以党王叔文,不得为善士于朝。……若子厚、晦之,皆非凡人,被恶名,虽欲自新,而死期至矣。” 他充分肯定柳宗元的才能,同时又因其陷王叔文党而“被恶名”“不得为善士于朝”而感觉惋惜。
在《上宋舍人书》中,李觏充分肯定了柳宗元对儒学的贡献。他说:
至于汉初,老师大儒,未尽凋落,嗣而兴者,皆知称先圣,本仁义。数百年中,其秉笔者,多有可采。魏晋之后,涉于南北,斯道积羸,日剧一日。高冠立朝,不恤治具而相高老佛;无用之谈,世主储王而争夸。奸声乱色,以为才思;虚荒巧伪,灭去义理。俾元元之民,虽有耳目弗能复视听矣。赖天相唐室,生大贤以维持之。李杜称兵于前,韩柳主盟于后。诛邪赏正,方内响服。尧舜之道,晦而复明;周孔之教,枯而复荣。 注释标题 《李觏集》,第290页。
在这段话中,李觏梳理了汉唐儒学的发展流变史。他认为:汉代,由于有大儒们的存在,儒学得以传承,而魏晋以后,佛老盛行,儒道衰羸,先圣之道不复能闻。唐代以降,天生大贤重整儒纲,前有李杜,后有韩柳,诛邪赏正,使尧舜孔子之道晦而复明、枯而复荣。这种观点是否准确,姑且不论,我们所感兴趣的是他对柳宗元的评价。在李觏看来,柳宗元与韩愈是中唐儒学复兴运动的主将,他们所领导的儒学复兴运动在当时得到广泛支持,终于使圣人之道得以恢复。这就充分肯定了柳宗元在儒学史上的地位。
李觏对佛教的态度与柳宗元是基本一致的,他受柳宗元影响的痕迹也是十分明显的。他说:“昔之排浮屠者,盖犹有过,徒非其非,而弗及其是。虽柳宗元尚不听退之,况其庳者乎?” 这是在评论韩愈与柳宗元两人关于排佛问题的争执。李觏认为,韩愈只看佛教“非”的一面,而不看其“是”的一面,这种态度是有失偏颇的,因此他认为柳宗元对韩愈的反驳是正确的。
与柳宗元一样,李觏对佛教持一种十分理性的态度。首先,充分认识佛教在教化、义理等方面的合理性。李觏说:“逮宋有天下,兵革既已息,礼乐刑政,治世之器既已完备,推爱民之心,以佛法之有益也,广祠度众,不懈益勤。” 他充分认识到佛法对稳定社会秩序所起的作用,甚至认为朝廷推行佛法是“爱民之心”的表现。其次,在肯定佛法重要性的同时,对其不利于社会的一面也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判。李觏曾从破坏社会生产、扰乱社会秩序、浪费社会经济等方面列举了佛教十大危害,也曾从绝亲弃君、不婚无后等方面批评佛教违背儒家伦理。第三,提出佛教不能偏离儒家之道。李觏说:“夫所谓修心化人者,舍吾尧舜之道,将安之乎?彼修心化人而不由于礼,苟简自恣而已矣。” 他还立足于儒家立场,规劝出家僧众遵守教规、依法修习:“吾愿释子,毋意于水,将意于理。尔身以澡,尔心以洗。洗心谓何?匪尘匪沙,匪刮匪摩。去尔羡欲,任尔平和。无可不可,所遇皆我,万物一焉。何者为因?孰谓之果?道不离人,吾身佛身,吾伪亦真。门前舟梁,自失要津。”
另外,李觏与柳宗元一样,立足于事功来批评孟子的义利观。柳宗元在《吏商》中批评了孟子“谋道不谋富”思想。他把人分为两大类:一是“诚而明者”,二是“明而诚者”,认为前者“不可教以利”,而后者不但可以教以利,而且能以利退害。同样,李觏也反对孟子重义轻利的思想,他说:“孟子谓‘何必曰利’,激也。焉有仁义而不利者乎?” 认为仁义与利是不可分离的,这种观点在宋代儒家事功学派中是很普遍的。
3.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年),北宋政治家、哲学家、文学家,“荆公新学”的开创者。在政治上,王安石积极提倡兴利除弊,领导“熙宁变法”,新法因遭到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的激烈反对而失败,王安石也因此罢相。理论上,王安石提倡“新学”,力排章句注疏之学,修撰《三经新义》(《诗义》《书义》《周礼义》)以实践其“以经术造士”之实用目的,还利用为《老子》作注、解释《洪范》、撰述《字说》等机会,为其政治改革提供理论根据,“荆公新学”的根本意旨在于发挥儒家学说经世致用之功能。
王安石对柳宗元有较高的评价。他说:“余观八司马,皆天下之奇材也,一为叔文所诱,遂陷于不义。至今士大夫欲为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八人者,既困矣无所用于世,往往能自强以求列于后世,而其名卒不废焉。而所谓欲为君子者,吾多见其初而已,要其终,能毋与世俯仰以自别于小人者少耳!复何议彼哉?” 这段话表达了三层意思:一,“八司马”都是“天下之奇才”,走上不义之路是受王叔文的诱惑;二,“八司马”被贬之后,“能自强以求列于后世”,所以其名不可废;三,后人以攻“八司马”而求名,是不足取的。与欧阳修反对韩柳并举相反,王安石主张两人并举,他说:“自孔子之死久,韩子作,望圣人于百千年中,卓然也,独子厚名与韩并。……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 他是站在“有补于世”立场之上来评价韩柳文的,故认为“独子厚名与韩并”。
王安石不但违逆当时抑柳潮流而对柳宗元做出较高评价,而且在思想上也与柳宗元有许多相近之处。在对待佛、道两教的态度上,王安石认为,尽管两教有悖于儒家的礼乐制度,但在学理上仍有可取之处,故主张立足于儒家立场来吸收佛道理论之长。在宇宙论上,主张“气本论”,认为“道”即是元气,是宇宙的本原,“道有体有用。体者元气之不动,用者冲气运行于天地之间” 。在心性论上,他否定道德先天论,反对以善恶论人性。以上这些方面,都与柳宗元的思想相一致,从中可以看出其前后相续的发展轨迹。
4.陈善
陈善,两宋之际人,著《扪虱新话》十五卷。《四库提要》评曰:“大旨以佛氏为正道,以王安石为宗主。故于宋人,诋欧阳修、诋杨时、诋陈东、诋欧阳澈,而诋苏洵、苏轼、苏辙尤力,甚至谓辙比神宗于曹操。于古人诋韩愈,诋孟子。……观其书颠倒是非,毫无忌禅,必绍述余党之子孙,不得志而著书者也。” 可以看出,陈善是王安石思想的追随者,反对排佛论。《四库提要》根据陈善诋毁众多反对改革的保守派,而断定他“必绍述余党之子孙,不得志而著书者”,又站在正统儒家立场之上,批评《扪虱新话》为“颠倒是非,毫无忌禅”。
《扪虱新话》卷十二有“柳子厚罪在朋党然有功不可掩”条:“予读柳子厚《伊尹五就桀赞》,未尝不怜其志也。伾、叔文虽小人,而子厚欲因以行道,故以就桀自比,此其本心也,然学者至今罪之。……《春秋》之法,不以功掩过,亦不以罪废德。责备而言,则子厚之罪,在于附小人以求进。若察其用心,则尚在可恕之域,况一时之善有不可掩者乎?” 这种观点与王安石是完全一致的。
5.叶适
叶适(1150—1223),“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反对朱熹“理学”与陆九渊“心学”,强调功利、注重事功,主张言必可行、开物成务。
叶适十分欣赏柳宗元的“辅时及物”思想。他说:“仆旧读柳子厚文,独爱其序送娄图南极有理,使世之君子,畔其道以从异学,劳而无成者,可以自镜。正惟不劳而成,固与龟蛇木石无以异耳。愿足下深思惟忠之事,而反复子厚之意,救世俗之失,正诸子之非,明圣人之经,是所期于少望者。” 叶适喜欢柳宗元《送娄图南秀才游淮南将入道序》的原因,在于其对事功的强调。娄图南“智可以任职用事,文可以宣风歌德”,却甘愿为处士,柳宗元批评他不合时宜:“幸而好求尧、舜、孔子之志,唯恐不得;幸而遇行尧、舜、孔子之道,唯恐不慊,若是而寿可也。求之而得,行之而慊,虽夭其谁悲?今将以呼嘘为食,咀嚼为神,无事为闲,不死为生,则深山之木石,大泽之龟蛇,皆老而久,其于道何如也?” 柳宗元主张人之生命的价值要与行“尧舜孔子之道”联系起来,叶适对这种观点十分欣赏,以此勉励后学致力于“救世俗之失,正诸子之非,明圣人之经”。
叶适不但喜读柳宗元之文,在学术观点上也受其影响很大。首先,在对待佛、老态度上,两人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叶适说:
自孟轲拒杨墨,而韩愈辟佛、老,儒者因之。盖杨、墨之道既已息矣,而佛、老之学犹与孔氏并行于天下,是以儒者望而非之,以为非是而无以为儒。夫望而非之,则无以究其学之终始,而其为说也不明。昔者恶夫攻异端者,夫不修其道,以合天下之异,而纷然攻之,则只以自小而为怨;操自小之心而用不明之说,而其于佛、老也,助之而已矣。且学者,所以至乎道也,岂以孔、佛、老为间哉?使其为道诚有以过乎孔氏,则虽孔氏犹将从之。惟其参验反复,要之于道之所穷,卒不可以舍孔氏而他求者,故虽后世亦莫得而从也。 注释标题 〔宋〕叶适:《水心别集》卷六《老子》,《全宋文》第二八五册,第362页。
叶适批评那些根本不懂佛道之学而妄加指责的儒者,认为这是“自小”即狭隘之心在作怪,这种“操自小之心而用不明之说”式的批评不但无损于佛老,反而有助之。他提出要打破“以孔佛老为间”之主观臆断,以“道”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并反复参验于实际。这其实与柳宗元以“佐世”来论证佛道存在的合理性是一致的。
其次,否定孟子在儒家道统中的地位。柳宗元着眼于事功而把孟子排除在儒家“道统”之外,他认为孟子“其功缓以疏”,不像孔子那样“急民”。受此影响,叶适也认为儒家“道统”只有尧、舜至孔子—段可信,至于孔子传曾子、曾子传子思、子思传孟子,多为后儒之浮论,不可尽信。他认为,孟子“专以心性为宗主”,背离了“孔子本统”,是后儒空疏学风的始作俑者,因此“舍孔子而宗孟轲,则于本统离矣” 。
第三,反对割裂义利关系。叶适批评董仲舒“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之说,云:“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 认为义应是利中之义,义与利是不可分离的,这种观点与柳宗元也是完全一致的。
6.陈亮
陈亮(1143—1194年),浙东“永康学派”的代表人物。陈亮反对朱熹、陆九渊空谈“道德性命”的学风,认为他们是“相蒙相欺,尽废天下之实” ,“书生之智,知议论之当正,而不知事功之为何物” ,严厉斥责他们的观点“是真腐儒之谈也” 。从经世致用角度出发,陈亮反对当时的排佛老风潮,认为佛老与儒“有无相通、缓急相救” ,反对政府干涉佛教事务,并主动为佛寺置田产、捐钱物。陈亮包容佛老、宽护佛教,但不失其儒家立场。“陈亮对佛教的宽护,根本看来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其最终目标是保护和弘扬儒学,推行儒学的价值。” 在义利关系上,陈亮坚持“义利双行”原则 ,认为所谓“王道”“仁义”无非是“爱人利物”的“救民之心”,而仁义之心必须通过利民的实事实功才能表现出来。
陈亮之学虽无明确的师承,但从强调儒学经世致用、辅时及物,强调儒佛道三教之间的互补互融,强调王道、仁义的民生内涵,以及强调“盈宇宙者无非物” 之宇宙观等方面来看,他是很欣赏柳宗元思想的。柳宗元的文章在南宋已经很流行,尤其受到事功学派的喜爱,所以,面对当时朝祚飘摇、国势衰微的形势,陈亮在与以韩愈为宗主的“道德性命”学派论战的时候,自觉地选择了柳宗元,这是完全可能的。
综上所述,柳宗元基于“辅时及物”立场之上的三教融合观对宋代事功儒学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这些重视事功的儒家学者,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积极兴利除弊的革新家,另一类是面对民族危亡的局势,反对理学空谈“道德性命”的事功派。北宋初年百废待举的社会现实与南宋时期民族危亡的社会危机,都与安史之乱后的大唐帝国相似,宋代重事功的儒家学者之所以自觉地选择了柳宗元,是因为其“辅时及物”的思想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相适应。
三、柳宗元三教观对宋明理学的影响
谈到宋明理学,人们一般会把源头追溯到中唐时期的儒学复兴运动,再把韩愈定位为理学滥觞时期的最重要代表。钱穆说:“治宋学必始于唐,而以昌黎韩氏为之率。” 陈寅恪《论韩愈》一文,从六大方面论述了韩愈在唐代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一,建立道统,证明传授之渊源;二,直指人伦,扫除章句之烦琐;三,排斥佛老,匡救政俗之弊害;四,呵诋释迦,申明夷夏之大防;五,改进文体,广收宣传之效用;六,奖掖后进,期望学说之流传 。因此,他认为:“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 《论韩愈》一文奠定了现代关于韩愈儒学地位研究的基调,尽管后人时有增减 ,但大致不出此范围。韩愈对宋明理学确实起到了开风气之作用,但柳宗元对宋明理学的贡献也绝对不能小视。上述陈寅恪对韩愈评论的第一、第二、第五、第六四个方面,在柳宗元身上也有鲜明的体现 ,除此之外,我们至少可以说,柳宗元贡献了两种对宋明理学来说必不可少而又为韩愈所反对的思想:一是反天命论思想;二是以儒为本融合三教的学术思路。
(一)播撒理性之种
宋明理学,相对于章句之学、考据之学而言,是一种义理之学,是一种以研究儒家经书义理、探究宇宙、心性本源以及万物之理的道德形而上学。“理学”之“理”在不同场合有不同的含义,陈来把它概括为五种:“宇宙的普遍法则,这个意义的理可称为天理;作为人性的理,可称为性理;作为伦理与道德规范的理,可称为伦理;作为事物本质与规律的理,可称为物理;以及作为理性的理,如理学讨论的理气相胜问题所表现的,可称为理性。” 不论以上哪种意义上的“理”,都是与“天命论”不能相融的。
朱熹把“天”的含义概括为:“要人自看得分晓,也有说苍苍者也,也有说主宰者也,也有单训理时。” “说苍苍者”,指以道家为代表的“自然天道观”;“说主宰者”,指汉唐以来的“天命论”;“单训理”,指宋代理学家以“理”取代“天”作为万物本原的思想。朱子又说:“而今说天有个人在那里批判罪恶,固不可;说道全无主之者,又不可。” 这是在批判“天命论”与“自然天道观”,从而彰显以“理”代替“主宰之天”与“自然之天”的合理性。在理学家看来,抽象无形之“理”是最高层次的实体范畴,是可以派生天地万物的本体,气是构成万物的具体材料,理与气的关系是:“有是理后生是气。……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 由此可见,理学的流行必须以摧毁“天命论”为前提。
摧毁“天命论”,为理学的形成与发展扫清障碍的人是柳宗元而不是韩愈。韩愈是一个“天命论”者,他认为“贵与贱、祸与福存乎天” 。韩愈在给柳宗元的信中,提出“天能赏功罚祸”的观点,表达对“天命论”的肯定,柳写《天说》予以反驳。柳宗元坚持天的物质性与自然性,提出“天人不相与”“功者自功,祸者自祸”等观点。后来,刘禹锡也加入韩柳二人关于天命的论争,写《天论》三篇申述柳宗元的观点。除此之外,柳宗元还写了大量批判“天命论”的文章,如《贞符》《蜡说》《时令论》《天对》《非国语》等。由于柳宗元、刘禹锡等人的努力,“天命论”在中、晚唐几近消逝,这为宋代理学的萌芽创造了良好的文化环境,正如洪修平先生所说:“这个时期柳宗元和刘禹锡在天人关系论上分合的意义,除了其对历史上的元气自然论和反天命论的继承、发展和总结之外,很重要的还体现了儒家理性主义的兴起,即并不仅关注天人的分别或人之外的天道的规律,而且还特别着眼于对人本身的理性力量的发现,以反对在天人关系问题上的蒙昧主义和泛滥于隋唐时期的祥瑞灾异,从而为人文化的儒家开辟了新的路径。”
(二)融合三教的学术思路
不论宋明理学家是否承认,理学是在涵泳三教的基础之上而形成的,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有学者说:“(理学)是以儒学的内容为主,同时吸收了佛教和道教思想,是在唐代三教融合、渗透的基础上孕育、发展起来的。” 赖永海先生说得更为具体:“儒家凭借着自己在中华民族的心理习惯、思维方式、宗法伦理等方面根深蒂固的影响,以及王道政治与宗法制度的优势,自觉或不自觉地、暗地里或公开地把佛、道二教的思维模式和有关思想内容纳入到自己的学说体系中,经过唐朝五代之酝酿孕育,至宋明时期终于吞并了佛、道二教,建立了一个治儒、释、道三教于一炉、以心性义理为纲骨的理学体系。” 总之,宋明理学的形成离不开唐代以来三教融合的文化土壤,“治儒、释、道三教于一炉”是宋明理学的根本特点。
前面我们说过,柳宗元是唐代儒家“三教融合”论的最高代表,他所指引的方向,恰是宋明理学的发展方向。宇宙论方面,柳宗元受佛教“缘起论”启发,悬置宇宙起源问题,坚持并发展道家的“元气”论,并把“元气”上升到本体高度,建立起“元气”自本自根的宇宙论。心性论方面,柳宗元在充分吸收三教资源的基础之上,重新界定“志”与“明”的内涵,并以“性静”作为儒佛道三教心性论的契合点。柳宗元在三教融合基础之上的理论建构,为宋明理学本体论、心性论的建设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以上两个方面,是柳宗元对宋明理学所做的最大贡献,当然其贡献远不止这两个方面,还有扫除章句之弊等。宋明理学与汉学在方法上最主要的区别就在于,汉学重视章句训诂,理学重义理发挥。扫除汉唐以来蒙在儒学之上的章句之风,是宋代理学产生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柳宗元与中唐“新《春秋》学派”对汉唐以来的章句之学进行了彻底清算,柳宗元指斥章句师为“腐败之儒”,说自己“幸非其人”,炮火十分猛烈。他们弃传谈经,专凭己意说经的治经方法,对宋儒以义理解经产生了直接而重要的影响,如宋儒“《春秋》学”著作200余部,走的基本上是中唐后期“新经学”的道路。柳宗元是中唐后期“新《春秋》学”思潮中的重要一员,他扫除章句之弊,为宋理学的产生做出了重要贡献。 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观新论--中国诗学研究专刊 (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