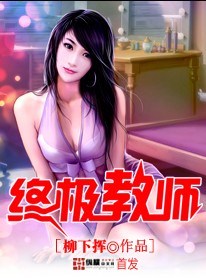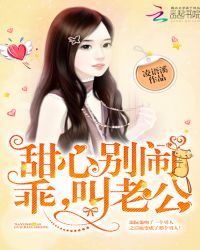第二节 柳宗元的儒“道”诠释原则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观新论--中国诗学研究专刊 (精)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第二节/
柳宗元的儒“道”诠释原则
柳宗元的儒“道”诠释原则,是针对魏晋以来儒学的弊端而提出来的。魏晋以来,佛、道两家思想大盛,而儒学则拘促于章句之学中难以自拔,在理论上几无建树。韩愈描述儒学的尴尬处境说:
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扬,则入于墨;不入于老,则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噫!后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孰从而听之? 注释标题 《原道》,《韩昌黎文集校注》,第14页
这种局面一直到中唐时期还没得到扭转。柳宗元批评当时的儒学说:
近世之言理道者众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无焉。其言本儒术,则迂回茫洋而不知其适;其或切于事,则苛峭刻核,不能从容,卒泥乎大道。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为灵奇,恍惚若化而终不可逐。故道不明于天下,而学者之至少也。 注释标题 《与吕道州论非国语书》,《柳宗元集》第三册,第822页。
初唐以来,“言理道者”都说自己的理论本于“儒术”,但在这种表面的兴盛背后却隐藏着三大弊端:一是“迂回茫洋而不知其适”,即隐晦曲折、漫无边际,不能经世致用;二是拘泥于“事实”,过于烦琐,不能从具体事实之中提取出儒学的真精神;三是“推天引神”,充斥着神异色彩。为了实现儒学的复兴,就必须以一种更加理性的态度对儒家经典进行重新诠释,从中开发出经世致用的“真精神”。于是,柳宗元远绍汉代“公羊学”,近承中唐“新《春秋》学”,提出了自己的儒“道”诠释原则。
一、从“公羊学”到“新《春秋》学”
《春秋》本是周王朝和各诸侯国历史的通称,后特指经过孔子修订的鲁国编年史 。它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722—前481)的历史,其记事简略,长则不过四十余字,短则仅有一字,这种记事简略的特点为后人的诠释留下了广阔的空间。诠释《春秋》之作,著名的有三传:左丘明《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 、公羊高《春秋公羊传》(简称《公羊传》)、穀梁喜《春秋穀梁传》(简称《穀梁传》)。“三传”分属于两种诠释系统。《左传》以《春秋》的记事为纲,增加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传说,以叙事为主,议论较少,属于以事解经者;《公羊传》《穀梁传》侧重阐发《春秋》经义,注重其经世致用之目的,以议论为主,叙事较少,属于以理解经者。
《公羊传》注重阐发《春秋》的微言大义,将其核心思想归结为“大一统” ,因为此思想与汉武帝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相一致,《公羊传》遂被武帝立为“官学”,成为今文经学的最高代表。
董仲舒继承并发扬了“《春秋》公羊学”微言大义的诠释方式,“推天道以明人事”,阐发其以“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灾异谴告”为核心内容的神学目的论,从哲学上为“大一统”思想作形而上的神学论证。具体而言,董氏对《春秋》的诠释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神异指向。董仲舒说:“有非力之所能致而自致者,西狩获麟,受命之符是也。然后托乎《春秋》正不正之间,而明改制之义。一统乎天子,而加忧于天下之忧也,务除天下所患。” 孔子与天相通,知天命成败。孔子“西狩获麟”,是天向他宣告其道已穷,命他作《春秋》以“明改制之义”“务除天下所患”。“西狩获麟”是孔子的受命之符。这种解释方法带有强烈的神异色彩。
第二,现实指向。董仲舒认为,孔子作《春秋》的目的是为人间确立是非善恶标准,为人间立法。他说:“《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 董仲舒不但强调《春秋》能在理论上给人指明是非善恶的标准,更强调把这种标准运用到现实生活之中去。他说:“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万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贤才,以待后圣。故引史记,理往事,正是非,见王公。史记十二公之间,皆衰世之事,故门人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为见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苏舆注曰:“空陈古圣明王之道,不如因事而著其是非得失,知所劝戒。” 这就是说,既要以《春秋》来明圣王之道,更要把它行诸于事。“《春秋》折狱”,就是董仲舒现实指向诠释原则的具体运用。
第三,“通变”原则。董仲舒说:“《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见其指者,不任其辞。不任其辞,然后可与适道矣。” 又说:“《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而一以奉天。” 苏舆认为“无通辞”与“无达辞”意思相同,都是“无达例”之意,他又引程子语曰:“《春秋》大率所书事同则辞同,后人因谓之例。然有事同辞异者,盖各有义,非可例拘也。” 针对《春秋》在语言上“无通辞”的特点,董仲舒提出两条诠释原则:一是“从变”,二是“从义”。“从变”,是“见其指者,不任其辞”,即透过字面之意把握其真实指向;“从义”,透过不同的指向把握恒常不变之道。苏舆对“从变从义”的解释非常精当,他说:“盖事若可贯,以义一其归;例所难拘,以变通其滞。两者兼从,而一以奉天为主。” 以义通事,以变通例,两者结合,从而达到奉天法古、经世致用之目的。
以上三个方面各有侧重,又互相联系。现实指向是董仲舒诠释《春秋》的最终目标,神异指向为人间指向提供形而上的根据,通变原则是人间指向得以实现的基本保证。柳宗元充分肯定了董仲舒诠释理论的人间指向与通变原则,又强烈地批判了其神异指向。
对柳宗元儒教观产生最直接而深刻影响的是中唐时期的“新《春秋》学派”。“新《春秋》学派”否定汉唐传注经学,认为它们“不合经”,主张“舍传求经”。虽然“新《春秋》学派”声称兼采三传、择善而从,但他们不满于当时“《春秋左传》学”过分注重章句训诂而不切实用的诠释方法,更倾心于“公羊学”的“通经致用”与“微言大义”。“新《春秋》学派”对“公羊学”的推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认为《公羊》《穀梁》优于《左传》。赵匡说:“今观左氏解经,浅于公、穀,诬谬实繁。若丘明才实过人,岂宜若此?” 他甚至认为《左传》的作者可能不是左丘明。抬高《公羊》《穀梁》而贬低《左传》的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们倾心于“公羊学”的经世致用,而不满于“《春秋左传》学”的名物训诂。
第二,对《春秋》宗旨的理解更近于“公羊学”。啖助说:“春秋者,救时之弊,革礼之薄。” 赵匡则曰:“啖氏依公羊家旧说,云《春秋》‘变周之文,从夏之质’。予谓《春秋》因史制经,以明王道。其指大要二端而已:兴常典也,著权制也。” 虽然啖、赵两人对《春秋》宗旨的概括有较大的不同,但不论是啖助的“救时之弊,革礼之薄”说,还是赵匡的“兴常典,著权制”说,都强调《春秋》经世致用的特征。
第三,采取空言说经、以经驳传等方法,冲破当时“《春秋左传》学”的束缚而把《春秋》经的诠释方向引向现实社会。
大盛于汉代的“公羊学”,由于其诠释方式的神异指向遮蔽了自身的现实指向而误入谶纬神学的死胡同。入唐以来,随着《五经正义》的颁布,《左传》作为《春秋》经的代表而成为文人学子入仕的必由门径,其天然的章句品格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中唐崛起的“新《春秋》学”,以摧枯拉朽之势冲决了章句之学的堤防,又剥去“公羊学”神异的外壳,重新把“《春秋》学”引向现实关怀。柳宗元对儒“道”内涵的诠释原则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建立起来的。
二、柳宗元与“新《春秋》学人”交游考
柳宗元受中唐“新《春秋》学派”的影响很深,他们所倡导的“疑古”“经世致用”思想是柳宗元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先来考察一下柳宗元与“新《春秋》学人”之间的交往,以便更好地理解其儒教观。
1.陆质
陆质(?—806),原名陆淳,后因避唐宪宗名讳而改名陆质,字伯冲,号文通,唐吴郡(今江苏吴县)人。陆质曾任左拾遗,转太常博士,迁左司郎中,后又改为国子博士,历任信、台两州刺史,征为给事中、皇太子侍读。陆质曾师事啖助和赵匡治《春秋》学,编撰《春秋集传篡例》十卷、《春秋微旨》三卷、《春秋集传辩疑》十卷,“务在考三家得失,弥缝漏阙”,观点“多异先儒”“实导宋人之先路” 。
柳宗元早年居长安时曾拜谒陆质。贞元二十一年(805)四月九日,陆质为皇太子侍读,同日柳宗元擢为礼部员外郎 ,两人居同巷,柳向陆执弟子礼。遗憾的是,“未及讲讨,会先生病”,尽管如此,柳宗元还是从陆质那里聆听了一些“要论”“教诲”,他表达自己对陆质的景仰之情曰:“恒愿扫于陆先生之门。” 同年九月十三日,柳宗元贬邵州刺史,十五日,陆质去世。十一月,在往邵州途中的柳宗元又被加贬永州,到永州不久,柳宗元作《唐故给事中皇太子侍读陆文通先生墓表》,由此可见柳宗元对陆质的一片敬仰之情。《答元饶州论春秋书》与《唐故给事中皇太子侍读陆文通先生墓表》,是研究柳宗元与“新《春秋》学”关系的重要文献。
2.吕温
吕温(772—811),字和叔,一字化光,河中人。祖父延之,官至浙江东道节度使;父渭,湖南观察使。吕温贞元十四年进士及第,又登宏辞科,授集贤殿校书郎。吕温与柳宗元是同僚,两人友情甚笃,柳宗元曾说“交侣平生意最亲” 。元和六年(811)吕温卒,柳宗元作《祭吕衡州温文》《同刘二十八哭吕衡州诗》《唐故衡州刺史东平吕君诔》等诗文以祭。
吕温很早就师从陆质治《春秋》学。他说:“某以弱龄获谒于公。” 刘禹锡也说:“(吕温)又师吴郡陆质,通《春秋》。” 吕温在“《春秋》学”方面造诣很深,柳宗元赞曰:“《春秋》之元,儒者咸惑。君达其道,卓焉孔直。”
吕温在“《春秋》学”方面对柳宗元产生了很大影响。柳宗元在《祭吕衡州温文》中说:“宗元幼虽好学,晚未闻道,洎乎获友君子,乃知适于中庸,削去邪杂,显陈直正,而为道不谬,兄实使然。” 可以看出,他对“《春秋》学”的了解是从与吕温交游以后才开始的,他第一次见到陆质的《春秋集传集注》也是在吕温处,从此以后,“恒愿扫于陆先生之门”。
3.韩晔、韩泰、凌准
“八司马”中,韩晔、韩泰、凌准三人都与柳宗元讨论过“《春秋》学”的问题。韩晔(生卒年不详),字宣英,京兆(今陕西西)人。韩泰(?—813),字安平,雍州三原(今陕西三原)人。凌准(?—808),字宗一,杭州富阳(今浙江富阳)人。据《答元饶州论春秋书》载,柳宗元当年曾在裴墐处听韩晔与吕温谈论“《春秋》学”,感叹“知《春秋》之道久隐,而近乃出焉”;在韩泰处得到陆质的《春秋微旨》;在凌准处得到陆质《宗指》《辨疑》《集注》三部《春秋》学著作 。
4.元洪
柳宗元《答元饶州论政理书》题下注曰:“《新史·年表》有元洪者,尝为饶州刺史,而时不可考。”元洪任饶州刺史的时间大约为元和七年至九年 。柳宗元的好友韩晔因王叔文党而被贬到元洪处做司马,元洪曾举荐韩晔代替自己的职位,柳宗元因此对元洪大加称赞。元洪精研“《春秋》学”,刘禹锡曾赞曰:“知天而不泥于神怪,知人而不遗于委琐。” 柳宗元早年就听吕温说起过元洪,并认为他在某些观点上“虽啖、赵、陆氏,皆所未及”。元洪、韩晔、柳宗元三人都热衷于“《春秋》学”,大概是因为韩晔所起的中介作用,柳宗元与元洪彼此之间有了较为深刻的了解,两人常以书信方式探讨“《春秋》学”与政理。《柳集》中有《答元饶州论春秋书》与《答元饶州论政理书》。
三、儒“道”诠释原则的确立
柳宗元在充分吸收中唐“新《春秋》学”诠释精华的基础上,剥除了历代经学家笼罩在儒“道”之上的厚厚的神圣、神异蔽障,并结合当时的社会状况,提出了自己的儒“道”诠释原则。
(一)去蔽与还原
柳宗元认为,对儒家经典进行重新诠释,首先要有一个“削去邪杂,显陈直正”的去蔽过程 ,包括去除章句之蔽、“神圣”之蔽、“神异”之蔽三个方面。
1.去除章句之蔽
柳宗元在《陆文通先生墓表》中批评《春秋》章句之学说:
孔子作《春秋》千五百年,以名为传者五家,今用其三焉。秉觚牍,焦思虑,以为论注疏说者百千人矣。攻讦狠怒,以辞气相击排冒没者,其为书,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或合而隐,或乖而显。后之学者,穷老尽气,左视右顾,莫得而本,则专其所学,以訾其所异,党枯竹,护朽骨,以至于父子伤夷,君臣诋悖者,前世多有之。甚矣,圣人之难知也。 注释标题 《陆文通先生墓表》,《柳宗元集》第一册,第208页。
《春秋》自问世以来,上千儒者“穷老尽气”、挖空心思地对其进行阐释,不同派别之间常常“攻讦狠怒,以辞气相击”,甚至造成“父子伤夷,君臣诋悖”的局面,写出的诠释著作虽然汗牛充栋,却“莫得而本”,结果不但不能挖掘出儒家的真精神,反而把它遮蔽得越来越厚,圣意越来越难知。
两汉儒学的最主要形态为经学。经学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前者注重对经书义理的发挥,治经强调微言大义、经世致用,与政治的关系密切;后者注重经书的文字校勘,治经强调名物训诂,与社会的关系相对远些。作为古文经主要著作的《左氏传》,对《春秋》的诠释采取的是“以事解经”的方法,这就决定了后来的研究者对其采取“名物训诂”的诠释方法,终因过分诠释而流于烦琐;作为今文经主要著作的《公羊传》和《穀梁传》,由于采取空言解经的方法,这决定了后来的研究者对其采取义理阐发的诠释方法,终因过分诠释而流于空疏。柳宗元所谓的“迂回茫洋而不知其适”,即是指今文经学的空疏之病,而他所谓的“切于事,则苛峭刻核,不能从容,卒泥乎大道”则指古文经的烦琐之病。西汉刘向治《穀梁传》,其子刘歆则好《左氏传》,柳宗元所谓的“父子伤夷”当指此事。柳宗元主张去除章句之学对儒家真精神的遮蔽,并不专指古文经或今文经,而是针对整个经学的过分诠释现象。他说:“马融、郑玄者,二子独章句师耳。今世固不少章句师,仆幸非其人。” 从这句话,可以明显地看出柳宗元对汉代以来儒家章句之学的极度不满。
2.去除“神圣”之蔽
儒家自古以来就有神化圣人的传统。孔子赞尧曰:“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赞禹曰:“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 孟子也说:“圣而不可知之谓神。” 所以,王充说:“儒者论圣人,以为前知千岁,后知万世,有独见之明,独听之聪,事来则名,不学自知,不问自晓,故称圣则神矣。” 沿袭此传统,后人在诠释孔子的过程中也不断将其神圣化,把他说成是“前知千岁,后知万世”的圣神。《国语·鲁语》多处记载孔子洞晓灵异之事,柳宗元认为这是对孔子形象的歪曲。他说:
左氏,鲁人也。或言事孔子,宜乎闻圣人之嘉言,为《鲁语》也,盍亦征其大者,书以为世法?今乃取辩大骨、石砮以为异,其知圣人也亦外矣。言固圣人之耻也。孔子曰:“丘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注释标题 《非国语上》,《柳宗元集》第四册,第1289页。
他认为,左丘明写《鲁语》应该选择有关孔子之“嘉言”,选择那些足以为“世法”的大的方面,而不应该选择这些稀奇古怪之事,孔子之所以比一般人知道的事多,是因为他“少也贱”,而不是天生的神异功能。柳宗元还说:“‘君子于所不知,盖阙如也。’孔氏恶能穷物怪之形也?是必诬圣人矣。” 他认为,孔子根本不可能知道这些灵怪之事,把这些东西写进《鲁语》简直是对孔子的诬蔑。
3.去除“神异”之蔽
前面我们分析了“公羊学”的代表人物董仲舒诠释《春秋》的方法,指出其神异指向、人间指向、通变原则三大特点,柳宗元在吸收其人间指向、通变原则的同时,对其神异指向进行了猛烈抨击。他在《贞符序》中说:
臣所贬州流人吴武陵,为臣言:“董仲舒对三代受命之符,诚然非耶?”臣曰:“非也。何独仲舒尔。自司马相如、刘向、扬雄、班彪、彪子固,皆沿袭嗤嗤,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类淫巫瞽史,诳乱后代,不足以知圣人立极之本,显至德,扬大功,甚失厥趣。” 注释标题 《柳宗元集》第一册,第30页。
董仲舒认为《春秋》是孔子受天之符命而作,柳宗元对他这种神化儒家思想的诠释方式大加痛斥,认为是“淫巫瞽史,诳乱后代”。除董仲舒外,司马相如、刘向、扬雄、班彪、班固等人的著作也都有宣扬符瑞灾异倾向,柳宗元认为这是对董仲舒思想的嗤嗤沿袭,并认为这种带有神学目的论色彩的诠释方法是“不足以知圣人立极之本”的,要想阐发出儒家思想的真精神,就必须去除汉儒蒙于其上的神异色彩。
综上所述,柳宗元竭力主张去除历代诠释者罩在“孔子”身上的神圣、神异光环,把他还原为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即他所谓“孔子氏,是亦人而已矣” 。他继承了刘知幾,尤其是“新《春秋》学”的怀疑精神,对儒家经典进行重新考定、阐发,把诠释的方向引向现实的国计民生。他的《非国语》贯穿着大胆的怀疑精神,把批判的锋芒指向被称为“《春秋》外传”的《国语》,他也因此被后人冠以“是非多谬于圣人”“悖理害道”等罪名。
(二)二大诠释标准
我们可以从柳宗元对《春秋》一书的评价中,看出他对儒家经典的诠释原则与标准。在《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中,他称赞其父曰:“得《诗》之群,《书》之政,《易》之直方大,《春秋》之惩劝。” 他把《春秋》的作用归为“惩劝”,即劝善惩恶,所以他又说“本之《春秋》以求其断” ,即从《春秋》中掘发出判断现实是非的标准。关于《春秋》的叙事特点,柳宗元说:“余谓《春秋》之道,或始事,或终义。” 受“《春秋》之道”的影响,柳宗元采取“以事明义”的方法来诠释儒家经典与思想,并从中抽绎出两条重要的诠释标准,即“求诸中而表乎世”与“唯当所在”。
1.“求诸中而表乎世”
“求诸中而表乎世”的儒典诠释原则,是柳宗元在《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一文中提出的。
往时致用作《孟子评》,有韦词者告余曰:“吾以致用书示路子,路子曰:‘善则善矣,然昔之为书者,岂若是摭前人耶?’”韦子贤斯言也。余曰:“致用之志以明道也,非以摭《孟子》,盖求诸中而表乎世焉尔。”今余为是书,非左氏尤甚。若二子者,固世之好言者也,而犹出乎是,况不及是者滋众,则余之望乎世者愈狭矣,卒如之何?苟不悖于圣道,而有以启明者之虑,则用是罪余者,虽累百世滋不憾而恧焉! 注释标题 《柳宗元集》第三册,第823页。
文中的李景俭(字致用)、韦词与路子(即路随),都是柳宗元学术上的好友。李景俭的《孟子评》久已佚失,但通过题目可以断定,这是一部评论孟子思想的书。韦词与路随都认为该书不合孟子原意,不符合“昔之为书者”的诠释原则。柳宗元却认为,该书的目的不在于探究《孟子》原意,而在于“明道”,即通过对《孟子》思想的诠释而抉发出其中的治世之道。
“求诸中而表乎世”,有两层内涵:“求诸中”,指探求内在的“圣人之道”;“表乎世”,指把这种内在的“圣人之道”运用于外在的社会实践。这一诠释原则包含两个判断标准:一是理论上是否合乎“圣道”,二是实践上是否合乎“世用”。柳宗元特别强调“圣道”与“世用”的结合,反对只求“圣道”而不求“世用”的教条式的诠释方式,他说:“得位而以《诗》《礼》《春秋》之道施于事,及于物,思不负孔子之笔舌。能如是,然后可以为儒。儒可以说读为哉?” 他认为,儒者的使命不在于颂读《诗》《礼》《春秋》等儒家经典,而在于把这些经典的“真精神”运用到现实生活之中,使其发挥“辅时及物”之作用。
2.“唯当所在”
柳宗元主张,对儒家圣人及经典的诠释要体现“当”的原则。这一原则是在总结“公羊学”及“新《春秋》学”诠释经验的基础上而提出来的。关于“当”的具体含义,后面再做详细说明,我们先通过“公羊学”“新《春秋》学”对《春秋》中“楚人杀陈夏征舒”一事的诠释及柳宗元对这一诠释的评价,来看“当”这一诠释原则的发展脉络。“楚人杀陈夏征舒”所叙史实是这样的:陈灵公昏庸无道,淫夏征舒之母夏姬,夏征舒怒杀灵公而自立,致使陈国大乱,灵公的宠臣公孙宁、仪行父逃奔楚国。楚兵入陈,杀夏征舒,并送回公孙宁、仪行父。就此事,《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一年”评论说:
此楚子也,其称人何?贬。曷为贬?不与外讨也。不与外讨者,因其讨乎外而不与也,虽内讨,亦不与也。曷为不与?实与,而文不与。文曷为不与?诸侯之义,不得专讨也。诸侯之义不得专讨,则其曰实与之何?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为无道者,臣弑君,子弑父。力能讨之,则讨之可也。 注释标题 《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六,《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284页。
这段话从“实”与“文”两方面来评论“楚人杀陈夏征舒”一事。从实际来看,臣弑君、子弑父的不义行为是应当受到惩罚的,所以楚王是可以诛杀夏征舒的,这就是“实与”。但按照《春秋》“大一统”思想原则,非天子之命,“诸侯之义不得专讨”,所以楚王是不能诛杀夏征舒的,这就是所谓“文不与”。“文”与“实”近于“经”与“权”。《公羊传》从“文”与“实”两方面诠释《春秋》的方法,为后来的“新《春秋》学”所继承。来看“新《春秋》学”对此事的解释。陆质《春秋微旨》说:
楚子之讨征舒,正也,故书曰“人”,许其行义也。入人之国,又纳淫乱之臣,邪也,故明书其爵,以示非正。《春秋》之义,彰善瘅恶,纤芥无疑,指事原情,瑕瑜不掩,斯之谓也。
此观点认为,楚人杀夏征舒是出于正义,但入人之国,又是非正义的。柳宗元总结“新《春秋》学”的这种诠释方式说:“见圣人褒贬与夺,唯当之所在,所谓瑕瑜不掩也。” 是褒还是贬,是与还是夺,不能单凭某一凝固的标准,而要以“当”为准的,“当”本身就是一种流动的判断原则。“公羊学”与“新《春秋》学”对《春秋》的诠释都是以经权结合为原则的,柳宗元在此基础之上提出“当”这个诠释原则,他对儒家经典的解释无不体现着这一原则。 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观新论--中国诗学研究专刊 (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