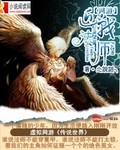第三节 柳宗元对道教方术的批判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观新论--中国诗学研究专刊 (精)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第三节/
柳宗元对道教方术的批判
先对“道人”与“道士”两个称谓作一简单辨析。这两个词本是“有道之人”或“有道之士”的简称,早在西汉时期就被用来称呼“方士”。汉魏时期,“道人”与“道士”主要用来指称佛教徒,北魏太武帝以后,也用来指称道教徒。唐代,佛教徒、道教徒都被称为“道人”或“道士”。但在《柳集》中,“道人”一般指佛教徒,如《晨诣超师院读禅经》“道人庭宇静,苔色连深竹”,称超禅师为“道人”,《霹雳琴赞引》也称其为“超道人”;“道士”一般指道教徒,如《摘樱桃赠元居士时在望仙亭南楼与朱道士同处》中的“朱道士”即是道教徒。
柳宗元对道教方术的批评主要体现在服食与服气两个方面 。事实上,服食与服气在唐代已经世俗化,不再是道士的专利,柳宗元所批评之人也多是与道士交往密切的文人士大夫,但作为方术,服食与服气仍应归属于道教。柳宗元在《送娄图南秀才游淮南将入道序》中引娄氏的话说:“少好道士言,饵药为寿,未尽其术,故往且求之。” 这句话中,娄氏把“饵药为寿”归为“道士言”。所以,我们把柳宗元对服食与服气的批评看作对道教的批评应该是没问题的。
唐代道教外丹术十分发达,各种炼丹药方大量涌现,帝王将相、王公贵族、文人雅士服饵成风,给当时的国家财政造成巨大的损失。据《旧唐书·宪宗本纪》记载,唐宪宗封道士柳泌为台州刺史,倾一州之财力为其炼丹。外丹术被很多人用来作为牟取暴利的工具,正如陈国符所说:“即在唐代外丹术兴盛之时,当时道士烧炼外丹,名为求长生,究其实质,已变为制造黄白,以规财利。”
服食与长生之间的正比例关系只能停留于理论层面,一旦验之于现实矛盾就暴露了出来。一些人长期服金丹不但没能长生,反而中毒身亡。据《廿二史札记》卷一九《唐诸帝多饵丹药》记载,唐代皇帝中,太宗、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等人的死都与服食金丹有关 。普通士人更是不胜枚举。韩愈长兄的孙女婿、太学博士李子,因服药而死,韩愈为之撰《故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列数外丹术的弊害:“余不知服食说自何世起,杀人不可计,而世慕尚之益至,此其惑也。往在文书所记,及再闻相传者不说,今直取目见亲与之游而药败者六七公,以为世诫。工部尚书归登、殿中御使李虚中、刑部尚书李逊、逊弟刑部侍郎建、襄阳节度使工部尚书孟简、东川节度御使大夫卢坦、金吾将军李道古。” 尽管韩愈曾言辞激烈地抨击外丹术,但他晚年可能也迷上了外丹。白居易《思旧》云:“退之服流黄,一病讫不痊。微之炼秋石,未老身溘然。杜子得丹诀,终日断腥膻。崔君夸药力,终冬不衣棉。或疾或暴夭,悉不过中年。” 白居易诗中列举的四个人物,第一个就是韩愈,其实,白居易本人也是一个外丹的炼食者。
柳宗元反对道教的神仙长生、灵魂不死之说:“仙者幽幽,寿焉孰慕!短长不齐,咸各有止。胡纷华漫汗,而潜谓不死!” 基于这一认识,柳宗元对外丹术持非常理性的态度。这反映在他与崔简、周君巢等人的书信之中。
崔简,字子敬,柳宗元的姐夫,贞元五年(789)进士。累官刑部员外郎,出守连州,改刺永州,流驩州。元和六年(811),柳宗元收到崔简寄来的石钟乳,发现质地不良,又听说崔简服后的症状,判断他肯定中了毒,因而写信劝他止服。崔简回信为自己辩护,柳宗元又写《与崔连州论石钟乳书》批评其对服食的迷信。在本文中,柳宗元告诫崔氏,服食那些粗劣的石钟乳会“使人偃蹇壅郁,泄火生风,干喉痒肺,幽关不聪,心烦喜怒,肝举气刚,不能和平” 。元和七年正月,崔简因服食钟乳身亡,柳宗元作《故永州刺史流配驩州崔君权厝志》谓其“饵五石,病疡且乱”,又作《祭姊夫崔使君简文》说“悍石是饵,元精以渝”,对崔简盲目服食表示惋惜。
柳宗元批评服食长寿之术,除批评其服食不精以至毙命外,更主要的还是批评其片面追求长寿的思想。他在《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一文中明确地表达了这一思想。周君巢于贞元十一年(795)中进士,比柳宗元晚两年,两人早年在京城时就相识,一起谈论“守先圣之道”之类的事情。后来周君巢热衷于道教的“饵药久寿”之术,并劝柳宗元与韩愈也参加服食的队伍。韩愈对此很感兴趣,并向他请教服食秘诀,留下“金丹别后知传得,乞取刀圭救病身”的诗句 。对于周君巢的“规劝”,柳宗元却采取了与韩愈截然不同的态度,他写《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一文,对周氏“饵药久寿”之论予以批评。
在本文中,柳宗元把寿分为“道寿”与“我寿”。“道寿”是指:“尝以君子之道,处焉则外愚而内益智,外讷而内益辩,外柔而内益刚;出焉则外内若一,而时动以取其宜当,而生人之性得以安,圣人之道得以光。获是而中,虽不至耇老,其道寿矣。” 能行圣人之道,使“生人之性得以安”者,人虽不能长寿而其道却能长寿。“我寿”是指:“视世之乱若理,视人之害若利,视道之悖若义;我寿而生,彼夭而死,固无能动其肺肝焉。昧昧而趋,屯屯而居,浩然若有余;掘草烹石,以私其筋骨而日以益愚,他人莫利,己独以愉。若是者愈千百年,滋所谓夭也,又何以为高明之图哉?” 这种无视生民的疾苦,只知“掘草烹石,以私其筋骨”之人,即使活到千百岁,也是夭折。柳宗元明确表示自己不愿意学习那些“山泽之臞者”,再三表示自己“无忘生人之患”,并劝周君巢“不为方士所惑”。
《送娄图南秀才游淮南将入道序》一文也表达了这一思想。娄图南少有大名,“通数经及群书”,且擅长诗文,但厌恶仕途,“少好道士言,饵药为寿”。柳宗元对其人生态度表示不满,认为他“智可以任职用事,文可以宣风歌德”,却放弃入仕的机会而甘愿做“处士”,这是不合时宜之举。柳宗元说:
若苟焉以图寿为道,又非吾之所谓道也。大形躯之寓于土,非吾能私之。幸而好求尧、舜、孔子之志,唯恐不得;幸而遇行尧、舜、孔子之道,唯恐不慊,若是而寿可也。求之而得,行之而慊,虽夭其谁悲?今将以呼嘘为食,咀嚼为神,无事为闲,不死为生,则深山之木石,大泽之龟蛇,皆老而久,其于道何如也? 注释标题 《柳宗元集》第二册,第656页。
柳宗元把个体生命的意义与“圣人之道”“生人之意”紧紧联系在一起,其儒家立场是十分明确的。
柳宗元对道教“服气”之术也进行了批评。“服气”又称“食气”,其理论首见于《淮南子·墬形训》所谓“食气者神明而寿” ,后来成为道教的主要养生手段之一。唐代,随着道教的兴盛,出现了大量有关“服气”的理论与书籍。如《洞玄灵宝玄门大义》:“服元气化为元气,与天地合体。服胎气返为婴儿,与道混合为一也。” 唐代道教认为,服元气即可化为元气,从而与道合一,这是一个返本还原的过程。《太上老君元道真经》还专门介绍各种各样的服气方法。
与服食一样,服气不当也会导致人死亡,这一点连道士也不讳言。唐代著名道士吴筠就曾说:“每寻诸家气术,及见服气之人,不逾十年五年,身已亡矣。” 柳宗元在《与李睦州论服气书》一文中集中阐述了对服气的看法。李睦州即李幼清,曾任睦州刺史。柳宗元、吴武陵、李幼清三人友善,经常有书信往来。李幼清热衷于道教的服气之术,“服气以来,貌加老,而心少欢愉”,吴武陵写千字长信加以劝阻,但收效甚微,柳宗元又写信,批评他迷信“服气书”所谓“恒久大利”之美言而不听友人的规劝。柳宗元的批评主要是针对李氏“守无所师之术,尊不可传之书”而言的,他说:“今兄之所以为服气者,果谁师耶?始者独见兄传得气书于卢遵所,伏读三两日,遂用之;其次得气诀于李计所,又参取而大施行焉。是书是诀,遵与计皆不能知,然则兄之所以学者无硕师矣。” 文中,柳宗元虽然没有直接否定道教的服气之术,但从“凡服气之大不可者,吴子已悉陈矣”这句话来看,他是持否定态度的。
中唐时期,道教的服食、服气之术,一方面得到一些文人士大夫们的热烈欢迎,另一方面也招致一些文人士大夫的激烈抨击。大多数抨击者是针对其对人体的伤害而言的,也有批评它在思想上不合老庄之道的。如梁肃批评“化金以为丹,炼气以存身”的道教徒说,“不思老氏损之之义,颜子不远之复,乃驰其智用,以符箓药术为务”,甚至认为他们不配称为“道流” 。与他们不同,柳宗元对道教方术的批评多不是针对方术本身,而是批评世人对它的迷信与盲从,尤其是批评道教方术信仰者只追求“我寿”而不顾“道寿”的人生态度。
柳宗元贬谪永州期间,心情郁闷,再加上足疾加重,也开始注意“服饵”养生。有人据此说他晚年崇信了道教方术,这种说法是欠妥的。柳宗元在《种术》中说:“守闲事服饵,采术东山阿。” 他所谓的“服饵”是指采服草药,而不是道教的服食金丹。他在《种仙灵毗》中也说:“我闻畸人术,一气中夜存。能令深深息,呼吸还归跟。疏放固难效,且以药饵论。” 前四句是在描述《庄子·大宗师》“真人之息以踵”的故事,此故事被后来的道教徒改造成服气修炼之术。对此修炼之术,柳宗元评价说“疏放固难效”,既然难以效仿,那么治疗疾病最好还是“以药饵论”吧,这里所谓“药饵”也是指采服草药。柳宗元在《种白蘘荷》中又说:“窜伏常战栗,怀故逾悲辛。庶氏有嘉草,攻襘事久泯。炎帝垂灵编,言此殊足珍。崎岖乃有得,托以全余身。” 可见,柳宗元的“服饵”养生与崔简、李睦州、周君巢等人对道教服食、服气之术的盲目崇信是有根本区别的。 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观新论--中国诗学研究专刊 (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