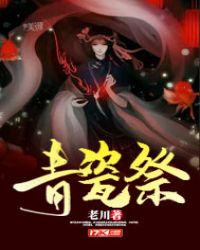第五节 柳宗元佛教观的特质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观新论--中国诗学研究专刊 (精)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第五节/
柳宗元佛教观的特质
前面四节,我们分别论述了柳宗元对禅宗、天台宗、净土宗、律宗的认知、理解与评价,下面再从整体上来考察柳宗元佛教观的特色。
一、融合性
中唐时期,佛教界的基本状况是:禅宗内部宗派林立,禅宗与教宗相互对立,教宗各派之间也互有矛盾。这时,佛教界出现了一股强劲的融合思潮,但大都是站在各自的立场之上,用自家的思想与方法去融合其他宗派,如宗密站在华严宗的立场上提出了较为系统的佛教融合论。在这一背景之下,柳宗元站在儒家立场之上,提出了自己的佛教融合观。与宗密出于“护教”目的不同,柳宗元佛教融合观的理论出发点是“佐道”。
柳宗元的佛教融合观,可按从小到大的顺序分为三个层次:统合禅宗南北,统合禅教,统合儒释。柳宗元所接触的佛教主要是禅宗、天台宗、净土宗、律宗四家,在这四家中,他对禅宗批评最多,尤其是南北宗之间的争斗。他说,五祖弘忍以下,禅分南北,南北宗弟子之间反戾斗狠,势如水火,“其道遂隐”。针对这种局面,他提出统合南北的主张。他所谓“统合”,不是用一方去融化掉另一方,而是本着“黜异蹈中”的原则,避开双方矛盾的焦点,提取出一个共同的、本质的精神,让这一精神贯穿于矛盾双方的理论与实践之中,从而达到“推一而适万,则事无非真;混万而归一,则真无非事”的理想效果 。柳宗元的这一理想是通过奉诏为惠能作碑铭来实现的。当时的情况是:禅宗内部,出现了“凡言禅皆本曹溪”的局面;政治上,上层统治者也倾向于南宗禅,在惠能去世一百零六年后又赐谥“大鉴禅师”,可能有抬出惠能以统摄禅宗的意图。柳宗元认识到,利用惠能来统合禅宗南北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所以在《大鉴碑》中,他一方面有意避开“顿悟”“法衣”这两个标志南北分离的敏感字眼,另一方面又把惠能禅的核心归为“性善”。他的用意非常明显,就是利用“性善”来统合禅宗南北,同时也为统合禅教、统合儒释埋下伏笔。
关于禅教之间的关系,柳宗元明确地说:“金仙氏之道,盖本于孝敬,而后积以众德,归于空无。其敷演教戒于中国者,离为异门,曰禅,曰法,曰律,以诱掖迷浊,世用宗奉。” “法”,在唐代与“教”意思相同。柳宗元认为,禅、法、律虽为“异门”,但都以“孝敬”为本,都具有“诱掖迷浊”之“世用”,在理论基础与现实作用上是一致的,这就具有了统合的基础。统合的方法是归于根本:“道本于一,离为异门。以性为姓,乃归其根。” “道本于一,离为异门”,可以说是对上面所引那句话的概括,“本于一”指“本于孝敬”,“离为异门”指禅、法、律。禅、法、律门类虽异,但在“性”上却是同一的。柳宗元认为:“性”,就体上说为“空无”,就用上说为“性善”;“本于孝敬”可以“归于空无”,也就是说,由“性善”之用可以通达“空无”之体。可以说,柳宗元统合禅教的最重要的依据就是“性善”,他在以“性善”统合禅教的同时,其实已经在不知不觉之中踏上了“统合儒释”的阶梯。关于他“统合儒释”的思想,我们将在第五章展开论述。
二、理性涵盖下的非理性选择
柳宗元对佛教的态度是非常理性的,这不仅表现在他对佛理的极大兴趣,对统合禅宗南北、统合禅教、统合儒释的极大热情,也表现在他把其“无神论”思想贯彻到佛教领域,表现出“以佛杀鬼”的气魄。但,在这种理性的支配之下,他又在努力唤起民众,尤其是那些“病且忧”者对佛教的信仰,鼓励民众以一种非理性的方式对待人生、对待生活。理性与非理性,这一对相互对立的范畴圆融地统一在其“佐世”的佛教理想之中。
作为一位儒学家,柳宗元竭力反对传统儒家思想中的天人感应论、及祭鬼祭神活动,主张把鬼神信仰从儒家思想中驱逐出去,以便更好地实现其经世之功用。同样,在其佛教观中,他也竭力反对鬼神的存在。
柳宗元崇佛去鬼的思想与佛教的鬼神观并不矛盾。佛教以缘起论来解释世界万物的产生,否定神创造说,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佛教可谓“无神论”的宗教。佛教一般按照生命形态与层次将世间分为六道,即天、阿修罗、人、畜生、饿鬼、地狱,其中前三道为世间的“上三道”,属世间善报,而后三道则为世间的“下三道”,属世间恶报。可见,鬼也像人一样属迷界,仍不能脱离六道轮回,地位比人低,更不具有主宰力量。佛教中,也不乏毁神去鬼的事例。据《宋高僧传》卷九《唐南岳石头山希迁传》记载,乡民多畏鬼神,常杀牛酾酒而祭祀之,希迁往毁神祠,夺牛而归,“岁盈数十” 。作为佛门高僧,石头希迁对佛教有着真诚信仰,却反对鬼神崇拜。这种崇佛去鬼的思想也同样体现在柳宗元身上。柳宗元崇佛去鬼的原因在于,佛教具有引人入善的“佐世”功能,而鬼神信仰却只能惑乱民心、扰乱社会。
柳宗元住在永州龙兴寺的时候,寺东北角一间堂房内的地面隆了起来,有四步宽,一尺五寸高。据说,刚建堂的时候,这块土地铲平了又长起来,那些参加铲地的人都不幸而死了。永州人本来就信鬼神,于是住在寺内之人都以为有神,谁也不敢再铲了。柳宗元翻阅《史记·天官书》《汉志》等典籍,皆不见有关息壤的记载,只有过去的一些“异书”记载“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之类的事情,他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可靠的。他认为,土地是不可能有神灵的,那些铲土者肯定是“死于劳且疫”,于是写了《永州龙兴寺息壤记》,并抄写在堂上,以破除人们的迷信异说。这可以说是他“无神论”思想最典型的表现。
再来看柳宗元在龙兴寺做的另外一件事。净土堂年久失修,房屋门窗已坏,墙上的佛像也脱落了,柳宗元与本寺住持重巽、刺史冯公等人一起重修净土堂,还把托名智顗的《净土十疑论》抄在墙壁之上,以期“观者起信”,并作《永州龙兴寺修净土院记》以记之。
以上这两种事都发生在龙兴寺内,都与堂舍的修葺有关。前者关乎鬼神,柳宗元抄《永州龙兴寺息壤记》于墙上,使观者信其无;后者关乎佛,柳宗元抄《净土十疑论》于墙上,使观者信其有。两相对比,其对“佛”与对“鬼神”的态度泾渭分明。
《柳州复大云寺记》更明确地表达柳宗元崇佛去鬼的思想。吴越之人鬼神信仰浓厚,每当得了重病,就请巫师来占卜、祈祥。先杀小牲畜,如果不见好转,就杀中牲畜;还不见好转,再杀大牲畜;如果还不见好转,就与亲人告别,说“是神不想让我活了”,于是废食蒙面等死。柳州人口越来越少,田地也大面积荒芜。社会治安混乱,“董之礼则顽,束之刑则逃”,礼与法均不奏效。于是,国家在柳州设了四座寺院,引导当地人信仰佛教,情况出现了好转。后来,大云寺被大火烧坏,一百多年没有修复,周围三百多户人家“失其所依归”,“复立神而杀焉”。柳宗元到柳州以后,“逐神于隐远而取其地”,修建佛庙,安居僧人,“会其徒而委之食,使击磬鼓钟,以严其道而传其言”。那些“病且忧”者来祈求安康,就告诉他多念佛、多做善事等道理,于是人们又“去鬼息杀,而务趣于仁爱”。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柳宗元提倡佛教信仰的两大原因:一,佛教能给人们提供精神的“依归”之所,尤其是给那些“病且忧”者带来希望。元和五年(810),柳宗元十岁的女儿和娘患了重病,无望之下,寄希望于佛,更名“佛婢”,又去发为尼,法号曰“初心”。虽然对佛的信仰并没有挽回她幼小的生命,但至少减轻了她对死亡的恐惧,使她相信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这大概就是柳宗元同意她去发为尼的原因。二,引导人“趣于仁爱”。柳宗元在《岳州圣安寺无姓和尚碑》中也说:“生物流动,趋向混乱,惟极乐正路为得其归。”这句话指出佛陀净土信仰在混乱之世的导善作用。以上两大作用,前者指向人的终极关怀,后者指向人的现世关怀,这两者结合起来便起到“以佐教化”的作用。所以说,尽管对佛教的信仰是非理性的,但柳宗元对非理性信仰的提倡却是理性的,理性与非理性圆融地统一于“佐教化”的目的之中。在儒学衰弱、于治世治心两方面都捉襟见肘的中唐社会,柳宗元的这一选择无疑是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三、“体用不二”的思维方式
柳宗元的佛教观始终贯穿着体用不二的思维方式。在佛教中,“体”一般指诸法无差别的体性,“用”则指诸法千差万别的现象。《景德传灯录》曰:“净者,本体也;名者,迹用也。从本体起迹用,从迹用归本体,体用不二,本迹非殊。所以古人道:‘本迹虽殊,不思议一也。’” 柳宗元在阐释其佛教观时,也是在这层意义上使用“体用”这对范畴的,他有时还用“性事”“本迹”等来表达。综观柳宗元对净土宗、律宗、天台宗、禅宗四家思想的论述,他始终把握着体用不二这条主线,既强调“体”上之“性空”,又强调“用”上之“妙有”,前者通向自由,后者通向秩序。
首先,柳宗元以体用不二的思维方式来批评某些禅宗学人“言体不及用”之病。一些禅宗学人“妄取空语,脱略方便”,一味强调“体”上之“空”,而忽略“用”上之“有”,结果一方面弱化了禅修实践的必要性,另一方面消解了生活实践的伦理性。柳宗元认为,这种“言体而不及用”的修行方式是“世之所大患”。他把佛教的基本精神概括为“本于孝敬,而后积以众德,归于空无”。“空无”是就体而言的,“孝敬”“众德”则是就用而言的,由体起用,由用归体,体用不二,这才是正确的修行方式。
其次,以体用不二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天台宗的“中道实相”理论。他所谓的“趣中即空假,名相与谁期”“涉有本非取,照空不待析”“体空得化元,观有遗细想”“无体空折色之迹,而造乎真源”等等,都紧紧抓住空有互融、体用不二这一核心思想。空、假、中三谛都是宇宙诸法的实相,三者相即而不可须臾分离,既肯定本体之“空”,又不废作用之“有”。他特别欣赏天台高僧为而未尝为、未为而亦为的人生态度。立足于此,他也充分肯定天台宗止观与戒律并重的修行方式。
第三,以体用不二的思维方式来论证净土宗西天信仰的必要性。净土宗提倡西天极乐信仰,这与大乘佛教诸法缘起性空的理论相矛盾,净土宗也因此招致来自本教之外其他宗派的批评。柳宗元对净土宗的这一思想是肯定的,他认为西天信仰能在“生物流动,趋向混乱”的世界里,给人指明“正路”。他是从体用不二的思维方式出发来论证的。就体上来说,诸法性空,西天极乐世界是不存在的;但从用上来说,西天极乐信仰又是把人度入“无生”的舟筏,因而它又是存在的。所以,他说:“境与智合,事与理并。故虽往生之因,亦相用不舍。……有能求无生之生者,知舟筏之存乎是。” “智”“理”是体,“境”“事”是用,体用相即,求无生而不舍生,虽往生而不舍相。所以,在《东海若》中,有人以“毗卢遮那、五浊、三有、无明、十二类,皆空也”来否定西天净土的存在时,柳宗元说:“子之所言,性也,有事焉。夫性与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子守而一定,大患者至矣。”
最后,以体用不二的思维方式来论证戒律的重要性。针对当时佛教界以修大乘为名而轻视戒律的局面,他提出“律为大乘”命题。这个命题是建立在体用不二的基础之上的。戒律作为维持佛教教团之道德性、法律性的规范是就用上而言的,其自身之体性也是空,所以柳宗元说“不取于法,故律为大乘” 。尽管戒律自性为空,但不能因此而“小律”“去律”,不然就会像某些南宗禅学人那样犯“言体不及用”之病。柳宗元在《岳州圣安寺无姓和尚碑》中说:“性海,吾乡也;法界,吾宇也。戒为之墉,慧为之户,以守则固,以居则安。” 虽然“性海”为空,但离开戒律则无以得入,甚至说“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柳宗元以体用不二来论证戒律的重要性,目的是把佛教的修行引向秩序性。
综上所述,柳宗元立足于体用不二的思维方式,特别强调“用”之重要意义,基于此,他论证了西天净土信仰的合理性和戒律的重要性,也强烈批评了一些禅宗学人“言体不及用”之弊病,从而把佛教的发展引向秩序化。另一方面,他也没有因为对“用”之重要性的强调而否定“性空”,正是由于对“性空”的了悟,才使那些高僧大德“不爱官,不争能”“闲其性,安其情”。柳宗元以体用不二、空有互融的思维方式,一面把佛教引向自由,一面又把它引向秩序,自由与秩序圆融统一,这是柳宗元佛教观的核心特点。 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观新论--中国诗学研究专刊 (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