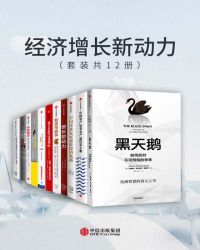第七章 世界经济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经济增长新动力(套装共12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第七章 世界经济
一、条件趋同
在第六章中,我们讨论了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间的差异。为更好地了解资本主义的未来发展,我们有必要把世界当作一个整体来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不同国家的福利水平有很大的不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明显不平等。另外,全球层面是否存在增长的巨大潜力。对于发展中国家,通过模仿富裕国家,根据自身条件调整技术,实现经济高速发展。如果这样的赶超进程出现,随着全球层面的合作,经济力量转移平衡,世界舞台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将在第八章详细说明这些问题。如果发展中国家的赶超进程结果不尽如人意,那我们需要探讨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令人失望的赶超进程是难以理解的,正如斯蒂夫·道瑞克和J.布拉德福德·德隆提到的,“经济学家预测20世纪经济增长模式为趋同状态,但最终结果却呈明显发散状态。这完全出乎他们的预料”。(Steve Dowrick and J. Bradford DeLong,2003,p.194)
实际上,正如第四章提到的,描写后进国家的大多数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依赖于赶超进程。因为和发达国家的当地情况或制度不同,后进国家模型的趋同通常是不完整的。如果赶超不仅仅开拓知识的外部效应,也和社会能力呈相关关系,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较低的国家的模型可能形成发散状态。尽管如此,道瑞克和德隆的观点也有他们的道理。我们对世界资本主义扩张的了解程度有限,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分析这个问题。因此,本章将主要从实证的角度研究后进国家的潜在趋同。
我们可以利用不同的方法对此进行研究。首先,调查历史叙事背景,了解个别国家模仿技术领先国家成功的案例。其次,利用统计的方法解决问题,收集对国家趋同化的一般见解。简要概述描述性方法后,我们将深入讨论统计法。
在第六章“进取和追赶”一节,我们总结得出,西欧国家起初连追都追不上技术领先国家——英国,更不用说赶超了。1820—1870年,工业革命在欧洲大陆发展举步维艰。1870—1950年被认为是大动乱时期,是技术领导地位从英国向美国过渡的时期。1950年后,西欧国家才在很多方面追赶上美国。但是,趋同又一次只有有限规模。道瑞克和德隆从更加广阔的视角对这些发展进行讨论。他们认为,俱乐部趋同(经济一体化)的概念源自威廉·鲍莫尔和爱德华·沃尔夫(William Baumol and Edward Wolff,1988),是他们分析的核心。俱乐部趋同指的是不同国家一起“促进技术转让、增长国际贸易、加大投资、普及教育,推动生产力水平和工业结构向(或至少朝着)产业核心发展”。(Dowrick and DeLong,2003,p.195)
道瑞克和德隆将世界范围的此类俱乐部趋同划分为1820年至1870年、1870年至1913年、1913年至1950年和1950年至2000年几个亚时期,他们说明了哪一些国家应该加入经济一体化进程,哪一些国家应该脱离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就这方面而言,1950年至2000年这一时期经济一体化成员是非常能说明问题的。在拉丁美洲,像委内瑞拉、秘鲁、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这些国家不再是经济一体化的成员。非洲很多国家在这个时期也被排除在经济一体化之外。然而,“东亚奇迹”使亚洲国家和地区进入经济一体化进程,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1965年后)和中国内地(1978年后)。在拉丁美洲,哥伦比亚和墨西哥也加入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20世纪80年代后,印度经济快速发展。他们用叙述方法讲述大量的细节,几乎没有提出任何一般性见解。然而,由此导致的问题并不是那么容易回答,他们不得不承认,“全球化的第二纪元(1950—2000年),经济一体化规模对全球化的影响没有那么明显,相较拉丁美洲,为什么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相对缓和友善?为什么地中海东部要比地中海西南部的一体化发展更好?”(Dowrick and DeLong,2003,p.203)因此,能否通过统计法获得对这个问题的一般见解有待证明。
第四章已经提到过,赶超意味着衡量劳动生产率的人均GDP的增长明显高于初期状态的人均GDP水平。对比其他国家,尤其是具有最发达经济体系的国家,人均GDP水平低的国家可以从其他国家的科技领域学到很多。模仿现有技术可以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在必要情况下,需要根据本地情况调整技术。通过对不同国家进行抽样调查,统计测试这个假设,结果显示是负面的。人均GDP的增长速度和它的初始水平之间没有统计上显著的反向相关。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2011b)绘制的图7.1正好说明这个结论。事实上,应该把每小时生产量,而不是人均GDP作为衡量劳动生产率的基准,但这个变量在佩恩表中不存在。虽然罗德里克并没有说明有多少个国家被抽样调查,数据集国家的数量是庞大的。我们可以通过划分亚时期增加观察组的数量。罗德里克从1970年至2008年这个时期开始,接着将这个时期明确划分为4个亚时期。图7.1的每一个观察组对应一个国家10年的发展。图7.1观察组的散点图显示,这些变量之间缺乏相关性。因此,世界经济不存在趋同性。如果根据人口规模对抽样国家进行权重,散点图发生变化。夏威尔·萨拉伊马丁的研究表明经济增长和初始收入水平呈负相关,因为“在亚洲,只有少数国家能趋同至OECD收入水平,而大多数国家还是偏离这个水平(尤其是非洲国家)”。(Xavier Sala-i-Martin,2006,p.354)如果我们希望研究世界收入分配的变化,这种方法是适用的。如果只是希望分析赶超增长,通过人口规模衡量不同国家是不合理的,正如萨拉伊马丁所说,赶超速度取决于国家要素。
图7.1 无条件增长回归(1970年至2008年十年际回归测试)
资料来源:Rodrik,2011b。
虽然不能总结无条件趋同结论,但条件趋同仍然是一种方案。这就意味着可能形成趋同,但需要考虑很多其他的因素,例如,扰乱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和初始值的直接联系。考虑其他大量的条件因素,影响趋同过程并不难,很多学者为此进行研究,利用回归分析测试条件趋同,结果存在本质的差别,存在相当大的疑惑。巴里·博斯沃思和苏珊·柯林斯(Barry Bosworth and Susan Collins,2003)对试验进行更新,检测以84个国家为样本的可能性,它们共占据世界生产总值的95%,以及世界人口的84%。他们坚持标准化,去掉影响实证研究结果的重要原因,也就是说,设置国家标准组、标准时期和标准条件变量获得回归结果。条件变量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在很多其他研究中都非常重要。因变量是1960年至2000年的人均产出增长率。和罗德里克的研究不同,他们并没有对主回归划分亚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和1960年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率相关,而不是劳动生产率的初始水平。在扩展回归分析时,需要区分条件变量、政策指标和其他潜在解释变量(见表7.1)。
表7.1 解释变量
注:此贸易政策措施,杰弗里·萨克斯和安德鲁·华纳(Jeffrey Sachs and Andrew Warner,1995)研究分析计算条件,被广泛用于实证研究。
表7.1显示的是最重要的变量,是博斯沃思和柯林斯根据变量类型的不同对其分组。条件变量表示的是初始状态的经济定位,平均寿命是国民健康指标。条件变量的人口统计是国家规模的维度。贸易工具是构造变量,可视为国家贸易倾向指标。地理划分以霜冻日数量以及热带土地面积百分比的加权值为基础。制度质量是以国际国别风险指南信息为基础的重要变量,测量和仔细权衡贪污、法律法规、侵占风险、政府机关对合同或债务的拒绝承认和官僚质量。
统计法的所有条件变量有很大的不同,尽管结论涉及预算平衡,这个区别结果并不适用于表7.1第二列的政策指标。博斯沃思和柯林斯对其他变量的重要作用进行研究。明显变量,如投资比率、教育水平和金融发展几乎没有任何影响。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的替代指标从统计分析的视角来看并不尽如人意。然而,大量的研究讨论了世界市场融入度对经济增长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总而言之,这些结果差别并不大,正如博斯沃思和柯林斯总结的,“这些回归分析的突出方面和传统政府政策没有直接相关。相反,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在短期内不会发生变更”。(Bosworth and Collins,2003,p.32)
有些人可能会问经济增长的多国抽样分析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见第三章)之间的关系。正如前面提到的,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产量增长率取决于工人数量的增长率,对应人口增长、资本存量增长和技术进步。这种关系可以轻易转换为解释人均产出增长和人均资本增长及技术进步的比率的关系。后一个变量可被定义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应用增长核算的简单技术,建立人均资本变化、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和人均产量增长速度的贡献率研究。将这个数值和国民收入的资本份额相乘可以得到人均资本增长速度贡献率。接着,通过人均产出增长速度减去人均资本增长速度贡献率得出全要素生产率变化。也就是说,技术变化以剩余值计算。作为整个计算过程的结果,剩余值不仅仅是严格意义上的技术变化指标,也是资本利用的效益改善和转变。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关联没必要对技术变化偏好(劳动力或资本节省)做出任何假设。
博斯沃思和柯林斯以原创的方式将两种实证研究方法结合。他们是利用与产量增长回归同样的解释变量获得人均资本积累贡献率和技术变化。这样的结果显示“变量影响增长的渠道”。(Bosworth and Collins,2003,p.159)从表7.2中,我们可以得出因变量回归系数的结果。同样,因为这些回归系数取决于相关变量的计量维度,其数值并没有多大研究价值。然而,如果将表7.2每一行的回归系数结合,我们可以得出条件因素和政策变量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值得注意的是,第二列和第三列的回归系数之和等于第一列回归系数的值。
从初始收入的回归系数明显地看出,“趋同过程可以通过资本积累和资源利用率得到证实”。(Bosworth and Collins,2003,p.159)这对于地理区分和人口规模也一样。平均寿命,尤其是制度质量通过全要素生产率改善影响经济增长,而政策变量预算平衡主要通过资本积累影响经济增长。然而并不是所有事情都如预期一般,“令人意外的是,贸易工具和贸易开放度的相关性更多是通过资本积累而不是全要素生产率。大部分的理论文献强调贸易的效率增益”。(Bosworth and Collins,2003,p.159)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政策变量开放度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7.2 1960年至2000年因变量回归系数的结果
注:括号的数值是t统计数据。
资料来源:通过博斯沃思和柯林斯的研究检索。
博斯沃思和柯林斯更新的统计结果意味着趋同最终取决于单独国家的初始值。然而,条件变量披露的信息有限,这些变量对于结论来说甚至是不必要的。罗德里克表明,在他的抽样国家样本中,条件趋同可以通过所谓的国家效应证明。这种情况下,对于每一个独立国家引入虚拟变量,标记该国家的特定位置。有些读者可能注意到,这种方法仅适用于明确划分亚时期的取样周期。这种类型分析方法被认为合并截面时间序列分析。图7.2是某一特定国家结果,和图7.1有明显的不同。根据博斯沃思和柯林斯的研究,国家的截面分析引入固定国家效应并不具有研究意义。然而,固定国家效应如同黑箱,难以理解。只能说博斯沃思和柯林斯的方法从某种程度上打开这个黑箱,并没有完全了解它里面的内容,正确的研究方法是将截面和时间序列数据结合,接着就证明国家回归系数的重要性。
图7.2 条件增长回归(1970年至2008年十年际回归测试)
资料来源:Rodrik,2011b。
通过进一步分析统计证据后,可以认为趋同取决于短期内并不容易改变的国家要素。因此,如果要取得任何进展,历史叙事只是一种建设性方案。有趣的是,这并不是唯一的方式。罗德里克的研究显示,无条件趋同并不适用于1990—2007年制造业处于四位数水平的劳动力生产率。此外,这个时期是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发展中国家的黄金时期,自1950年后,它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超过发达国家。下一部分将讨论罗德里克的研究结果。
二、结构主义
1990年至2007年,因为经济日益全球化,这段时期是发展中国家的显著增长时期。基于这样的背景,玛格丽特·麦克米伦和丹尼·罗德里克指出,“几乎无一例外,发展中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后日益融入世界经济,工业品关税低于以前,外国直接投资达到新高”。(Margaret McMillan and Dani Rodrik,2011,p.2)因此,正如罗德里克阐述的,制造业趋同明显。如果考虑固定国家效应,结果将更加简洁明了。此外,一些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了,他们并没有调查1990年至2007年的总量经济无条件趋同发生的原因。然而,可以想象,制造业的国际竞争比其他行业更激烈。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被认为是二元经济——在不同的产业劳动生产率有明显的差异,如第四章(图4.10)所示,在一些更加先进的经济体,这些差异更加尖锐。因此,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实现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样式,整体经济生产率将更高。当然,这也意味着农业领域和受保护部门的就业率更低。在这个假设案例中,麦克米伦和罗德里克计算得出印度的平均生产率增长可能翻倍,而中国的甚至可能达到三倍,这种影响对一些非洲国家甚至更大。然而,这样的一个理论构想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存在误导。只要促进生产要素有效配置,学者应该对比边际生产力而不是平均生产力。而且,这样的要素重置影响相关行业的边际生产力。尽管如此,在发展中国家,生产要素可能不是根据新古典主义理论进行分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不同国家的制度要素不同。在第四章的“结构转型”部分韦尔分析了落后国家缺乏流动性的可能原因。
全球化浪潮迫使发展中国家调整行业结构。赶超导致不同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持续增长。另外,因为节省劳动力,这些部门的就业率有所下降,问题在于是不是所有下岗工人都应该重新被制造业聘用从事相关工作。一些人提出,我们可以通过淘汰效率低的公司从而节省劳动力。部门寡头垄断的理论表明,利益最大化垄断联盟的收益定价非常高,以确保低效率公司(边缘公司)能继续在市场占据一席之地。如果垄断联盟也参与市场竞争,垄断将不复存在。此外,我们需要研究发展中国家效率最高的企业能否应对全球竞争。一方面,这些国家的薪资水平相对较低;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生产率也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提高可以节省成本,提高这些国家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然而,这种机制并不意味着相关企业能扩大其在世界市场的版图。
根据麦克米伦和罗德里克的研究,经济总量中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以通过两个因素解释。第一个因素包括不同领域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加权综合,加权值是就业总人数相关部门的就业份额。据他们解释,第一个因素属于生产率增长的组成部分,第二个因素是结构变化术语,它等于就业总人数份额变化综合乘以初始情况相关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我们可以假设第一个因素是正数。因此第二个因素是负数。尤其如果这些行业的就业率下降是劳动生产率(人均产量)提高。“如果流失的劳动力最终导致较低生产率,全球范围经济增长将更加举步维艰,甚至产生负面影响。”(McMillan and Rodrik,2011,p.13)当然,如果流失的劳动力导致失业严重,上述论断的依据将更加充分。
上述分解适用于1990年至2005年38个国家、9个行业部门的抽样调查,如图7.3所示。亚洲和拉丁美洲、非洲之间存在明显差异。拉丁美洲、非洲出现负增长结构变化,而亚洲结构变化归因于全球经济生产率增长。负增长结构变化意味着劳动力从制造业、交易服务等高产部门重新走向低产部门,主要包括一些非正式部门,甚至是农业部门。如果不同洲的国家经济增长差异的绝大部分可以通过结构变化术语解释,结构变化术语的重要性将更加明显。罗德里克提供了更多细节,“亚洲在1990年至2005年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每年超过非洲3个百分点、拉丁美洲2.5个百分点,在这样的结构变化术语差异中,非洲占1.8个百分点(61%),而拉丁美洲是1.5个百分点(58%)”。(Rodrik,2011,p.29)当然,我们要记住抽样调查的国家样本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比如说,非洲9个国家一起占据撒哈拉以南地区人口的一半。此外,抽样国家包括9个拉丁美洲国家和10个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和印度。当然,这样的抽样国家比例并不能影响罗德里克对这一重要现象的进一步调查。
图7.3 “内部”和“结构变化”之间的增长分解(1990—2005年)
乍一看,部分读者可能以为制造业生产率的趋同是因为“在这期间,抽样调查的所有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受到全球化进程影响”。(McMillan and Rodrik,2011,p.22)然而,这一点和不同洲的国家的结构发展趋势并不一致。当然,越来越激烈的全球化进程是一种全球现象,这样的一个事实意味着不同国家因为当地情况和地方政治的不同,其全球化进程也会不同。进口竞争使得本地制造业竞争更加激烈。如果国内企业把产品价格定得高于世界市场价格,不仅忽略较低的薪资水平,国内市场的开放度也会有很大的问题。为了提高竞争力,国内企业需要规范化,降低成本,并通过提高生产力在市场占据一席之地。如果真的是这样,世界市场的防御阵地和扩充就不是任务的重中之重了。
根据麦克米伦和罗德里克的研究,在全球混乱竞争市场的情况下我们需要理智地控制下降趋势。在拉丁美洲和非洲,政策制定者选择日益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此外,这些国家在货币估值过高的背景下实现自由化主要是希望反通货膨胀。麦克米伦和罗德里克提出,“估值过高的通货紧缩措施确保可贸易行业进一步发展,淘汰低利润率的制造业”。(McMillan and Rodrik,2011,p.23)
另外,麦克米伦和罗德里克指出,不同大陆的国家发展差异是因为专业化模式差异。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自然资源和初级产品丰富,尽管相关领域部门生产力水平高,它们对总量经济的贡献是有限的。相反,其促进负增长结构变化。罗德里克提出“这是另一种自然资源的诅咒”。(Rodrik,2011b,p.32)然而,如果不对其进行进一步说明,这样的解释远远不够。如“荷兰病”所示,某个国家所具有的原材料或矿物资源禀赋可能会提高实际汇率,影响其他制造业部门。但自然资源是否对经济增长产生不良后果还有待观察。
加文·莱特和杰西·杰拉斯塔(Gavin Wright and Jesse Czelusta,2004)通过研究过去和近期矿物相关经济的发展,反思资源诅咒。调查结果显示,资源禀赋并不意味着该国的发展依赖于意外利润,宏观经济增长低。有些时候也可能导致资源价格陡升,如20世纪70年代一样。然而,正如莱特和杰拉斯塔指出的,这段时期相当特殊,“因为研发、挖掘、提炼和利用技术发展,矿业生产不断扩大,20世纪70年代的市场表现和20世纪90年代的市场表现形成了鲜明对比。换句话说,这是个学习的过程”。(Wright and Czelusta,2004,p.36)
饭冢美智子和卢克·泽特(Michiko Iizuka and Luc Soete,2011)从更广阔的视角讨论了资源禀赋国家实现经济高增长的可能性。他们以作为经济增长发动机的自然资源为基础分析赶超进程,尤其是对拉丁美洲国家的分析。他们认为,因为自然资源开采的经济活动最近发生变化,一些学者先前的很多假设将不复成立。饭冢美智子和卢克·泽特具体提出以下几点。
(1)自然资源生产不再是“飞地”,和前向关联、后向关联的其他活动相关。
(2)利用生物科技、纳米技术和环境科技的新知识提高知识密集型生产活动的潜力。
(3)可能将自然资源生产为基础的新知识应用到其他行业,形成所谓的“倾向迁移”。
(4)因为自然资源生产的特殊本质要求结合环境条件,包括气候、地理、土壤等。
(5)因为全球市场划分实际就是产品特性(质量、独特性、专业性)的划分,而不是产品类型(制造业、农业)的划分,这意味着,适合市场策略的自然资源导向型的产品更具吸引力。
他们的探讨得到实证研究的支持。实证研究表明,2000—2009年,拉丁美洲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产品出口比例高于以制造业为基础产品的出口。世界经济中的自然资源繁荣为赶超进程创造条件。利用这样一个机会,拉丁美洲国家开始投资知识导向型领域,如人力资本、院校学府和研发部门。尽管总体结果比较满意,但“这些政策措施能否促进拉丁美洲国家朝知识导向型经济转型还有待研究,毕竟所有的这些措施都是初步措施”。(Iizuka and Soete,2011,p.14)相反,莱特和杰拉斯塔就同样的问题提出比较乐观的看法,“实际上,就抽样调查的所有国家而言,与地质勘探相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公益事业证明,国家支持或补贴的勘探活动通常会对省域经济或国家经济带来较大的收益回报”。(Wright and Czelusta,2004,p.35)
回到麦克米伦和罗德里克的分析研究,我们可以总结得出,他们对结构变化的差异的解释归根结底是新兴工业主题的详细说明。发展中国家经济一体化要求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这样的论断是可行的,至少适用于现阶段。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受保护行业必须能面对世界市场的竞争。阿西莫格鲁等学者认为,为确保始终走在技术前沿,有必要对这些政策进行调整。正如第四章中“赶超和制度”部分提到的,发展中国家必须及时将以投资为基础的经济战略调整为以创新为基础的经济战略。
罗德里克的著作反复提到新兴工业主题。他将转向研究过去发达国家和地区,以及所谓“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腾飞的原因。问题的关键在于,为创建工业桥头堡,必须克服市场缺陷。罗德里克再次列举这些不完整性。(Rodrik,2011b,p.37)
(1)学习外部效应:其他企业或工业的外部效应。
(2)协调外部效应:协调突发的投资需求。
(3)信贷市场缺陷:项目融资问题。
(4)工资溢价:监管和其他成本,提升薪资水平。
罗德里克认为,现代工业的市场失灵相对敏感。因此,“经济增长要求采取补救措施解决‘特殊’行业的问题,而不是一般政策”。(Rodrik,2011b,p.38)
以中国为例,罗德里克似乎是对的。依赖产业政策调控的国家的经济始终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然而,从较小的范围来讲,印度和巴西的崛起更多的是因为制定市场自由化和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政策。就这些国家的发展而言,罗德里克提出自己的批判立场,“三心二意、混乱自由化的印度并不能作为多边机构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参考的范本”。(Rodrik,2011,p.18)然而,麦克米伦和罗德里克认为“混乱自由化”的定义尚不明确,甚至不清楚这些政策是通过怎样的方式促进结构变化的。关于这方面更进一步的认识可以研究发展中国家竞争和创新的案例。
三、增长放缓
赶超的自限性会导致增长速度减慢。限制越多,能从技术领导者学习的就越少。第四章中“复制技术”部分提到,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大部分的实证文献并不会考虑落后经济体的增长率逐渐下降的原因,博斯沃思和柯林斯在本章“条件趋同”部分的分析也提到这一点,在他们的更新研究中把人均产量增长速度和人均收入关联,并增加其他变量建立这种条件关系。博斯沃思和柯林斯的研究的起始点是抽样国家的横截面资料。因此,研究只分析了1960年至2000年每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而罗德里克把这段时期分成几个亚时期进行研究,在他的分析中,因为赶超进程取得进一步进展,后期经济增长速度略微下降。但因为特定国家条件改善,总体而言,经济增长率呈上升趋势。20世纪90年代后,因为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其他新兴国家也是如此。
在最近的研究中,一些经济学家,包括巴里·艾肯格林、朴东炫和申宽浩(Barry Eichengreen,Donghyun Park and Kwanho Shin,2012)指出,走在技术前沿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他们总结这些国家发展的限制如下,“后发经济体的高速增长势头持续时间并不长,最终导致就业不充分的农村劳动力被耗尽。在制造业就业的劳动力达到最高,经济增长严重依赖于更困难的服务部门生产率提高”。(Eichengreen、Park and Shin,2012,p.43)
他们认为,如果某个时期(t)满足以下条件,这段时期可被定义为“增长放缓”时期。
(1)超过连续7年时间,实际GDP增长率平均高于3.5%。
(2)接下来7年时间,实际GDP增长率平均下降两个百分点。
(3)200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不变价格计算)超过10 000美元。
最后一个条件不适用于尚未完成赶超进程的国家,见第四章中“复制技术”部分查特吉,范·斯海克和德·格鲁特提供的数据统计。艾肯格林等人以抽样国家调查和1957年至2007年的数据为基础估计经济放缓的可能性。应用的方法是概率单位回归,因变量是二元的,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判定经济增长是否放缓。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取决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00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最高,为15 389美元。除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外,回归分析也计算了该变量的平方值。因此,概率分布可能为反抛物线,如图7.4所示。横轴是抽样调查中人均收入增长速度放缓的国家。在反抛物线最顶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等于15 389美元,2005年的平均观察值(图7.4的条形图)是16 740美元。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某个特定值并不适用于作为解释变量,另外,根据一个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技术领先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据艾肯格林等学者估计:“如果某国人均收入占领先国家的58%,就有可能出现经济速度增长放缓。”(Eichengreen et al.,2012,p.66)这样的结果似乎意味着要赶超技术领先国家很难,但也不是不可能。在第六章我们提到,如果以劳动生产率作为相关标准,大部分西欧国家的确曾成功赶超其他国家。艾肯格林等学者的研究使用单位人力生产量作为技术知识量度,这不是最适合的指标。欧洲经济体在20世纪70年代后半叶经济增长的确放缓了。然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放缓最主要的原因是劳动力参与率降低。因为缺乏相关数据,劳动力参与率这个指标对其他国家是否适用有待研究。
图7.4 经济放缓的频数分布(不包括原油出口国)
资料来源:Eichengreen et al.,2012。
艾肯格林等学者调查了其他变量对经济放缓可能分布的影响。对于调查数量有限的国家,所收集的数据主要关于就业总量中制造业比重,调查显示,就业总量中制造业就业比重峰值达23%。此外,研究显示,对货物贸易越开放的国家,其经历经济放缓的可能性越小。除作为构造指标的低估实际汇率外,政策变量对经济放缓没有多大影响。从统计学角度来看,艾肯格林等学者总结得出,严重估值偏低的国家更容易受到增长放缓的影响。不同的学者对此提出不同的解释,但因为缺乏理论框架支持,这些解释还有待研究。
艾肯格林等人的分析多多少少受到印度、巴西,最重要的是中国惊人的急剧增长启发。这些文章的标题不包括“对中国的影响”的解释,新兴经济体的发展的地缘政治后果非常重要。我们将在第八章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基于这样的背景,艾肯格林和他的共著者强调中国经济可能放缓是可以理解的。《经济学人》编辑部在深入探讨艾肯格林等人的研究贡献时或许慎重考虑这点,问题在于中国有没有可能突然增长放缓。
根据现阶段所掌握的数据,中国经济突然增长放缓似乎不大可能。2007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美国的19.8%,如果百分比达到58%,放缓概率将达到最大值。假设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以每年9.3%的速度增长,而美国以每年1.9%的速度增长,中国经济突然增长放缓也不是不可能。2015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只是美国的14%。据估计,只有到2023年,中国和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率才有可能达到58%。以这些结果为基础,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经济放缓也是不久的将来的事情。2002年之后,没有制造业就业占就业总数比重相关的数据,艾肯格林等人假设这种比率将逐年上升一个百分点。“如果假设没错,制造业就业占就业总数比重接近23%的时候,经济增长就有可能放缓。”(Eichengreen et al.,2012,p.80)回归方程结果显示,自变量(人均收入、增长预放缓率、贸易开放度和支出结构)统计结果显著,艾肯格林等人预计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可能性加大到73%。
而霍尔兹(Holz,2008)的研究发现恰恰相反,他将中国内地的经济结构和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经济结构对比,这些国家和地区到目前为止的赶超进程都超过了中国内地,中国内地现阶段的发展如同这些国家和地区30年前的发展。1978—2005年,中国农业就业占就业总数的比重从70%下降至45%,每年降低一个百分点。以这样的速度,“中国农业劳动力份额实现占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农业劳动力份额的10%还需要35年的时间。”(Holz,2008,p.1669)其他指标的统计结果也得到同样的结论,他最终总结,“中国还有30年的持续增长时间”。(Holz,2008,p.1683)艾肯格林等学者和霍尔兹研究结论的差别集中于中国经济未来的不确定性。因为收入分配不公引发的一些风险,如金融不稳定性或社会不稳定性也是他们的观点有分歧的地方,所有的这些不确定性代表任何风险可能,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针对这些不同的风险也提出相应的措施。表7.3是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数据。
表7.3 2000年至202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年度百分比)
资料来源:Conference Board,2011。
首先,左边一列是2000年至2010年这些国家的实际增长率,中间一列是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根据基础情景提出的预估数据,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预测表明对比过去,除中国外,所列举国家的经济增长都在加快。尽管增长相对放缓,中国产量占全球产量的比例从2010年的16%上升至2020年的24%。印度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明显落后。除此之外,世界经济的增长有赖于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和印度。说明这些数据时,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指出,“因为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资产泡沫或未能适应资本流动的大波动,这些国家情况将越来越悲观,可能导致全球增长从2010年至2020年下降2个百分点”。表7.3右边一列是这些选择的国家和地区的悲观数据。
越来越多的大众媒体把重点放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将在某年超过美国国内生产总值。至于具体是哪一年,由购买力平价(PPP)指标计算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决定。因为不是所有商品都适于贸易,基于实际汇率的国内生产总值的跨国对比往往是失真的。在中国,劳动密集型服务成本远远低于美国,利用购买力平价指标计算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可以考虑所有这些因素。在此文献中,应使用不同的计算方法确定购买力平价比率。根据这些计算结果,在基本数据这一列,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将从2010年的21%上升至2020年的40%。这些数据以佩恩表为基础,偏离艾肯格林等人的调查结果。在这些表格中,替代购买力平价指标适用,但长期而言,这些图表还是适用的。如果中国成功保持当前高度经济增长,中国的福利水平将在21世纪中期和美国齐平。
四、评价
全球化意味着越来越多国家参与世界市场,据估计,落后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福利水平将向发达国家靠拢,但这个假设尚未得到20世纪的事实数据证实。相反,落后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福利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对这样相反发展的相关解释研究使得经济科学家相当困惑。基于这样的背景,德隆提出,“我必须承认我并不知道这样发展的原因,而且要找到原因也相当困难”。(DeLong,2001,p.1)
为取得这个复杂问题相关的知识,不同的研究学者选择不同的方法,道瑞克和德隆选择描述性方法,这个方法的核心是“俱乐部趋同或经济一体化”概念。一方面,把抽样调查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世界技术领先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作为工业发展指标。另一方面,明确划分亚时期,建立“俱乐部趋同或经济一体化”。全球化导致经济一体化逐步扩大,但1950—2000年,因为政治原因,一些国家并不能参与经济一体化进程。道瑞克和德隆认为,经济将消除不同国家之间的贸易壁垒。落后工业化世界发展的国家是因为它们不能摆脱贫困陷阱,“落后国家依旧落后,所以它们只能从海外购买投资商品,要完成技术转型的成本很高,而且寻找支持大众教育的资源稀缺”。(Dowrick and DeLong,2003,p.218)
对这些问题的统计分析旨在说明实现经济一体化需要克服的障碍,其中心思想是经济一体化是有条件的。国家的经济增长不仅仅由初始情况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关条件决定,也受到其他很多变量的影响。学者针对这些条件做了大量统计研究。博斯沃思和柯林斯利用了相对长时间应用于不同国家的实证框架评估、研究结果,他们研究的样本包含84个国家,因变量是1960年至2000年人均产量平均增长率。他们从狭义角度和政策指标区分这些条件变量,这些条件变量被视为内生变量。条件变量适用于初始情况,这些变量包括健康、人口规模、地理划分和制度质量,连同初始情况的人均收入,构成这些变量和统计学角度的产量增长相关关系。政策指标,如通货膨胀的变化、经济的开放程度和预算平衡,对经济增长速度影响不大,甚至没有影响。这些发现意味着经济增长最终由短期内不能实质变革的变量决定。因此,经济一体化严重依赖于这些国家的特定条件,这一点也得到罗德里克的证明。他研究了1970年至2008年混合截面时间序列样本,这种方法提供了引入固定国家效应的可能性。尽管缺乏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关的无条件趋同,但国家模仿足以刺激条件趋同。
描述性方法和统计学方法结合最终得到明确的结果。西方国家福利水平经济一体化的可能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特定情况,然而,这些所有讨论都不能得到一致结果,或达成共识。在其中一项研究中,麦克米伦和罗德里克跳出了这个僵局,分析了9个不同水平国家38个部门的一体化进程,讨论1990年至2005年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在此期间,除了一些国家例外,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越来越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这一点可以通过一些国家惊人的增长率体现,尤其是中国和印度。
从国家的内部因素和结构变化因素分析国家生产率增长是麦克米伦和罗德里克结构主义方法的特性。首先,内部因素等于单独部门生产率增长的加权总和,加权值是突出部门就业比重占就业总数的份额。其次,结构变化元素指的是生产力水平的内积(时间结束)和跨部门就业比例变化,表现不同部门之间劳动力重新分配的影响。如果劳动力从低生产力部门向高生产力部门流动,总劳动生产率上升。反之,则总劳动生产率下降。如果是后者,结构变化可以视为负增长结构变化。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新兴国家受影响的部门生产力持续提高。如果能提高这些趋同部门或一体化部门在就业总量的比重,总劳动生产率也会显著上升。相反,如果活跃部门的劳动力节省伴随着劳动力流失,则发展中国家将不可避免地陷入负增长结构变化,导致生产率增长速度普遍降低。在这些国家中,因为受部门劳动力短缺的影响,受保护行业的生产力大幅下降。因此,生产要素没有得到有效配置,这种情况被划分为所谓的二元经济。
实证研究清楚表明,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亚洲结构变化元素是正增长,而拉丁美洲、非洲出现负增长结构变化。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差异,主要包括三个潜在原因。第一,非洲和拉丁美洲拥有大量有利可图的自然资源可供开采,但这些活跃部门的就业率并不高。因为自然资源的开采同样以知识投资及研发为基础,对经济的其他部门有很大的外部效应,莱特、杰拉斯塔和饭冢、泽特对这一点持争议看法。资源富集国家因此可达到高增长率,但资源诅咒仍然是一个谜题。第二,因为国际市场的竞争,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制造业被迫提高效率,解雇低生产率工人。相反,亚洲式的全球化以双轨改革为基础,各式各样的进口竞争活动获得政府的支持,而新出口导向型活动发展迅速。第三,我们不能忽视实际汇率的重要性。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面临估值过高的货币政策,而亚洲国家通过有针对性的实际汇率支持其工业发展。
中国、印度和巴西这些国家的一体化使得西方国家备受困惑。我们经常提到,就国内生产总值的绝对规模而言,中国经济将在不久的将来超过美国。然而,这个发展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超过美国。与此同时,很多事情都在发生改变。后者的观察是艾肯格林、朴东炫和申宽浩的研究中心,他们估计,通过大规模的国家抽样调查,猜测人均收入将最有可能增长放缓。此外,其他因素如增长的预放缓率、贸易开放度和支出构成也有可能影响经济增长。基于所得结果,他们预计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减缓的可能性加大。对于这一点,其他学者比较乐观,霍尔兹认为中国在赶超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之前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预测,2010年至2020年,中国经济仍将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正如上面提到的,第八章将讨论地缘政治后果。 经济增长新动力(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