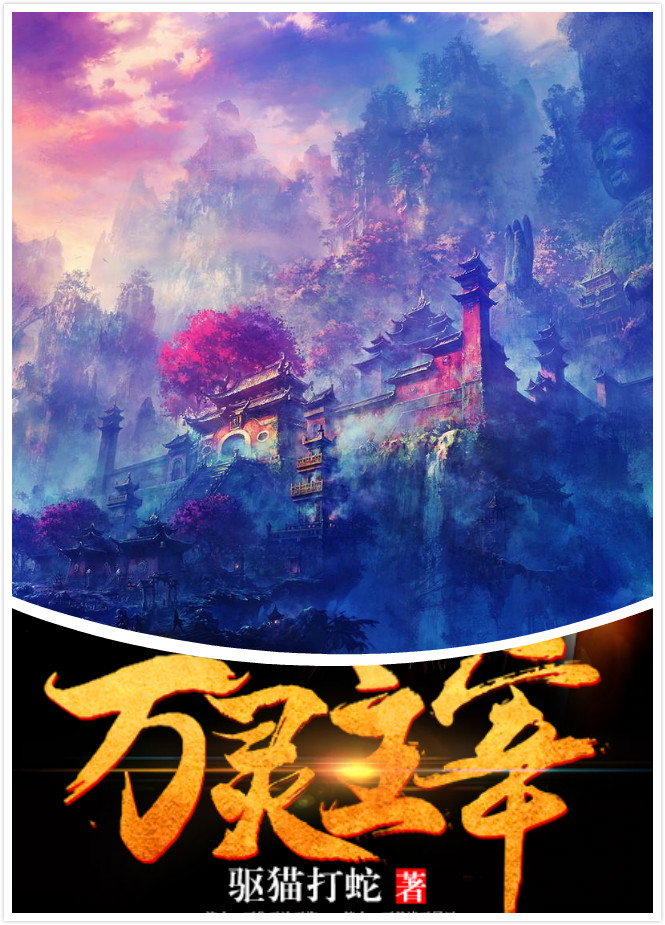与风投天使们的密会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经济增长新动力(套装共12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与风投天使们的密会
呀,他与天使角力,并且得胜;他哀哭,向他求恩。
——《圣经·何西阿书》,12:4
2010年9月
“就是这儿了,它应该在我们眼前才对。”
“我没看到。”
“地图上就标在这儿,是这儿没错。”我有点绝望地重复道。
“给他们打电话吧。”MRM提议说。
“我的天!5点过5分。我们迟到了。”
我们无可挽回地意识到,自己第一次与投资人见面就迷路了。迷路了,而且已经迟到了。会面的地点安排在洛斯阿尔托斯的一家星巴克,这里是围绕著名的中心城市帕洛阿尔托和圣何塞的南湾郊区城市方格中的一块。每块城市方格都有独立的门牌号规则和街道格局,直角栅格里随机穿插着一些城市规划者为了让那些灰泥粉刷的丑陋房屋看起来更“有机”而规划的毫不实用的蜿蜒道路。我们要去的地方是“洛斯阿尔托斯乡村俱乐部北边的星巴克”,这个乡村俱乐部是投资人每天下午三四点钟锻炼身体的地方。当我们满怀信心地从AdGrok总部出发时,完全没有料到Google地图会给我们指错方向。
MRM开着他的本田雅阁家庭轿车,我在前面用Google地图导航,没有想到Google地图这么不靠谱。
带着越来越不安的情绪,我拨通了星巴克的电话,像傻瓜一样望着路边的街道牌,问他们是不是在这条街上。
“啊,对……地图说我们已经到了,但好像还没有到。我们在二号街上。抱歉……”
可恶!
“跟拉塞尔说我们会迟到很久,看能不能改期吧。”我对MRM说。他是一开始的联系人。
我们和AdGrok传奇里最重要的两位投资人的关系就是这样开始的。后来,在一位投资人已经给了我们一些钱以后,我们得知当时他不仅对我们的无能感到厌烦,而且还很生气。差一点他就要把我们“拉黑”了;如果他真这样做了,这本书也就到此结束了。
那么,那个救了我们一命的人是谁呢?
拉塞尔·西格尔曼(Russel Siegelman),一位完美代表了硅谷科技业的典型的老派天使投资人。现在的一批“假天使”能和这些“老天使”共存于世,令许多人都不胜唏嘘。
麻省理工学院本科,哈佛大学MBA毕业,头戴哈佛商学院“贝克学者”光环的他,曾在微软有过长久的职业履历。他领导了MSN和Salon.com的诞生。前者是类似于雅虎的门户网站和邮箱服务,在整个门户网站世界被Facebook摧毁之前,它有过自己的风光时刻。之后拉塞尔在凯鹏华盈待了10年,这是和红杉资本同级别的顶尖风投公司(缩写为KPCB,圈内人常叫它Kleiner)。在代表凯鹏华盈投资了多家公司并成为其董事会成员之后,拉塞尔把全部精力转移到了私人天使投资——当然了,除了他参与专业骑行运动的精力。每一位除了钱和时间什么都没有的硅谷巨富都会花大量时间钻研一些健康而无用的技能,比如公路骑行和风筝冲浪之类的。拉塞尔体格健壮,肌肉发达,脂肪量低,就像战时精锐部队的士兵。阿吉里斯和我一致认为他就像以色列国防军的伞兵:值得信赖,有威慑力,令人不可小觑。“以色列伞兵”是他的正式绰号。
拉塞尔用自己的钱投资,所以无须听命于任何个人或机构,只需要对自己一个人负责就够了。如果你能让他的钱翻一番,他会很高兴;如果能翻三番,他将高兴极了;如果还能更多,那就再好不过了。但如果公司看起来好像快撑不下去了,他会想要把钱要回去,而不是一笔勾销。拉塞尔是那种在第一次互联网浪潮时给甲骨文、太阳微系统(Sun Microsystems)和eBay这些公司开出第一张支票的人。那个年代的天使投资人在人们眼中真的就是长着翅膀从天而降、可以助力你的商业冒险、让你一飞冲天的超自然生物。他们是理性的,只求一点还算可以的回报,不会要求几百倍的投资回报率。他们也很专一,因为你不是他们拿别人的钱投了50家公司来均摊风险用的。他们拿出自己的钱来参与这种商业游戏,而这钱也来自同样的游戏。
基于他的老派作风,我们在拿到投资之前接受了十分全面但有点没有章法的调查。他找了一些从事搜索营销业务的朋友,让他们帮忙看看我们是不是真的懂我们在做什么。他还把我们规划的线路图给另一些朋友看了看,以了解行业里的大玩家(比如Facebook)是不是已经在做类似的事。他个人和我打过几通很长的电话,相互试探和品味对方的风格,互相斟酌彼此的性格和作风,看有没有希望顺利磨合。
幸运的是,我们在演示日前一天就联系到了拉塞尔(虽然我们的第一次面谈由于Google地图的误导而泡汤),并且已经与他和他的助手面谈过很多次。也就是说,在我们与其他投资人接触之前,前面说的那些调查就已经开始进行了。我们很快发现,时机就是一切,如果我们没有提前好几周勾搭上拉塞尔(然后他再来勾搭我们),我们很有可能就失去了这位最主要的投资人和一位能让我们起死回生的天使。
在通过他匆匆安排的种种考验之后,他邀请我到他位于帕洛阿尔托老城的家里。即便在已经很尊贵的帕洛阿尔托市,也有多个级别的阶级划分。老帕洛阿尔托是硅谷传统精英居住的地方。史蒂夫·乔布斯和Google联合创始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都曾在老帕洛阿尔托居住过。林荫庇护的宽阔街道两旁藏着典雅的都铎风、工匠式或者仿西班牙风的豪宅,这些豪宅常常都由围墙包围,由花园植物点缀(YC领袖PG也住在这样的房子里)。这些地块令人意外地低调——帕洛阿尔托并非一直都是超级富豪聚居的飞地,事实上,它远远不是。如果需要大片房产,你应该搬到阿瑟顿或者伍德赛德那种更偏远的郊区去。很多硅谷精英的家庭壮大之后也确实会这样做。
拉塞尔位于圣丽塔大道的宅邸没有让人失望。那是一栋翻新过的工匠式宅邸,布满了山墙和弧形窗,墙体上点缀着昂贵的石头和木制装饰。拉塞尔在前门迎接我,穿着他的日常便服,一件旧T恤和短裤,看起来就像(可能也确实是)刚刚结束了一场长时间骑行。房子内部富丽堂皇,有很高的拱顶。可能是因为房子外面有一部分被厚厚的阔叶植物覆盖,这个巨大的拱顶空间颇让人感到有些意外。
我们经过拉塞尔的办公室,办公室里是密集如亚马孙丛林的硬木家具,绕过一个巨大的旋转式楼梯,我们来到了开放的起居室空间。拉塞尔的儿子正在旁边的小休息室里打游戏,我冲他笑了一下,算是打了招呼。拉塞尔领我在餐桌前坐下,他坐主位,我坐桌子边的某个角落。我们开始讨论这次交易的细节。这是我们投资人和创业者相亲程序中的第三次约会(也许你要抱怨我怎么又把融资比作求偶),正是应该决定要不要出手的时刻。
“那你们计划的封顶估值是多少呢,要融多少钱?”
啊,封顶估值!拉塞尔终于要和我聊正事了。
这个数字是第一次融资的早期创业公司最为看重的数字。它值得我们仔细介绍一下。
创业是拿别人的钱来做商业实验。
支持这场实验的资金是这样来的:第一笔钱叫种子轮投资,就像播种一颗神圣的红杉树种子,等它发芽。一般来说,这笔钱来自熟识的朋友或家人,或者拉塞尔这样的天使投资人,又或者克里斯·萨卡(Chris Sacca,我们很快会说到他)这样的“假天使”。AdGrok这样的小企业和通用汽车这样的巨型公司都会通过债券和股份换取投资。创业公司拿到的第一笔钱通常是以债务形式记录在案的,这有点反直觉,也不太符合实际,因为这笔账不是借多少就得还多少的真正的欠款。
所有处于创业初期的公司,除了那些一开始就筹集了超大笔资金的公司,都会把债务融资处理成所谓的“可转换债券”。尽管名字花哨,但它本质上不过是一种基于名义利率的债务。如果公司被收购或筹到了更多的钱,这笔债券可以转换成公司的股权,这样投资者就从债权人摇身一变成为公司股份的实际持有者。这听起来复杂,其实很简单。简单来说就是:我“借”给你10万美元开公司,如果你从别的地方拿到另一笔资金,那我应该得到价值10万美元的股份,不论到时候公司的股价是多少。
下面是一个简单的例子。注意,其中用到的数字只是为了解释方便,不代表现实世界。
投资人给了你一张10万美元的支票,作为创业启动资金。一年以后,你的产品和用户量达到某个里程碑,你以1 000万美元的估值融到了100万美元(这是种子轮后第一笔融资的典型金额,我们叫它“A轮”)。于是,那笔10万美元的原始债务转换成了公司的股票。估值1 000万美元,投资人投了10万美元,因此投资人拥有这家公司1%的股份。
从投资人的角度看,这实际上是有问题的。假设你是一家泡沫高潮时期最热门的初创企业,外界给了你一个非常疯狂的估值,比如说1亿美元。那我们可怜的天使投资人就只能拥有你公司0.1%的股份。也就是说,公司做得越好,早期投资人拿到的就越少。虽然说(理论上)他保证能拿到与后续投资人相同的股票价格,但这其实是对他所承担的风险无比错误的定价,因为他在很早之前就花了钱,而那时这家公司失败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于是就有了投资人的好朋友:封顶估值。这个数额规定了在引入更多资金之际,计算之前投资人的可转换股份时,公司估值的上限。在之前的例子里,如果我们为10万美元的投资设一个300万美元的封顶估值,那么,即使这家公司后来融资时实际估值为1 000万美元,这位天使投资人获得的股份也能达到10万÷ 300万=3.3%,远远超过没有上限的情况下算出来的1%。天使投资人换取股份的实际股价将基于估值上限(而非实际估值)确定,这就意味着相对于其他投资人,他用非常大的折扣购买了相同的股份。因此,这个封顶估值,就算没有在合同里明说,也从实质上被认为是天使投资人在写支票那一刻对这家创业公司的估值。刚起步的创业者时常有意无意提起这个封顶估值,就好像他们的公司真的值这个价钱一样。事实上,这不过是一次模拟运算的输入变量罢了,未来如何,还有待检验。
以股份而非债务的形式为创业提供资金,又是另一套不一样的玩法。可转换债券在谈判时,是没有一个大家都公认的估值的。你可以像四处采集花粉的蜜蜂一样,在不同投资人之间飞来飞去,谈出不同的封顶估值,不会有人对你提出异议。但是,如果用定额股份来交易,则需要有一个所有人都同意的每股价格及总共可交易股数。每一位股权所有人和投资人都必须在合同上签字。一般来说,这样的融资轮次会有一位领投者,由当前轮投资最多的人或机构担当。他们会帮助你联系其他人进行跟投。在这一过程中,合同之类的法律工作更复杂,也更昂贵。然后银行忙活一阵子,你就发财了。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兜售带封顶估值的债券就像是一个一个地勾引5个女人,而按股权融资则相当于说服5个女人同时和你上床。后面这项任务显然比前者困难得多。
为什么人们如此沉迷于封顶估值或真实估值?除了像炫耀阳具一样吹嘘大小以外,这个数字还有什么意义吗?有的。因为每个创业者都有一个巨大的敌人,一个藏在每张资产结构表里的恶棍,一个慢慢带来凋敝和衰败的魔鬼:股权稀释!这和一个很明显的事实相关——每家公司都是一块巨大而诱人的芝士蛋糕。一开始,你和合伙人可能拥有蛋糕的90%(另外10%预留给了未来的员工,成为期权池),每当你融到一笔钱,属于创始人的那块蛋糕就变小一点。在同等投资的情况下,你的估值(包括封顶估值)越高,投资人能拿走的就越少。每一轮后续融资时你都要拿一点蛋糕出来,不管投资人怎样参与这一过程,通过债务也好,股权也好。所以每位创业者都十分努力地想把估值做得尽可能高。推高估值就意味着可以给卖出的那一块蛋糕更高的定价,或者说把它切小一点。要拿到同样的钱,价格越高,需要交出的蛋糕就越小。
在帕洛阿尔托迷人财富的温柔包围下,拉塞尔和我坐在他餐桌旁谈判的正是AdGrok这块芝士蛋糕的价格——一个决定一切的假设性估值。在2010年夏天,对一家被YC看中的精英创业团队来说,600万美元是一个还不错的封顶估值。800万美元左右就算极好了,只有Hipmunk这种非常轰动的公司才能拿到。Hipmunk是一家旅游公司,一位Reddit创始人的第二个创业项目,它得到了接近这个数字的估值。我们这批YC校友封顶估值的中游(我们所处的等级)在300万到400万美元之间。这次餐桌谈话发生时,演示日已经圆满结束,我们正与多位投资人接洽。根据我探到的口风,我相信至少我们做到300万美元是没有问题的,可能还可以更多。于是我这样回答了他关于融资的问题:“拉塞尔,我们想按400万美元的封顶估值来筹集40万到75万美元。我知道我们谈到过300万美元,但我认为其他投资人现在不是按这个数字来打算的。”用自己的钱下注的拉塞尔对这个消息表示震惊。
“这可真是有意思了。”
一片安静。
“你和其他投资人定下来的时候通知我……”
然后他慢慢地摇了摇头。
在创业游戏中,我少有的派得上用场的个人技能之一是我检测人类弱点的能力。人类的弱点就像是粘在鞋子上的新鲜狗屎一样,那味道可以穿越整个房间,而我可以闻到它。拉塞尔的犹疑和若有所思的摇头动作清楚地告诉我:如果好好推一把,他是可以按400万美元封顶估值来投资的。现在我们只需要给他一点紧迫感。
很快,情况也确实更紧迫了——不过那并没有如我们所愿地把估值推得更高。
AdGrok的另一位重要投资人是“以色列伞兵”的完全对立面。他就是克里斯·萨卡,他当时是,现在也是硅谷最著名的天使投资人。张扬的个性,鲜明的观点,社交媒体的红人,Google比较早期的员工,Twitter和Uber的早期投资人,他是初创投资领域仅有的六七位明星投资人之一。当他那闪着24K金之光的名字出现在你的资产结构表里,将激发那个十足重要但又难以实现的奇迹:吸引其他没骨气的投资人跟投。那些人只要看到他的名字就要跪下。和拉塞尔不同,他不用自己的钱投资,至少不全是用他自己的钱。在他那个等级的投资人阶层里,那些微型风投基金管理着2 000万到4 000万美元的资金,而这些资金多来自那些不想亲自筛选公司和参与投资游戏的科技界其他有钱人。克里斯·萨卡这种职业投资人虽然看起来很厉害,但其实也是在为别人打工,而且还有不止一位老板。所有那些给他们钱让他们投资的人都是老板。如果这些基金不能产生丰厚的收益,那他们就只能回去做独立的个人天使投资人了(如果他们自己的钱还有剩余的话)。
演示日那天,我一走下讲台萨卡就给我发了邮件。“我喜欢”是他邮件的标题,邮件正文提到了他的Google背景以及他对我们正在做的东西的理解。
萨卡后来会成为故事的核心人物,但是我们只有一次面对面谈话,而且还是演示日一周以后由他提出来的。这一周的延迟是因为他住在湖畔滑雪胜地特拉基镇。他家坐落在距离旧金山三个小时车程的太浩湖旁有如天堂般的高山里。年轻的创业者在那边租房子住,年长有钱的投资人(比如萨卡)则在那儿买了房子。
我们见面的地方在砖房咖啡馆,一家奇怪的低矮的西部主题两层楼酒吧餐厅。它位于旧金山市场街南区的核心地带,是硅谷人士密谋融资和收购事宜常去的一个地方。它旁边就是人们请客户吃饭才会来的精品牛排餐厅“亚历山大”(人们在这里挥霍享用新鲜的黑松露菲力牛排)。一个街区以外就是旧金山的创业宇宙中心南方公园。
阿吉里斯坚持要参加这次“化缘之旅”,尽管我努力想让他和MRM远离这闹心的要钱过程。我们进去的时候萨卡已经到了。他穿着一件西部主题的牛仔衫,坐在一个有硬木靠背的卡座里,非常符合他在社交媒体上体现出的人格特征(也和今天这个会面地点非常搭)。他做了一个要站起来和我们握手的样子,然后我们三个人挤进卡座,开始谈正事。
就像当初YC面试时一样,阿吉里斯和我轮番上阵应对萨卡,向他传播如今已演练多次的AdGrok“福音”。不到一个半小时之后,萨卡宣布:“我加入!”至此会议基本上就结束了。就是这么简单。
双方站起来准备离开,萨卡冲向门口,快速左转沿楼梯走上了二楼。我们信步走出餐厅,有点难以相信这一切怎么这么简单。在门口我们遇到了所罗门·海克思(Solomon Hykes),我们同一批的YC创业者。我们匆忙地问候了几句,有点愚蠢地宣布了我们在这里和萨卡见面。“我也是。”他说着,跳跃着走上去往二楼的楼梯。
在开始或者结束与某位知名投资人的会晤时撞见YC同学的场景是这种会议的常态。那感觉就像是所有人都在参加一场活动地点遍布整个湾区的速配活动,从旧金山的咖啡馆到门洛帕克的会议室。所有人都急于找到可以令配对成功的共通点,然后(需要的话)再进行下一次会面,或者(在可能的条件下)写一张支票。
对我们来说,至少在那一刻,这是一次胜利。更重要的是,这次胜利让我们跑在了融资竞赛的前列。萨卡已被我们收入囊中,我们的资产结构表上有了一个金光闪闪的名字。但我们还得向更多的钱进军,如果我们想真正成功的话。 经济增长新动力(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