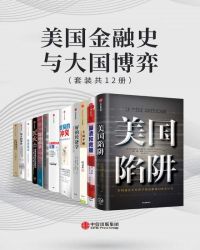结语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美国金融史与大国博弈(套装共12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结语
就像本书展示的那样,美国的贸易政策始终在政坛引发激烈争议。分散于全国各地的各利益集团,通过不同政党和当选议员体现自己的利益所在,要么努力扩大出口,要么竭力限制进口。这些群体或者受益于国际贸易,或者受它所累。它们之间的紧张关系贯穿了美国的整个历史。
然而,稳定一直凌驾在这种冲突之上。美国的贸易政策经历了三个不同的时期。财政收入、限制及互惠等目标分别成为各个时期的政策要务。在每个时期内,尽管贸易政策的方向始终冲突不断,但贸易政策相对保持稳定且不易发生改变。它们之所以能够保持稳定,部分原因在于美国的政治体制使人们难以改变现状。因此,美国贸易政策的特征之一是“冲突下的稳定”。
例如,在1860年至1934年政府利用高关税限制进口时,人们对贸易政策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但在这75年的时间里,政府基本没有对贸易政策进行调整。反对现行政策的人群只有两次机会降低关税,其中一次被浪费了,另外一次短暂成功后被迅速逆转。同样,在1934年之后的互惠期(到现在为止已经延续了80多年),人们的争论焦点在于到底要批准贸易协定进一步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还是让它们维持现状,他们不再争论是否要回到高关税时代。从历史的角度看,美国在特定时间点考虑的贸易政策往往局限在极窄的范围内。
如果只关注贸易政策上爆发的直接冲突,那么可能会忽略它的长期稳定性。在20世纪60年代初,雅各布·维纳(Jacob Viner)警告说“国会……出现了向贸易保护主义倾斜的趋势。”在20世纪70年代初,弗雷德·伯格斯滕(C.Fred Bergsten)警告说:“自1934年以来,美国的贸易政策一直追求自由贸易,而现在它在稳定地偏离这条轨道。”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还有其他不少人警告保护主义将死灰复燃,随后在21世纪头10年,人们称全球化的趋势即将逆转,自由贸易政策马上就要走到尽头。不过现在回头看,虽然当时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提出这些警告,但这些言论有些夸大其词。 注释标题 这些引文及其他类似引文来自Pastor(1983)。作者将它们称为‘哭泣叹息’综合征。 相反,尽管出现了一些停顿和倒退,但看起来美国自1934年以后一直在相当稳定地朝着减少贸易壁垒的方向前进。只有时间能证明特朗普在2016年竞选活动中发表的反贸易言论是否会切实地转化为政策行动,并改变上文的结论。尽管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可能增加,就像20世纪80年代美国与日本之间那样,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美国会全面摒弃开放贸易政策或者贸易政策的“互惠”阶段行将结束。
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开始强调互惠,代表着美国的贸易政策兜了个圈子又回到原点。互惠始终是美国贸易政治的长期政策目标和传统。美国的开国元勋一直希望以开放和非歧视的方式推进贸易。美国赢得独立后惊讶地发现,一旦自己脱离了大英帝国,就在贸易和航运上面对很多歧视性政策。在18世纪80年代,美国未能完成贸易政策谈判,它的经济又因为排除在殖民国家的市场之外而蒙受损失。这些艰难的经历给美国的贸易思想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1793年托马斯·杰斐逊发布的《通商限制报告》坚称不应该容忍“不公平”的外国贸易壁垒,应通过谈判或反补贴措施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这份报告成了如今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每年发布的《对外国贸易壁垒的国家贸易评估报告》的前身。
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并不担心互惠问题,因为它的主要贸易伙伴英国一直奉行单边自由贸易政策。在此期间,贸易政策主要属于国内政治问题。但是,到了19世纪末,殖民地开始回归贸易优先政策,人们重新主张在公开、非歧视的基础上推进世界贸易。1899年国务卿海约翰的“门户开放”照会充分反映了这种主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也是出于这些想法坚持认为,美国以平等和非歧视的方式进入世界市场能够服务于其国家利益。在这两种情况下,美国都没有认真地推出相应的政策举措,但随着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爆发,世界贸易环境急剧恶化,改变了整个局势。英国及其自治领在1932年《渥太华协定》中决定采取极端贸易限制措施,并重新启用关税优惠政策,使美国贸易政策急剧转向。它的政策目标变成清除那些不利于美国出口的优惠政策和歧视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贸易政策的根本目标是完成贸易协定谈判降低贸易壁垒。“本届政府在贸易政策方面最重要的承诺是打开市场并扩大贸易,在可能的情况下通过多边贸易协定实现这个目标,在必要的情况下通过双边贸易协定实现这个目标,并且推行贸易法律来抵制其他贸易国的不公正贸易行为。” 注释标题 参见PPP(1993),第2卷:第2198页。 这是克林顿政府于1993年发布的官方声明,不过基本上它可以用来描述过去80年里任何一届美国政府的贸易政策。这份声明表明美国贸易政策的目标本质上存在连续性。
在协助建立《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之前,美国已经为了实现18世纪80年代确定的初始目标走过漫长的道路,即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开放和非歧视性贸易。各次贸易谈判已经将发达国家的进口关税降至较低水平。作为本书的主要关注点,美国的进口关税也处于历史低位。2016年,所有进口产品的平均关税为1.5%,应税进口产品的平均关税为5.0%。虽然关税的下限为零,但近年来关税水平并没有明显下降,而且近期全面清除关税的可能性很小。当然,美国与其他国家一样仍然设置了很多非关税贸易壁垒。从历史的角度看,目前美国仍然对贸易非常开放;它的进口产品中有70%免交关税。
要想继续推进降低贸易壁垒的进程,美国的互惠时代是否会延续下去取决于总统的领导力。除非国会认为可以通过贸易解决重大政治问题,否则它本能地避免对贸易政策采取任何行动。由于贸易政策的调整总会引发国内争议,所以国会需要有极其充分的理由努力降低贸易壁垒。政府必须说服国会相信贸易协定可以解决重大经济问题,才可能推进这方面的工作。从1947年的第一次《关贸总协定》谈判、20世纪60年代的肯尼迪回合到80年代的乌拉圭回合,美国在互惠时代推出的每一次重大贸易倡议都是为了解决美国出口商当时面临的巨大障碍:如20世纪30年代的“帝国特惠制”、50年代创建的欧洲经济共同体、随后欧洲在80年代提供的农业补贴和当时匮乏的知识产权保护。在每一种情况下,美国国内都形成了广泛的政治共识,即与贸易伙伴开展谈判解决出口商面临的问题符合美国的国家经济利益。 注释标题 请参见Dür(2010)。 没有令人信服的案例表明外交政策严重阻碍了出口,或者对外交政策的考量使美国有充足的理由在贸易政策方面采取行动。这意味着近年来要想获得国会对新贸易协定的支持难上加难。
或许在当前这个互惠阶段,美国贸易政策面临的一个更严峻挑战是,保护主义不断以新的形式涌现。2009年大衰退造成的后果之一是,全球很多国家采用了微妙的监管歧视措施保护并支持本国企业。这些“灰色地带”的政策远远不如关税或其他边境措施那么透明,因此通过谈判清除它们的难度更大。此外,当前的贸易协定不仅涉及关税、配额和补贴等传统的贸易壁垒,对监管协调、制定产品标准和保护知识产权等问题同样高度关注,所以对国内经济的干扰程度也相应地“水涨船高”,遇到国内的政治阻力在所难免。由于监管保护主义的使用日益普遍,达成复杂的贸易协定的希望又不断破灭,所以贸易政策前景的不确定性比过去有增无减。
最后,我无法克制心中的强烈愿望,还是打算用预测未来政策走向的方式为这部长篇史书画上句号。如果说我们从过去学到的教训是“(美国的贸易政策保持着)冲突下的稳定”,那么可以轻而易举地由此得出一个结论:未来的事态发展会和过去高度相似,互惠时代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如果说过去导致美国贸易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的是内战和大萧条,那么现在很难预见什么时候会发生下一轮将贸易政策推向其他轨道的政治或经济动荡,尽管出现了特朗普总统在选举中成功突围这样的意外。
不过,谢茨施耐德(E.E.Schattschneider)和他探讨《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的经典著作《政治、压力和关税》(Politics,Pressures,and the Tariff)讲述了一个警世故事,提醒我们不要对过去的经验过于自信。谢茨施耐德(1935,第283页)总结说:“对1929年至1930年修正关税法案的压力政治进行研究的结果表明,要求下调关税的政治力量凝聚在一起后不足以扭转政策走向,使美国重返低关税或自由贸易体系。”但不幸的是,这本书出版一年前,美国就已经通过了《互惠贸易协定法案》。这一法案标志着美国贸易政治的主要目标从限制进口转向互惠互利,最终使美国关税创下历史最低水平。考虑到这一“前车之鉴”,或许我们唯一可以确信的是,正如詹姆斯·麦迪逊很久以前预测的那样,未来美国贸易政策必将爆发很多新的冲突。 美国金融史与大国博弈(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