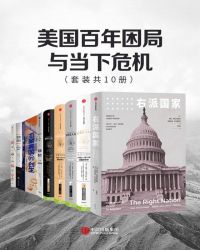13.通过移民和行动来构建新亚裔美国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美国百年困局与当下危机(套装共10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第四部分
全球化世界中亚裔美国的重建
13.通过移民和行动来构建新亚裔美国
自20世纪60年代起,一个新的亚裔美国开始形成。其开端是1965年移民与国籍法,该法放宽了移民政策,并迎来一大波来自亚洲各地的新移民,其中很多与“二战”前的移民社会关联不大。在过去的50年间,亚裔美国人的社区数量呈指数规模增长,加上从东南亚而来的难民,亚裔社区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和跨国化。
第二个主要变化是亚裔美国人广泛参与到公民权利、妇女解放,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权利,乃至结束越南战争等运动之中。在这些政治参与之外,逐步出现独特的亚裔美国人运动,旨在帮助人们确认亚裔美国人的多样性,并号召亚裔们采取行动。在数十年被媒体和立法者们无差别地集体认定为威胁美国社会的“东方人”后,新一代自觉、主动地自我认定为亚裔美国人,并联合起来共同推动多族裔联盟与行动。他们拥有共同的历史和当下的经历,要求在美国社会中获得全面的接纳与承认,并组织起重要且长期的机构和组织,处理具体的亚裔美国人问题与不平等现象。
当代亚洲去往美国的移民同1965年移民与国籍法直接相关。支持移民的改革源自冷战政策和20世纪60年代的公民权利运动。当时,美国专注于其自由与民主的价值观念相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基于种族不同而对移民区别对待,暴露了美国移民立法的虚伪。这种强有力的领导来自时任总统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他于1958年出版《一个移民的国度》(A Nation of Immigrants)一书,对美国的移民传统进行毫不掩饰的颂扬,并呼吁移民改革。
肯尼迪遇刺后,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接续了这一事业,并宣布1924年移民法中的来源国配额制“与我们美国的基本传统不符”。这一对美国移民传统的新支持谨慎而带有偏见。正如国会辩论所表明的,来自欧洲的移民仍然被优先考虑,而且总统也强调,这一法律的初衷是纠正配额制对南部和东部欧洲人所犯的错误。更重要的是,他将美国移民改革与美国的国际形象和目的联系起来。在1964年的国情咨文演讲中,约翰逊强调,伴随着移民改革,“这一由来自各地移民构建的国度,可以问现在想要入境的人:‘你可以为我们的国家做什么?’[而不是]‘你出生于哪个国家?’”总统继续说,一项新的移民法可以帮助美国完成她的“终极目标”,即创建“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一个多样性安全的世界,在那里所有人、物和想法可以跨越任何边界与障碍自由移动”。
移民改革的支持者们注意到,法案可能会导致“大规模”的非洲人和亚洲人进入美国,或使美国成为拉丁美洲人“清卸场”。最终的法案规定了第一年移民美国的全球名额,或者说,数量限制。当总统约翰逊在自由岛以自由女神像为背景签署移民法时,他向美国人保证“这不是一个革命性的法案”,“它不会影响成千上万人的生活”。
图40.总统林登·约翰逊签署移民法,旁观见证的有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伯德·约翰逊(Bird Johnson)夫人、穆里尔·汉弗莱(Muriel Humphrey)、参议员爱德华·(泰德)·肯尼迪[Edward(Ted)Kennedy]、参议员罗伯特·F.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等人。纽约自由岛,1965年10月3日。
事实证明总统是错的。1965年的移民与国籍法,又称《哈特—塞拉法》(Hart-Cellar Act),原意是要在国家移民政策上迈出第一大步,但是在过去半个世纪里,由于缺乏全面的移民改革,这项法律仍是今天移民政策的基础,它无疑影响了成千上万人的生活,而且改变了亚裔美国人和美国的历史方向。实际上,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群体比亚裔美国人从这一法律中获益更多。1965年移民法导致三个主要变化。首先,这项法律禁止以国家为来源的配额制,引发了与早期移民相比,无论是在规模还是在族群构成上,都有本质不同的大规模移民新纪元。在1965年之前,移民最高峰的10年是1911—1920年,总计573.6万名移民进入美国,他们大部分来自欧洲。20世纪80年代,统计显示有733.8万名移民来到美国,随后1991—1997年有694.3万名移民。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在以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高的速率接纳移民。2010年,美国有4 000万在外国出生的居民,占总人口的13%。他们中超过一半是在1990年后进入美国的;三分之一是在2000年后进入美国的。
1965年后的移民也与以往的移民有着显著不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移民主要来自欧洲,而新移民主要来自亚洲和拉丁美洲。在20世纪80年代,来自这两个地区的移民超过总移民的八成。这一模式到21世纪仍在继续。2010年,在美国的外国出生居民中有53%出生于拉丁美洲,28%出生于亚洲。5 500万拉美裔美国人(包括外国出生和本土出生)构成了总人口的16%。2011年,包括外国出生(59%)和美国出生(41%)的亚裔美国人口总数为1 820万,约占总人口的5.8%。同时来自亚洲的新移民人数占移民总数的比例还在增加,构成了自2008年来所有到达美国的外国出生人口的40%。
其次,这一法律更倾向于接受家庭团聚和具备职业技能的移民。这一政策对亚洲移民有利,他们来到美国以满足其对专业技能的需求,同时与已经在美国的家人团聚。近期的移民法延续了这一趋势。举例来说,1990年的移民和国籍法,增加了临时签证,即H-1B签证的外国高技术的“外来工人”(guest workers),而且美国公司,特别是高科技公司,也积极从亚洲招聘高水平员工。亚洲移民获得约四分之三的H-1B签证,仅印度人就在2011年获得了12.9万个H-1B签证中的56%。
最后,一个显著的变化是1965年移民法对全球移民限额的确立,以及首次对来自西半球移民的新限制。这一法案开启了自20世纪70年代便成为移民争论焦点的非法移民的新纪元。
1965年后从亚洲和拉丁美洲来的移民导致美国社会在各个方面的种族重组,从政治和教育,到医疗保健和跨种族婚姻,都受到影响。亚洲移民的增加、经济投资和对美国的贡献改变了所有美国人的日常生活。这些移民集中在西部和东北部,但是近几十年亚裔美国人开始在每个区域增长,而且2000—2010年,亚裔人口数量在每个州都有所增加。举例来说,北卡罗来纳州,现在有相当多的印度人口,同时明尼苏达州是仅次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第二大赫蒙(Hmong)人的聚居地。
现在的亚洲移民与几十年前相比,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过去,亚裔移民受到移民法的高度控制,而强调家属移民和职业、高技术移民的美国法律,意味着新来者中的大部分人是来加入已经在美国的家人,并带来一批在教育和职业技能方面与早期移民不同的移民。与20世纪早期来到的、主要为单身男性劳工的移民不同,现在女性移民在所有移民中占据更大数量,而且很多是作为家属移民的。在美国海外出生的亚洲人口中,女性事实上占据多数(54%)。最近来自中国、印度、菲律宾、韩国、越南和日本的移民,62%是因其已经在美国的家人而获得绿卡。而且由于过去对成为归化公民没有禁止,美国59%的外国出生的亚洲成年人归化为了美国公民。
在亚洲移民内部也存在更大的多样性。1960年,日裔美国人是亚裔美国人口中的最大群体,占到亚裔总人数的50%,但是自1924年后来自日本的移民就处于低位,到2010年,日裔美国人在亚裔美国人口中只占7%。来自中国的移民数量仍然较大,而且相较于20世纪早期,来自菲律宾、印度和韩国的移民也大为增加。除此之外,在1965年以前只有少量移民到美国的国家,如越南、柬埔寨、老挝、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现在的移民数量一直保持稳定并持续增加。
最近来自亚洲的移民还代表着突出的教育背景和职业技能的多元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来自印度、菲律宾、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的工程师和医学专家构成了这些职业在全美劳动力市场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同时,很少接受过教育和缺乏职业技能的移民人数也在增加,导致亚洲人在教育和阶级分层中占据两个极端。2000—2010年,亚洲非法移民也占据美国1 100万非法移民人口的相当比例(10%~11%)。
在华裔美国人中也存在类似的多样性。1961—1998年,大概有150万移民,男女比例相当,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1972年中美正式建交后的1977年中国大陆开始允许移民)进入美国。从1960年到1990年,在美华人差不多每十年翻一番。1960年,美国只有不到10万中国出生的华人移民。到2010年,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美国的成年华裔美国人超过330万,构成亚裔美国人口中的最大族群,也是亚洲之外最大的华人群体(包括台湾人),他们代表着24%的美国亚裔成年人口。其中有76%为非美国出生,69%为美国公民。近几十年中国移民的数量巨大,现在外国出生的在美华人甚至已经超过了本土出生的美籍华人。
这些华人移民美国的原因各异。很多中国人在20世纪60年代根据1965年移民法作为学生或学者初次来到美国。另外一些人是为了同家人团聚而来到美国。先移民者积极资助他们的配偶、孩子、父母和兄弟姐妹来到美国,这些人同样又带来了他们的全部家庭成员。以家庭为基础的移民链如此之广,以至于1965年移民法被人戏称为“兄弟姐妹法”(Brothers and Sisters Act)也就不足为怪了。肯尼·赖(Kenny Lai)在20岁的时候先到达香港,并与其妻子在1978年成功到达美国。
由于美国1990年移民与国籍法重视工作移民和资本投资,因此高技术水平和受教育的华人移民,作为临时外国劳工被引入美国就业于“特殊职位”,或是作为乐于将资本投资于美国企业以换取永久居留权的投资者们被引入美国。在25岁及以上的华裔美国人中,有超过一半(51%)拥有学士学位,而在全美,这一数据为28%。他们的人均收入中位数(5万美元)高于其他亚裔美国人(4.7万美元),也高于所有美国成年人(4万美元)。受雇的在中国出生者中,几乎1/4从事信息、科技和工程相关工作。
这些精英和职业移民们属于“上层的、高端的华人”,他们之中有讲英语的科学家、房地产大亨、资本主义企业家,以及职业精英。这些职业移民中的很多人在郊区形成了新的族裔飞地,包括华人自己的银行、餐厅、商场和汉语报纸。在南加利福尼亚州蒙特利公园(Monterey Park),华人占到了超过1/3的人口,这座城市也因此有了“第一个郊区中国城”的绰号;与此同时,纽约市内现在也有数不清的中国城散布在五个区。
当这些受过良好教育和高收入的华裔美国人描绘出一幅令人惊讶的经济成功的肖像图时,华裔美国人实际上在社会经济阶梯的两端都不乏代表。他们同样也是“下层的、低端的”中国人,他们是缺乏技术的工人、服务生、家政工人、制衣工、厨师和洗衣工。举例来说,20世纪90年代初,来自中国的女性移民组成了旧金山缝纫机操作员中的80%。类似的,华人移民女性占据制衣行业劳动大军的85%。她们在妻子、母亲,以及工人的多种角色中切换。作为工人,她们的工资为其家庭经济做出了重要的财务贡献。但是在家里面,人们还期待她作为传统照顾者的角色,做饭、打扫、洗衣、购物,照顾孩子、丈夫,有时候还要照顾父母。慢慢地,一些事情开始在家中改变。1992年一个中国缝纫女工告诉社会学家周敏(Min Zhou)说:“我丈夫完全不敢小看我,他知道只靠他自己不能养家。”
由于有限的英语能力和职业水平,仍然有很多中国女性移民不仅在工作选择方面受限,也在缝纫工厂中受剥削,从事低工资工作。一些女性为担起自己的责任,同时争取一些工作保障和工作条件的改善。例如,纽约中国城中的缝纫工,组织起价格相对低廉的儿童照顾事业。1977年,一群工人向国际妇女缝纫工人联盟(International Ladies’ Garment Workers’ Union)表达了她们的诉求。当她们的诉求不被理睬时,积极分子开始组织日托,有时候她们会带着孩子一起去见联盟的负责人。1982年,国际妇女缝纫工人联盟协商一项新的联盟契约时,这些积极分子起到重要作用,她们动员2万名中国城工人走上街头支持罢工。联盟同契约商重新谈判,并承认积极分子的日托工作,国际妇女缝纫工人联盟于1984年开办了第一家日间托儿所。
其他“下层”华人,包括那些非法进入美国的华人。他们既没有职业技能,也没有给他们提供帮助的已经在美国的亲属,据估计,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有15万华人非法进入美国。很多人来自福建省这一中国南方贫困的沿海农业省份。他们指望着一夜暴富,冒着巨大风险,花费巨大,以实现长久以来的“美国梦”。正如在20世纪之初,拉丁美洲国家成为进入美国和加拿大的后门一样,有时在走私者或“蛇头”的帮助下,他们进行长期、迂回和危险的旅行进入北方。1989年,王丽丽(Lily Wang)花费3万美元被指引从福州到香港,再到泰国、玻利维亚、墨西哥,最终越过边境进入美国。到2010年,中国移民的这一花费已经涨到8万美元。
难以计数的中国人死于途中。1995年,18名中国人在去往匈牙利的途中,因窒息死于密封拖车里。5年后,58名中国人在英国的多佛被发现死于一个装满腐烂西红柿的冷藏箱中。1993年,一艘名为“金色冒险号”(Golden Venture)的船载着260名中国移民在纽约洛克威半岛附近游荡。船上的中国人被船员要求自己游上岸,他们从甲板上跳下海,其中10人被淹死。2005—2008年,美国边境巡逻队逮捕了6 000名企图穿越美墨边境非法进入美国的中国人。据估计,在2009年,美国大概有12万名非法移民来自中国。
即使他们能够一路幸运地进入美国,非法的华人移民也常常面临着多年的剥削。他们藏匿在内城区,做着低贱的工作以偿还高额的走私费用。他们向家里汇回钱款,期待亲戚们的到来。有些人为了极低的工资而被囚禁、殴打,或是被迫为低得可怜的工资而工作。极少数人还清了他们的债务,甚至获得经济上的成功。另一些人只能面对艰难困苦,甚至命丧美国。例如,王丽丽起初在服装厂工作,最后却沦为妓女。她总结说:“美国不是天堂,而是地狱。”
同样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来到美国的,还有中国被收养的儿童。
到2000年,中国已成为提供国际收养儿童的主要国家,同时当年有超过5 000名被收养的中国儿童来到美国。作为一种人道主义行动和美国多元化进程的象征,华人收养计划帮助美国创造了更多的“国际家庭”(global families)。
与中国移民类似,菲律宾人自1965年后来美的人数也在增长。1965年移民法通过后的20年里,几乎有66.5万名菲律宾人进入美国。从1990年到2000年,菲律宾移民增长了66%。2010年,美国国内有超过255万菲律宾人,占亚裔成年人人口的18%。这些人69%在国外出生,3/4是美国公民。
来到美国的菲律宾移民只是菲律宾大规模全球移民的一部分。作为全球经济重组的结果之一,以出口为导向的国家如菲律宾,依靠其国民移民来为自己的经济带来外汇。超过800万,或占菲律宾总人口1/10的菲律宾人,当前在海外140多个国家工作。他们从事护士、医生、教师、演艺人员、家政,以及在集装箱轮船和豪华游轮上做海员,这些离散的菲律宾人或许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离散群体。超过60%的海外工人是女性,反映了移民的性别模式,总的来说,他们汇回家的钱款支撑了他们家庭和国家的生命线。
就像前几十年,绝大多数在国外定居的菲律宾人来到了美国。美国持续地存在于菲律宾的移民文化当中。正如20世纪之初美国的教育、富裕和流行文化——更不用说已经在美国的亲朋——吸引着绝大多数的菲律宾人来到美国。
菲律宾移民仍然受美国与菲律宾的殖民和军事关系的影响。在1946年美国结束对菲律宾的长期殖民关系后,贸易关系、军事援助,以及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将两个国家紧密地连接起来,也促进了特定的菲律宾来美的移民者类型,尤其包括特殊服兵役成员和医疗专家。1970年,1.4万名菲律宾人在美国海军服役,数量超过本土服役的海军人数,而今天,菲律宾人是继墨西哥移民之后,在美国军队中第二大外国出生的退伍军人群体。
同样,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菲律宾给美国带来了最多的职业移民。菲律宾护士、医生和其他医疗从业者被美国医疗机构大量聘用,以缓解医疗部门人力短缺的压力,特别是在中心城区和乡村地区。到20世纪70、80年代,菲律宾人成为美国医疗专业人员的最大供给来源。2010年,超过15%的菲律宾出生的男性就职于医疗保健行业,几乎23%的菲律宾出生的女性为注册护士。他们成了菲律宾“新的国家英雄”。
菲律宾的政治形势,特别是在费迪南德·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1965—1985年)高压执政期间,以及反政府武装所造成的内乱,也促进了海外移民。马科斯在1972—1981年实行军事管制,并对媒体和立法实行极端严格的控制。他的很多政敌都被捕入狱。
持续大量的失业和不充分就业,以及收入的不平等的状况,使移民文化得以持续。在祖国很难找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将其技能带到其他国家。接受美国式教育系统、精通英语、熟识美国文化——菲律宾人为移民到美国做了充分准备,而他们的技能也正是美国所需。1972年,《洛杉矶时报》报道,一天中有超过2 000名菲律宾人申请入美签证。
然而,不是所有菲律宾的医疗工作者都能够在美国寻找到合适的就业机会。加试和美国医疗的需求,以及工作场所中的种族主义,经常造成新移民就业的障碍。当很多人成功地应对了埃德加·甘博亚(Edgar Gamboa)博士所称的,针对外国出生的医生的“微妙种族主义”时,其他人则要经历重新获得证件的漫长历程和测验,或是最终在与他们的医疗训练不相关的领域工作。
菲律宾护士在美国也面临障碍,他们采取了集体行动予以回击。当20世纪70、80年代爆发针对外国训练的护士和执照的抵制时,菲律宾护士组织起来发出统一的声音,以减轻菲律宾护士在海外所面对的困苦,并且维护了外国护士公平地得到许可证的程序。例如,作为外国护士保护基金(Foreign Nurse Defense Found)执行秘书的菲律宾护士诺玛·沃森(Norma Watson),在给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信中,呼吁关注渗透在这一职业中的习惯性歧视。“外国护士,特别是菲律宾人,是‘医学世界的苦力’(COOLIES OF THEMEDICAL WORLD)……我们对于卑躬屈膝姿态和文化上的非攻击性厌倦、疲惫了……我会乐于看到所有的外国护士都走出这个国家的医院,再来看看会发生什么。”沃森对罢工的幻想永远不会实现,但到1981年,菲律宾的护士组织成功地迫使加州注册护士委员会(California Board of Registered Nursing)建立无歧视的许可证考试。
在1965年美国移民法颁布后的数年,来自印度和1947年成为独立国家的巴基斯坦移民也在增加。1980年美国人口普查记录国内有371 630名南亚人,包括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和斯里兰卡的移民。1990年,这一数字为919 626人,几乎增长到三倍,而到2010年,全美有284万印度人,363 699名巴基斯坦人,128 792名孟加拉人和28 596名斯里兰卡人。
来自印度的移民者构成南亚移民的主体。他们是亚裔美国人中的第三大群体,其中87%出生于美国之外。不像20世纪之初主要来自旁遮普地区——现分属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少量移民,当前的新移民来自印度各个地方。另外,加勒比、东非、加拿大和英国带有印度血统的人也移民到美国。20世纪之初的移民几乎都是男性劳工,而当前的印度移民者则由男性和女性共同组成。相较于其他移民群体,印度移民明显受到了更好的教育。绝大部分人能够流利地说英语,而且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包括物理学家、工程师和计算机科学家。这既源于印度的经济条件,也因为美国有利的移民政策。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印度的经济无法赶上它所培养的大学生毕业的速度。1974年,印度有10万名工程师无法找到工作。与此同时,美国根据1965年移民法对技术和专业人士的偏好,招募了这些高技术人员。
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员在海外寻求机会的同时,正值美国1965年移民法为这些有科学技能的人提供签证的时期。拉姆·嘎达(Ram Gada)就是20世纪60年代来到美国的人之一。他获得工程学位后在孟买的一家汽车公司工作,但是他觉得自己在印度没有未来。已经在美国的朋友和亲戚鼓励他来美国,并帮助他申请高级机械工程的奖学金。他的父母认识生活在北达科他州的人,于是他背起行囊来到北达科他,获得硕士学位,并最终定居于明尼阿波里斯。
嘎达绝非个例。1974年就业于美国的4.6万名印度移民中,1.6万人是工程师,4 000人是科学家,还有7 000人是物理学家或外科医生。1975年,准许进入美国的印度移民有93%是“专业/技术工作者”及其配偶。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当前的印度移民有81%已获得大学学位,这让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极有竞争力。如此多受过高等教育和有技能工人的到来,对美国工业产生了深远影响。学者A. L. 萨克森尼安(A. L. Saxenian)估计,到1998年,中国和印度移民在加利福尼亚的硅谷创立了超过1/4的科技公司(约2 000家),并提供6万个工作岗位。截至2012年,15.5%的新兴公司都是由出生于印度的移民企业家创立的。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有几乎一半的计算机相关的H-1B签证(给予符合当前美国经济需求的高技术工人)给了来自印度的工人。超过1/4的印度出生的受雇者工作在信息技术领域,有1/3的印度出生的女性工作在商业、管理和信息技术领域。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移民开始多样化,其中已经在美国的家庭成员的亲属来美的人数也在增加。1991年,44 121名印度移民中,有35 000人在美国已有家庭成员。不像那些有高学位的人能找到白领工作,这些工人阶级移民通常没有大学学位,只能在小杂货店、加油站或汽车旅馆里辛勤劳作。事实上,由印度人开设的汽车旅馆约占美国的一半。这些汽车旅馆的所有者通常来自古吉拉特邦(Gujarat),这是印度西部的一个邦,他们来自巴克他(Bhakta)和帕特尔(Patel)的农村地主家庭。很多人有已经在美国的专业移民亲属,并已经将资金投入到他们的汽车旅馆中以保障经济安全和居住之所。很多这些成功的企业依赖于无须付工资的家庭移民女性在日常的家务劳作之外来清洁房间、做家务、接待和从事办公室的工作。一个家庭旅馆所有者的妻子告诉采访者说:“我大概在早晨五点半起床,为家人做早餐并为两个孩子准备好上学。如果有客人,我会为他登记。孩子们上学后我清洁房间……铺床,洗好衣物……并整理房间。”一些汽车旅馆的印度人所有者,移民美国时资金不多,后在经济上获得了成功。但是他们仍高度边缘化于主流社会。
正如最近印度移民中的阶级分化一样,男性和女性移民的机会也不同。2012年7月,印度报纸《印度人报》( The Hindu)发表了一篇揭露印度女性在美国面对“梦想破裂之海”的文章。很多人都凭她们自己的实力获得了高等专业教育的文化水平,但却作为工作在持续扩展的IT企业、拿着H-1B签证丈夫的配偶,只能拿H-4签证。受签证的限制她们不能工作,这些曾经能够自立并发展自己事业的职业女性,发现自己在美国孤独、绝望,没有方向。拉什·巴特纳格尔(Rashi Bhatnagar)是一名在印度有硕士学历,且事业成功多年的H-4签证拥有者,她发现来到美国与从事IT工作的丈夫团聚后只能窝在家里。她建立了一个脸书(Facebook)群体,起名为“H-4签证,一个诅咒”。
2010年的美国人口普查显示,总共有超过173万印裔美国人,他们是20世纪90年代增长最快的亚裔美国人群体。在更多工薪阶层的家庭成员加入已经在美的家人的同时,他们也在语言、宗教,尤其在阶级分层方面越来越多元化。这些印裔美国人在全美定居,但其聚居区之一,或称小印度,是位于纽约的杰克逊高地(Jackson Heights)。
来自巴基斯坦、孟加拉和斯里兰卡的移民,也在20世纪90年代后逐渐增长,大部分新来者通过家属移民而来。20世纪90年代,巴基斯坦裔美国人至少增长了88%。超过13.4万移民在1990年至2000年间进入美国。超过7万名孟加拉人在同一时期来到美国。2010年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已有超过40.9万名巴基斯坦人和14.7万名孟加拉人身在美国。
很多巴基斯坦移民,是作为更大的全球范围内巴基斯坦移民群体中的一部分而来到美国的。人类学家朱娜德·拉那(Junard Rana)发现,他们的移民梦滋生于已在外国的亲朋的口耳相传、巴基斯坦电视剧和好莱坞电影之中。最大的群体作为建筑劳工去往了中东。这些“迪拜查娄”(Dubai chalo)工人阶级移民与工作在美国、加拿大或欧洲的受过职业教育的“阿美利坎”(Amrikan)巴基斯坦移民不同。新兴的移民群体如孟加拉人和斯里兰卡人在人数上虽然不多,但其影响力却在增加。同样聚居于纽约,这里的7.4万名孟加拉人是该城第11大外国出生人口群体,而在斯塔顿岛的5 000名斯里兰卡人是斯里兰卡之外最大的斯里兰卡人聚集区。
自1965年起,朝鲜移民(绝大部分来自南部)来到美国的人数也猛然上涨。197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美国有70 598人具有朝鲜血统。20年后,统计人口几乎达到80万,而在2010年,朝鲜裔人口已接近126万。几乎80%都是在外国出生,而67%的朝鲜人是美国公民。这种移民的快速增长,原因在于韩国的政治不稳定与经济混乱。冷战期间,美国大规模投资韩国经济以助其遏制社会主义。朴正熙的军事独裁统治发起加速工业化的计划,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韩国作为亚洲“四小龙”(还包括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之一为人所知。这一快速的工业化扩张带来大量的工业劳动力,但是也要付出一些代价:低工资、政府镇压劳工起义,以及韩国工人阶层的收入高度不平等,大量农村到城市的移民与增加的人口密度。急速的人口增长也加重了这一问题。从1960年到1975年,韩国人口从2 500万增加到3 500万。随着改变社会经济机会的减少,越来越多中产阶级韩国人考虑移居海外。韩国政府也将其作为控制人口的计划而积极推动海外移民。
同早期去往美国的那一拨移民一样,新来者中也有男有女,而且趋向于家庭移民。大部分人很快成为归化公民。专家和学生是最初韩国移民的主体,包括物理学家、护士、药剂师和牙科医生。但是就像最近的菲律宾移民一样,一旦到了美国,他们就无法保证总能找到对口的工作。在韩国获得的职业证书,在美国也并不是总能通用,而移民们又受其英语不流利所困。例如,1983年移民美国的韩国工程师韩哲宏(Han Chol Hong),就很难找到工作。当他离开工程领域后,进入一所管道和焊接学校学习,但无法找到工作。他取得粉刷房子的资格证,但仍在找工作上存在困难。最后他不得不看守大门以维持生计。
作为他们职业地位下滑的一个结果,很多韩国移民比如韩哲宏将他们和其他韩国人的资产投入一种被称为“金”(kae)的信用评价系统来开展自己的生意。韩国人聚集在美国内城区并接管了之前掌握在老犹太人、意大利人和希腊人移民及其第二代家庭手里的食品商店和小商业的所有权。当一个朋友告诉韩哲宏,在洛杉矶中南区有一家食品杂货店要出售后,他和他的家人买下它,并成为很多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城市里经营小商业的韩国移民企业家之一。每天早晨5点起床进货,随后韩哲宏让商店“从早8点到晚8点,一周7天,每年365天”营业。他解释说,他很少歇业。韩哲宏承认:“做这一行需要艰苦工作,但我是自己的老板……没人能对我颐指气使。”
韩国移民的高峰期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那时候很多到来的移民有家庭成员已经在美国生活。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韩国的生活水平和民主化进程有所改进后,去往美国的移民数量也随之下降。但韩裔美国人仍然充满活力。1997年,美国有近13.6万家工商企业为韩国人所有。到2010年,超过一半的韩裔美国人有学士学位,而全美平均水平只有28%。但是和华裔美国人一样,韩国人也分布在经济阶梯的两端。总的来说,他们比美国人拥有更高的个人平均收入中位数,但同时他们也有更高的贫困率。
就在新的亚洲移民来到美国的同一时期,另一个同样巨大的变化在亚裔美国群体之中发生。不同的亚裔美国人积极分子开始联合起来以获取认可、政治权利和平等。他们展望着一个新的亚裔美国和一个新的美国。
一些积极分子在“二战”结束后,立即跨越种族界线开始为平等而战。例如,日裔美国人和非裔美国人团结在一起,挑战洛杉矶附近如克伦肖(Crenshaw)这些只允许白人居住的社区。这种不同种族间的结盟,有助于城市公民权利的推进,并为随后数年跨种族行动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在20世纪60和70年代,新一代积极分子成长起来,并在母国和海外扩大了早先数代人对抗种族主义和不平等的斗争。他们是更大的社会公平运动的一部分,改变了美国社会与政治,同时也为特殊的亚裔美国人事业组织活动。
尤里·河内山(Yuri Kochiyama)、菲利普·维拉·克鲁兹(Philip Vera Cruz)和格蕾丝·李·博格斯(Grace Lee Boggs)是部分从非裔美国人民权运动或农业工人运动开始其事业的人。作为日裔移民的尤里·河内山,于1921年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她同其他日裔美国人一起被监禁在阿肯色州的杰罗姆集中营。战争结束后,她回到加利福尼亚州继续承受着反日情绪。每天晚上,都有人在她做服务员工作时叫她“日本鬼子”(Jap),更甚者会将装有热咖啡的杯子扔向她。她很快同丈夫比尔一起搬去纽约,就是在那些日子里,尤里·河内山遇见了黛西·贝茨(Daisy Bates),她是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小石城分会的主席,曾指导小石城的9个人在他们学校展开废除种族隔离的运动。尤里·河内山解释说:“就在我遇见黛西·贝茨之后,我开始对民权运动产生强烈的兴趣。我一直关注着报纸上关于整个南方爆发的民众骚动和示威活动。”这一新的意识为河内山家一个重要的时期打下基础。她回忆说:“人们在为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奋斗,我开始意识到我也需要为自己的权利而战斗。”后来,尤里·河内山成了一名社区的组织者,马尔科姆·埃克斯(Malcolm X)的一个亲密伙伴,是新兴的东海岸亚裔美国人运动与正在进行的民权运动的重要连接力量。她用自己的声音和能量从事多种运动,包括抗议美国在亚洲的帝国主义,支持纽约学校的族裔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她和比尔在战时安置和平民拘留委员会做证。晚年时,她在2001年9月11日后仍活跃于释放政治犯和结束种族压迫的活动中。
另一个早期的亚裔美国人活动家是菲利普·维拉·克鲁兹。克鲁兹是20世纪早期最早一波来美国的菲律宾人之一,他在明尼苏达州和华盛顿的农场、罐头工厂和餐厅里工作长达30年之久。当他于20世纪50年代移居到加利福尼亚州后,他开始投身于菲律宾劳工运动,并帮助农业工人组织委员会(Agricultural Workers Organizing Committee)组织了一系列有效的罢工和联合抵制运动,并在1965年让德拉诺(Delano)的葡萄工业瘫痪。这些行动推动农场工人联合会(United Farm Workers)的形成,这一联合会将菲律宾农场劳工与其他族裔群体联合起来,包括墨西哥人。维拉·克鲁兹在奇卡诺人凯萨·查维斯(Cesár Chávez)手下担任农场工人联合会副主席一直到1977年。在晚年,他通过基层组织以其对劳动人民的权利的热心,以及献身民主和团结一致的信念,教育了新一代活动家。
同克鲁兹和河内山一样,格蕾丝·李·博格斯也在20世纪60年代对社会正义运动积极起来。1915年博格斯出生于一个中国移民家庭,在罗得岛的普罗维登斯长大。她考上了巴纳德学院,随后又进入布林莫尔学院就读,1940年她在那里取得博士学位。由于无法在学术界找到工作,她移居芝加哥,在那里加入非裔美国人民权运动,同西印度马克思主义者C. L. R. 詹姆斯共事。她被非裔美国人争取民权的斗争所激励,特别是劳工领袖A. 菲利普·兰多夫(A. Philip Randolph)于20世纪40年代成功地在美国国防工业确立平等的招聘实践。博格斯回忆道:“当我看到一次运动的成就,我就对自己说:‘伙计,这就是我一生想要做的事情。’”她与非裔美国人活动家詹姆斯·博格斯结婚,并于1953年搬去底特律。这对夫妻并肩作战数十载,在20世纪末的很多社会以及她所称的“人性化”运动中起到关键作用,包括民权、黑人权力、劳工问题、妇女权利、反战活动、环境问题和亚裔美国人权利等。格蕾丝·李·博格斯在90多岁时,出版了一本自传和一本论文集,仍在表达她的坚定信念和思想的力量,她希望能成立组织以建设21世纪的美国,一个所有“民族和种族和谐地生活在一起”的国度。
就像博格斯、克鲁兹和河内山一样,越来越多的亚裔美国人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推动激进的亚裔美国人政治进入新纪元。受公民权利、黑人权利和反战运动的激励,同时还受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如中国的毛泽东、北越的胡志明、朝鲜的金正日、阿根廷的切·格拉瓦(Che Guevara)、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和阿尔及利亚的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的影响,这些新的活动家呼吁所有亚裔美国人以及其他有色人种的联合,呼吁经济正义、社区服务和以亚裔美国人为中心的教育和艺术。他们拒绝被贴上“东方人”这一在美国十分流行的标签,同样拒绝“模范少数族裔”这一专注于合作与同化的刻板印象。取而代之的是,他们自称为亚裔美国人,一种强调所有亚洲移民和族裔社会的泛族裔(pan-ethnic)认同。他们“试图通过建立跨种族联盟和跨国团结来实现激进的社会变革”,据历史学家达里尔·梅达(Daryl Maeda)的研究,他们致力于终结美国和美国之外的压迫。政治、文化和社区组织的建立,最终让亚裔美国人在美国政治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使其声音有所体现。
大部分活动家都是从其他的社会运动中开始的。亚裔美国人参与了南方的民权运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言论自由运动和20世纪60年代的反越战运动。但是现存的亚裔美国人组织没有一个集中关注亚裔美国人自身的特殊问题。就像活动家家市冈裕次(Yuji Ichioka)所回忆的,他们“有太多亚洲人在政治示威中,但没有任何效果。每个人都在更大的集会中迷失了”。他和他的搭档艾玛·吉(Emma Gee)认为,如果亚裔美国人能够联合在一杆“亚裔美国人的旗帜”下,他们将能获得更大的影响力。与其他社会活动家一起,家市冈和吉于1968年5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组建了亚裔美国人政治联盟(Asian American Political Alliance)。正如家市冈所说,该组织明确将几代来自不同族裔和阶层背景的亚裔美国男女联合起来,成为第一个使用“亚裔美国人”一词来“代表我们所有有亚洲血统的美国人”的社会组织。
亚裔美国人政治联盟关注三个目标,这有助于明确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广泛的亚裔美国人运动。第一,亚裔美国人政治联盟致力于无视族裔和其他区别而将所有亚洲人视为一个政治群体。其早期的文件之一描述了组织的目标,亚裔美国人政治联盟在开始描述每一个目标之前,都以共同的短语“我们,亚裔美国人”(We Asian Americans)开始。第二,亚裔美国人政治联盟明确地批判美国是一个种族主义、帝国主义,以及剥削的社会。反对“模范少数族裔”所预设的亚裔美国人不是美国种族主义受害者的形象,亚裔美国人政治联盟宣称,“亚裔美国人长期被主流种族主义者剥削和压迫”。第三,亚裔美国人政治联盟坚守其同其他国内外“第三世界公民”跨种族联合的承诺,并保证它“支持所有被压迫的人民及其解放而进行的斗争”。自认为是美国第三世界的一部分,亚裔美国人同其他非白人群体,包括非裔美国人、奇卡诺人、波多黎各人和美国原住民联合起来,这些群体同样受到类似的种族压迫和经济剥削。亚裔美国人政治联盟强烈反对美国的帝国主义,尤其批评越南战争。
伯克利亚裔美国人政治联盟的历史不长,在1969年末就解散了。然而它对推动洛杉矶、纽约和夏威夷类似组织的建立帮助很大,如纽约的“亚裔美国人行动会”(Asian American for Action)和“义和拳”(I Wor Kuen),这是同“黑人权利”运动结盟的最大的亚裔美国人革命组织。他们和其他组织共同帮助形成新的亚裔美国人意识,并推动创建新组织来表达亚裔美国人的不同需求,为这一不断增长的共同体发声。
一些最早的活动发生在大学校园。1968年,亚裔美国人政治联盟在旧金山州立大学与第三世界解放前沿(Third World Liberation Front,TWLF)的奇卡诺人、土著美国人和非裔美国人学生联合起来,该组织认为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是美国内外有色人种遭受压迫的根源。第三世界解放前沿要求教学课程和计划需反映有色人种的历史、需求和经验,1968年11月6日,该组织在旧金山州立大学校园内发起一次罢课。这些学生领袖得到来自民权运动组织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tudent Nonviolent Coordrnating Committee,SNCC)前任主席斯托克利·卡迈克尔(Stokely Carmichael)的支持与帮助。他呼吁学生夺取权利为“真正的控制”而战。其后发生了抗议、示威、静坐和占领大楼,超过700名学生在随后5个月里被捕。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校园同样淹没在激进主义之中。非裔美国人、奇卡诺人、亚裔美国人和美国原住民学生群体对校园管理有类似的不满,认为缺少与他们相关的课程和项目。伯克利第三世界解放前沿组织起来,以表示跨种族的团结,并于1969年1月22日发起一场被达里尔·梅达称为“教育中的自决”(self-determination in education)的活动。随后3个月里,学生反对者和他们的盟友肩并肩对抗封锁校园道路的警察,还在校园各处拉起反对条幅。警察使用直升机和催泪弹对示威者予以反击。被捕的人成倍增加,警察与反对者的冲突非常激烈,以至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罗纳德·里根威胁说要实施戒严,并派遣国民警卫队进驻伯克利校园。
1969年3月,旧金山州立大学和伯克利大学的校园示威都在几天内落幕。旧金山州立大学的罢课因创设国内第一个族裔研究院而达到高潮。在伯克利,一个族裔研究学系也得以建立。不日之后,类似的努力在美国高等学校的校园里传播开来,并扩展到社区,进入主流文化和主流政治。起源于大学校园的活动,最终激发了整整一代人自觉表达声音并寻求改变。
图41.第三世界解放前沿罢课支持者们聚集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萨瑟门前,1969年1月28日。
亚裔美国人活动家在校园的斗争,与以社区为基础的活动家争取“为人民服务”项目以给穷人和工薪阶层的亚裔美国人提供廉价住房、社会服务、医疗保健和劳工权利的影响类似。城市和乡村的运动在全国范围涌现。这些活动中最重要的行动之一是拯救国际旅店(International Hotel)的运动,这是一幢位于旧金山中国城和马尼拉城边缘的单间出租建筑,那里居住着年老的菲律宾裔和华裔工薪阶层。
当旅店老板在1969年威胁要驱逐居住者时,社区活动家们团结起来租下这一建筑,对之进行修缮,并为房客们带来亚裔美国人商品和文化艺术组织。三年后,旅店又一次发出威胁,而一个联合亚裔美国人群体、学生和租客的组织再次起来对抗驱逐。尽管他们竭尽所能,驱逐计划还是得以执行。1977年8月3日,驱逐日最后一晚,200名活动家聚集在旅馆内予以阻止,同时2 000名支持者包围了旅店,形成一堵人墙,重复地喊着“停止驱逐!我们哪儿也不去”,并唱着民权运动抗议歌曲。第二天凌晨,250名全副武装的警察开始用棍棒殴打示威者。警长助理使用大锤和斧头破坏大门并将租客和示威者赶出房间。
图42.建立基于社区的医疗服务是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亚裔美国人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1973年中国城健康博览会,纽约。
守护国际旅店的行动失败了。长期租客被赶出门外而建筑也被夷为平地。然而,守护国际旅店行动激发了旧金山的中国城和日本城的其他廉租房行动。同样重要的是,它将来自不同代际、族裔、政治理念和阶级的支持者们团结到一起,动员起基础深厚的支持并成为不朽的遗产,诞生了新一代的政治活动家,并继续为他们的社区服务,且在随后的数十年里进入美国的主流政治。
就在他们努力满足每一个社区的居民的基本需求时,这些亚裔美国活动家也将自己视为一个更大的、全球范围内抵抗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一分子。他们通过宣称与受美帝国主义侵害的亚洲国家人民团结一致,来表达这种国际主义。而且他们激烈地反对越南战争。很多人相信,这场战争不过是美帝国主义在亚洲持续的最新进展。它曾导致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的爆炸,对冲绳的占领及朝鲜战争。亚裔美国人反战示威者打出写有“停止轰炸亚洲人民”和“停止杀害我们亚洲兄弟姐妹”的条幅,强调美国对国内亚裔和亚洲压迫的相似之处。
海湾地区亚洲人反战联盟(The Bay Area Asian Coalition Against War,BAACAW)声明,其目标是“建立一个亚洲人反对越南战争的稳固、广泛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并用“一方受难,八方支援”条幅将在美国受压迫的亚洲人与战争连成一体。一些活动家访问中国、北越和朝鲜,试图同亚洲的亚洲人建立联系,探索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是如何运转的。战争结束后,亚裔美国活动家继续为改变而努力。他们誓要“将抗争带回社区”,来帮助被忽视的穷人和工薪阶层的亚裔美国社区提供医疗和就业服务。
亚裔美国人在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中的参与,使他们卷入了20世纪60、70年代其他的激进运动之中,包括妇女解放运动和同性恋解放运动。受一些男性活动家同人所表现出的沙文主义的影响,亚裔美国女性很快开始形成自己的组织,以在社区内外提倡性别平等。同其他民权运动中的女性活动家们一样,亚裔美国人女性活动家也在组织内承担着次要的、陪衬的角色。当男人们做出决定、发表演讲,作为组织的公共形象出现时,女性则被要求打印传单、简讯,做笔记,准备咖啡,甚至清洁厕所。亚裔美国人女性越来越意识到她们身上的“三重压迫”,即有色人种、女性和工人,她们开始组织起来在其社区内部寻求改变。
亚裔女性联盟(Asian Women United)和亚裔女性组织(Organization of Asian Women)等团体在20世纪60年代末以及70年代繁荣发展起来。大部分由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女性领导,这些组织致力于通过教育和服务项目提升女性的社会地位。但是还有难以数计的亚裔美国人女性活动家,如韩裔美国人、酒店业从业者银淑·佩里(Unsuk Perry),她作为联盟服务者经常为其韩裔工人们翻译,以确保他们明白自己所拥有的权利。还有住房活动家李昌兆(Lee Chang Jok),她在20世纪70、80年代不知疲倦地保护旧金山中国城低收入房客的权利。
类似于亚裔美国人女性参与女性解放运动源自她们处于其他社会正义运动的边缘一样,亚裔美国人同性恋、双性恋及跨性别(LGBT)激进主义者也从其他社会正义运动中发展起来。亚裔美国人同性恋、双性恋及跨性别者强烈感到他们被从大部分白人主流同性恋、双性恋及跨性别者的组织中排挤出来。另外,其他的解放运动,最多对同性恋、双性恋及跨性别者问题表示不屑,最糟的甚至是厌恶。活动家、作家和记者海伦·奇亚(Helen Zia)回忆起20世纪70年代在波士顿被其他亚裔美国人和黑人解放活动家们审讯的经历。奇亚说,在解放运动中“没有同性恋的一席之地。我还没有公开,而他们明确表示如果我公开了,将被迫离开解放团体。这种威胁让我在随后的几年里都保持沉默”。
图43.亚裔美国女性在更大的妇女解放运动中的积极表现。“认可妇女权利时代的一天,1977年8月27日。”
同其他肤色和盟友的同性恋、双性恋及跨性别者们一起,一场亚裔美国人中的同性恋、双性恋及跨性别者运动在1979年10月开展开来,当时有超过600名黑人、拉丁美人、美国原住民、亚洲人和白人,参加在华盛顿特区召开的第一届全国第三世界男女同性恋会议。同一周的周末,第一次争取男女同性恋权利的游行开始,参与者包括一个新成立的亚裔男女同性恋团体。活动家崔妮蒂·奥多纳(Trinity Ordona)称这次活动是“一项意义重大的亚裔男女同性恋运动”的诞生。另一组织——亚洲/太平洋男女同性恋(Asian/Pacific Lesbians and Gays,A/PLG)于1980年在洛杉矶成立,这是第一个代表该城亚裔男女同性恋权利的组织。这些组织和其他组织一道凸显了亚裔美国人同性恋、双性恋及跨性别者所面临的特殊问题,并让他们能够在亚裔美国人社区内外组织活动对抗反同性恋的人,为那些患有艾滋病的人或艾滋病毒携带者提供支持。
到21世纪初,亚裔美国人同性恋、双性恋及跨性别者已经不再是亚裔美国社区的边缘群体,相反,他们变得越来越活跃和凸显。他们致力于提升影响亚裔美国人和同性恋、双性恋及跨性别者群体相关问题的关注度和支持度,比如平等。亚裔美国人组织实际上在一些州已成为同性婚姻辩论的主角。奇亚解释说:“每个人都意识到他们是亚裔同性恋者和同性恋的亚洲人。”她与其伴侣也是加利福尼亚州最早同性结婚的情侣之一,“同性恋区域与亚裔人区域之间的空间也略有拓展”。
除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和社会正义运动之外,日裔美国人也开始渴望回顾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迫迁移和监禁的经历。正是吉永爱子(Aiko Herzig-Yoshinaga)在纽约参与反战和亚裔美国人运动的经历,触发了她重新看待自己作为日裔美国人在战争年代被对待的记忆。通过她自己参与亚裔美国人采取的活动,她开始思考并“回顾我们自己在战争年代的经历,它为什么发生,以及结果我们遭受了什么”。
20世纪70年代,对审查和追究战时不公正的支持开始增长,许多日裔美国人组织开始活动,以寻求官方道歉和美国政府对战时监禁的赔偿。日裔美国人社区内部在政治策略和监禁意义的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但不同团体最终在努力获得赔偿的基础上取得一致。多年辩护之后,这一运动开始越来越引人注目。1976年,总统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官方宣布,对日裔美国人在战争时期的驱逐和监禁是一个“悲剧”。总统承认:“我们现在知道——当时我们就应该知道的——不仅监禁是错误的,而且日裔美国人一直以来都是忠诚的美国公民。”
美国战时平民再安置和拘禁委员会(U.S. Commission on Wartime Relocation and Internment of Civilians)成立于1980年。第二年,国会在全国20个城市举行听证会。超过500名日裔美国人被取证。那是他们中的很多人第一次公开谈论其在战争时期的经历。1982年,委员会发布报告《被剥夺的个人正义》(Personal Justice Denied),包含听证会上集中营被关押者给出的证词,以及被吉永爱子和她的研究团队发现的证明日裔美国人没有叛国的重要政府文件。该报告在总结中对政府行为做了严厉责备:“9066号驱逐行政命令的颁布不是出于合理的军事需要。”恰恰相反,种族偏见、战争狂热和政治领导的失败导致这一令人震惊的政策。“对有日本血统的美国公民和居民造成严重的不公平,这些人没有任何个人被正规审查或抓住针对他们的可靠证据,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美国政府驱逐、转移和拘禁了。”
委员会建议通过一项国会两院联合决议,对驱逐和转移道歉,建立一个教育和人权基金,对每一个幸存者进行赔偿。1985年,南加利福尼亚的曼赞纳集中营被指定为美国国家历史名胜。同时,开始在法律上努力推进重新审议三个战时最高法院的案件(平林、安井和是松),他们因政府的战时行为而遭到制裁。1988年,美国国会通过《公民自由法》(Civil Liberties Act),由里根总统签署生效。这一法律以国家的名义对转移与监禁日裔美国人致歉,受9066号行政命令影响的每个幸存的日裔美国公民获得2万美元的赔偿,同时确立了教育和其他计划。
加拿大效仿美国政府,对日裔加拿大公民做了官方道歉和赔偿。为日裔拉美人争取赔偿的努力则需要更长时间。1996年,美国政府对被它的行动影响的日裔拉美人进行了官方致歉并提供少许补偿。然而,主张赔偿日裔美国人就等于鼓励他们的运动继续进行。
图44.在众人注目下,总统罗纳德·里根签署1988年《公民自由法》,在这一法律中,国家向战时被转移和监禁的日裔美国人道歉。1988年8月10日,华盛顿特区。
美国政府的赔偿,远远不足以补偿日裔美国人在战争期间所遭受的财务危机。这些赔偿也不能让日裔美国人在精神上恢复如初。然而,日裔美国人赔偿运动起了纠正历史不公正运动的先锋作用,通过创建持久的教育资源以帮助防止过去错误的重现,就像议员丹尼尔·井上(Daniel Inouye)所解释的,这是帮助美国的“民主观念更趋完美”。活动家梶原仁司(Hitoshi H. Kajihara)也补充说:“我们书写了美国历史中的一页。” 美国百年困局与当下危机(套装共10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