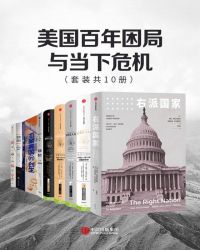14.跨国移民与全球美国人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美国百年困局与当下危机(套装共10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14.跨国移民与全球美国人
迪帕·帕特尔(Dipa Patel)和她的丈夫普拉提克(Pratik)发现自己同时扎根于美国和印度。普拉提克在印度古吉拉特邦的一个小镇长大,后到美国,获得计算机科学学位,并和他的表兄弟们开了一所计算机学校。他搬到美国后,在波士顿地区一家大型电信公司的装配线上找到一份工作。晚上,他在波士顿大学攻读硕士学位。迪帕是一家计算机制造公司的质保主管。在美国待了5年之后,普拉提克和迪帕申请了美国公民身份。他们两个年幼的女儿正在学习美国童谣,最近帕特尔一家在新罕布什尔州南部的郊区买了自己的房子。从表面上看,帕特尔一家正生活在“美国梦”之中。
但正如社会学家佩吉·莱维特(Peggy Levi)所展示的那样,像帕特尔这样的家庭同时也在追求“印度梦”。普拉提克和迪帕定期寄钱回家,支持他们在古吉拉特邦已退休的父母。普拉提克捐助他的家乡创建计算机学校,除了支付他们在新罕布什尔新房子的按揭贷款,还翻修了在波德里(Bodeli)的家,现在有了一幢新的带有西式浴室的两层小楼。他们与家乡古吉拉特邦保持联系的另一种方式是通过宗教。他们每个周末都在位于马萨诸塞州洛厄尔(Lowell)的印度教寺庙做礼拜,它属于印度古吉拉特邦的一个印度教教派,并与世界各地的教徒保持着联系。
迪帕和普拉提克的跨国生活是通过他们在美国的社会经济成就,以及他们与印度家庭的亲密关系和强大的古吉拉特身份认同而得以实现的。美国和印度政府都没有试图限制这种跨国活动。认识到海外印度人在印度经济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印度政府非常努力地促进这些联系。从2003年开始,印度批准了在美国和英国的印度人的双重国籍。
迪帕和普拉提克突出了最近美国亚洲移民最具决定性的特征之一——跨国本质。就像横渡太平洋的轮船往来对19世纪后期来自亚洲的移民产生了革命性影响一样,最近交通和通信技术的进步,如更频繁和更便宜的航空旅行、电子邮件、手机、社交媒体也同样改变了人们迁移的方式,以及今天他们的跨国界生活。
当代移民作为新全球模式的一部分,在这种模式下,人们在世界各地迁徙,有时在他们的一生中,为了寻找更好的生活,为自己和家人寻找更好的生活,他们会迁徙多个地方。有时,迁徙只是暂时的;有时则是永久性的;还有的时候,迁徙则是循环的,人们回到他们出生的土地或者其祖先出生的土地。在20世纪晚期和21世纪初,亚洲移民实践了所有这些移民模式:正在进行的跨太平洋跨国移民,美洲大陆内部的再移民,甚至“返回”亚洲的移民。他们正在铺设新的“成为美国人”的道路,并通过弄清楚如何置身于一个变化中的世界而让自己具有“全球性”。
并非所有移民都是跨国的,而且跨国生活也不是没有风险或意外的后果。阶级地位、性别、教育和收入是重要的影响因素。美国的国际关系和对国家安全的关切也允许某些类型的移民跨国主义存在,甚至被鼓励,而其他移民的跨国活动——特别是那些与恐怖活动嫌疑分子有关的人——被视为威胁。但是,尽管存在持续的不平等,一些人在“此处”和“彼处”之间找到平衡,同时不排斥一个族裔或一个国家的身份认同。这影响到我们所有人。最近移民和他们的孩子在美国的比例越来越大。(2011年,他们占总人口的18%。)随着全球化带来的各种可能和挑战,美国人与更大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因此,了解跨国移民的经验,就是了解在全球化时代成为美国人意味着什么。
在经济谱系的一端是亚洲人,他们是“灵活的公民”(exible citizens),这一术语被人类学家爱华·翁(Aihwa Ong)用来形容那些寻找最佳投资、工作和居住地的精英移民。翁写道:“灵活积累的新策略,促进了对公民身份的灵活态度。”但对政治不确定性的真正担忧也是如此。20世纪90年代,中国香港有10%的居民(约60万)持有外国护照,以之作为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之后的保障。在英国经济实力下降和亚洲资本主义崛起之间,但不确定中国大陆对香港的治理会是什么样子,许多人都在寻找海外避风港。
一些国家的政府迅速采取措施,以方便这些人的入境。例如,带着大量资本的移民投资者可以进入美国和加拿大。在1983年至1996年间,约有70万中国企业家移民给加拿大带来了数十亿美元的投资。他们与来自印度、菲律宾、中国香港、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和中国台湾的其他亚洲移民一起,帮助重振了一个“连接全球的太平洋加拿大”,其贸易流动以及社会、文化和政治联系日益将加拿大转向太平洋。在美国,移民投资者(EB-5)签证计划,给予在美国投资50万或100万美元并创造或保留至少10个美国就业岗位的外国公民永久合法居住权。作为1990年移民法的一部分,移民投资者计划直到最近才引起人们的兴趣:现在,亚洲的移民投资者,尤其是来自中国的投资者,几乎已经把每年发放给投资者和他们直系亲属的1万张签证的上限给用掉了。
全球化和新的移民法也造就了新型的“太平洋往返”旅居者。19世纪晚期,离开家乡到美国餐馆或洗衣店艰苦工作的中国农民已经被取代。现在,有一位“空中飞人”父亲,他的妻子和孩子们移居美国以获得居住权,他则穿梭在太平洋的上空。
这些新的灵活家庭关系——完整的家庭分开——通常会与日常的现实相冲突,这些现实挑战着先前的安排、期望、家庭和性别角色。一些婚姻结束。一些亲子关系遭受了痛苦的考验,家庭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中国的妻子被送到美国来管理郊区的住宅和生活,而她们的丈夫在世界各地旅行,她们常自嘲为“寡妇”。加州硅谷的其他女性已经成为成功的企业家,她们把自己多年的生活和养育子女经验用于利润丰厚的房地产事业,帮助其他新抵达的空中家庭融入他们的新生活。
另一群新来的亚洲移民是“降落伞儿童”(parachute kids),他们独自生活在美国,或与照顾者和亲戚在一起,进入小学、初中和高中。在一群年龄从8岁到17岁高度选择的年轻人中,这些孩子的父母要么是在太平洋穿梭,要么是全职留在亚洲。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降落伞儿童”的父母主要来自中国台湾,大部分居住在南加州,但也有来自中国香港、中国大陆、印度、韩国和菲律宾的降落伞儿童。
国际学生一直是美国重要的亚洲移民群体。但是,亚洲和美国的一些新情况已经产生了一种年轻的学生,他们的家庭试图同时在两个社会生活。例如,在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境内的竞争教育环境下,一些“降落伞儿童”为了更好地进入美国著名高等学府,并在亚洲或美国获得好工作,都在寻求大学前的美国教育。任何一种选择都是可以接受的,而且人们认为,任何未来的决定都将基于战略上对孩子及他们家庭的改善。社会学家周敏(Min Zhou)写道:“空降到美国的降落伞儿童不仅满足了家庭的教育目标,而且是未来投资的一种实用方式。”
全球化和新的移民模式也造就了新一代的“跨国母亲”。在中国大陆的“空中父亲”和中国台湾的“降落伞儿童”经济谱系的另一端,是这些移居国外工作的妇女,她们几乎总是在从事家政服务、教学或医疗保健方面的工作。许多菲律宾工人属于这一类。迫于国内经济不平等的压力,她们被迫出国,离开在菲律宾的家庭和孩子们,工作很长一段时间,然后把钱寄回去。她们的工资通常是家庭的主要支柱。维姬·迪亚兹(Vicky Diaz)今年34岁,是五个孩子的母亲,在美国工作。在时间跨度长达9年的时间里,她与在菲律宾的丈夫及孩子们一共只待了3个月。她试图用物质上的东西——洗衣机、汽车、电视,还有财政支持——来弥补她的缺位。然而,这些伴随着毁灭性的心痛。她悲叹道:“我最难过的是,在他们童年的成长过程中,我不在他们身边。”她并不是个例。许多菲律宾女性(以及其他移民妇女)现在都是跨国母亲。
今天的跨国移民不仅通过移民和家庭模式跨越国界。他们也通过购买的物品(以及他们购买这些物品的地方),所收看的电影和电视节目,以及消费的新闻来实现跨国生活。跨国的生活不需要实际跨越国界,但可以通过文化和消费来实现。例如,在湾区的印度移民经常去印度的杂货店购买小扁豆、香料和其他对印度烹饪至关重要的配料。他们还购买从印度进口的各种消费品,如化妆品、音乐、宝莱坞电影、宗教偶像、服装和珠宝。人类学家普尔尼马·曼克卡尔(Purnima Mankekar)解释说,购买这些商品,可以唤起移民对家乡的记忆,让他们与印度保持联系。一位店主告诉曼克卡尔:“他们不仅是来这里买杂货的,而是为了整个过程。他们是来‘印度购物’。”这些商店还充当着重要的社区会议场所,提供有关工作、住房和学校的信息,以及最新的八卦消息。在这里,传统的性别角色和社区制裁也可以发挥作用。对于一些移民妇女来说,杂货店是控制她们的丈夫允许她们自己去的“安全”地方。
媒体是跨国移民相互联系,以及他们与故土联系的另一种方式。例如,为服务于越来越多的华裔美国人,中文媒体近年来经历了戏剧性增长。社会学家周敏在美国发现了至少200家中文媒体,其中包括报纸、电视和广播节目,以及在线交流。这些媒体机构的所有者要么是华裔美国人,要么是中国的跨国企业。在一些海外华人媒体公司的案例中,这些媒体报道的内容涵盖了当地华人社区的事件,故土(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以及世界各地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新闻。中文媒体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移民在与家乡保持联系的同时如何融入当地社会。例如,南加州的报纸通过分类广告、商业目录和新闻报道,提供有关就业、住房、教育、儿童保健、医疗保健、税收和移民的重要信息。电台节目提供关于洛杉矶湖人队季后赛、加州能源危机、好莱坞八卦,以及中美关系最新发展的中文报道。周敏解释说,“即便是对英语一窍不通,移民也会知道他们周围的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不管这些事是发生在大街上还是在世界的另一边。
就像前几代移民把钱寄回故土家庭、家乡、组织和政府一样,今天的移民在更大的规模上延续了这一趋势。这些国家的政府给予他们特殊的准入、特权和荣誉,以使移民通过有形的投资与他们的出生地联系在一起。例如,越南政府在1986年通过了一项名为“创新”(dôimói)的政策,以吸引外国资本,包括越南侨民的汇款进入该国。在20世纪90年代,越南人(即所谓的“临时旅居者”)每年向越南家庭寄回大约6亿~7亿美元的资金。
这是一个全球性现象。在美国的印度移民也同样保持着与母国紧密的跨国关联,印度裔美国人和印度政府都鼓励为母国项目提供资助。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印度的英文报纸《印度海外报》(India Abroad)经常几乎不加掩饰地呼吁在印度投资。印度政府通过赞助投资规划会议为之做出一些努力。这是一个聪明的策略。印度的海外人口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到20世纪90年代,印度裔美国人的数量和财富都在增长。1999年,印度政府开始推行特殊的移民证件,称为“印度血缘卡”(Persons of Indian Origin Cards),允许“非居民印度人”(non-resident Indians)在没有签证的情况下访问印度,拥有自己的财产,购买政府债券,并申请印度的大学。2000年,印度政府设立印度侨民高级委员会,以加强和促进海外印度人对发展和慈善项目的贡献。北美的印度人予以热情地回应。仅在2005年,印度就收到了270亿美元的汇款。非居民印度人已经成为印度的“新贵宾”(new VIPS)。
与北美的印度移民一样,菲律宾裔美国人“巴利克巴恩”(balikbayan),因为他们寄给家庭和家乡的汇款,而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菲律宾的民族英雄。2009年,《菲律宾每日问讯报》(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报道说,菲律宾裔美国人向菲律宾汇款80亿美元。因此,“巴利克巴恩”在“回家”期间享受各种福利待遇,比如减免机票、延长签证、减免税收,以及在到达马尼拉后优先的移民和海关服务。
菲律宾裔美国人现在与菲律宾联系在一起的是数千个跨国的家乡、地区、国家协会,以及专业和校友组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菲律宾裔美国人已经组建新的机构,明确侧重于菲律宾社区的直接投资和伙伴关系。在菲律宾移民专业人士的带领下,这些团体的目标范围广泛,他们关注的是学者乔伊斯·马里亚诺(Joyce Mariano)所称的“国土开发”和“移民捐赠”(diasporic giving)。菲律宾裔美国人医生、护士以及菲律宾裔美国青年志愿者的医疗任务也在进行。菲律宾裔美国人在菲律宾为慈善事业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慈善事业有多种目的。它允许菲律宾裔美国人为他们的祖国做出贡献。它还重申离散的菲律宾人作为英勇的“巴利克巴恩”的地位,帮助他们在美国和离散中定义自己,并使在美国出生的一代与菲律宾保持联系。
跨国亚洲人不满足于仅仅为亲戚、家乡或国家政府提供资金。就像前几代人一样,他们也积极地影响母国的社会和政治变化。同样,印度裔和菲律宾裔社区也提供了有益的例子。在美国,第一个印度妇女组织成立是为了帮助移民妇女适应美国社会。到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像新泽西州的“马纳威”(Manavi)这样的组织,把重点放在其社区的家庭暴力和印度妇女等问题上。新一代的南亚女权主义者开始形成具有地方性和国际性的组织,并且超越国家和宗教的身份。和早期移民一样,一些印度裔美国人认为他们参与印度政治是在母国和移入国的生活和身份的反映。2014年,当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访问美国时,有3万人涌进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Madison Square Garden)参加一个项目,该项目突显印度总理和印度裔美国人的成就,如第一位印度裔美国小姐尼娜·达乌利(Nina Davuluri)。印度裔美国人马妮莎·维尔马(Manisha Verma)解释说,莫迪的访问和他在美国受到的摇滚巨星般的对待,“给印度带来了改变的希望,这将帮助印度人在美国拥有更好的自尊和形象”。
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在美国的一些菲律宾人组织,如“自由团体”(Kalayaan),纽约的“民主菲律宾支持委员会”(Support Committee for a Democratic Philippines),以及芝加哥的“民族主义菲律宾人协会”(Samahan ng Makabayang Pilipino),它们的政治活动都集中在菲律宾。当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于1972年9月21日宣布戒严令时,这些组织准备做出回应。费迪南德·马科斯暂停民主治理,其政府实施大规模逮捕平民的行动。据报道,数百名持不同政见者被拷打,还有许多人逃到国外,主要是逃往美国。
马科斯的行径激励了新一代积极分子,他们致力于在菲律宾和美国创造变革,卡罗尔·奥杰丹—金布罗(Carol Ojeda-Kimbrough)就是其中一个。她是一名菲律宾医科学生,在实施戒严令时,加入一群参与组织马尼拉城市贫民的社区活动人士。随着马科斯政府的政治镇压的继续,军方官员开始走访金布罗的家,并询问她其他活动人士的下落。由于害怕被逮捕,她投奔了其在美国的父母。在洛杉矶,她开始参加反戒严联盟的会议,并加入“民主菲律宾联盟”(Katipunan ngmga Demokratikong Pilipino),该组织实施了一项跨越太平洋的“双面”(two-sided)政治计划。对于奥杰丹—金布罗来说,她在美国居住并没有影响她对菲律宾的承诺。她继续其反马科斯激进主义,并开始着手从事影响菲律宾裔美国人的问题。1986年,美国政府放弃对马科斯政府的支持,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菲律宾人在美国的积极行动。
除了跨越太平洋的高度跨国,当代亚洲移民在美洲内部也具有跨国性。以美国华裔巴西移民贝莱莎·李(Beleza Li)为例。她在接受采访时说:“我的家族史是一个永不停止寻找更好机会的历史,无论是在中国、巴西还是美国。”这个家族的移民史是在贝莱莎的祖姑母在20世纪50年代移民到美国开始的,她在旧金山一家血汗工厂工作时,把钱寄回了留在中国的家庭。贝莱莎的祖父用这些资金于1961年移民到巴西,并开了一家咖啡馆。他花了20年的时间才把妻子和儿子带过来,但他们一到巴西,全家很快就适应了。贝莱莎回忆道,即使祖母不停地在工厂里工作16个小时,“巴西仍旧像地球上的天堂”。但在2002年,这个家庭搬到了美国。“他们相信‘美国梦’是终极梦想。”她解释说。
李的一家并不是唯一的例子。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巴拿马的华裔中产阶级和精英阶层就把出国留学看作是获得流利英语,获取美国名校学位,并可能获得美国国籍的重要途径。此后,巴拿马和美国之间的跨国家庭和循环移民变得司空见惯。
在秘鲁和古巴,中国人也为了躲避政治动荡向北迁移。当胡安·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Juan Velasco Alvarado)将军在l968年从费尔南多·贝朗德(Fernando Belaunde)总统手中夺取政权,并没收许多中国人从事的农业地产和工业企业时,大量的秘鲁华人离开秘鲁前往美国和加拿大。同样,当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革命政府将私人商业收归国有,并威胁到许多拥有小商店和餐馆的华裔古巴人的生计时,古巴华人逃到迈阿密、纽约、多伦多、马德里和其他地方。到20世纪60和70年代,成千上万的华裔古巴人和古巴人一起逃往美国。
拉丁美洲的南亚人和韩国人也因为经济原因,沿着一条向北的道路移民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南亚人从加勒比海、圭亚那和苏里南迁移到美国。2000年,仅在纽约市就有15万~25万名印度加勒比人。他们融合了英国殖民者、加勒比海和印度的身份,以经营小型企业而闻名,这些小企业反映了他们混合的传统,比如食品卡车和餐馆,提供烤鸡、烤肉和木豆。
有相当数量来自拉丁美洲的韩国移民也在20世纪90年代来到美国。在阿根廷,游击战和高通胀让一些家庭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迁离。巴西的高通胀和经济不确定性同样导致巴西人,包括韩裔巴西人,在20世纪90年代初移居美国。1999年对洛杉矶韩裔社区的一项调查估计,有10%或2万~3万人是来自南美的二次移民。大多数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移民到巴西或阿根廷,在来美国之前在那里生活了15~20年。
来自拉丁美洲的亚洲移民对创造新的社区和身份认同提供了很大帮助。在洛杉矶,这些亚裔拉美裔人可以从高度集中的多种语言服务中汲取这种认同,并表达他们的“拉美特性”,以表达他们对亚洲和拉美遗产的敬意。日本裔秘鲁人的餐馆,韩国裔巴西人的协会,以及华裔巴西人教会都将社区成员聚集在一起。在纽约,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拉美裔华人或华裔古巴人的餐馆一直为来自古巴的华人移民提供服务。这些餐厅为不同的顾客提供古巴和华裔美国人美食,并将中国、拉丁美洲和美国的文化融合在一起。在阿根廷长大的韩裔,二次移民到美国后,在与美国的亚裔和拉美裔移民的合作中既使用西班牙语也使用韩语。为了重建他们作为韩国人、拉丁美洲人和美国人的身份认同,这些移民在国家和社区之间来回穿梭,创造新的离散文化,同时重新定义了种族和民族身份认同。
除了拉丁美洲的亚裔移民,亚裔和拉丁美洲人之间的异族通婚率也在不断上升,这也造就了一个日益壮大的混血亚裔族群。根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居住在美国的亚洲和拉美混血的美国人有40多万。正如历史学家罗伯特·罗梅罗(Robert Chao Romero)所解释的,这些奇诺奇卡诺人(Chino Chicanos)正处在锻造自己独特身份认同的过程中,这种身份认同来自他们的亚洲、拉丁美洲和美国的经验。
就像最近亚洲移民到美洲以及美洲地区内部移民,作为20世纪晚期和21世纪早期全球趋势的重要指标一样,新的亚洲“回归”移民的增加亦是如此。在新的全球高技能工人和企业家的竞争中,美国不再是许多潜在移民的首选目的地。特别是亚洲及其强大的经济体正把人们拉回自己的家园。故土征聘政策吸引人们到中国台湾、韩国、印度和中国大陆。在某些情况下,早先来到美国的亚洲移民的子女甚至孙辈,选择“回归”他们祖先的故国,寻求经济和其他机会。由于这些新移民中的许多人有时离开他们的祖籍国一到两代的人,而且通常不会说当地的语言,这种返回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返回故土,而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回归。
日裔拉丁美洲人是第一批返回亚洲的人。在20世纪80和90年代,日本蓬勃发展的经济吸引了拉丁美洲的日本人来做临时劳工,从事大多数土生土长的日本人所拒绝的“3K工作”:kitanai(肮脏),kitsui(艰辛),kiken(危险)。1990年,日本政府改革移民法,为在国外的日本国民以及日本移民的子女和孙辈创造新的“长期居住”状态。第二年,83 875名日本裔巴西人进入日本。到1996年,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的日本人社区建立起稳固的移民文化。
中国和印度在21世纪早期的快速发展,为归国移民及其后代提供了更多的经济机会。在美国或加拿大留学的中国和印度学生在获得学位后越来越多地返回母国。在美国出生和长大的印度裔美国人也越来越多地生活和工作在他们的父母几十年前就已经离开的国家。正如2003年移居印度的印度裔美国人安纳德·吉里德哈拉达斯(Anand Giridharadas)所解释的那样,“随着西方经济的动荡和就业的困难”,移民的第二代子女正在越来越多地探寻母国的机遇。他继续说,移居印度的想法“在移民家庭中传播开来”。
中国移民,尤其是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士,也正在返回中国,以利用中国强劲的经济。中国政府以住房保障和在大小城市出现的新商业园区中的优惠承诺吸引他们。这些海归像中国的“空中飞人”一样,拥有多重护照,他们也寻求未来最大化的选择。他们确保入籍美国是在美国扎根的一种方式,同时也利用美国的其他特权。美国公民的身份,包括更多的国际流动性,以及在全球劳动力市场上的优势,这些地方通常付给美国公民更高的工资。
在寻找经济机会的过程中,移民和他们的后代回到亚洲,而另一组人则前往他们出生的国家寻找根源,并在某些情况下改变了最初促使他们国际迁移的体制。学者金·帕克·尼尔森(Kim Park Nelson)估计,大约有四分之一的韩国被收养者会返回韩国一段时间,还有少部分返回韩国定居。韩国政府签发的特别签证和双重国籍的选择允许韩国被领养人在他们的出生国享有特殊权利。韩国被收养的作家兼活动人士简·琼·特恩卡(Jane Jeong Trenka)是这些返回者之一,他与其他国际领养的韩国人合作,对国际领养的过程和后果提出质疑,并为韩国被收养者提供支持。
在进一步全球化和大规模移民的这段时期,亚裔美国人也在形成新的离散族群。从1990年开始,在印度以外居住的印度裔人口和居住在中国以外的中国人的数量都翻了一番,分别达到1 400万和900万。韩国侨民是在日本殖民主义和朝鲜战争期间及之后的必然产物,包括生活在160个不同国家的大约570万韩国人。在美国和加拿大,有越南人家庭分散在边境的两侧,以及法国和越南。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巴西的日本人后代有620 370人;美国有760 370人;秘鲁有55 472人;加拿大有55 111人;阿根廷有29 262人;墨西哥有14 725人;巴拉圭有6 054人。
在这些离散族群中,有新的身份认同和组织将这些社区与他们的亚洲家园以及美洲的其他地区联系起来。这些并不是新现象,而是几个世纪以来确立的模式。全球化加剧了世界各地的移民和跨国身份认同、共同体以及全世界亚洲人后裔的行动主义。移民们已经和他们社区、州和国家之外的其他亚洲人后裔建立了联系,这样做有助于记录共同的历史和建立跨国界纽带。
例如,和20世纪初华裔美国人形成跨国商业和文化联系一样,今天的华人社区继续以非正式和正式的方式保持跨国界联系,包括每年将中美洲华人聚集在一起的惯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美洲的日本人也开始建立联系和组织,包括泛美日裔协会(Pan American Nikkei Association),将西半球的日本人后裔联系在一起。与美国和加拿大的南亚人在20世纪早期形成政治和支持网络的方式类似,今天的南亚移民也保持着跨越不同大陆数个国家的积极的跨国家庭网络。例如,加拿大、英国和美国的南亚人已经形成了学者基纳·德赛(Jigna Desai)所称的“棕色大西洋”(Brown Atlantic)身份认同,并将他们和南亚联系在一起。
今天的亚洲移民旅程是流动的、多方位的、全球化的。同样,身份认同并不局限于一个地方,而是同时认同于许多地方。移民在他们移动的不同国家之间,以及他们打算要去的其他地方保持时间、忠诚度、金钱和身份认同的平衡。最近移民的子女和孙辈是否会保留或改变这些跨国行为尚不清楚,但他们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将非常重要,因为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我们都在学习成为全球的美国人。 美国百年困局与当下危机(套装共10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