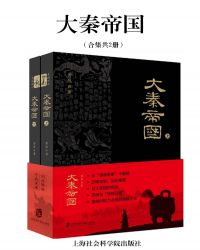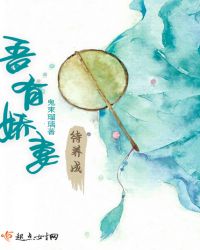“邯郸党”入主咸阳宫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人生必读经典历史丛书:时代帝国三部曲之大秦帝国(上 下)(套装共2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邯郸党”入主咸阳宫一个老大男人忽而被再次怀胎生出
异人在吕不韦的帮助下,经过一番曲折才逃出被围的邯郸城,回到了阔别二十余年的故国。
《史记》只说向“守者吏”送了六百斤金子的贿赂,大概是城门官行了方便放出去的。小说家据此又有许多想象和创造,譬如有的说是先把赵王派来监视的官吏灌醉了,再扮作商人混出城去的。有的说是吕不韦装做行商,带着满载货物的车子,而异人就藏在货车里,就这样出了城。新近出版的一本小说想象尤为奇特,说是恰好那日有一批犯人要押到城外去斩首,便买通监斩官,让异人扮作一名死囚犯,跟着被押出城去,真犯人都被杀了头,他这个假犯人便获得了自由。
不管怎么说,在异国他乡度过了少年、青年的异人,当他第一脚踏进函谷关,第一眼看到故国景物,第一口呼吸到从渭水平原上吹来的清新的空气时,该是激动异常的!这时候童年的记忆会带着温柔的馨香、张开美丽的翅膀向他飞来。在所有记忆中最美好的莫过那张动人的笑脸,那双给过他最真挚的爱抚的手,那便是生他养他、一想起来就会不禁热泪盈眶的母亲。
异人的生母是安国君众多姬妾中的一个,叫夏姬。
按照据说是周公制定的礼制,凡是妾生的子女要称父的正妻为“嫡母”,亲生母亲反而不能称嫡。
问题的严重性还不止此。
《史记·吕不韦列传》只用两个字便准确地判定了夏姬一生的命运:“毋爱”。毋,即“无”。一个生活在帝王后宫的女人,没有得到帝王的宠爱,就等于成了一具失去了生命的躯壳,许多使她肝肠寸断的事便会一件接一件发生。譬如说,早些日子里,她听说邯郸来了个大富商,给华阳夫人送了不少奇珍异宝,这么三说两说夫人被说动了,就要立异人为嫡嗣。事情还惊动到王后、王上,很快都同意,只待举行仪式。过去还只是口头上叫叫,此仪式一旦举行,那就从法律上承认异人成了华阳夫人的亲生儿子。异人不明明是她怀胎十月生的吗?可如今,他长成二三十岁的大男人以后,却忽然又钻进另一个女人的肚子再生了出来!这不是抢劫吗?作为生身母亲的她不应当奋起抗议吗?不,不,她必须高兴,也只能高兴,先去向王后谢恩,然后再去向那个明明自己不会生育却有了“嫡嗣”的女人祝贺和感谢!至于她心里是什么滋味,只有夜深人静时她那个被泪水浸透了的枕头知道!
再譬如说,处在她这种景况下,唯一能够给她带来安慰的是儿子,偏偏儿子一去二十余年,声息全无,而战争的阴云又始终笼罩在她最关注的那片土地的上空,这漫长的岁月是怎么熬过来的,只有她那颗滴着血的心知道!如今,终于听说儿子就要回来了,她想去看看他吗?她愿意他来看看她吗?当然想!当然愿意!但是……她不敢!
异人与吕不韦同坐于一车,在卫护部队的严密保护下,进入了巍峨的秦王宫。
他一下车,同样处在两种感情的旋涡中。如果要讲出自真心的感情,此刻他恨不得马上奔去跪倒在生身母亲夏姬跟前;但是为着满足一个作为男人的更大欲望,为着那个尚悬在半空却已那样诱人的王位,他不得不首先去拜见实在说来还相当陌生的华阳夫人,然后才能去见生身母亲。
这是一路来吕不韦教的。现在他对于这位阳翟巨贾真可谓言听计从,且出自真心的折服。
他们在馆舍安顿下来后,一面请人去通报安国君和华阳夫人,等待着他们安排出适当时间来接见;一面筹办礼物、衣装,异人还得精心作一番打扮。
不用说所有这一切花费,又都来自吕不韦的腰包。
在吕不韦的指导下,两名侍从帮助异人穿戴完毕,他临镜一照,不由惊叫起来:这还是我吗?
异人头戴高高的章甫,身穿博袍、长裙,竟然变成了一个楚人!
楚人奉祝融为先祖,祝融是火神,故楚人尚红。异人穿着绣有奇禽异兽的红袍红裙,全身像一团色彩斑斓的火。
这又是吕不韦教的:第一次见面最关紧要。华阳夫人是楚国人,到她这个年岁就会越发怀念起故土来,你这身打扮就会给她留下一个美好的第一印象,从而博得她的欢心。
一个大男人,做出此种儿女态,想来颇为不易。异人居然做得出,足见王位的诱惑力该有多大!
华阳夫人一见异人那情状,果然高兴得不得了,又是称赞他天资聪明,又是说他能讨人喜欢,且说道:我原本是楚国人,你真是我亲生儿子呢!我的儿,为娘索性把你名字也改一改,就叫楚儿吧!
异人连忙跪地拜谢,从此便改名为“子楚”。
刚才一番热闹,在一旁的安国君不免有些冷落。这时候他以一个父亲的严肃态度问道:我的儿,你能吟诵几篇诗书来给为父听听吗?
子楚陡然紧张起来,勉强吟诵了几篇,又说道:孩儿少小流离在外,缺少严师教授,不习于吟诵。以后当用心学习,还求父亲大人教诲。
安国君说:好吧。那你就在宫中住下来,去歇息吧!
但是子楚还不能就这样退下。他记着吕不韦的话,第一次见面是至关重要的,而刚才安国君对他的考试,显然只够个勉强及格。他还得设法补救一下。想来想去,终于想出安国君也是去过赵国的,便抓住这个题目再说几句奉承话:父亲大人,孩儿在赵国时逢到一些豪杰之士,他们都说曾经有幸结识过父亲的,对父亲的人品都十分敬慕,至今还常常西向仰望您呢!
安国君果然高兴了,说:哦,还有此等事吗?又问道:我儿这回从赵国来一路有些什么见闻?
子楚想了想说:赖王上圣威,如今我秦国疆土日趋广大,只是边境关塞似尚有疏漏之处,在此多事之秋,当以谨慎为好。所以依孩儿之见,不如每天早闭晚开,缩短开放时间,不使细作有隙可乘。
这一回安国君真的高兴了,大声称赞道:说得有理,难得我儿有此等心计!
吕不韦计谋第一步终于成为现实:子楚被安国君立为嫡嗣。
公元前251年,在位长达五十六年的秦昭襄王在病榻上安详离世。
已经五十三岁的太子安国君继承王位。他在主持隆重的国丧的同时,便同时考虑如何继承父志,进一步发展秦国。看来他是主张以宽厚治国的,《史记·秦本纪》记下了他这样一些最初举措:“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亲戚,弛苑囿。”最后一项是倡导国王及王室人员生活要俭朴些,缩小苑囿,减少游猎一类事。
在这同时,立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为太子。
这年十月,安国君正式举行即位典礼,便是秦孝文王。
各国都按惯例派来使节祝贺。赵国也表示了和解之意,特派人送来了子楚夫人赵姬和她的儿子嬴政。
这时发生了一个惊人的事件:在王位上才坐了三天的孝文王突然去世了!
于是刚被立为太子的子楚便匆匆继位,这便是秦庄襄王。
这样,当快满十周岁的嬴政第一次踏进自己国家时,他竟要接连参加或目击两次丧礼和两次王位继承典礼。这在秦国历史上,实属绝无仅有。
对这样频繁、仓促的王位嬗替事件,史书在记载时仍然用了一如既往的平静语气,给人的印象是一切正常。但小说家们却无法按捺住跃跃欲试的想象力,认为其中必有蹊跷。他们对吕不韦其人似乎都没有好感,这一回他就被列为重点怀疑对象。这是明人冯梦龙在《东周列国志》中写下的一段话——
孝文王除丧之三日,大宴群臣,席散回宫而死。国人皆疑客卿吕不韦欲子楚速立为王,乃重贿左右,置毒药于酒中,秦王中毒而死。然心惮不韦,无敢言者。于是不韦同群臣奉子楚嗣位,是为庄襄王。
“国人皆疑”,就是说国都咸阳城里的人都怀疑是吕不韦害死了孝文王,我觉得这很可能是事实。这“疑”首先是从秦王宫是里传出去的。谁呢?主要是孝文王的那二十几个公子,其中尤其是公子傒和太傅士仓。《战国策·秦策五》说:“子傒有承国之业,士仓又辅之。”子傒是孝文王的长子,若按通常的嫡长继承原则,他是当然太子,事实上也大体作了这样的安排,因而派了士仓辅佐他。但是可恶的阳翟巨贾从中一捣鬼,却让一个既非嫡又非长、从小抛掷在邯郸的空质子,大摇大摆地坐上了太子位,这合理吗?公平吗?这口气能咽得下去吗?不仅如此,邯郸人不来犹可,一来就来了四个,是十足的邯郸党!如果真叫那个空质子当上太子,那么很快他就会当上国王,那个邯郸街头的臭婊子就成了王后,再叫小杂种当上太子,下贱的买卖人当上丞相,那我们嬴秦几百年祖宗创下的基业不是要付之东流了吗?所以很可能还在孝文王活着的时候,种种攻击邯郸党的言词,包括有事实根据的和无中生有的,便蜂拥而起。其中就可能有嬴政是吕不韦野种一类说法。恰在这时,只当了三天国君的孝文王死了,而且确实死得不明不白,于是文章便立刻转而集中做到“王上被害”这个最新鲜、最富有煽动性和号召力的题目上来,首先是秦宫皆疑,进而“国人皆疑”!
那么吕不韦毒死孝文王这件事是否实有呢?冯梦龙手法很高明,他就这么用一个“乃”字做连词一路这么写下来,既不作肯定,也不作否定。不过读完全文,还是会给你一个印象:此举很可能有的!
当然不能说绝对没有,但据当时实际情况看来,我以为这种可能性接近于零。吕不韦当时连一官半职都还没有捞到,在这种情况下,纵然他腰缠万贯,但要深入禁宫在短短一两天之内,贿赂国王亲近去干给国王下毒这样一件犯了十恶不赦大罪的事,绝非想象那么容易。更为重要的是,吕不韦是一个很有政治头脑的人,他懂得孝文王的暂时存在,对他计谋的实现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他早已看出孝文王性格软弱,多半要受华阳夫人操纵,而此时这个宣太后式的楚国女子,实际上成了所谓“邯郸党”的头子。在这种格局下,有孝文王这块牌子存在,对“邯郸党”赢得时间,站稳脚跟,扩大影响,发展势力,都极其有利;而敲掉这块牌子,那将是一次吉凶未卜的极大冒险。当然,这种格局如果凝固不变长此下去,那么总有一天“邯郸党”是会感到不可容忍的,而时已年过半百、且体弱多病的孝文王,几乎使他们用不着预先担心真会有那么一天。以吕不韦的智慧,而甘冒“弑君”之大不韪,心急慌忙地去做一桩无利而有害的蠢事,我觉得简直不可思议!
尽管吕不韦下毒实属子虚乌有,但既已出现“国人皆疑”这样的效果,这篇文章肯定做得有声有色。有此舆论为先导,便不难发动一次叛乱。所以即使史书没有记载,在孝文王猝然离世这段时间里,秦王宫内有过一次以公子傒和士仓为首的或大或小的叛乱事件,我想还是十有七八可以肯定的。
叛乱是被镇压下去了,而且没有留下痕迹,也不见有反复。
镇压叛乱的总指挥当然是吕不韦。他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之下被迫临时举起指挥之剑的。在父亲面前他曾经说过喜欢冒险,但那是经过慎重考虑、周密调查以后的冒险。这种被逼出来的、瞬息之间就要作出应对的冒险,在他还是第一次。但此险非冒不可,不然就是为山九仞而功亏于一篑!居然又让他一举成功。这该是这位阳翟巨商在因国势日隆而变得愈来愈傲慢的嬴秦宗室面前的第一次亮相。无论他们是否愿意接受,这个出身卑贱的铁腕人物,他的机敏,他的果敢,还有他的老练,大概都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参加叛乱的公子傒结局如何呢?史书中自然找不到答案。毛丕震老先生用他多年心血写过一部小说叫《祭始皇》,说是被庄襄王处斩了的。此后史书中也确实再也见不到公子傒等人的影踪,我也只好这样相信。好在此事如果真的这样发生了,也还不能据此断定那个长期在邯郸街头被人蔑视、卑视的空质子,原来竟有如此凶残!不是你吃掉我,便是我吃掉你。人一进入宫廷,这类事就变得司空见惯。
公元前250年,太子子楚即位为庄襄王。他的养母华阳夫人成了华阳太后,他的生母夏姬终于也被尊为夏太后。
次年,吕不韦当上了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雒阳十万户。他的千金买国的计谋到此已全部实现。
周朝王运至此彻底终结
秦国两代国王在短短数天之内相继死去,其间还可能有过一场不大不小的内乱。这些动向无疑会被山东六国的高层统治者及时、准确地获得,他们之中因屡受攻伐侵削而积聚下来的仇怨,终于等到了一次可以略微宣泄一下的机会。心活手痒一点的,不由会升起一种跃跃欲试的冲动:能不能趁这个难得的时机兴兵攻它一下呢?
各诸侯国有这种想法并不意外,使人感到有些新奇之处的是,这一行动的牵头者竟是个蕞尔小国:东周。“庄襄王元年……东周君与诸侯谋秦”,《史记·秦本纪》就是这样明明白白写着的!
我在前一章里,把周赧王和东、西周戏称为大、小周。“大周”和“小周”之一的西周已在那时灭亡了,如今孤零零的还剩下这么一个小东周。东周之君的自我感觉依然保持良好,一如既往地以大周王朝正统代表自居。他远远望到河西咸阳上空升起了淡淡的几丝不祥的云翳,立刻有了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使命感,火速派出使节去向各诸侯国联络,筹划联合讨秦事宜。
这一信息自然也立刻被新一代秦国决策者们获得。
吕不韦现在正处于踌躇满志之中。如果把秦国比作一艘艨艟巨舰,那么他实在还是一名新上任的舵手。接连几阵狂风骤雨,随后又是冲天巨浪和不测的暗礁,居然还是让他三下两下撑了过来。自己颇为得意不说,周围很快聚集了一大批追随者、崇拜者,自然也少不了阿谀奉承者。与当初一个人跑单帮似地入秦游说的景况比起来,不啻天壤之别。
但他自己心中有数,那些武将们对他绝不会心服。自商鞅变法以来,秦国就是一个最讲究以军功进爵的国家。纵然不是亲自挥戈跃马驰骋疆场,也至少得指挥或部署打赢一两回胜仗才能立住脚跟。特别像他吕不韦这样一个出身商贾的外籍客卿,没有赫赫军功就休想坐稳这把丞相交椅!
好了,机会很快来到。
吕不韦提出要亲自带兵去讨伐东周。庄襄王着实一惊,说:卿在一旁辅佐寡人不是好好的吗?带兵作战是那些武将的事。再说万一失败了就会有损卿如今的声威,倘有不测,更叫寡人如何是好?
吕不韦说:请王上放心。打仗难免有风险,但这一仗臣已有八九分把握。
庄襄王被说服了,拜吕不韦为大将,命其率领精兵五万,讨伐东周。
吕不韦毕竟与一般武将不同,他更懂得舆论攻势的作用。在将士们开始东渡黄河时,他发布了一篇檄文,先言大周王朝的赫赫功业,但自周都东迁以后,历世昏庸无道之主已将周国运丧尽,再历数东周之不义,竟欲乘秦国上下痛悼二王之时作祸为寇,实为天理人伦所不容;然后笔锋一转,面对广大民众及山东诸国公告道:义军之来也,攻伐无道而拯救生民也!义军之过也,秋毫无犯而市肆勿变也!诸侯列国若出兵相助,当为本军所欢迎;若助纣为虐,则同在歼灭之列,不谓言之不预也!吕不韦在后来组织编撰的《吕氏春秋·十二纪》里,收录了八篇洋洋洒洒的军事专文,想必就是根据自己经验和参照各种兵书写就的。
令吕不韦不无遗憾的是,这次讨伐东周的胜利得来未免太轻松了。也许是这篇檄文起了点作用,山东诸国竟没有一个敢出兵救助东周的。秦军刚踏上东周国都巩(今河南巩县西南),城门早已大开,臣子们各作鸟兽散,东周之君则匍匐在地,颈脖上自己套了绳索,但求能免一死。至此(公元前249年),周王朝的最后一根小尾巴也被割掉了。中华大地上从此开始了连象征性的统一君主也不复存在的真正“群龙无首”的时代,即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所谓“无天子”时期。吕不韦下令把宫中器皿及东周所属那一小片土地,即偃师、谷城、平阳等总共七个县的图籍一起装上车乘,又把东周之君推上囚车,浩浩荡荡班师回朝。庄襄王很高兴,率领文武百官亲至城郊迎接。尽管这回轻易取得的胜利从战例上说算不上辉煌,但它使秦国连接了继续东进的战略通道,并从观念上取得了统一天下的合法地位。就是在看惯了多次凯旋归来的秦师的咸阳人看来,也因这一回囚车中押着的竟是大周王朝最后一个末代小国君而激起新的兴奋点,沿街观望的人群如潮,着实热闹了一番。
庄襄王还颇有点王者风度,认可了吕不韦的建议,非但不杀东周君,还赐号周君,封以阳人之地(今河南临汝西北),使其得以建立祖庙,不绝祭祀。
本章第一节里,提到有个吕不韦可能是殷商遗民后裔的传说,倘若传说有据,那么便在我们面前呈现了一个有趣的历史循环圈:八百多年前周人灭亡了商朝;八百多年后,正是一个殷人后代最终完全彻底地灭亡了周王朝。
如果可以把来自邯郸的三男一女称作“邯郸党”的话,那么从此开始便是邯郸党的黄金时代。庄襄王和丞相吕不韦威望日隆,稳固地扎下了根基。做了王后的赵姬,由于她的美貌、聪灵、贤淑,加上能歌善舞,深得生性开朗的华阳太后的欢心。小男孩嬴政也在快活地渐渐走向少年。他一度处于潜伏状态的智能一经激发,便奇迹般喷涌出来,加上太师吕不韦悉心辅教,学业上也有了长足进步。他将被立为太子,几乎已成定局。
在这期间,秦国国势又迅速跋扈飞扬起来,不断向东推进它的疆域。请看《史记·秦本纪》的记载——
庄襄王元年,使蒙骜伐韩,韩献成皋、巩。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
二年,使蒙骜攻赵,定太原。
三年,蒙骜攻魏高都、汲,拔之。攻赵榆次、新城、狼孟,取三十七城。
秦国的国界已经扩展到黄河以东接近魏国大梁。屡战屡胜的蒙骜将军,这时又紧锣密鼓地筹划着向魏国发起更大规模的进攻。
大梁不已是魏国国都了吗?只要一登上大梁城楼,就可以清楚真切地望到,在猎猎鼓动的大纛下气势汹汹的秦国军队。
魏国的危亡近在旦夕。魏国的心脏在剧烈颤抖。大梁一片恐慌。
胜利在战场之外
十年前,在魏国与赵国的关系史上,曾经发生过一个轰动一时的事件,便是信陵君魏无忌的窃符救赵,解了邯郸之围。因此一举,信陵君在诸侯国间声望如日中天,但却因窃了他异母哥哥安釐王的虎符,又杀了大将晋鄙这两件事,兄弟俩从此反目成仇,信陵君一直居留在赵国,断绝往来已达十年之久。这时候,当年曾经暗中代为信陵君窃符的如姬对魏王说:事到如今,恐怕只有去把无忌公子请回来,请他去联合各国,合力抗秦,魏国才或有可救。
魏王叹息一声说:以前是我不让他回来,如今只怕我去请,他也不肯回来了呢!
如姬说:以前的事,大王认个错就是,你们总是骨肉兄弟吧。再说无忌是忠于故国的,眼看魏国危在旦夕,他是不会不顾念到社稷宗庙的。妾身以为只要大王去请,公子总能回来。
但是魏王派出的使节星夜赶到邯郸,信陵君却拒绝接见。这位魏公子心头仍然梗着那个十年前的芥蒂,担心会受到魏王冷遇而不想回国,但内心对故国的眷恋之情又无法平静。劝说的人多了,不胜其烦,索性下令守门人:有谁敢为魏王使节通报的,斩!
命令刚下达,偏有两位门客名叫毛公、薛公的,来见信陵君说:某等追随公子多年,原以为公子乃当今一大丈夫,今日之事,倒使我们认清以前的看法错了,故特来向公子告别!
信陵君大吃一惊,慌忙起身作揖挽留:请二位先生务必说个明白,无忌若有怠慢高士之处,当依先生所教立时改正!
毛公、薛公说:哪里是公子怠慢了门客,分明是公子怠慢了自己安身立命之根本!
信陵君说:恕无忌无知,求二位先生明教。
毛公、薛公说:公子所以能名重于赵国,誉满于天下,就因为您十年前率领魏国十万精兵力克强秦,救了赵国。如今眼看魏国已置于秦国砧案,大梁万千生灵命悬一丝,而公子尚在此耿耿于个人些微旧怨,此实为大丈夫所不取。若使大梁为强秦所破,先王宗庙将夷为平地,公子尚有何面目立足于天下!
《史记·魏公子列传》记述到这里,用急促的语气,写下了以下三个短句:
语未及卒,公子立变色,告车趣(通“促”)驾归救魏。
消息传到咸阳。
吕不韦和庄襄王都有些惊慌,他们估计魏国一旦打出信陵君这面旗帜,很快便能得到列国响应,形势就会变得十分严峻。正当他们召集大臣、谋士商议时,又得到情报说,果然赵、韩、楚、燕四国已接连发兵援魏。于是庄襄王便立刻下令已接近大梁的蒙骜退兵,并增兵严守函谷关,务必阻挡五国联军于关外。
秦庄襄王三年(公元前247年),信陵君魏无忌被魏安釐王任为上将军,率领五国联军从大梁出发,向秦军发起反攻。双方大战于河外。联军巧妙地切断了秦军的后路,接连取得胜利。秦将蒙骜战败逃走,秦兵退至函谷关坚守。联军对垒了一个多月后,胜利班师。
信陵君入魏境离大梁还有三十余里,魏安釐王已率领文武大臣在那里恭候。兄弟俩阔别十载,在凯旋的欢呼声中相会,可谓悲喜交集。大梁城里欢腾的人群如山似潮,争着一睹抗秦英雄、他们的魏公子的风采。魏王特拜信陵君为国相,又封给他五座城池。信陵君名扬天下,各诸侯国的宾客都来向他进献兵法,求得指教。信陵君都给予题名,汇集成一部书,便是《魏公子兵法》。
吕不韦生平遭到了第一次失败。
失败是痛苦的,但唯有从失败中学习才是最深刻的。从善后处理看来,吕不韦仍不失为一个大家。
第一,他没有处斩打了败仗的蒙骜,继续予以信用。蒙骜自然感恩不尽,立誓下次攻魏非死必胜。
第二,他已从魏国的这次胜利中,看到了潜伏于魏国最高层中的失败因素。这种因素虽然尚处于隐微状态,但只要恰当地给予一点外力激发,它便会很快膨胀起来而陷于不可自拔。
这一回他运用的又是财富的魔力。
身带巨金和厚礼的秦国使者彬彬有礼地出现在魏王宫里,同时又神秘地穿行在大梁城内的东街西巷。
最先被策动起来的是晋鄙的部属和门客。他们至今还怀念着自己的主将,因而对窃符杀晋鄙的信陵君依旧心存怨愤。于是魏王几乎天天都可以听到如下一类诋毁魏公子的话——
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为魏将,诸侯将皆属。诸侯徒闻魏公子,不闻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时定南面而王。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史记·魏公子列传》)
魏公子信陵君名震诸侯,各国只知有公子,不知有魏王。诸侯都在争相拥立公子,公子也有意要想南面称王。魏安釐王听了这些话,自然要心生猜忌,进而开始戒备。
与此同时,耀眼的金银珠宝和措辞婉转的信札同时出现在信陵君的面前——
公子殿下:语云“百世一人,千载一时”,此诚殿下之谓也!两败秦军,连救赵魏,盖世实无第二人。是以功存魏室而名满天下,令诸侯宾客引领翘首为望。近闻上国大王已有让贤之意,此实天下人之公愿也。今奉上不腆之礼,聊以预布贺忱,专候登位佳音。
此时的信陵君虽已有些陶醉在自己的声誉里,但凭他的智慧还是看出了其中叵测的居心。他拒绝接受礼物,同时把这封信送去给魏安釐王看,并说:人臣义无私交,秦王来书及珍宝,臣均不敢受,望大王明察!
魏安釐王原已心存猜疑,见信沉吟半晌,却忽而说道:秦人向为虎狼之心,寡人又何至于轻信秦人而不顾念棠棣情深呢!
其实他已经中计。
吕不韦不惜重金施行此计,是由于他早已看出魏安釐王心地偏窄,对信陵君存有畏忌,只要略施离间,便可奏效。
那还是多少年以前。一次这对异母兄弟在一起下棋时,忽从北部边境传来烽火警报,说是有赵军来犯,快要进入魏境。魏安釐王立刻停止下棋,准备马上召集大臣来议。信陵君却劝止说:大王别急,那是赵王在游猎,不是来进犯魏国的!一边说一边继续从容落子。不一会儿,果然有人来复报说,确实是赵王游猎,没有入魏境。魏安釐王不由大惊,问信陵君是怎么知道的,信陵君说,他的门客中有人连赵王最隐秘的事都能探得到,所以他知道。《史记·魏公子列传》在记述此事后,又写了这样一行字:
是后魏王畏公子之贤能,不敢任公子以国政。
几天后,魏王借个由头,让别人代替了信陵君的上将军之位,并收回了他的相印和兵符。信陵君自知不可能再为魏王所信用,便托病不朝,只顾与宾客通宵长饮,狎近女色,以消磨时日。这对异母兄弟,终于因各自性格上的弱点,以反目相向为结局。只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都在三年后的同一个时间,离开了这个世界。
吕不韦听到信陵君已死,立刻起用蒙骜统兵伐魏,终获大胜,一下子掠得了二十座城邑。
经过失败再获得的胜利越发显得珍贵,吕不韦不免显出了几分得意。这一天,他在辅导嬴政阅读《尚书》中的《秦誓》时,讲到了当年崤山之败秦穆公不是诿过于孟明视等将领,而是素服罪己,因而后来能称霸西戎后,便把这回攻魏由败到胜的战例也说了说。他自然再三说明这是王上的决策,可内心少不得有几分骄矜。不料,少年嬴政听了却说道:太师,弟子却觉得这次伐魏还只能算个半胜。既然已经攻取二十座城邑,为什么不乘胜挺进大梁,一举灭了魏国呢?
吕不韦看了看面前正用奇亮的眼光逼视着自己的少年,缓缓说:还没有到这个时机。你要记住一句话:成事在天。
嬴政紧接一句:可上回弟子读《汤誓》时,太师讲到商汤被囚于夏台时就考虑了兴商大计,当时太师不是还特地教弟子要记住“谋事在人”吗?
吕不韦着实吃惊,一时语塞。
——要是我,我就要乘胜进兵大梁。城破之后,屠城三日,再班师!
少年显出惊人的自信。
吕不韦一听急了:不,不!兵为天下之凶器,务必慎用。你一定要记住:王者之师伐无道而救生民——这是用兵之道的要旨。
——可弟子不想做王者,只想做胜利者。胜利者有权惩罚失败者,这是公平的:谁叫他失败呢?
多少年后,大梁街头的道道血河证明了少年此时并非虚言。
流浪儿初为王太子
现在让我们腾出一点篇幅来,根据一些零星资料,稍作推想,时间倒回到两三年前,来简略描述一下少年嬴政进入秦王宫后的最初印象。
车子一到咸阳城郊,嬴政就远远望到在迎候他们母子的队伍中,有个中年男子微笑着冲着他招手。他穿戴着华贵的衣冠,最显眼的是一抹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胡须,像一只风菱搁在唇上。
他认了好半天,才从遥远的记忆里钩起几片淡淡的影子,勉强拼到一起,知道是他的叔父,就是吕不韦。
叔父抱起了他,粗硬的胡须扎得他的脸颊痒痒的,叫着他的小名说:小黑蛋蛋,你都长到这么高啦!
这感觉,这声音,在他记忆里保留了好些年。
成群的车乘一齐向秦王宫进发。他就坐在叔父身旁,在车轮和马蹄声的合奏中,听叔父讲述咸阳宫的来历。叔父说那还是多少年前有个大能人叫商鞅的设计监造的,由众多宫殿组合在一起,连成一个整体,居高临下,气势雄伟。这么说时,叔父指指前方,果然遥见那连绵起伏,像是山峦般的重重层楼,夕阳下,那楼脊和飞檐闪着金灿灿的光芒。城有南门、北门、西门,车队是从西门进入的。宽大的城门前,左右另有两座高大的建筑,他把后脑勺仰到了后背,也还没有望到它们的顶。叔父说那叫冀阙,是专门用来向臣民发布教令用的。有时王上举兵向别国发起征战,也在这里授予主将符节,下达战令。将士们一个个铁甲金戈,战马长啸,战旗猎猎,气势十分雄壮。
嬴政看着、听着,感到十分新奇、兴奋。而当他进入一群又一群的宫殿后,眼前满是五彩缤纷、金碧辉煌,反不知道看什么好了。单是那瓦当上的雕像,就让你看得眼花缭乱。呵,这是母子鹿瓦当,那小鹿仔正在吸吮妈妈的奶呢!呵,那是龙虎斗瓦当,一龙一虎,斗得可厉害呢!……
嬴政做梦也没有做到,自己竟会在这样一个叫作王宫的新奇世界里居住了下来!
不过,可以自由玩耍的时间只有三天,叔父便做了他的太师,开始了诵读诗书,进修礼、乐、射、御、书、数等等功课,日复一日的枯燥乏味的王子生活。这时候再看那一抹黑胡须,就觉得它像一张拉满弦的弓,硬绷绷的,从没有一点笑意。大约过了半年多后,才渐渐适应过来,学业有了长进,那弓上紧绷的弦也卸下了,常常可以听到太师满心喜欢的朗朗笑声。那抹黑胡须呢,这时变成飞鸟的一对翅膀,活泼泼地鼓动着,又让他记起了刚进宫时那个可亲可爱的叔父的样子。
这一天,已经做了王后的母亲说:今日我要带你去拜见华阳太后,你父亲能够坐上王位,全靠了太后的支撑。所以你一定要懂规矩,懂事理,让太后欢喜你。
这事太师预先给他说过的,还教他在功课方面做了好些准备,以应对太后的查问。不过他还是着实有些紧张,只顾小心翼翼跟在母亲长裙后走。不知走了多少时候,待到母亲立住脚就要跪拜的时候,他才偷偷张去一眼,果然窥见在高堂上端坐着一位锦衣浓妆的贵妇人。他连忙也拜伏在地,听到说“起——”才敢起来,恭恭敬敬侍立在一旁。母亲在向太后禀报,无非是说孩子从小在外,有失教养,望太后多多训教等等。许久听不到应声,他不由瞥去一眼,看到太后缓缓地从侍女端来的漆盘上接过香茗,微微嘬了一口。忽而转来扫视的目光,他连忙低下头。听得太后在问:几岁啦?声音刚落,母亲已暗暗在牵他衣角。他先有些心慌,赶紧命令自己镇静,回答说:启禀王太后,十二岁。
——唔。生辰在哪个月?
——孟春之月。
——知道孟春之月的月令吗?
嬴政心中跃跃了,这一问恰好问到不久前太师教过他的功课上。便朗声背诵道:孟春之月的天象是:太阳的位置在营室宿;黄昏之时,参宿出现在南方中天;黎明之时,尾宿出现在南方中天。孟春三月的物候是:东风和畅,大地解冻,冬眠的动物开始苏醒活动,大雁由南向北飞行……
——唔,说得还可以。我再问你:孟春之月做天子的衣、食、住、行该是怎样呢?
——依据孟春之月月令,天子该穿青色的衣服,佩戴青色的玉器,吃的是麦食与羊肉。天子居住于明堂之东的青阳堂左侧室,乘坐饰有青凤銮铃的大车,车前驾着叫苍龙的青色的骏马,车上插着绘有龙纹的青色旗帜。
华阳太后雍容端庄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意,说道:嗯,很好。你能再吟几首诗给我听听吗?
嬴政有了几分即将过关的松快,应答一声“是”,便边舞蹈边吟唱起来——
南山有台,北山有莱。
乐只君子,邦家之基。
乐只君子,万寿无期。
南山有桑,北山有杨。
乐只君子,邦家之光。
乐只君子,万寿无疆……
华阳夫人高兴得大笑起来,从座席上跽身一伸手,把还在舞蹈中的嬴政牵住,揽进怀里,亲了亲,说:呵,是我的小孙儿,好孙儿,将来定会成就大事业的!
不知为什么,嬴政觉得被拥在太后怀里,比在母后怀里要亲切得多,舒贴得多。这种感觉,他也保持了很久、很久。
嬴政在王宫里住久后,一待落课,有时又不免撤起野来。一次把一个男孩子打哭了,事后又很快忘了这件事。这一天他向太后请安出来,在后宫长长的甬道内走着,背后忽而有人连声叫着哥哥,他没有弟弟,自然也不去在意。可偏偏背后急速的脚步声正在向着他近来,不由回过头去看看,却正是那天被他打哭过的男孩子。那男孩子说:那天是小弟无礼,触犯了兄长,请兄长恕罪!说着怪别扭地行了个大礼。这倒反使嬴政不好意思起来了,赶紧还礼,说明是自己粗鲁,不该动手打人。只是他不明白,何时有了这么一个只比自己小一两岁的弟弟。那男孩子说,他叫成𫊸,确实是他的异母弟弟。这使嬴政大感意外,而且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厌恶之情:父王怎么能这样呢,而且难保没有别的弟弟妹妹吧?正这么想时,站在远处的一个艳装美容年轻女子还在那边放声过来训教成𫊸,说着要他对兄长尽礼的话。嬴政这才猜到成𫊸的赔礼原是他那母亲——多半是父王的又一个姬妾吧?——指使来的,并非出于自愿,难怪刚才他说话的口气那样勉强。果然,当嬴政顾自离开那里时,还隐隐听到母子俩在那里争执,传来一句两句成𫊸的话:哼,凭什么我要向他赔礼!……将来总有一天……看吧!
这种不愉快的感觉,也在嬴政心底壅塞了好些日子。
但不久,一个惊人的事件发生了:只当了三年国王的秦庄襄王又突然去世!
这是秦国历史上一个非常时期:在不到四年时间里,先后死了三个国王。
历史老人像是有点耐不住了,接连擂响三通急鼓,催促大秦帝国的主角赶快登场。
于是,王冠便落到了一个年方十三岁的少年头上。 人生必读经典历史丛书:时代帝国三部曲之大秦帝国(上 下)(套装共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