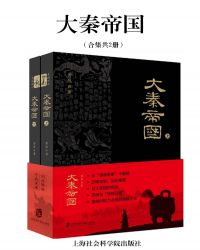血的疯狂与心的挣扎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人生必读经典历史丛书:时代帝国三部曲之大秦帝国(上 下)(套装共2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血的疯狂与心的挣扎
第二十八颗将被割下的头颅
想象一下吧:社会给了一个人以至高无上的权力,却还没有成熟到能够产生出相应的制约机制,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手执太阿剑的人一旦暴怒起来时,他将会如何动作呢?
这就是这些天来在咸阳宫里发生的事情。
巍峨、庄严的秦王宫前,血淋淋地挂着一排人头,人头之下是一大堆人的手和脚,截去四肢的身躯,还被蒺藜刺得血肉模糊,堆叠在一起,竟已有小山般高!
数一数,头颅共二十七颗,手和脚是相等的:都是五十四只。
这就是说,已有二十七位大臣,在秦王赢政冲冠一怒之下死去。
但他仍处在狂怒中,很可能还要杀人。那血淋淋的残躯堆上插着这样一块牌子:
有为太后事敢再谏者,定斩勿赦!
所谓太后事,是指王太后赵姬因与嫪毐叛乱有牵连,被秦王嬴政逐出咸阳甘泉宫,送到雍城阳宫幽禁了起来。此事已经过去了数月,臣子们觉得一个王太后,居然还被自己王儿隔离在僻远的冷宫,过着凄凉孤寂的日子,实在有违人伦,因而接二连三地提出了及早迎回太后的谏言。臣子们都是些饱学之士,以为他们的进谏是以经书为据的,就是孔子编撰的《春秋》上隐公元年那段记载:“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郑庄公用武力平息了他弟弟共叔段的叛乱,由于牵连到他母亲武姜,在处理善后时就把武姜送到城颍幽禁了起来,临行还对武姜发誓说:不到黄泉,此生不再与你相见!后来有位叫颍考叔的大夫,想了个巧妙的办法去说动郑庄公。他拿了礼物去拜见庄公,当庄公请他吃饭时,有意把肉拣出舍不得吃,说是要带回去孝敬母亲。庄公一听受了感动,说:你有母亲可以孝敬,偏我就没有!经过一番对话,颍考叔听出庄公已有后悔之意,只是还碍着那个“不到黄泉不相见”的誓言,便说:那有什么难处呢?只要掘地三尺,在地道中相见,不就是誓言中所说的“黄泉相见”了吗?郑庄公照着这样做了,于是母子俩便在地道中重新相会,和好如初,并即兴赋诗,儿子唱:“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母亲应和:“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
但是咸阳宫里的臣子们想错了!他们错就错在没有看到这两件相隔五百余年的事有两点不同:秦王嬴政不同于郑庄公;赵姬不同于武姜。
于是头颅便从他们颈上一颗接一颗地被割了下来。
最先出来想学一学颍考叔的是一位掌管文书图籍并负有监察责任的御史官,他在一次上朝时跪奏了这件事,恳请秦王允许把太后迎回咸阳内宫来。
嬴政一听,胸口那团好不容易勉强覆盖住的怒火又被撩了起来。他表情冷漠地对着左右两班文武官员问道:尔等有谁赞同他的禀奏吗?
好几个臣子齐声回答:臣等都赞同。臣等以为迎太后回宫,上应天理,下合人情,请大王恩准。
——赞同者站出来!
包括御史官在内,一下站出了十三位大臣。
秦王的怒火上又浇了一勺油。他亲政不久,如今竟有这么多人敢于一下站出来,他觉得简直是向他示威,是对他的至高无上权力的挑战。他击案一吼:推出去断肢枭首!
眨眼间,十三颗头颅和二十六对手和脚示众在殿前的台阶上。
但竟还有不怕死的,接二连三又有几批大臣为太后事来进谏,也都被当场杀死,现在已杀了二十七个。
血越流越多,越流越红。
秦王下令去插上那么一块诫牌,说:看有谁胆敢再来送死!
话音刚落,宫外闯进一个人来,从从容容拾级而上,吟唱似地呼喊道:齐客茅焦进谏!
宫殿两旁胆战心惊地鹄立着的文武百官,听得这声叫唤,不由侧过头去看,只见来人年纪不过二十有余,头戴破旧的进贤冠,身穿粗鄙的缊袍,一个来自齐国尚未受到聘用的宾客,分明还只是一介寒士,越发使他们惊愕不已。
秦王嬴政按剑而坐,厉声吼道:大胆儒生,你没有看到立在阶前的诫牌吗?
齐客说:茅焦正为此而来。大王不听说天上有星辰二十八宿吗?如今才死了二十七人,还差一个。不才茅焦,若能进入诸位贤臣之列,实为三生有幸。为此特来进谏,以便凑足那二十八宿之数。
秦王说:敝国朝堂之事与你一个齐客何干?
茅焦说:事关天理人情,谁人都该冒死进谏。
秦王冷笑说:区区一介寒士,也胆敢来违抗寡人,定杀不赦。但寡人不会成全你的,不让你去凑足二十八之数。寡人要叫你尸骨无存,化作一缕青烟而去。来人哪,架起鼎镬来!
左右立刻应命。朝堂阶下的尸首堆旁又架起了巨大的鼎镬,不一会儿便冲起了炙人的烈火和呛鼻的油烟。
齐客茅焦整冠拂衣,缓步来到鼎镬前,望了望翻腾不息的滚油,再拜而起,从容说道:臣闻之,有生者不讳死,有国者不讳亡;讳死者不可以得生,讳亡者不可以得存。臣之死,已在眼前,自然不必再讳死。只是臣死之前,敢请为大王生死存亡进一言,不知大王是否愿意一听?
秦王说:有道鸟之将死,其鸣也哀。就让你哀鸣一下吧!
茅焦说:臣听说大王还想统一天下,有这回事吗?
秦王说:有又如何?
茅焦说:但不知大王用什么来统一天下?用幽禁生母、杀戮直言进谏之臣的办法吗?用这口正在烧着的鼎镬,对付一个不远千里而来愿为秦国兴盛献出忠诚的宾客的办法吗?不才稍读史书,单知夏桀、商纣以鼎镬之威、炮烙之刑先后把好端端的夏朝、商朝葬送了,却从未看到过有哪一个国君以如此狂悖之举而能安国兴邦的!文王、武王是这样做的吗?春秋五霸是这样做的吗?大王的列祖列宗是这样做的吗?这样的事,一旦为中原各国所知,谁还肯来臣事秦国呢?如此下去,大王莫说欲统一天下,就连秦国也断难幸存,大王自身也无法安保。古语云:狂暴之极,败亡在即。不信,且拭目以待吧!臣言已毕,请大王施刑吧!
茅焦脱冠解袍,高视阔步向鼎镬走去。
两班文武百官听得无不为之动容,秦王嬴政的暴怒也稍有缓解。有那么短暂的一息,他甚至觉得齐客的这些话正是从自己胸口呐喊出来的。他不正是以成就帝王之业自许、以有宏阔气度自励吗?不是也懂得统一天下需要有众多大臣的佐助吗?但自从嫪毐之案发生以来,他自己也无法理解的某种可怕的狂躁情绪,不时在心头勃然拱起。当他用了极大克制力把它压抑下去后,就小心翼翼绕开它,不敢再回头看一眼,更害怕别人提起,几个月的日子就是这样过来的。岂料那些可恶的臣子们,却有心与他过不去,一而再、再而三地老揭他这块心病,狂怒之潮冲破了他好不容易堆叠起来的堤防,只好一任它吞没自己的理智,做出一件接一件的狂悖事情来。茅焦的这番话虽也平常,但在他头脑已处于躁热状态的此时此刻,倒也不失为一帖清凉剂,使他突然记起了自己还有着那样一个大目标。但他又觉得作为一个国王,说出的每一句都必须赋予至高无上的权威,绝不许别人违抗,自己也不应轻易收回成命。因而他虽没有下令施刑,却也没有宣布恕罪,只是冷冷望着那个来自齐国的宾客一步一步走向鼎镬。
现在离鼎镬只有三五丈了,茅焦却越走越快。他正要纵身跳去……
我忽然停住笔,倒并非故作玄虚,制造悬念,实在有几句话得赶紧说明一下。
关于向秦王进谏迎回太后事,《史记》有录,但只提到茅焦,既没有提到二十七位大臣进谏并被杀的事,也没有说秦王要烹茅焦;所载茅焦说辞也很简略,仅谓:“秦方以天下为事,而大王有迁母太后之名,恐诸侯闻之,由此倍(通背)秦也。”刘向《说苑》的记载则要详尽得多,且有近似小说的细节描写。我的上述描述主要取材于《说苑》。但原文茅焦的说辞似有明显不合情理处,他是这样说的——
陛下车裂假父,有嫉妒之心;囊扑两弟,有不慈之名;迁母阳宫,有不孝之行;从(通“纵”)蒺藜于谏士,有桀纣之治。令天下闻之,尽瓦解无向秦者,臣窃恐秦亡,为陛下危之。所言已毕,乞行就质(通“锧”,刑具)。
茅焦是个说客,不是谏臣。谏臣中颇有一些不惜以生命殉他所信奉的某种道义的,说客却不是这样。说客并非没有自己信念,但他们主要目的毕竟还是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禄。尤其是这位茅焦,他是在用自己性命作孤注一掷式的赌博。《资治通鉴·秦纪一》记到茅焦决定入宫进谏时,有这样一句话:“茅焦邑子同食者,尽负其衣物而逃。”可见那是一次多大的冒险啊!头颅可不能当儿戏。茅焦在陛见秦王之前,对自己的说辞肯定是费尽了心计的,他必须使这篇说辞有相当大的把握说动对方,才敢于把一生就这么一次的赌注押上去。他又肯定是个极顶聪明的人,不至于会说出“假父”、“两弟”这类只会激怒对方而又远离主题的傻话来。要知道说客面对的是握有生杀予夺极权的人。说客无权谴责,尤其不应谩骂。他的成功要诀只能建立在两个字上:迎合,即摸准对方心思,然后因势利导进说。这就是对游说之术作过最深刻研究的韩非说的那句话:“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韩非子·说难》)
根据韩非指出的“要诀”,我对茅焦的说辞作了像上文那样的改动。
即使这样,依照秦王嬴政那刚愎自用的性格,特别是在他这种狂怒未息的情况下,只怕茅焦还是难逃被油炸的命运。
纵然历史上暴君杀人的事数不胜数,但像这样一颗一颗接连割下二十七颗人头,眼看还要生烹一个人的事,毕竟罕见。嬴政是在一种怎样的心理状态下做出这种惨无人道的蠢事来的呢?
挣脱樊笼的兽性
现在我们就来作点尝试性的分析。
他还只有二十三岁,童年的记忆对他并不遥远。
事情是由臣子们向他进谏迎回母亲引发的。
一提到母亲,他便会在内心发出痛苦的呼喊:呵,母亲,你是一个多么使孩儿难堪和羞耻的母亲啊!……
本世纪初,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法曾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弗氏根据自己研究所得,从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中提取了主人公“杀父娶母”这个主要情节,然后加以普遍化,从而为一切乱伦欲望创造了“俄狄浦斯情结”又称“恋母情结”这样一个用语。在弗洛伊德看来,这个“恋母情结”几乎可以用来解释人世间的一切。譬如他解释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时,就以“恋母情结”作为主人公丹麦王子哈姆雷特性格和心理的核心。父王被叔父杀死,母亲被叔父占有,哈姆雷特的整个复仇过程,正是在“恋母情结”支配下进行的。同样,在弗氏看来,人们在剧场里所以深深被哈姆雷特所吸引,也是由于观众在无意识中也有此“恋母情结”,因而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于是我想,如果让弗洛伊德来分析秦王嬴政此时的心理状态,十有八九他也会安上一个万能的“恋母情结”。不是吗?正是由于触怒了他潜意识中的这一情结,才使他对嫪毐产生了如此超常的仇恨,非车裂灭族而后快!甚至对两个世事未谙的孩子、他的同母弟弟也不肯放过,用残酷的囊扑之刑将他们处死!对赵姬仅作迁出咸阳处理,还照顾到她毕竟是他母亲。但此恨未消,此怒未灭。如今,臣子们的进谏,无意间又将他的这块好不容易按捺下去的心病翻将出来,于是便以十倍的疯狂索要报复,一颗接一颗地割下了那些胆敢触犯他隐痛的人的头颅!
这样解释,似乎确实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说明问题。
不过,正如有些学者早已提出过批评的那样,用“恋母情结”说明一切,未免有泛性论的弊病。事实上,历史事实和生活常识告诉我们,幼辈对于长辈,特别是对女性长辈过分放荡的性行为,都会激起强烈的并带有本能性的反感。这似乎并不一定牵涉到所谓原始的性冲动。可以为此作出证明的事实是:女儿对母亲的爱显然扯不到性上头去,但女儿一旦发现母亲有所谓“不轨之举”,同样会引起强烈反感。所以如果一定要使用“情结”这一范畴,我以为还不如说存在一种“血清情结”更为确切些。子女都希望自己血管里流的是属于父母的纯净的血,即要求这一对父母只属于他们,决不让别人沾染。这种感情人类大致到接近进入文明社会就开始有了,由于年代的久远,几乎已积淀融化为一种本能。当这种本能遭到无理侵犯时,所属的个体通常都会引起某种说不清道不明,且又是全身心的憎恶,以至狂怒,有时甚至还会酿成意想不到的悲剧。最典型的事件发生在春秋陈国的灵公时代,其事载于《左传·宣公十年》,要比秦王嬴政这个二十七颗人头惨案约早三百六七十年。
陈国有个夏姬,是个被小说家们称为“有骊姬、息妫之容貌,兼妲己、文姜之妖淫”的女人,刘向的《列女传》说她“三为王后,七为夫人,公侯争之,莫不迷惑失意”。其中陈灵公与大夫孔宁、仪行父更成为夏姬的常客,他们甚至无耻到各以在与夏姬交媾后再能得到她的亵衣为最大荣耀,还拿到朝堂来相互争看夸说。不少人都以此嬉戏为乐,唯有一个人被深深激怒了,他就是夏姬的儿子徵舒。
徵舒也是大夫,该已有二十余岁。这一天徵舒回家,恰好碰上陈灵公与两个大夫又在与夏姬一起饮酒。灵公嬉戏着说:徵舒身躯魁伟,长得很像是你们两位呢!孔宁、仪行父赶紧说:臣等不敢。你看他两眼炯炯,极像主公,大概正是主公的血肉吧?三人拍手大笑。据《史记·陈杞世家》记载,悲剧便从笑声中开始——
徵舒怒。灵公罢酒出,微舒伏弩厩门射杀灵公。孔宁、仪行父皆奔楚。灵公太子午奔晋。
悲剧造成了陈国的灭亡,国君的丧生,两个大夫、一个公子的逃亡。其他随从之类被杀的肯定还有好些。微舒索性自立为陈侯,结果又引来楚国的干涉,大军压境,杀了徵舒,又不知道有多少无辜的人跟着掉了脑袋。楚国原想把陈国据为己有的,只是后来因为有人反对,才不得不让太子午继位,总算恢复了陈的祭祀。
徵舒的杀机就是起始于那种本能的勃发,那种无法容忍的耻辱感,那种说不清、道不明,且又是全身心的憎恶,当它发作时,只图一泄,既无明确目的,也不考虑后果。他自立为陈侯,那是后来的事,不会是他原初动机。
对徵舒,别人可能因他的弑君篡位而觉得无法原谅,秦王嬴政却肯定对他怀有深深的同情,因为他自己现在也浸没在类似的恨海里。只是他比徵舒更甚,因为他还有一种姑且名之为“望族心理”的特殊心理。与那些自幼生活于帝王世家的孩子不同,他的“望族心理”要到十岁那年才开始萌生并勃发。在这之前只是听母亲训教时说起过,但那毕竟是虚幻的。这一年,他结束了在邯郸的近似流浪的生活,一脚踏进巍巍皇皇的秦王宫,才突然真切地感受到原来自己确实是如此辉煌家族中的一员,流在他血管里的血该是多么显贵和崇高!但在内心深处,由邯郸时期那种饥寒岁月与眼前王宫生活形成强烈反差所产生的自卑感,肯定要潜藏相当长一个时期才会渐渐淡去。他努力争取这个王族对他的承认,不仅名义上,还有感情上。他终于赢得了这一步,其标志便是他获得了华阳太后的欢心。这样每当他跪拜在功绩著于秦土、声名远播于列国的列祖列宗神位前时,便会涌起阵阵强烈的自豪感。他从秦襄公到昭襄王这一长串声威赫赫的名字中汲取到无穷的精神力量,正是从这里,奠定了他极高的自负和自许,立誓不仅要成为秦国的雄主,而且要成为天下的共主!
正由于嬴政的“望族心理”是后起的,因而也特别敏感,也可说特别脆弱,特别具有排他性。有一种隐忧,不时会冒出来折磨他。他不愿想到,却又不可能不想到:他竟会是那样一个母亲孕育出来的男人!
邯郸时期偶尔在母亲房里撞见的那些男人的嘴脸,雍城棫阳宫里那龙凤床上可以想见的情景,还有两个肉滚滚的被称之为他弟弟的形象,甚至那个真假难辨的他是吕不韦私生子的传说也可能有所耳闻……就是这些汇成了一只不祥之鸟展开黑色的大翅膀一直紧跟着他,像长有一对大钳的蝎子不时啃啮着他的心。当那种无处诉说又无法诉说的憎恶感向他袭来的时候,他会突然跳出一个可怕的念头:这么说,流在我身上的血是污秽的?!呵,上天啊,你为什么要这样惩罚我呢?
但这样的自问,只许由他自己暗暗想到;绝对不准许任何人窥测,自然更不容许别人说起,即使暗示也是罪该万死。在这里,经由至高无上权位的催化,自卑感与自大狂混合成了一种可怕的变态心理。作为参照,不妨提一下朱元璋。这位明朝开国皇帝年轻时曾做过和尚和强盗,从现代观点看来,这根本算不得什么。但朱元璋却神经兮兮地因此而制造了大量令人毛骨悚然的惨案。譬如,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为按察使作贺冬表,其中有一句“仪则天下”;澧州学正孟清为本府作贺冬表,用了“圣德作则”一语,都是歌颂性的,却万万没有想到大祸临头,竟被处以极刑。还有,祥符县学教谕贾翥为本县作正旦贺表,其中有一句“取法象魏”;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贺表,用了“体乾法坤”一语,两人也复因此成了钦定要犯,立刻处斩。这样的案例还可以抄出长长一大串,这些人真叫做脑袋掉了还不知是怎么掉的呢!
朱元璋因何而龙颜大怒呢?原来他以为他们都在暗示隐藏在他心底的忌讳。“仪则”、“作则”中的“则”不是与盗贼的“贼”读音相近吗?“取法”的谐音是“去发”;“法坤”的谐音是“发髡”,那意思不都是剃了光头吗?大胆刁民,竟敢如此亵渎本皇,还不罪该万死!
如此奇特的联想,只有自己存有心病,而又时时处处在设法掩蔽、绝不容别人窥测的人,才会有!
秦王嬴政的狂怒,也是由于在他看来别人是在有意揭发他的心病引起的。
弗洛伊德认为人格是由“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构成。秦王嬴政此时这种近于疯狂的变态心理,也可说是与生俱来的依然保留着兽性原质的本我,从潜伏状态中奋起挣脱自我的樊笼而控制了全身。它渴望宣泄,渴望涤荡,因为他手握王权和利剑,便肆无忌惮地用别人的血来宣泄、涤荡自己,这样就制造了一幕接一幕的惨剧。
写到这里,不由感慨系之矣!我国古代曾经创造过令世人瞩目的灿烂的文明,其中也包括政治文明。但这种政治文明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对握有国家最高权力的帝王,没有创造出一种相应的制约机制。要知道人是需要他律和自律的。一个失去他律和自律的人,残存于人性中的兽性便会挣脱樊笼为害他人;而如果这个人还是手中握有生杀予夺大权的帝王,更将酿成巨大的灾难,就像后来做了秦始皇的嬴政炫耀自己手中权力时说的那样:天子一怒,那可就是“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刘向《新序》佚文)啊!
在仲父“换班”背后
让我们赶快接上被打断已久的话头:茅焦会不会被油烹?
依照《说苑》的记载,茅焦非但没有下油锅,而且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就在前面已引起那段文字之后,接下去便是——
皇帝(指嬴政)下殿,左手接之,右手麾左右曰:“赦之!先生就衣,今愿受事。”
乃立焦为仲父,爵之为上卿。
转眼之间,阶下囚跃升到“上卿”的高位,并被尊崇为“仲父”,这只能说是出现了奇迹。接下去便是一个热烈、隆重的大团圆的结局:
皇帝立驾千乘万骑,空左方,自行迎太后阳宫,归于咸阳。太后大喜,乃大置酒待茅焦,及饮,太后曰:“抗枉令直,使败更成,安秦之社稷,使妾母子复得相会者,尽茅君之力也。”
顺便说一下,《史记·秦始皇本纪》只说是“秦王乃迎太后于雍而入咸阳,复居甘泉宫”,没有提到加爵尊号于茅焦。
刘向是西汉人,离秦还不太远,他的记载该是可信的。但秦王嬴政对茅焦态度瞬息之间如此大转变,恐怕不会单是茅焦那样一篇并不高明的说辞之功。如果允许想象的话,我以为其中可能还有这样一个插曲——
茅焦已经到鼎镬跟前,正要纵身跳去,从宫殿后面传出了一个苍老的女人的声音:先生莫跳,先生莫跳啊!……
一位穿着尊贵的绛服的老妇人,在两名太监的搀扶下,从后宫跌跌撞撞赶来。
她就是华阳太后。
正是这位如今在秦王宫里要算最为德高望重的王太后,几个月前救过吕不韦一命,这回又使茅焦免遭鼎镬之灾。
秦王嬴政没有料到已经惊动了后宫,急急下殿迎向王太后请安。太后气得全身颤抖,点着嬴政的鼻子“你、你、你”了好一会也没有说成一句话,却激起了一阵咳嗽。两名太监连忙把她扶到座上,为她轻轻捶背。嬴政恭敬地侍立在一旁。太后缓过气来时,挥挥手说:都退下吧!
当人们都退去时,华阳太后猛然推开为他捶背的太监,神情激愤地对着嬴政厉声斥道:你、你、你如今好大的胆啊!你刚亲政,就接连杀了先王二十七位忠义大臣,还要把齐国来的客人油烹!你以为你亲政就无人管得了你了吗?可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可以代表三世先君来惩治你!刚才我真是想要命令刀斧手把你这个无道昏君推出去斩了去祭祖庙的,你以为我做不到吗?不信你就试试!我只是想到先王驾崩得早,你毕竟还年轻,才没有那样做。现在我问你:你知罪不知罪?
嬴政慌忙跪下说:孙儿知罪了,求老太后饶孙儿这一次。
两个太监跟着同时跪下。
太后说:当初,你刚从邯郸来的时候,给我吟诵《南山有台》,一个多么知书懂礼的孩子,真叫我欢喜不尽。那时候你为我祝寿,祝我万寿无疆。可如今当上国王,就做出此等残暴事来活活气我,你是存心咒我早死不成!算我白疼了你,早知这样,当初就不该让先王立你,早早废了省得我如今看着呕气!
嬴政一听,连连呜咽着说:孙儿不敢、孙儿不敢!老太后要打我要罚我都可以,只求祖母大人一定要保重玉体,千万不要生气……
一边说一边不住地磕头,已经止不住眼泪的滚落。
他是真心的。在这一瞬间,他的正常的人性重新控制了全身,恢复了自我。作为人,他是孤独的。他早已没有了父亲,有一个母亲,但他却觉得无法爱与被爱。众多臣子和嫔妃见他都诚惶诚恐,没有真正的感情交流。唯一能作为长辈来爱他的,只有这位太后。他实在太需要太后的爱了,除了感情需要,他这个来自邯郸的孩子,只有被纳入这位太后的怀抱以后,才最终消除了卑怯的阴影,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是秦国显赫的列祖列宗的后裔,这个辉煌的王室当中最可骄傲的成员。此外,华阳太后高贵的门庭,大家闺秀的气度,都使他沐浴到一种荣耀。
华阳太后见他这样,倒又不忍了,便说:起来吧,你能听我的话,我还是高兴的。我已经老了,疼你也好,骂你也好,都不会有多少日子了。你有空,还像过去那样,常来看看我吧!说着就要回后宫去的样子。
嬴政刚起身,听到太后最后几句话,不由一阵心酸,又不由扑倒在太后面前,伏在她膝上呜呜哭了起来。华阳太后抚摩着他起伏不停的肩头说:我的儿,你倘有为难之处,讲给祖母听听也好。
嬴政抬起头来说:我就是……恨母亲……
——为什么要恨自己亲生母亲呢?
——就因为她……她不该让那么多男人喜欢她!
——呵,我的儿,你怎么会这样想呢?一个女人,能得到许多男人喜欢,或者容貌美,或者有才干,总有她特别引人之处,应该是荣耀的事。我头一回看到你母亲,她那惊人的艳丽就使我心里有说不出的羡慕甚至嫉妒,可你做儿子的怎么反而要恨她呢?
——就因为这样,我就觉得我身上的血不干净。
——哈哈,你真还是个孩子呢!那么我倒要问问你:你一个男人,如今有了王后,还有嫔妃、侍女、才女一大堆,难道将来生下的太子、公主,血就不干净了吗?
——可我是男人!
——女人不也同样吗?
——但是……
——听话。我得去歇息了,你明天就去把母亲接回来吧!
华阳太后出场调停自然纯属虚构,我这样做的用意并非妄想为《说苑》补阙,也不存在要揭露秦王嬴政或为他开脱的动机。我只是尝试着把以暴君面目出现的嬴政仍然当作一个寻常的人来看待,然后寻找一下他此时此刻的心理轨迹。
那么加上华阳太后这么一个因素以后,疑问是否就没有了呢?
还是有。
华阳太后固然可以“软化”处于暴怒中的秦王嬴政,但嬴政还是不大可能在顷刻之间就如此信任和重用一个齐国客卿,要知道“仲父”在当时是一个极崇高的荣誉称号,在整个春秋战国五百余年间,能够享受到此种殊荣的大臣也只有屈指可数寥寥几位。
原来的仲父吕不韦失势了,一夜之间突然又冒出了一个新仲父,这种仓促的“换班”是否意味着背后另有蹊跷呢?
郭沫若对此作了研究,他在《十批判书》有这样一段评论——
茅焦所以解说于秦始皇的,一定是替太后与嫪氏洗刷,而对于吕氏加以中伤。这是很容易的,便是要说吕氏才有篡夺的野心,而太后与嫪氏是忠于王室的人。要这样说,才能够转得过始皇的意念,而始皇的意念也就真转了。……特惜茅焦之说,内容失传,谅也无法传于外,太史公只是信笔敷衍而已。
此说相当可信。当时游说于列国之间的说客,都是些极有头脑和眼力的人,他们的拿手好戏便是精于窥测尚处于潜在状态的国际、人际矛盾,并以种种巧妙手法组合起来为我所用。当秦王嬴政怒气冲冲地在那里一个接一个杀人时,茅焦就在一旁作精细的观察和研究。他自然早已看出秦王此时真正的对手不是已经镇压下去的嫪氏,而是基本上尚未触动的吕氏,因而此时秦王杀性之起分明出于感情用事。他又很懂得心理学,知道像嬴政这样性格刚烈的人,需要等他积郁在胸口的怒气释放到相当程度才可进说。这“相当程度”是极难掌握的:过早白白赔上一条命,过迟就显不出“说”的功绩。秦王嬴政已经杀了二十七人,茅焦出场了。他那篇早有准备的说辞其核心内容,就是劝说秦王将惩治重点从嫪氏转向吕氏,或者不妨归结为这样一句话:大王,你不是要完成统一大业吗?那就请赶快校正一下您的靶心吧!
至于郭氏所说的“为太后与嫪氏洗刷”的话,我还是觉得茅焦是不会说的。对太后,他只及母子之情;对嫪毐则只字不提。因为他深知那是一个感情危险区,其下有陷阱,他不会那么傻!
这样,处于盛怒中的秦王嬴政,听茅焦一说,突然记起了早已自许的那个宏大目标,又看清了实现那个宏大目标眼前急需清除的真正对手。茅焦的说辞只有以转换箭靶为核心,才会对秦王产生振聋发聩的作用,茅焦自己也才会有立刻爵为上卿、尊为仲父之可能。
后来秦王嬴政对嫪毐集团的处理接连降温,而对吕不韦的处理则日益升级,这一成反比例发展的事实也证明了茅焦很可能起过这一类作用。
秦始皇十年(公元前237年),同是一条开始封冻的渭河,在它北岸东西向的驰道上,有两队车驾正在行进着。那气势宏大、人情欢畅的一支是从雍城向咸阳过来的,居中的那辆金碧辉煌的乘辇上坐着一对母子,右边是秦王嬴政,左边是太后赵姬。那仅有三五辆车乘、人情沮丧的一支,是由咸阳向东出关去河南的。已被撤去丞相职位的吕不韦就坐在中间那辆前后用荆条遮蔽起来的轵车上。他与他年轻时代相爱过的情人,与他悉心教导和辅佐过的秦王,就这样擦肩而过,未能见到一面,而且此生永无相逢之日。
如前文所述,对吕不韦的惩处已有过两次:第一次是欲杀而侥幸未杀;第二次是免去相位,幽禁起来。
接下去作出的是第三次:逐出咸阳,“就国河南”,即回到他的封地河南。
这河南不是现在的河南省,系古邑名,指如今河南省境内洛阳西郊涧水东岸之地。吕不韦的这片封地是异人(后更名子楚)立为庄襄王时封给他的:“封为文信侯,食河南雒阳十万户。”据《史记志疑》引金耀辰语谓:“河南即周王城,雒阳即成周,并为东、西周之地。”据此则其地当在昭襄王、庄襄王分别灭西周、东周后,才为秦所有。
车乘缓缓通过了函谷关,吕不韦不免会回忆起二十余年前身带重金第一次入关为异人游说咸阳宫的情景吧?人生如戏剧,从入关到出关就演完了全剧的主要内容而走向黯淡的尾声。
历史上,人们对吕不韦颇多微辞,唯有一位先贤认为他的尾声别具辉煌和深意,那就留到下一节去说吧。 人生必读经典历史丛书:时代帝国三部曲之大秦帝国(上 下)(套装共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