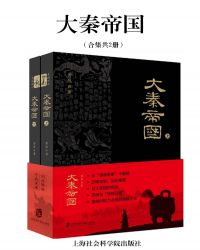由绝对权力点燃的愚昧之火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人生必读经典历史丛书:时代帝国三部曲之大秦帝国(上 下)(套装共2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由绝对权力点燃的愚昧之火
一位智者的忠告
在说焚书坑儒前,我想先介绍几句这两个暴虐事件的历史由来。
春秋战国实际上有两大战场,一个是军事的,另一个是思想的。特别是到了春秋末期和战国时期出现的那种“处士横议,百家争鸣”的盛况,各种学派间相互争战的激烈程度,丝毫不逊色于军事战场,而其广泛性和深刻性则远胜前一战场。
思想战场的近期目标,大体与军事战场相同,即为了治理好本国,战胜对手,并最后使中国复归统一。正是基于这一点,诸侯列国中一些有作为的君主,都清醒地认识到了战争的胜利,不仅需要有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更需要拥有一批奇才异智的谋臣策士。“七国虎争,天下莫不招致四方游士”(《容斋随笔》卷二)。礼贤下士成为时尚,养士之风大盛。魏文侯、齐宣王、燕昭王等,都以好士著称。此外,被称为战国四公子的齐孟尝君、魏信陵君、楚春申君、赵平原君,和后起的秦国穆公、孝公,以及丞相吕不韦,都喜好宾客,以优厚的待遇广招天下学士而著闻于当时。这样“士”这个阶层便从列国纷争中游离了出来。他们通常很少、甚至没有故国观念,不再受地域限制,一旦学有所成,便负笈四游,巧妙地利用诸侯对智力的重视和列国异政所造成的统治空隙,自由地鼓吹或辩驳各种学说。在那样一个战乱频仍的年代里,反而奇迹般地为士这个阶层提供了一个充分表现和施展他们才智、抱负的空间舞台。
但思想战场与军事战场毕竟还是不一样。如果说,军事作为达到某个政治目标的一种手段,随着该目标的实现它的使命也就终结的活,那么在思想战场上所展现出来的那些宏廓的主题和具有恒久生命力的内容,却决不会因为一个短期的目标而停下步来。像道家、儒家、墨家等等学说,是我们民族发展到那个时代的最高智慧结晶。对于这些学说来说,实现统一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内容,它们不仅探讨了统一后的如何安邦定困、经世济民,更深入思考了人生、社会以及宇宙诸多问题。许多重要认识或发现,超越时空局限而闪烁出具有永恒含义的真理光芒。
偏在七国纷战到接近最后冲刺阶段,历史却进入到一道特殊港湾。在这道可说是相互作最后生存肉搏的港湾里,稍微离开鼻尖远一点的思考都成为奢侈或迂腐,急功近利成了共同追求的时尚。就像前三章一节描述合纵连横之说应运而兴时所说的那样:“合纵、连横都是就当时列国现实利害关系成说,学术的理性含量似乎并不多。但你千万别轻视它们。当它们狂飙似地席卷华夏大地之时,其余诸家学说骤然变得黯淡无光,什么老子贵柔,孔子贵仁,墨子贵廉,似乎一下子变得毫无意义。”
现在我补充一句:只是在那个短暂的特殊时期里,道、儒、墨等学说才“似乎一下子变得毫无意义”。其实它们的意义始终存在着,是真理总要发出闪光来。
就在当时,一位智者郑重地说出了他的不无忧虑的忠告。
这位智者便是以孔学继承者自任,吸取了道、法、墨、名等学派若干思想的先秦最后一位儒学大师荀子。
大约在秦昭襄王五十年(公元前257年)前后这段时同里,荀子曾到已经称雄一时的秦国作过一番游历,并与昭襄王和丞相范睢各有一次对话。
对话内容,现在我们可以从《荀子》的《强国篇》和《儒效篇》读到。
范睢请问荀子,对秦国有何观感。荀子根据自己的亲见亲闻,认为秦国山川险固,百姓纯朴,百吏肃然,士大夫“不比周、不朋党”,朝廷“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因而可说己接近“至治”。但他接着说这种“至治”是以一个诸侯国的要求而言的,如果比之“以王者之功名”,那么“其不及远矣”。他指出了“不及”之所在——
是何也,则其殆无儒耶?故曰: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
荀子作为一个儒家,把儒家之于国家的兴亡关系作了突出的强调:如果全用儒学,便可称王;如果参杂用儒,则可称霸;要是排斥儒家,国家就会灭亡。
也许是问题的尖锐引起了秦昭襄王的注意,于是便亲自召见荀子,询问他儒学究竟有无益于人之国。荀子作了长篇回答。他从儒处于“人之上”和“人之下”两个方面作了论述。他似乎是有意先从“人之下”谈起。说儒即使处于“人之下”的情况下,也能做到如何不顾个人“穷困冻馁”,仍然“明于持社稷之大义”等等。昭襄王更关心的当然是儒处于“人之上”如何,他急不可待作了插问,于是荀子便回答说——
其为人上也,广大矣!志意定乎内,礼节修乎朝,法则度量正乎官,忠信爱利形乎下。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不为也。此君义信乎人矣,通于四海,则天下应之如讙(齐声相应)。
这次对话的结果是:“昭王曰善”。
后来的事实说明,秦昭襄王的这声“善”,不是无辞辩对,便是出于礼貌。实际上终昭襄王一生,都没有采纳荀子的忠告。后继的孝文、庄襄二世都匆匆而过,便传到了秦始皇;而秦始皇可谓独尊法家,非但忠实信奉和推行韩非学说中的法、术、势那一套,而且往往把它们引向极端,因而离荀子的忠告更加遥远。不过,昭襄王也好,秦始皇也罢,之所以把荀子的忠告置于脑后,固然有他们性格和学养的因素,但更为主要的还是他们所处的特殊的时代使然。试想一下,如果真要照着“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不为也”去办,昭襄王还能称雄诸侯吗?秦始皇还能兼并六国吗?应当承认,他们是被时代推选出来的雄主,特别是秦始皇,他是如此善于发现和抓住机遇,全不顾旁人如何劝说,即便是智者的忠告也罢,断然作出对策,采取一切能够采取的手段,去摘取那颗分明已经成熟的果子。在这方面,荀子显然望尘莫及。
秦始皇干脆利索地获得了全胜。但这只是军事战场的全胜。当时或至少事后他应当认识到:如何同时获取思想战场的胜利呢?
很可惜,他没有。
在秦国有一个人,倒是早就这样思索过了的,他就是吕不韦。
如果说,荀子的忠告突出了对儒学的强调多少还带有门户之见的话,那么吕不韦以他的《吕氏春秋》表明,他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具备了大统一共主的胸襟。思想不可能用暴力去消灭,论战的胜利并不意味着一种思想消灭了另一种思想,而只能是在更高层次上兼容了诸家之长。《吕氏春秋》正是力图在执守根本道义,即所谓“执一”的前提下,采取一种较为宽容的政策,尽可能使诸家之长都能为未来的统一国家所用。近些年来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发表了类似这样的看法:“如采用《吕氏春秋》作为施政方案的话,秦王朝断然不至于这样短促灭亡。”(杨宽:《吕不韦和吕氏春秋新评》)纵然历史不能假设,但从理论上这样推断,还是相当可信的。
可惜的是,秦始皇在无情地清除了吕不韦集团的同时,又如同弃掷敝屣似地抛弃了曾经作为他启蒙课本的《吕氏春秋》,非但当时和事后都没有去想一想秦国历来偏重法家路线的传统有何不足之处,帝国建立后反因暂时的成功而更加执迷于严刑峻法和穷兵黩武,超负荷地使用还处于初创时期的帝国机器。在这种情况下,兼并时期因迫于大势而处于潜伏状态的种种矛盾便日趋表面化和激烈化,秦帝国的最后崩溃已是指日可待的事。
能够较为清醒地预见到这种危险的,不是别人,又是那些多智、饱学而又颇有政治斗争经验的“士”这个阶层。
曾经在群雄纷争年代扮演过那样重要角色的各派学士,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如今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大致说来,有这样几种情况——
一是隐姓埋名,浪迹天涯,寻找机会作反秦之举。如前面已提到张良、张耳、陈余等等都是,已被杀害的高渐离也属这一类。
再一种情况是与帝国采取不合作态度,因慑于高压,有的归隐山林,与世无争;有的潜心学术,闭门著述。前一类最著名的有所谓“四皓”:东园公、甪(lù)里先生、绮里季和夏黄公。他们退入商雒,隐居肺山,作歌唱道:“莫莫高山,深居逶迤。晔哗紫芝,可以疗饥。唐虞世远,吾将安归?驷马高盖,其忧甚大。富贵之畏人,不如贫贱之肆志。”(《高士传》)后一类,如汉初传《诗》的浮丘伯、申公、穆生、白生,传《易》的田何,传《礼》的高唐生,传《春秋》的公羊等等。
第三种情况是归顺了秦帝国,成了帝国中央或地方政权机构官吏。《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多次提列“博士七十人”,原来当系为各派学士,其中可能又以来自原六国的居多。在地方政权机构担任职务,总数自然要超过此数。譬如孔子的八世孙孔鲋,在帝国时期就曾做过原鲁国地区的“文通君”。
这第三类学士,要算是对秦帝国虽驯顺的一类。秦始皇看中他们的,可能也正是这一点。帝国任用他们自然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必须绝对忠实于始皇帝和秦帝国,不允许把原有学派的主张带进来。
可以想见,他们之中多数人为了保持生存和禄位,是不能不阿曲以取容的。但他们是历经数百年百家争鸣的最后一代传人,自由辩说几乎已成了他们生命的组成部分。而深厚的学养和丰富的历史知识,又使他们很容易看到荀子当年忠告中预言的那些可能出现的恶果,如今不幸而正在成为现实。他们常常有一种骨鲠在喉的感觉。不管他们将要说出来的见解是否带有学派偏见,从主观上说,他们之中多数实在是忠实于帝国、忠实于秦始皇的啊!
但此时的秦始皇,已经变得连这样的不同见解也无法忍受了。
一旦发觉那个思想战场还隐蔽地存在着时,他便使出了在军事战场获得过一次次全胜的老办法:血与火!
李斯的三级跳
笫一个暴虐事件,却是由一个喜庆场面开始的。
据《史记》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寿。”
有个博士仆射周青臣,先向秦始皇祝寿进颂,颂词内容与巡游碑石刻辞一个调调,无非是“日月所照,莫不宾服”,“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等等。
秦始皇听了很高兴。
就在这时候,出现了一个异样的声音。博士齐人淳于越说了这样一番话——
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通“猝”)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
这篇直犯“龙颜”的强谏,使喜庆气氛顿消,朝堂空气立刻紧张得凝结起来。
这位淳于越,便是太子扶苏之太傅。他的进言包含两层意思:第一,认为像周青臣那样当面阿谀皇帝只会加重皇帝的过错,不能算是忠臣。这表明淳于越依旧保持着一个学士的风骨,且确实出自一片忠心,但他所面对的阻力却无比强大。因为这样当面阿谀秦始皇,既不是周青臣一个人,也不止是这一次。从帝国建立开始,它实际上已形成为一项法定的制度。
第二,认为应当“师古”,即效法古代,实行封建制。他举出实例以史为鉴:齐有田常,姜齐终为田齐所代;晋有六卿,六卿之中的韩、赵、魏后来瓜分了晋国。秦帝国如果不分封子弟,一旦出现像田常、六卿那样重臣起事作乱,没有子弟封国的“辅拂”,帝国又“何以相救”呢?
关于究竟是实行封建制还是郡县制的争论,早在八年前就有过一次。因何而旧案重提,史书没有提供答案。事实上,此时郡县制早在全国推行。不久随着南征北伐的胜利,又在岭南增设了三郡,在北方新置了四十四县。说是淳于越想再来翻个个儿,主张重新全面推行封建制,未免距离现实太过遥远。一种可能是,八年来,鉴于强力全面实施郡县制而引起的一些矛盾,尤其是不安定因素已不断有所暴露,他希望局部实行一点分封以为辅助。进言中特别提到田常、六卿那样的潜在危险,想必也是有所指的。如果真有所指,那肯定是指李斯。八年前的那场争论,正是以主张郡县制的李斯驳倒主张封建制的王绾为结局的。当时王绾为相;两年后,王绾的名字在秦始皇东巡的随从名单中又出现过一次,从此再无影踪。而与此同时,李斯受到秦始皇的更多的重用,不久便接替了王绾的相位。相传巡游中所立碑石刻辞均出自李斯之手,那些恰恰正是淳于越最反感的标准“面谀”。
秦始皇大概已是怒不可遏了,但他却还强忍着,与八年的的那场争论一样,又下谕旨让群臣讨论。
李斯是个极机敏的人,即使淳于越纯属无意,他也能听出那弦外之音来。他立刻作出了长篇驳词。不能说他起来反驳全是因为对方暗指了他,但有了这么点因素他的驳词就更加咄咄逼人。他的战术是跳跃式的:淳于越在进言中对“面谀”的指责和对重臣的忧虑,他一概置之不论,一跳,由实跳到虚:从该不该“师古”的高度立论。这一招,确实颇为高明,这使他的讲话听起来有一种前无古人,独领风骚,不断奋击进取的气势,很合秦始皇的胃口。他是这样说的——
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
两点结论:“师古”之路不通;淳于越是个“愚儒”。
事情到此本该了结了。李斯忽而话锋一转,又一跳,从淳于越这一个别“士”,进而对帝国整个“士”阶层发起责难——
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于下。禁止便。
李斯所以要对整个士阶层发起进攻,很可能从日常接触中摸到了秦始皇对士已经很厌恶的内心。不过我能说出来的根据只有一条,就是登泰山进行封禅礼前后鲁地儒生给秦始皇留下的不愉快的印象,《史记·封禅书》特地记过一笔:“由此而绌儒生。”在李斯看来,只有在诸侯纷争时期,才需要以优厚的待遇招致那些游学之士;一旦统一局面出现,帝国子民只要做两件即可:所有百姓老老实实种田做工;所有士人一门心思学法守令,不使自己言行违禁。可如今儒生学士们还在引古论今,说三道四,那不就是惑乱黔首、率群造谤、结党营私吗?他认为如此下去,就会降低皇帝威势,因而必须明令禁止!
淳于越不过是在朝堂上说了那么几句话,李斯却一下子推演出这么一大套吓人的罪名来,他这第二级跳也实在跳得太远啦!
不过仔细想来,李斯纵然有夸大,恐怕也并非全是无中生有,至少说明了学士们对朝政是有不满的。“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在朝堂上他们只好在内心暗自嘀咕,走出朝堂才敢相互有所议论。其中自然也不会没有意在反秦之论,但多数应属于对帝国未来命运的担忧。李斯的这种描述,恰恰反映了多数学士在秦始皇高压和独断下,那种报国无门的苦恼和无奈,怎么也得不出“惑乱黔首”、“率众造谤”、“党与成于下”的结论来!
李斯却还觉得不够,第三次再跳一级:从人跳到书,奏请秦始皇烧书。除“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外,其余书都要烧。所谓《焚书令》的主要内容为——
(一)命令史官将所藏史书,除《秦记》外全部烧毁;
(二)除博士掌管的国家藏书外,天下凡藏有《诗》、《书》、百家诸子著作者,一律将此类书缴到所在郡县主管处烧毁;
(三)有敢三三两两谈论《诗》、《书》者,处以死刑并暴尸示众;
(四)有敢以古非今者,灭族;
(五)官吏若已发现而不检举者,与之同罪。
(六)本法令公布后三十天内还不焚烧者,脸上刺字,罚做筑城劳役。
秦始皇对李斯的全部建议,说出了一个启动邪恶之门的字:“可”!
于是一场焚毁文明的大火便首先在咸阳,接着又在全国各郡县守令所在地熊熊燃起。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大都设有史官专门从事历史记载。这类记载中,难免有对当时秦国的“刺讥”,这当然是秦始皇最不可容忍的,所以被列为《焚书令》第一条:除《秦记》外一律焚毁。就因这一烧,致使司马迁写《史记》时屡屡感到列国资料的缺乏,连声长叹:“惜哉,惜哉!”(《史记·六国年表》)
《诗》、《书》及百家著作,也是焚烧重点。这类书我们现在之所以还能读到,全赖当时一些志士仁人冒着生命危险千方百计地转移和秘藏。这样的人一定很多,见之于史书记载的,除了上文已提到的孔鲋,还有孔腾和伏生——
孔腾,字襄,畏秦法峻急,藏《尚书》、《孝经》、《论语》于夫子旧堂壁中。
秦时禁《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大兵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
以上均引自《汉书·艺文志》。
今天,当我们读着这些“火”口余生的典籍时,不能不为那些冒死保存人类智慧和文明作出贡献的先哲们深表敬意。而当我们看到古籍那些残简缺篇时,又不能不谴责那场罪恶的大火!
不管有多少理由,如说什么“厚今薄古”呀,“统一思想”呀,都不能为这愚蠢之举辩解。这场大火做了一个极坏的结束:春秋末期以来那种百家竞说、生气蓬勃的自由探索氛围,不管人们如何向往,从此永远只存在于高远的历史天空之中。这场大火又开了一个极坏的头:它使历朝历代那些名目各异的摧残文明之举仿佛有了先例可援,其流风“久远得多么骇人啊”(鲁迅语)!此外,难道还需要再说些什么吗?
“秦坑儒耶?儒坑秦耶?”
李斯的第三级跳,从人跳到了书,学士们侥幸得免了吧?不,后来的事实说明,这只是暂时放过,相隔不到一年。焚烧竹帛的余火未灭,秦始皇又制造了一起暴虐事件:发生于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的“坑儒”。
事情的导火线是侯生、卢生这两个曾被秦始皇派去求仙药的方士的出逃。据《史记》本纪记载,两人在出逃前有一番议论,认为秦始皇这个人,“天性刚戾自用”,特别是兼并六国后,“以为自古莫及己”,又极度“贪于权势”,“事无大小皆决于上”,自己日夜操劳,对大臣都不信用。而且按照秦法。一种方术只准施用一次,“不验,辄死”。因此他们认为不能再为这样的人求仙药,“于是乃亡去”。
秦始皇听说侯、卢二生逃走,雷霆大怒。本纪载录了他大怒时说的一番话,内容有两条,一是认为侯、卢二生以及徐、韩终、石公等人非但骗去了他数以巨万计的财物而始终未见仙药影子,而且还在背后诽谤他。如果单是这一条,那么或关或杀也只涉及到少数几个方士,但是还有第二条。秦始皇的意识流也像李斯一样飘忽无规则,突然从方士跳到了儒生,从少数人跳到了多数人——
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
廉问,意为暗中察问。这就是说秦始皇动用了现代人称之为特务的秘密侦探手法,但即使用了这种方法,也只是“或为妖言”:有的人可能有妖言惑众嫌疑。秦始皇竟以此为据,诏令御史拷问所有儒生,制造了一起史无前例的骇人听闻的惨案——
于是使御史悉问诸生,诸生传向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
四百六十余名学士,就这样在严刑拷问下,深文巧诋,辗转牵引,然后以“犯禁”的罪名一起活埋了!这些人的姓名一个也没有留下来。我能够想到的就是一年前在朝堂上直言进谏的淳于越,此后史书上再也见不到他名字,估计很可能就在被活埋之列。
这时候的秦始皇已经毫无理性可言。他杀人完全是出于感情用事,即为了宣泄因受骗和受人背后指责所引起的狂怒。
事情到此还没有完。据一些史籍记载,还可能发生过第二次坑儒事件。
东汉人卫宏在《诏定古文尚书序》中有这样一段话——
秦既焚书,恐天下不从所改更法,而诸生到者拜为郎,前后七百人。乃密种瓜于骊山陵谷中温处。瓜实成,诏博士诸生说之。人言不同,乃令就视,为伏机,诸生贤儒皆至焉。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终乃无声也。
这是说设下了两个骗局。先是以封郎官为诱饵,把全国七百名学士骗到咸阳,接着又以种于骊山陵谷“温处”的瓜提前结实这种异常的自然现象,骗他们去一边观看一边议论。正当他们相互辩论得难解难分时,预先埋伏的机关突然发射,将七百名学士全部坑杀。此事如果属实,秦始皇为了杀人,真可谓煞费苦心。但因过于使用了心术和机巧,使有些学者怀疑它的真实性,认为这种做法不符台秦始皇的地位和性格。如《史记志疑》引《雍录》语说:“议瓜之说,似太诡巧,始皇刚暴自是,其有违己非今者,直自坑之,不待设诡也。”不过卫宏的这段材料,屡为《史记·儒林列传·正义》、《汉书·儒林传注》、《后汉书·陈蕃传注》等所引;而且骊山温谷从此就叫坑儒谷,在汉代又称愍儒谷,唐代还称愍儒乡、旌儒庙,至今那里还流传着一些有关焚书坑士的民间传说,当不至于纯属子虚乌有。这段材料至少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秦始皇焚书是既焚咸阳也焚全国各郡县的,而他所坑四百六十余名学士全属咸阳,还有全国各地数量更多的学士,按他一贯的性格和作用,难道能网开一面、稍示宽容吗?
富有戏剧性的是刘向《新序·反贾》的一则记载:秦始皇坑儒的导火线是方士侯生、卢生的出逃,后来其中之一侯生终于被捉到,并押解到了咸阳,秦始皇将会怎样对待他呢?
据说,秦始皇特地“升东阿之台,临四通之街”,准备在大庭广众之下把侯生通骂一顿然后“车裂之”的。但侯生倒过来却把秦始皇大骂了一通。从生活上如何竭欲穷奢,一直骂到对百姓如何横征暴敛,然后与历史上圣王比,自然根本无法比;又与历史上暴君比,则认为千倍、万倍于他们。秦始皇听了居然“默然之久”,接下去的对话是——
始皇曰:吾可以变乎?,
侯生曰:形已成矣,陛下坐而待亡耳。……
始皇喟然而叹,遂释不诛。
刘向完全是在做小说,无非是想借这么一个形式对秦始皇作一番讽刺和痛骂。不过就是作为小说也不甚高明,因为这样的结局明显违反秦始皇性格。此外,《淮南子·人间训》和《湖南通志·方外志》,则提供了侯生、卢生下落的另一种说法。前者认为他们逃亡到了海上,后者说隐居于邵陵云山。
胡亥赶上了末班车
焚书、坑儒两桩暴虐事件,是秦帝国临近灭亡的信号;而这个信号恰恰是由帝国的创建者秦始皇本人发出的。唐代司空图的《铭秦坑》,言简意赅,深刻地揭示了“灭人实为自灭、坑儒即是坑秦”这个平凡的真理——
秦求戾儒,厥民斯酷;
秦儒既坑,厥祀随覆。
天覆儒仇,儒祀而家;
秦坑儒耶?儒坑秦耶?
在坑儒过程中,帝国朝堂上能够稍稍发出一点正直之声的,只有一个年轻人。他多少看到了一点这种暴行将带来严重后果,并曾试图劝谏秦始皇不要这样做。这个年轻人就是秦始皇的长子、淳于越的弟子扶苏。
扶苏的进谏与太傅淳于越被坑是否有关,不得而知。他进谏的主要内容,可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
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
他从天下初定的大势,诸生皆诵法孔子并未犯禁的事实,说明不应对他们“皆重法绳之”;对那样做将出现“天下不安”的严重后果更深表忧虑。秦始皇听了以后却是:
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
此时蒙恬正将三十万之众驻守北边并督造长城。这就是读者在上章之末已经看到过的那一幕:在修建长城的工地上,突然来了一位年轻人……
值得一提的是秦始皇因何而怒?这怒与前怒内涵显然不一样。从后面将要说到的,秦始皇临终前还给扶苏写了特地盖上御玺的遗诏来看,他并没有一怒之下要废黜这位长子的意思。处理此事时,他是恢复了理智的,只是恨铁不成钢,嫌儿子太软弱,成不了大事。其中最使他反感的可能就是那句“诸生皆诵法孔子”的话。扶苏大概忘记了他老子最讨厌的就是早被商鞅、韩非先后分别讥之为虱子、蛀虫的儒家那一套!所以秦始皇决定让扶苏去北监蒙恬,使其握有相当大兵权(详后文),很有点要他到艰苦的环境和重要的岗位上去锻炼锻炼的意思吧?
但扶苏的离开咸阳,对秦帝国未来命运来说,却实在是超出秦始皇意料的一个严重事件。
据翦伯赞在《秦汉史》中分析,随着秦始皇的进入暮年,这时候的帝国宫廷内部大致已形成了三种派别政治力量。其一便是以扶苏为首的新贵族派,大多数公子和公主都属于这个派,因扶苏系长子,在习惯上最有可能被立为太子而享有特殊地位。其二是以李斯为首的官僚派,这一派拥有雄厚的财政后援,把持着中央机构,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秦帝国大政方针。其三是以赵高为首的宦官派,宫廷中的“中人”或“内官”大多属于这一派。他们包围着秦始皇,掌握着宫廷的机要和秘密,一旦出现某种时机,就会利用他们能够接近皇权核心这个极有利的条件,运用他们的机智和狡诈成为主宰局势的一种特殊力量。
扶苏为人,据赵高评价是“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见《史记·李斯列传》),显然不大为其余两派人所喜欢。扶苏离开咸阳出现了空缺,等于为两派发展势力腾出了余地,该是使他们高兴的;但扶苏一旦与过去曾战功赫赫、如今又拥有数十万之众的蒙恬结合,对他们来说又是一桩十分可怕的事情。由于秦始皇的狂暴,既使内外各种矛盾日趋激化,又使自己生命快速迫近黄昏,于是,还不满十周岁的大秦帝国,双脚已踏上了命运女神福耳图娜那个不断转动的圆球,它的未来岁月布满疑云迷雾,变得不可捉摸起来。
不过秦始皇作为开国大帝,在他亲手创建的那样一种集权专制格局下,只要他活着,不管病、老、昏、暴到何种程度,他的绝对权力决不会动摇。各派也只能在暗中较劲角斗,纵然日趋激烈,却不可能表面化。
第二年,即秦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度过的。扶苏频频送来谏书,除了对政局的关切,也表明他这位长子对未来的大位是决不肯轻易放弃的。李斯则继续发挥自己这派优势,竭力从政治主张方面迎合秦始皇。此时秦始皇已改称“真人”,因相继发生的陨石事件和玉璧事件而内心愈益郁闷。李斯就组织手下的一批博士创制《仙真人诗》,并配以音乐,为秦始皇演奏。赵高此时的权位虽然还难与扶苏、李斯正面较量,但他是秦始皇第十八个儿子胡亥之傅;而这个才智平庸、离太子之位不下十万八千里的小男子,却因长子扶苏的出走而突然升值。赵高巧妙地抓住这一时机,把赌注全押在刚满二十岁的公子胡亥身上,百般调教他如何利用秦始皇开始进入老年的孤寂心理,想方设法去亲近和讨好这位皇帝兼父亲。即将出观的事实证明,赵高的计谋获得了巨大成功。
又过了一年,现在已到了决定秦帝国未来命运的最后一年了: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
这一年十月,也即秦历新年,秦始皇将作最后一次全国性巡游。
这次巡游,随行的大臣有左丞相李斯、上卿蒙毅和中车府令赵高,右丞相冯去疾则留守在咸阳。
在以往的四次巡游中,从一些地方志的记载来看,秦始皇大概都要选心爱的子女带在身边,以排遣旅途寂寞的。其间,并有一子一女先后死于旅途:子葬于大城县段堤村(《顺天府占迹考》引《城冢记》),女葬于曲阜女陵山(《山东通志》)。
前四次,胡亥都没有获得这项殊遇。这一回,由于近一年多来他已获得了秦始皇的相当欢心,因而当即将成行时,他过来请求说:臣儿最喜欢到父皇帝国各处看看,请父皇恩准。秦始皇听得高兴,果然答应。
由于此事关系重大,《史记·秦始皇本纪》特记下一笔:
少子胡亥爱慕请从,上许之。
就这样,胡亥抢搭上了始皇全国大巡游的这趟末班车。
因此一举,当皇冠出人意料地忽而从天空降落时,起决定作用的便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连历史老人也显得无奈了。 人生必读经典历史丛书:时代帝国三部曲之大秦帝国(上 下)(套装共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