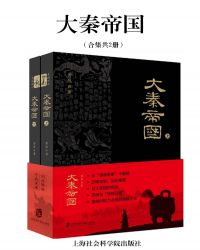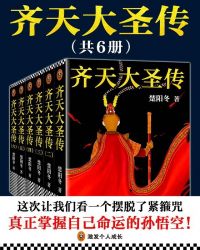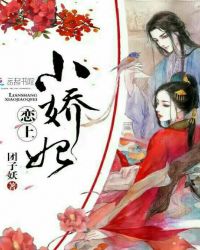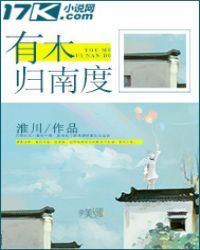中原人对历史的再创造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人生必读经典历史丛书:时代帝国三部曲之大秦帝国(上 下)(套装共2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中原人对历史的再创造
秦帝国何以二世而亡,正如学者们已经作出的研究那样,是由政治、经济以至道义等多种原因造成的。如果从本书特定的视角出发再多作些思考,就可看到还有一种不应被忽视的精神力量那时起过相当大的作用,它就是故国心理,或者叫作故国观念。
这里的国是指诸侯国,与我们现在说的国家、祖国还不是一回事。诸侯国也即封国。我国至商代,分布在中原一带的,大致还是一个个以血缘为维系纽带的氏族群体,各自保持其独立发展。周灭商而兴,因分封诸侯而在中原划分出许多封国,这便出现了同一氏族分属于不同封国,而同一封国又由不同氏族混合而居的情况。开头,封国的建制是很松散的,封国之间也较少往来,但时间一长,情况渐渐起了变化。所谓战国七雄,大都已有数百年历史,最年轻的韩、赵、魏也存在了一百多年。更重要的是如此漫长的时间,几乎都是在相互争战中度过的。战争原是个无情的怪物,但在参战各方内部却因面临战争一下子变得命运与共而反比平常更为有情。本来封国都属诸侯宗室,与平民并没有多少关系。但战争一来,动辄“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这便使得国中大多数人渐渐把自己与国家的兴衰存亡联系了起来。此外,由于世代聚居一地,加上较为接近的民俗世情,自然也会产生一种亲和感。因而所谓故国观念,对故土的缱绻之情,当时该是普遍存在的。在秦之前,无论商汤或周武,都是以联合诸侯共伐“无道”的形式据有天下的,那样除了夏桀或商纣宗室,其余诸族大都不会有被征服的感觉。但秦却没有条件这样做。秦灭周根本用不着联合诸侯,轻而易举,灭周后却还得花很大力气逐个吞灭诸侯才能一统天下。这也就是说,秦的天下主要不是由灭周而得,而是从诸侯手里夺来的。这样,秦始皇在挥剑削平六国的同时,也就血洗了六国人民的故国之情,无意间在数倍于秦本土的中原大地上普遍撒下了反秦种子。
这还只是问题的一面。
同样的,秦人也有自己的故国观念。他们在这片关中土地承受过屈辱,经历过艰辛;如今,凭着这片土地,他们居然把那些多少世代来一直在他们头顶高视阔步的中原诸侯一个个降伏在自己脚下,这真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事变啊!这个事变反映在秦人头脑里就是:秦人征服了中原人!既是征服者自然有权惩罚被征服者。秦始皇在兼并六国过程中动辄“屠城”、“灌城”,连普通士卒也受到影响,常常以征服者自居,傲视以至凌辱中原人。秦始皇虽然做了天下共主,但他的故国观念似乎没有多少改变。他建立的帝国仍然称秦,他毁废六国国都,却把那些各具特色的宫殿在咸阳照式照样造了起来,甚至开始全国大巡游时,也先要在自己故国兜一圈。这样,当帝国大厦在华夏大地上建立起来时,无论在秦人或在中原人观念中,只有一根柱子是属于秦的,其余六根柱子分明都还残留着当年列国标记。这当然非常危险。
在秦国兼并六国决战中,楚国反抗最为激烈;楚亡后,楚人对被秦国害死的楚怀王,对在抗秦战争中壮烈牺牲的大将军项燕,都一直深深怀念着。特别是楚国出了位伟大的诗人屈原,在他那些雄浑瑰丽的诗作中,把产生于特定时空条件的故国之情,升华到了具有永恒魅力的一种人类共有的纯真感情。所有这些都说明楚人的故国之情比其余五国更为浓烈。如果历史照此轨迹发展下去,那么楚南公的预言很可能就会应验:“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见《史记·项羽本纪》)
而如果楚南公的预言果真应验,那么中国历史就会陷入秦人—中原人相互报复、列国存亡交替的循环圈,那将是莫大的悲哀!
历史没有走这条路。
或者说,当历史的车轮很有可能折入这一岔道的时候,被两只巨人的手一左一右握住,换了个方向,由岔道转入到正道。
不过那实在不是什么巨人之手,而是两个普通贫苦农民沾满牛屎、长满老茧的手。他们的名字一个叫陈胜,一个叫吴广。
陈胜、吴广这两个秦帝国的最主要的掘墓人,同样也是由秦帝国自己造就的:帝国首先剥夺得他们一无所有,接着又逼得他们无路可走。而在帝国时代,处于这种境遇的人千千万万。因而这两个人代表着一个阶级,代表着帝国人口构成中的最大多数。这样,当他们面临到所有可能选择的出路都写着一个“死”字的时候,他们选择了造反,同时也就唤醒了所有同类遭遇的人。事情便这样出人意料却合乎情理地发生了:最先起来倾覆秦帝国大厦的,不是六根柱子中的任何一根柱子,而是肩负着整座大厦重压的基础。对于陈胜、吴广所代表的农民阶级来说,故国观念已降到极其次要的地位。道理很简单:人总得首先能勉强活下去,才能再顾及其他。陈、吴等起义的初衷就是要争取基本生存权:“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史记·陈涉世家》)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我们要活!这声呐喊因它激起了最大多数人的共鸣而显得如此洪亮而有力,以至包括项羽、刘邦在内的所有起义者一开始都自愿归之于陈胜、吴广的大旗之下。这就清楚不过地向世人表明,这场斗争的性质既不是六国为复国而抗秦,也不是中原人联合起来共同反秦;而是帝国范围内所有被奴役的阶级、阶层、民众,一齐起来抗击秦帝国的暴政。
所以我想这样说:随着大泽乡一声怒吼,中国政治斗争舞台上出现了一个全新的人物,他的登场,标志着秦人——中原人之间那个很有可能出现的“循环圈”已被冲破,从此历史将在一个新的起点上演进。
这就是以陈胜、吴广为代表的中原人,客观上对历史作出的一次伟大的再创造。
这里特别值得提一下张良。自从在焚烧中的故国国都侥幸逃亡出来后,张良便以“为韩报仇”作为自己生命的全部价值。一听到陈胜、吴广发难,他便立刻响应;见到项梁后的第一句话就是要求寻访韩公子成,并立以为王。由此不难看出他的故国之情是十分强烈的。但张良又是一个极为难得的能够与时代同步前进的人。随着时变发展,他用自己的理智说服自己的感情,突破“为韩报仇”的狭隘心理,具备了一种创造新历史的眼光和魄力。因而在后来的楚汉战争中,当郦食其建议刘邦以复立六国之后来摆脱为项羽所围的困境时,他详细论述了其中弊端,说服刘邦放弃了这种违背历史规律的做法。
不过在当时,能够像张良这样清醒地顺应历史大势,自觉更新自己观念的人,毕竟只是凤毛麟角。抗秦复国依旧是六国之后的强烈愿望,故国之情更是还相当普遍地存在着。
凡是精神的东西,既无法强行压服,更不能用暴力去消灭。
于是,历史需要遴选出一个恰当的人,来演绎一个悲壮的故事,最后由他自己来对这种观念和这种愿望举行一次葬礼。
选中的人是再恰当不过的:他生于楚国将门之后,长乎故国患难之秋。他身长八尺,力能扛鼎。他从小立下宏志:要学万人敌;要取秦始皇而代之!
此人姓项名籍字羽,以字名世,通称项羽。
项羽简直就是屈原那些雄浑瑰丽诗句的化身,通身闪发着一种纯真、豪放的人性的光辉。只有他堪称是那个时代的真正英雄。他率领江东八千子弟,破釜沉舟,跃马横槊,战遍河南河北,破关西进,杀秦王,焚秦宫,没有等到那场冲天而起的复仇大火熄灭,便又率领着他的江东子弟回马故土。听听,这个南国丈夫说出的话有何等率真!
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
接着,项羽自封为西楚霸王,并一口气封了十八个诸侯王,竟是秦始皇歼灭的诸侯国数的三倍!历史在这里打了个回旋,似乎又要回到那个列国纷争的循环圈。但既然大泽乡的怒吼已经唤醒了最大多数的底层民众,那么历史已注定了这种回旋只能是以项羽为主人公的那个悲壮故事中的回光返照式的仓促一章,其意义无非是为最后的葬礼准备下丰盛的牺牲而已。
清波粼粼的乌江,不过是南国水乡中的寻常一景,此后它却将永享盛名了!因为在这里演出了中国历史上最悲壮的一幕,一位亘古无双的英雄在江畔用佩剑割下了自己价值千金的头颅。
项羽兵败垓下在乌江畔自刎前,乌江亭长欲以船急渡项羽去江东为王,这位末路英雄朗然一笑说道——
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无言,籍独不愧于心乎?
呵,江东有此英雄,河山为之增色!
于是我想,项羽如果战胜了刘邦,那么很可能残暴、昏庸远胜秦始皇,而功业、政绩则无一可与后者相比。但他却是英年而死,死得又如此壮烈,这不仅为他个人生命史加演了一个最为光辉的尾声,也为到那时为止的中国历史写出了一篇悲壮的跋文。项羽的头颅是献给六国亡灵的祭礼,用以祭告他们:诸侯纷战数百年的恩恩怨怨,从此终于永远成为历史。
项羽为昨天打上了一个句号,陈胜、吴广为明天完成了一个开篇。接下去的事便是谁来谱写这部新历史的第一页。
应命而出的是刘邦。
刘邦此人,历史学家们,特别是文学家们,大多对他没有好感。的确,作为一个人,他在慷慨、坦荡的项羽面前黯然失色。但我们还得承认,他是由时代推出来书写这部新历史的合适人选。他有一种本事,就是把从陈胜、吴广直到项羽无数英雄豪杰浴血奋战创造出来的成果,统统收集起来为他所用;随后,又将那些创造者逐个降服或者消灭。这自然不大符合我们这些普通人的道德准则,但在政治学那里,他却会得到一个堂皇的评价,叫作具有“王者气度”。
至于刘邦做了大汉帝国开国皇帝后,一些文人学士见他出身微贱以为脸上无光,便挖空心思为他编造假家谱,说什么刘姓原为帝尧后裔,刘邦祖母是与龙交配才生下刘邦父亲,母亲又是吞了龙珠才生下了刘邦等等、等等,那非但是一派胡言,而且实在是大帮倒忙!因为事情很清楚:如果刘邦真是王室贵族后裔,那么充其量只能做个项羽第二。刘邦的幸运,恰恰在于他是“泗水亭长”这个比平民高不了多少的身份,这才使他能够摆脱故国观念的羁绊,跳出封国地域的拘囿,具备一种气度,一种眼光,直接去继续陈胜、吴广的未竟事业,抓住历史机遇,创立一个真正大统一的大汉帝国。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史记·高祖本纪》)
刘邦在故乡沛县大宴父老子弟时即兴创作并吟唱的这首歌,却确实表现出一种所谓王者气度,它预示着新生的大汉帝国即将创造出一个辉煌的未来。 人生必读经典历史丛书:时代帝国三部曲之大秦帝国(上 下)(套装共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