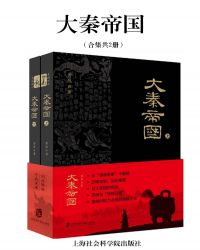被玩弄于手掌之上的和氏璧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人生必读经典历史丛书:时代帝国三部曲之大秦帝国(上 下)(套装共2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被玩弄于手掌之上的和氏璧
“第五纵队”在行动
魏国国都大梁。
一家公馆内,年逾七旬老将军廉颇,正在设宴款待来自邯郸的赵王使者。
两人对席。
只见老将军一拂胸前银髯,以洪钟般的嗓音大吼一声:进餐!
侍从不敢怠慢,立刻穿梭上下。不一会,主客几案上都已摆满了酒食菜肴。不同的是摆在客人面前的都是些精巧的器皿,食物的切割、制作也十分精细;而堆叠在廉颇几案上的都是大桶大盘,那些流着浓油的肥肉块块有巴掌大小。老将军说声请,就畅怀狼吞虎咽起来,不一会面前的饭食已一扫而光。这一餐老将军究竟吃了多少?《史记》本传记了一笔账:“一饭斗米,肉十斤。”
这当然不会是正常进餐了,它实在暗藏着老将军一番颇为悲壮的苦心。
廉颇是赵国负有盛名的大将。他伐齐、攻魏、败秦,屡建奇功,被拜为上卿。他曾一度居功自傲,不甘心位于丞相蔺相如之下;一旦认识了错误,又主动登门“负荆请罪”,演出了一出“将相和”的千古佳话。但人总是要老的。在他年过七旬后,赵王起用年富力强的乐乘来代替他,他却一怒之下攻打了乐乘,后又赌气投奔了魏国。实际上他身居大梁,梦绕邯郸,那颗牵系着故国的心又如何割舍得下!在这种情况下,魏王自然也不会信用他。老将军终日无所事事地住在公馆内,赵国受到秦国侵伐的消息又一个接一个传来,这种日子实在太难熬啦!忽听得赵王派来了使者,他立刻想到很可能赵王迫于强秦威势有了重新起用他的意向,一时欣喜若狂,于是便来了这么一番表演,希望给使者留下一个印象:廉颇虽老,勇猛不减当年呢!
吃饱喝足,廉颇又带客人来到广场,跃马横戈,驰骋如飞,随后又表演了一套精湛的武艺,这才跳下马来,心不慌,气不喘,笑声朗朗说道:某在先生面前献丑了。还望先生代某多多拜上大王,臣廉颇尚有余勇,亟待报效疆场!
老将军说着这些话时,流下了老泪。作过这番表演,他实在已力竭心衰,自知毕竟已老。但他无法忍受在安闲中享尽天年,只要一息尚存,宁愿把血洒在搏杀强秦的战场上。
这时候,秦军对邯郸的威逼正在日益迫近。赵王派出使者去大梁看望廉颇的用意,确实是想去了解一下老将军的健康状况,是否尚有可能骑马出阵。廉颇的这一番表演,留给使者的该是一个忠心烈烈、余勇尚存的老将军印象吧?但他在回报赵王时却说:廉将军年事虽高,饭量倒还不小,只是与臣同坐了不一会儿,就上了三次厕所!
赵王居然就这么相信了,再也不想召用廉颇。
使者为什么要说谎?因为他受了赵王宠臣郭开给的一点金子。
郭开为什么要收买使者说谎?因为他收受了秦王嬴政派出的顿弱等人的大量金子。他从大量的贿赂中分出一点碎金来,就断绝了廉颇最后一次报效故国的机会,不用戈戟弓箭,却实际上替秦国消灭了一员曾使秦军屡屡受挫的大将。
这就是秦王嬴政指挥下另一支地下部队——“第五纵队”的威力。
但廉颇毕竟是一员名震华夏的老将,你赵王不用,中原诸王谁不想拥有他呢?这时候捷足先登者楚王便立刻暗中派出使者以隆重的礼遇迎接廉颇入楚。老将军开头还在等待邯郸方面的消息,后来得知已被奸佞出卖,不由仰天长叹一声,无奈中接受了楚国的邀请。廉颇一入楚,楚王立刻拜为上将,但老将军却犹是浑身不自在,看着楚国军旗和那些穿着楚国军服的士卒,觉得那样陌生,自然也谈不上建功立业。不久便在悒郁中死去。临终前,说了一句很伤感的话:“我思用赵人。”——我连做梦都还在想着指挥赵国将士呀!
廉颇一死,赵国将领中能够抵挡秦军的只剩下一个人,那就是李牧。
李牧因镇守北边和攻燕、却秦屡建战功,已深得赵悼襄王信用,赵王把他视为当年秦国的白起,因而也封他为武安君。要剪除这样一员得宠的爱将,自然要比除掉已经失宠的廉颇困难得多。
于是“第五纵队”便把它的无形而可怕的手插进赵国后宫,出现在赵悼襄王的枕头边。
这个接受了秦国贿赂,开始在赵王耳边中伤李牧的便是赵悼襄王的王后。
据《史记》和《列女传》记载,悼襄王后原是邯郸街头的一名倡女,曾经嫁过男人,可能是出了偷情一类风流事,整个宗族都被她闹得一团糟。后来就做了寡妇。偏是因她长得艳丽娇媚,被赵王一眼看中娶进了后宫。这件事朝堂上下都不赞成,其中尤以李牧反对最烈,而大夫郭开却百般迎合,并因此而得宠。后来寡妇生了儿子迁,便很快被立为王后。她原已对李牧怀着仇恨的,现在又受了秦国珠宝,一举两得,自然更要卖力地告枕头状了。但当时赵王还离不开李牧这员得力大将,所以新王后的谗言效果不大。以后公子迁渐渐长大,原已立的太子嘉自然要倍受新王后的冷落。一幕废立太子的宫廷传统闹剧便由此开场。赵王拗不过新王后的日夜纠缠和郭开在一旁的再三怂恿,终于废了太子嘉而立迁为太子,并由郭开做太傅。公元前236年(秦始皇十一年,赵悼襄王九年),秦军对赵一战,赵国就丢失了阏与、邺等九座城市。病倒在床的赵王一听这消息,就在忧愤交集中突然死去。太子迁即位,这便是赵幽缪王。新王后成了王太后,郭开也被封为丞相。
赵幽缪王五年(秦始皇十六年,公元前231年),也就是魏、韩两国同时向秦国分别献出丽邑、南阳之地以求宽容的那一年,赵国也接连不断受到秦国的进攻。偏在这时,赵国境内发生了大地震。震中在代地,据《史记·赵世家》记载:“自乐徐以西,北至平阴,台屋墙垣大半坏,地坼东西百三十步。”处于天灾人祸双重苦难中的赵国臣民,用他们的观察力和想象力唱出了这样的歌谣——
赵为号,秦为笑。
以为不信,视地之生毛。
但这歌谣在传唱过程中渐渐起了变化,变成了这样——
赵国何号?秦国何笑?
有木生子,盗国盗宝。
邯郸城内无论白发老翁,黄口小儿,都在这样传唱。茶楼酒肆,往来客商都在谈论和猜测:这个将要出卖赵国的、姓李的国贼究竟是谁呢?
这自然又是秦王的“第五纵队”在行动。歌谣首先是从赵王宫里传播出来的,制造者便是郭开和王太后。
已经登上了丞相、王太后这样的极位,按一般常情,似乎应当致力于与李牧这样的武将合作,以抵御外敌巩固自己的地位才是。但他们不这样想。在他们心目中,李牧是比秦国更可怕的敌人。因为他们以为,前者的危险是直接的、经常的、眼前就感受到的;而后者则还隔着一定的时空距离,他们并没有直接感受到。这便是当国家处于存亡绝续生死关头,有些佞臣甚至君主会取“宁与外寇,不与内贼”态度的心理基础。更何况在郭开和王太后看来,秦国哪像是外寇呢?它已经为他们送来了那么多奇珍异宝,还许诺他们更加稳固可靠的尊位,那不正是自己的恩人吗?
于是若明若暗的歌谣,很快又变成了指名道姓的谗言,有关李牧叛赵、秦将要封李牧为相的话,便在邯郸大街小巷沸沸扬扬地流传开来。
将军与到处飞舞的青蝇
李牧不仅英勇善战,而且精于谋略,他曾多年镇守在赵国的北方边境代地雁门郡,防御匈奴。他治军有一套特别的方法。练兵时,每天都要宰牛给士卒吃,直到他们吃饱喝足浑身是劲时,才开始正式操练,且要求极其严格,非达到规定标准决不罢休。他极注意侦察敌情,充分发挥烽火台的作用,所以匈奴稍有一点风吹草动他都能及时掌握。而对匈奴的骚扰活动,他的处理更是与众不同。他下令说:“匈奴即入盗,急入收保,有敢捕虏者斩!”(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就是若有匈奴来犯,应立即坚壁清野,严禁捕虏匈奴士卒,违者定斩勿赦!这样多少年来,还从未与匈奴交过锋,百姓财物倒也没有受损失。只是时间一长,给了匈奴、也包括赵国边境士卒一个印象:以为李牧胆小怕打仗。这件事传到邯郸,赵王很为不满,下令斥责李牧说:身为守边大将,如何能如此怯敌。以后凡遇匈奴来犯,必须出战!
李牧对王命竟敢不予理睬,照旧固守他的不出战策略。赵王大怒,下令撤回李牧,另派别的将领去镇守。在以后的一年多里,与匈奴的大小战争不断,且又每战必败,百姓生命、财物损失惨重,边境又不得安宁。赵王这才只好再命李牧去守边。李牧却来个杜门不出,推托说有病不便应命。赵王再三强令李牧率兵前往,李牧说:大王如果一定要启用罪臣,则请大王允许臣仍依前法,才敢奉命。
赵王不得不答应了他的请求。
这样李牧再度出守雁门,果然还照老样子,从不与匈奴兵戈相见。这么过了几年,匈奴一无所得,更以为李牧只会自守,不会打仗,就准备大规模来犯。再说守边赵国将士,每日只是领受犒赏,严格操练,也都愿有一战,以显身手。到这时,李牧才宣布不日即将与匈奴作一决战,但严命不许走漏任何消息,一切务必听将令行事。他亲自选定战车一千三百乘,骏马一万三干匹,弓箭手十万,能够攻坚执锐的精兵五万,日夜加紧训练。与此同时又命人大出放牧,满山遍野尽是牛羊,以引诱匈奴来抢掠。
果然匈奴眼红了,接连出动几小股人马来劫夺,李牧下令只许败逃,不准还击。匈奴士卒满载而归,把喜讯报告了单于王。单于王非常高兴,亲率大批士卒,汹涌来犯。但这一回他要大倒其霉了,《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是这样记载的:“李牧多为奇陈(通“阵”),张左右翼击之,大破杀匈奴十万余骑。灭襜褴,破东胡,降林胡,单于奔走。”
从此,李牧的威名远震北边,匈奴闻之丧胆,十几年之内不敢接近赵国边境一步。
当秦国在中原拉开大决战序幕后,赵国每每在遭到秦军猛烈进攻的紧急关头,便从北边火速调来李牧率军抵抗,李牧也屡屡得胜。一时间,李牧的名字不仅成了赵国的荣誉和骄傲,对已被秦军强大攻势威吓得惶恐不安的其他诸侯国,也是一种慰藉和鼓舞。
秦始皇十八年(公元前229年),秦王宫内文武大臣齐集,经过商议,最后由秦王嬴政作出了大规模兴兵立即攻灭赵国的决定。
其实所谓大规模兴兵只是为了营造一种声势,要灭亡赵国只需割下一个人的脑袋就行,这个人就是李牧。
杀李牧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宫廷内;也不是秦国派人去杀,而是由赵王自己来杀。这就要看“第五纵队”的工作成熟程度而定。现在秦王认为条件已经成熟了,于是便拿太阿剑的剑锋在地图上那么点了一下。
说起来,赵氏与嬴秦还是同祖。在周穆王时代,善于驾车的造父为穆王御而有功,因而赐造父以赵城,世代为周大夫。幽王后周室衰落,叔带奔晋,事晋文侯。晋文公称霸,赵氏世为霸佐。四传至赵襄,赵、韩、魏三家分晋而有赵国,开国君主为赵烈侯。开始建都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后迁都邯郸。据苏秦说赵王时称:赵“西有常山,南有河漳,东有清河,北有燕国”;“山东之建国莫强于赵。赵地方三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数年”(《史记·苏秦列传》)。自赵烈侯至赵幽缪王(赵王迁),历经九世、一百七十六年。赵为三晋中的强国。其间,锐意改革的赵武灵王,实施胡服骑射,攻灭中山,打败林胡、楼烦,建立云中、雁门、代郡,国势大盛。以后不断与秦较量,互有胜负。自长平一役惨败于秦后,赵国渐次落入低谷。到了末代赵王迁,庸弱无能,奸佞专权,唯一能够抗击秦军的就剩下李牧,真所谓社稷存亡系于一将了。
战幕是这一年的冬季拉开的,且看在司马迁笔下,两国是如何调兵遣将的——
秦国:大兴兵攻赵,王翦将上地,下井陉。端和将河内;羌伐赵,端和围邯郸城。(《史记·秦始皇本纪》)
赵国:秦使王翦攻赵,赵使李牧、司马尚御之。(《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王翦,这位秦王吞并六国的扛鼎大将,现在出场了。这是他在中原战场上第二次亮相。第一次就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他与桓攻赵国之阏与,一战而拔阏与、邺等九城,气得重病中的赵悼襄王一命呜呼。这一回,他将与赵国现存最负盛名的大将李牧对阵,真可谓棋逢敌手,将遇良才,该是有一番好杀的。但是按照谋臣们的计议和秦王的决定,王翦不得不暂时放一放他最擅长的刀剑,而去演一出戏。
再说李牧。
李牧已是第三次被从驻防的雁门火速调回与秦军交战。与前两次不同,这回一踏进邯郸,就发觉周围忽隐忽现的一片嗡嗡声。他惊疑地细细一辨认,竟都是些红头绿翅的青蝇!
青绳就是谗言,就是像青蝇那样到处飞叮而最终将致人以死命的谗言。
在激愤中,他记起了一首诗——
营营青蝇,止于樊。
岂弟君子,无信谗言。
营营青蝇,止于棘。
谗人罔极,交乱四国。
李牧陷入了极大的郁闷和痛苦。
在战场上,他手持长矛能杀退千军万马;在宫廷里,他面对这群嗡嗡营营的青蝇,却无可奈何。
他明知放出谣言说他要反赵降秦的人,恰恰正是那些收受秦国贿赂、卖力为秦国行反间计的人,但他无法去辩白。只有“岂弟君子”,才能“无信谗言”,可如今赵王幽缪左右已被奸佞小人包围,又有谁能听信他的辩白呢?他是一员守边武将,纵有满腹文韬武略,却不明宫廷内部那些暗藏机关,只要一脚踏进,便会落入陷阱。
由王翦统帅的秦军已攻下井陉(今河北井陉西北)。军情火急。李牧不得不含恨立即与将军司马尚一起应命奔赴前线。
两军对峙,各扎下长营。战马长啸,旌旗劲舞,一派大决战前的威壮气势。
由王翦导演的戏就这样开场。
李牧正要下令出击,秦营忽而飞出一匹快马,向赵营送来了以大将王翦名义写出的要求和解的信函。
这使李牧大出意料。但王翦之名,他早已如雷贯耳,且钦慕其为人。何况对方信函陈辞又委婉恳切,自然也不便拒绝。古人有言:来而不往非礼也。李牧当即修书一封,感谢秦方美意,并提出:贵军若能退避三舍,则敝军将遵此行事,并约定地点双方晤谈。王翦立即又复来一信,李牧也随之再致一信。
够了,有这两来两往的书信,便足可致李牧于死命。
李牧并没有因王翦的两次来信而放松斗志,他仍然严命将士作好作战准备,特别要警惕秦军的袭击。
只是他万万没有料到,袭击不是来自正面,而是来自背后;不是来自秦营,而是来自赵王宫。
一队快马,飞速自邯郸奔来,进入了赵军营帐。为首的是宗室公子赵葱与原为齐将的颜聚,他们向李牧宣读了赵幽缪王的一道谕旨。
郭开禀奏赵王说,他已得到密报:李牧临阵叛赵,与王翦信使往来,情况十分危急。赵王一听大惊,立刻派人去暗暗窥察,果然得到“证实”。于是便下达了这道谕旨:撤去李牧和司马尚将军职务,由赵葱与颜聚接替此职。
君主一言定九鼎,全军自然没有一个敢不拥护的。曾经叱咤南北疆场、横扫匈奴和强秦的大将军,顷刻之间已成孤身一人。古人有言:谗言恶似虎。李牧终于看到青蝇变成了猛虎。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说李牧对赵王如此荒唐的谕旨曾经有过反抗,但是没有成功——
赵王乃使赵葱及齐将颜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赵使人微捕得李牧,斩之。废司马尚。
“微捕”就是秘密逮捕。一代名将,就这样被谗言之虎吞没了!后人为纪念这位将军,曾立庙以祀。元代大都闾过此庙时,以《武安君庙》为题赋诗咏叹曰——
策马行行过土门,
特来祠下吊将军。
断碑冷落埋秋草,
遗址荒凉锁暮云。
籍甚名声天地久,
凛然生气古今存。
歇鞍几度伤怀抱,
衰柳寒蝉噪夕曛。
赵王迁自毁长城。失去了主将李牧的赵军,乱作一团,溃不成军。王翦统率秦军,长驱直入,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便占领了邯郸,扫平了赵国全境,时为秦始皇十九年(赵幽缪王八年,公元前228年)。
王翦屯兵于邯郸之北的中山,向咸阳发去捷报,并请示秦王:能否以灭赵之师,乘胜北进,一举攻灭燕国?秦王嬴政得报大喜,却突然作出一个决定:他要亲自去看一看已经匍匐在自己脚下的赵国!
苦难而美丽的童年呵,你在哪里?
庞大的军队,威严的卤簿,出咸阳,越函关,在中原大地上隆隆行进。
端坐在装饰华丽的乘辇里的是秦王嬴政。
这一年他三十二岁,一别邯郸已有二十二个年头。
他突然决定要去硝烟未尽、血流未止的邯郸,首先自然为了炫耀秦国的威势,为了享受作为胜利者看到战败国的土地在他脚下颤抖、臣民们在他马前哀号时的快感。但是否也会有那么一瞬间,油然而起一种游子重归故土的脉脉柔情呢?
我想会有的。
无论童年的生活有多么艰难困苦,一旦被纳入回忆之库,照例要涂上一层玫瑰的色彩,这种色彩还将随着年华的渐次流逝而不断加深。此情此意,人所共有。何况对当时的嬴政来说,并不全都是苦难。此生最难忘的美味,不正是一年一度迎春时节母亲为他做的那碗羹汤吗?最好看的戏,不正是邯郸街头那些不知来自何方的精赤条条的汉子们的角力和杂耍吗?还有,他那最初朦胧的青春意识,不正是从卖唱于邯郸酒楼的那些特别妩媚的女子脸颊上获得的吗?
人生都只有一个真正的黄金时代,那就是一去不再的童年。
这样,当他坐在乘辇里,随着车厢轻微的晃动不断向东行进时,他会看到微风拂过漳河水面那粼粼的清波,听到每年春水旺发时河水向东南流去的哗哗声。纵然他如今已是威震中原的霸主,但他毕竟也是喝着怀抱邯郸城的漳河之水长大的呀!
四周突然响起了狂潮般的欢呼声。
两名一直持戟挺立在乘辇左右的侍卫,小心翼翼地揭开遮蔽在车前的用虎皮精制的茀。
眼前漳河的水波消失了,乘辇已来到邯郸之郊。出现在秦王面前的是一片狂呼着万岁的人群。他们都是秦国将士。
秦王屹立在车台上,俯视着这欢腾的人潮,徐徐进入了邯郸城。欢呼声轰走了童年的所有记忆。他感到自己是那样的崇高和强大,古往今来无人可与匹敌。当他这样想时,便以胜利者的目光,睥睨着这片被降伏的国土,以及国土上蝼蚁般的人群。
秦王嬴政就这样进入了赵王宫。
王翦拜见秦王嬴政后,说赵王迁已做了俘虏,等待发落。
随着阵阵喝斥声和锁链磕撞的声响,赵王迁已跪伏在阶前。他只是牲畜似地唔唔呜呜了几声,说不成一句话。王翦命人把顶在赵王迁头上的一张帛书呈上来,侍者代为念道:
罪臣赵迁,万死难赦;
衔璧舆榇,乞赐就木。
秦王突然爆发出一阵得意的大笑,大声说道:将璧玉呈上来,待寡人一观!
所谓“衔璧舆榇”,是上古曾行过的一种投降重礼。投降者背负棺木,意为等待处死;口衔璧玉以为进见之礼。不用手持而用嘴衔,是因为双手已自行反剪着。赵王迁刚才唔唔呜呜说不成一句话,就是由于嘴里衔着璧玉的缘故。
璧玉把玩在秦王手心。他看出来了,这正是那件价值连城的稀世之宝。不由朗声大笑着说道:这不正是先王欲以十五城相换而不可得的那块和氏之璧吗?
众人听说,也都投去惊奇、兴奋的目光,啧啧赞叹不绝。
在这块璧玉上已经演出过楚国卞和“三献璧玉”、张仪“失璧受辱”和赵国蔺相如“完璧归赵”三个故事,分别表现出坚定执著、不甘屈辱的昂扬的人格精神。现在正在表演的已是第四个故事,那是一种卑微的生存欲望,姑名之曰“以璧赎命”吧!赵王迁虽在投降书中“乞赐就木”,但此刻控制他全身的却是一种求生本能。他渴望能够用这样一种作践自己的方式让胜利者去享受狂傲,而自己得以获准苟活下去。
还跪在阶下的赵王迁,惶恐而又焦急地等待着那位胜利者能够掷出一句恩准不杀的诏谕来,而秦王嬴政却几乎已经把这个阶下囚给忘了,顾自把玩着掌上宝玉,连连惊叹不已。此时此刻,受着这种等待的折磨和煎熬的赵王迁,不知是否在仟悔:怎么能那样稀里糊涂下令杀了李牧呢?
在赵王迁的感觉中,几乎是等待了一百年,秦王嬴政这才想到还跪着一个阶下囚。他淡淡一笑,手一挥说:念尔有代为寡人诛杀李牧之功,下去吧!
赵王迁连连山呼万岁,磕头谢恩。
据《淮南子》记载,赵王迁后来被迁徙到了蜀地房陵,羁居于一石室之中。夜深人静时,闻有淙淙流水之声传来。问了侍从,才知房山之下为沮水,沮水东流而达于汉水。不由凄然长叹,作诗一首道:
房山为宫兮,泪水为浆;
不为调琴奏瑟兮,惟闻流水之汤汤。
水之无情兮,犹能自至汉江;
嗟余万乘之主兮,唯有梦魂绕故乡!
不久,他便在忧愤中死去。
秦王嬴政在邯郸期间,是否去看了他童年时代的居处,史书没有记载,我猜想他是去过的。
这该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这里的每一件旧物都是一柄钥匙,打开了他一扇又一扇的记忆之门。闻着旧居的那些气味,开头或许已有点陌生,但很快就感到是那样亲切和温馨。于是那些宫廷搏击、疆场杀伐的情景便渐渐隐去,而久违的童年纯情便扑面而来。他看到众多熟悉的身影和听到絮絮的日常细语。这其中,有他最先死去的父亲,有被他威逼着死去的叔父吕不韦,还有已经进入老年的母亲,此外就是父母的朋友和他自己的那些小伙伴。他会真诚地忏悔自己曾经有过的过失,而谅解别人所有的错处。这时候,他最大的心愿便是能与他们之中任何人说些话,来证明他记忆中的这一切都是真实的,都曾经那样发生过……
这当然都是我的猜测。不过我相信,当一个人真情投入于童年回忆时,他会重新拥有一颗赤子之心的。
据《史记》本纪记载,偏在这时从咸阳传来的一个噩耗给了秦王嬴政重重一击,使他的感情突然起了个大变化:“始皇帝母太后崩。”他陷入了巨大的痛苦。这痛苦不是由于他爱母亲,而是因为他曾经恨过母亲。而今人一死,所有的恨都转化为双倍的爱,汹涌地向他袭来,而他却被抛掷到了一片无可诉说的空旷之地。呵,母亲,你怎么不让孩儿有一个当着你的面狠狠责备、惩罚自己的机会就匆匆走了呢?
出人意料的是,这个刚烈的国王内心的这种痛苦,突然又化为一种残忍的暴力,挥起了他的屠刀。这是《史记》本纪所作的记载——
秦王之邯郸,诸尝与王生赵时母家有仇怨,皆坑之。
这些被活埋的人的罪名是所谓“仇怨”,而判定“仇怨”的依据,是嬴政还保留着的童年时代的某些记忆。但我们知道,他的那些记忆是被他自己以为母亲“不贞”而引起的激愤情绪扭曲了的,因而所谓“仇怨”者,其中有一些却正是赵姬当年的友人以至情人,现在都被他这个儿子统统活埋了!作为母亲的王太后赵姬若泉下有知,不知对此将作何感想?
两个欲挽狂澜于既倒的太子
就像韩国灭亡时,张良从虎口逃出力图为韩报仇那样,赵国灭亡时,也有一个青年人从已经沦陷的邯郸逃出,力图恢复赵国,他就是赵悼襄王原立的太子嘉。
太子嘉与王室残余势力数百人,一起逃到赵国北部边境代地(今河北蔚县东北),在诸大夫拥立下称为代王。代地已与燕国接邻。赵、燕两国在历史上也曾不断相互攻战。战国初期,主张合纵的纵横家苏秦一次对赵王讲了一个“鹬蚌相争”的故事。他说我今天经过易水边时,看到一只河蚌在晒太阳,有只鹬就来啄蚌肉,相互咬住不放,结果让渔翁一抓而得了利。故事里把鹬、蚌比作燕、赵,渔翁比作秦国,告诫两国不要自相残杀,最后让秦国得利。故事虽然说得很有道理,但却往往不及实际利益更具有引诱力,两国还是常常为眼前的一丁点小利而争战不休。如今赵国已只剩下一个尾巴,燕国也处于岌岌可危之中,这才终于想到了有联合起来的必要,只可惜落花流水春去也,为时已晚。此后不久,便爆发了荆轲刺秦王事件,秦王冲冠大怒,一声号令,数十万秦军以掀天揭地之势扑向居于最北面的燕国。燕王喜早已吓得丧魂落魄,又遑论联合抗秦;太子嘉所能提供的兵力只是杯水车薪,要对付强大的秦军无异以卵击石。这样到燕国被秦军攻灭时,胜利者略施余勇,跃马横戈一挥,同时也就将“代国”这个小朝廷夷为平地。公元前222年(秦始皇二十五年),太子嘉被迫自杀,赵国的这条小尾巴也不复存在。
上文提到,此后不久便爆发了荆轲刺秦王事件,下面我们就来谈谈这个事件。
荆轲是受人指派入咸阳刺秦王的,这个指派人便是燕国太子丹。
太子丹一生下来似乎就注定要成为政治牺牲品。他的祖父,也就是燕孝王只坐了三年王位就死去,他的父亲燕王喜尚未成年就当上了国王。这种情况的出现,就活该做太子的倒霉了:不是在宫廷内百无聊赖地忍受那漫长的等待,就是得到异国他乡去当质子。太子丹的命运是后者。他的质子生涯还在儿童时代就已开始,第一次是赵国。在富庶奢华的赵国国都邯郸,他认识了如今已显出一副要吞并六国威势的秦王、那时还是个邋里邋遢的流浪儿的嬴政。他比嬴政要大六七岁,倒还是成了好伙伴,一起在邯郸街头、漳河边上玩耍,用来排遣那些无聊、寂寞的时光。后来总算回到了燕国,以为可以过几天舒服日子了,谁知一场政治游戏,又给他带来了厄运。那便是秦国在吕不韦为相期间,起用年仅十二的甘罗,经那小娃娃一番游说,赵悼襄王居然乖乖地言听计从,暗中与秦合谋讹诈燕国。燕国不仅丧城失土,还不得不第二次把他这个燕太子作为质子发送到更为遥远的关外之地去做政治抵押品。他在秦国咸阳一待就是七年。这时他已经四十余岁了,质子生涯几乎囊括了他从童年到壮年的全部岁月。这其中的辛酸滋味,世上又有谁人能体会得到!
但更使太子丹痛苦的是故国的羸弱和衰落。他的先祖燕昭王所营造的那个招徕四方贤士、破齐七十余城的辉煌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如今的燕国已落到欲求自存而不可得的地步,而父亲燕王喜却还只知游乐和苟且偷安。作为一个生活在异国他乡的质子,对故国的荣辱强弱有最灵敏的感受。他与嬴政那种曾经有过的伙伴友谊自然早已烟消云散。如今他们一个是强大的霸主,一个则是类似附属国的臣仆,再也没有任何平等可言。他曾经上书秦王及早终止这种实际上是由一个政治骗局造成的出质与受质的关系,让他回到燕国去。秦王的回答竟是那样蛮横和霸道:放你回去可以,但得等到天雨粟,马生角!从秦王说出这句话时那倨傲睥睨的眼光里,他一下子学懂了人生最宝贵的一课:作为一个人,与其跪着生,不如站着死!作为一个国家,与其成为附庸,不如在轰轰烈烈一战中灭亡!
公元前233年(秦始皇十四年,燕王喜二十二年),当怒潮似的秦军东渡黄河向三晋之地发起猛烈攻战的时候,被羁留在秦王宫之侧公馆内的燕太子丹,便开始实施他的突围计划。
他知道这已是最后时刻,无论对于他的人生,还是他的故国,都不能再有任何犹豫。
但是他突然病倒了,整整三日三夜都处于狂乱和昏迷状态中。
公馆里专为宾客和质子治病的医官,进进出出,忙作一团。尽管质子在这里常常受到贱视,但如果作为质子而死去,难免引起没完没了的外交纠纷,所以也不可等闲视之。
奇怪的是,到第四天凌晨,太子丹不翼而飞。秦王立刻命人紧急搜索,找遍咸阳城的每个角落,也不见有丝毫影踪。
于是便下令全国所有城关要塞,图形度牒缉拿逃亡质子太子丹。
三天后的傍晚,当夕阳落上崤山,函谷关守吏正要锁闭关门的时候,有一支送葬队伍还要出关。队伍后面还跟随着三五个死皮赖脸要丧家行善的乞丐,一个个蓬发垢面,浑身散发着冲鼻的酸臭。守吏也懒得查问,就让他们一起出了关,随即关上了沉重的石门。
没想到,这乞丐之中的一个,却正是与周室同姓、贵列王侯的燕国太子丹!
这位才智、品德都属平平的太子,却将以他最后一次人格闪光而名留千古。 人生必读经典历史丛书:时代帝国三部曲之大秦帝国(上 下)(套装共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