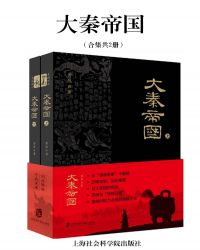易水悲歌壮千古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人生必读经典历史丛书:时代帝国三部曲之大秦帝国(上 下)(套装共2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易水悲歌壮千古
一位以自刎激励刺客的长者
太子丹回到故国,很快进入了一种忘我状态。
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起初,太子丹也许还只是出于个人的复仇动机,最多也只是为了维护王国的生存。但在与众多高士的秘密接触、交谈中,他的思想和感情得到了净化和升华。他认识到,他们将要采取的行动是为了维护人的尊严,而且这行动本身就是人格精神的一次大昂扬。
这样,看来只是一次暗杀活动,在当事人心目中却有了崇高、宏大和近乎神圣的意义。
面对如此崇高、宏大的共同使命,个人的生死荣辱就显得微不足道。
下面将要出现的一个个热血飞扬的人物和情景,由于时代已相隔得那么遥远,有些可能是我们现代人很难理解的,或者觉得如此轻生并没有多少意义,更何况“刺秦”之举也并不可取。不过若就人性和人格力量而言,那一瞬间所放射出来的如此率直、真挚、瑰丽夺目的闪光,反倒因它已随着时代远离,永远不可能在人世复现而显得弥足珍贵,从而不能不令人屏息慑惕,肃然起敬。
太子丹沐浴更衣,手捧扫帚恭候在门前,等待着一位长者的到来。
这位长者名叫田光,是太子丹的太傅鞠武推举的。
太子丹逃回到燕国国都蓟(今北京城西南),他父亲燕王喜开头倒是喜出望外,但后来得知他是逃跑出来的,立刻吓得惶恐不安,提出要去向秦王认罪,再把他送回秦国去。父子俩一谈就崩,太子丹就索性从东宫搬出,避开燕王喜,独自暗中实施他的抗秦计划。据《史记·刺客列传》记载,在这期间太子丹一面结交和招募四方豪杰之士,一面寻求贤士的指教。他先拜访了他的太傅鞠武。鞠武洞悉时势,精细地分析了秦国山川地理、文臣武将种种有利因素,认为秦国东进中原之势已不可逆转,而且只要秦王有意,那么“长城之南,易水以北”,即燕国辖境,也将很难保住。因而他劝太子丹尽可对此取达观态度,不要因个人受到欺凌,而“欲批其逆鳞”,去做螳臂挡车那一类事。太子丹跪地不起,说明欲抗强秦并非单是出于个人私怨,务求恩师指点。鞠武说:容老臣三思。过了三天,太子丹再去拜见太傅,鞠武已作过一番深谋远虑,向太子丹展示了他的抗秦计划。他认为关东诸国如今已丧失了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时机,再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独与秦国抗衡,唯一的出路便是联合起来。因而他建议太子丹派出使者西面去结交三晋,南面去联合齐、楚,北面再去和匈奴单于通好,如此方可捆缚秦国这只凶猛的雕鹫。太子丹一听说:呵,太傅!您这计划花费时间太多了,可我此刻心如焚炙,片刻也无法等待下去。有道成事在天,谋事在人。上天难道就不能容我一逞其意吗?还求恩师另外再给弟子指一条路!
鞠武沉吟良久,仰天一声长叹,说道:罢、罢、罢,就算老臣多事,为你引出一个人来。有道一时之强弱在力,千古之胜负在理。我燕国纵然力不胜秦,且为后世留下一条千古之理吧!
太子丹连连叩头致谢,询问高士姓氏。鞠武说:此人就是田光先生,身居陋巷的燕国名士。其人秉性耿介,纤尘不染。知深而谋远,勇猛而沉着。遇事可与共谋,有难可堪托身。
院门启开,现在这位须眉皆白的田光先生,正策杖曲腰缓步走来。
太子丹没有想到田光竟已如此老迈,却也不敢怠慢,连忙躬身迎上前去,一边为客人扫径,一面后退着为老人引路。请入内室后,亲自为客人拂拭座席,待老先生安席后,才敢在一旁侍坐。
仆婢退避,门窗都已关严。
太子丹离席长揖恳请道:燕国与秦国势不两立,丹与嬴政不能共存。祈求先生赐教弟子。
田光说:太子错爱了。你没听说骐骥在盛壮之时日行千里,而待它衰老连驽马也可以占先的故事吗?太子听太傅说起的大概是盛壮之时那个田光吧,如今你看我已衰老到这个地步,还能派什么用处呢?
太子丹说:可弟子也知有一个关于马的故事:当年管仲跟随桓公伐孤竹,春往冬返,迷失中途。管仲说,老马之智可以识途。乃放老马于前而随之,果然得通。如今丹也迷失走道,老先生难道不能为弟子指引一条道路吗?
老人朗声笑着说:如此说来,我这匹老马还有一点用处呢!只是老朽终生一布衣平民,不敢与闻宗庙社稷之事。既然太子如此抬举,我就为太子择一智勇而少壮之士以自代吧。但不知太子门下如今可用者已有几人,容老朽一一相过,再作商量。
太子丹立即命人把他门人新近招纳的几位勇士夏扶、宋意、秦舞阳等一齐请来与田光相见,略作交谈,勇士退走。太子丹忙问道:先生观感如何?
田光默然。因为在他看来,夏扶为血勇之人,怒则面赤。宋意为脉勇之人,怒则面青。秦舞阳为骨勇之人,怒则面白。这类怒形于色之人,见不得场面,如何成得了事!
太子丹不免有些焦急,又问:在先生看来,他们之中谁个堪当此任?
田光说:恕老朽直言,此辈人等,只宜为太子府上守门饲马。
太子丹不由一惊,说:那是否请先生为弟子推荐一人?
田光略为沉吟,说:老朽有一好友,新从邯郸来游,名唤荆轲,实为神勇之人,喜怒不形于色,或可当此重任。
太子丹大为惊喜,慌忙一揖说:弟子愿与荆卿结交,烦请先生代为引见,不知可以沾光否?
田光说:敬遵台命!
太子丹恭敬地送田光到门口。一种即将面临一搏的巨大兴奋使他心颤不已。荆轲之名他已有所闻,那是一位侠骨冰心、艺胆双绝的烈士,若得与之结交,何愁大事不成!
老人回身一揖就要出门了,太子丹突然想起了什么,赶上两步,四顾无人,悄声说道:弟子适才所言,乃燕国存亡绝续大事,望先生勿泄于外人。
田光淡然一笑说道:老朽不敢。
田光上车,路过市巷,恰好见到荆轲与他新近结交的好友高渐离从一家酒肆出来。两人已有几分酒意,步履踉跄,相互倚持着,高渐离击筑,荆轲相和歌,唱的是《易水谣》。两人仰面流涕,旁若无人。
岁已暮矣,
而禾不获,
忽忽兮若之何?
岁已寒矣,
而役不罢,
兮如之何?
荆轲先祖为齐国人,后来迁居到卫国。他自幼喜好读书和击剑,及长,负笈仗剑,游历四方。先后到过魏、赵等国,曾以剑术游说君主,终因他的孤傲而不被信用。他游历到榆次地方时,曾与当地著名剑客盖聂讨论剑术,两人十分投缘。但有一次因对某一剑术见解不同,盖聂瞪了他一眼,他竟因此不辞而别。但后来荆轲却又常常怀念盖聂,认为此生尚未见到过如此艺胆相合的人。
来到燕国,他结识了田光、高渐离等人。高渐离善击筑,筑声悲壮,催人泪下。荆轲或依声舞剑,或引吭高歌。两人常常忽而畅怀大笑,忽而痛哭不已。大醉时,曾仰天而问:值此末世,人生天地间,当何以自处,何以自命?
田光把荆轲请回家里,然后说道:荆卿平生常恨天下无知己,如今若有智伯登门相求,荆卿愿意做豫让否?
荆轲长叹一声说:只恨智伯尚未复生啊!
田光说:如今燕太子丹,礼贤下士,折节重客,十倍当年智伯。不知荆卿愿意一试胸中之奇志否?接着便把太子丹急切要求结交的话说了说。
荆轲说:既如此,太子何不自来呢?
田光说:太子说他唯恐壮士不肯屈就,所以先使老朽代为引见,此刻他正在家门口恭候呢!
荆轲猝然起立一揖说:请先生就道,轲愿随从!
田光却没有起座,缓缓抚着长剑说道:古训有云:“长者为行,不使人疑。”这回太子丹以燕国存亡之事有谋于田某,且嘱咐道:勿泄于外人。这便是对田某尚存疑虑。荆卿尔且自行吧,请代为转达太子尽可放心,老朽此生再也不会泄于外人!
说完,淡淡一笑,竟饮剑自刎而死。
田光说他的死是为了让太子丹放心,从此不会再有第三个人知道此事;《史记·刺客列传》记此事时还有一句话:“欲自杀以激荆卿。”
荆轲出神地看着老人的热血沿剑刃喷出,突然似乎意会到了什么,头也不回,立刻登车去拜访太子丹。
一个以头颅献给刺客的叛臣
荆轲进见太子丹。
宾主就座,默对良久。
荆轲这才说到田光已死。神色漠然,竟无一丝悲切之意。
太子丹一听,裂眦瞿视有顷,忽而不能自制,扑地跪拜,膝行流涕,吞声饮泣。
荆轲依旧肃然跽身于座,面冷似铁。
太子丹再次就座,转为平静地问道:老先生临行之时,可有什么嘱咐?
荆轲冷不丁说:轲以为,老先生并没有死,他仍然侍从于太子之侧。
太子丹陡然一惊,拱手谢过上天:天帝以荆卿赐丹,这不仅是燕国之大幸,也是中原之大幸!
接着,太子丹便向荆轲说出了他将派荆轲去执行的破秦计划。据《史记·刺客列传》记载,这计划的要点是利用秦王的贪欲,身带重利去接近秦王,或是劫持,或是刺杀。劫持是上策,劫持不成则刺杀。所谓劫持,是仿效春秋时代鲁国勇士曹沫的做法。公元前681年,曹沫随鲁庄公至柯地与齐桓公会盟。这之前,鲁国屡受齐国侵伐,失地颇多。会上曹沫突然挟持桓公,以剑相胁,要求归还被侵夺的鲁国土地,不然立刻同归于尽。桓公不得不同意这项要求,后来如约归还了鲁国失地。这一回,太子丹的如意算盘便是在劫持秦王后,不仅要胁迫他交出侵燕之地,还要他交出对诸侯列国所有的侵地,并认为这样做是“大善”。如果秦王不肯答应,就当场刺杀。秦王一死,据太子丹的估计,秦国统治集团特别是握有重兵在外作战的大将,会因为互相猜疑而发生内讧;而关东列国则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合纵起来,如此内外一夹攻,则“破秦必矣”!
荆轲静静听完了太子丹的计划,却依旧表情漠然,竟不说一句话。
太子丹屏息绝气等待了好一会,才小声问道:不知壮士以为可行否?
荆轲似乎没有听见,顾自一手抚摩着剑柄,双目直视窗外。突兀自语一句:只有他!随即又加大声音说:就是他!
原来,荆轲以为要劫持或刺杀秦王绝非易事,必须得有一个非凡人物做副手,想来想去,觉得只有一人,便是在游历榆次时结识的盖聂,非他莫属!
太子丹知道荆轲已经许诺,欣喜异常,立刻尊荆轲为上卿,选择最好的官舍来让他住。这以后,太子丹每日来官舍问候荆轲,以全牛、全羊、全猪供餐,还有奇珍异宝、高车驷马、侍姬美女,供他恣意享用。太子丹有一匹心爱的千里马,一次荆轲偶尔说了声:千里马的肝特别肥,味道一定很美吧?这一天侍女端来的餐盘上就多了一道美味,便是那匹千里马的肝。一次太子丹陪荆轲在华阳台饮酒,令美女一旁鼓琴助兴。荆轲不由称赞道:好一双灵巧的手!不一会侍女便来向荆轲跪献一盘血淋淋的东西,竟是那美人之手!
就在这期间,秦将王翦率领数十万大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转眼间便席卷赵国全境,做了俘虏的赵王迁被押向房陵。王翦兵屯中山,其前锋已触到燕国南部,仅以易水一线之隔,连鼓角声也已隐约可闻。
燕国颤抖了!蓟城恐慌了!
太子丹急急赶到荆轲官舍说:纵然丹诚意永远奉陪壮士,无奈易水就要遭秦军玷污,那是燕国万千臣民母亲之河啊!
荆轲说:这轲也已经知道。太子不来,轲也正要前去拜见。只是还得带上一两件足以使秦王相信的礼物,不然就休想去接近他!
太子丹说:是否可以带上督亢地图?秦王对燕国这片富饶的土地可是垂涎已久了啊!
督亢是古地名,在今河北涿州市东南,其处向以肥沃著称。清代阎尔有诗云:“上古膏腴环督亢,中山意气感壶餐。”
荆轲说:以督亢为礼,只怕还不够分量。轲以为,至少还须带上一个人的头颅,方可使秦王深信不疑。
太子丹不由一惊,说:那是谁的头呢?
荆轲于是便说出了这个人名字:樊於期。
樊於期其人,仅见于《史记·刺客列传·荆轲》,说他“得罪于秦王,亡之燕”,“秦王购之金千金,邑万家”。但樊於期究竟犯了什么大罪,致使秦王嬴政要用黄金千斤、封邑万户这样巨额赏赐捉拿这位逃亡者,文中没有说。《汉书·邹阳传》提到樊於期这个人名时,有个注:“於期为秦将,被谗,走之燕。”被谗什么呢?也没有说。从那以后的两千多年来,樊於期的行迹一直成为悬案,引起人们猜测。明代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说秦王嬴政之所以要悬赏追杀樊於期,是由于樊在嬴政即位初期,不仅策动长安君成叛乱,还为他草拟了以揭露嬴政系吕不韦私生子为主要内容的檄文。从秦王嬴政对樊於期如此深恶痛绝来看,此说似也能言之成理。但毕竟属小说家言,缺少依据。近代杨宽先生著《战国史》,在说到赵将李牧大败秦将桓时,作了一注,认为“樊於期即是桓齮,音同通假,犹如田忌或作田期、田思。桓于秦王十四年败走,燕太子于秦王十五年由秦归国,时代也正相当”。若据此,樊於期是因打了败仗逃亡的,这当然也可成一说。但嬴政一生,出如此高额赏格捉拿国内叛臣,仅此一次;后来还将樊的父母宗族全都杀绝,也属罕见。从这些情况看来,樊於期应犯有比一次战败更让嬴政无法容忍的罪,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不过那已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问题了,且让历史学家们去研究吧,我们还是赶快回到荆轲与太子丹的对话上来。
太子丹一听要带上樊於期的人头,迟疑再三,说:樊将军是因遭到困厄才来投奔丹的,丹又如何能忍心呢?
荆轲默然。
太子丹又说:请壮士费神再思,能否另选别的礼物?譬如奇珍异宝,只要燕国有。
荆轲依旧默然。
荆轲在沉默中已作出了决定:不为难太子了,由他自己去找樊於期。
这该是一次古往今来罕见的谈判了吧?——谈判的内容为割下一方头颅的问题。
荆轲是这样开头的:秦国对樊将军何其狠毒啊!将军的父母和族人,不是被杀就是被收为奴仆,如今还在用千斤黄金和万户封邑的赏格索要将军的首级。将军意欲奈何?
樊於期仰天叹息,涕泣良久,说:樊某每念及此,痛入骨髓,只恨报仇无门啊!
荆轲说:如今轲有一法,既可报将军之仇,又可解太子丹之患,将军以为何如?
樊於期听了立刻移席向前说:请快说吧,於期该如何行事?
荆轲说:轲已定下愚计,欲入咸阳刺秦王,只恐无缘得以接近秦王。若能携将军首级入宫进献,秦王定然愿意传见。到那时,轲将左手抓住秦王之衣袖,右手以匕首刺其胸膛,如此便可一举而得两功:既可使将军报仇雪恨,又为燕国涤除耻辱。不知将军以为可否?
樊於期一听,爆目裂眦,偏袒捶胸大呼道:这正是樊某日夜切齿咬牙、痛心疾首的一件大事啊,今日万幸而得足下明教,在下就此拜别吧!
当即离席拱手一揖,在大声欢笑中抽剑一挥,他那颗喷着热血的头颅便随剑滚落了下来。
太子丹匆匆赶来,伏尸痛哭。但事已如此,也只好将樊於期的头颅封入木函,随即隆重安葬其残体。
在这之前,太子丹已秘密派人四出寻求最锐利的凶器,最后从一个姓徐的赵国人那里以百金高价购得一柄长一尺八寸的匕首,再命人在毒液里淬砺,用来试人,只要见到一丝血星便立刻倒毙。又给荆轲配了一名副手,叫秦舞阳,是燕国名将秦开的孙子,著名勇士。他十三岁就开始杀人,悍勇激烈,没有一个人敢于正眼看他。但荆轲仍不满意。他还等待着游历榆次时相识的盖聂。他早就派人去暗中求访过,只是这位最能获得心艺默契的剑友,至今仍未有回音。
在等待中,他还亲自为盖聂准备了一份行装。
但心急如焚的太子丹却不能再等了,他急急跑来对荆轲说:出发的时间已经到了,是否能允许我派遣秦舞阳先起程?
荆轲立眉嗔目怒斥道:先派遣人去,这是什么意思?有去无回的无能之辈派一万个也没有用!
说罢把已为盖聂准备好的行装狠狠一摔,就飞身上鞍,策马急驰……
一个血写的典故:图穷匕首见
眼前这条宽不过十丈的易水河,却要因即将发生的一幕而留名青史了。
易水位于今河北省西部,易县境内。在战国时代,易水之北为燕,易水之南属赵。如今赵已为秦所灭,易水便成了燕秦界河。燕国臣民日夜为之惴惴不安的是,秦军那些高脚宽腰的关中烈马,只要一发起性来,便可轻而易举地从南岸跃身到北岸。在万般无奈之中,他们最后只好把生存的希望寄托在一柄其长尺八的匕首锋刃上!
现在,一支近百人的队伍正面南背北走着。他们穿戴着白衣白冠,一个个表情肃穆。
走在队伍中间的太子丹牵着马,马上骑着危冠雄发的荆轲。
没有一丝杂响,除了沉重的脚步声和马蹄声。
已经入冬了,稀疏的败草在寒风中颤抖。漫天彤云,正预示着一场即将到来的暴风雪。
望到了缎带似的易水,听到了它低沉的呜咽,人们渐渐缓下步来。
一个同样是白衣白冠的勇士急急追赶而来,怀抱着一张筑,他是高渐离。
席地而坐,设宴饯行。
高渐离击筑,荆轲倚声和歌。
筑声蓦地变调,进入悲怆的清商音域。荆轲散发舞剑,仰天号歌——
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行云为之停留,易水为之哭泣,宾客随从无不流涕太息。荆轲仰面长吁,气冲霄汉。彤云渐散,似有白虹微露。筑声又变为慷慨悲壮的羽调。竹尺急风骤雨般击打于弦上,声似金戈铁马,刀枪齐鸣。众人莫不嗔目奋励,发尽上指冠。荆轲再次引吭高歌——
探虎穴兮入蛟宫,
仰天嘘气兮成白虹!……
《史记·刺客列传》描画的这些易水壮别场面,悲恸千古,震撼了多少人的灵魂!
行笔至此,我却忽而闪过一个有违两千多年来几成定说的的念头,说出来可能有点“煞风景”,想了想,还是说出来吧。
在我看来,这样宏大的送行队伍和如此慷慨悲歌的场景,在已成为燕、秦边界的的易水之畔是不大可能出现的。理由很简单:这不是公开宣战,而是一次极端秘密的刺杀活动。为筹划这次暗杀,太子丹已暗中苦心经营了四五年,一直慎之又慎,即使对田光老人也要特地关照一句“愿先生勿泄”,以至使得老人甘愿为此自灭其口。很难设想,竟会在临行时公然来这么一番大张旗鼓的壮别,特别是送行的人还一个个“白衣白冠”,那不等于在向咸阳公开发布将去进行一次决死刺杀的消息吗?但《史记》又确实是这样写的,这该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我猜想太史公为荆轲作传时的心态是这样的:他可能并不赞成荆轲刺秦王这一具体行动,但对荆轲那种执着于自己心志,不惜以生命一搏的昂扬精神,却又深为感动。那是在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南游江淮、北涉汶泗期间,一次他来到易水之畔,但觉秋风萧瑟,清波凝寒,斯人已逝,古今同哭。不由胸臆勃勃,文思喷涌,便信笔勾勒了这么一幅寄托着作者无限情思的画图。所以纵然“壮别”的具体情节并非实有,但就概括那个特殊时代的精神风貌这一点来说,却又具有高度的真实性。
蓦地,高渐离挥手用力在弦心一划,声如裂帛,随即戛然而止。
人人敛声屏息,穆然肃立。唯有易水在寒风中轻声呜咽。
太子丹复引卮酒,跪进荆轲。荆轲一饮而尽,与秦舞阳一起腾跃登车,劲鞭疾驰,竟然没有回头看一眼!
咸阳,威震中原的咸阳。
但即使是秦王宫内,也同样有可以用金子征服的人。
这是事先买通好了的。有个得宠于秦王的中庶子,名叫蒙嘉,在得到荆轲千金巨贿后,便在秦王嬴政面前说了一番极有利于荆轲实施计划的话。他是这样说的:大王,燕王确实已经屈服于大王的声威,再也不敢抵抗大王派去的军队;他只希望全国上下都能成为大王的臣民,就像秦国的一个郡县那样按时交纳贡物和赋税。但燕王由于内心恐惧,自己不敢贸然来拜见大王,特地派出使节,还在朝堂上举行隆重仪式,随带叛臣樊於期的首级和燕国督亢之地的图籍,远道来咸阳进献给大王。如今燕使上卿荆轲已在馆驿候旨,一切唯大王之命是从!
秦王嬴政听了很高兴,对樊於期已经就戮尤为称快。于是命侍臣准备朝服,设九宾之礼,传谕使者到咸阳宫进见。
荆轲捧着樊於期的头颅函前行,秦舞阳双手托着督亢地图匣紧随而进。巍峨的秦王宫已在面前,手执斧钺戈戟的虎贲三步一岗,威严地分列两旁。
侍卫官一声传宣,声震瓦檐。随后又寂静下去,静得只有自己的心跳声。
两人开始升阶。足下的乌舄踏在石阶上,犹如空谷传响。跟随在后面的秦舞阳听着听着,脸色忽而煞白,浑身颤抖不已,脚步也慢了下来。一旁侍卫官立刻逼问:使者因何如此慌张?
荆轲回头望了秦舞阳一眼,笑着从容答道:此人原系北番蛮夷粗鄙之徒,才进燕宫不久,生平从未见过皇都天颜,故而悚惧恐惶。还请上国宽宥其罪,以顺利完成此次使命!
终于登上了大殿。
按朝制规定,再一次接受身上有否携带武器的检查;并脱下舄履,恭立等候下旨。
秦王传下谕旨:只许正使一人上殿。
左右便喝令秦舞阳下阶。
荆轲一人捧着头函拾级而上。来到殿前,双手过额呈进,侍者接过,献给秦王。秦王命侍者开函核验,证实确系樊於期首级。秦王挥手令侍者持下,忽而侧过脸来冷不丁问道:何不早杀叛贼来献?
荆轲回答说:樊贼畏罪叛逃,窜伏北漠,敞国寡君悬千金之赏,才得以获致。原想生擒而来,唯恐远涉数千里之遥途中生变,故断其首级来献,愿以此略纾大王天怒。
秦王听了颜色转和,不再有疑。
此时秦舞阳仍捧着地图俯首跪于阶下。
秦王下旨道:取督亢地图来,与寡人一观!
荆轲迅即下阶从秦舞阳手中接过地图,再双手捧着历阶上殿,亲呈秦王。秦王将图卷缓缓展开,细细观看……忽而眼前一亮,司马迁记下了这样六个字:“图穷而匕首见。”(《史记·刺客列传》)在这同一瞬间,那把雪亮的匕首已被荆轲抢先抓住。他迅即跃前一步,左手趁势抓住秦王衣衫,右手就用那把匕首直刺秦王前胸。秦王大惊侧身一躲闪,避开了匕首的尖锋;再奋身一跃,衣袖已被扯断。荆轲抛去断袖,直扑秦王再次奋力刺去。秦王边逃边拔佩剑。他这一日的佩剑名鹿卢,长八尺,在奔逃中手难以往下提,一时无法拔出来,而荆轲的匕首不断在他身前飞刺。朝堂群臣面对这突发事变却手无寸铁,已是慌作一团。有几个勇敢的徒手扑上前去,也先后被荆轲击倒。
原来秦法规定,百官上殿,无论文武,概不许持尺寸利器。凡平日所佩刀剑都必须解脱陈列于殿下,且非奉宣召任何人都严禁擅自上殿。因而在禁卫森严的咸阳宫里,出现了荆轲一人持匕首追逐挂着长剑慌乱逃躲的秦王,众侍从却仅有几人敢于徒手近前与之搏斗这样一个奇异而惊险的场面。
秦王座旁有一屏风,其高八尺。眼看要被荆轲执持,秦王尽力一跳,撞倒屏风,慌忙躬身冲出,又差点撞在巨大的铜柱上。荆轲一跃而过倒地的屏风,紧追不放。秦王只得绕柱躲避,已有气喘慌乱之色。这时候近旁有个名叫夏无且的侍医忽而想到捧在手上的药箱,便用力向荆轲掷去。荆轲奋臂一挡,药箱碎裂落地。秦王趁这时机再次拔剑,但还是没有拔出。不知谁大声嚷道:大王,从背后拔剑,快拔呀!秦王受到启示,迅速将剑鞘推到背后,果然拔出。一剑在手,胆气大壮,立刻转身向荆轲砍去。荆轲几番腾跃,不意为铜柱所挡,秦王一剑,击中荆轲左腿。荆轲一跃而起,奋力将匕首向秦王咽喉掷去。秦王猛一闪身,匕首从他耳边擦过,铿锵一声,钉在殿侧铜柱之上,火星迸出。秦王再次举剑进击。荆轲被连创八剑,倚柱而笑、大声骂道:暴君,你还能享国多久呢?我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想生擒你,逼你交出侵占诸侯之地,以此报效太子。我死后,还会有人继我此行的,你等着吧!
这时候众多侍臣一拥而上,将荆轲击杀。秦舞阳也同时毙命于阶下。后来荆轲还被灭了七族。
燕太子丹长达五年的刺秦之谋,至此以彻底失败告终。
秦王嬴政也不能算是这一事件的胜利者。他是在极偶然的情况下侥幸脱险的。这沉重的一击使他有好几天神情恍惚,抑郁寡欢。但从后来的行迹看,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奋力于他的统一大业,不受丝毫影响。事后他赏赐和惩罚了在这事件中有功或有过的官员。侍医夏无且赏赐最多,获得黄金二百镒。镒为重量单位,二十两或二十四两为一镒。秦王说:无且最爱护我,所以用药箱投击荆轲。
在历史上,持正统观点的历史学家对荆轲刺秦之举大多取贬责态度。如宋代司马光就说:“燕丹不胜一朝之愤,以犯虎狼之秦,轻虑浅谋,挑怨速祸,使召公(燕先祖为召公奭)之庙,不祀忽诸(意谓忽然而亡),罪孰大焉!”对荆轲,更认为他:“怀其豢养之私,不顾七族,欲以尺八匕首强燕而弱秦,不亦愚乎!”(《资治通鉴·秦纪二》)但司马迁却总是别具慧眼,不以成败论人事,而以人的心志,即以人应当执著自己的信念为视角,对此事作出了独特的评价。他认为荆轲等人“以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通“皎”,明亮)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史记·刺客列传》)!有点出人意料的是被钟嵘《诗品》称之为“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读了荆轲事迹后,竟也不由为之意气奋然,一反宁静淡泊的田园风格,写出了《咏荆轲》那样激昂悲壮的诗篇,使千余年后的我们读时还能感受到诗人那颗不平静的心——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
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
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
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
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
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
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
萧萧哀风逝,澹澹寒波生。
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
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
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
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
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
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
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
想以儿子首级换取王位的父亲
秦王嬴政被燕国刺秦之举激怒了!
秦始皇二十年(公元前227年),秦王火速发兵急赴已被攻灭的赵国,与屯兵在中山之地待命的王翦之师会合,计四十万之众,统由王翦率领,跨过易水,讨伐燕国。沿途破关克城犹若摧枯拉朽,无可阻挡。太子丹和代王嘉虽在易水之西有过几次抗击,但都迅速被粉碎。到第二年十月,秦军包围了燕国国都蓟城。
孤城内的燕王喜恐惧万状,想要开城投降,仿效赵王迁行“衔璧舆榇”之礼,太子丹则力主突围出去,另谋生存发展之路。终于组织到几千精兵,突围获得成功。父子俩依靠这点力量,迤逦东进。经过长途跋涉,来到辽东襄平(今辽宁辽阳市),以为此处负山阻河,犹可据守,便安顿了下来。仍自称燕王。
王翦攻下蓟城,实际上已灭了燕国。便班师回朝,告捷咸阳。
此时王翦已年近花甲,长年风餐露宿搏杀于疆场,如今又接连攻灭赵、燕两国,积劳成疾,已有不胜之感,请求告老。秦王虽有不舍,却也不便强留,便厚加赏赐,准其荣归频阳。王翦回到故里,清静无为,每日忘情于介子河、南葱山之间。一代名将,归老居然能以山水自娱,倒也着实难得。
关东六国,到这时已灭了一半。秦王嬴政命令三军将士稍作休整,再以胜利之师,集中主力攻楚,同时准备进军大梁。燕国尚未最后灭亡,他余怒难消。因而又派大将李信,率领一部分王翦之师,进军辽东,务必全歼。
流亡在辽东苟延残喘的燕王喜,命悬一丝。
燕的先祖召公奭与周同姓,也姓姬。周武王灭纣后,封召公于北燕,因而有了燕之名。召公曾治西陲之地,政绩卓著。因他常常议决政事于一棵棠树之下,他死后人们怀念他,便作了一首《甘棠》诗,一唱三叹,情深义重,收入今本《诗经》,传为千古佳话,以致“甘棠”一词成为德政的典故。召公九传至惠侯,周室开始衰落,发生了厉王逃亡到彘地那样的事件。八传至庄公,齐桓公称霸,攻伐山戎,为燕辟地五百里,燕国由此强大。又十九传至文公,而苏秦说以“合纵”之术,文公之子始称王,即燕易王,并列于战国七雄。据苏秦说燕王时称:“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粟支数年。”(《史记·苏秦列传》)易王传至哙,为齐国所灭。哙子燕昭王复国,用乐毅为将,联合五国一战而得齐七十余城,成为燕国最强盛时期。昭王四传,便是到了眼前这位穷途末路的燕王喜。
燕王喜离开繁华的蓟城,来到这荒僻寒冷的辽东之地已有不胜凄凉之感,又听到秦王发兵来攻,更是雪上加霜。想来想去,只有一个自称代国的小朝廷,或许还能伸过手来帮他一把。于是便火速向太子嘉发去一封求救书。辽东与代地相距千余里,来去一月有余。回书到之日,襄平尽在秦军包围之中,燕王喜已成了瓮中之鳖,釜中之鱼。但求救书终于有了回音,还是燃起了他一线希望,急急拆封。回书是这样写的——
晚辈嘉拜于燕国大王尊前:嘉以为虏秦犹然穷追上国不舍者,唯因太子丹使荆轲行刺故也。大王若杀丹以献秦王,则秦师必退,而上国宗庙社稷得以永存。值此存亡危急之秋,嘉不揣愚陋,竭诚上达,望贤者三思而择焉。
这太出燕王喜意料了!用杀死儿子以求得仇敌宽恕的办法来保存自己,有违于人伦常情。老国王不免在心中狠狠骂起了太子嘉。想当初你这个赵国流亡太子从邯郸一片血海火山中逃出,仓皇如丧家之犬,竟然要到我燕国廊檐边来建立一个什么代国。如果我当时还记着燕、赵世仇的话,趁机一口吞灭你这个小朝廷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我非但没有那样做,还答应了你联合抗秦的要求,才使得你这个流亡小朝廷苟存至今。不幸的是我这个堂堂召公奭之后如今也成了流亡国王。我看得起你写信要你伸手帮一把,你小子不发一兵一卒却出了这么个馊主意!
可骂完了转而一想:不照这小子的馊主意做又能怎么办呢?燕王喜是不到二十岁就接他短命的父亲王位的,到这时候已做了近三十年国王,虽说不是屡败于赵,就是受辱于秦,无一建树可言,但想想当国王的味道还是不错。只要不是在屈膝向外国强敌求和的场合,而是面对着匍匐在地山呼万岁的万千本国臣民,他自觉还是够威风的。无论如何流亡国王也总还是个国王吧,能够多当一天也好,不,半天也好!
于是老国王秘密召见嬖幸之臣,流着眼泪商议如何实施杀子求存之计。
太子丹察觉了父王的密谋,急忙设法从襄平逃出,在辽东—个叫衍水的地方(今辽宁太子河)藏匿了起来。
太子丹第一次从秦国逃亡,是秦王嬴政要杀他;这一回从襄平逃亡,竟是自己的父亲要杀他。更叫他难以相信的是,这一回先后要追杀他的两股力量居然联合起来了:“其后[秦将]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斩太子丹。”(《史记·刺客列传》)你看,他们一个以大军追捕,一个派出使者逼杀,配合得何等好啊!
当太子丹的首级被装进木匣,燕王喜老泪纵横地大恸不已时,一件奇事发生了:明明还在夏季,却忽而漫天白雪飞舞。民间文学创作者们自然又要据此生出“冤气感天,天怒而降雪”一类话头来了。不过《史记·秦始皇本纪》倒正是这样记着的:“大雨雪,深二尺五寸。”
秦王嬴政在得到燕太子丹首级后,不是出于仁慈或宽宥,只是为了集中兵力攻打庞大的楚国,才下令李信暂时班师。这样,燕王喜才得以在流亡王座上又摇摇晃晃坐了五个年头,大概味道还是不错吧,只是不知道这些年月里他是否常常梦见失去了头颅的儿子?
待到秦王一攻灭楚国,便立即派出年轻的战将王贲率军轻骑飞袭辽东。小将军英姿勃发,手到擒来,老国王终于也做了俘虏。时为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燕国至此终于彻底灭亡。 人生必读经典历史丛书:时代帝国三部曲之大秦帝国(上 下)(套装共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