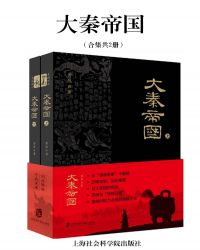接过盘古氏的巨斧(下)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人生必读经典历史丛书:时代帝国三部曲之大秦帝国(上 下)(套装共2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接过盘古氏的巨斧(下)
撒下严密的法网
秦帝国仿佛所向披靡的强大权威力量,是依靠严峻的法制支撑起来的。当帝国之车威严地在华夏大地上转动起来时,它的轨道就是法制。当然也可以说这种法制是帝国统治阶级即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的集中表现,但事实上通常却正是秦始皇个人意志的表现。
秦帝国的法制,不妨用两句话来概括:比以前任何时期完备,比以前任何时期严酷。
秦国自商鞅变法后,就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备而严峻的法制。商鞅以李悝《法经》为基础,“改法为律”,成为“《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等六律(见《唐律疏义·序》)。此后一百多年根据需要又陆续制定了一些新的法律条文,到秦帝国建立后更作了全面的扩充和修订,以至完备周密到可以实现“事皆决于法”(《史记》本纪)的地步。
但是过去由于文献和资料不足,对帝国法制具体情况往往语焉不详。可喜的是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第十一号墓出土了一千余支秦代法律的竹简,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这个使学者们长期困扰的问题。日本学者大庭修说他一看到新闻报道就“翘首盼望”着这批秦简内容的发表。发表后他作了这样的评价:“这次发掘的结果,使大量秦律内容得到理解,其数量远远超过汉律令的佚文”;“而且在这些条文中可以见到与汉津和汉代官制非常接近的内容,不仅是单纯地对秦代研究有用的史料,而且对汉代法律的理解和研究也极为有益。”
(《秦汉法制史研究》)。
云梦《秦律》出土后,大致可以为秦帝国的成文法典勾勒出以下概貌——
第一,属于刑书、民事和诉讼法方面的,除了商鞅变法时颁布的“六律”,出土《秦律》中还有一篇《法律答问》,是一种解释性律文,共一百八十七条。内容涉及到刑事方面的犯罪构成、量刑标准、刑事责任、共同犯罪、犯罪未遂、犯罪中止、数罪并罚;和民事方面的婚姻的成立与解除,财产的继承以及损害的赔偿等等。其中还有一些牵涉到诉讼权利、案件复查、自首、诬告、失刑、不直、纵囚等诉讼法的理论原则问题,都是秦以前文献记载所未见的。此外,散见于《史记》、《汉书》等史书中的还有不少,如“舍人法”、“什伍令”、“禁父子兄弟同室内息令”等等。
第二,属于行政法方面的,有《置吏律》、《行书律》、《内史杂》、《尉杂》等。秦帝国在建立庞大的中央集权官僚机构的同时,还因实行郡县制而委任了众多的地方官吏,这种情况是过去实行封建制时代从未有过的。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一套管理官吏的法律便应运而生。从这些律文中可以看出,帝国对官吏的要求颇为严格,对在职官吏,规定有名目繁多的考课法,从基层评比到政府机构“上计”,实施严格的奖惩制度。《史记·蔡泽列传》中还提到:“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这就是说,官吏犯法不仅本人要受到惩处,他的保举人也要连坐。云梦秦简中有一篇长达近两千字的《为吏之道》,对官吏从执行政务到个人修养提出了全面要求。其中提到:“临财见利,不敢苟富;临难见死,不敢苟免。”特别严禁“非上”,即对秦始皇必须绝对忠诚:“非上,身及于死!”
第三,属于经济法和军事法方面的,内容更为完备,有些规定得十分具体、细致。如《田律》、《厩苑律》、《仓律》、《金布律》、《均工律》等经济类法律,固然表明了帝国“以农为本”的策略思想,同时对手工业和商业也相当关注。其中不仅有所有制关系、农田水利、山林保护和工商管理等条文,包括种子保管、防风防涝、除虫灭害等等都有明细规定。《仓律》中还有这样的条文:“县遗麦以为种,用者殽禾以臧(藏)之。”这是要求留作种子的麦子,应像收藏谷子一样注意收藏好。下面这条有关种子使用量的规定更具体得有点类似经验介绍:“种:稻、麻,亩用二斗大半斗;禾、麦,亩一斗;黍、荅(dá,小豆),亩大半斗;叔(菽),亩半斗。”《均工律》中规定:“隶臣有巧可以为工者,勿以为人仆养。”这说明帝国对手工业方面的技术力量是注意保护并尽量发挥其专长的。属于军事类的有《军爵律》、《除吏律》、《中劳律》、《屯表律》、《戍律》、《公车司马猎律》和《秦律杂草》中的有关条文。秦国自商鞅变法后就以“农战”为兴国之道,经过兼并六国之战,对军队自然更加重视。这些律法条文中,对服兵役年龄、士吏简练、军伍纪律、战斗指挥、功过奖惩、爵位予夺以至军马饲养等,都有明细规定,目的都是为了使帝国始终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
为了强化法,秦帝国强调“以吏为师”、“以法为教”,因而狱吏特别受到重用,这就是《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的:“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曾任主管刑法的廷尉的李斯后来做了丞相,精于狱法的赵高不仅被举为掌管皇帝乘舆路车的中车府令,还当了王子胡亥的太傅。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强大的普法宣传声势,规定官吏要定期向平民宣讲法律。秦始皇四出巡游每至一地的勒碑刻石,也多以宏扬帝国法制为主题。如——
《琅琊台刻石》:“瑞平法度,万物之纪……”
《芝罘刻石》:“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
《会稽刻石》:“秦圣临国,始定刑名,显陈旧章……”
秦帝国所以要这样做,原是由秦始皇那样推崇以韩非为代表的法治思想所决定的,但为了强化权威,却再一次把“五德终始”说中所谓以水德受命抬了出来:“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对《史记》本纪中的这段话,《索隐》作了这样解释:“水主阴,阴刑杀,故急法刻削,以合五德之数。”这就赋予“事皆决于法”以“受命于天”的至上意义,包括种种酷烈的刑罚也变得神圣不可侵犯。其突出表现在——
【“轻罪重罚”成了指导思想】
说起来,这又是从韩非那里学来的。韩非的“重刑论”是建立在人的本性都是自私这样一个基本认识上的。他在《六反》中说:“所谓重刑者,奸之所利者细,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蒙大罪,故奸必止者也。所谓轻刑者,奸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轻视)其罪,姑奸不止也。”轻罪重罚人们觉得不合算,就不会去犯罪;重罪轻罚则有利可图,于是作奸不止。由此推出的结论是:“故曰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此所以为治也。重罚者,盗贼也;而悼惧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于重刑?”
秦帝国法制中许多地方充分体现了“轻罪重罚”的特点。以《法律问答》为例:
同父异母相与奸,可(何)论?弃市——弃市就是在闹市区执行死刑,并抛尸示众。
誉适(敌)以恐众心者,翏(戮)。翏者可如?生翏,翏之已乃斩之之谓也。——士兵为敌人说几句赞誉的话,就被认为动摇军心,先刑辱示众,再杀死。
女子甲去夫亡,……论可也当黥城旦舂。——妻子背夫逃亡,就得被在额上刺上字,涂上墨,再罚去服筑城、舂米等劳役。
隶臣将城旦,亡之,收其外妻、子,子小未可别。——罚做筑城劳役的刑徒逃亡,就要罚他妻子、儿子做奴隶,儿子即使尚年幼,也不得赦免。
甲盗,臧(赃)直(值)千钱,乙智(知)其盗,受分臧不盈一钱,同乙可论?同论。——连相差一千倍也不作区别,一律同罪!
【刑罚酷烈、繁多】
秦法刑罚之烈、刑名之多,也是旷古未闻。总的可分徒刑、肉刑、死刑、族刑和杂刑等五大类。单以死刑为例,散见于《史记》等文献记载的就有——
腰斩——商鞅变法令规定:“民不告奸者腰斩。”(《史记·商君列传》)后来李斯就是被腰斩于咸阳市的。
枭首——斩下首级高悬示众。嫪毐集团中卫尉竭等二十人,皆处枭首之刑。
弃市——在闹市处死,并露尸街头。如“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史记·秦始皇本纪》)
戮刑——见前《法律问答》摘录。秦始皇弟长安君反,死屯留,军吏皆斩并戮其尸。
磔刑——破裂罪犯的肢体至死。车裂,即五马分尸,也是磔刑的一种。商鞅和嫪毐先后被车裂。
坑刑——也就是活埋。秦始皇“焚书坑儒”,“坑”了四百六十余名儒生,即用此刑。
定杀——投入水中活活淹死。《法律问答》:“疠者有罪,定杀。定杀何如?生定杀水中之谓也。”
镬烹——即油烹。前五章二节说到的齐客茅焦即险遭此刑。
具五刑——《汉书·刑法志》对“具五刑”的解释是:“先黥、劓(yì),斩左右趾,笞杀之,枭其首,菹(zū)其骨肉于市。其诽谤詈诅者,又先断舌。故谓之具五刑。”李斯就是具受五刑并被灭三族的。
此外还有“凿颠”、“抽筋”和绞刑等等。这些大多属奴隶制时代的野蛮刑罚,秦始皇却把它们继承了过来,有的更变本加厉,可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法制完备本是一个进步,但如此酷刑,却又是一大倒退,这大概是自以为集三皇五帝之尊的秦始皇没有想到的吧?
【行赏告奸,扩大株连】
这是秦律“刻削,毋仁恩和义”(《史记·秦始皇本纪》)的又一突出表现。
《法律问答》中有不少条文是鼓励同里、同伍以至父子、兄弟、夫妇之间相互告发和惩罚相互庇护的。如“夫有罪,妻先告,不收母妻媵臣妾、衣器当收不当?不当收。”这就是说夫妇之间一方犯罪,另一方有履行自告即告发的义务,这样做了以后不但可以自免,还可保住属于自己的那部分财产和婢仆;不然就将受到同样惩处。这种规定与儒家的主张“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春秋公羊传·闵公元年》)大相径庭。如儒家思想吸收较多的《唐律》有这样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父、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尽管实际上唐代对平民百姓并不见得就那么仁慈宽厚,但从理论上说毕竟还是不一样。
《史记·商君列传》载录的秦孝公变法令中还有这样规定:“不告奸者腰折,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赏罚之间相距天壤。据《史记索隐》:“告奸一人则得爵一级”。“爵一级”是一个什么样的官职呢?《韩非子·定法》称:“商君之法: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爵一级”大致等于多少价值呢?秦国曾实行过鬻爵制:“令百姓纳粟千石,拜爵一级。”一爵之价,竟是十二万斤粟子!一个普通农民可能一辈子也种不出这么多粮食来,而告奸一人便可“得爵一级”,这是多大的诱惑啊!这样比算可能不一定准确,但至少说明赏格是很高的。如此重罚与重赏双管齐下,当时告密之类的事一定发生过很多。纵使仍会有不为威胁利诱所动,甘愿以生命去殉道义的人,但他们却往往显得那样孤立。这种法令,我以为甚至比“具五刑”之类更野蛮,它要肢解的是人的灵魂。当然不能一概反对告发,但也不能否认这类极端规定对一个民族品性曾经起过的销蚀作用。它制造了一批犹大式的小人。鲁迅先生的小说《药》便是以一个告密事件作为背景材料的,读过小说,谁还能忘记那几个血淋淋的人血馒头呢!
又是轻罪重罚,又是行赏告奸,被认定为“罪犯”的面已经够宽的了,但秦帝国似乎觉得还不够,再加上一条措施来延伸它的网络面:扩大株连。“连坐法”是早在秦孝公时期就实行了的,有所谓家属连坐、邻里连坐、职务连坐或部门连坐等等。这样一人犯罪,或亲属,或邻里,或同伍、同事都要受到惩罚。在秦代灭家、灭宗、灭族的屡见不鲜,还有灭三族、七族、九族甚至有灭十族的:秦破魏时,有一公子逃亡,于是通令全国:告者赐金千斤,匿者罪至十族。这一切,正是秦帝国被后人斥为“暴秦”的一个重要原因。后世帝王们对此,则往往采取既暗中摘取山栗子,又公开骂它多刺的做法。例如据《汉书·刑法志》记载,汉代的法律就是“相国萧何捃摭(jùn zhí,摘录)秦法,取其宜于时者”编纂而成。正如清代学者孙楷《秦会要序》中指出的:秦法固峻刻,但“自汉以来递向沿袭,群以为治天下之具,无外于此”!
棋枰与棋子
古代人的生活,远没有现代人这样安定。由于地理或气候条件的变化,为着生存和繁衍,集体长途迁徙是常见的。《史记·殷本纪》:“自契至汤八迁。”《尚书·盘庚》:“盘庚五迁”。周的先租初居于邰,传至公刘迁到豳,到古公亶父时才定居于周原。只是这类迁徙都是由当时各该部族领袖自己作出决定的。周灭商而君临天下,接着又严厉镇压了商纣之子武庚发动的反周叛乱,这才出现了有一定规模的强迫性的迁徙,《尚书·周书》中的《多士》、《君陈》、《毕命》等篇,便留有周对殷商旧臣、遗民先后几次实施惩罚性强制迁徙的记载。就像本书一章一节所记述过的那样,嬴秦的先祖当时也是受到此种惩处的一个群体。他们离开了世代相依为命的东方故土,历尽长途跋涉的艰辛,来到关外这片陌生的西陲之地。八百多年过去了,历史倒过来了,如今轮到他们来对别人作出类似处理了!
实施迁徙,这是秦在帝国建立前就执行的一项政策。如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时,在京城有数以千计的人反对新法,就下令把他们迁到边疆去。秦昭襄王时每攻占新地,就迁徙秦民去充实。秦始皇自己在初亲政时,也先后将与嫪毐、吕不韦两个集团有牵连的数千户迁至蜀地房陵。当然所有这些都远远不能与帝国时代相比。从帝国建立开始的近十年时间里,迁徙达二十余次之多,规模之大,延续时间之长,在历史上都是空前的。迁徙地域既有通都大邑,也包括南北边陲。迁徙对象除了六国后裔、各地豪富,还有罪犯、渎职官吏和商贾、赘婿以及一般平民。手握至高权力的秦始皇,视帝国疆域为棋枰,随意调动枰上的棋子。有数字记载迁徙万户以上的就有: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将各地豪富十二万户迁移到咸阳;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徙“黔首”三万户至琅邪台下;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迁徙三万家到丽邑,五万家到云阳;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迁徙三万民户到北河、榆中定居。设想一下,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或同时,或先后,有几支成千上万扶老携幼的人群,艰难地跋涉在或是南疆、或是北国动辄千百里之遥的迁徙路途上,那是一种多么惨烈却又壮观的景象啊!痛苦、怨愤、病残以至死亡自不待言,但那一行行交错纵横于华夏大地上的脚印,尽管深深浅浅、凌乱不一,却已是南北东西无所阻隔,列国疆界只是作为历史陈迹还存在着,从而向世人宣告了这样一个事实:帝国确实已实现了空前大统一!
说秦始皇是在随意调动枰上的棋子,是就他根本不考虑被调动者的意愿和艰辛而言的;在他自己,却还是有经过深谋远虑而形成的以巩固发展帝国为目的的总体构想。在这一点,他又不愧为一位具有远大战略眼光的政治家。
总的看来,大体出于以下几种考虑,文中所举实例,均引自《史记》或《汉书》、《后汉书》。
一是为了惩罚。对象多为六国王室贵族及部分罪犯。如秦灭齐,迁齐王建于共;灭赵,迁赵王迁于房陵等,本书前已提到。此外还有:“秦灭魏,迁于湖阳,为郡族姓”;“秦既灭韩,徙天下不轨之民于南阳”。以至到了后世,列国之后往往各地可见:“定理、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颇有赵、齐、卫、楚之徒。”
二是为了实边。也有些并非属于边陲之地,只是秦始皇觉得需要进行移民加以充实的地区。此类迁徙人数最多。如充实南疆的: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谪遣戍”。还有充实北边的:“秦遣蒙恬攘却匈奴,得其河南造阳之北千里,地甚好,于是为筑城郭,徙各充之,名曰新秦。”为着充实的目的而作的迁徙,如果对象并非需作惩罚的罪犯,后期帝国还采取了一些奖励措施,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的有三次: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即免除迁徙者十二年徭役;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徙三万家丽邑,五万家云阳,皆复不事十年”;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徙北河、植中三万家,拜爵一级”。
三是为了工程。主要是修筑阿房宫和始皇陵。“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徙送诣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丽山”。还有就是造长城: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以适戍西北取戎为三十四县,筑长城河上。蒙恬将三十万”。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方越地”。所谓“不直”,指官吏断案违反了法律规定,也带有一定的惩罚性。
第四,姑名之为“特种考虑”。这主要指发生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那一次:“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既称豪富,显然非指一般的富裕人家,而是那些既有经济实力又有政治影响的豪门望族。在帝国诞生之初,一下子把如此众多的天下豪富都集中到帝国京都咸阳来,究竟为了什么呢?在这期间,秦始皇做的每一件事都有强烈的政治性和目的性,迁徙豪富这样大的事自然也是经过他和他的谋士们的慎重考虑,但留给后人的却只有猜测。学者们或从政治着眼,或从经济立说,分析了当时所以要这样做的原因。如林剑鸣认为“迁徙豪富,其目的是打击他们势力”(《秦史稿》);田昌五说是“进一步加强了对他们的控制”(《秦汉史》);郭志坤则认为有两个目的:“第一,在政治上对他们进行打击”;“第二,促进首都咸阳经济的发展”(《秦始皇大传》)。笔者不才,再也想不出别的可能来,以为三位所论大抵总是对的。可供参照的是汉高祖刘邦在灭秦兴汉初期,也曾进行过一次类似的迁徙,不妨看看此策之建议人建信侯刘敬是怎么说的——
[刘敬曰]:“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饶,可益实。夫诸侯初起时,非齐诸田,楚昭、屈、景(田氏和昭、屈、景三姓,分别为原齐、楚王室)莫能兴。今陛下虽都关中,实少人。北近胡寇,东有六国之族,宗强,一日有变,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臣愿陛下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杰名家居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
上(指汉高祖刘邦)曰:“善。”乃使刘敬徙所言关中十万余口。(《史记》本传)
刘敬说的好处有二:一是平时可借以防备匈奴;二是一旦天下有变,可率领他们向东征伐。总起来便是“强本弱末”。
值得注意的是,汉初迁徙六国之后及豪杰名家的安置地为整个关中;总人数是“十万余口”。
秦始皇迁徙天下豪富总数多达“十二万户”,而又全都安置在咸阳。
这使我不免起了疑问。
一是当时中国人口总数,据唐代杜佑在《通典·食货志》中估计也只有一千五百余万(《帝王世纪》、《文献通考》同此),是否真能产生如此众多“豪富”?
二是如果数字属实,事情就有点麻烦。
“十二万户”,会有多少人口呢?他们都是“豪富”,大概打光棍的不会太多,更多的则是妻妾子女成群,媵臣婢仆如林。像吕不韦那样的豪富,《史记》本传是有明确记载的,叫作“家僮万人”。即使前呼后拥、左跟右随之类强令他们统统不许随带,那么每户五口总是不能再少了吧?那就是六十万!咸阳原有多少人口,无从稽考。不妨做个比较。杨宽《战国史》认为战国时期“各国的国都中,以齐国临淄规模为最大,也最繁华”。临淄的人口据《战国策·齐策一》说当时的纵横家苏秦有过一个估计:“临淄之中七万户”。如果也以五口一户计算那就是三十五万。后起且居于关中的咸阳显然不可能有这么多。以一个不到三十五万人口的城市,能一下子吸纳六十万人口吗?即使出现了奇迹,那么一个外来人口占绝对优势的咸阳,还可能是原来的咸阳吗?此路不通,再换个方式试试。就算帝国建立后,咸阳人口暴增了一倍多,也达到了六十万,怎么样呢?麻烦还是不小:第一,那样公元前三世纪的咸阳,居然有了一百二十万人口,这是否有点近乎天方夜谭了呢?第二,即使这样,咸阳居民与外来豪富也还只有一比一。既称“豪富”,必然是那些既有智谋又有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的人,一比一,“控制”、“打击”得了吗?更何况豪富们是敌忾同仇、一致抗秦,而咸阳市民们则各有打算、形同散沙呢!所以如果真有那么多豪富,为帝国安全计,还不如散居在原址的好。一声号令统统迁徙集中,那无异于太阿倒持,开门揖盗,在帝国京城安置了一颗威力无比的定时炸弹。不错,秦始皇一向以喜好极端、善走险棋著称,但也不至于险到如此可怕程度呀!
我怀疑“十二万户”这个数字至少夸大了一百倍。但我疑而无据,所以只好打个过门,叫做“特种考虑”。特种考虑者,我回答不出也!
南征与北伐
统一六国战争的硝烟虽已止熄,但秦始皇并没有停止挥动他南征北伐的长剑。他的方针是:以减免赋税、减轻刑罚、奖励工商等怀柔政策,安定作为后方基地的巴蜀,同时南征百越、北伐匈奴,以继续扩展和巩固边疆。
南征与北伐究竟何者为先,当时秦始皇可能与群臣有过商议,并产生了不同意见。此事在《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似有端倪可察。话是传主主父偃在奏文中说的。他说秦始皇在并吞六国、海内为一后,仍然“务胜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进谏以为“不可”。理由一是,“匈奴无城郭之居,委积之守,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二是“轻兵深入,粮食必绝”,难于成功;三是即使胜利,“得其地不足以为利也,遇其民不可为役守也”。结果是“秦皇帝不听,遂使蒙恬将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为境”。
但实际上,下令蒙恬北伐匈奴的事,《史记·秦始皇本纪》有明确记载,发生在帝国建立后的第六年。这是否可以这样理解:秦始皇虽然不同意李斯进言,但行动上还是先采取了南征方案;主父偃只是为了叙述方便,略去了中间一段曲折。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一向“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的李斯居然能正面顶撞“上意”,秦始皇居然还能多少听从一点与自己相反的意见,这在帝国时期都是要算极为稀罕难得的事了。
南征时间可能在帝国建立之初,发兵五十万,统率大将为国尉屠睢(suī),目的是要平定百越。
百越也称百粤,是古代我国东南滨海诸少数民族,如瓯越、闽越、于越等的总称。百越之地,被古代中原人视为“文身断发”的蛮夷之族,传说中舜曾去南方“巡狩”,禹也曾“南抚交趾”,在当时人们意念中似乎已到了南天尽头。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华夏民族诸支族便渐次日益接近,并相互渗透。百越中最著名的一支于越,便在春秋时建立越国,与隔江相望的吴国演出了一部雄烈悲壮的“吴越春秋”。至战国,越国为楚国所征服。秦在灭楚的同时,也降伏了越君,置其地为会稽郡。这样秦帝国一建立,平定和统一大多居于岭南之地的百越,便成了题中应有之义。
但这一带有横亘于湘、桂、赣、粤间的南岭山脉,山高林密,峰峦峡谷重叠,沟渠川壑交错,不仅车行无路,连士卒也难以通行。岭南诸越凭借着险峻的地势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战斗进行得异常艰苦、激烈。《淮南子·人间训》记下了这次战役的全过程——
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馀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即史禄,秦御史)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百越中一支)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勇猛之人)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适戍以备之。
五十万大军,兵分五路,苦战三年,结果却是主将屠睢被杀,又“伏尸流血数十万”,遭到了严重挫折。原因除了地形险恶以外,还有越人的骁勇、机智和顽强。你杀了他们的君主,他们就迅速推选出一个勇猛之人来当头,再跟你干。打了败仗,他们退入丛林,宁肯与禽兽相处,也不当你的俘虏。他们还充分发挥自己善于爬山越岭和划船荡舟的特长,利用深山林密河流纵横的特殊地形,不断跟你神出鬼没“打游击”,致使人地生疏兼不惯水土的秦军“屯守空地,旷日持久,士卒劳倦。越乃出击之,秦兵大破”(《汉书·严助传》)。
从秦军主观方面来说,遭致失败还有一个原因,由于地形复杂,运输艰难,后勤供应不上。
这些困难自然是吓不倒秦始皇的。据《史记》及《汉书》等记载,他立即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增加兵力。命令任嚣、赵佗率领大批“楼船之士”赶赴岭南增援;同时,“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即岭南地)”。赵佗吸取屠睢教训,采取了一些缓和做法,如鼓励士卒与越民杂处等。为了稳定军心,又特地上书秦始皇“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始皇批准了他的请求,从内地派去了一万五千名“无夫家者”妇女。
二是派遣史禄凿渠通航。史禄凿通的这条渠就是著名的灵渠。灵渠又称湘桂运河或兴安运河,在今广西兴安县境内,长三十余公里。整个工程由铧堤、大小天平、南北渠道和秦堤、泄水天斗门等组成。兴安地势极高,地貌复杂多变,灵渠开凿后,原来互不相涉的湘漓二水竟在此汇流,从而出现了北水南合、北舟越岭的奇观,真可谓巧夺天工。宋人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中有这样介绍——
其作渠之法,于湘流砂嗑中垒石作铧嘴,锐其前,逆分湘流为两,激之六十里,立渠中,以入漓江与俱南。渠从兴安界,深不过数尺,广丈余。六十里间,置斗门三十六,土人谓之斗。舟入一斗,则复开一斗。俟水积渐进,故能循岩而上,建瓴而下。千斛之舟,亦可往来。治水之妙,无如灵渠者。
灵渠与帝国建立前分别由李冰、郑国修建的蜀地都江堰、关中郑国渠一样,是秦代创造而遗泽千秋的巨大水利工程,史禄的名字与李冰、郑国一样永远为后人所传颂。但在当时,灵渠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军事。灵渠通航后,帝国威力得以顺利施及岭南,军事上取得节节胜利,很快实现了全面占领。接着在那里设置了南海、桂林、象三郡,并征发五十万罪徒去戍边开垦。从此,长江以南广阔土地尽入秦帝国版图。
就在南征即将告成的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始皇帝又一道诏令,急命“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史记》本纪)。
这里所说的“胡”,主要是指匈奴。
匈奴之名在古书上记载不一,《史记索隐》记有“尧时曰荤粥,周曰猃狁,秦曰匈奴”的说法。战国时期,七国之中有秦、燕、赵三国的北部边境与匈奴为界。大致说来,当时居住于东北和北方的匈奴等少数民族,要比中原地区落后一个社会发展阶段,至战国末期才开始进入奴隶制社会。匈奴奴隶主贵族利用骑兵的优势,经常南下深入中原,进行骚扰和掠夺,还为此制定了特别奖励措施。如《史记·匈奴列传》中就有这样记载:“斩首虏,赐一卮酒,而所得卤(虏)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故其战,人人自为趣(趋)利。”赵武灵王锐意革新,改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而置云中、雁门、代郡。后赵将李牧守边时,匈奴不敢南窥十余年。秦灭赵决战一拉开,赵急调李牧及驻边赵军回师援救,匈奴又趁机纷纷南下。因而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就准备乘势北伐,上面已经提到,可能由于李斯的进谏才暂时搁置了下来。
促使秦始皇突然作出决定北伐的,是因为这一年他在巡视北边时,有个燕地人叫卢生的,呈奏了一件神秘的“录图书”,上面有这样一句话:“亡秦者,胡也。”由此触发,秦始皇毅然下决心立刻平定东北及北方地区的东胡、匈奴,以绝后患。
蒙恬是秦昭襄王时代著名将领蒙骜之孙,秦始皇灭楚主将蒙武之子,蒙门三代,都为秦将。蒙恬还有弟蒙毅。在兼并六国中,王翦父子是扛鼎大将;在帝国时期,蒙氏兄弟,恬任外战,毅为内谋,皆为栋梁重臣。蒙恬的勇猛和智谋,在灭齐之战中已锋芒初试。这次他受命率领三十万大军北逐匈奴,被后人形容为“若鸷鸟之追群雀,匈奴势慑,不敢南面而望十余年”(《盐铁论·伐功》)。这次北伐胜利,不仅收回了在秦与中原决战期间被匈奴乘机夺去的河套以南地区和原为赵地的九原郡,还扩大到河套以北阴山一带地区,共立三十四县,并重新设置了九原郡。随即秦帝国对这些设立的郡县采取了记载于《史记·匈奴列传》的这样两项措施——
因[黄]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
——即征发数以万计的中原内地人到这些新地区去充实户籍和开垦土地。
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缮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
——这样,就使历史上这些一向被视为化外“荒服”之地,也与帝国京都和中原诸地连接了起来。
修造帝国围墙
现在就要说到造长城。
修造诏令是在北伐第二年,即匈奴基本平定,大批戍边人员正在纷纷被征发而来的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下达的。督造长城的人正是在北伐匈奴中建立了大功的蒙恬。《史记》本传称:
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
从此,以龙的传人自称的华夏民族,有了一个永恒的物化象征:一条体长万余里的石龙。
这条巍峨、苍莽的石龙,由白水之畔起身,沿着奔腾的黄河,越过苍凉的阴山,然后蜿蜒东行;跨过祟山峻蛉,穿过茫茫风沙,至辽水又蓦地探身南下,最后在渤海湾舒坦地横躺了下来。也许它要畅饮东海之水,用以滋润华夏大地上它的万千子民?或者它要用自身的这个形象,向世人昭示一个真理:人与山、与水,原本就属一体吧?
站在这古老的长城之前,我们只有仰视,只有惊叹。
无法想象,我们民族为何在那历史的一瞬间竟会焕发出如此宏大的创造伟力!无法想象当时数十万人劳作在绵延千万里高山大河间的造城工地上,那是一种何等艰巨、又何等壮观的景象!无法想象如此众多的每块重达两千余斤的长方石,如何被肩扛手举运上连飞鸟也难以止栖的峭壁上去的!无法想象那时来自北国南疆操着各地方言的数十万先人,他们为此付出多少智慧和血汗,忍受了多少个霜晨和雪夜?他们熬尽精力的体躯有多少就长眠在他们自己修造成起来的这长城之下?尽管孟姜女属于传说,但既然有数十万征夫必然有数十万孟姜女,无法想象这数十万“怨女”和“弃妇”又如何在孤灯下度过她们凄凉的一生?
我们无法想象,只有仰视和惊叹。
如今,中国长城已作为全人类的骄傲,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遗产保护目录,全世界不同肤色的人们都向它投来了惊奇的目光。长城作为蕴含着巨大而深邃的文化意义的历史遗迹,无疑将与世长存;但它同时又作为秦帝国和秦始皇暴政的象征,千百年来被人们论说不休。唐代诗人汪遵以《长城》为题赋诗咏叹道:
秦筑长城比铁牢,
番戎不敢过临洮;
虽然万里连云际,
争及尧阶三尺高。
这是讥讽秦帝国纵有长城似钢铁,终因暴虐二世而亡;不如像传说中的帝尧那样,所居之处俭朴到“土阶三尺”、“茅茨不剪”,却能修盛德以感化四夷,舞干戚而有苗来服。
讥讽是辛辣而深刻的:万里钢城竟不敌三尺土阶。的确,历史一再正告世人:不可一世的暴力,最终总要在朴素的真理面前败下阵来。
不过我却想暂时放过对长城的功过评价,由这首诗生发开来谈点想法。
诗人是在做诗,不应从科学史观上去作苛求。事实上如果要求秦始皇也实行土阶三尺,就如同要求帝尧去造长城一样不合事理。
仔细想来,帝尧时代也实在只可能有土阶三尺。在远古时代,非但不可能造长城,也根本不可能有“长城”这个概念。从产生造长城的构想到实施造长城,都是要到春秋战国以后才有可能的事。而像绵延万余里这样大统一的长城,也唯有秦始皇和秦帝国才想得出,并做得到。
这是因为战争是发展的,战争中使用的进攻和防御的工具、设施也是发展的;战争的进行固然会对生产力带来强有力的刺激,但战争中使用何种武器装备和防御设施,归根结底还是决定于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何种程度。
帝尧时代如果发生战争,只能有一些木、石武器。可能还使用过猛兽。如《吕氏春秋·行论》说到鲧因为尧没有让他做“三公”,就“怒其猛兽,欲以为乱”。猛兽还不止一匹两匹,而是一大群:“比兽之角,能以为城;举其尾,能以为旌”。《尚书·甘誓》是夏启讨伐有扈氏的一篇动员令,其中有命令“车左”如何、“车右”如何的话,可能那时已有了兵车。但兵车和青铜武器的盛行,该是已到了商、周时代。那时,兵车多寡便成了实力强弱的主要标志,在先秦典籍中,我们经常可以读到“千乘之国”、“万乘之君”一类话。乘,就是一车四马。“万乘”甚至成了君主的代称。周代贵族子弟的必修课有六门,即所谓“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中“御”,就是要学会驾车。但一进入战国,特别到战国后期,随着铁制武器的出现,步、骑兵迅猛崛起,例如在秦国吞并诸侯大决战的各个战役中,只有兴发多少万兵卒的记载,似乎再也见不到兵车的影子。原来曾经逞雄一时的兵车渐次成为明日黄花,纷纷从前线退伍下来做了后勤运输辎重工具或防御障碍物。
在骑兵崛起过程中,应当看到当时居于我国北方那些惯擅骑射的少数民族作出的贡献,同时还不要忘记提到一个人,就是赵武灵王。
战国中期,赵国在与北邻中山国,特别是与善于骑射的东胡、林胡、楼烦等部族的交战中,屡战屡败。惨痛的教训使赵武灵王认识到了中原诸国仍以兵车为主的作战格局的落后性。但要学骑射,首先得从改变服式做起。于是赵武灵王不顾“大中原”传统思想的强烈反对,身体力行,带头脱下宽袍大袖、上衣下裳的中原服装,穿起了便于骑马驰骋的胡服短衣长裤,并且就这样上朝议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教百姓”(《史记·赵世家》)的首创性举动。在赵武灵王倡导下,赵国很快建立起强大的骑兵,并在战争中屡屡得胜。各国奋起仿效,骑兵这种奔驰如闪电、进击似霹雳的新型兵种,就这样跃上了七雄纷争的战场。在当时苏秦、张仪这两位纵横家的说词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些统计数字:秦、楚、赵各有“车千乘,骑万匹”,燕“车七百乘,骑六千匹”,魏“车六百乘,骑五千匹”(见《史记》、《战国策》)。这些数字虽难免有夸大不实之处,但至少说明短短几年工夫骑兵已取得了与兵车平起平坐的地位,它预示兵车为主的战争历史行将结束,以步骑兵结合的格局主宰战场的时代就要到来。
但就像既已出现“矛”必然会造出“盾”来一样,世界上的事情总是一物降一物,相互制约着的。大规模步骑兵结合对抗作战方式很快产生了它的对立物——长城。
战国时期,赵、齐、楚、魏、燕、秦和中山,都先后在自己边境的某一段造过长城。秦始皇造的万里长城,其中有些区段就是利用了原来秦、赵、燕的旧长城修缮、扩展、连接而成。
长城可说是城堡构想的延伸,是古代防御体系的极顶。
长城只产生在东方的中国,是有其独特的时空条件决定的。除了由帝王封建制转入帝王集权制这样一个特定的时代,还因为有大致以黄河南北为界,以农耕为主的中原和以游牧为主的北疆这样一种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一部双方争战不休的历史。所有这些一旦进入手握着至高至上权力、一声令下便能集结起人世间所有能量的秦始皇的头脑,便促使他产生了要为帝国西北部建造一道弯弓形的大围墙的构想。但如果我们深层地想想,就不难发现这一构想其实是个奇特的矛盾统一体:它一方面表现了秦始皇以为自己“无所不能”,可以凭意志创造人间任何奇迹;另一方面则又反映了他已认识到自己“有所不能”,不能勉强去做那些永远做不到的事。因为很显然,不惜以沉重代价强力南征北战所张扬的是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而修筑长城,把已竭尽努力扩展了的家国围护起来,所透露的则是一种消极的防守思想。这一点前人早有指出。如汉代桓谭在《新论》中说:“夫以秦始皇之强,带甲四十万,不能窥河西,乃筑长城以分之。”把秦始皇当时的心态揭示得更为清晰的则是中国现代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他在《建国方略》中说:“秦始皇虽以一世之雄,并吞六国,统一中原,然彼自度扫大漠而灭匈奴,有所未能也,而设边戍以防飘忽无定之游骑,又有不胜其烦也,为一劳永逸之计,莫善于设长城以御之。”一个“有所未能”,又一个“不胜其烦”,为“一劳永逸”计,不如造长城吧!在这里,我们终于极难得地看到了秦始皇毕竟还是一个现实的人,他不能不正视现实。
有大量的文献记载和孟姜女哭长城一类传说可以证明,秦帝国民众当时是反对造长城的。那正是战乱频仍的分裂局面结束不久,就像《史记·蒙恬列传》所揭示的那样:“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民众多么需要有一个休养生息的时期啊!偏偏秦帝国却几乎在同一个时间内,又是南征北伐,又是筑阿房、穿郦山、修直道、造长城,无论人力、物力、财力,都远远超过了可以承受的程度。如此繁重的负担,帝国又总是以暴力强制民众接受的。“当此之时,男子不能修农田,妇人不得剡麻考缕(剥麻纺线),羸弱服格于道,大夫箕会(苛敛民财)于衢,病者不得养,死者不得葬”(《淮南子·人间训》),平民百姓实在无法忍受了!
但无论如何,长城还是造了起来。对古代底层民众曾经做出的如此巨大的牺牲,我们只能表示深深的敬意。
造了长城,自然不可能真的“一劳永逸”地终止长城内外的争战,但长城的存在,在古代生产力和科学技术都还处于初始阶段的条件下,对北部边疆的来犯者多少会有一种制约作用,从而给生活于华夏大地的我们先人增加了一点安全感。
长城又是以帝国围墙的形式出现在世人面前的,因而在围墙怀抱之内,又有了一种大家庭的亲和感。翦伯赞先生在《秦汉史》中把秦人比作“历史的酵母”,他认为后来的所谓汉族,原是由殷族、周族、北狄、西戎等不同的种族亲和而成的,这中间秦族起了很好的催化作用。秦人原由东海之滨来到西陲,后来又由西而东,“他冲决了中原诸国之封建地方区划的堤防,打通了一切阻碍经济文化和血统交流的障壁,使中原诸文化种族,在他的冲刷与激荡之中,融化混合而凝结为一个整个的种族,即后来的所谓汉族”。秦族“冲刷与激荡”中之最烈者,便是秦始皇的兼并战争和帝国建立后的设置郡县、三大统一、实边迁徙、南征北伐等等,以及最后这个休止符:造长城。
当然,如果打开今天我们国家的地图,那么就会清楚地看到当年秦帝国这道围墙所怀抱的地区还不到整个疆域的三分之一。而事实上生活在这片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所有男女都属于一个和睦的民族大家庭。这最好不过地说明了长城的军事意义早己消失得无影无踪,但它留下的历史的意义、文化的意义和审美的意义,将不老长青。夕阳西落,长城内外一片金黄。蜿蜒裸露的城墙上长满着兴莽的荒草,残缺的烽火台边点缀着不知名的野花。岁月悠悠,人世沧桑。任何人,面对着这道横亘于天幕间的古老的大围墙,都会不由在脑海里复活起那一整部邈远、恢宏而苍凉的历史来,遥想、追怀、咏叹不休。
本章给大秦帝国勾勒了一幅轮廓,很难说有几分像。
末了还得补写一笔的是,在修造长城过程中,突然有一天从咸阳来了一支车队,从一辆装饰着金玉的乘辇上走下一个戴着远游冠的少年来。少年携带着秦始皇的诏旨,他是被派来监督蒙恬将军建造长城的。
这少年的到来,引起了人们极大的震动。因为他不是别人,而是公子扶苏,秦始皇的长子,人们按习惯已经认定的皇太子。
没有人会想到,扶苏自然也不会想到,从此他永远不可能回咸阳,永远不可能再见到他的父亲秦始皇。
扶苏离开京城被派到黄沙漫天的北疆来督造长城,该带有被贬斥的意思。他因何而被父亲秦始皇贬斥,这在后面八章二节还将谈到;这里先要说的是,就因他这一失宠而离开咸阳,便给了他弟弟、秦始皇的第十八子胡亥造成了可乘之机,以至当秦始皇在第五次巡游途中溘然离世时,赵高矫旨与李斯合谋让胡亥即了皇帝之位。于是,千百年来人们在对秦二世而亡发出感叹的同时,又一再惋惜起扶苏的长城之行来了!
明代李贽甚至认为派扶苏去北监蒙恬这正是“灭秦的大机栝”(《史纲评要·后秦记》);近代章炳麟还说:“借令秦皇长世,易代以后,扶苏嗣之,虽四三皇、六五帝曾不足比隆也!”(《秦政记》)
这当然只是旁人的一种猜测或假设,秦始皇自有他自己独特的想法。这位始皇帝和他所创建的秦帝国,还有着一段辉煌与暴虐并存、文明与野蛮迭现的历史要走,让我们还是循着主要由伟大历史学家司马迁记下的轨迹再来作一番最后的探访吧!
庄严、宏大的仪仗,雄壮、森严的卫队,秦始皇开始了五次全国性大巡游。
他站到泰山之巅,万木肃立,众山低头;芸芸众生似乎都成了蝼蚁,整个华夏大地仿佛在他一握之中。
他终于登上了功业和人生的顶峰,但他和他的帝国的悲剧却也就这样开始。
他狂躁不安,动辄暴怒,并在狂躁、暴怒中杀人,焚书、坑儒……直到最后实际上是自己戕杀了自己。
以上便是下一章的主要内容。
作为一个已经失去理智的暴君,秦始皇似应受到人们鄙弃;但作为一个特殊的人,一种特殊的心理,我想我们还是应该去接近、研究和理解他。为此,我尝试着进入他的内心,去感受他那种特有的狂傲、孤独和恐惧;直到在那个悲怆的沙丘之夜,静候在一旁观察他弥留之际的种种反应,目送他带着遗憾和隐忧孤单地向另一个世界走去…… 人生必读经典历史丛书:时代帝国三部曲之大秦帝国(上 下)(套装共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