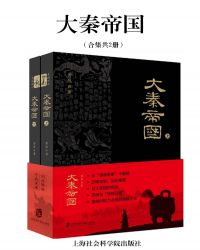灵车里凑成的三驾马车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人生必读经典历史丛书:时代帝国三部曲之大秦帝国(上 下)(套装共2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灵车里凑成的三驾马车
矫诏就从尸体旁发出
秦始皇临终之际的自信瞬间成了泡影。
这个中华第一帝国的始皇帝与他以后的那些帝王一样,生前那种一言九鼎的绝对权力,随着心脏的停止跳动顿时化作烟云散去。
赵高非但扣留了按秦始皇遗嘱必须以最快速度发出的遗诏,而且倒过来拿它作为一种威慑力量去胁迫他的未来同盟者就范,以实现他的全部计谋。
《史记·李斯列传》详细载录了赵高先后利诱与威胁胡亥、李斯入彀后,再共同密谋的全过程。
赵高先去找胡亥。
他对这个秦始皇的第十八个儿子说:皇上已经驾崩。临终时,对诸位公子都没有封王封侯,唯独对长子扶苏有一书在此。如果此书发出,扶苏来到咸阳,那么下一步便是他嗣立为帝,拥有整个天下,而您却连一寸土地也没有,这该如何是好?
胡亥说:也只好如此。古人有言,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既然父皇没有分封诸子,为臣、为子都应当遵从,还有何话可说!
赵高逼近一步说:不见得一定就是这样!如今帝国的大权,全在公子与高,还有丞相三个人手中了,天下事全凭我等一言。请公子早为自谋。须知为人臣与人臣于我,受人控制与我控制人,这可大不一样啊!
胡亥遽然作色说:不能那样做!废兄立弟,便是不义;不奉父诏,便是不孝;才智浅薄,强自为功,便是不能。这不义、不孝、不能皆为逆德背理之事,天下不服,岂可妄为!若执意孤行,必然遭致国危身殆,社稷祭祀也终将难保!
赵高哑然失笑说:公子不信高言,总该相信历史吧?从前汤、武弑主,天下都称大义,并没有人说他们不忠;卫辄杀父,卫国都称颂其德,孔子作了记载,也不认为他不孝。况且从来大行不顾小谨,盛德不矜小让,事贵达权,岂可墨守成规!倘若顾小而忘大,后必有悔;犹豫而让人,反遭其害。只要果断地敢作敢为,连鬼神也会退避三舍,何愁大事不成!愿公子三思。
胡亥喟然叹息一声,心已被说动,且说道:如今大行未发,丧礼未终,怎么可以为了这样的事,去干扰丞相呢?
赵高兴奋地紧接一句:此事好办!时机、时机,稍纵即逝,刻不容缓。丞相那里,臣即去说动,公子尽可放心!
好了,胡亥已落入赵高掌握之中,形成二比一的态势,说动李斯就不再是难事。
赵高又去找李斯。
李斯正关切着遗诏的事,一见赵高就问:赴北边的特使是否已经出发?
赵高说:遗诏现在公子处,高正为此事来与君侯商议。如今皇上驾崩和留有遗诏之事,外人全都还未曾听说,这样,究竟立谁为太子,就看君侯与高如何说了。君侯意为如何?
李斯不由一惊,说:足下此话从何处得来?此等亡国灭族之言,岂是为人臣者所当议论的!
赵高说:君侯却先莫惊慌。高有五事,愿求教君侯。
李斯说:你且说来。
赵高说:君侯不必问高,但当自问:才能与蒙恬比比如何?功绩与蒙恬比比如何?谋略与蒙恬比比如何?在天下人口碑中,与蒙恬比比又如何?最后,同长子扶苏之情好与蒙恬比比又如何?
李斯说:此五者,斯自然皆不及蒙恬。只是不知足下何故要以此责斯?
赵高说:高岂敢有责于君侯,只是提醒一句罢了。高原本一内宫厮役,赖粗知刀笔,入事秦宫已有二十余年。这么些年来,高从来见过秦国封赏过的功臣,有能连事二世君主的,最终还不是都遭到了诛夷!如今皇上有二十余子,皆为君侯所熟知。拿长子扶苏来说,他刚毅勇武,善于任人和激奋将士。如果依照皇上遗诏由扶苏嗣位,那么他必然任用蒙恬为相,到那时,君侯难道尚得保全印绶、荣归乡里吗?高曾受诏教习胡亥,他仁慈笃厚,敬贤礼士,拙于言辞而明于心志,在所有公子中无一能及。高以为应立胡亥为嗣,请君侯计议酌定。
李斯微露嗔怒说:请勿再言!斯仰受主诏,听由天命,自身得失利害已无暇顾及了!
赵高说:安可以转为危,危可以转为安。如今安危之势未定而听任其事,这如何算得明哲之士呢?
李斯勃然变色道:斯原本上蔡布衣,蒙皇上宠擢,才得以为相,又加封为彻侯,子孙也都获得高位重禄。皇上以帝国安危存亡属斯,斯如何能有负此重托呢?有道忠臣不避死,孝子不惮劳,作为人臣,斯只有克尽职守而已。请你不要再说了,免得斯因此获罪!
赵高看出,李斯实际是色厉内荏,已经显示出了内心的虚弱。刚才,他有意不把胡亥这张牌摊出来,现在他觉得已到了适当加点威慑力量的时候了。于是便又说道:从来圣人无常道,无非能见微知著,见末知本,适变顺时,观指睹归而已。方今天下权命,已全在胡亥握中,高也已遵从胡亥意旨,当可得志遂行。只是想到与君侯交好多年,不敢不以真情奉告。君侯老成练达,该能明察此中利害。有道从外制中为之惑,从下制上为之贼,君侯难道真愿意置身于此外、此下吗?其实,秋霜降,草木落;水解冻,万物苏;人事代谢,也属理之固然。先哲有言: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望君侯明断速决!
李斯默然良久,叹息一声道:历史明鉴,历历在目。晋废易太子,三世不安;齐桓兄弟争位,身死为戮;纣杀忠戮戚,社稷倾厄,国为丘墟。此三事皆违天逆理,最终导致宗庙绝祀。我李斯还是个人呀,怎能参与此等逆谋!
赵高听后故作愠色道:君侯既已如此说,高自然也不便勉强,只是尚有数语作为最后忠告。从古以来,大凡上下合同,事可必成;内外如一,业可永久。君侯若能听高之计,便可长为列侯,世世称孤,且寿若乔松,安享天年。倘若舍此而执意不从,不但自身危在旦夕,还难免祸及子孙,高实在为君侯寒心。有道善处者能因祸为福,请君侯择取吧!
说完这番话,赵高便做出要走的样子,实际是在观察对方的反应。
李斯这才明白了自己已处于二比一的危势之中。若待不从,祸患在即;勉强屈从,又觉违心。一时无法摆布,不由仰天长叹,垂泪自语道:我生不逢辰,偏遭乱世,既不能以死效命,又何以安托此身?主上不负臣,臣却要有负主上了!……
看看李斯也已被降服,赵高拱手一揖,便快步去向胡亥禀报。一开口,兴奋得已改称胡亥为太子了:臣奉太子之命,往达丞相,丞相岂敢不俯首遵奉。现请太子明示!
胡亥听了喜出望外,立刻召李斯来见,共商国是。
经过赵高这么一番奔走拉拢,决定未来帝国命运的三驾马车很快凑成。接下去便发生了《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的这样三件事——
高乃与公子胡亥、丞相斯阴谋破去始皇所封书赐公子扶苏者。
——秦始皇临终时那样艰难地写出的遗诏,这时大概还字迹未干,而他的继承者们却就在他尸体旁公然拆封,弃之如同废物。这实在是对秦始皇一生汲汲以求“独断”权势的一个极大讽刺。
诈为丞相斯受始皇遗语沙丘,立子胡亥为太子。
——李斯刚才还说过什么忠臣不避死、孝子不惮劳一类话,决心要克尽职守;现在却公开说谎了,而且是一个弥天大谎:以唯一的遗诏接受者的身份,证明秦始皇临终立胡亥为太子。
更为书赐公子扶苏、蒙恬,数以罪,赐死。
——胡亥还没有正式继位就先开始杀人,杀一切在他看来有碍于他继位的人。
这篇伪造的秦始皇赐长子扶苏以死的遗诏,据《史记·李斯列传》记载全文如下——
朕巡天下,祷祠名山诸神以延寿命。今扶苏与将军蒙恬将师数十万以屯边,十有余年矣,不能进而前,士卒多耗,无尺寸之功,乃反数上书直言诽谤我所为,以不得罢归为太子,日夜怨望。扶苏为人子不孝,其赐剑以自裁。将军恬与扶苏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谋,为人臣不忠,其赐死,以兵属裨将王离(王翦之孙)。
矫诏封就后,胡亥派出他宠幸的侍臣作为特使,迅速飞送扶苏所在的上郡。又恐扶苏违诏争先入咸阳,因而在这同时,又趁着天色微明,将秦始皇尸体安置于辒辌车,即日兼程回都,直至过雁门、入九原后,又演出了以鲍鱼乱尸臭那样一幕。看看已近咸阳,早有留守京都的右丞相冯去疾率众在郊外迎候。胡亥此刻最关心不是什么迎候,而是抢先一步进入阿房宫,占据皇帝大位。于是当即由赵高传旨:皇上疾重免朝。冯去疾等都还蒙在鼓里,对那一阵阵铺天盖地的奇臭自然不免惊疑,却也不敢多问,当即拥着辒辌车一齐驰入秦皇城。
胡亥该放心了:扶苏并没来咸阳。现在,他急于等盼的是:派出的宠臣来复命时,不知能否提着扶苏、蒙恬的头颅来?
三颗给嗣位做祭礼的人头
上郡。
绵延起伏,两端都望不到头的长城工地。
离工地不远是一片兵营,居中为将军帐。
将军帐内,一场悲剧即将发生。
现在扶苏以兴奋的心情在跪接父皇赐书。听到父亲巡游天下祷祠名山以求延寿,感到一阵担心和作为长子不能尽孝的不安;不料再听下去竟是“赐剑以自裁”,接着便是使者掷下一柄闪着寒光的冷剑。犹如一个晴天霹雳,他被猝然降临的灾难震得不能自制,回到内营,悲泣不止,也没有多想,便要举剑自刎。蒙恬抢上一步劝止说:皇上命臣将三十万众守边,以公子为监,这是关系帝国安危的重任,非得主上亲信,如何可以轻易授人!如今皇帝巡游在外,太子又未立,但凭一使者,便欲自杀,如何能知道他其中不藏诈谋呢?且待派人驰赴行在向上请命,倘然属实,再死也不迟呀!
扶苏自然也有怀疑,但经不住使者连番催促,速令自尽,逼得他胸无主宰,便对蒙恬说:父要子死,不得不死。我死便罢,何必多请!说罢便抽剑一挥,冰锋入项,颈血狂喷,当即倒地。
扶苏之死,很有点类似一章二节里提到过的晋太子申生,扶苏是又一个申生。
我忽而想,假设秦始皇在扶苏这个年岁上遭遇到同样的处境时,他会不会也说声“父要子死,不得不死”便挥剑自刎呢?我想可以肯定不会。由此说明,申生、扶苏的悲剧既有外部多种社会原因,也有个人性格因素。这也就是说,扶苏实在一点不像父亲。这使我又一次想到了他那个史书上并没有记载而我妄称她为郑姬的母亲。遥想她不仅端庄娟秀,而且善良温文,扶苏的性格大概主要取她的遗传基因。这样的女子很可爱,这样的男子纵然也令人羡慕,但在那个特殊的时代里却往往难以成就大事,特别是在残忍的政治角斗中更难免成为牺牲品。明代李贽在《史纲评要·后秦记》中认为,秦帝国所以速亡,是由“贼臣赵高杀太子,立胡亥”造成的,“使扶苏嗣位,即二世、三世传之无穷,何所不可”!如果扶苏嗣位,秦帝国的命运可能会有所改变,至少不至于那样残暴;但说能“二世、三世传之无穷”,恐怕未必。本书《结语》将讨论秦何以会速亡这个问题。我以为无论由谁继位,情况或时间可能稍有变更,但秦帝国的灭亡却是必然的。不过人心总是向着善良的弱者-边,一个像扶苏这样的好人被杀害了,人们会久远地同情和怀念他。扶苏死后,当时肯定有不少人为之深深惋惜;而当看到秦二世才智和胆识根本不能与秦始皇相比,而暴虐和残忍却超过乃父时,人们更会很自然地怀念起扶苏来。这从后来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打出的旗号中也可以得到证明:“乃诈称公子扶苏、项燕。”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从民欲也!”(《史记·陈胜世家》)
扶苏死后,子女是否同时被杀,无从查考。《陕西通志·陵墓》记载了兰水县东北七十里有两座女冢,相传为扶苏二女葬处。既说是二女而又葬于一处,该是尚未婚嫁的少女,且又同时死亡,那就很有可能是受到扶苏之案的株连。据《史记·高祖本纪》载录汉高祖刘邦的话说,秦始皇等人“皆绝无后”,所以特予若干家以为守冢。这就同时说明扶苏也是绝了后的。但马非百在《秦集史》中却引录了王桐龄《东洋史》一则很有意思的材料——
日本史载有融通王者,又号弓月君,于应顺天皇时率一百二十七县人口逃至日本,居于太和。其部民能养蚕,善织绢帛。仁德天皇见而爱之,赐融通王子孙姓秦氏,分置其邻族于各处,以养蚕为业。雄略天皇时,秦氏部民滋生至一万八千六百余人。朝命融通王之孙秦酒公率之养蚕,蚕大繁息。新成大藏以酒公为长官,赐姓大秦。融通王据称乃秦公子扶苏之苗裔云。此言果信,则扶苏虽不得良死,而其子孙尚能在中日两国文化史上作出巨大贡献,亦所谓“仁者必有后”者非耶?
我则以为这只能作为传说来读,但其中所寄托的愿望却是真诚的。其实,马老先生所引的“仁者必有后”这句古语,也只是人们的一种愿望,并非总是事实。鲁迅先生在《我谈堕民》中还说过相反的话。他认为“是好人的子孙会吃苦,卖国者的子孙却未必变成堕民的。举出最近的例子来,则岳飞的后裔还在杭州看守岳王坟,可是过着很穷苦悲惨的生活,然而秦桧、严嵩……的后人呢”?
现在再来看看蒙恬。
这员守边大将当然不肯就这样死。使者急于回报邀功,便把他交给狱官,先囚禁于上郡阳周,自己则立刻回咸阳复命。胡亥听到扶苏已死,心上重负顿解,高兴之余,倒也有意要宽容蒙恬,但赵高却非但不肯放过蒙恬,连恬之弟蒙毅也要一并杀之而后快。这里有一段宿怨。原来,蒙氏兄弟为蒙骜之孙,蒙武之子,蒙氏一门三世为秦将,功勋卓著。赵高在进入秦宫后,据《史记·蒙恬列传》记载,曾犯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当高罪死,除其宦籍”。后因秦始皇看他办事机敏,就赦免了他,恢复了他的官职。如今赵高觉得终于等到了一个报复蒙氏兄弟的机会。他趁机向胡亥进谗说:臣听说先帝在世时,早欲择贤嗣而立,以陛下为太子;只因蒙恬擅权,多次谏阻;蒙毅又在先帝面前日短陛下,致使先帝遗诏,改立扶苏。今扶苏已死,陛下登位。若蒙氏兄弟不诛,则其必为扶苏复仇,恐陛下终难以安枕,不如早日除之,以绝后患!
胡亥最关切的自然是帝位能否坐稳,听赵高这么一说,立刻下诏缉拿正在“还祷山川”后归途中的蒙毅。毅就缚后,暂时被拘禁于代地监狱。
这样,秦始皇时代的两位重臣,被分别囚禁于上郡和代郡;他们兄弟二人东西相隔近千里,却同时笼罩在死亡的黑影中。
丞相李斯,眼看着昔日的同僚命悬旦夕,却不置一词。
倒是年幼的皇孙子婴,勇敢地站出来作了这样一番直言进谏——
臣闻故赵王迁杀其良臣李牧而用颜聚,燕王喜阴用荆轲之谋而倍(通“背”)秦之约,齐王建杀其故世忠臣而用后胜之议。此三君者,皆各以变古者失其国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谋士也,而主欲一旦弃去之,臣窃以为不可。臣闻轻虑者不可以治国,独智者不可以存君。诛杀忠臣而立无节行之人,是内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斗士之意离也,臣窃以为不可。
这段话载录于《史记·蒙恬列传》。赵王、燕王、齐王事,见前六章各节。其中“立无节行之人”一句,明显暗指当时已是炙手可热的显赫人物赵高,说明这位小皇孙不仅有识,也有胆。
但是,胡亥褊窄的胸襟早被赵高所进的谗言塞满,再也听不进别的话。他派出一个叫曲宫的御史,搭乘驿车来到代地,传谕谴责蒙毅说:先帝尝欲立朕为太子,而卿乃屡屡阻挠,究竟如何用心?如今赵高以卿为不忠,罪当连及宗族。朕颇为不忍,只是赐卿以死。卿当曲体朕心,速即奉诏!
蒙毅跪着对答说:如果责臣以不能获得先帝的称意,那么臣自年少时就开始事奉先帝,谨顺上意,迭沐厚恩,直到先帝崩逝,该是使先帝称意了吧?如果责臣以不知太子的才能,那么太子独自跟随先帝,巡游天下,宠幸远远超过诸位公子,臣还能有什么可怀疑呢?再说先帝选立太子之事,那是思虑了多年的结果,臣又能有何言敢谏,何谋敢进?且其时臣又未侍于先帝之侧,何嫌何疑,乃加臣罪?臣非敢以粉饰言辞来逃避死罪,只是因为事情牵累到先帝的声名,又恐近臣蛊惑嗣君,故臣不敢无辞。从前昭襄王杀白起,楚平王杀伍奢,吴王夫差杀伍子胥,三君所为,皆贻讥后世。所以说圣帝明王,不系无罪,不罚无辜。请贤大夫垂察,代为上达,则罪臣幸甚。
那曲宫早已知道胡亥是非杀蒙毅不可的,已没有耐心再听,抽出佩剑,手起锋落,蒙毅已倒在血泊中。
接着胡亥又派出使节赴上郡阳周去向蒙恬宣读诏书,说是卿过错甚多,而卿弟又犯有大罪,故赐卿死!
蒙恬作了长篇辩答,其辞载录于《史记》本传。辩辞一开头便说——
自吾先人,及至子孙,积功信于秦三世矣。今臣将兵三十余万,身虽囚系,其势足以倍畔(通“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
蒙恬是秦国继王翦之后的著名大将,将兵三十余万在外守边十数年,确实有可能藉以发动叛变。事实上,富有政治斗争经验的李斯、赵高也已经估计到了这一点。《资治通鉴·秦纪二》在记到蒙恬被囚于阳周后,特地点出一句:“更置李斯舍人为护军”,就是派李斯信得过的家臣到原由蒙恬所率数十万之师去担任护军都尉。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胡三省在注中作了解释:“当是时,恬已属吏,恐其军有变,故以李斯舍人为护军,使之护诸将也。”不过,在这里,关键人物是扶苏。扶苏一死,即使蒙恬所部叛变,估计也不可能坚持多长时间。
蒙恬在辩词中还详细讲述了周成王初即位的故事。当时周成王还“未离襁褓”,所以只好由周公旦辅政,即所谓“负王以朝”。当年幼的成王得了重病时,周公旦又以剪下指甲投入黄河这样表示罪己的虔诚态度向神祈求:“王未有识,是旦执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并把这些话写下来,藏之于金縢(金属装饰之盒)之匮。后来成王亲政,便有贼臣出来中伤周公旦,说他就要作乱,王若不备,必遭大祸。成王居然信了,一怒之下,要向周公旦问罪。周公旦只好出奔他国。这年秋天,庄稼一片丰收景象,但到收获时节,忽而雷电交加,狂风大作,庄稼倒伏,国人大恐。成王与大夫们穿上祭天礼服,打开金縢,看到了周公旦记下的话,才深深感到自己错了,杀了贼臣,又把周公旦请了回来。蒙恬是将自己比作了周公,是贼臣的中伤,才使他落到了这个地步;又把胡亥比作成王,希望他能明察——
夫成王失而复振则卒昌,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而不悔,身死则国亡。臣故曰过可振而谏可觉也。察于参伍,上圣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于咎,将以谏而死,愿陛下为万民思从道也!
但是使者说,他只是依诏执法,不敢把蒙恬的话达于上闻。于是蒙恬仰天大呼:“我何罪于天?无过而死乎?”如此良久,最后被迫吞药自杀。
蒙恬不仅善于打仗,传说还发明了毛笔和筝。童蒙课本《千字文》中有一句“[蒙]恬笔[蔡]伦纸”,流传极广。
对蒙恬的被迫自杀,《史记》本传评语认为不值得同情:“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太史公从秦帝国初立,百姓需要休养生息,国事百废待兴,秦始皇不应兴师动众修造长城,这自然是具有经世济民眼光的确论;指责蒙恬没直言强谏,反而“阿意兴功”受命督造长城,似也不无道理;但因此而认为“兄弟遇诛,不亦宜乎”,是否对这两位古人过于苛求了呢?不过比起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秦纪二》的评论来,《史记》毕竟要高出一筹。这位司马迁以后最著名的历史学家先指责蒙恬在暴秦时期助纣为虐“不仁可知”,接着笔锋一转称道起蒙恬的“宁死不贰”来了:“然恬明于为人臣之义,虽无罪见诛,能宁死不贰,斯亦足称也。”唉唉,蒙氏兄弟倘若泉下有知,读此不知将作何感想?
三个心腹大患除去了,胡亥便一面为秦始皇发丧,举行隆重的葬礼,一面忙着为自己筹备登临极位的盛大庆典。
秦二世的“借光术”
读中国通史,可以看到一个几乎成为规律的现象:在声威赫赫的一代雄主离世后,继位者多半平庸甚至昏庸。也许正是由于他们自己平庸或昏庸吧,因而通常总是要想方设法借先皇巨大的光辉来折射自己,运用这种“借光术”使自己突然一个早晨膨胀至无穷大,成为所谓“当之无愧”的继承者。
最常见的借光术之一便是在历史条件下,以所可能做到的最宏大的规模,最隆重的方式,为先皇举行葬礼,自己则以对先皇最崇敬、最忠诚的姿态出现在公众面前,以便在人们心目中使自己与那个高下悬殊的前任一夜之间能够并列起来。
即将成为秦始皇继承者的胡亥,扮演的就是这样一个角色。
胡亥的平庸或昏庸,论者都较为一致。刘向的《新序·杂事五》记了这样一件事——
秦二世胡亥之为公子也,昆弟数人,诏置酒飨群臣。召诸子,诸子赐食先罢。胡亥下阶,视群臣陈履状善者,因行践败而去。诸子见之者,莫不太息。
这虽是一件小事,多少也可看出此人胸襟之褊窄:连看到群臣放在台阶上的鞋子有样式较为好看一点的,他也气不过,硬是要踩坏了再离去,难怪诸位公子要对他这种恶少行径摇头叹息了。
现在胡亥就要嗣位,自然要利用秦始皇葬礼,对他来说也就是第一次在皇室和群臣面前亮相的机会,着意重新塑造一下自己的形象。
胡亥主持下的秦始皇葬礼,史书没有完整载录,下面是一些散见于古籍的零星记载——
穿三泉,下铜(一作“锢”)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通“藏”)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史记·秦始皇本纪》)
合采金石,冶铜锢其内,漆涂其外。被以珠玉,饰以翡翠。中成观游,上成山林,为葬(同“埋”)之侈至此。(《汉书·贾山传》)
昔始皇为冢,敛天下瑰异,生殉工人,倾远方奇宝。于冢中为江海川渎及列山岳之形。以沙棠沉檀为舟揖,金银为凫雁,以流璃杂宝为龟鱼。又于海中作玉象鲸鱼。衔火珠为星,以代膏烛。光出墓中,精灵之伟也。(王嘉《拾遗记》)
如此穷奢极侈的葬礼,睡在铜棺中的秦始皇如果还能有知,他将作何表示呢?他将暴怒!这当然不是因为靡费,而是因为他看出,尽管参加葬礼的臣民人山人海,可是毫无真实可言,除了虚情假意,便是装腔作势。
没有一滴出自真情的眼泪;
没有一丝发自内心的悲哀。
他自然知道不肖之子胡亥如今正在扮演什么角色,他后悔不该让他随从第五次巡游,使这逆子有了可乘之机。
这时候他很可能会羡慕起一个人来,那就是被他逼死的吕不韦。吕不韦丧葬时,不仅有成百成千人真心吊唁,还有成千成百人为他“窃葬”。这些人非但绝对不是慑于权势应召而来,恰恰相反,是冒着生命危险违禁而来;他们向死者捧出的是一颗真诚的心。
秦始皇从此是永远地陷入彻底孤独了:“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李白:《古风·其三》)
但胡亥却还觉得不够,还要在负担已经够多的秦始皇尸体上再加重罪恶。他接连下了载录于《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这样两道命令——
先令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从死。
——野蛮的人殉制度在秦国虽比中原六国延续时间要长,但到秦献公一即位也就宣布“止从死”,废除了这种违反最基本人权的野蛮制度(见二章一节)。时间过去了一百六七十年,现在胡亥却又把它搬了出来,借口是没有生育过的后宫嫔妃不宜再出宫,结果是“死者甚众”。这个“甚众”里埋着多少条女子性命,只要看看秦始皇时后宫有多少人便大致有个数。《史记正义》引《三辅旧事》说:“始皇表河以为秦东门,表汧以为秦西门,表中外殿观百四十五,后宫列女万余人,气上冲于天。”如果这一记载确实,那么秦始皇有二十余个儿子、十个女儿。就算:这三十余个子女均为独生,“列女万余人”除去三十余人,被迫殉葬的至少还有整整一万!
大事毕,已臧,闭中羡,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臧者,无复出者。
——臧通“藏”。臧者,就是在陵墓中负责放置珍宝礼器等人。羡,指墓中甬道。为什么在落葬完毕后,要封闭墓道中门,把藏者和工匠统统活埋在地宫里呢?借口就是为了防止泄密。用如此惨无人道的方法害死的人究竟有多少,《史记》无录,《汉书·刘向传》记下了一个约数:“多杀宫人,生埋工匠,计以万数!”
如此残暴的葬礼实在是旷古未闻了!但当时的胡亥却肯定不会这样想。他可能为此而得意,以为这正是表明他对秦始皇的忠诚:为颂扬父皇神圣的声威,为使父皇陵墓万世长存,他设想得何等周到啊!
胡亥正是带着这种得意的心情,在臣民们的山呼“万岁”声中,大摇大摆地登上了大秦帝国的极位,宣布自己是秦二世皇帝,这一年(公元前209年)为秦二世元年,恢复自称“朕”。第二得意人该是赵高。他已任为总管宫中事务的郎中令,成为九卿之一,受到二世皇帝特别信用而专权用事。李斯此时还能勉强自保,内心虽是忐忑不安,屁股总算还依旧坐在左丞相位上。
胡亥的借光术还没有演完。继位后的第一道诏旨就是要再次借光:“二世下诏,增始皇寝庙牺牲及山川百祀之礼。令群臣议尊始皇庙。”
一是要增加秦始皇寝庙祭祀时的牺牲及祭品;二是要把秦始皇庙尊奉到比所有上古帝王包括嬴秦列祖列宗都更要崇高的地位。
尽管秦二世在其他方面可说一无建树,但他在一个巨人刚刚离世的那种氛围下提出这两点,倒也有他高明处,那就是决不会有人反对,调子只会越唱越高。果然,《史记》本纪接下去作了这样记载——
群臣皆顿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虽万世世不轶(dié,更迭)毁。今始皇为极庙,四海之内皆献贡职,增牺牲,礼咸备,无以加。先王庙或在西雍,或在咸阳。天子仪当奉酌祠始皇庙。自襄公以下轶毁。所置凡七庙,群臣以礼进祠,以尊始皇庙为帝者祖庙。”
就是说,要把始皇庙尊奉为秦帝国此后历世皇帝的祖庙,规定四海之内都要按职阶来贡献祭品,一切祭祀礼仪都完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为了突出秦始皇,嬴秦的历世先祖只好委屈一点了:自襄公以下的祭庙一律毁废。
如此这般做了以后,秦二世坐在那原先父亲坐的大位上,不知为什么,心里还是不怎么踏实。总觉得阿房宫实在太宏大,每次沿着陛阶一档档登上那高位去,又觉得实在太高。
于是他决定第三次借光。
这一回,要学他老爷子的样,也来一次全国大巡游。且看《史记》始皇本纪的记载:“先帝巡行郡县,以示强,威服四海。今晏然不巡行,即见弱,毋以臣畜天下。”当年,俺老爹是通过大巡游威服四海的;如今,俺要是不游一游,岂非让人小看了,还怎么让天下臣服呢?那就走着瞧吧!别觑着俺年少,咱照样也能游!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春天,小皇帝开始依样画葫芦地大巡游:用与秦始皇一样庞大的卤簿仪仗,走与秦始皇当年走过的相同路线:从咸阳出发,北至碣石,南达会稽;每到一地,也学着老子的样子不是登山,就是观海,照样也要刻石;不过没有另外立石,而是同刻在秦始皇所立刻石之旁。据《史记》记载其所刻之辞为——
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今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
这篇称之为二世诏书的刻辞,照例由李斯以小篆书丹,精工刻就。内容无非说,这些金石碑刻全是始皇大帝制立的,但原刻辞中没有指明这一点,为了免使年代久远后被人误以为是后世皇帝制立的,特作此说明。
这样两篇刻辞并列在一起,实在有些不伦不类。但秦二世这一回更得意了:这一下谁还敢说,朕不是与先皇并列在一起了呢?
以上所述,便是由秦始皇创立的帝王集权制所规定的、号称皇帝的这个国家元首大位,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传世接代。
皇帝之位,这是一个充满着诱惑力的神奇的宝座,同时也是一张罪恶的魔椅。坐上它,就意味着拥有万里江山,万千臣民,拥有生杀予夺的一切权力,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珠宝美女;坐上它,却又意味着成为众人所妒,众矢之的,如临深渊,似履薄冰,没个安生时日。它使多少人迷恋得发狂,又使多少人丧失了生命。它在中国延续两千余年的漫长历史中,不说改姓换朝期间的大砍大杀,单是每个王朝内部的传世接代,也不知演出了多少出兄杀弟、弟杀兄,父或母杀子女、子或女杀父母的惨剧,为的就是争夺这个神奇的宝座,这张罪恶的魔椅!
纵然这类惨剧从人类一跨进文明社会门槛就有,但作为“帝王集权”这种国家制度发展史上的第一幕,却是由秦二世这个历史舞台上既低能、又昏庸的匆匆过场人物揭开的。
不过,这还只是第一幕。除去那因其卑贱通常不予计数的埋在地宫下的一两万人以外,帝国朝堂上现在还只落下区区三颗人头,只能算是刚开了个场。更大量的流血还在后头呢!
“愿身不复生帝王家”
《史记·李斯列传》在将要记述后面许许多多血淋淋的场景前,却用“二世燕居”这样悠闲的文句起笔,实在妙不可言。
燕,通宴,就是安闲。的确,经过三次借光,秦二世自我感觉俨然一代雄主,坐在皇帝大位上已经十分安闲了。但安闲是一种人生境界,并非人人都能享受。有些人安闲不到半日,就会感到腻味。这不,秦二世现在已经耐不住了,觉得需要寻点刺激,于是便把赵高召来说:人生天地之间,犹如白驹过隙,太短暂啦!如今朕已君临天下,想要充分享受声色滋味和满足心志所乐,同时又要安社稷而乐万姓,长有天下,享尽天年。这样能做到吗?
赵高一听,正中下怀,他早就等待着这句话了。在他的计谋中,所谓三驾马车只是一个短暂的过渡阶段。第二步便是分解这三驾马车,由他独擅大权而玩弄小皇帝于股掌之上。但要做到这一点还很不容易。正像有一次他自己向秦二世吐露心事时说的那样:臣本是一个卑贱的内侍,幸而得到陛下的抬举,才得以掌管宫禁事务。可帝国朝堂上文武重臣济济,还有众多皇室公子,有谁会甘心听命于臣呢?他们“特以貌从臣,其心实不服”。赵高说的这句话,倒是事实。怎么办?办法他早已想好,就是借秦二世之手向他们一个个开刀!只是就像做文章那样,一时还找不到好的开头。现在小皇帝提出要玩乐了,文章以此为开头做下去可谓顺理成章,且天衣无缝。
他先来个欲抑故扬,针对秦二世既要长有天下,又想充分享乐的话头,回答说:只要是贤明的君主,一定能够做到;若是昏庸的君主,那就行不通。陛下是从古至今最贤明的君主,所以当然能够做到了!
秦二世听得喜笑颜开,当即说:那朕现在就要各种享受,就由卿代朕去办吧!
这回答也在赵高意料之中。他故意先作迟疑,随后突然一下跪伏于地,禀奏道:臣不敢逃避斧钺之诛,昧死请言,如今还没有到可以高枕无忧,尽情享乐的时候,愿陛下听臣一句话:危险还在眼前!
秦二世不由一惊,赶紧赐以平身,让赵高站着尽奏。赵高下面的话见之于《史记·李斯列传》,是专为后面大杀旧臣及诸公子制造口实的——
夫沙丘之谋,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诸公子皆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属意快怏皆不服,恐为变。且蒙恬已死,蒙毅将兵居外,臣战战栗栗,唯恐不终(不得善终)。且陛下安得为此乐乎?
说诸公子及群臣已对沙丘矫诏引起怀疑,这首先自然是赵高用来威胁秦二世的,但也很可能是事实。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恐有变”也并非全是捕风捉影。秦二世一听急了,连忙问该怎么办,于是赵高便说出了早已想好了的全部计划。综合《史记》始皇本纪和李斯列传的记载,这个罪恶的计谋大致包括以下内容——
(一)诛杀对象:诸公子、公主;诸大臣;并“以罪过连逮”到一些近侍郎官和部分郡县守尉。此外,还要杀掉秦二世“生平所不可者”。
(二)立案方法:第一,“愿陛下遂从时毋疑,即群臣不及谋”,就是说要赶在群臣合谋反叛之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网打尽;第二,“严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诛,至收族”。也就是要严刑逼供,扩大株连,直到灭族。
(三)善后措施:“尽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所亲信者近之。”就是要来一个大换班,大翻个儿:“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则上下集而国安矣!”
赵高此人从来为当国者所不齿,但他这三点计谋,却可谓流风百代,一直为两千多年来历世新君所乐于暗中忠实奉行,只是花样有所变换而已,即所谓“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也!这原是帝王术中一大奥秘,不料却被粗鄙的百姓一眼看穿,且在戏台上唱了出来,道是:“万里江山万里云,一朝天子一朝臣!”
且说当时,秦二世听完赵高全部计谋,学着秦始皇那种一言定乾坤的气派,手一挥说出了一个字:“善!”
在这个“善”字之下,究竟躺着多少冤魂,因未留下确切记载,连司马迁也只好记了这样一句:“不可胜数。”
朝廷及郡县臣属中被杀的,除李斯外,一个也没有记下来;对公子、公主的诛杀,散见于《史记》的有以下多笔。先说公子——
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阳市;
六公子戮死于杜。
两者相加,已有十八人。用了两种死刑。僇,据《礼记·大学》郑玄注为“大刑”,也即“辟”,就是砍头。戮,《国语·晋语九》韦昭注:“陈尸为戮”,即杀后再暴尸示众。
以上诸公子的审问官,都是赵高:“群臣诸公子有罪,辄下高,令鞠(通“鞫”,审讯)治之。”赵高自称长于刀笔,精通狱法,惯于罗织周纳,诸公子落到他手里,自然绝无活命指望。
再说公主——
十公主死于杜。
实在令人难以置信,秦二世竟连他那些文静秀丽的姊妹也不肯放过!“”与“磔”同,即袭其肢体而杀之。想象一下吧:十位少女,一起被刽子手一刀刀割裂她们娇嫩的体躯,直到她们撕心裂肺的哭叫声也渐渐微弱下去时,再砍下她们的首级。而坐在高殿上下令处以此毒刑的,正是她们的弟弟或哥哥——胡亥!呵,人世间怎么会出现如此野蛮、残忍、丑恶的一幕呢?这些自幼长于深宫的公主,如果说有什么过错的话,那就是不该生于帝王家。她们在忍着剧痛临死时,一定也会像六七百年后的南朝宋刘鸾那样向苍天大声呼喊:唯愿来生不再生于帝王家!
但屠杀到此还没有完。
“公子将闾昆弟三人,囚于内宫,议其罪独后。”这可能是一母所生的兄弟三人,由于生性敦厚,一时实在抓不到可以定罪的辫子,因而暂时囚于内宫,放到最后一批处理。秦二世挖空心思,终于挖出了一个罪名,便派使者去对将闾等三公子说:“公子不臣,罪当死,吏致法焉。”这是一个主观罪名。什么叫“不臣”?就是你没有臣服我秦二世大皇帝;无论你怎么辩解,只要我认定你不臣就是不臣,就得杀!
将闾明知辩解无用,临死前还是要一吐胸中奇冤——
阙廷之礼,吾未尝敢不从宾赞也;廊庙之位,吾未尝敢失节也;受命应对,吾未尝敢失辞也。何谓不臣?愿闻罪而死。
这是一只孤雁在临烹前的悲鸣。我处处、时时、一言一行,都是遵照礼制规定做的,总算谨小慎微了,哪有半点“不臣”呢?我不敢不死,只是要求在死前讨个“说法”:“愿闻罪而死”。对他这个可怜的要求,使者回答是他没有资格参与皇上计议,他只能奉诏行事。于是——
将闾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无罪!”
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剑自杀。
嬴秦自从襄公立国五百多年来,尽管也有过多次宫廷内讧,却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惨烈过!咸阳宫自从秦孝公修造启用一百多年来,纵使也有过一些屠杀事件,却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到处流淌着殷红的鲜血!
死亡的恐怖不仅震惊了京都,也震惊了整个帝国。司马迁接连记下了两个“振恐”:
宗室振恐!
黔首振恐!
这时候,却偏有一座府第显得异常宁静。
它就是秦始皇众多儿子之一的公子高之家。
门窗紧闭着。僮仆婢女早已遣散。母亲和妻妾都穿戴得整整齐齐安坐在席上。几个孩子也都依偎在母亲或祖母怀里不出一声。最小的一个,已衔着母亲奶头进入睡乡。
没有像其余诸公子府上那样恐慌,忙乱;没有人呼天抢地地哭叫。
没有,丝毫没有。
她们似乎在等待什么?
是的,在等待,而且是急切的等待。
等待获救吗?——不,等待死神的到来,而且是急切的等待!
如果这时候带着秦二世诏旨的搜捕队破门而入,她们便会如释重负地哄住受惊的孩子,一起平静地束手受捕,带着宽慰、带着希望走向死亡。
这个希望便是:公子高已于当天拂晓扮成一介寻常书生逃出咸阳城去了!
这群女人就怀着这样一个高于她们生命的希望,等盼着死神快快到来。
她们甘愿以自己的死,来掩护公子高的生。
黄昏来临了,她们万万没有想到,等来的不是死神,而是逃亡一段路程后又奔了回来的公子高!
破门而入的公子高,双膝跪倒在母亲面前,哭着哀求:不,母亲!臣儿绝不能把生留给自己,而把死亡留给母亲!臣儿作为七尺男儿,也不能为了自己活下去,而把妻妾儿女送向断头台。臣儿已经想好了一个办法:臣儿要用自己的死,换来母亲和妻妾儿女的生!
母亲一听,气得浑身颤栗,严命儿子立即出逃。一群妻妾携着孩子全都跪地,恳求公子赶快逃生。
这座宁静了一整天的府第,此刻已笼罩在一片惊慌、恐怖、凄惨之中。
公子高挣脱这群女人的拖牵,急步冲进书房,紧锁房门,匆匆写就了这样一封奏书——
臣高昧死谨奏:昔先帝无恙时,臣入则赐食,出则乘舆。御府之衣,臣得赐之;中厩之马,臣亦得赐之。臣当从死而不能,为人子不孝,为人臣不忠。不孝者无以立于世,不忠者无以存于天下。臣请从死,愿葬骊山之麓。唯上幸哀怜之。
奏书呈到咸阳宫正殿,秦二世看了大为高兴:朕正要命人去捉来正刑,他倒自己上书来请死了,这不省却朕好些精力了吗?又转念一想:莫非此中暗藏计谋诈变?朕得时刻提防着,莫为这些满肚子诗书的兄长们所算!立即召来赵高商议。赵高说:慑于陛下圣威,如今这些人担心死都来不及,哪里还会有诈变呢?二世这才放心,恩准公子高从死。
公子高是作为给秦始皇殉葬处理的,所以在三十余名公子、公主中得到破例的优待:“赐钱十万以葬”。
到这时,我国历史上皇位传世接代的第一幕,总算听到了落幕的锣声。
这数十名有幸生在帝王家的青年男女,他们的不幸也因为生在帝王家。
没有人知道他们被僇、戮、的尸骨存于何处。
他们自己也万万没有想到,事隔两千多年后,他们的墓葬地竟会成为人们研究的一个课题。
已经出版过多种秦始皇陵考古专著的王学理先生,不久前在新著《秦始皇陵研究》中宣布:秦公子、公主的墓葬有几处已经找到,都在秦始皇陵东陪葬墓区。提出的根据是:这些墓主身首异处,尸骨不全,被处死方式很可能是射杀或肢解;墓旁剩有用以取暖的柴火灰烬,说明墓葬时间是在寒冷的冬季。这些,都与秦公子、公主被害时的情景及时间是一致的。此外,这些尸骨经鉴定女性在二十岁左右,男性为三十岁上下,这又与秦始皇死年五十岁时他的子女们的年龄大体相符。至于秦宗室当时都是杀戮于市曹的,为何又搬到秦始皇陵畔来陪葬呢?王学理的回答是:“道理很简单,因为这些人的社会影响,具有二世、赵高们意想不到的号召力。杀戮是为了消灭政敌,既然目的已经达到,就按当时的社会意识……把他们陪葬到郦山。此举既反映了这些阴谋者的虚伪,无疑也是始皇用人失当而造成绝嗣误国的悲哀。”
被处死的三十余名秦公子和公主,《史记》只留下了扶苏、将闾、高三个名字。有意思的是,在这些陪葬墓中,还发现刻有“荣禄”、“阴”字样的两枚私印,王学理认为:“可以断定:前者为公子,后者为公主,从而也填补了史载之缺失。”
现在好了,该杀的人已经全部杀尽。秦二世一边擦洗满手血污一边想:这一下总可以高枕无忧、尽情享乐了吧?
《史记》始皇本纪在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四月,即在陈胜、吴广揭竿面起,全国掀起汹涌的反秦怒潮前三个月,记下了秦二世这样一些倒行逆施的诏令——
复作阿房宫。
尽征其材士五万人为屯卫咸阳,令教射狗马禽兽。
当食者多,度不足,下调郡县转输菽粟刍藁,皆令自赍粮食,咸阳三百里之内不得食其谷。
用法益深刻。……
这些诏令,秦二世自然还是要依赖三驾马车中的另外两匹老马去受命实施的。两匹老马之一的赵高这时候却在想:现在离计谋的全部实现只差一步了:如何最后再借一次小皇帝的手把李斯也干掉呢? 人生必读经典历史丛书:时代帝国三部曲之大秦帝国(上 下)(套装共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