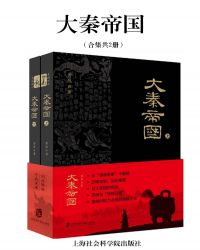两匹老马的一场肉搏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人生必读经典历史丛书:时代帝国三部曲之大秦帝国(上 下)(套装共2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两匹老马的一场肉搏
陷在泥淖里的艰难自拔
一失足成千古恨!
这句俗语不知是否能够用来描述李斯近日来的心情。
以下记述和分析,主要依据《史记·李斯列传》,凡出自本传的引文不再加注。
李斯生于楚国上蔡,先在郡里做小吏,后又去追随荀卿学帝王之术,学成后再西游入秦成为吕不韦门客。如此推算起来,他该是略少于吕不韦而长于秦始皇,这时候大约已到了近七十的年岁。一个人到了这个生命历程上,而又处于并不得意的时候,通常是会有所反省和自责的。在那个决定帝国命运的沙丘之夜,李斯开头对赵高说的那些要恪守人臣职责的话,不能认为全是虚伪,只是到了最后在他看来个人的荣辱存亡都处于迫在眉睫的临场一决时,心上的天平才在无奈中向屈从一方作了倾斜。这当然是一次不可原谅的屈从,已经不知有多少人为此丧失了他们无辜的生命。李斯自己,现在也不得不啜饮着由那些血浆酿成的苦酒。
这苦酒有多种成分。杀了那么多人,作为左丞相,他是难以推卸其责的。而胡亥继位后,“法令诛罚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畔(通“叛”)者众”;“赋敛愈重,戍徭无已”,这自然也引起他不安。除此之外,他之所以屈从,原是为了保住自己的爵禄富贵,而如今眼看着赵高那咄咄逼人的气焰,使他明显地预感到自己已处于岌岌可危之中。
不过比较起来,所有这些都还是次要的。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七月,一个晴天霹雳突然震响,秦帝国第一次被推上了存亡绝续的险境:“楚戍卒陈胜、吴广等乃作乱,起于山东,杰俊相立,自置为侯王,叛秦,兵至鸿门而却……”
李斯心急如焚了!在如今的三驾马车中,毕竟只有他,早在平定嫪毐集团叛乱前,就臣事秦始皇一起奋斗过来的。整整二十八个春秋了,他不能忘记兼并六国大决战中那些既紧张又兴奋的日日夜夜。他对秦帝国有着血肉感情,这不会虚假。除此之外,他总还坐在相位上,关系到帝国存亡的如此紧迫大事,叫他如何能不急!
李斯一次又一次地请求秦二世给予机会进谏,二世都没有准许。
这一天,李斯终于受到了召见,他急忙上殿去准备禀奏。谁知秦二世召他根本不是为了听他进谏,反而一见面就提出了长篇责问。这篇责辞很能反映在帝国存亡危急关头秦二世还在想些什么,所以特地予以全文抄录。
吾有私议而有闻于韩子也,曰:“尧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斫,茅茨不剪,虽逆旅之宿不勤(艰苦)于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粝之食,藜藿之羹,饭土匦(guǐ,此处指粗陋食具),啜土硎(xíng,此处指粗陋饮具),虽监门之养不觳(què,俭薄)于此矣。禹凿龙门,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决水致之海,而股无(bá,肉),胫无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于会稽,臣虏之劳不烈于此矣。”然则夫所贵于有天下者,岂欲苦形劳神,身处逆旅之宿,口食监门之养,手持臣虏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贤者之所务也。彼贤人之有天下也,专用天下适己而已矣,此所以贵于有天下也。夫所谓贤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万民,今身且不能利,将恶能治天下哉!故吾愿赐(通“澌”,穷尽)志广欲,长享天下而无害,为之奈何?
李斯一听惊住了!秦二世关心的根本不是什么帝国命运,而是如何随心所欲地尽情享受!在责辞中,二世还引了韩非的话,认为像唐尧、夏禹那样住比旅店还简陋的居处,吃的是比看门人还粗劣的食物,干的是比奴隶更苦更累的活计,这只有不肖的人才会那样去自讨苦吃,贤明的君主是不屑一顾的。君主之所以要拥有天下,拥有天下之所以可贵,只为两个字:“适己”,就是说整个天下都为了让他一个人尽情享受!最后,秦二世给李斯出了一道题目,命他交出答卷来:我既要“赐志广欲”,又要“长享天下”,你说吧,该怎么办?
在这种情势下,为私利所困的李斯再次显出了怯懦的弱点,不敢犯颜直谏,仓皇退下朝来。
李斯非但没有从泥淖中自拔出来,而且陷入了更大的矛盾和痛苦。
在这个时候,他很可能会想起扶苏来:如果在那个如今一切祸乱之根的沙丘之夜,我不是屈从,而遵照先皇遗诏迎回扶苏来继位,处境是否会比现在好一些呢?
事实上,真让扶苏继位,李斯将会有怎样的命运,也很难逆料。因为赵高说的话也不无根据:“高……管事二十余年,未尝见秦免罢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诛亡。”商鞅、范睢、吕不韦等等不都是这样的吗?但李斯还是会那样想。人在处于逆境时,难免会对事件初端曾经可能有的另外一种或几种选择,赋予比现实更美好的结局而加以追念。
但接下去李斯连在这样的追念中犹豫彷徨的时间也没有了,他遭到狠狠的当头一击,于是便在悚惧惶恐中又做出了第二次不可饶恕的屈从。
这狠狠一击来自他的政敌赵高。
李斯的长子李由,时任三川郡郡守。三川之地为函谷关东西必经通道,前三章二节在说到秦武王攻取三川之地宜阳时,曾经作过一点介绍。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七月,一夫作难,群雄并起。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被迫发出一声怒吼,立刻得到全国响应,各地反秦义军很快形成燎原之势。作为主力的西征部队,兵分三路,意欲对秦帝国心脏咸阳形成包围之势。其中第二路和第三路分别由铚人宋留和陈人周文率领,前者从南阳挺进武关,后者绕道主攻咸阳。第一路由假王吴广率领,进攻属于三川郡的荥阳,以开辟进军咸阳的东西通道。这样,首当其冲的三川郡郡守李由,就要与吴广的一路军交锋了。为避其锐,他采取闭城固守策略;义军几次进攻不下,双方暂时处于胶着状态。出乎李由意料的是,由周文率领的三路军,却正是利用了这种胶着状态,绕过荥阳,长驱千余里,直逼函谷,其前锋已威胁到咸阳。
荥阳前线这些急速发展中的消息,自然都没有逃过眈眈虎视于一旁的赵高的眼睛。现在他觉得铲除最后一个政敌的机会已经来到。他抓住李由阻击不力这个突破口,暗中派人搜集材料,上书诬陷李由通盗谋反,并向李斯发出责问:“居三公位,如何令盗如此!”(《史记·李斯列传》)李斯害怕了,为求自保,再次屈服于压力,向秦二世进呈了一份让他在回顾自己一生时感到羞耻的奏书:《谏督责书》。
李斯阿进“督责”之谏
《谏督责书》洋洋千余言,略长于李斯名篇《谏逐客书》。
如果说《谏逐客书》是李斯这颗政治明星跃升长空的信号的话,那么《谏督责书》便是它行将陨落的回光返照。前一谏里那种指画天下江山的气度,那种卓厉风发的进取精神,以至包括清朗酣畅的文笔都统统不见了,留在后一谏里的,只有狐假虎威的武断和霸道以及畏首畏尾的谀词和媚语。可以想见,昔日《谏逐客书》的作者今日写这样的文字,内心一定也是很痛苦的,但这种痛苦只能引起人们厌恶,毫无美感。
《谏督责书》共分四段。从第一段导论可以看出,作者完全是在奉诏作文,根据秦二世出的那道题目编写答案。问:如何做到既可“赐志广欲”,又可“长享天下”?答:臣昧死上言,请陛下实行督责之术吧!
夫贤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责之术者也。督责之,则臣不敢不竭能以徇(效命)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义明,则天下贤不肖莫敢不尽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能穷乐之极矣。贤明之主也,可不察焉!
实行这妙不可言的督责之术,既能独制天下,又可穷乐之极,而且还是“贤明之主”的专利,秦二世单是读了这段导论,想必就会乐不可支的。
第二段是总论,依照秦二世提出的题目,论述君主拥有天下的目的何在:是自适,还是适人?要旨就是主张自适,反对适人。文中引用了申不害的一段话:“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为桎梏”:君主拥有天下而如果不肆情纵恣地享受,那拥有天下岂非成了镣铐!谁把天下当作镣铐了呢?那就是一味只顾为天下之民而劳苦的唐尧和夏禹。这些内容简介大多是秦二世责辞的复述,只是文句略有变换而已,明显看出作者为了媚上而在曲意学舌。唯一的新东西,是把这两者区别硬拉到是否行“督责”这个题旨上来:行督责之道,则专以天下自适也;不能行督责的结果,则以天下为桎梏也!
第三、四两段回答如何实行督责,分别从君与民、君与臣两个方面作了论述。对民众强调要严刑峻法。引了韩非的一段话:“慈母有败子而严家无格虏。”但这话有很大的片面性:慈母家并非都是败子,而主人严厉的家里不见得就没有强悍不驯的奴隶。作者引用这句话的目的,是想借以说明:只有严刑峻法、轻罪重罚,民众才不敢轻易犯法,君主才得以长享天下和久处尊位。轻罪重罚到什么程度?文中举了商鞅之法中的一个案例:“刑弃灰于道者。”谁把灰倒在道路上,就刑罚谁。据《史记正义》说,其刑罚名称为黥,也称墨刑,就是额颊刺字,再涂上墨。李斯认为如此轻罪重罚的意义在于——
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罚也。彼唯明主为能深督轻罪。夫轻罪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
为了说明这层意思,文中例举了众多日常生活现象。譬如:地上有些许布帛,通常人们见了都想拾取;百镒美金在库,连跖这样的强盗也不敢来抢夺。其中原因并不在于一般人私心重或盗跖欲望浅,而是在于前者法律并不一定会予以惩处,后者只要一动手刑罚就立即跟上。据此,李斯认为——
明主圣王之所以能久处尊位,长执重势,而独擅天下之利者,非有异道也,能独断而深督责,必深罚,故天下不敢犯也!
最后一段论君臣关系,强调君主要独断专行,权力绝对不能让臣下分享。为了做到这一点,君主必须将以下三种人排斥在外——
一是“俭节仁义之人”,因为有这些臣子在朝堂上,那么“荒肆之乐辍矣”,君主就不能随意欣赏荒诞放肆的音乐了;
二是“谏说论理之臣”,因为有这样的臣子在旁边,那么“流漫之志诎矣”,君主就不能随心所欲了;
三是“烈士死节之行”,因为如果让这种行为在社会上显扬开来,那么“淫康之虞废矣”,君主就不能自由享受淫逸娱乐了。
李斯在写这几行文字时,不知道有没有想到过自己:他属于哪一类人呢?就在受到秦二世责问以前,他不是还一再想就陈胜、吴广山东之乱问题向二世进谏吗?而且他此刻正在写着的不就是一份谏书吗?而他居然把“谏说论理之臣”列于君主必须排斥的三种人之一,这实在令人惊诧莫名!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李斯认为自己就该列在被排斥人之一;或者他承认自己已经没有资格做谏臣和进谏,他只是在阿谀求容!
这与其说是自嘲,不如说是悲哀。
李斯忍着内心的这份悲哀,还得把颂歌唱下去——
凡贤主者,必将能拂世磨俗(抗世绝俗)而废其所恶,立其所欲,故生则有尊重之势,死则有贤明之谥也。是以明君独断,权不在臣也。然后能灭仁义之涂(通“途”),掩驰说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聪明,内独视听,故外不可侵以仁义烈士之行,而内不可夺以谏说忿争之辩,故能荦然独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
由此,强行得出全篇结论便是“国富君乐”。请看这“国富君乐”他是怎么演绎出来的吧!——
若此则谓督责之诚,则臣无邪,臣无邪则天下安,天下安则主严尊,主严尊则督责必,督责必则所求得,所求得则国家富,国家富则君乐丰。故督责之术设,则所欲无不得矣。群臣百姓救过不给(补救过失还来不及),何变之敢图?若此则帝道备,而可谓能明君臣之术矣!
尽管李斯这篇谏书的主要论点,如严刑峻法、独断专行等,都可以从韩非和商鞅的著作中找到依据,但把它们整合而成一种名之为“督责”的统治术,还是应当归之于李斯名下。如果这也算是一种理论,那么把它归属于法家体系大概不会错。只是应当说明它已是法家的末流。法家著作《商君书》,特别是《韩非子》,博大精深,自成体系,不愧是一个时代的智慧结晶。而所谓督责之术,是专门摘取其中若干过激论点,使其从整个体系,也即从它的合理的存在环境中游离出来,并把它引向极端,重新组合,且用之于一个已经建立了统一的大帝国的新时代,这就变成了赤裸裸的独裁和暴君的统治理论,说得彻底一点,便是一种导致亡国的理论。
公平地说,这当然违反李斯本意。
但不能否认,这却又是他经过一番苦心思索以后才写出来的。
如何理解此种矛盾现象呢?我的看法是:《谏督责书》不是李斯真实的政治主张,但却是他那可悲的性格的真实反映。
结果是这样的——
书奏,二世悦。于是行督责益严,税民(向民众抽税)深者为明吏。二世曰:“若此则可谓能督责矣。”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杀人众者为忠诚。二世曰:“若此则可谓能督责矣。”
看到“二世悦”,李斯大概也是高兴的;但高兴以后内心又作何感想呢?
看到“二世悦”,赵高脸上自然也呈高兴之状,但心里却很不高兴了。哼,就算暂时让你领先了一分,咱们走着瞧吧!
赵高巧解“朕”字含义
随着督责术的实行,朝堂上下,咸阳内外,臣民的怨愤在迅速积聚、激化,纵然不敢公开反对,暗中议论则愈来愈盛。这时候李斯似乎又有了重新受到信用的迹象,因而议论集中到了赵高身上。赵高自知“所杀及报私怨众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毁恶之”,因而便紧急行动起来,运用自己的巧智,挽回面临的殆势。
秦始皇曾一度将皇帝自称“朕”改成自称“真人”,秦二世嗣位,又明令恢复自称“朕”。可这位已经二十一岁的皇帝,似乎连“朕”是什么意思也还没有弄懂。
于是赵高便利用自己曾是太傅的身份,以向秦二世解释“朕”字含义为幌子,把面奏皇帝之权全都抓到自己手上来。
赵高玩的这套花样《史记·李斯列传》有详录。我们先来看看他是怎么解释“朕”这个字的含义的——
天子所以贵者,但以闻声,群臣莫得见其面,故号曰“朕”。
“朕”字本有多义,其中常用的,一是朕即身,也即自身,古人用来自称,义与我、吾等同;至秦始皇才宣布朕为皇帝自称。二是朕为征兆,预兆。作为皇帝自称自然该取第一义,赵高却玩了个花招,改取第二义,并作了随心所欲的发挥。
秦二世居然听信了。赵高立刻抓这个机会,趁势贩卖他的私货——
陛下富于春秋,未必尽通诸事,今坐朝廷,谴举有不当者,则见短于大臣,非所以示神明于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与臣及侍中习法者待事,事来有以揆(研究处理)之。如此则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称圣主矣。
这就是要秦二世深居禁中当傀儡,不要临朝管事。理由是你皇帝尚年轻,未必什么都懂,若是当朝断事,容易露短,反而有损于自己的“神明”。所以皇帝尽可安居深宫,大臣奏事上来,让我赵高和几个熟习法典的内侍来酌情处理。这样大臣们就不敢上奏那些混淆是非的事,天下都将称颂陛下为圣主。
结果是:“二世用其计,乃不坐朝廷见大臣,居禁中。”
赵高之所以能够售其计,除了他那个曾经是太傅的身份对二世有一种迷惑作用,还因为类似这种所谓“虚君实臣”的理论,在那个时代是颇为流行的。如《管子·霸言》:“夫权者,神圣之所资也;独明者,天下之利器也;独断者,微密之营垒也”。《韩非子》的《主道》、《扬榷》篇:“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虚静无事。以见疵”;“上固闭内扃,从室视廷”。这里的根本区别,在于主动权究竟掌握在谁手里。无论是管子的“独断于微密之营垒”,或韩非子的“虚静无参,从室视廷”,都只不过是君主使用的一种南面术,也即帝王术,是一种方法,一种手段,君主绝不会放弃主动权。就像《吕氏春秋·君守》说的那样:“大圣无事,而千官尽能”,君主只是不参与具体政务,事情都让臣下去做,自己则行使任免、奖惩之权。这也就是说,在国家权力运作过程中,要把君主行使的决策、指挥职能,与臣子也即行政机构行使的实施决策和具体启动运作职能区别开来。在当时社会条件下,这样区分不失为一种合理的政治主张。而赵高由巧解“朕”字含义而诱使秦二世在禁中“深拱”起来的计谋,则是以这种南面术为幌子,实际上是要秦二世靠边站,由他一人来专擅朝政。
奇怪的是,李斯谏行“督责”之术,秦二世很高兴地采纳了;这回赵高再献“深拱”之计,他也采纳了,简直像杂耍场上一条猴子,随便抛去一个花花绿绿的什么玩意儿,它都会高兴地抱住。不过,毫无原则的秦二世还是有他自己的“原则”的,那就是既要感到自己至尊至上,又要充分获得感官享受。
这样,赵高便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赵高常侍中用事,事皆决于赵高。”
现在赵高已可玩弄二世于股掌之上了,这也就是说,已经到了可以收拾李斯的时候了。
这一天,赵高特地去拜谒丞相府,寒暄过后,故意渐渐把话题引向山东乱事。李斯毕竟还是牵挂着帝国命运的,顿时锁眉长叹,唏嘘不已。赵高便趁机说道:关东群盗多如牛毛,警信日至。听说山东六国后裔,如今都在纷纷图谋复立,倘若任其长成羽翼,这秦氏天下实在堪忧啊!
李斯说:皇上近日来,不知可有励精图治、全力平乱的意向?
赵高移席近前说:主上太年轻了,成日里只是耽于淫乐。如今又急于征发役夫,修筑阿房宫,采办狗马,珍禽异兽,充斥宫廷,且从不知自省。高几次想进谏,终因位卑职贱,人微言轻,不敢唐突啊!
这么说着,长叹不已。
李斯也随之扼腕而叹,说道:皇上年少,如今若能有周公旦再世就好了!
赵高忽而兴奋地接口说:高倒记起一事来了:那回沙丘之夜,高曾听君侯说过先帝曾以存亡安危属君侯的话,那时君侯不正以周公旦自况的吗?高以为,如今朝堂上下,也唯君侯一人,既为先帝功臣,又受当今隆恩,德高望重,主上可以听从进谏。君侯曾经说过,有道忠臣不避死,孝子不惮劳,为帝国前途计,君侯何不一谏呢?
李斯被赵高一番话说得心热了起来,也无暇去想其中是否藏着蹊跷,便说道:斯欲进谏已经多时了,只是皇上如今已居于深宫,不坐朝廷。斯所欲言之事,又是不便于由别人转达的。想要当面进谏,又没有合适机会,所以一直延搁至今。
赵高说:这好办。君侯若是真要进谏,待高探得主上有闲暇时,即来报知君侯,君侯前去面奏便是!
李斯很高兴,便在府第里闭门不出期盼着。
过了两天,赵高果然派人来说,君上此刻正闲暇无事,机会难得,请君侯急速进宫。
李斯不敢怠慢,匆匆换上朝服,赶到深宫门外,求见皇帝。
这时候,秦二世正在宫中宴饮,左拥右抱,与一群美女作乐。忽有内侍来禀报说,丞相李斯求见。二世怫然说:有何要事,来败朕酒兴?说朕正忙着呢,快叫他回去吧!
又过了两天,李斯再次由赵高派人通知而进宫,却再次因二世正玩乐在兴头上而无法晋见。
读者不难猜到,赵高是有意选在这种时候通知李斯来进见的。
李斯这样前后求见了三次,自然全被二世叱回。
秦二世发怒了。他对赵高说:朕平常闲暇的时间很多,丞相倒不来奏事。每次朕正在宴乐,他就偏偏在这个时候来求见了,这事情很怪!怕是丞相因朕年少轻视朕,或者故意刁难朕吧?
赵高故作一惊说:哎呀,这事可太危险啦!沙丘那个计谋,是丞相一起参与的。如今陛下已即临帝位,而丞相恩宠没有增加,爵禄未见加赏,他自然内心不满,有意轻视或刁难,还是小的呢!臣有一事,已经狐疑很久,只是怕有违圣听,一直不敢禀奏……
秦二世大声催促:卿快奏来!显然他已被赵高撩拨得怒火中烧。
赵高说:丞相原是楚国上蔡人,如今在山东犯上作乱的众盗之首陈胜、吴广,原来也都是楚国人,而且就是丞相邻县之子,他们本有乡邻之谊。所以这回强盗在楚地公开横行,吴广率领众盗侵犯山川之地时,丞相之子李由身为三川令,却只是固守,不肯出击众盗,致使盗酋周文得以破函谷、逼咸阳。臣听说李由与群盗之间多有文书往来,只是由于还未曾核实,所以不敢来奏禀陛下。如今看来,丞相很可能就是因为未获增封加赏而心存不满,由其子与群盗勾结起来,借此机会裂地为王。而且丞相府又在宫外,丞相之权又重于陛下,一旦起谋,后果不堪设想啊!
秦二世又信了,就决定惩办李斯。
但这一回昏庸的二世倒忽而有了一点清醒。因为赵高说得很含糊,他怕不确切,就派人去核查三川郡郡守李由与盗贼暗中勾结的实际情况。
《史记·李斯列传》记到这里时有这样一句:“李斯闻之。”
禁宫之内如此机密情报,居住于宫廷之外的李斯是怎么“闻之”的呢?这只要联系八章一节中提到的秦始皇随口说了声李斯出行车马太多,立即有人暗中去报告李斯一事便可明白。在宫廷各派的权力角逐中,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赵高虽然已经笼络二世、专擅朝政,但他手下不见得就没有李斯的人。
李斯得密报,这才发觉自己已经坠落在赵高设下的陷阱里了!陷阱从来都是设置在花丛下的,李斯只好责怪自己不该在赵高那些谄言媚语下失去了戒备。而且这一回是直接得罪了皇帝,触犯了龙喉下那片其长径尺的逆鳞。儿子李由的所谓通盗案,也落到了皇帝手里。李斯越想越怕,寝食难安,紧张地思谋着如何来跳出眼前这一灭顶的险境……
坠落陷阱后的垂死挣扎
在这期间,《史记》始皇本纪和李斯列传各记载有李斯的一次进谏,内容全异,估计可能是两次。
本纪载录的一次是李斯与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劫一起进谏的。一种可能是,此时巳感到岌岌可危的李斯,觉得需要拉二冯壮壮胆。进谏内容是为止息盗患提供对策的,李斯也许想借以重新获得二世的信用。
关东群盗并起,秦发兵诛击,所杀亡甚众,然犹不止。盗多,皆以戍漕转作事苦,赋税大也。请且止阿房宫作者,减省四边戍转。
谏言认为“盗多”杀而不止的原因有两条,一是戍守、漕陆运输等各种差役太多、太苦;二是赋税太重。这虽不能说是民众奋起抗秦的全部原因,却正是其中两个重要原因。谏言提出的对策也是两条:停止修造阿房宫,减省四边屯戍和物资转送。这样既可减少大量劳役,又可节省国家开支因而得以减轻民众赋税负担。
秦二世根本听不进去。
他在批复中又引了韩非那段记述尧、舜、禹贵为天子仍然苦心劳身的话,然后说——
凡所为贵有天下者,得肆意极欲,主重明法,下不敢为非,以制御海内矣。夫虞、夏之主,贵为天子,亲处穷苦之实,以徇百姓,尚何于法?朕尊万乘,毋(无)其实,吾欲造千乘之驾,万乘之属,充吾号名。
秦始皇当年巡游全国时,也只有八十一辆属车,如今这位小皇帝居然认为自己既已为万乘之尊,因而要建造什么“千乘之驾,万乘之属”,才能与他名号相称。好在他不久便被迫自杀,要不,如果真把这千乘加万乘的车驾连接起来,那不是要出现第二道长城了吗?
秦二世非但拒谏,倒过来又责问三人——
且先帝起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边竟(通“境”),作宫室以章(即“彰”)得意,而君观先帝功业有绪。今朕即位二年之间,群盗并起,君不能禁,又欲罢先帝之所为,是上无以报先帝,次不为朕尽忠力,何以在位?
李斯等三人的进谏,竟被认为是犯了“上无以报先帝,次不为朕尽忠力”的大罪,处境已十分危险。
李斯的另一次见之于《史记》本传的进谏,可能是紧接此次进谏以后。
这一天,秦二世在甘泉宫“方作觳抵优俳之观”。
觳抵,即角抵,是秦汉时期一种技艺表演,大致类似现代的摔跤。
李斯刚要进宫,听得阵阵喝彩声从宫内传出。秦二世正在赵高等人的侍侯下,看得手舞足蹈入了迷。李斯有了上几回教训,既不敢再让谒者通报,更不敢唐突进去,只是站在阶前徘徊,一种莫可名状的怨愤和耻辱感折磨着他那颗怯懦的心。他多么想立刻转身回相府去,但一想到那个更可怕的厄运已经笼罩在头顶,又不忍就此离去而失却一个或许还能勉力挽回命运的机会。
偏是冤家路窄。
赵高偶尔离席出来走走,一眼看到在阶下悻悻徘徊着的李斯,自然立刻明白了一切,却故意大声吩咐宫前和廊下手执戟钺威严地站立着的虎贲卫士道:尔等听着:皇上今驾幸于此,一切闲杂人等必须肃静回避。凡有敢滞留不避者,格杀勿论!
两个卫士小心翼翼地来到李斯面前,恭恭敬敬地转达了郎中令的命令。
一团怒火猛地拱上心头。李斯怒斥一声:大胆,我自有事求见皇上,与尔等何干!
双方争执了起来。
站在宫门口的赵高,兴奋地远远看着自己导演的这一幕,着实欣赏了好一会,才走出宫去,喝退卫士说:谁让你们如此无礼!你们难道连丞相都不认识了吗?又急急走下阶去恭敬地说道:君侯要见主上,何不让人通报呢?现在高就为君侯去通报如何?
李斯狠狠朝赵高瞪去一眼,拂袖转身就走。
当他登上车乘时,几次大声喝令御者加鞭,就像背后正追赶着一群饥饿的猛虎。
回到相府以后,李斯觉得他不能就这样束手待毙。只要还存在一线希望,就得挣扎!
他在几案上铺开绢帛,写出了又一份谏书。
臣闻之,臣疑(通“拟”)其君,无不危国;妾疑其夫,无不危家。今有大臣于陛下擅利擅害,与陛下无异,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罚,以威行之,期年遂劫其君。田常为简公臣,爵列无敌于园,私家之富与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群臣,阴取齐国,杀宰予于庭,即弑简公于朝,遂有齐国。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之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于齐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韩为韩安相也。陛下不图,臣恐其为变也。
陛下,赶快采取措施呀,您身边的赵高就是当年宋国的子罕、齐国的田常、韩国的韩玘式的人物,太危险啦!——这便是李斯这份谏书的要旨。
谏书内容无疑是切中要害的,但李斯的这种挣扎却只能加速自己的灭亡。因为他的这次进谏与二十五年前韩非的进谏(见六章一节)极为相似,只不过位置倒过来了。那一次韩非在秦王嬴政面前诘难李斯的伐韩论和揭露姚贾私交诸侯之罪,而李斯、姚贾当时正为秦王嬴政所信用,因而反被怀疑为是在离间他们君臣关系,秦王嬴政一怒之下便“下吏治非”;这回是李斯在秦二世面前揭露受到二世信用的赵高是个危险人物,他难道还能逃脱类似韩非的结局吗?
也许是谏书把问题提得太尖锐了,迫使秦二世单独召见李斯。
秦二世在李斯面前,反把赵高夸奖了一通。他说:赵高纵然是个宦官,可他没有因为安逸而随心所欲,也不因为危难而改变忠心。他到这里受事以来,由于忠诚而得到提拔,因为信实而持有禄位。朕确实认为他很善良,可你却偏偏怀疑他,那是为什么呢?再说朕这么年轻就失去先父,缺少识见,不习治民,而丞相你已年老,朕若不把国事托付给他,又能托付给谁呢?而且赵高为人精廉勤力,下知民情,上适朕意,你可不能再怀疑他啦!
李斯知道自己已经全军覆没,只是还想最后挣扎一下。他说:陛下,事情可不是这样啊!赵高原是个卑贱的人,他根本不懂道理,他的权势已经可以与陛下并列,他却还是贪得无厌,求利不止,这样的人对陛下太危险啦!
有句谚语说得好: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囿于成见的秦二世怎么也想不通,李斯为何要平白无故如此怀疑赵高。他甚至有一种担心:怕李斯会去杀赵高。对,得提醒一下赵高!于是便召见赵高,把李斯谏书的内容全告诉了他。到了这一步,赵高已欣喜地看到李斯的末日近在眼前了。落井再下石,他巧妙地拾起李斯谏书中田常那块石头,再向李斯掷去:陛下,真正的田常就是丞相呀!丞相现在所以还有顾忌,正是因为有臣赵高在,所以他要杀臣。只要臣一死,他就可以放手像田常那样做弑君谋位的事啦!
秦二世忽而觉得恍然大悟,就说:那就把李斯交给卿去办吧!
李斯落到这个狡猾而残忍的政敌手里,还能指望有什么善终吗? 人生必读经典历史丛书:时代帝国三部曲之大秦帝国(上 下)(套装共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