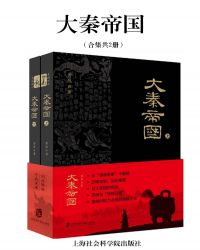铁与血的变革在关中大地掀起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人生必读经典历史丛书:时代帝国三部曲之大秦帝国(上 下)(套装共2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铁与血的变革在关中大地掀起
奇才应《求贤令》西来
秦孝公参加即位大典时(公元前361年)的心情,与其说是兴奋,不如说是激愤。
父亲的临终嘱咐已深深烙印在他心上,而山东列强愈演愈烈的角逐形势,却使他一颗热血喷涌的年轻气盛的心,焦躁不安。诸侯们经常在这里、那里会盟,任意分割着天下,却把已经具有相当实力的秦国仍然视为夷戎之邦而有意冷落在关外。特别咄咄逼人的是东邻魏国,新近派大将龙贾沿洛水修筑了一道长城,从郑向北,不仅将原曾属秦的河西、上郡等广大地区圈了过去,而且还以高墙为隔,这不是想要永远把秦国封闭在关中一隅吗?耻辱啊耻辱,诸侯如此鄙视我秦国,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耻辱呢?
大典礼毕后,孝公立即召群臣商议,拟定并实施广布恩惠、救助孤寡、招抚战士、明定立功受奖等措施,并在国中发布了一道载之于《史记·秦本纪》的著名的《求贤令》——
昔我缪(通“穆”)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通“狄”),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奏,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如同上章二节中《五张羊皮买到一个贤佐》说的那样,秦穆公在用人制度上开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这个优良传统被忽视近三百年后,现在又由秦孝公的这道《求贤令》获得了继承和发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求贤令》提出的求贤范围不限于“群臣”,还有“宾客”,即向诸侯各国智能之士敞开了欢迎的大门。秦国由此建立的“客卿”制度,不仅开辟了丰富的人才资源,还可藉以强我弱敌,无论对近期的与列强争雄,还是为未来兼并六国、创建大一统的秦帝国,都是一个极重要的条件。
但一项全新的改革,其开创性的重要意义,开头并不一定很快为人们所认识。《求贤令》发布数月,还未见有大贤大材来应求,孝公不免内心郁郁。这一日他正在栎阳宫饮酒,偶见窗外鸿雁飞过,不由举首追视,喟然长叹。侍候在一旁的寺人景监说:君上因何目视飞鸿而叹?
孝公说:往昔齐桓公曾经说过:吾得仲父管仲,犹飞鸿之有羽翼也。可寡人至今空有冲天之志而尚无羽翼之助,怎不叫人兴叹呢?
景监说:臣舍下有一客卿,不知君上是否愿意一见?
孝公说:当然愿意,卿快去为寡人引来!
景监说:但此人是新近从敌国魏国来的,而且正是魏王弃之不用的,可以吗?
孝公说:敌弃之,我用之,不是更好吗?快快召来吧,寡人在此立等!
客人被引进来了,孝公问他治国之道,客入列举上古伏羲、神农、唐尧、虞舜的事例作答,还没有说完,孝公已听得呼呼大睡。事后孝公对景监说:你那客人是个无知妄人,说的话迂腐陈旧,毫无用处。这样的人你推荐来做什么?
过了五天,景监又去对孝公说:臣下客人说他话还没有讲完,请君上允许他再来拜见一次。
孝公仍然问他治国之道,这一回客人详细陈述了夏禹分划土地、规定赋税,以及商汤、文武顺天应人的事迹。事后孝公对景监说:你那客人博闻强记,知道的老古董倒真还不少,但古今事异,对现实有什么用处呢?
于是景监便去对那个客人说:足下对君上说话,应当投其所好。您怎么可以老是拿那些老祖宗的传说和陈年账簿去亵渎君上的清听呢?
客人说:我正试着呢!第一次我讲帝道,他根本不想听;第二次我讲王道,他也不大想听。请允许我再见一次,这一次我将以霸道之术进说君上,君上肯定喜欢听!
这个将以霸道之术游说秦孝公的客人,便是商鞅。
商鞅原是卫国人,是卫君的庶孽公子,因称卫鞅或公孙鞅;入秦后受到孝公重用,被封为商君,历史上习惯称他商鞅。
商鞅觉得自己的故国太微弱,不足以施展他的才学,于是便西游至魏,一时又难以晋见魏惠王,只好暂时栖身于丞相公孙痤门下,做了个相府属官中庶子。公孙痤偶而与他商议一些事,他提出的谋略屡屡得中,这便引起了公孙痤注意,准备伺机引荐给惠王,委以重任。公孙痤还没有来得及这样做,不料一场重病,竟至奄奄一息。这一天,惠王来看望公孙痤,见他病成这样,便问道:万一相国有个意外,寡人将托付谁来治理这个国家呢?
公孙痤这时便乘机说:起用中庶子卫鞅吧。鞅虽年少,却是当世奇才,胜过臣十倍。
惠王不以为然,以沉默为答。
公孙痤又说:大王如果不用鞅,那就一定要杀了他。不然让别国用了,那就会反过来成为魏国大害。
惠王漫应一声说:好吧。
离开相府,惠王登上车乘不由叹息起来:唉唉,这个公孙痤呀,怎么病到如此地步了呢?他竟然糊涂到让我把国家去托付给卫鞅,又说如果不用就要杀了他。把一个中庶子看得如此重要,那不是白日说梦话吗?
公孙痤却因对惠王提了不用卫鞅就不如杀之的建议而心有不忍起来。怎么说,也不应在自己临死前再做一桩如此不人道的事吧?就把商鞅召到病床前来,把适才自己与惠王的对话全告诉了他,又说:王上已经答应我要杀你了,你还是赶快逃走吧!
商鞅笑笑说:王上既不能听相国之言用臣,又怎么能依相国之言杀臣呢?
后来商鞅照旧留在相府,果然平安无事。
这回秦国发布了《求贤令》,商鞅闻讯即肩背行囊,渡黄河、入函谷,来到秦都栎阳,并通过寺人景监而得以晋见孝公。
商鞅初见孝公,首次说以帝道,再次说以王道,似乎他口袋里什么都有,任凭买主挑选。这是因为,他曾经向对当时各派理论都深有研究的鲁国人(一说晋人)尸佼学习过,而商鞅真正的学问还是在法家方面,也就是他自己说的“霸道之术”。《史记》本传说他“少好刑名之学”。所谓刑名之学,就是还处于萌芽状态的帝王集权制度提供理论依据和实际措施的法家学说。更为难得的是,商鞅曾在经法家初期代表李悝的治理而强盛一时的魏国作过长期游历,使他有机会实际接触了许多当时最先进的改革经验。后来的实践也证明,商鞅不仅是出色的理论家,更是一位卓有成效的实干家,在法家群星中放射着特别耀眼的光辉。后起的秦国能一跃而成为改革最彻底、成效最显著的佼佼者,这位为人“刻薄”、“少恩”,“卒受恶名于秦”(《史记·商君列传》赞语)的商鞅,应当公平地给他记上首功。
一次关系到国运的大辩论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商鞅是怎样以霸道之术进说孝公的。
孝公一听说商鞅还有霸道之术,即命景监传见,颇有些急不可待地说:先生既有霸道之术,何不早早赐教呢?
商鞅说:臣不是不想说,只是怕有违君上圣意。因为霸道与帝王之道不一样。帝王之道是出乎民意,顺于人情的;而行霸道可能就要违逆人情民意。
孝公勃然变容,按剑横目说:怎么能违逆民意人情呢?
商鞅故作一顿说:事理就是如此,臣只是照实说出罢了!
孝公说:既如此,请道其详。
商鞅指指几上的一张琴又说:琴瑟若是音律不调,就非得改弦更张不可。国家也如此,发展到一定阶段,就非得做些大的调整不可。可一般的臣民只图眼前安逸,长远的计虑他们不愿想也没有这个能力去想,古语说的“民可与乐成,不可与虑始”,就是这个道理。当初管仲相齐的时候,把国家划分为二十五个乡,规定四民各守其业,把旧制度全改过来了。开始民众感到不便,纷纷反对。后来新制度很快显出了成效,齐国九会诸侯,一匡天下,国君享受到了荣誉,民众得到了实利,到这时候人们才看到管仲实在是真正为国家、民众着想的啊!
孝公说:先生若果有管仲致霸之术,寡人自然要委以国政听从先生的了。但不知其术何在?
商鞅说:国家不富,何以兴兵;兵力不强,何以胜敌!要想国富,最重要的是要大力农耕;要想兵强,最重要的就是鼓励参战。如何做这两点?就是要重赏和重罚。重赏,民众就会知该做什么;重罚,民众就会知道不该做什么。赏与罚都要言之有信,政令一经宣布,必须坚决执行。果真这样做了,国家肯定会富强起来!
孝公说:好啊,这些办法能做到!
商鞅说:办法虽好,没有称职的执行人还是不行;有了称职的执行人,任用不专一仍然不行;任用专一了,别人一出来说三道四就犹疑同样不行!
孝公说:唔,有理,请再说下去!
商鞅却请求告退。
孝公说:寡人正要听听先生的全部霸术,怎么就要告退了呢?
商鞅说:臣请君上细细思量三日,决定可还是不可,然后臣才敢全部说出来。
商鞅从栎阳宫告退出来,景监见到他责怪说:君上一再称赞你说得好,你不趁此机会好好说一说,反倒要君上仔细想三日再说,这不是存心要挟君上吗?
商鞅说:我是担心君上决心没有下定,中途变卦呀!
但只过了一天,孝公就派使者来请,商鞅却以三日约期未到而谢绝了使者。景监劝他还是应该去。商鞅说:如果我第一次与君上相约就失信,将来还如何取信于君呢?
到了第三天,孝公特地派了车子来请。相见后,孝公赐坐,诚意请教。听着、听着,孝公的膝头不知不觉地一点点往席前挪动,两人越靠越近。商鞅一连说了三天三夜,孝公始终兴致勃勃,毫无倦色。
孝公已有意任用商鞅了,但为了尽可能获得大臣们的支持,决定先在朝堂上进行一次辩论。
秦孝公三年(公元前359年),这场关系到秦国命运的大辩论就在栎阳宫进行,《史记》本传及《商君书·更法》、《新序·善谋》对此均有详录。读时给人一个突出的印象是,作为新旧两种势力代表的辩论双方,确实做到了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在辩论中,秦孝公也表现出颇有从善如流的气度。
辩论开始前,孝公作了简短的致辞,说明强秦必须变法,只是还顾忌到一点:怕因变法而引起“天下议已”。据此,商鞅针锋相对地指出:“疑行无名,疑事无成”:要成功一件大事,不能因为害怕别人议论或反对就犹豫不决。接着又作了阐释和引申。他说:一项具有远见卓识的举措会引起一般世俗愚见的议论或反对,原本属于常见现象,决不能成为不实现这项举措的依据。所以,有至高道德的人,不会去随和世俗偏见;成就大功业的人,不会去同凡夫俗子谋议。一个英明的君主,他的行动准则必须是:只要能使国家富强,就不必再去效法旧的典章制度;只要能够使民众获利,也就没有必要再去遵循周礼的那些规定!
孝公听了不由脱口赞道:说得对啊!
大夫甘龙却紧接一句:说得不对!进而反驳说:贤明的君主不会违逆民俗去施行教化;明智的臣子不会变更法规来治理国家。顺乎民俗施行教化,不费力气就可成功;沿袭成法治理国家,官吏驾轻就熟,做百姓的也愿意服从。
话音刚落,商鞅就直截了当指出:甘龙的话是典型的世俗偏见!接着他说:寻常之人习惯于旧习俗,一般学者又沉溺于自己狭隘的知识范围。这两种人叫他们做个奉公守法的官吏倒是可以的,但却不能同他们讨论关系到国家长远利益的大事。夏、商、周三代礼制不同都成就了王业,春秋五霸法度各异也都建立了霸业。智者制定法度,愚者被法度所制;贤者变更礼制,不肖者受拘于礼制——这历来就是智愚贤不肖的区别!
这场唇枪舌剑的辩论持续了相当长时间,商鞅据理力争,气势逼人,明显占着上风。这时又一位大臣杜挚从未来改革的结果提出反对意见,有点以守为攻味道。他说:没有百倍的利益,不能改变法度;没有十倍的功用,不能更换器物。总而言之一句话:遵照周礼符合正宗,效法古制不会有错!
商鞅针锋相对紧接着说:恐怕不见得吧?夏桀、商纣遵循旧礼就亡了国,商汤、周武不依古制却反而获得了天下。所以我也是总而言之一句话:治理天下并非只有一种办法,只要有利国家就该不依古制!
静静听着的孝公,这时果断地做出了结论:鞅之言善,着拟《变法令》!
当即拜商鞅为左庶长,掌军政大权,相当于中原诸国的正卿或国相。并谕告朝堂群臣:今后国政,悉听左庶长施行。有违抗者,与违抗寡人同!
一场伤筋动骨的大改革
秦国的变法运动持续时间长达十余年,主要法令均由商鞅草拟,先后分几次公布,其改革的范围和深度远远超过山东诸国,许多带有根本性的改革内容,可谓伤筋动骨,目的是要使已经显得老朽的秦国再度获得青春。本书依据预定的写作构想,侧重点在人际纠葛和人的命运及人生况味,有关经济、政治一类典章制度则从简。因而尽管商鞅变法在秦国历史上具有转折性的重大意义,有关变法内容也只能极简略地作一点介绍。
【奖励农耕,提倡首富】变法之初,先发布了一项《垦草令》,鼓励人们垦荒开地,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带有根本性的改革措施。如规定按田亩和粮谷收入征税,即实行带有地主土地所有制性质的租税制,这等于废除了奴隶制经济制度。整顿吏治,禁绝官吏的胡作非为、拖延渎职;强调全国政治制度的严正和统一,提高工作效能。为了“重农”,对富族大户,规定不准豢养游手好闲的人,对商人和商业活动作出了种种限制;对一般居民,禁止自由迁徙与旅行;对农业劳动者,则用限制受教育的方法,使其愚昧无知,从而安心于故土故居,尽力农耕终身。随着改革的深入,后来又公布了一些法令,规定凡由耕田或纺织而生产粟帛超过一定数量的人,可免自身徭役;凡因经营商业或因怠惰而贫困者,要连同其妻子儿女一起没入官府为奴。此项所谓“重本(指农)抑末(指商)”政策,以后便成为秦国历代相沿的国策。从一般经济发展规律来看,“重本抑末”未免带有很大的片面性,但在秦国却自有其一定的实际原因。这里地广人稀,又多荒山荒原,农业,尤其粮食生产落后于中原诸国,而城市商业活动则相对地较为繁荣。此项政策的实施,可以使更多劳动力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去,迅速改变农业落后面貌。同时因有“致帛粟多者,复其身(免除徭赋)”等规定,势必导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这种贫富不均现象不仅不为新法所禁,而且正是它要提倡的。因为出现首富,正可以形成越来越多的新兴地主,符合地主占有制经济的发展要求。
【奖励军功,严禁私斗】推行以军功授官爵的新制度,取代原来贵族阶层可以无功受禄的旧传统。爵分二十等级。具体做法是:凡在战争中杀得敌方甲士一人并取得其首级者,赐爵一级,赐田一顷,宅九亩。斩得敌一甲首者,还可役使一人为自己奴仆;得到五个甲首,即可役使五家为自己农奴,等等。
在奖励军功的同时,严禁私斗,特别是“邑斗”。邑指小城邑,在奴隶制时代为大小奴隶主们所占据,他们为相互争夺土地、财产不断进行争斗。这些争斗,当初在许多情况下曾是新兴地主阶级借以萌发成长的温床,但在地主阶级掌握了政权、新的经济、政治制度业已确立后,它就转而成为破坏性因素。新法严禁私斗,违者将被处以重刑,目的在于消除奴隶主势力反抗,巩固和加强国王集权制。
【推行法冶,轻罪重罚】据说商鞅是带着李悝的《法经》来到秦国的,将《法经》的思想和刑律贯彻于秦国的法令中。这些法令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新兴地主阶级利益,其基本原则是“轻罪重刑”。商鞅认为只有对轻罪处以极重的刑罚,才能迫使人们不敢犯罪,即所谓“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
不仅如此,新法还实行了“连坐法”。
秦在献公时期就曾进行过户籍编制,商鞅变法时重新作了更为严密的编制,规定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并与推行严刑峻法挂起钩来,即实行所谓“伍、什连坐法”:一家有人犯罪,四家都要同坐。在平时,五家之间要相互监视,发现有“奸人”应向官府告发,告奸者可以得到同在前线斩得敌人首级一样的奖励;而若匿藏奸人,则要受到与投降敌人同样的处罚。
秦孝公十年(公元前352年),即进行初步改革后的第七年,新法已收到显著成效,孝公升商鞅为大良造,命其进一步草拟法令,推进变法。两年后,一场全面的、深刻的变法运动在关中大地上兴起。其内容,概而言之,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开阡陌、平封疆。阡陌指田亩中间或四周的小路,实行井田制时为公、私田之间的界线。封疆指奴隶主贵族各个封邑间的相隔离地带,作为各自占有范围的标志。开掘阡陌,平毁封疆,不仅可以扩大耕地面积,也是最后从地表上消除奴隶制痕迹的一项措施。
(二)普遍建立县制。早在春秋时期,秦、晋、楚等国就开始零星地设立过一些县的建制。进入战国后,秦国主要在东部地区继续设立了一些新县。在变法运动的促进下,这时秦国已将全国划分为四十一个县(一说三十七个),县以下有乡、里、聚(村)等组织,建立起一套直属于王国的地方政权机构,取代了原来奴隶主封邑林立的割据状态。
(三)实行“口赋”,即实行不是按户、而是按每户人口数定赋的“人丁税”制。规定一家有两个以上男劳力而不分炊异居者,赋税就要加倍。这是从经济上对宗族共居大家庭的一种制约,迫使男性成年人独自去建立小家庭,自食其力。目的也是为了促进农业生产,并扩充劳役与兵役的来源。
(四)统一赋税制度。以前奴隶主贵族征税畸轻畸重,十分混乱;开阡陌、平封疆后又出现了大量个体农户,需要对赋税进行整顿和统一。变法后赋税分军赋与田租两种。军赋按户起征,以供军需之用;田租则按各户受田多寡,每年向国家缴纳定量实物,包括粮食、饲草,及禾秆等。
(五)统一度量衡进位制和颁发标准的度量衡器具。如规定一步为六尺,二百四十方步为一亩等。保存至今的青铜器物中,我们还可见到“商鞅方升”等原物。
(六)革除陋习,树立新风。秦人长期与戎、狄各族杂处,保持着父子兄弟同室而居的原始社会偶婚遗风。这种旧风俗既不利于后代健康成长,也有碍社会正常秩序的建立。新法禁止此等陋习,并竭力提倡“乐战轻生”的新风气,以获得军功为门第的最大光荣。经过长时间的实行对比鲜明的奖惩措施和强大的舆论造势以后,在秦国可以做到“民闻战而相贺也”的地步,甚至“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商君书·赏刑》),可谓尚武思想已深入到日常生活。
就在大规模推进变法运动的当年(公元前350年),秦国进行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迁都:从栎阳迁至咸阳。秦的几次迁都,均贯串着一个“东进”的意图,和为未来称王天下的宏大构想。咸阳今址在陕西咸阳东北二十里,位于九山之南,渭水之北,古时山南水北皆称为阳,因称“咸阳”。其地恰好据于秦岭怀抱,三面而守,既可浮渭而直入黄河,又可由终南与渭水之间的大道进入函谷。咸阳秦宫的格局是商鞅采集中原诸国宫殿的式样建造的,美轮美奂,恢宏壮丽。以后,它就成了大秦帝国的国都。
左手举赏金,右手执屠刀
商鞅在变法之初,为了使民众相信官府言既出、信必从,采取了一个当时被看作是极为奇特的做法,不过我们现代人倒是早已司空见惯了的,那就是广告术。
堂堂的国之法典竟要靠广告术来推销,历代论者对商鞅的这一做法颇多贬词。但宋代的王安石却写了一首《咏商鞅》赞道:
自古驱民在信诚,
一言为重百金轻。
今人未可非商鞅,
商鞅能令政必行。
应当说,这广告还是做得相当高明的。在首批新法草拟就绪即将公布之前,商鞅命人在国都南门外立一根三丈之木,派官吏守着,对过往行人说:左庶长有令:有谁能将此木徙至北门,立刻赏以十金。一时观者如潮,议论纷纷,但因莫测其意,疑惧兼有,还没有一个人敢于去搬动这根大木的。商鞅看了很高兴,又下了一道命令,把赏金加到五十金。这时远近闻讯赶来的人越聚越多,而疑惧也更大。这时偏有一人站出来说道:得不到赏金,总不至于遭罚吧?赏不到五十金,多少有点碎银花花也好!说罢,就把三丈之木一口气搬到了北门。商鞅当即亲自颁赏五十金,并且夸奖他说:你是一个好臣民,能够听从我左庶长的命令!
这个广告术,在商鞅之前就有一个人做过的,那就是吴起。稍有不同的是,商鞅是“移木赏金”,吴起同则是“偾(fèn)木赐爵”。吴起治西河时为了取信于民,就在南门外竖了一根木柱,宣布若有人能扳倒它就让他做长大夫,有个人这样做了,就真的让他做了官。不知商鞅是否从中受了启发,总之他获得了很大成功。这件奇事一时传为轰动国都的大新闻,几乎妇孺皆知,都说左庶长言必信、令必行,不可等闲视之。
商鞅用五十金买到了预期中的信誉后,立即公布了他的第一批新法。每项新法中,都有这样一条:政令既出,不问贵贱,一体遵行;有不遵行者,戮之以徇!人们既已深信左庶长是“言必信,令必行”的,有谁还敢说个不字呢?
但由于每项新法内容都有一些出人意料的大改革,与人们已经习惯了的思想认识和生活方式大异,一时怎么也无法适应。特别是宗室贵族和在旧制度下获利较多的人,改革触及到了他们的根本利益以至生存权,引起激烈反对。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单是在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这数以千计的反对者如果都是平民百姓,对付起来也许并不太难,可偏偏其中有一人竟是太子,也就是秦孝公的儿子驷,也即后来即位的惠文王!
这不仅是对新法的严重考验,更是对商鞅,特别是对秦孝公的一次公开挑战。
商鞅毫不示弱,他甚至暂且按下那数以千计的普通者,决心首先要绳之以法的恰恰就是这个太子。他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欲法之行,必自上刑之!
孝公面临到了两难选择:要太子,还是要新法?或者说是要亲子之情,还是要理想中的功业?
二者只许择一,中间没有妥协余地。
孝公在授权商鞅变法时,曾在朝堂上当着全体大臣的面说过:今后国政悉听左庶长施行,有违抗者与违抗寡人同。
现在,他能收回这个话吗?他能违抗这个话吗?他收回,他违抗,便是一个孝公收回、违抗另一个孝公,其结果就会是取消了孝公!
孝公作出了一个历史性抉择:寡人再说一遍:今后国政,悉听左庶长施行。有违抗者,与违抗寡人同!
商鞅于是宣布:论太子以罪,这一点不变。考虑到太子毕竟为国君之嗣,不可以直接施刑;且太子年幼无知,多系他人教唆所致。因而决定惩罚太子的两个师傅:太师公孙贾,处以黥刑:用刀刻刺额面,再涂之以墨;太傅公子虔原处鞭刑,后因再次非议新法而处以劓(yì)刑:割去鼻子。
解决了这桩棘手的太子案,商鞅声震朝野,接着便大开杀戒,用极其残酷的手段来镇压新法的反对者。甚至当新法初见成效时,有人改变原先认为新法不便的看法,对新法说了几句好话,也被商鞅指斥为“乱化之民”而强迫迁徙去了边城。因为在商鞅看来,他立法,别人只有执行的义务,绝无任何说三道四包括顺着说赞扬话的权利。《史记集解》引了刘向《新序》一则材料说:商鞅“内刻刀锯之刑,外深铁钺之诛”,对触犯新法的人动辄处以酷刑,其中有一天竟在渭河之畔杀了七百余人,致使“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可能不无夸张,但其惨酷之状确实令人怵目惊心。
但新法的成效也十分显著。《史记·商君列传》称:“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通“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宋代司马光盛赞秦孝公用商鞅变法的成功,认为其可贵之处在于一个“信”字——
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反之:欺其邻国,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所利不能药其所伤,所获不能补其所亡,岂不哀哉!(《资治通鉴·周纪二》)
变法的巨大成就,表现了商鞅在经国治民方面的非凡才能和那种令人望之生畏的凛冽威势。但商鞅的才华还不止此。他也有心要炫示一下自己多方面的光彩。此时他已升任为大良造,成了秦国三军统师。接下去我们将看到,商鞅在驰骋疆场和折冲尊俎方面,同样表现出过人的胆识、出众的智慧,还有那种使人不寒而栗的无情、狡诈和残忍。 人生必读经典历史丛书:时代帝国三部曲之大秦帝国(上 下)(套装共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