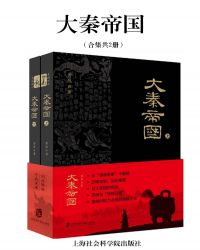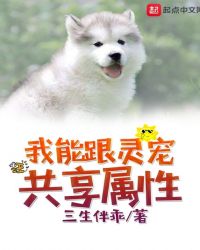力挽四世之衰的风雨归来人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人生必读经典历史丛书:时代帝国三部曲之大秦帝国(上 下)(套装共2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力挽四世之衰的风雨归来人
秦家小子忽而进入了龙钟老态
历史的长河从来不是止水,而属于秦国的这条历史支流,又显得特别曲折汹涌,忽而激起拍天巨浪,忽而又坠落深谷,似乎有意考验着秦人的意志和毅力,看他们能否首先战胜自己然后战胜环境,进而成为顽强的胜利者。
当战国时代的帷幕揭开时,秦国又落后了。在那样一个争战激烈的时代里,落后就意味着挨打甚至灭亡。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秦国不得不在内外交困的低谷中挣扎着。
战国时代是风云激变的时代。新兴的地主阶级日趋得势,而没落的奴隶主阶级愈益凋零。铁制的、远比铜制的更有效率的生产工具和更具杀伤力的武器,大规模地投之于实际应用。生活的节奏加快了,社会发展的步子加大了,任何固步自封、安逸自得的幻梦都将被无情的现实狠狠击碎。
战国时代又是大改革的时代。由分晋而立的魏、赵、韩三国首倡其声,迅速建立起能基本适应于新兴生产关系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即在经济上,开裂“阡陌封疆”,出现了土地私有制;在政治上,废除领主贵族的世卿世禄,改行官僚制度。三国很快国富兵强,令人刮目。接踵而起的是齐、郑、宋,经过改革,也都成效卓著。改革则存,不改革则亡,逐渐成为社会共识。
战国时代已是一个接近收获的时代。历经数百年的争战,产生出一大批高智商的先知先驱,他们深切地观察、体悟现实,有的已若隐若现地望到了明天,纷纷著书立说,创立各自学派,为当今国君提供各种如何治理目前和开辟未来的方案。最先出现的是春秋末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和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进入战国时期,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兵家等等相继兴起,形成了一派百家争鸣的壮丽景象。
很可惜,局促于关中的秦国却仿佛置身于这滚滚的时代洪流之外,颇有点向隅而泣的悲凉感。
秦国的再次落后是有原因的。
从主观上说,战国初期的几代国君,自厉共公、躁公、怀公、灵公、简公、惠公到出子,都较为平庸。后来秦孝公在《求贤令》中提到,特别是其中厉、躁、简、出四世,弄得国家内外交困,致使“诸侯卑秦,丑莫大焉”。
从客观上说,秦国毕竟是后起之国。它是在中原诸国奴隶翻度已进入停滞、衰落状态下建立起奴隶制国家来的。基于本身的历史、地理原因,也鉴于山东诸国已经暴露出来的矛盾,秦国的奴隶制采取了独特的经济结构和政权形式。它不实行分封制,土地占有权集中于王室,政权形式则采取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军事专制。当年,秦正是依仗自身的这些特点显示出来的优越性,战胜了原来要比它强大得多的“老大哥”。如今,同是这些特点,却成了它继续向前发展的羁绊。很显然,原先实行分封的中原诸国,国内因有卿、大夫封地和采邑而形成大小割据的状态,一旦奴隶制进入危机阶段,就比较容易分化瓦解,也就是说新兴的经济、政治体制比较容易生存、发展并脱颖而出。而秦国的新兴势力却在“集权制”的樊笼中东碰西撞,生长极其艰难。此种时间空间的错位,便造成这样一种历史景观:当年,秦国犹如虎虎有生气的后生青年去与那些垂暮老人较量,着实风光了一阵子;曾几何时,那些垂暮老人经过一番脱胎换骨的改造,一个个或先或后返老还童,而当年那个关西秦家小子,如今若是临镜一照,就会忽然发现自己已是头童齿豁,一声“无可奈何花落去”的长叹,进入了龙钟老态。
可悲的是秦国上层集团内部那些守旧势力囿于狭隘的自身利益,不肯“临镜一照”,不承认自己已进入老年,不愿意也来一番脱胎换骨。
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当中原诸国气势磅礴的改革大潮掀起时,一些旧的奴隶主贵族慑于新兴的地主阶级的威势,纷纷逃往秦国。如韩、赵、魏三家将晋国的旧贵族智伯消灭后,智伯之族智开便“率邑人”匆匆逃往秦国。昔日被中原权贵们讥之为“化外之地”的秦国,如今却成了他们的避难所和安乐乡!
在这种情况下,秦国的被动挨打当然是不可避免的了。以下便是随手从史书中摘出的记录,而且还仅限于与东邻魏国一国的战事:秦灵公六年(公元前419年)魏入侵秦,在少梁筑城,秦反击无效,魏“复城少梁”。秦简公三年(公元前412年),魏再次攻秦,在秦东部边防重镇临晋以及元里筑城。过了不到一年,魏第三次来攻,深入到洛阴、郃阳等地筑城……
不仅是外寇,还有内乱。传说中的“盗跖”,可能就是这一时期秦地奴隶起义的一个著名领袖。有关跖的情况,诸书记载、解释不一,大致可以推定他生活在战国初期。至于他的活动区域,陈鼓应先生注《庄子》引了李奇注《汉书》的一条材科,认为:“跖,秦之大盗也。”古书中所说的“大盗”,大多指奴隶或农民起义中有影响的人物。“盗跖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所过之邑,大国守城,小国入保,万民苦之”。这虽是《庄子·盗跖》篇中带有夸张性的描述,但也不至于毫无所据。
与外寇内乱互为因果的,则是秦国上层统治集团的内讧。造成内讧的根本原因,与宪公、武公、德公时期那次内讧一样,是君权的旁落和庶长的专权。
公元前428年(秦怀公元年),秦躁公死。此时秦国的大权又落到了以庶长为代表的守旧势力手中。守旧派的贵族们立躁公之弟怀公为君。但不到三年,大庶长灶和其他一些贵族又一起逼死怀公,再立怀公之孙灵公为君。这时候出现了一个尽管尚是少年,却思想激进、主张改革的人物,便是灵公之子公子连(又名师隰)。公子连被立为太子后,广交新兴势力,很快得到拥护并成为他们的代表。灵公在位十年后就去世了,按正常程序继位的应为太子连。但就在这时,控制政权的守旧势力经过周密策划,硬是阻止了太子连的即位,却从遥远的晋国接回灵公的叔父悼子,于公元前414年立为国君,是为秦简公。在这种情况下,公子连不得不离开故土,东渡黄河,流亡国外。
简公在位十五年,秦国仍滑行在下坡路上。简公死,继位的是他的儿子惠公。惠公曾经立誓振兴,在击退东邻侵犯、稳定西南局势方面也获得了一些成效,无奈沉疴已久,一时难以回天。而他自己,却在居位十三年后,不幸因病猝然壮年离世。
惠公一死,大庶长和守旧的贵族势力为了便于控制,特意从惠公的儿子中选了个年方四岁的出子来继位。出子是被后来称为小主夫人的母亲惠后抱着登上国君大位的。当隆重的即位典礼开始时,在母亲怀中的出子哭了。他哭是由于受了惊吓:弄不懂周围那些大钟大鼓为什么突然一下都响了起来!
这时候在离雍城数百里的黄河西岸,另有一个年近五十岁的人,也在为这个不吉利的继位典礼而哭。他望着滚滚西去的渭水,想象着渭水北岸雍城蕲年宫里正进行着的那一幕;他为自己而哭,也为故国而哭。
这个哭着的中年人,便是已经在国外流亡了二十余年的公子连。
袭关:一次新旧势力的较量
公子连为故国而哭,首先是由脚下这片河西之地引起的。
他站在风陵渡口,触目皆是新兴的魏国权力的标志:管理渡口的是魏国官吏,近旁左侧是魏国烽火台,右侧则是魏国领土标柱。他还知道,只要渡过黄河,东行数十里,那里便是魏国国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部)。各国使节穿梭往来,四海名流富家云集,呈现一派强盛兴隆景象。
不错,这里的一切如今都已被打上了魏国的标志。但作为嬴氏宗室的一个公子,他怎么能够忘记,这河西之地原本是秦国的领土呢!秦国的列祖列宗为了获得这片土地,曾经花去了多少心血!穆公以大半生精力“三置晋君”,首得河西八城。以后又经历世君主的连续努力,到厉共公时代,已只剩下大荔戎国还没有被收服。厉共公十六年(公元前461年),秦以修筑河堤为名,派出两万大军向大荔迫近,随即来了个出其不意的突然袭击,攻陷了大荔国王城。至此,历经近两百年的苦心经营,这片富饶的河西之地才终于全部为秦所有。
得之如滴水,失之若落潮。正是在公子连流亡期间,从简公二年到七年(公元前413年~前408年)这短短四五年时间里,河西之地就几乎全部易为魏主。
瓜分晋国三家之一的魏国所以能以如此显赫的声势迅速崛起,就在于魏文侯先后信用李悝、吴起等重臣,对经济、政治以至军事制度作了重大的改革。李悝为魏国提出了不少有利于新的土地制度发展的措施,实行“尽地力之教”,使魏国迅速富强起来。李悝的《法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法典,不仅对魏国,对以后中国法制的建立都有深刻影响。吴起原是卫国人,因有杀妻求将、母殁丧不临两项劣行,在齐、鲁等国都受到冷遇。吴起来投魏国,魏文侯明知他有劣迹还是任以为将。吴起首先在魏国推行征兵制,精心训练了一支战斗力极强的称之为“武卒”的特殊部队。在受命带兵击秦时,他对秦军的特性作了深刻的剖析。他认为:“秦性强,其地险,其政严,其赏罚信,其人不让,皆有斗心,故散而战。”据此,他提出的对策是:“击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士贪于得而离其将,乘乖猎散,设伏投机,其将可取。”以后的事实证明,吴起的这些策略屡屡获得成功。不仅如此,在战斗中,身为大将的吴起,还能与士卒一起冒死奋战,生活上与他们同甘共苦,甚至还为负创的士卒吮吸脓血,因而士卒们都不惜生命愿为主将死战。在这种情况下,秦军与魏军一接锋,就失去了往日威风,屡战屡败。秦简公六年和七年(公元前409、408年),吴起两次率兵攻秦,临晋、元里、洛阴、郃阳等河西城邑,尽落魏人之手。接着,魏国堂而皇之地在这里设立河西郡,并大兴土木建筑郡城,吴起被任命为首任河西郡郡守。此后,这个新建的河西郡,对于秦国,不啻是插入胸侧的一把利剑;对于魏国,则是一个可靠的前哨阵地。机智峻刻的吴起,正是凭借这个阵地,“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余则钧解,辟土四面,拓地千里”(《吴子·图国》)。
公子连有二十余年的流亡经历。他亲眼看到古老的中原诸国所以能复兴,皆得益于改革。而河西之地得而复失的惨痛教训,更时时击撞着他的心:如果能回国主政,决不能让秦国再置身于时代洪流之外,非坚决实行改革不可!
他急切地等待着可以回国的时机。
四岁的出子当然谈不上当政,因而君权落在他母亲即小主夫人之手。据《吕氏春秋·当赏》记载,小主夫人是“用奄变”,即依靠宦官之类内侍官的机变获得这个权力的。小主夫人与扶植出子上台的大庶长、旧贵族是否有过斗争,缺少文献可凭,但他们都是旧势力的代表,想来就不难暂时结为统一战线,支撑这个拒绝任何改革的奇特的政权。结果是:“群贤不说(通“悦”)自匿,百姓郁怨非上。”(同上)这个腐朽的政权,已经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
出子做了两年挂名国君后,即公元前385年,公子连决定采取行动了!
经过一番筹划,并通过秘密渠道与一位支持改革的庶长取得联系后,公子连选择了一个风雨之夜,轻车简从,越过已为魏地的河西边界,准备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回国夺取君位。
对这次入国争位的记载,仅见于《吕氏春秋·当赏》。其中牵涉到两个古地名,即“郑所之塞”和“焉氏塞”的所在地,各家注释不一。有的竟说远在甘肃平凉境内,与秦都雍城相距数千里之遥,除非公子连忽然变成了孙悟空,不然就断难有回国指望了。为此,我特地登门去请教了从青春年少直到满头银丝一直孜孜于《吕氏春秋》研究并乐此不疲的陈奇猷老先生。陈老如数家珍地当场向我说出了一连串古籍记载,据此推定“郑所之塞”在今陕西渭水南岸华县附近,“焉氏塞”则在渭水之北今富平县关山一带。据此,老先生向我描述了两千三百多年前这场曲折惊险的入国争位袭击战,我听着也不禁要为公子连捏把汗!
大雨瓢泼。三辆战车,数匹快马,越过渭河平原,踅入少华山北麓,沿山路疾行。站立在头一辆战车上的公子连已被雨水和泥浆溅得满身湿透却犹是大汗不止,一个劲地催促着快、快、快!他是有意选择风雨之夜入国的,却不曾料到竟会如此地风狂雨骤,刚才因被山洪所阻已经耽误了半个多时辰,如果不在酉时三刻前赶到郑所要塞,那就意味着此举很可能失败。根据事先得到的情报,酉时三刻前要塞守令为封哙,是支持公子连的。过此时间后将换成另一人,事情就变得吉凶难测。
山路经过几回盘旋,进入一道两旁崖壁陡峭的峡谷后,突然感到四周已被暮色裹住,一行人速度也被迫慢了下来。公子连迅即从车上跳出跨上骏马,加鞭冒雨飞奔,几个随从也跃马跟上,终于赶在酉时初刻来到要塞。公子连在随从的协助下,换上礼服,保持适度的庄重,命侍从去叩关。没有想到出来迎接的要塞守令不是年轻的封哙,而是年老又特别勤于职守的右主然,他是因为看到大雨,唯恐有闪失,提前来接班的。
右主然很快认出了公子连,郑重施礼道:公子一向可好?
公子连赶紧还礼说:连亡命山东多年,赖祖宗荫庇,少有长进。此次回国,不期而得与伯父在此相见,实为连之大幸。说时又深深一拜。
右主然答拜后却说道:老臣为秦国尽职有年,一向信守为臣大义,不能同时忠于二主,还望鉴谅;公子,请多多自勉吧!说罢,趋而旋走,退入要塞,并命令守卒关门。
这时候,三辆战车数十名士卒也已赶到,群情激愤,都要求作孤注一掷式的冲击。但公子连想到,那样即使侥幸入关,也早已引起雍城方面的警觉,就失去了袭取的可能。于是断然做出决定,拨转马头,南渡渭水,绕道桥山山脉,经由长达数十里的古驿道,赶在天亮前到达入秦的另一个要塞——焉氏塞。根据情报,这个夜晚焉氏塞的守令为菌改,比较倾向新兴势力,或有可能接纳入国。如果到那里后也遭到拒绝,那就只好强行入关,与之决一死战了!
整整一夜的冒雨奔波,居然一切如事前所设想的那样,焉氏塞守令菌改,将公子连一行人全都接入要塞,并立即派人去雍城与那位庶长联系,求得内应,以便入国争位。
不料焉氏塞另一个忠于小主夫人的守令却抢先暗自向雍城方面发去了警报。小主夫人得报,立即命庶长发兵火速赶往焉氏塞去堵截。出发时下给士兵的命令是:外寇入侵边境,命令你们去消灭他们!从雍城到焉氏塞有近百里路,但走着走着,那位庶长却趁机做了手脚,命令变成为:不是去打击外寇,是去迎立新君啊!士兵们全都响应,欢声雷动。
庶长与菌改一起,率领着大批士卒,拥着公子连,浩浩荡荡地进了雍城,把大郑宫团团围住。小主夫人被迫自杀,才满五岁的出子也被乱军杀死。他们的尸体被抛进了深渊。
秦献公的遗恨和遗嘱
公元前384年,公子连即秦国君位,就是献公。
秦献公即位后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对右主然和菌改,该如何进行惩罚或赏赐?从当时献公的个人恩怨来说,自然是要对拒绝他入国的右主然以重罚,给迎接他入国的菌改以重奖的。他也曾想这样做了,但这时大夫监突却谏诤说:君上不可以这样做。凡是一个国君要赏赐或惩罚臣下,必须排除私人感情上的好恶,一切只能决定于臣下行事对国家有利还是有害。如其有利,即使个人感情上很憎恶,也要赏赐;若是有害,即使个人感情上很要好,也该惩罚。
献公听了认为有道理,但是联系到眼前这两个人,又觉得有些难以接受。他说:那么难道对右主然就不该惩处,对菌改也不应赏赐?
监突说:依臣之见,以为不可。君上只要这样想一想便可明白:这些年来,秦公子逃亡在外的还有好多。如果接纳入国的可以受到赏赐,而拒绝接纳的要受到惩罚,照此行事,臣子们不是都要争先恐后地去迎接他们入国了吗?真要那样做,国家还会有安宁之日吗?
献公深以为然,就决定免去右主然之罪,让菌改任大夫之职。对二要塞守卒,则每人赏赐大米二十石。
献公经过一番整顿,政局转入平稳后,就着手进行带有改良色彩的一系列改革——
【废止人殉】人殉是伴随着原始部族制瓦解而萌芽,至奴隶制建立而盛行的一项残酷的丧葬制度。那些惨状,至今我们尚能从发掘的墓葬中部分地看到。最初是男女合葬,常常是男子仰身直肢,而女子则侧身曲肢,表现出父系时期女子屈从于男子的一个社会侧影。到了夏商时代,一些君王或贵族死去时,就要迫使相当数量的男女奴隶为之殉葬。据墨子提供的数字说:“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夫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墨子·节葬下》)从已经出土的一些墓葬中可以看到,墓主的尸骨总是仰卧居中,而人殉的尸骨则多为弯腰曲肢,侧身而侍。有的还明显留有捆绑着被杀害的痕迹。奴隶主贵族所以要这样做,基于当时他们信奉的一种观念,认为死后在另一个世界里,他们仍然可以役使奴仆臣妾侍奉自己,继续享受生前的舒适生活。
迫使别人用生命为自己殉葬,在现代人看来,是绝对不可思议的事。但人的观念是他所处的特定时代的客观存在的产物。在奴隶制社会里,奴隶主认为臣服于他们的奴隶与其所拥有牛马珠宝一样,同是物质财富的一部分。既然他们有权将生前喜好的珠宝或使用过的器皿陪葬,理所当然也有权让所蓄有的奴隶为他们殉葬。这种违反最起码的人道的残忍制度受到抨击直至废止,要到生产力发展到相当程度,生产关系和经济结构有了一定改变,人的个体价值渐渐被受到重视以后才有可能。《左传》中僖公十九年和昭公十年、十一年(公元前641年和前532、531年)等处,就都有主事者欲杀人祭祀而受到谏阻或反对的记载。很可能即使在那种情况下,奴隶主贵族还是想方设法死命抓住这个被认为可以显示自己身份和权力的腐朽制度,后来只是迫于日益强大的舆论压力,才不得不改为具有人形的“俑”,即陶偶、木偶来代替人殉,以权且满足一下他们那种欲罢不能的变态心理。尽管孔子的政治主张是落后于时代的,但事关人道,他却表现了一个时代智者的敏锐观察力和寸步不让的战斗精神,他愤怒地责斥道:“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梁惠王上》引)
在人殉问题上,秦国要比中原诸国落后一大步。
秦族进入奴隶社会后,也就有了人殉。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第一次出现在秦武公死时(公元前678年),从死者有六十六人。特别是秦穆公去世,人殉竟达一百七十七人之多!人殉中有子舆氏三兄弟,是当时入们心目中的“良臣”,他们殉葬时那种“惴惴其栗”的惨状,引起人们极大的同情,有人特地写了首《黄鸟》诗哀悼他们,此诗现在我们还可以从《诗经·秦风》中读到。穆公死时离后来孔子对始作俑者的责斥还不到一百年。秦这边还在用活生生的人殉,而中原之地不久连俑殉也要受到抨击,难怪当时墨子要称秦人为“秦之野人”了。由此不难想见,献公一即位就果断地宣布“止从死”是要冒相当风险的,旧奴隶主贵族不会轻易放弃他们这种已经享受了数百年的特权。实际上从近年来发掘的若干秦墓也得到证明,献公以后直到战国末期并没有完全废止人殉。但无论如何,献公的“止从死”还是一项有胆有识的进步举措。
【编制户籍】秦献公十年(公元前375年),下令全国按五家为一“伍”的单位编制起来,称为“户籍相伍”。周王朝在建立初期也曾采取过类似措施,对居民以五为单位进行编组:五户为邻,五邻为里。但周时的邻、里只包括奴隶主和自由民,而秦此时所编的“伍”则包括原来的奴隶。这一点区别十分重要。原先自由民和奴隶主在“国”,奴隶居在“野”,两部分人贵贱界限十分清楚。进行这种新编制的意义,在于取消了“国”与“野”的界限,等于在法律上承认原来的“野人”与“国人”处于同样的地位。当然要完全取消这种由长期历史原因造成的贵贱界限决非一次户籍编制所能奏效,但这至少也是新兴势力长期斗争的一种结果,是他们力量日趋强大的一个标志。
采取这种措施还有一个军事上的意义。在这以前一个时期,秦军的大部分是庶长之类奴隶主贵族首领的私属部队,往往成为他们手中的作乱工具。“户籍相伍”后,便于将居民基层组织与军队编制结合起来,必要时可以统一征集兵员,这就剥夺了贵族培植私人武装的特权,保证了国君对军队的统率权,为进行更大改革提供社会条件。
【迁都栎阳】迁都的时间是在献公即位第二年(公元前383年),这表明他一当政就定下了要继承先祖东进的长远理想和复取河西之地的近期目标。秦都原在雍城,处于关中西部,与中原距离较远,有鞭长莫及之叹。栎阳(今陕西临潼东北武屯镇附近)南濒渭水,位于关中平原东部,沟通着中原与西北政治经济往来。《史记·货殖列传》称:“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这一记载,现在已为出土文物所证实。如1962年,曾在栎阳故地发现一只铜釜内藏币八枚,经鉴定是战国时期通货。据此也可大致推知当时栎阳的繁荣景象。献公七年(公元前378年)又“初行为市”,这既是秦国整个经济有了相当发展的反映,也是栎阳这座国都迅速繁荣起来的必然结果。
献公采取这些改革措施后,国内实力有了较快增强,于是便在他当政后期,接连向东邻“三晋”发起反击,秦国开始由失败转向胜利。
首次得胜是在献公在位第十九年(公元前366年)。这一年魏、韩两国国君在宅阳相会,秦国出其不意地向韩、魏联军发起攻击,大败联军于洛阴。两年后,秦军深入到河东,在石门与魏军大战,斩首六万,取得了多少年来少有的大胜,以至于那个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周显王也赶紧派使节前来祝贺,赐以称为黼黻的礼服。又过了两年,魏国向韩、赵两国发起大战,并在浍大败韩、赵。正当韩、赵与魏鏖战之时,秦国又伺机向魏发起袭击,在少梁大败魏军,获取了庞城,并俘虏了魏将公孙痤。在这期间,献公称“伯”,表示自己地位已高于一般诸侯。
但长期的流亡生活断送了献公的青春年华,在位二十三年后他即进入了衰老多病的垂暮岁月,带着壮志未酬的遗恨死去(公元前362年)。临终时,他殷殷嘱咐刚举行过冠礼的儿子渠梁——即将继位的秦孝公:没有收回河西之地,这是为父的耻辱。你可要继承父志啊! 人生必读经典历史丛书:时代帝国三部曲之大秦帝国(上 下)(套装共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