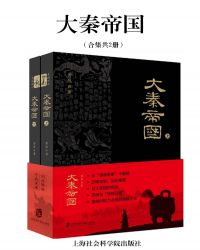短命的国王与泼辣的太后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人生必读经典历史丛书:时代帝国三部曲之大秦帝国(上 下)(套装共2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短命的国王与泼辣的太后
“一窥周室,死而无恨”
秦国朝堂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活跃气氛。不仅是几个侏儒经常插科打诨逗人欢笑,还有受到武王重用的任鄙、乌获、孟说等闻名天下的大力士,在殿阶前广场上练武,不时传来围观者们阵阵的喝彩声。
新继位的秦武王,就喜欢在这样的氛围中处理朝政。他不稀罕那些尊卑森严的礼仪,臣子们也乐得一起开心。常常朝会一散,这位年轻的国王就赶紧脱去一身累赘的朝服,拍拍肌肉饱绽的胸部,一蹦一跳走向殿前练武场。只听得他发声喊,硕大的石鼓已高举在他头顶。群臣拊掌欢呼,武王也畅怀大笑,从中得到极大的满足。
但武王决不止是“好戏”,更好功。他一登上王位就宣布了要在自己手里完成帝王之业的决心。他说:“寡人欲容车通三川,一窥周室,死不恨矣!”(《史记·秦本纪》)他所说的“三川”,当时还是韩国的一个郡,因境内有河(指黄河)、洛、伊三水而得名。容车,泛指装饰华丽之车。武王一旦乘着这样的车辂驶近三川之地,那么他日夜想望要“窥”的“周室”,离他的马鞭子也已经不远了。
这里说的“周室”,就是迁都雒邑后,其疆域、人口、实力都远远不如战国七雄当中任何一个诸侯的周王朝,当然名义上它还是统一的周朝天子的象征。说起来未免有点滑稽,就是这么个小朝廷,到周考王时期(公元前440年~前426年)又分封出一个更小的诸侯国,称西周;这西周后来又分裂出一个小国,叫东周。到周赧王即位(公元前314年)后,东、西周正式立国分治,居然还各有各的国都。这样便有三个称“周”的政治实体:一个是名义上的周王朝,不妨称之为“大周”;另外两个是诸侯国,就称“小周”吧。“大周”和“小周”都姓姬,都出身于帝王世家,都是周王朝的后裔。几百年来形成的所谓“望族心理”,使他们始终具有一种高踞于众生之上的优越感。也许正是依靠了这一想象中的精神支柱,他们才得以在几乎与周围一片大动荡处于半封闭状态下一代接一代地支撑了下来,《战国策·东周策》记了一则充满幽默意味的轶事,说是一次有个温地人要进一个小周国,城门官不纳。这个人说我是这里主人,你怎么不让我进去?可城门官问他住在哪里哪巷,他又回答不出,于是就把他囚禁了起来。小周国君派人来审问他:你明明不是这个城里的人,为什么要说是这里主人?这个温地人说:我小时候读《诗》,《诗》里有这样四句诗: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既然您周天子管理着天下,天下的臣民都是您的臣民,那我就是您的臣民,走遍天下都在您的土地上,我不就到处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了吗?
这个温地人,可说是位出色的心理学家,他抓住仅有弹丸之地小周国国君的虚荣、自大心理说了这么一番话,果然立刻获得释放。
“小周”国君尚且如此,至今仍然掌握着多种传国宝器的“大周”国君,自然更可名正言顺地以“奉天承运”的天子自居了。
但现在这位年轻气盛的秦武王,却偏说要窥他一窥!
张仪离秦奔魏,对秦国无疑是一大损失。但继张仪之位的樗里疾、甘茂左右二相,也都是颇为杰出的智能之士。樗里疾,原是惠文王的异母弟,即武王叔父,为人滑稽多智,秦人号称“智囊”。甘茂,下蔡人,熟习百家之说,曾佐惠文王定蜀,功绩卓著。雄心勃勃的秦武王依靠这两位肱股大臣,开始他理想中的帝王之业。
第一个目标,便是要攻取韩国的三川之地:宜阳(今河南宜阳西)。
武王继承父亲惠文王的故伎,派出樗里疾到韩国去任相,同时命甘茂出使魏国,联魏伐韩,以内外相应、左右包抄之势,迫使韩襄王就范。
甘茂已完成联魏使命,先派副使向寿回国向武王复命,同时带来一句有意要使武王起疑的话:臣劝大王还是不伐韩为好!武王一听,猜到其中必有蹊跷,便亲自备驾出迎,到息壤之地与甘茂相会,询问中途提出不伐韩的缘故。
其实甘茂哪里是真的不想攻韩,恰恰相反,怍为一个外籍客卿,他是想用攻取宜阳这—件大功劳,作为自己在秦国坐稳相位的奠基石。《战国策·秦策二》就有一语道出了甘茂的这种心态:“我羁旅而得相秦者,我以宜阳饵王。”其中除了他自己对“羁旅”处境敏感的体验,恐怕多少还隐含着一点商鞅、张仪结局的阴影。
君与臣在息壤相会,甘茂备述攻取宜阳实为东进立一门户的重大意义和路遥地险等艰难之处,纵然为王业所需但劳师费财,且也不是短时间内轻易能够攻取得到。武王一听已经明白了甘茂没有完全说出的话,便说:取宜阳进而窥周室,正是寡人此生大愿。所需将士、资财,全由卿开口就是!
甘茂等待的就是这句话,只是觉得还不够。于是又说了一个《曾母投梭》的故事:任谁都不会相信像曾参这样的大贤人会杀人,更何况是他母亲呢?但因为有一个与曾参同名的人杀了人,人们便一个接一个跑去报告正在织布的曾参母亲。耐人寻味的情景就这样出现了:第一个人说曾参杀人,母亲断然不信;第二个人又去这样说,母亲还是不信;第三个人再去说曾参确实杀了人,母亲丢下梭子,跳过墙去躲藏了起来。甘茂说:如今臣的贤名远不及曾参,而大王相信臣的程度,也未必像曾母相信儿子那样,而一旦宜阳暂时攻不下来,诽谤臣的人肯定不止三个,那时大王会不会也丢下手中梭子呢?臣无惧韩国利兵坚城,所怕的就是大王丢梭子!
武王说:卿尽可放心,寡人愿与卿誓盟。
甘茂伏地再拜:臣受命,万死不辞!
于是君臣歃血为誓,藏誓书于息壤。秦发兵五万,由甘茂统帅,向寿为副,进函关,下洛河,围攻宜阳。
但一围五个月,宜阳据险固守,就是攻不下来。
朝中反对的人越来越多,要求尽快班师的谏书连篇累牍。武王未予理睬。这时候左相樗里疾正从韩国回来,也认为应赶快撤师。他说:宜阳城方八里,材士十万,积粟可食用数年。而秦师已疲惫不堪,实难与之周旋,再拖延下去,怕会有变!
樗里疾是王叔,又是刚从韩国回来了解敌国内情的人,武王坚持不住了,终于投出了他的梭子:召甘茂班师。甘茂当即派人送回一信,武王拆封一看,只有两个字:“息壤”。武王立刻醒悟,再调兵五万,由乌获、孟说率领,急赴宜阳助战。甘茂受到极大鼓舞,经过一番谋划后,选定次日凌晨三鼓发起攻城。他倾囊倒箧拿出全部私金用来奖励将士。他说:如果明天攻不下来,就以宜阳城郭作为我的坟墓!
凌晨一场恶战,直打到夕阳西下,终于破城而入,斩首七万有余。韩襄王恐惧了,赶快派出相国带着玉帛宝器入秦求和。武王大喜。一面召甘茂凯旋回师,留向寿安守宜阳;一面命樗里疾先率领战车一百辆往三川开路,他自己则带着一班勇士同日起程,直发周都雒邑。
庞大的战车行列隆隆行进在三川大地上,孱弱的韩国在车轮下颤抖,中原诸国都为之震惊。纵然春秋战国以来。历代周天子都早已形同虚设,但雒邑毕竟是王都之地,岂可容忍全副武装的战车横冲直撞进入王城之门!试问大周王朝自从文武圣君立国七百余年来,何曾见过一个诸侯之国竟敢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行径来!想当年,晋文公想叫周襄王到践土会盟,在文书中用了“召”这个字,孔子写《春秋》时就要大发感慨并挖空心思为之讳饰,如果孔老先生活到现在,亲眼看到这种“犯上作乱”行为,还不知道会气成怎么样呢!就说你秦国自己吧,那年秦穆公发兵偷袭郑国,秦师仅是路过雒邑北门,将士们也还不得不一个个免胄下车以示尊敬;但因有的没有按周礼规定缓步行进而是跳上车去的,也遭到当时天下人一致谴责,后来秦军果然在崤山全军覆没,那可真是天报应啊!可如今,你们居然敢于以全副武装进犯神圣的王都之地,难道不怕上天降下比崤山之败更惨重的灾祸吗?
当然,中原诸国国君还有几句话是不便公开说的,那就是:周天子这只鹿,人人皆可逐而得之,不让我独得,也至少要共享,岂容你关西蛮子一人独吞!
偏偏这时候的名义天子周赧王是个软骨头,一听到隆隆的战车声,赶紧穿戴得整整齐齐,伏道恭候着秦武王的到来。
就在这时,楚国派出的使者,昼夜兼程,飞马来到。
楚以中原六国大阿哥的架势,对周赧王这种有损天子威仪的做法提出了诘难。
周赧王让能言善辩的侍臣游腾,去应对这位怒气冲冲的南国使者。
下面便是两人一番极妙的对话。尽管周天子已沦落到徒具虚名的地步,可你看,作为代言人的游腾,却依旧优游从容,硬是还保留着往昔天朝大国的泱泱风度呢!
游腾:先生从郢城来,暮春三月,正是江南花开莺啼之时吧?听说上国新制了一口大钟名为大吕,欲与齐国大吕之钟媲美,那钟声一定很优美吧?可惜我无缘聆听。
楚使:臣也很可惜,此次来朝觐王都,非但再也听不到优美祥和、能使风凰来朝的韶乐,一路来但见北邙蒙羞,洛水呜咽,大都王气从来没有这样黯淡过!
游腾:先生如此关心宗周社稷安危,实为难得。那我就讲一个因贪钟而亡国的故事吧,不知先生是否愿意赐听?
楚使:请说。
游腾:当年晋国上卿智伯瑶想要攻伐仇犹,便说我送你一口大钟。仇犹因贪图这口大钟,专门造了条道路来运钟。结果钟运来了,智伯瑶的军队也跟着进来了,仇犹就这样亡了国。
楚使:这个故事应当由我来说。难道王上没有看到跟在大钟后面的秦军已经进来了吗?
游腾:可区别就在这里!当年仇犹为什么灭亡呢?因为他看不到智伯瑶的计谋,没有防备。如今我王英明,对秦国的虎狼之心早已洞察无遗,所以是表面谦恭,实际早有戒备。这次武王到来时,王上命数百精兵,长戟居前,强弩列后,名为护卫,实为囚执。所以请先生回复楚王并中原诸王,尽可高枕无忧!
亏他有脸说得出!
不知是真是假,据《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记载,楚王听了他派出的使者的这番传话,居然还“乃悦”呢!
与弥漫着腐朽的虚荣之气的中原相反,正在迅猛崛起的关西秦国,讲究和关注的却是实力和实利。
实际上,秦武王如果真想灭掉这个名义上的周王朝,可说不费吹灰之力。但他不会那么傻。正像有一次周赧王通过使节对别人说的那样,此时周室土地,“绝长补短,不过百里”,因而“裂其地不足以肥国,得其众不足以劲兵”;虽属蝇头小利,但倘若你胆敢对它有所动作,那么“虽无攻之,名为弑君”(《史记·楚世家》),就会招来诸侯声讨的大祸。所以最有利的选择,就是像现在这样,借天子的空头名望,起到一种威慑作用——山东诸国你们都给我竖起耳朵听着:连堂堂的周天子也不得不为寡人伏道恭迎,尔等有谁还敢对寡人说三道四吗?哼!
年轻的国王大摇大摆走着,媚态可掬的周天子在一旁陪侍着。
他们一起走向宗庙。
请注意:这不是诸侯国的宗庙,是已立国七百余年的大周王朝的宗庙。
一行人历阶而上。
尘封的石门徐徐推开。
一片昏暗中,数十只蝙蝠因受惊而东西飞撞。
帷幕拉开,一座座巨大的周鼎赫然矗立在目。
——哈哈,我早说过,我一定举得起来!
秦武王一下甩掉了累赘的锦袍玉带,拍了拍鼓绽黝黑的胸脯……
这个关西蛮子硬是举起了九鼎
九鼎究竟铸于哪个年代,历来众说纷纭,大体有黄帝、尧舜、大禹、夏启等多说。《史记·封禅书》记下了一个方士说的黄帝造鼎的经过,近于神话,自然不足信,但十分有趣——
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堕,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胡髯号,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
看来究竟铸于哪个年代已无从确考,大概总是某个圣帝明君吧?其后即由夏传至商,再传而至周。
读古书,常常会碰到一个奇特的词汇:“问鼎”。
语法常识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动宾词组。意思无非是问一下鼎的形状、大小、重量等等,如此而已。
如果这是一个外语词汇,那么这样解释或许可以得到满分。但它却是一个在中国特定时代产生的特殊词汇,上述解释就完全错了,错了十万八千里。
“问鼎”曾经是一个极其可怕的罪名。在帝王制度——包括帝王封建制和帝王集权制存在的长达数千年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内,一个人或一群人,一旦被安上这个“问鼎”罪名,那么他或他们,就难逃被杀、剐、烹、磔以至诛灭九族的命运。
你问什么都可以,但就是不能问鼎。鼎是万万问不得的!
原因在于,此鼎非一般作为器皿用的鼎,而是宗庙重器,国家社稷之象征。国家乃“余一人”之国家,寡人之国家,朕之国家,岂容尔等普通臣民置喙!因而如果有谁胆敢问鼎,那不就是妄图犯上作乱、篡王夺位吗?不就要吞并天下、暴虐生灵吗?这就罪该万死!
载录于《左传》的第一次问鼎事件,也就是“问鼎”这一词汇的出典,发生在公元前606年,相当于秦国历史的共公时代。楚庄王因伐陆浑之戎而在周王室境内阅兵,周定王派王孙满去表示慰劳,庄王便乘机“问鼎之大小轻重焉”。那时王孙满回答的口气还是相当的强硬:“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没有实力做后盾,单是嘴巴强硬似乎并不顶用。自从楚庄王开了这个口子,类似事件便不断发生。除了楚国,还有齐国和魏国,自然更少不了秦国。每当一国提出此种非分企图时,犹如平静的水面忽然投下一石,当即波翻浪涌,使节往来,策士游说,如此这般忙乎一阵子,然后复归平静,那些鼎也还是纹丝不动地珍藏于周室宗庙内。
但是一件令人惊恐的事终于发生,多种史籍均有郑重记录,叫作“九鼎震”,在当时引起人心的震动,该不下于天崩地裂。其事发生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秦国历史为简公时代。鼎为什么会震动?是怎么震动的?史书无确记,后人只好猜测:或者为雷电所击,或者因地震所致。但那时人们大都把它作为周朝国运将尽的征兆来看,最聪明的要算瓜分了晋国的韩、赵、魏三家,他们吃准东周小朝廷因“九鼎震”而越发心虚腰软的恐慌心理,抓住这个时机,纷纷上书要求承认他们为诸侯国。这时候的周威烈王早已既无威也不烈,只好照准不误。于是在这同一年,韩、赵、魏以正式诸侯国的身份加入群雄角逐的疆场,此后大部分史家便以此作为春秋、战国的分界线。
如果说“九鼎震”还只是大自然开的一次玩笑,那么如今有那么一个关西蛮子宣称要用双手把鼎举起来,那就切莫再以玩笑视之!
刚才由大力士孟说先作试举,现在,年轻气盛的秦武王,已摆开了举鼎的架势。
他的身前和左右担负护卫之责的,分别是孟说和任鄙、乌获,他们同样精赤着上身。四个猛夫结实、黑亮的肌肉,一起在九鼎前灼灼闪光。
周赧王则站在略微远一点的暗角处,脸上依旧媚态可掬,心却在暗暗哭泣——夏传立国宝器,祖宗太庙重地,居然遭到如此鲁莽亵渎,他这个无能的姬姓王族后代能不痛哭吗?
武王开始举鼎……
且慢!
我不由得停住了笔。
鼎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多大?多重?我不敢问鼎,心里总得大致有个谱,才好落笔。我无缘亲见目睹,这是绝对肯定的;问题是古书上记载不一,且愈说愈玄,叫我如何写法!
首先是鼎的只数就没个准。
有的说,禹划地九州,一州一鼎,故有九鼎。
有的说,九州之牧,共同进献黄金,集而铸鼎,所以称九鼎,其实只有一鼎。
还有的说,到东周末年的周显王时代,其中一鼎沉于泗水,后来秦始皇巡游天下至泗水命人打捞,没有捞到。这是说先是九鼎,后来成了八鼎。
再有一说:黄帝铸一鼎,禹铸九鼎,又变成了十鼎。
更有一说,列鼎是有制度的,得按级别分配: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据说周时有诸侯三千,照此算来,鼎的数目就该多到成千上万!
其次是它的重量,更叫我无所适从。
《战国策》中一个叫颜率的人说,从前周伐殷获得九鼎,一鼎要用九万人拖拉,九鼎共用九九八十一万人,就算每个人只用一百斤力气,那么一鼎就有九百万斤,九鼎共重八千一百万斤!不要说在夏禹时代,就是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也还无法完整地把它们铸造出来吧?再说面对着如此庞然大物,除非疯子或白痴,还有谁会说要用双手把它举起来呢?
《左传》中一个叫王孙满的人却又说,九鼎的大小、轻重,完全决定于据有它们的人道德品质状况如何。若是道德高尚,鼎虽小也重;如果品性低下,鼎虽大也轻。这不又变成可大可小的洋泡泡了吗?……
这类玄妙莫测的说法还有很多,我不想再抄。
且看看近代学者对九鼎问题是怎么说的。下面是收录于《古史辨》的20世纪20年代胡适和顾颉刚在通信中谈到九鼎问题的一些看法的摘录:
“九鼎”,我认为是一种神话。铁固非夏朝所有,铜恐亦非那时代所能用。——胡适
九鼎的来源固是近于神话,但不可谓没有这件东西。看《左传》上楚子问鼎,《国策》上秦师求鼎,《史记》上秦迁九鼎,没于泗水,恐不见全假。九鼎不见于《诗》、《书》,兴国迁鼎的话自是靠不住。或者即是周朝铸的,置于东都,以为观耀;后人不知其所自来,震于其大,遂编造出许多说话耳。——顾颉刚
不过我倒认为“编造出许多说话”来的,主要的不是后人,而是当时人,特别是九鼎的拥有者,上面提到的王孙满便是其中一个。实在说来,也只有把九鼎说得玄妙莫测才能使原本极普通的物质器皿具有某种超物质的神秘力量,从而担负起象征国家社稷这样宏大的使命来。试想一下,如果像现在通行的产品说明书那样,把鼎的形状、尺寸、重量以至具体浇铸时间、地点一一开列出来,人们就会说:什么宝器不宝器,不就是烧煮青菜萝卜用的一只三脚锅子吗?有什么稀罕!果真出现这种情况,那么鼎的拥有者——天子或皇帝,还怎么能使万千臣民甘心情愿且又诚恐诚惶地匍匐在自己脚下呢?
所以鼎非但问不得,记载得清楚明白也将犯大忌!
请读者原谅,我只好自己用笨办法来一番大胆推测——
鼎的只数:按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古书记载以九鼎为多,故定为九鼎。
鼎的模样:《史记·赵世家》说,秦武王举的是其中一只“龙文赤鼎”。据此,鼎当为赤红色,上铸有龙纹。既名为鼎,当不至于离作为实用器具的鼎太远。所以以大致与我们能从博物馆或寺庙里看到的那种差不多:三脚两耳,中为圆鼓形。
鼎的重量:100—800公斤之间。根据是《史记·秦本纪》中一句话:“王与孟说举鼎,绝膑。”膑者,膝盖骨也。武王既然可与大力士比武,力气当不会小,鼎倘在一百公斤以下,决不至于使他如此狼狈。但如果重量超过八百公斤,不借助工具,单用双手,即使挪动一下已极困难,那就连“绝膑”的可能性也不再存在。
好,允许我就依此勉强写下去——
刚才孟说试举时,是用双手握住三足中的两足往上举,因而重心稍有偏移,脚步踉跄,未及过顶就摔了下来,实际上不能算是成功之举。
武王看出了这种举法的弱点,提出改为握住双耳倒举。
——倒举!
当这两个音从武王嘴里说出时,站在一旁的周赧王立刻吓白了脸。他的几个侍臣有的浑身颤栗,有的一头趴倒在地,口中喃喃不已。
倒举——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征兆啊!
——哈哈,倒举!寡人就是要倒着把它举起来!
武王说完这句话,顿时敛住笑,叉开双腿,来一个骑马蹲裆式。吐气,吸气,然后缓缓伸出手去,稳稳抓住左右双耳。他一个示意,三位勇士各执一足同时小心翼翼地徐徐将鼎倒立起来,直到确认不偏不倚时再放手。
现在这闪着赤红色光亮的宝器就稳稳地倒立在武王的双握上。他屏息绝气,双唇绷成一线,两眼脱如铜铃。当他缓缓收腿,向上挺举时,鬓发根根直竖,毕毕剥剥地爆出串串火星,在场的人都大惊失色。直至看到铜鼎终于过顶,才暗暗、微微吐了口气,却谁也不敢欢呼出声来。可武王自己却先在心里笑了。他甚至贪心到想走一两步试试。就在这时,他身躯一斜,龙纹赤鼎轰然摔下,最先触地的那一足,入土竟有三尺来深!
倒在地上的国王,一阵胜利的大笑后,大口大口的鲜血从他嘴里涌出。这说明他不止是绝膑,还造成了内伤。
三个月以后,即秦武王四年(公元前307年)深秋,这位年仅二十三岁的国王含笑死去。
像希腊神话中的著名英雄阿喀琉斯一样,在“或者做一个庸人而长寿,或者做一个英雄而早死”的人生抉择面前,秦武王也坚定地选择了后者。他早就说过:只要一窥周室,死而无恨。
如此人生,不可无诗。可惜一时找不到前贤时俊的题咏,我只好勉为其难,姑以《举鼎赞》为题,草拟一绝,曰:
惊雷劈天落,
狂飙扫地空;
吾生求一逞,
万世倏忽同!
令人震惊的是,后来竟然把武王的死归罪于孟说,不仅杀了他本人,还灭了他九族。
武王死得过于年轻,没有留下儿子,继位的是他的同父异母的弟弟侧,又名稷,即昭襄王。
但昭襄王此时也还只有十九岁,这时候一个强有力的女人跻身进入了秦国朝堂,她就是昭襄王的母亲宣太后。
奇谋发生在禁宫深处
在秦国历史上,后宫女人介入朝政的共有三人,其余两人分别在宣太后之前和之后。之前的是出子之母,史称小主夫人;之后的便是帝太后,即赵姬,秦始皇之母。但就影响的深度与强度来说,她们都不能与宣太后相比。宣太后,这个来自楚国宗室,姓芈(mī),号八子的女人,实在不简单!
说她不简单,是因为她运用手腕和裙带关系,几乎把整个朝政都控制到自己手心,上下左右,差不多都成了她的人。不像小主夫人和帝太后那样,哭哭啼啼,偷偷摸摸,昙花一现,后来又都弄得声名狼藉。宣太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秦这样的大封国临朝称制的女性,专权达二三十年之久,一直活得威风、快活,直到年过古稀临终前,还要耍出一段风流插曲来!
宣太后有两个弟弟,魏冉和芈戎,都成为秦国大臣。魏冉封为穰侯,五次任相,在相位时间共计二十五年之久,时间之长,在秦国所有任相人中间是创纪录的。芈戎封为华阳君,又号新城君,后来一度也担任过左丞相。除昭襄王外,宣太后还有两个儿子:芾和悝(kuī),分别封为泾阳君、高陵君。穰侯、华阳君、高陵君、泾阳君,时称“四贵”。还有那个与甘茂一起攻下宜阳后又坚守宜阳的向寿,也是宣太后的外族。太后从小把向寿带在身边,因而向寿与昭襄王“少与之同衣,长与之同车”(《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关系非同寻常。客卿甘茂,后来就因害怕向寿进谗,投奔了齐国。
武王举鼎,猝然长逝。他没有儿子继位,诸多兄弟便开始激烈争夺。宣太后依靠魏冉等众多亲族的权势,把自己儿子侧扶上王位,成为昭襄王。庶长壮及诸公子发动叛乱,魏冉动用秦国的强大武装力量,实行残酷镇压,凡参与叛乱的诸公子均被杀,连原为魏国人的武王的王后,也被逐回魏国。
宣太后的不简单,根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还有更出人意料的表现。
昭襄王即位的典礼终于隆重举行,各国都派出使节来祝贺。
庆典过后,各国使节都已踏上归程,唯独义渠国国君被挽留了下来。
义渠是西戎中较为强悍的一支。义渠君生得浓眉深目,是那种惯于弯硬弓、骑烈马的伟男子,他等待着昭襄王的召见。直到先被内侍引着来到甘泉宫,又被宫女引着进入懿和宫时,才知道召见他的竟是宣太后!
宣太后是惠文王王后,其时守寡已有四年多。根本用不着掩饰,她就这么堂而皇之地找了个男子汉气味十足的情夫。她是在楚王宫里长大的,楚王好细腰的时尚,使得楚宫女子个个特别袅娜妩媚。这时候她还只有三十多岁,想必风韵依旧,义渠君当也喜出望外。
此后,义渠君自然乐意常作出访秦之行,他们的这种关系保持近三十年之久,以至生有两个孩子,大模大样地就在秦宫内成长了起来。
作为一个大国国政的实际执掌者,宣太后的风流举止和毫无顾忌的言谈,确实出格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她竟然在外交场合,以谈自己性生活的感受来要挟对方为秦国谋求更多实利。
那是昭襄王七年(公元前300年)的事。楚军围困韩国雍氏已有五个月,韩国接连派使者求救于秦,宣太后却还没有忘记自己的娘家,多少有些偏心于楚,就是不肯出兵。后来韩国又派了个名叫尚靳的使者,经过一番曲折,总算见到了昭襄王。尚靳说:鄙邑作为上国的屏障,这些年来,每逢上国有召,韩国的军队就像大雁那样立刻列队赶来应召。如今韩国有难,有道唇亡则齿寒,还望大王早救鄙邑于水火。
昭襄王禀报了了宣太后,太后说:韩国来了那么多使者,只有这个姓尚的还说得有点道理,传他进来吧!
尚靳战战兢兢地来到太后殿,宣太后劈头就说了这么一番话——
当年,我侍奉先王的时候,他总喜欢先把一条大腿搭在我身上,这使我常常疲乏到不能支撑。可当他把身体整个儿压到上面时,我反而感觉不到他的重量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我也得到了好处。同样的道理,如今要秦国去解救韩国,我们士兵不多,粮食也不足,每天得用千金去应付这巨大的消耗,就会感到支撑不起来。你们总得也给我得到一点好处才是呀!
用这种方式进行外交谈判,恐怕是外交史上绝无仅有的吧?
但宣太后绝不是通常的荡妇。她很懂得政治,懂得如何去攫取个人权势,扩大秦国基业。不错,她对感情的追求也很强烈,但当两者发生矛盾时,她会毫不犹豫地以抛弃感情需要而去追求前者。
事实上,宣太后所以要把义渠君引上自己床笫,更多的还是出于政治考虑。
原来西戎中义渠这一族,特别桀骜不驯。早在秦穆公时代,就与秦几经较量。后来穆公任用由余,使西戎包括义渠在内的八个戎国表示臣服。但以后义渠族多次反复,不断兴兵攻击秦境,秦躁公十三年(公元前430年),曾一度攻入秦国心腹地区渭阳。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与秦为敌的诸侯国,有时会利用这股不驯服的势力怂恿他们到秦后方去骚扰。譬如弃秦奔魏后的公孙衍,就曾向义渠君提供过秦对义渠的策略秘密,说其中的奥秘是这样的:当秦国与中原诸国交好时,它就会来进攻掠夺义渠;当秦国自己受到别国威胁时,它就要送厚礼给义渠,以示笼络。义渠要进攻秦国,就要趁这个时候。不久,秦国因受到山东五国联合进攻,便向义渠君送去“文绣千纯,妇女百人”。义渠君记着公孙衍的话,乘机向秦后方发起进攻,果然大有收获。
现在好了,宣太后用她温暖的怀抱,硬是把一块百炼钢融化成了绕指柔,桀骜不驯的义渠君突然变得温文尔雅起来。在近三十年这样长的时间内,尽管秦国不断与山东各国轮番角逐较量,无暇西顾,但义渠君仿佛已忘记了公孙衍传授给他的策略秘诀,从未乘机向秦发起过进攻。
但真到了这一步,义渠君的价值也已所剩无多。
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72年),宣太后及其谋臣们觉得有余暇可以从东线抽出一部分力量来到西线做点事了。这天晚上,宣太后又把义渠君召进了甘泉宫。从此,义渠君便再也没能直着走出来。
随后,秦军轻而易举地消灭了已经没有国君的义渠国,设置了陇西郡、北地郡和上郡,巩固了对北部地区的统治。
这便是《史记·匈奴传》记下的这样两句话:“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至于这天晚上宣太后是如何杀死义渠君的,史书无录,我也不想来作任何虚构性的描述。
此刻,控制着我思绪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宣太后在伸出致情人于死命之手以前,是如何首先掐断自己的情丝的?无论如何他们是有过近三十年的姘居关系,还养育了两个孩子的呀!但为了权势,为了秦国的基业,她居然如此果断地伸出了她那只致命之手——首先致自己情感以死命,然后致一个男人以死命。这或许也有些可敬,但更多的却是可怕!
最后,我想用一个采自《战国策·秦策二》的简短的插曲来结束这一节。
秦昭襄王四十二年(公元前265年),享年七十有余的宣太后,在行将进入弥留之际,下达了她的最后一道指令:葬我的时候,一定要让魏丑夫为我殉葬!
魏丑夫是宣太后爱宠的面首。听到要他殉葬,非常害怕。近臣庸芮就帮他去说情。庸芮说:太后,你说人死后是有知觉呢,还是没有知觉?
宣太后说:没有知觉。
庸芮说:既然没有知觉,那么让一个太后所爱的人白白殉葬对太后又有什么意思呢?
宣太后说:或许有知觉吧?
臂芮说:那就更不妥。要是人死后有知觉,先王已在泉下等了几十年,太后去后侍奉先王还来不及,哪还顾得上魏丑夫呢?
宣太后先是一愣,继而终于说出了两个字:有理。
魏丑夫总算保住了一条性命。 人生必读经典历史丛书:时代帝国三部曲之大秦帝国(上 下)(套装共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