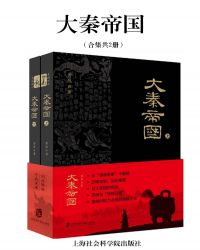流星·彗星·哈雷彗星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人生必读经典历史丛书:时代帝国三部曲之大秦帝国(上 下)(套装共2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流星·彗星·哈雷彗星
“像历史长空中的流星”——林先生这个形象而确切的比喻,启发我想再来作一番也许属于蛇足的引申。窃以为秦帝国就其存在的短暂而言,确实恍若流星;但它留在人们观念中的形象,似乎更像彗星。这不仅因为秦帝国时期,彗星屡屡经天,而且景象诡异,因而司马迁在记载这一天文现象时,用了多少带点惊愕的语气:“秦始皇之时,十五年彗星四见,久者八十日,长或竟天”(《史记·天官书》);也不仅因为秦始皇亲政甘泉宫和死于沙丘的前夕,都有彗星出现——我主要取彗星的象征意义。
彗星可谓横空出世。它脱出了一般行星的常轨,仿佛是突然出现在天空。它那由彗核、彗发和彗尾组成的灿烂的光带,“长或竟天”,气势恢宏地划过天空,蔚为壮观。秦帝国也是以脱出那个时代人们通常能够预想到的王朝模式而豁然问世的。它以强大的国家权力承认和确立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在这种生产关系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以皇帝为绝对权威的集权专制的政权形式,以及为此而设置的包括郡县制在内的一系列行政立法和典章制度,也被当时许多人视同彗星的出现那样不可理解。人们看着从咸阳宫上空升起一道道奇异的光亮,阵阵头晕目眩之后,在野者开始默默诅咒,在朝者有的冒死进谏,有的阿顺求容。突然有一天,秦帝国这颗彗星消失了,但它所创立的那些当时不被理解的国家权力形式、典章制度,特别是“皇帝”这个至高无上的称号,却千年百代地沿用了下来,并被奉为天经地义。
彗星的另一象征意义是灾难。
把彗星这一特殊天体视为会给人间带来灾祸的“妖星”,认定彗星的出现为“凶兆”,在中国有过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如《左传·昭公十七年》就记有彗星的光芒扫过天空,“诸侯其有火灾乎”这样的话。因受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就连太史公司马迁也不无类似想法,因而他在上面引用过的那段“彗星四见”的记载后又写道:“其后秦遂以兵灭六王,并中国,外攘四夷,死人如乱麻”,并认为“自蚩尤以来,未尝若斯也”!
但秦帝国,特别是秦始皇晚年和秦二世时期,实行的确实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暴政。秦政的酷烈是有传统的。秦穆公之世尽管颇多建树,但他死时竟要一百七十七人殉葬!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对反对新法者进行了严厉的镇压,据刘向《新序》著录,仅一次就在渭河边杀死七百余人,“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秦始皇更把这种残酷的统治手段发展到了极端。一听说有人借私学“逆古以害今”,就点燃了焚烧《书》、《诗》和百家著作的火焰。为求长生受了方士的骗,又据告密的人说咸阳有儒生在妖言惑众,一怒之下,就把四百六十余名儒生捉来全都活埋!为建造骊山下的秦始皇陵墓,征发了七十余万人力,陪葬了无数奇珍异宝,为防止泄密,竟然将数以万计的工匠坑杀在陵墓之旁。修筑长城固然是出于维护边防的需要,但以动员三十万之众的规模,长年累月劳苦于白山黑水之间,古书上屡屡描述的“死者相属”一类惨状,决非言之无据。早在那个凄婉悱恻的《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以前,就有了这样的民谣:
生男慎勿举,
生女哺用脯。
不见长城下,
尸骸相支柱。
孟德斯鸠对暴政作过一个很有意义的分析,认为:“暴政有两种,一种是真正的暴政,是以暴力统治人民的;另一种是见解上的暴政,即当统治者建立的一些设施和人民的想法相抵触时让人感觉到的那种暴政。”(《论法的精神》)秦帝国的暴政可说是这两种因素兼而有之,而在它后期,则几乎全部属于第一种暴政。
彗星的出现,又是一种世界性景观。当那神奇瑰丽的景象展示在太空的时候,居住在地球上相对经纬度的人们,一抬头都能看到。分别居住于五大洲的世界各国人民,最初对中国人的认识,正是通过彗星般崛起的秦帝国。因而无论古代希伯来文或印度梵文都用“秦”或近似秦的译音“支那”、“脂那”、“震旦”等来指称中国。研究秦史有年的马非百在《秦始皇帝传》对此作了考订,并列举了众多实例——
如古代印度梵文,称中国为支那(Cina)或支那斯(Chinas)。希伯来文圣经《旧约·以赛亚书篇》则称为西尼姆(Sininm)。英国人斯坦因自中亚盗窃的康居国文遗书中,则称为秦斯坦(Cynstn),罗马拉丁文名著《爱利脱利亚洋海纪事》亦载有秦国(Jhin)之名,并谓其大都城为秦尼(Jhinae)。此外希腊地理学家雷脱美之《地理书),有秦尼国(Sinae)与塞里斯国(Seres)之名。希腊僧人科斯麻士之《世界基督教诸国风土记》,有秦尼策国(Jzintza)及秦尼斯达国(Jzinista)之名。亚美尼亚史学家摩西之《史记》,则谓中国为产丝之国,其国名为哲那斯坦国(Jenasdan)。陕西西安府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之叙利亚文,则称中国为秦那斯坦(Zhinastan),长安为克姆丹(Khumdan)。而中世纪阿拉伯之著作,则直称为秦(Cyn或Syn或Jhin)。波斯诗圣费杜西于其诗中,记载中波两国人民交往甚多,其称中国皆为支那(China)……晚近日本人亦仿效西方人称中国为支那。
国际著名汉学家、宾夕法尼亚大学荣誉教授卜德先生在《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写道:
说明帝国的威名甚至远扬于中华世界以外的例子是,秦(Ch’in)这一名称很可能是英语“中国”(China)及各种非汉语中其他同源名称的原型。例如,“Thinai”和“Sinai”就作为这个国家的名称出现在公元一、二世纪的希腊和罗马著作中。但是,中国人由于秦帝国统治的暴政,对它始终非常憎恨,因而反而很少用这个名称来指代自己;他们在过去和现在都用“中国”这一常见的名称来称呼自己。
当然,中国人所以不用“秦”,而用“中国”这样一个称呼来指代自己国家,自有其更深层的地理、人文和历史渊源,并非由于秦帝国实行了暴政。但在了解到短暂的秦帝国的最初闪光,竟然在世界历史上留下如此鲜明的印象以后,我们还是不禁会对它涌起一种特别的感情。
据英国天文学家克劳密博士推算,秦王嬴政亲政前夕在咸阳上空出现的彗星,正是一千八百多年后由英国天文学家哈雷首次计算出它的轨道因而获得命名的哈雷彗星。由此,我还想进一步把秦帝国比之为哈雷彗星。
哈雷彗星不会像流星那样消失,它平均以76年为周期向地球人类光顾一次。秦帝国作为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自然一经消逝永不复返;但在历史学,或者说人们观念中这个特别天宇里,它却像哈雷彗星那样,两千多年来,一而再、再而三地高悬中天,展示它的吉凶未卜、善恶难定的光焰,一次又一次地吸引百家争鸣,引起世人瞩目。
在我国历史上,还没有第二个如此短暂的王朝使得人们具有如此恒久的兴趣去关注它,包括一般人作为历史故事来欣赏的兴趣,和历史学家们进行理性探究的兴趣。
最先试图对秦帝国作出评价的是汉朝人。但他们往往偏重于对秦暴政的指控,且又好作夸饰渲染之词。这当然也是可以理解的。历史上一个新王朝的建立,每每要在一个相当长时间内着力揭示被战胜国的黑暗面,甚至明知夸大或无中生有也在所不惜,以更显出自己诛伐无道的光明所在。秦国兼并六国过程中也曾这样做过,如今是六十年风水轮流转,当年的胜利者被推到了受指控的位置。除此之外,对一般人来说,指责一个已被埋葬的暴君,不必再有任何顾忌,非但可以宣泄郁积已久的愤懑,通常还能受到新的当国者的赞许,何乐而不为!因此,凡是对待这类时期的史料,在用过一番真伪鉴别工夫后,最好再捏在手心挤一挤,以便挤出其中水分。
不过汉初年轻而负有盛名的政论家贾谊写的《过秦论》,行文恣肆汪洋,立论也还较为平正。文中认为秦帝国的短命是由于错过了两个本可很好巩固、发展自己的时期。第一是南面称帝之初。饱受长期战乱之苦的天下元元之民和四方之士,终于又见到了天子,因而莫不虚心而向上,斐然而向风。如果能在这个时候“守威定功”,那便是“安危之本”。但秦始皇却没有这样做。第二是二世初立之时。对秦始皇的暴政记忆犹新,所以天下黎民莫不引颈企盼着二世的举措。对饥寒交迫中的劳苦者,只要略施恩惠便会得到满足,即所谓“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资也”。但是智能和胆略都远不及乃父的秦二世,却以昏庸和游乐荒废了这个良机。
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里大段大段引录《过秦论》原文,并赞扬道:“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表明他对贾谊观点的认同。作为一个杰出的历史学家,司马迁还针对当时一般学者对秦帝国的偏见,提出了一个极具现实性、又富有深远意义的告诫。他说:“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史记·六国年表》)用耳朵进食,食而不知其味,却还自作聪明地“举以笑之”,这个讽刺是辛辣的,却也活脱脱画出了一些人的浅薄相。对待历史和历史人物,特别是对待秦史和秦始皇,这种“耳食症”,的确值得我们经常警惕。
精于帝王术的汉高祖刘邦,在赐予已经断绝了后嗣的秦始皇帝以二十户人家守护陵墓,以显示其宽容和仁爱的同时,对待秦帝国的历史地位却过于霸道,霸道到甚至不承认它的合法存在。
这就要说到那个叫作“五德终始”的天命归属图式或称国运代谢学说了。本书第七章将对这个似乎玄妙深奥的学说作简略介绍。实际上。它的核心内容也就那么一句话:认为王朝的更替是严格按照土、木、金、火、水这“五德”相克或相生轮流转的。从黄帝开始,分别是:黄帝,土德;夏禹,木德;商汤,金德;周文王,火德。大秦帝国建立时,宣布以水德受命于天,代周火德而兴,并采取了一系列与水德相应的措施。现在看来这自然很荒唐,但当时人们却信以为真,因而一个朝代能不能符合其中相应的一德,就变成了它是否符合正统、能否获得上天受命这样一个根本性的大问题。
大汉帝国成立后,按照“五德终始”说,应是汉土克秦水而兴,以土德受命。尽管汉初法制多承秦旧,但汉高祖却决心与已被推翻的秦帝国彻底划清界线,硬是跳过秦而径直与周拉上关系,宣布仍以水德接续周的火德。这样一来,秦帝国就被排除在五德更迭的循环圈之外,等于失去了历史地位。显赫一时的秦帝国,此时已可怜兮兮地落到了被开除“史籍”的地步!开头汉帝国的决策层都觉得这种做法一了百了,很痛快。但渐渐终于有人感觉到了其中的不妥处。你根本不承认秦帝国的合法存在似乎还容易做到,但那空荡荡的十五个年头,和这十五个年头里发生的事、出生的人往哪里搁呀?聪明人毕竟还是有,于是别创一说曰“闰统”。此说认为,就像历法中过若干年会出现一个闰月那样,“五德终始”在不断演进过程中偶尔也会出现“闰”,秦帝国也就是这么被“闰”出来的一个“统”!这一回,秦帝国的史籍总算勉强保住了,但却被打入了“另册”。就是说,它是一颗没有正规星座、横穿而入的彗星,一颗哈雷彗星!
此后两千年,这颗哈雷彗星不时在历史上空出现,特别在唐宋时期,多次爆发出耀眼的光亮。唐太宗李世民与周围群臣,唐宪宗时期的韩愈、柳宗元,宋神宗时期的王安石、司马光,还有集宋代理学之大成的朱熹,或在朝堂,或在学界,多次就秦帝国和秦始皇的兴亡荣辱、功过是非展开论说争辩。其间,尤以柳宗元的《封建论》影响最大。
柳宗元生活在晚唐时期,昔日盛唐的辉煌,经安史之乱一劫,转眼已到了夕阳西下,统一的李唐山河被藩镇列强分割殆尽。这不由人又一次勾想起那五霸争强、七雄逐鹿的春秋战国时代,想起那猛烈崛起又迅速坠落的大秦帝国。
问题是这样提出来的:秦帝国因何而迅速灭亡?
韩愈是主张分封制的,因而他认为“无分势于诸侯”是秦二世而亡的首要原因(见《韩昌黎集·杂说》)。
柳宗元的《封建论》恰好与韩愈针锋相对,竭力反对分封。也许在柳宗元眼里,当时藩镇的跋扈割据,正是当年诸侯裂土争战悲剧的重演。他以汉朝实行过部分的封侯封王,魏、晋承袭此制而相继迅速衰落;唐朝废除分封,完全采用州县制却已巩固地享有了二百余年国运,这样两个对比事实为据,证明郡县制优于分封制。至于秦速亡的原因,他认为“非郡县之制失也”,“失在于政”,就是说是由为政者的暴虐造成。
时代发展到了明清,世界各民族的相互交往成了潮流,古老的中国缓慢地启开了国门。也许国人在睁眼看世界的同时,却不无羞惭地看到了自己的陈腐与落后,因而要求血与火的锤炼与变革,希望有雄才大略的铁腕人物出世,渐次形成了人们的共同愿望。于是,两千多年前的秦帝国又成了时兴的话题。这一时期对秦的指责还是有的,例如王守仁就对秦的诸如焚书坑儒等暴政,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但更多的却是赞扬。此时这颗再度悬上历史学上空的彗星,“凶兆”的含义消失殆尽,济世救国的吉祥含义大放异彩。石破天惊,李贽竟然赞誉秦始皇为“千古英雄”、“千古一帝”(分别见《史纲评要·后秦记》、《藏书·世纪列传总目》)。继起的王夫之,针对前人常以秦不分封诸侯是“私天下”的指责,提出他的独特的见解:“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读通鉴论》卷一)及至晚清,章太炎在《秦政论》、《秦献记》等文章中,一再张扬秦政,认为古代称得上以公正治天下的,莫过于秦王朝。他特别称道秦始皇自己“负扆(yǐ,屏风)以断天下,而子弟为庶人”这种不以血缘关系封侯赐爵的无私精神,认为他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帝王都要崇高。
比喻总是跛脚的。把秦帝国比作哈雷彗星,只是取了它往往隔若干时间又要成为社会舆论热点这样一义。实际上,这种“彗星”并非来自天外,而是出自人们心间。正是现实生活的需要,决定了人们希望从以往历史中去汲取点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种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践》)。本身已包含有丰富历史内容的秦帝国,仿佛恰恰由于它的短暂,反而越发显出问题的尖锐性和对比的鲜明性,因而更加吸引人们去探究它、解剖它、吸吮它或排斥它。不用作细致考察便可以看到,秦帝国的每一次被引起论辩,都是某种社会现状的折射。当社会由乱而治时,主要是在朝者便会出来揭示秦的残暴,并声言自己将以秦为鉴,实现长治久安;当社会由治转乱时,主要是在野者便会站出来,赞扬秦的革古鼎新胆略,呼唤秦始皇式人物的再世——这大概就是历史学上空这颗哈雷彗星的轨迹吧。
不过,两千多年来,无论论辩双方如何水火不容,寸土不让,有一点却完全一致:双方都认为到战国末期,山河复归一统既是大势所趋,也是人心所向。
问题是:为什么完成统一大业的,不是别国,偏偏是山东六国公认为“天下之仇雠”(见《史记·苏秦列传》)的秦国呢?不是别人,偏偏是被认为“行桀纣之道”(见《说苑·至公篇》)的秦王嬴政呢? 人生必读经典历史丛书:时代帝国三部曲之大秦帝国(上 下)(套装共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