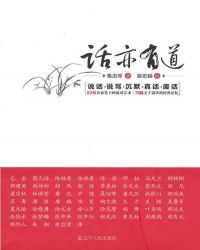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话亦有道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谈说谎 吴鲁芹
说谎不是好事,但有时也不可避免。偶尔说一两句无伤大雅的谎言,若也算是罪恶,普天之下,清白的人就很少了。
自诩生平从未说过谎的人,一定是个骗子,因为他对自己都不诚实。不久以前,美国有本杂志,分门别类,列举了几十个问题,测验一个人究竟“成熟”(Mature)到什么程度。其中有一项:“你相信你有生以来从未说过谎吗?”若有人天真烂漫,在答案上写个“是”,这一题他就得不到分;距离“成熟”的阶段,也就远了一步。说生平不说谎,等于说生平不做梦,实在叫人难以置信。
说谎可能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坏习性之一,如好色,如贪嘴。这种坏习性在某些人身上是显性的,在某些人身上是隐性的。程度深浅,因人而异,但绝迹是很难的。照十六世纪英国学人海武德(John Heywood)的理论,不说谎的只有两种人:一是智力商数特低的白痴,一是在呀呀学语的幼儿。如果允许我加注脚,我要说白痴和幼儿,非不为也,是不能也,绝不是他们得天独厚,可以免疫。《旧约·诗篇》,亦曾慨乎言之,说“人都是谎言者”。这简直是盖棺定论,直率到毫无转圜的余地。我想,平时喜以圣贤自况的人,看到这一句,一定感到触目惊心,进退维谷。他们既不屑降格与说谎者谊属同类,然而弃万物之灵以外,亦别无可为。这时他们唯一的去处,可能只有遁入空门,了此余生。“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佛门弟子大约可以自负是不说谎的。
平心而论,纯为说谎而说谎,与存心欺骗的说谎不同,也不该受同一待遇。凡损人利己,或者损人未必利己的谎言,是大谎,是不可宽恕的罪恶。无害于人,可以自娱,亦可娱人的谎言,说时,或为缓和对方的不安,或为减轻自己的窘相,我们可以名之曰小谎,说得恰到好处,且是一种艺术。王尔德(Oscar Wilde)在《论说谎之式微》(The Decay of Lying)一文中,所说“只有一种谎,是绝对无可厚非的,那就是为说谎而说的谎”,大约就是指后者。我们平时做主人发请帖,自谦略备菲酌,严格说来,是谎。面对山珍海味,犹连声简慢,也是谎。在席间碰到武人,偏说他文采风流;碰到文士,偏说他胸藏韬略,这样宾主会更尽欢,空气会更和谐。因为出色当行,就同说女人会生孩子,并不足奇;不当行而能出色,才是稀罕。我们见到别人的子嗣天资鲁钝,不像有什么大出息,也还得用“大器晚成”一类词语来补救,叫人安心,叫人瞩望于虚无缥缈的未来。就同我们对姿色十分平庸的女子,有时不免也要从优考核,赞美两句;万不得已,还得借用“内在的美”、“灵魂的美”等等新文艺术语,来支持自己别具慧眼的论断。老实说,这些十之八九是谎,但都无大碍,有时且叫人感激。如果谎言也能有好处,应该止于此矣。说谎者若知道律己,似乎到此就该悬崖勒马。倘使明明借钱还赌债,偏说孩子生病缴不出住院费,无意之间,已越过小谎与大谎的分水岭,日久成习,也就不可收拾了。当然,更甚于此的,如外交舞台上的谎,政治舞台上的谎。这其中有些谎,也许太大了,太美了,真正死心塌地去相信的人反而不多。
在日常生活中,颟顸的上司,最易听信善于蒙混的部属的谎;溺爱的父母,最易听信宠坏了的子女的谎;恋爱期间的窈窕淑女,最易听信好逑君子的谎。女人们从豆蔻年华无邪的时代开始,直到中年发福不再窈窕为止,似乎变化多端,唯独有一件事一成不变,那就是相信谎言。《乞丐的歌剧》作者盖·约翰(John Gay)曾有妙句云:“男人说谎,女人信谎。”人间的许多热闹,说不定就得力于这样的分工合作。
不过说谎总不是件好事。它的效用,有时是十分短暂的。歌德所说:“当我错了,谁都看得出来;我若说谎,那就不然。”充分描绘出说谎者沾沾自喜的神情。其实这只是自得其乐的片面的想法,不大靠得住。日子一久,谎话往往不攻自破。世间最经不起时间考验的,莫过于谎言。希腊一位大悲剧家索福克里司①就曾说过:“谎话自来难长寿。”这话大约是从“自古红颜多薄命”变化而来,因为谎言也是美丽的居多。时人作文常说赤裸裸的真理,可见谎话是穿了衣裳,打扮过了的。
通常最令听者莞尔、说者难堪的是说谎者健忘,无意中首尾不能呼应,忘记了说第二个谎来支持第一个谎。“天下没有比一个健忘的说谎者更凄惨的了。”“一个对自己的记忆力没有多大把握的人,最好别干说谎这个行当。”因为他若没有莎士比亚剧中说谎圣手孚尔斯塔夫爵士(Sir John Falstaff)那套自圆其说的独到本领,就要自讨没趣,说不定会把自己弄到无地自容的地步。一个人说了谎,实在是无形中为自己平添了一层负担。有时候“逼得要造出二十个谎,来维持第一句谎话于不坠”。这形同作茧自缚,不上算得很。我们有时听大人物演讲,只见他口中天花乱坠,脸上一片虔诚,好像句句肺腑,语语真诚,听来心中不免纳闷。其实这只不过是演说者谎说多了,自己也信以为真了。能跟着说谎的人把谎言信以为真,是有福的人。
英国散文家司越夫特②(Jonathan Swift)曾说:“一个人如果能有第二种视觉,看得清人身上的谎,像在苏格兰有人可以看得到幽灵那套本领,那他处今日之世,目睹萦绕于人们脑际那些说谎念头,大大小小,形形色色一定有无穷的乐趣。”我十分怀疑,一个人真有了这种本领,是否真是福分。
英文中向有白谎(white lie)一词,指一种无大害可以宽恕的谎言。这种以颜色为谎言分类,以颜色深浅辨其轻重,别致而且中肯。准此类推,弥天大谎,应称黑谎,该与黑心、黑社会、黑暗势力同流,无怪其可怕可恶了。西方人对说谎之辱,向不等闲视之,有时会立即报以老拳。可是在用字上,其深恶痛绝的程度,似乎表达得不如我们淋漓尽致。区区浅学,不知英文中有无用“撒”字来描摹“说谎”这个动作,不让我们专美。撒字一词,道尽了对谎言之不屑。平常,撒字多半用在说明排泄不洁之物的动作。我不相信,世上对满口谎言,一泻千里的长才,能找到更不敬的字眼。
(选自《鸡尾酒会及其他 美国去来》,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1月版)
吴鲁芹(1918—1983),字鸿藻,上海人。早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外文系。曾先后在武汉大学、台湾师范学院、淡江英专、台湾大学等校任教。1956年与友人创办《文学杂志》。1962年赴美,任教于密苏里大学。著有《美国去来》《鸡尾酒会及其他》《瞎三话四集》《余年集》《暮云集》《英美十六家》等。 话亦有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