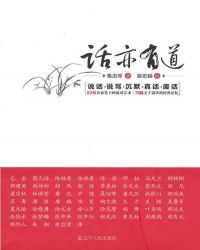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话亦有道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语言对于思想的反响 唐钺
语言和思想并不是有必不可分离的关系。我们的思想作用,固然在许多时候是含有语言—无论是说出来听得见或是不说出来听不见的—但有时只有手脚或躯干这微细的动作,或是脏腑,血管,泌腺等等的微细的变化,或是视觉器官或听觉器官的某一部分微细的激动,思想就可以进行。然而通常的时候,思想作用是含着语言的。思想可以说是人类的使用符号的行为。虽是许多作用都可以做思想所用的符号,但在思想的发达史上占极重要的位置的符号要算语言。小孩子学说话,其实就是在那里学思想。在小孩子,思想和语言几乎有必不可离的关系。小孩子自个儿想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常常通通说出来。许多成年人思想的时候也常常自言自语:这些事实,可以证明语言对于思想有极密切的关系。成年人思想时候的自言自语虽然常常是不出声的,但它的存在是没有疑问的。
语言对于思想的贡献是很大的。一来,其他的作用,如手脚的或脏腑的变动之类,虽是也可以作思想的符号,但是这些作用,对于思想上许许多多的微妙的差别,是否能够对它们中每个都给予一个符号,是个问题。语言所含的声音(和依据语音的文字)的配合似乎比那些作用的配合,种类更多,变化更大,更可以代表思想上的复杂之点。(当然就是语言,也不能把思想上的各方面全部表现出来;但这是另外一件事。)二来,总使其他作用也和语言一样地能够传达思想上的微细的区别,它们绝不及语言那样兼有确定和永久的性质。单就一个人来说,此刻的思想,假如不用语言表现出来,将来就很难记准确,记得清楚。这样一来,就使他很难根据旧的经验去推求新的知识。再就人类的大团体说来,假如人人的思想都不用语言表出来,这个人绝没有机会利用那个人的思想的结果;人类的知识,不消说是不能够进步的了。手脚与躯干的动作,虽也可以表示意思于旁人,但这些动作不特配合的花样不多,并且表现要费许多时间,远不及语言那样便利。假如我们复杂的抽象的思想,也像聋哑人一样,用手指表示,一定不能够把它像语言那样精确地传达出来。还有更要紧的是:手足和躯干是应该用去做别的事情的;假如让它“讲话”,恐怕人的一生所能做成功的事情不见十分多!
语言是用来代表思想的,它似乎应该是永远受思想者支配的。但实际上却不全是这样。培根说的好:
人们设想他们的理性支配言语,但其实言语对于悟性起反响;这种情形曾经使哲学和各科学成为似是而非和委靡不振的学问。(Bacon,Zovom Organuum,Aph.LIX)
培根曾把思想的谬误分别做四种偶像,其中一个—市场的偶像—就是指由语言的反响而生的谬误。欧洲从前有个外交家说语言是创造来隐匿思想的。许多语言对于思想的反响,几乎要使我们相信语言是把来混乱思想的!
语言对于思想的反响,有许多;现在姑且说以下几种。
(第一)话相同而意思不相同。这当然是大家都知道的一种最普通的现象。无论哪一种语言,都没有一个话只代表一个意思的。因为语言是许多人不知不觉的产品,所以不能够那样直截了当。纵使我们能够在一个时期把一切的话的意思都固定得没有含糊,过了一会儿,又必定有许多话是各个代表两三个意思了。所以这是没有法子除掉的毛病(在实用上,或者竟然不是毛病,而是便利)。同一个话而代表不同的意思的,例如: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说是孔子的话)“文”字可以说是“辞藻缤纷”,就是有装点的意思。也可以说是“文理密察”,就是“有条理”的意思。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篇》)《荀子·正名篇》原说“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但“伪”字原有两个意思,怪不得后人的误会。《孟子·离娄上》说:“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孟子的“故”,与荀子的“伪”意思差不多。但“故”字这样用法,比较不容易误会。
《世说》述:“徐孺子年九岁,尝月下戏,人语之曰:‘若令月中无物,当极明邪?’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无此必不明。’”前“明”字是光线的强,后“明”字是看得清楚。两个“明”字意义完全不同,不应该相提并论。
(第二)意思相同而话不相同。这种情形似乎不会引起误会。但其实不然;因为不少的无谓的争辩由它引起。例如:
(甲)“要法律上和道德上的责任有意义,必须人们做事能够自由。”这个话所谓“自由”就是“自决”—自己决定—的意思,并不是“‘无因而忽然如此做’的意思”。假如咬定道德责任所需要的自不是自由决,也会发生无益争论。
(乙)我曾听见一个外国老教士和一个乡下人争辩说中国人拜天不对,应该拜上帝。听这位老教士的口气,他显然不知道中国的“天”字,在用来指所崇拜的对象的时候,就是他的上帝。
(第三)一个话和它所要表示的意思不刚刚相当。这种话不但常常使听的人受骗,并且说话的人自己也常常受骗。例如把一国中比较保守的分子叫做“顽固派”或叫做“稳健派”:顽固派含有坏的色彩,稳健派含有好的色彩,都不是与所要表示的恰好相当。这两种话都已经含了主观的评判在内,并不是仅仅表示事实。政治活动中所用的语言,这类很多。如“人才内阁”,“稳健的主张”等类的话所含的意思往往是比实际所代表的事实多了以外的许多色彩。这种话最会淆乱人家的“听闻”。
(第四)不适用的比喻。用得得法,固然可以助听者的了解;但也容易误用,因为使他们反而疑惑。
《世说》载车胤怕多请教请教谢安会使谢安疲倦。袁羊说,不必虑到这一层,因为“何尝见明镜疲于律照,清流惮于惠风?”。但人的被问难的确是和镜子照影像清水被风吹一样的不费力吗!
英国喀莱尔①(Carlyle)反对代议政体说,假如船长每事都要船员投票公决,一定没有法子使他的船达到目的地。但国民与政府的关系等于船员与船长的关系吗?不用说别的,只想到船员是船长的雇佣,但国民绝不是政府的雇佣那个事实,就知道这个比论是拟不于论了。
(第五)缺乏意思的话。这种毛病可以说不是把话来代表意思(那是应该的),乃是把它来代替意思。例如:
王守仁与罗钦顺书里说:“格物者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正心者正其物之心。诚意者诚其物之意。致知者致其物之知。前三句还勉强可通,后三句实不可解。
邵雍《皇极经世·观物篇》之五十二说:“有日日之物者也,有日月之物者也,有日星之物者也,有日晨之物者也。有月日之物者也,有月月之物者也,有月星之物者也,有月晨之物者也。有星日之物者也,有星月之物者也,有星星之物者也,有星晨之物者也。有晨日之物者也,有晨月之物者也,有晨星之物者也,有晨晨之物者也。日日物者飞飞也,日月物者飞走也,日星物者飞草也,日晨物者飞木也。月日物者走飞也,月月物者走走也,月星物者走草也,月晨物者走木也。星日物者草飞也,星月物者草走也,星星物者草草也,星晨物者草木也。晨日物者木飞也,晨月物者木走也,晨星物者木草也,晨晨物者木木也。”这不过把“日月星晨”四字和“飞走草木”四字做排列(Permutaion),哪里有什么意思。
语言既然有这样误人的能力,所以我们不能不时时预防,尽量少用歧义的字,少说模棱的话。不必过于尊重文章要有变化的修词法则,对于一样的意思,不敢用一样的话代表它。听人说话,要记得不同的话未必有不同的意思。说话不要比所要说的意思说得太少;但也不要说得太多。用比喻固然因为两件事物有相同的地方,但千万不要忘记了它们也有不相同的地方。不要以为所说的话,自己仿佛觉得有意思就够了,要看看所说的话是不是不仅仅的一句话。总而言之,谨慎为妙。因为语言对于思想是有不小的反响的,所以谨慎并不完全是利他的,一半还是利己的。
(原载1927年3月5日《现代评论》第五卷第117期)
唐钺(1891—1987),原名唐柏丸,字擘黄,福建闽侯人。早年就读于英华书院和福州中等商业学校。1911年入北京清华学校,1914年毕业后赴美国留学,先后入康乃尔大学和哈佛大学研究院哲学部心理学系深造,1920年获博士学位。1921年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清华大学心理系教授、系主任,商务印书馆编辑部哲学教育组组长,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第一任所长、研究员。1949年后历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心理系教授,兼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全国政协第二、三、四、五、六届委员。著有《西方心理学史大纲》《唐钺文存》《国故新探》《修辞格》等,译有《人的义务》《功用主义》《论人生理想》《论情绪》《论思想流》《宗教经验之种种》《道德形而上学探本》《心理学原理》《感觉的分析》等。 话亦有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