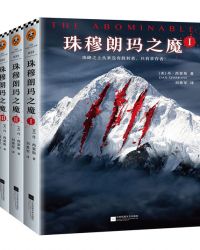第22章 登山者(17)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珠穆朗玛之魔(全集)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巴赫纳先生还是刚刚成立的德国-奥地利登山协会领导人。”西吉尔说。
这句德语就连我都能听懂。我从登山杂志中得知,正是卡尔·巴赫纳倡议把德国和奥地利的登山俱乐部联合在一起。
西吉尔指了指巴赫纳旁边的两个年轻人。“我猜你们从杂志上已经了解到阿图尔·维曾巴赫最近攀登冰川的壮举了……”
比较靠近我们的那个人朝我们的方向点点头。
“……这位是他的登山拍档,尤金·洛温赫茨。”
我知道,这两位年轻人因为设计出了非常短的冰镐而名声大噪,那东西实际上就是冰锤,因此,在短冰镐、登山钉和冰锥(像理查这样爱登山的英国人则把使用这种方法登山的德国人戏称为“悬挂和重击派”)的帮助下,就可以非常快速地登上或许会令我们铩羽而归的冰壁,因为我们这些人在攀登冰壁时都是使用老式登山方式,在冰壁上开凿踏脚处。
“上个星期,阿图尔和尤金只用了十六个小时就沿着直线路线攀上了德朗峰北壁。”西吉尔说。
我太惊讶了,不由得吹了声口哨。仅用十六个小时就沿直线路线爬上了全欧洲最难攀爬的一座北壁?如果这是真的——德国人说起登山似乎从不曾吹牛——那么这两个坐在我右边喝啤酒的男人真可谓开创了登山历史的新时代。
理查噼里啪啦快速地说了一句德语,后来他把这句话翻译给我听:“两位先生,你们有没有把新型冰镐带在身边?”
阿图尔·维曾巴赫把手伸向桌下,拿出了两把短冰镐,它们的斧柄长度还不到我自己那把木柄冰镐的三分之一,斧刃则要尖利和弯曲得多。维曾巴赫把这两件革命性登山工具摆在他面前的桌上,却没有将它们递给我或理查,让我们近距离瞧一瞧。
这倒是无所谓。光是看着这两把短冰锤(这名字比较适合),我就能够想象,这两个人是怎么劈凿出踏脚处,一路上把长登山钉或新式德国冰锥凿进冰山里,以保自身安全,登上了冰雪覆盖的德朗峰北壁。而且,我可以肯定,他们也用到了10爪冰爪——这东西是1908年由英国人奥斯卡·埃肯斯坦发明的,可英国登山者倒是很少用到。现在这些新一代巴伐利亚州冰山攀登者经常使用这种10爪冰爪,他们一路把这些冰爪和短冰镐凿进巨大的冰壁里向上爬。这不光是设计巧妙——简直就是技艺高超。我不知道这么说是否公平,如果这能有任何意义的话。
西吉尔介绍了最后三位登山者——一位是冈特·埃瑞克·里格勒,两年前,也就是1922年,他成功地改造了德国登山钉,使之适用于攀登冰川;一位是卡尔·施耐德,我在杂志上看到过这位年轻人的神奇经历;还有一位是约瑟夫·维恩,这位登山者的年纪比较大,出于某种原因,他把头发都剃光了,他在登山杂志上说他的目标是要带领苏联和德国联合登山队攀登列宁峰和苏联高加索地区其他不可能攀登的山峰。
理查用流利的德语表达了我和他见到这些伟大的巴伐利亚登山者所产生的荣幸之情。这六个受到夸奖的男人——算上布鲁诺·西吉尔正好是七个——根本没有任何反应,连眼睛都没眨巴一下。
理查又喝了一大口装在那种沉重啤酒杯里的啤酒,然后对布鲁诺·西吉尔说:“现在我们可以谈谈正事儿了吗?”
“这可不是像你说的‘谈谈’而已,”西吉尔厉声说,他那巴伐利亚式的礼貌突然间彻底消失,“那是审讯,仿佛我身在英国的法庭里。”
听了他这话我目瞪口呆,可理查只是笑着说:“不要紧。如果我们是在英国的法庭里,那么我肯定戴着搞笑的白色假发,而你呢,肯定是在被告席上。”
西吉尔蹙着眉。“我只是一个证人,迪肯先生。只有被告——往往是有罪的人——才会在英国法庭的被告席中,不是吗?证人就坐在……坐哪儿呢?应该是法官旁边的一把椅子上,是不是?”
“是,”理查表示赞同,他依旧笑眯眯,“我说得不对,予以纠正。我们用德语说话,以便你所有的朋友都能听懂,可以吗?稍候我会翻译给杰克听。”
“不用了,”布鲁诺·西吉尔说,“我们说英语。你的柏林口音真叫我这听惯巴伐利亚口音的耳朵难受。”
“抱歉,”理查说。“不过我们都认为你是唯一一个看到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勋爵和他的登山同伴科特·梅耶在雪崩中丧生的证人,不是吗?”
“迪肯先生,你到底是仗着什么权柄,在这里审讯……或者说是问询我?”
“一点儿权柄都没有,”理查平静地说,“我和杰克·佩里到慕尼黑来找你谈话,全是要帮布罗姆利夫人个人一个忙。她的儿子在登山时突然去世,她只想知道更多细节而已,这完全可以理解。”
“帮布罗姆利夫人一个忙,”西吉尔说,即便那浓重的德国口音也掩不住他声音里的挖苦意味,“依我看,帮了这个忙,肯定能得到一大笔钱。”
理查依旧保持微笑,等待着。
终于西吉尔砰地一摔他那空空如也的石头啤酒杯,招呼一旁恭候的服务员再来一杯,然后嘟囔着说:“关于那次事故,我早就把我所见到的一切细节都对德国《登山杂志》说了,还就此写了信给你们的皇家地理登山俱乐部杂志。”
“那只是一篇非常简短的报告。”理查说。
“那次雪崩是瞬间发生的,”西吉尔说道,“你参加过马洛里早前率领的两次珠峰探险,你见过雪崩吧?或者起码在阿尔卑斯山时也该见识过吧?”
理查点了两下头。
“那你就该知道,不管是一个人,还是许多人,这一秒他们还在那里,等到下一秒他们就消失了。”
“是的,”理查表示同意,“可很难了解清楚珀西瓦尔勋爵和那个叫梅耶的人到底在山上做了什么。他们为什么到那里去?为什么你和你的六位德国朋友也在那里?你告诉《法兰克福日报》,当你在定日镇听说有一个奥地利人和一个英国人在西藏定日镇租了牦牛,买了登山装备,你们就改变了路线,还说你和你的朋友们纯属好奇,才会向南去调查一番……仅此而已。”
“我对报纸说的都是实话,”西吉尔说,语气有些不屑,“你和你的美国同伴不远万里来到慕尼黑,就是为了听我确认我所说过的话?”
“你从前的证词意义不大,或者说根本没有意义,”理查说,“如果你能帮助我们找到遗漏的事实,那么布罗姆利夫人,也就是小珀西瓦尔的母亲,将会非常感激。她心心念念想的就是这事。”
“你到这里来,就是为了帮一位老太太了解更多……你们英国人怎么说来着?……关于她儿子之死的细节。”西吉尔说,那表情简直就是在冷笑。我真惊讶,理查居然一直都没发脾气。
“那位科特·梅耶是不是来自你的……哦……登山队?”理查问。
“不是!在定日镇的藏人告诉我们他的名字之前,我们从没听说过此人……那些藏人还说他和英国的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勋爵骑马向东南方向的绒布寺去了。”
“这么说梅耶根本不是个登山者?”
西吉尔喝了一大口啤酒,打了个嗝,耸耸肩。“我们谁也没听说过科特·梅耶这个人。我们只从那些和他说过话的定日藏人口中听说过他的名字。坐在这张桌子上的人几乎认识每一个德国和奥地利的真正登山者。是不是,我的朋友们?”他的这个问题是在问他的德国同伴。他们点点头,几个人还连连称“是”,虽然刚才西吉尔才和我们说,他们都听不懂英语。
理查叹了口气。“你宁可让我问你各种问题,让你感觉像是在法庭里,西吉尔先生,你为什么就不能把你知道的事儿和盘托出呢,说说你们为什么会在通往珠穆朗玛峰的路上?你们看到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勋爵和科特·梅耶在干什么?或许你们甚至还知道为什么这两个人的马会被枪杀。”
“等我们到那里的时候,他们的马已经死了,”西吉尔说,“如你所知,迪肯先生,一号营地是一片崎岖不平的冰川堆石地区。或许他们的马都摔断了腿。也可能是布罗姆利先生或梅耶先生发了疯,所以把马都打死了。谁知道呢?”这位德国登山者又耸耸肩。
“至于我们‘跟踪’布罗姆利和梅耶两人到绒布冰川去的原因,”西吉尔接着说,“让我来告诉你一些我没对任何人说过的秘密。我和我的六个朋友只是想去见见乔治·马洛里、诺顿上校和其他登山者,我们听说他们那年春天去登珠峰了。很显然,因为我们旅途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中国,所以一直没听说马洛里和欧文已经遇难,甚至不知道他们的探险队有没有抵达那座山。不过,当定日镇的藏人告诉我们,布罗姆利已经出发去了他们口中的珠穆朗玛峰,我们就打定主意,就像你们英国人和美国人常说的,‘为什么不呢?’于是,我们就去了东南方,而没有返回北方。”
不知什么原因,西吉尔的德语口音开始在我听来非常刺耳。
“当然了,”理查说,他的语气文质彬彬,却显得坚持不懈,“当你们看到诺顿和马洛里的大本营已经废弃,只剩下一些帐篷碎片和尚未吃过的废弃罐头,你肯定就明白,登山队已经离开了。那为什么还要继续沿着冰川向上攀登北坳和更高的地方呢?”
“因为我们看到两个人正从北部山脊下山,而且显然他们碰到麻烦了。”西吉尔厉声道。
“你们在大本营就能看到那两个人,那里距离珠穆朗玛峰可有12英里啊?”理查问,听他的语气,与其说他是在质问,倒不如说只是好奇罢了。
“不,不!发现死马之后我们就去了二号营地,而且认为我们此前从未听说过的布罗姆利和那个叫梅耶的人可能碰上麻烦了。我们从马洛里的二号营地看到他们在山脊线上。我们用的是德国精密望远镜,蔡司望远镜,那可是世界上最棒的。”
理查点点头,认可这话属实。“这么说,你们一看到北坳下方1000英尺处废弃的马洛里三号营地,就搭建了你们自己的营地,然后爬上了北坳。你们有没有用到诺顿上校的探险队在那最后100英尺垂直冰壁上留下的绳梯?”
西吉尔手指一摇,否定了这个假设。“我们没有用到他们的梯子,也没有用固定绳索。我们用的是我们自己攀登冰川的冰镐和其他德国登山技术,才爬上了那面冰壁。”
“嘉密·赤仁说看到几个你们的人顺着桑迪·欧文的绳梯从北坳上下来。”理查说。
“嘉密·赤仁是谁?”西吉尔问道。
“就是你们遇到的那个夏尔巴人,那天就是他举着左轮手枪对准了三号营地附近的地方。你还把布罗姆利之死的事儿告诉了这个人。”
布鲁诺·西吉尔耸了耸肩,冷笑一声。“夏尔巴人。你们听着,夏尔巴人满嘴谎言。我和我的六个朋友根本就没靠近那架都已经磨损的绳梯。你们也看到了,根本就没那个必要。”
“这么说,你们纯粹是为了到中国探险,可你们还把登山和登冰川的设备带在身边。”理查说着拿出烟斗,开始往里面塞烟叶。这个巨大房间里的烟雾已经浓得不能再浓了。
“中国有很多高山和陡峭的山口,迪肯先生。”西吉尔此时的语气已经不是充满敌意,而是有些瞧不起人了。
“我无意打断你的叙述,西吉尔先生。”
西吉尔又耸耸肩。“如你所说,我要叙述的已经不多了,迪肯先生。我和我的朋友去攀登北坳,是因为我们看到那两个从北部山脊下来的人有麻烦了。一个似乎出现了雪盲症,被另一个人牵引着,几乎可以说是另一个人在搀着这个人了。”
“这么说你们是在北坳扎营了?”理查说着点燃了他的烟斗,嘬了几口,让烟叶烧着。
“没有,”西吉尔大声说道,“我们没在北坳扎营。”
“嘉密·赤仁看到,在北坳的那道壁架上至少有两顶帐篷,而诺顿和马洛里的四号营地曾经就在那里。”理查说。他的声音听上去又一次是好奇的意味多,质问的意味少。他就是在帮一位伤心母亲的忙,探明实情,从而弄清她儿子失踪的团团迷雾,让她得到慰藉。
“那些帐篷是布罗姆利的,”西吉尔说,“一个已经被高山上的狂风吹烂了。就是因为这风,退下山来的布罗姆利和梅耶才被迫离开了山脊线,到了五号营地上方的冰壁上,那里的积雪很不结实。我用英语和德语向他们喊话,叫他们不要去那面冰壁,因为那里的雪太不稳固了要不就是风太大了,他们没听到我的话,要不就是他们压根儿没想搭理我。”
理查微微扬了扬两道浓眉。“你们的距离已经近到可以和他们讲话了吗?”
“是向他们喊话,”西吉尔说,他的语气分明是对反应迟钝的儿童说话的语气,“我们之间的距离有30米,或者更远。随后,他们脚下的雪开始摇晃,然后大量积雪呼啸着,从那面冰壁向下坠了数千英尺。他们在这次雪崩中彻底消失了,我没有听到他们发出任何声音。”
“你们就没试着到下面去看看他们是不是还活着?”这声音里没有夹杂着任何谴责的意味,可布鲁诺·西吉尔依旧很生气,怒目而视,仿佛受到了多大侮辱似的。
“根本就不可能下到那面冰壁下面去。根本就看不到那面山壁的本来面目了。山壁上的雪全都被雪崩卷走了,很显然小布罗姆利和科特·梅耶都死了,被埋在数千英尺山下几吨重的雪中,没命了,完蛋了。”
理查点点头,仿佛他完全能够理解。我还记得,他曾经眼见着乔治·马洛里攀登通往北坳的那道长雪坡,并且提醒他不要这么做。1922年,在珠穆朗玛峰的一次雪崩中,这座雪坡夺去了马洛里七位挑夫的性命。
“这些事在你给报纸的报告中都写了,其实你只是重复了一遍,说什么通往六号营地的山脊上狂风大作,珀西瓦尔勋爵和梅耶先生不得不退到北壁的岩石滩和冰雪上,以便能够下到五号营地,”理查说。
“是的,一点儿不错。” 珠穆朗玛之魔(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