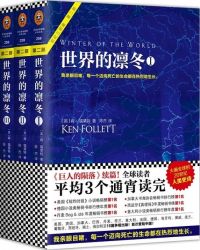第76章 1942年,华盛顿(3)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世界的凛冬(全集)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石墨是制造铅笔笔芯的原材料,石墨散发的粉末覆盖了整个墙面和地板。所有在壁球场的人都像矿工似的黑着脸,身上的白色实验服也都积上了厚厚的一层灰。
石墨不是爆炸物的原料——把它用在核反应堆上是为了抑制核反应堆的放射性。不过反应堆上的一些砖块上钻了小洞,小洞里充满了能传播中子的二氧化铀。反应堆里有十根放着操纵杆的管道,操纵杆由十三英尺长的镉制造而成,镉对中子的吸收力比石墨还要强。目前,这些操纵杆保证着反应堆的平安无事。如果把它们抽走,反应堆就要爆炸了。
铀元素每时每刻都在散发着致命的射线,不过石墨和镉把这些射线吸收干净了。不断“滴答”响的计数器和默不作声的圆柱形描笔式记录器,都在对射线的能量进行计算。格雷格所在通道旁的控制器和仪表,是这里唯一能散发出热量的东西。
格雷格参观反应堆的这天是12月2日,星期三,风很大,天气非常冷。这天,预计反应堆将第一次达到临界值。格雷格代表格罗夫斯准将观摩这次实验。有人问他,格罗夫斯为什么不亲自来。格雷格暗示,格罗夫斯准将生怕爆炸,遇到不测,所以派他来。这么说让他感到非常高兴。事实上,格雷格承担了一项更为邪恶的任务。他将对所有参加这个项目的科学家进行初步评估,判断谁也许会造成安全上的风险。
曼哈顿计划的安保工作非常艰巨。项目的领导者都是些外国人。参加项目的美国人也大多是共产党人或有许多共产党朋友的左翼分子。如果把全部可疑的人都解雇的话,就没人为这个项目干活了。格雷格的任务就是要把那些最具有安全风险的科学家剔除。
恩里克·费米大约四十岁。他个子矮,鼻子小,没多少头发。观察惊人的科学实验时,费米总会露出会心的微笑。他穿着一件背心,外面套着大衣。上午,他下令实验开始。
他下令技师在反应堆里只留一根操纵杆。格雷格问:“一下子拿走这么多吗?”他觉得这么做似乎太猛了一些。
站在格雷格身边的科学家巴尼·麦克休说:“昨天晚上我们就拿过这么多,反应堆运行得非常好。”
“很高兴听你这么说。”格雷格说。
矮胖的大胡子麦克休在格雷格的嫌疑名单上排得很靠后。他是个美国人,对政治没有兴趣。他身上唯一的可疑之处,是他的妻子——她是个英国人,这不算一个优点,但因此叛国似乎也不大可能。
格雷格以为操纵杆的进出需要一种复杂的装置,实际上比他想象得要简单。技师循着一个靠着反应堆的扶梯攀爬上去,爬到一半时用手将操纵杆从反应堆里直接取出来。
麦克休告诉格雷格:“我们本想在阿尔贡森林做这个实验的。”
“那是哪儿?”
“在芝加哥西南二十英里处,是个人迹罕至的地方,不会造成任何破坏。”
格雷格忍不住颤抖了一下。“你们为什么改变了主意,在五十七街的市中心做这个实验?”
“雇来的建筑工罢工了,我们只能自己建。这样一来,反应堆就不能离实验室太远。”
“你们想把芝加哥所有人的命都搭进去吗?”
“应该不会出这种事。”
格雷格原本觉得不会有事,但现在他的想法变了,他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几步。
费米正监视着一台报告实验各个阶段射线水平的监视器。他下令把最后一根操纵杆拿出来一半,显然实验最初几个阶段都按照计划顺利地进行了。
项目组准备了一些安全措施。如果射线强度升得过高的话,一根悬挂在反应堆上的加重杆会自动落下。为了防止加重杆失灵,一根用绳子系在过道栏杆上的横杆会将其取代,一个看上去很傻的年轻物理学家拿着把斧子站在栏杆旁,在危机来临时会把绳子割断。
项目组的最后一招,是安排在房顶附近的三人敢死队,他们站在建造房子时留下的电梯平台上,拿着大罐硫酸镉,准备在射线强度突然失控时,像浇灭篝火一样倒在反应堆上。
格雷格很清楚,中子的数量会在千分之一秒内成倍增长。费米说增长的速度没那么快,可能要好几秒才会成倍增长。如果费米的判断正确,那实验就没问题了。如果他的判断错了,那么拿着罐子的敢死队和拿着斧子的物理学家就会在眨眼间汽化。
在格雷格耳中,滴答声趋于平稳。他急切地看着拿计算尺的费米。费米看上去很开心。格雷格想,费米这样很自然,如果发生不测的话,厄运会降临得非常快,在场的人来不及想任何事就会随着反应堆的爆炸而灰飞烟灭。既然这样,还担心什么呢?
滴答声的频率变慢了。费米笑了笑,命令技师再把操纵杆拉出来六英寸。
更多的科学家穿着冬天的厚重冬装——大衣、帽子、围巾和手套——登上了台阶。格雷格对安全措施的匮乏感到吃惊。没有人检查这些科学家的证件——这里的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是为日本效命的间谍。
在这些人中,格雷格认出了早已名声在外的齐拉特。莱奥·齐拉特身材高大,体格健壮,圆脸,有一头厚重卷曲的头发。他是个理想主义者,认为原子能可以把人类从苦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看到原子能将用于战争,他的心情很复杂,但为了世界的永久和平,他还是毅然决然地加入了这个项目组。
操纵杆又被拉出来六英寸,滴答声的频率更快了。
格雷格看了看表,这时是十一点三十分。
突然一声巨响,所有人都跳了起来。麦克休说:“该死。”
格雷格问他:“发生什么了?”
“哦,我明白了,”麦克休说,“射线的强度触发了安全机制,放下了紧急操纵杆,没什么大不了的。”
费米大声宣布:“我饿了,大家吃午饭吧。”他的意大利式英语非常难懂,格雷格听成了“我是匈牙利人,我们去午摊吧”。
这时候他们怎么还能想着午餐呢?但没人跟他争辩。“谁都不知道实验需要多久,”麦克休说,“也许要整整一天,趁可以去吃饭的时候,赶紧去吃吧。”格雷格被他们不紧不慢的态度急坏了,气得直想大吼大叫。
所有的操纵杆被重新插进了反应堆,锁进其既定位置。然后所有人都离开吃饭去了。
大多数人去了芝加哥大学校园里的餐厅。格雷格买了个烤奶酪三明治,坐在名叫威廉·伏龙芝的物理学家身旁。大多数物理学家都穿得很不讲究,伏龙芝却与众不同,他身着一套绿西装——扣眼、领衬、肩垫、肘垫和袋盖,都用棕色麂皮缝制。在格雷格的嫌疑人名单中,伏龙芝排得很靠前。他是德国人,但在30年代中期去了伦敦。他反对纳粹,但不是共产党——他是个社会民主党人。他娶了个搞艺术的美国女孩。吃饭时,和伏龙芝聊了一阵后,格雷格觉得没理由怀疑他:他似乎很喜欢住在美国,除了事业,对其他都兴趣不大。但谁也说不清,一个外国人内心的信仰究竟是什么。
吃完午饭,格雷格站在废弃的体育场上,看着千余个空旷的坐席,想到了乔治。他没有告诉任何人,自己有个儿子——甚至对玛格丽特·科德里都保密,即便他很享受和她的亲密关系——但他想告诉自己的母亲。
不知为何,他感到非常骄傲——除了简单地让杰姬受孕之外,他什么都没为这个男孩做过,但他还是感到骄傲。他尤其感到兴奋。他似乎在开始某种冒险。乔治要长大,要学习,要改变,将来还会变成一个真正的男人。格雷格会一直守护着他,观察着他的成长,为他取得的成就而高兴。
下午两点,科学家们重新集合。走道里,监视仪器的科学家大约有四十来人。实验被小心地重置到了他们饭前的状态,费米不时过来看一眼仪器上的数字。
过了一会儿,他说:“把控制杆拉出来十二英寸。”
滴答声变快了。格雷格期待声音像上午一样逐渐平稳下来,但那种效果并没出现。滴答声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最后发展成持续不断的咆哮声。
格雷格发现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转向了描笔式记录器,这才意识到射线强度已经超过了计数器的最大值。好在计数器的数值范围是可调的。随着射线强度的增大,数值范围也不断扩展。
费米举起手,所有人都不说话了。“反应堆到了临界状态。”接着,他笑了——却什么都没做。
格雷格想尖叫,该死的,赶紧关掉吧!可费米仍然在不紧不慢地看着描笔式记录器。费米的身上有种不怒自威的气质,没人敢挑战他的权威。链式反应发生了,但还在可控范围之内。他让反应发生了一分钟,接着又是一分钟。
麦克休喃喃地说:“我的上帝啊!”
格雷格不想死。他的理想是当上参议员。他想和玛格丽特·科德里一直腻在一起。他想看到乔治上大学。我的人生还没过完一半呢,可不能现在就死,他想着。
最后,费米命令把控制杆推回反应堆内。
计数器的滴答声慢下来,最后完全停止了。
格雷格的呼吸恢复了正常。 世界的凛冬(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