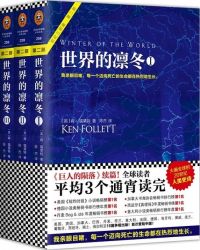第49章 1940年,阿登高地(1)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世界的凛冬(全集)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埃里克·冯·乌尔里希在堵车中度过了法国战场的前三天。
埃里克和朋友赫尔曼·布劳恩是第二装甲兵团附属医疗队的成员。通过比利时南部的时候,他们没有目睹任何军事行动,只看到了延绵不断的山和树林。他们听说这一带是阿登高地。他们行进在狭窄的公路上,有些地方甚至没有铺沥青,一辆抛锚的坦克很快造成了五十英里的堵车。他们被困在队列中,滋味比行军还要难受。
赫尔曼布满雀斑的脸上流露出不耐烦的神情,他用别人听不到的声音轻声对埃里克说:“简直他妈的太傻了。”
“你是希特勒青年团的一员——不应该说这种话,”埃里克轻声说,“要对元首有信心。”他并没有真生气,只是给赫尔曼一点提醒。
动起来的滋味也不好受。他们坐在军用卡车的后地板上,公路上尽是树根和弹孔,卡车在行进时颠个不停。埃里克希望能马上投入战斗,以便脱离该死的卡车。
赫尔曼提高了声调:“我们到底是来干什么的啊?”
坐在副驾驶座上的医疗队队长雷纳尔·韦斯医生说:“元首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他的决定永远是正确的。”韦斯表情一本正经,埃里克却似乎从他的语调中听到了一丝嘲讽的味道。黑发、戴眼镜、身材瘦削的韦斯少校经常嘲讽地议论军队和政府,但旁人又无法从他谜一般的话语中找到任何把柄,因此谁都不曾举报过他。另外,军队战时也需要韦斯这种技术精湛的名医。
车厢里另外两个医务兵都比埃里克和赫尔曼年龄大。名叫克里斯托弗的医务兵对赫尔曼的问题有独到的见解:“法国人多半没料到我们会打到这里,毕竟这里的地形太复杂了。”
他的朋友曼弗雷德说:“我们恰好可以做到出其不意,没遇到多大抵抗便直扑法国边境。”
韦斯嘲讽地说:“你们的策略真是让我醍醐灌顶,我终于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上这里来了。”但他没说他们错了。
让埃里克惊讶的是,直到这时还有那么多人对元首缺乏信心。他的家人仍然对元首的胜利视而不见。他的父亲一度曾经很有权势,现在却是个卑微的小人物。沃尔特不但不对攻克蛮荒的波兰感到高兴,反而长吁短叹着波兰人民的遭遇——他一定是偷听敌台得知了他们的遭遇。这会给全家人惹上麻烦的——不向纳粹设在街区的监管员报告的话,包括埃里克在内的全家人都会因此而获罪。
埃里克的母亲也好不到哪里去,她常会拿个放着熏鱼和鸡蛋的小包消失上一阵子。她不做什么解释,但埃里克可以肯定母亲是把小包拿给洛特曼夫人了,洛特曼夫人的犹太丈夫已经被取消了行医的资格。
尽管如此,埃里克还是把绝大部分军饷都寄回家里。他知道如果不寄钱回家的话,他的父母就要受冻挨饿了。埃里克不赞成父母的政治观点,但是他爱他们。他父母也是一样,他们对埃里克支持纳粹的政治态度非常气愤,但打心眼里爱着他。
埃里克的妹妹卡拉本希望能和埃里克一样成为一个医生,她在得知医生在当今的德国只能是男人的职业时曾感到非常愤怒,不过她已经接受了现实,经过培训当上了更适于女孩的护士。卡拉和埃里克一样,也在用微薄的工资支援着父母。
埃里克和赫尔曼本想进步兵营。他们想象中的战争是面对敌人,杀死对方或为祖国牺牲。但他们现在谁都杀不了。他们都上了一年的医学院,所受的培训是军队的宝贵财富,因此他们都当上了医务兵。
5月13日,在比利时的第四天中午之前,围绕着他们的只有坦克和卡车的轰鸣声。这天中午,他们开始听到一种更响亮的声音。轰炸机盘旋在他们头顶,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进行轰炸。呛人的烟味使得埃里克的鼻子一阵阵地抽搐着。
下午,他们在俯瞰河谷的高地上休息。韦斯少校说下面是默兹河,他们已经到了色当的西面,因此他们已经进入了法国的领土。德国空军的战斗机一架接一架地从他们头顶飞过,对他们前面几英里河岸上散布的村庄进行轰炸,那里也许隐藏着法国的防御阵地。烟雾从被不计其数的炮火击中的民房和农舍喷涌而出。炮火一阵连着一阵,埃里克为被困在炼狱里的所有灵魂感到惋惜。
这是埃里克目睹的第一场战事。不久之后他就将投入战斗。到时,也许会有些年轻的法国兵站在安全的制高点,为战死受伤的德国兵感到伤心。想到这里,埃里克的心像打鼓似的一阵兴奋。
向东眺望,景物影影绰绰,埃里克看到战斗机像空中的小墨点一样四处舞动,烟柱不时腾起,这时他才深切地意识到战争就在眼前,就在离自己只有几英里的河岸上展开。
过了一会儿,空袭结束了,战斗机折转向北。从他们头顶飞过的时候,机翼摆动了几下,像是在向他们祝福“好运”。
在离埃里克不远的一块通向默兹河的平地上,德军的坦克相继投入了战斗。
他们离敌人还有两英里,但法国炮兵已经开始从城里对他们发起炮击了。埃里克非常吃惊,他没想到有这么多法军的炮兵会在轰炸中幸存。炮火如织,埃里克听见炮弹穿过田野的呼呼声和落地时泥土四溅的声音。他看到一发炮弹正中在坦克上,烟雾、金属和人体碎片齐齐从坦克的炮口中喷射出来。埃里克不禁一阵心悸。
法军的炮火没能抵挡住德军的前进。坦克群不断地从河岸向被韦斯称为唐奇里的小镇东面进发。坦克后面跟着乘着卡车或步行的步兵。
赫尔曼说:“空袭还远远不够。我们的炮兵在哪里?我们需要炮兵打掉镇上的炮兵阵地,使坦克和步兵可以跨过河流,在河对岸建立桥头堡。”
埃里克想扇他耳光,让他闭上那只爱抱怨的嘴。马上要投入战斗了——参战士兵必须保持积极的心态!
韦斯却说:“布劳恩,你说得对,但我们的弹药车还堵在阿登高地上。现在我们只有四十八颗炮弹。”
一个红脸上校从后往前跑过队列,向队列里的士兵大喊:“继续前进,继续前进!”
韦斯少校指着前面说:“我们将在东边的那个农庄建立起战地医疗站。”埃里克看到那是幢离河八百码的灰顶矮房。“很好,我们出发吧!”
他们跳上军用卡车,乘着呼啸的卡车下山,到了平地以后向左转入了一条颠簸的机耕道。埃里克很想知道德军会拿房子被充当战地医疗站的那家人怎么办。他觉得德军会把那家人赶走,如果胆敢惹麻烦的话,应该会把他们枪毙吧。但两军对垒之间他们又能去哪儿呢?
他根本用不着担心:这家人早就离开了。
根据埃里克的观察,农庄离战火最激烈的地方只有半英里。他觉得在离敌人这么近的地方建立战地医疗站根本没道理。
“抬担架的,赶快把担架抬到战场上,”韦斯叫道,“等你们回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把医疗站布置好了。”
埃里克和赫尔曼从医疗储备车上拿了一副卷起的担架和一个急救包,风风火火地朝战场上冲了过去。克里斯托弗和曼弗雷德跑在他们前面,十来个战友跟在他们身后。埃里克高兴地想,这是一个成为英雄的大好机会。他一定要做个在战火面前保持镇静的战斗英雄,而不会像有些软蛋一样被炮火吓得屁滚尿流,找个防空洞躲起来。
他们冲过田野,跑到河岸上。这段路并不短,要把伤者从河边抬回医疗站似乎困难重重。
他们经过几辆被击毁的坦克,但坦克上已经没有了幸存者。埃里克把头移开,尽量不去看变形的金属上烧焦的人体残骸。他们周围有法军的炮弹飞过,但并不算太猛:河边的防御已经减弱了许多,大多数法军的大炮都被德国的轰炸机端掉了。但这是埃里克第一次经历被人炮击的状况,他孩子般用双手遮住眼睛,却还是一个劲地拼命往前跑。
这时,一颗炮弹炸在了他们的行进路线前。
一声炸响,土地像被巨人踩在上面一样抖了三抖。克里斯托弗和曼弗雷德被击个正着,埃里克看到他们的身体像是失重了一样被炸得飞了起来。炮弹的冲击波把埃里克撂倒在地。他面朝上躺在地上,地上的灰泥雨点般落在他的脸上,不过他幸运地没有受伤。他挣扎着站起身,面前躺着克里斯托弗和曼弗雷德血肉模糊的尸体。克里斯托弗像个被撕碎的破娃娃一样,四肢被拧断了。曼弗雷德的头颅从身体上分离,掉在自己穿着靴子的双脚旁。
埃里克吓傻了。在医学院,他还没处理过断肢和流血的尸体。他只见过解剖教室里风干的尸首——学生们每两个人分到一具,埃里克和赫尔曼分得一个老妇干枯的尸首——除此之外,他就只见过手术台上被切开的活人身体了。但无论哪个都没有战友突然间被炸开的尸身给他带来如此巨大的冲击。
他只想快点往回跑。
埃里克转过身。他满心都是惧怕,别的什么都顾不上了。他开始朝他们来的路往回走,向着远离战场的森林走去。他的脚步很坚定。
赫尔曼救了他。他挡在埃里克身前说:“别犯傻!你想去哪儿啊?”埃里克没有停下,想从赫尔曼身边绕过去。赫尔曼照着他肚子就是一拳。埃里克弯下腰,跌坐在地上。
“别想走,”赫尔曼急切地说,“你会因为开小差被枪毙的!赶快振作起来!”
埃里克在调整呼吸的时候恢复了理智。他不能逃跑,他不能当逃兵,他意识到自己必须留在这里。他渐渐用意志战胜了恐惧,缓缓站起身来。
赫尔曼警觉地看着他。
“对不起,”埃里克说,“我吓坏了,现在我好多了。”
“那就拿起担架往前走!”
埃里克拿起卷起的担架,把它平衡在肩膀上,转身就跑。
快到默兹河的时候,埃里克和赫尔曼发现他们站在了步兵们之间。一些步兵从卡车后车厢里拿出充气橡皮艇,把它们抬到河边。德军坦克不断对法军的防守阵地进行炮轰,掩护橡皮艇下水。恢复了斗志的埃里克很快发现这是场注定打不赢的战斗:法军藏在墙壁后面或是躲在建筑物里,德国的步兵却暴露在河岸上。橡皮艇一入水,就暴露在密集的机关枪火力之下。
河流中上游右拐。步兵只有退出一长段距离之后,才能躲到法军的火力之外。
河岸上已经出现了很多死伤者。
“把这个人抬起来!”赫尔曼果断地说。埃里克按照指示弯下了腰。他们在呻吟的士兵旁打开担架。埃里克按学到的步骤从瓢里给他喂水。伤员脸上有数不清的伤口,胳膊也折了。埃里克猜想他被机关枪击中,但幸运地没有伤及要害。他没看到很多血,因此他们不需要用止血带为伤员包扎。两人把伤员放上担架抬起,开始朝急救站走去。
一路上,伤员不断因为痛苦而大声喊叫。他们停下时,伤员不断催他们“快一点,快一点!”,痛苦地咬紧了牙关。
抬担架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还没走到一半,埃里克就觉得自己手都要断了。但他知道病人正忍着剧痛,只能硬撑着继续朝前跑。
埃里克欣喜地发现,周围已经没有法军的炮火了。法军把所有炮火击中在河岸上,试图阻止德军跨过默兹河。
过了好一会儿,埃里克和赫尔曼才抬着担架回到充当急救站的那幢农舍。韦斯已经把农舍重新布置了一遍,华而不实的家具被搬了出去,地板上标注了摆放病人的位置,餐桌成了做手术的地方。他告诉埃里克和赫尔曼把伤员放在哪儿,接着让他们到战场上再去抬一名伤员。
跑回河岸要容易些。走的是下坡路,担架上也没有伤员。到达河岸时,埃里克担心自己会不会再一次吓破了胆。
他惊恐地发现战事比刚才更为激烈了。河中间有几艘泄了气的橡皮艇,岸上的尸体更多了——德军依然没能到达对岸。
赫尔曼扯着嗓子朝埃里克大喊:“这真是场灾难,先等炮兵来进攻。”
埃里克说:“那样就会让法军有时间加强防守,失去出其不意的效果。我们就没必要跋涉到阿登高地了。”
“但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啊。”赫尔曼仍旧在发牢骚。
埃里克的内心对元首是不是永远正确提出了疑问。这种想法使他削弱了信心,几乎站不稳了。好在战场上没时间给他多想,他们在一个一条腿几乎都被炮弹炸掉的伤兵身旁停住了脚步。伤兵二十岁出头,和他们差不多年纪,一头古铜色的头发,皮肤苍白,脸上都是雀斑。他的大腿下半部分被炸断了,断口血肉模糊。奇怪的是,他出奇地清醒,像期望有天使从天而降般瞪大了双眼,望着他们。
埃里克找到了腹股沟处的止血点,开始帮他止血。赫尔曼拿了条止血带,放在止血点上。之后他们把伤员抱上担架,扛起来往回跑。
赫尔曼是个忠诚的德国人,但他有时候也会暴露出一些负面情绪。埃里克就不一样了,他完全不敢暴露自己的沮丧和无奈,避免降低战友们的士气——这样可以使他远离麻烦。
但他还是不能不想。穿越阿登高地的行动似乎并没有给德军带来预想中唾手可得的胜利。默兹河的防线尽管并不坚固,法军的回击却异常猛烈。埃里克想,他的第一次战斗经历应该不会使自己丧失对元首的信心吧?他对自己会产生这种想法感到非常恐惧。
他不知道东线德军的进展是否比这边快。第一装甲师、第十装甲师和埃里克所在的装甲师齐头并进,第二装甲师已经到了边境,他们一定在默兹河上游展开攻击了吧。
他胳膊上的肌肉一阵阵地疼。
他们第二次回到了急救站。急救站异常繁忙,地板上躺满了呻吟的伤兵,满是血污的绷带扔得到处都是。韦斯少校和助手们忙着诊断一位位断肢的伤兵。埃里克从没想过伤兵会如此集中在这么个狭小的地方。元首谈战争的时候,埃里克从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
这时埃里克注意到自己带来的伤员已经闭上了眼睛。
韦斯测了测伤兵的脉搏,声音沙哑地责难道:“把他抬到谷仓去——别把没救的家伙抬回来。” 世界的凛冬(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