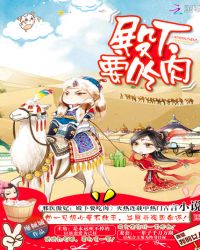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月出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大雪在深夜时分沉沉地压了下来。有一种寒冷的幽香从窗缝里透了进来,裘灏从书页上抬起头来。窗外只有轻微的风声,一半是被紧闭的窗户隔绝了,一半也像是被沉重的雪势压住了。
取暖的铜炉在床边冒着热火气,使得房间里有些闷,隐隐透进来的寒气带着一种新鲜的甘甜,裘灏深深吸了一口气。他将手里的书刊翻到最后一页,那里登载着一则出州军校招生的消息。他又仔细地阅读了一遍。
自毕业后回乡,他已经在家闲了三四个月了。
父亲有意为他在水利部寻一份体面的差事,可是这事办了许久,白花了许多钱,还是没有结果。那些受父亲所托的人,有的说是如今湘州这样正经的差事已经越来越难找了,他们自己的子弟都尚且难办;有的则说,湘州这几年钱都花在军费上了,水利部哪里有钱招人。
这和裘灏原本想的不一样。他以为自己从大学毕业,是必能谋得一份称心的差事,不必让父亲操心的。如今看着父亲为他奔波操劳,他颇不忍心,也颇不服气。
“你不要急,我们慢慢地问着,总能找到一份差事,”父亲总是体谅他的心情,“世道虽难,我们家的境况却是不必担心的。至多你回家来,跟着我做生意。只是可惜了你学的这一身本事。”
一身本事。
裘灏垂着头看那则招生消息。
世道艰难,他的一身本事没有用武之地,又算什么呢?
夜晚很安静,只有窗外的风声回荡着,他将书页折了起来,抬手轻轻丢在一旁的书桌上。
就在这时,他听到了走廊上有轻微的声响。
是脚步声。
他连忙熄了灯,在窗户透进来的一点微弱光线里屏息听着。
那是极轻的脚步声,像是踮着脚尖一般,悄悄来到他门前。
门是反锁了的。为的就是防着毛毛再摸进来。
裘灏已经抓到几回,毛毛跑来他房里睡时,总会趁着他睡着的时候亲他。毛毛的亲吻很轻,像是胆怯,但是如果不打断的话会很漫长,像是依恋。他有几次就是在这样的亲吻里迷迷糊糊地醒过来,伴随着零碎的甜美的残梦。
起初,他还觉得这是毛毛粘他,和小时候一样。直到有一回,他醒过来时清晰地感受到自己身体的变化。毛毛还傻乎乎地在他喉结上甜甜腻腻地亲吻,整个人都拱在他怀里,亲昵地贴着他。
这让他狼狈极了。
毛毛太干净了,不知道这样简单的亲热,就能勾起人许多肮脏的本能。
裘灏左思右想过好一阵,想起傅乐群在他十几岁时同他说过的那些话。那些话无疑是能教人懂事的,可那样的混账话怎么能说给毛毛听呢?
门外窸窸窣窣,是摸索门锁的声音。毛毛显然是受挫了。裘灏听着他在门外摸来摸去,渐渐急躁起来。门被轻轻地敲响了。
裘灏立刻心虚地裹着被子躺下,自欺多过欺人地闭上眼睛。
敲门声很轻,然而一直没有要停的意思,就像毛毛那些轻而绵长的亲吻。
裘灏紧锁眉头,烦躁地叹了口气。
有轻微的“喀嚓喀嚓”声,像是毛毛抓住门锁晃了两下,终于静了下来。
等了一会儿,确实没动静。裘灏睁开眼,轻轻坐起身来,却没有听到毛毛离开的声音。又过了片刻,他听到了轻微的抽气声。
这抽气声他很熟悉,是毛毛压抑哭泣时会发出的声音。
以往毛毛并不是这样的,小时候,他哭起来总是惊天动地,脸涨得通红,呜哇呜哇的。
也许是因为长大了,他现在哭起来也像个大孩子了,垂着头,长长的睫毛落下来,掩着泪珠。肩膀微微地抖动,胸口微微的起伏,却哭不出声,只有呼吸间无法抑制的抽气声,压抑地吐露着他的感伤,却更让人觉得心疼。
裘灏迟疑了一下,翻身下来,去把门打开了。
毛毛站在门外,只穿了一件白棉布衣,看见他的同时,发出了一声委屈的呜咽。
“毛毛,”裘灏赶紧把他抱了进来,“你怎么没披上衣服?”
门板挡住了走廊上的寒意,裘灏摩挲着毛毛颈后,觉得他肌骨都被冷风浸透了。
“傻毛毛。”他心疼地把他裹进怀里,拉起被子来把两个人严严实实地盖住。
毛毛在他怀里发着抖,连牙齿都在打战,呼吸间还带着潮湿的泪意,都扑在他颈子里。
“别哭了,毛毛,”裘灏满心的愧疚,“哥哥不该锁门的。”
天寒地冻,外面那么黑,那么冷,他跑过来时,一定是满心的无忧无虑,带着小孩子的淘气和俏皮,以为自己一推门就能扑到哥哥身边去,从没想过哥哥会把他锁在门外。
裘灏心疼得不知该怎么弥补,只有不断地替他拭去脸上的泪,低低地向他保证:“毛毛别哭了,哥哥再也不会锁门了。”
这句话像是安抚了毛毛,他轻轻“嗯”了一声,像是忍耐不住的委屈,又像是按捺不住的撒娇。
“哥哥,我头疼。”他喃喃了一句,便像是哭倦了一样,低头又往裘灏怀里拱了拱。
裘灏抱紧了他,在他额发上轻轻吻了一下。
夜愈来愈深,雪愈来愈重。
裘灏总是不能睡得很沉,半梦半醒地,疲惫倦怠地,觉得自己仿佛满怀里抱着取暖的铜炉。铜炉有些淡淡的香甜味,越来越热得烫手。
他费力地睁开眼睛。
是毛毛在他怀里,浑身滚烫。
糟了,他立刻反应过来,毛毛发烧了。
他想起身,却被毛毛死死扣住了。他这才发现毛毛是整个人缠在他身上的。也许是因为病痛不适,毛毛轻轻地、撒娇一般地在他身上蹭着。裘灏猝不及防,被他蹭得也浑身火热起来。
“毛毛。”裘灏抬起手臂,想把他推开。
“嗯。”毛毛像是烧得迷糊了,发出粘腻的哼声。他几乎是半趴在裘灏身上,觉察了裘灏要推开他似的,抗议一般地贴得更紧了。
裘灏立刻意识到毛毛也不仅只是发烧了而已。他心里轻轻一跳。
毛毛连呼吸都是火热的,身躯柔韧,每一个微小的动作都显得天真而坦白。
少年的腰肢像初春的垂柳一样柔,气息甘冽得像茉莉熏的酒。那柔情连着酒意,渗透了人的筋骨。清凌凌,麻酥酥,都是醉人的滋味儿,让人满怀里搂着,也仍贪心不足。裘灏脑子一热,竟顺着本能将毛毛往身下一压,重重地呼吸着。
窗外透进来晦暗的清冷的光线,落在他的枕上,带着冰冷的雪意。裘灏渐渐清醒了过来,连忙弓起身体,猛地和毛毛拉开距离。
这一夜终究不得安生。厨房的女工起来给小少爷熬汤药,嬷嬷也被惊动了,端了一盆温水来,反复替毛毛擦拭额头和手心。
裘灏倚在房门边,一言不发地看着。
毛毛小时候一旦病了,他也是多半要陪在跟前的。因为父亲向来不多管,毛毛跟前冷清。也因为温氏向来省事,不敢为毛毛多争一毫一厘。更因为毛毛向来粘他,看不见哥哥就要闹起来,闹得人都近不了身。
女工来喂汤药时,毛毛迷蒙地睁开了眼睛,若有所感似的,向裘灏这边看了过来。
只看了一眼,他就又安心地昏睡过去。
摆早饭的时候,家里上下就都知道,毛毛又病了。这样的事,众人都是习以为常了。裘仕昌听女工说了两句,嘱咐她单给毛毛做点清淡的吃食,甚至没去探望,只顾着同傅乐群忧心裘灏的前程。
“当初送瀚白学水利,我想着是好的。水利是关系民生的大业,怎么会没有工程要做呢?总归以往的工程,也要检查检查,翻修翻修嘛。这怎么不需要人手呢?”
瀚白是裘灏的字,这字也是裘仕昌亲自取的。裘仕昌还是个老派的人。
“我的二叔,”傅乐群对他这番论调不以为然,“人家话已经说得明白了,我看是没什么余地了。你究竟是为裘灏谋前程,还是一心要和他们水利部过不去?他们用不着人,我这里用得着啊!”
裘仕昌立刻不吭声了。
“怎么?二叔你舍不得了?”傅乐群笑嘻嘻,“你放心,我敢在你面前起誓,包管裘灏升官发财,一路顺遂。你恐怕不知道,湘州军现在正是在招读过书、有学问的年轻人。一般的中学生,来了都是个宝贝,何况裘灏是大学生,还是名牌大学出来的。”
“我不求他升官发财,”裘仕昌咳嗽了一声,“我只求他不要虚度时光,能有些作为。”
“那就更对了,现在军队里正是大有作为的时候。保卫湘州一方安宁,百姓安居立业,这不是好事吗?”傅乐群说着,眼神在裘灏身上绕了一弯儿。
裘灏想起那则出州军校的招生信息,竟不由觉得心里一动。
“我不能送他参军,”裘仕昌断然拒绝,“湘州军是什么样子,你自己心里清楚。”
“二叔,瞧你这话说的,”傅乐群突然有些讪讪,“你就看着我,你觉得我是什么样子?”
在湘州,人人都知道坊间的常谈:军队里学不出好人。再好的孩子送进去,出来就是吃喝嫖赌抽烟土。这句话固然有夸张之处,但大体不错。
湘州有尚武的传统,故而湘州军曾经一度是有过赫赫威名的。可惜辉煌了没多久,就逐渐从内里腐败起来,走了下坡路。现在湘州军的大多数士兵都是各种关系补进来吃饷的,许多人并没有打过仗,却是讹钱赖账的一把好手,又是赌场、妓院和烟馆的常客。
就是这些人败尽了湘州军的声誉,使得寻常有些体面的人家,都不肯把子弟送来参军了。
“你信我的,”傅乐群拍着胸脯,“我这新官上任,就要烧他三把火。现在人人都说出州办新式军校,讲究培养有理想、有志气、有真才实学的新式军队。我也认准了这个主意不错。就让裘灏跟着我,必定有他大展拳脚的时候。”
裘灏刚想问几句关于出州军校的事情,就见女工过来说:“大少爷,小少爷醒了,要找你呢。”他立刻站起身要走。
“饭还没有吃,做什么去?”裘仕昌有些不悦。
“我和毛毛一起吃。”裘灏有些敷衍地回了话。
他回房里时是急切的,可看到毛毛时又迟疑了。
毛毛正眼泪汪汪地跟嬷嬷闹脾气,不肯吃药,看见他进来,就信任地伸出手臂,要他坐在自己身边。
他一面怀疑自己怎么当得起这样的信任,一面泰然地坐了下来,向嬷嬷道:“我来喂他。”
“哥儿,他都多大了,叫他自己喝!”嬷嬷一副生气的模样。
毛毛怕苦,喝药向来是难缠的。
可裘灏一端起药碗来,毛毛就乖乖地,等着他一勺一勺把药汤喂到唇边。
嬷嬷一拍巴掌,声音脆响,不知道是欣慰还是气恼:“我去收拾早饭来。”
房间里的铜炉熄了,余温却还没散尽。裘灏将药汤喂完了,才问毛毛:“苦吗?”
“苦。”毛毛皱皱眉。
“毛毛乖。”裘灏表扬地揉揉他的头发。
毛毛撒娇地仰着脸看他,娇憨的神态还有几分小时候的影子。
“干什么?”裘灏看着他被药汤润湿的嘴唇,有些不自在起来。
毛毛一抬手臂,搂住他的脖子,肩上披着的衣服滑落在一旁。
裘灏倾身去拿那件衣服,却不料毛毛同时凑近了。
一瞬间,裘灏觉得自己仿佛吻着了一片欲雨的云彩,清润柔软,残留着一点干净的药香。在有自觉之前,他竟闭上了眼睛,晕头转向地跌进了云彩里,喉结处温热地发痒。
“咣。”
背后传来一声巨响。
裘灏喘息地睁开眼睛,看见毛毛仍茫然地仰着脸,嘴唇殷红,眼睛湿润。
他连忙回身,却见傅乐群又“咣”地一声,把门甩上了。
“裘灏,毛毛,”傅乐群压低了声音,却没能掩饰惊诧,“你们搞什么鬼呢?”
“你三哥见过世面。这也算不得什么大事。”傅乐群叼着烟斗,吞云吐雾。
他把裘灏带来了临湘一处有名的清吟小班。裘灏还没来过这样的地方,有些意外这门庭的奢华与姑娘的骄矜。
“什么畜生不如的人我不认识,什么乌七八糟的事我没见过,”傅乐群轻佻地笑了笑,压低声音,“若不是毛毛病着,今儿我也要带他来的,可我方才这么一看,哟,没一个姑娘的模样儿比得上毛毛。”
“三哥。”裘灏皱起眉,警告地看他一眼。
傅乐群好整以暇地看着他,嘴边带着一点冷笑,笑得裘灏竟有些底气不足起来。
“我他妈的早该明白,这世上哪有坐怀不乱的真君子,你只不过是打定主意要寻一个天仙,”傅乐群意味深长地看着他,“可毛毛是你的弟弟,他长得再好,也是你的弟弟。”
茶杯在桌上一顿,裘灏握着茶杯的手绷紧了,露出筋骨的线条。
自从昨晚那脑子一热,他一直心口纠结,恨不得有人痛骂自己一顿。可等傅乐群真的开了口,他却又受不住心里翻江倒海的羞耻。
“我并没有对毛毛做什么。”他低声辩解。
“你还想对他做什么?”傅乐群也压低声音,“你自己想想!谁家的兄弟是你们这个样子?都亲上嘴了,你还要怎么样?”
“我没有要亲他,就是两下里……一时凑巧了。”
“凑巧?”傅乐群冷笑,“要是当时你对面儿是我,还能这么样凑巧吗?”
裘灏又皱眉看了他一眼。
“别说凑巧了,就是毛毛缠着你亲,你不惯着他,他亲得到?”傅乐群仿佛有意要刺痛他,“要是换我缠着你亲,你能惯着我吗?”
当然不可能。裘灏心知肚明。
他苦笑了一声,觉得自己心头翻滚的热烈、羞耻和愧疚,终于都渐渐地冷却,取而代之的,是平静的理性,和淡淡的自我憎恶。
“我是个畜生。”他话音平淡,仿佛倦怠一般,自己对自己盖棺定论了。
“这就对了,”傅乐群却收起了尖刻,话音又圆滑地流淌起来,“这事其实简单得很,三哥给你找个漂亮的孩子不就完了?管保你就是个人了。”
※※※※※※※※※※※※※※※※※※※※
三哥心里明白,就算把自己切成一盘猪头肉,小崽子也不会愿意下口的。 月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