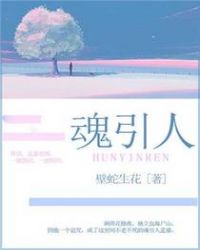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月出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春水才暖,江面上浮着几只白鸭,天色向晚了。
杏红色的晚霞里,虎溪寨的码头旁次第亮起了零星的灯盏,高的是在吊脚楼上,低的是在岸边的船。
一条船赶在余晖里慢慢靠了岸,船是从鹰湖城来的,载着的是两个外乡客。
老船夫听他们的口音,一路相问。
“是哪里人?”
“湘州人。”
“算是近邻。怎么上楚州来?”
“在楚州做事。”
“又怎么要来虎溪寨?”
“养病。”
老船夫把两个人又仔细打量了。
说话的那个身材高大,目光炯炯,有精悍之气,不像个病人。还有一个趴在船舷出神地看着晚霞,体格瘦弱得多,一张脸儿白白的,生得是着实俊俏,像是画儿上走下来的人。
见多识广的老船夫心下了然。这几年有洋人在虎溪寨主持了一家什么疗养院,有许多穿白色袍子的人在这里做事,来往的都是些看上去很体面的城里人。有的人来待一阵,就离开了。也有的人流连不去,或者更甚者,就在那疗养院里走了。
这样的事,老船夫是见过的。曾有一个也很俊俏的小伙子,来虎溪寨时惹得几个寨子里年轻的女孩每晚轮流去他窗外唱歌。他也是很瘦弱,病得很厉害,甚至没能撑到夏季结束。老船夫不由同情地看着船舷旁漂亮的青年。不知怎的,看他那样的漂亮,就觉得他必然福寿不长。向来都是这样的,仿佛只有他年纪轻轻地就去了,留下许多给他唱歌的女孩黯然神伤,才对得起那样出众的相貌。
船只稳稳地在码头靠岸了,他们听见胡琴的声音,还有女人柔声唱的小曲儿。
“胡琴真好听。”船舷旁的青年起身时,向着同伴露出秾丽的笑容,比水面上粼粼的霞光更为动人。连老船夫也被晃了眼。
这个春天里,怕是要唱满九十九个夜晚的情歌了。
“这是哪里的胡琴?”那青年问。
老船夫一摆手:“是妓船上的。”
“什么船?”青年又问。
他的同伴听明白了,像是制止地说:“毛毛。”
老船夫却不介意,向码头旁的几条小船一指:“都是往来的客商、水手们的相好,拉琴的是她们的干爹。”
青年听了,有几分羞赧,却还硬撑着,做出通达世故的样子,天真地向同伴争辩:“我知道这样的事,我见过的。”
他的同伴不再多说什么,向老船夫递来了船钱。给的很丰厚。老船夫连忙推让一番,返还了一部分,却还是留下了比日常所收更多的数目。作为补偿,他殷勤地扶着那羸弱的青年下船,又祝愿他:“这个寨子里好,连洋人都说好,在这里疗养一春,包管你这一年都百病不侵。”
青年明显是个涉世不深的,听了几句好听的话就又动人地笑了起来,低下头来感谢。
“一年?”他的同伴眉头一皱,唇边却仍含着笑,像是开玩笑,又像是真心不悦。
“一生平安。”老船夫立马补上一句。
高大的男人从他手里把青年接了过来,先是握住青年的手指,后又只是抓住他的袖口。
河滩上有一个穿着很体面的人笑呵呵地走过来迎接,那高大的男人忙转身寒暄,把抓着青年袖口的手背在身后。青年有些不安分地偷偷扭着手腕,老船夫一开始以为他是要挣开去,后来才看出他是在想方设法地再握住同伴的手。
他的同伴一直巧妙地躲开他的手指,引得他渐渐急躁起来,幅度很大地甩了一下胳膊表示不满,却又并未真的将同伴的手甩开。
只是片刻后,迎接的人笑着转身,带着他们离开,就见那高大的男人一手提起行李,另一手轻轻一勾,便将青年的手勾在掌中握紧了。青年倏地回身,扬起脸看他,又露出了笑容。
晚霞已经渐渐地淡了。这河滩上再没有什么能与那笑容争辉。
疗养院的食物是西菜,大都是荤食,温潋秋只吃了一点沙拉,几片蘸了奶油的吐司。
大概是因为旅途悠缓,他很饿,却没有什么可吃的东西。
来接他们的人是裘灏在中央军校楚州分校的新同事,是楚州本地出身的军官。就是他介绍温潋秋来虎溪寨的疗养院。他像是看见了温潋秋的食不下咽,逗弄地对他眨眼:“等一会儿,悄悄地,我带你们出去吃。”
果然,疗养院的晚餐收了,他就带着他们出去,到河滩旁的担子前吃宵夜。
担子里卖的食物也就是那么几样,最有本地特色的是烤得金黄油润的小土豆,柔滑细嫩的粉皮,还有包了河鲜野菜的馄饨。温潋秋连吃了好几个小土豆,还添了两盒粉皮,就连裘灏喂过来的带荤馅的馄饨也没有拒绝。
那位楚州军官大喇喇地叫来了许多瓶酒,对着裘灏长吁短叹起来,说他们是同病相怜。等酒喝多了,他就开始大骂,说军委现在就是某些人的天下,不说怎么打仗,就搞一套“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眼下该用人的时候,却把他们扫到楚州任闲职,还把薪水打了折扣。
温潋秋停住了吃,在旁听得愣愣的,看着裘灏。
这些话他从没听裘灏说过。
在鹰湖城的几个月,他确实注意到裘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清闲。对此他是很高兴的,可裘灏却异常沉闷,有时候一人独坐出神,还会发出叹息。
就在不到一个月前,淞浦城沦陷,紧跟着就是整个淞州的陷落,中央军大举撤退。裘灏在家里也没有任何的评价,但他显然是低落的,手指总是突兀地搁在膝头。温潋秋猜想他大概是需要烟酒来发泄,但他在家时向来不沾这些。温潋秋猜想他大概也需要自己来陪伴,但当着温氏和家仆,裘灏也并不与他厮近。
温潋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总是一人独坐的样子,只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悄悄地跑进裘灏的房间,趴在裘灏的怀里,闻着他身上略带颓丧的气息,摸着他下颏上扎手的胡茬,身体发软,却勉力地把手肘撑在他肩头,绵连地在他唇上亲吻。
他不知道该怎么安慰裘灏,只是想起素雪说过的话。
“哥哥,不打仗也没关系的,我们就过风花雪月、琴棋诗酒的日子。”
裘灏还是沉默着,在一点黯金色的灯光下看着他。
风花雪月、琴棋诗酒的日子当然好。可裘灏不是素雪,那不是他的抱负。温潋秋很明白。
“起初我也傻,他们不让我做事,我还发脾气,”那位军官醉醺醺的,还在说,“后来我就想明白了,何苦非得做个劳碌命?有一日清闲,老子享一日清闲。不让我做事,好得很,我什么事都不做了,我就来休养。”
他醉得眼睛都有些睁不开,暧昧地“嘿嘿”笑:“你别看这个寨子偏僻,生活简朴。可是风景好,人好。虽然没有舞厅、戏院,但有的是取乐的地方。白天就是游山玩水,钓鱼,晚上么,就是码头边的吊脚楼和船。”说着,他把手肘搁在裘灏肩头,推了他一下。
裘灏看起来仍旧是清醒的,并没有搭理他,而是看向温潋秋。
“怕什么?都是男人!是不是,弟弟?”那军官也瞥了温潋秋一眼,又用手肘推着裘灏,“这寨子里的姑娘也多是美人,你要是有那个艳福,也许哪天有姑娘看上了你,哎,事情很容易就成了。虎溪寨一带的姑娘和别处可不同,没和这里的姑娘谈过情,你就算不知道情i爱的滋味。”说罢,他不忘抬手往温潋秋面前一招,一视同仁地道:“弟弟也是。”
“你们兄弟都长得好,”他眯缝着醉眼,仔细看了看温潋秋,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只管放心,这寨子里的姑娘哟。”
他像是忘记了愁叹,有滋有味地喝了一杯酒。
虎溪寨的姑娘有多不同,温潋秋很快就领教了。
他和裘灏一起在寨子里散步的时候,就忽然有女孩笑盈盈地走上来,故意踩他一脚。温潋秋很惊愕,紧接着就又被踩了。
“你干什么?”他被踩疼了。
旁边有人在笑,还起哄着让他踩回去。
“毛毛,”裘灏勾着他的肩膀往身旁带,“别欺负女娃娃。”
温潋秋只得算了。
没过几日,他又看见两三个女孩聚在疗养院门口,围着一个年轻的女护士闲聊。
女护士大概在这里待久了,跟她们都很熟络。温潋秋经过的时候,那几个女孩子都在笑,而女护士把他叫住了。他一停下来,那几个女孩子们就只抿着嘴,也不说话了,只是看着他笑,又推女护士。女护士只好笑道:“她们都说你怎么这样白,问你是不是涂了粉。”
温潋秋被她们笑得羞赧起来,只丢下一句“没有”,就慌忙要走。
“有人要给你唱整夜的歌,你愿意不愿意呢?”女护士又追在他身后问。
温潋秋迟疑了。
他初来楚州时就带着一本记录楚州民歌的《采风集》。可民歌自然是鲜活的才好听,带着此乡此地的水土浸润才地道。
“是谁?”他按捺不住好奇,“谁会唱?”
女孩们又哄笑起来,带着很重的口音道:“我们都会唱。”
“什么时候?在哪里唱?”他又问。
“在你的窗外唱,也能在你的房里唱,”她们火热而明亮地笑,“还有河滩上游的情人坡,你同哪个去?”
听到“情人坡”,温潋秋顿时又脸红了。
那位楚州军官前几天带他们去看过,说情人坡是本地青年男女聚集对歌的地方。尤其每年上巳、中秋,情人坡将回荡彻夜的歌唱。有情人会凑成双对,在天空和大地之间,成为灵肉合一的爱侣。
“不,不是,”他面红耳赤地道,“就在这里唱行不行?等一等,我回房间一趟。就在这里唱。”
女孩们笑而不答。
等温潋秋抱着乐谱纸和笔墨匆匆地出来,却见那些女孩们都不在了。
夜深了,温潋秋却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自从来到疗养院,他一直是和裘灏分开住的。两个人的房间也并不是紧挨着的。有几次他央求裘灏陪着他一起睡,可一来那位楚州军官总是拉着裘灏出去吸烟打牌胡混,常至深夜才回来,二来疗养院的房间板壁极薄,有时裘灏临睡前来看看他,亲亲他,他只要一出声,就会被裘灏掩住。
真是在哪里都不得自由,温潋秋心中郁郁。
他每常临睡前想起裘灏,总觉得身体燃起了火似的,无法扑熄,无法入梦。
焦躁不安地,他又翻了一个身,想着裘灏不知今晚什么时候才能结束牌戏。也许是最后一把了,也许裘灏已经回房间洗漱了,也许就是下一秒——
“簌簌。”
一阵摸索声,门忽然开了,温潋秋立刻抬起身:“哥哥?”
一柄烛灯先探了进来,走进来的人身姿婀娜,是个女孩——不,不是一个。温潋秋惊慌地看着三个女孩鱼贯进了他的房间,围了上来。
温潋秋顿时吓得抱着褥子站了起来,贴着墙壁,也无处可躲。
那三个女孩举着烛灯,照得脸面明暗不定,影子浓淡地铺满了他的房间。
她们围着他嘁嘁擦擦地说话,可他原本就不大听得分明本地口音,此时更是连一个字都听不进去,只能害怕地问:“你们要做什么?怎么能随便进来?快出去!”
她们也在说,他也在说,谁也没听见谁的话。
温潋秋想从床上下来,三个女孩齐声嚷嚷了起来,他又被吓得退回去了。
“你们到底想做什么?”他简直想哭了。
只见三个女孩齐心协力地把他抱着的被褥拽住了,“噌”地一下利索地从他手中抽了出去。
温潋秋猝不及防,低低惊叫了一声。
她们又仰着脸看他,叽叽喳喳地说话,还伸手要来碰他,温潋秋惊恐万状地叫了声:“哥哥——”
又有人进来了,温潋秋求救地看过去。
不是裘灏,是一个值夜的护士。她匆匆走上来,拉住那几个女孩子训斥了几句,让她们把被子放下了。
“你不要怕,”护士安慰道,“她们说是来给你唱歌。”
“她们,她们还抢我的被子。”温潋秋还是惊魂未定,气恼地控诉着。
正闹着,裘灏来了,见门是开着的,也是一怔。
“哥哥!”温潋秋立刻大声叫他,紧接着腿一软,沿着墙壁缓缓坐下,委屈地开始哭。
“没事,没事,”那护士看看裘灏,再看看温潋秋,一时又是着急,又是笑,“她们说你的皮肤很白,想看看你是不是全身都这样白。她们以为你晚上睡觉是要脱掉衣服的,所以想进来看一看。我替你教训她们了。”
裘灏拨开几个女孩,刚靠近就见温潋秋伸出手臂,像是要他抱。
当着人,裘灏不愿和他太过亲昵,只是扯过被角把他裹了裹。可温潋秋固执地划开被角,又伸出手来,眼睫脆弱地颤抖,嘴唇娇柔地翕动,哀伤得软乎乎、雾蒙蒙,像是个受了委屈的小娃娃。
他是吓坏了,不过是几个野性未驯的小女孩,就把他吓坏了。
再顾不上什么避嫌,什么体面,裘灏连被子一兜,把他整个人抱进怀里,泰然地往床沿一坐,伙同护士一起,把那几个小女孩训斥了一顿。小女孩们像是知错了,讪讪的,也不叽叽喳喳了,只是还用乌溜溜的眼珠看他们。
温潋秋又往裘灏怀里拱,不想让她们看,却不知道,就是他这副样子才更引得人好奇。
好容易将人都打发了,裘灏低下头,就见温潋秋还贴在他脖颈里,哭得情真意切。
“好了,毛毛,”他想放开他,“她们都已经走了。”
他很想说他两句,也不知这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几个小姑娘就能把他吓成这样。可一看见温潋秋哭得睫毛湿漉漉的模样,裘灏便一个字也说不出口了,只觉得怀里的温软潮湿渗透了衣着,掺进了发肤血肉,惹得心口跟着软乎乎、雾蒙蒙地,浑浊得像夜雨前的乌云。他按捺不住地将人揉了又揉,团了又团,一边亲吻,一边喃喃。
“我真是把你惯坏了,毛毛,我真是把你惯坏了。”
可是又能怎么办呢?
门重新关严实了,被褥重新铺陈好了,下半夜的月光照在床边了。温潋秋还趴在他身上哭,哭得可怜兮兮:“哥哥,你今天不能走。你得陪着我。”
“哥哥陪着你。”
“以后也得陪着,一直都得陪着。”温潋秋一边哭,一边却得寸进尺地要求。
“哥哥以后都陪着你,”裘灏心里明白他小小的狡黠,却仍旧呵护备至地捋着他的头发,娇惯过头地哄着,“无论什么时候,一直都陪着你,好吗?”
“好。”
温潋秋还抽抽噎噎的,却像是满意了。
※※※※※※※※※※※※※※※※※※※※
被葛格勒令不能欺负女孩纸的底迪被女孩纸欺负了【笑哭】 月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