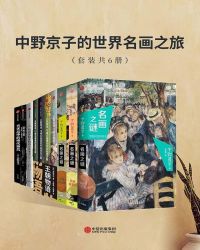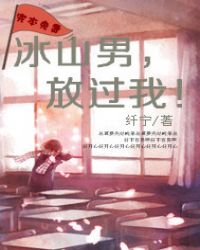XIX 醉生梦死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中野京子的世界名画之旅(套装共6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XIX
醉生梦死
苦艾酒vs伏特加
我曾在动物纪录片中看到过这样一幕——从树上熟透落下的果实通过自然发酵产生了酒精成分,各种动物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它们享受美酒,醉态百出。脸比屁股还要红、忍受着宿醉的猴子,步履蹒跚、最后一屁股坐到地上的长颈鹿……醉倒之后的动物简直与人类一模一样,让观众们忍俊不禁。
动物们应该也很清楚酒精的妙处,才会不约而同地在同一季节出现在同一地点,享受片刻的酣醉。这是酒神巴克斯 之宴的动物版。不过,无论长颈鹿多么喜欢喝酒都不会酒精中毒,因为那些自然发酵的甜美汁水在它们的人生(兽生?)中,只是时间限定的天赐褒奖而已。
而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类与酒的关系也是这样的。
据说人类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就已经饮酒。中世纪时,人们掌握了制造蒸馏酒的技术,那时的酒被称为“生命之水”。由于这种蒸馏酒的产量极少,因而数个世纪以来都是只属于特权阶级的奢侈品。同一时期虽然也有面向大众供应的果酒和啤酒,但就当时的文献记录来看,这些饮品只用少得可怜的酒渣制成,虽然名称里带了个“酒”字,但味道淡得几乎与水没什么区别。老百姓只有在祭祀和节庆等特殊日子才有机会尝到领主提供的醇正佳酿。
时间到了17世纪。此时,贫苦庶民的生活场景也开始成为艺术题材,他们烂醉如泥、酒后痴狂的模样在绘画作品中出镜率奇高。也许大家会觉得奇怪,好端端的画这些做什么?难道是订画的有钱人吃饱了没事干,一拍脑门想了解一下基层群众的业余生活?其实正确答案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首先,达官贵人们爱看老百姓喝酒撒欢与前文中提到的我们爱看动物醉酒纪录片是一个道理;其次,作为领地的主人看到领土富饶、领民饮酒享乐,心中自然无比满足;再次,下等人的醉酒狂态还能成为劝诫世人远离酒精的道德寓言(据说有的画家还会把“酒即毒药”的铭文画在画中)。
同时,老百姓对此也有自己的说法。仅限节庆之际才能尝到的美酒与自己平时喝惯的寡淡酒水简直天差地别,不但酒精度数翻了好几番,口感也甘美异常,此时不醉更待何时!要知道,等明天睁开双眼,等待自己的又是看不到尽头的贫苦日子和难以下咽的食物。
时代转眼步入了工业革命时期,大量制造酒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价廉物美的酒水大消费时代拉开帷幕。原本属于上流阶层专利的酒精依赖症现在也开始在中下层社会中蔓延。很快,“蔓延”变成了“大爆发”。每日都在切身体会着“人生苦短”四个字的底层民众才是真正需要借酒浇愁的一群人,他们看到便宜的美酒岂有不蜂拥而至的道理?
日本的烧酒、英国的琴酒、法国的苦艾酒、俄国的伏特加……
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德加笔下印象派时代潜藏在巴黎的黑暗面:
这幅作品的画面边缘被直接切断,不比一般的绘画作品内容完整,好似一张纪实照片(当然这其实是经过画家精心设计的巧妙构图)。一对青春已逝的男女坐在装潢简陋的廉价咖啡馆里。从左手边那张以凌乱笔触画成的报纸来看,这幅画的发生时间应该在大清早(当时的报纸只有晨报),画中的两人应该是共度一晚的妓女和嫖客吧。
埃德加·德加
《苦艾酒》
1875-1876年,油画,92cm×68cm
奥赛博物馆藏(法国)
两人虽然比肩而坐,但彼此对对方都毫无兴趣,背后的浓重倒影更让他们显得孤独寂寥。也许是为了让自己从宿醉中清醒过来,眼圈泛红的男子正喝着冰咖啡,而旁边的女子则是一副完全放空、什么都不愿意思考的模样,面前摆着早起的第一杯酒,落寞空虚的人生状态由此可见一斑。
此时此刻,预备两年后召开世界博览会的巴黎正朝着现代化大步迈进。王政时代那些以脏乱差著称的背街小巷被整顿一新,绚烂的“花都”正在逐步成形。市民富庶,劳动阶层也得到许多优待和保障,人们对光明的未来深信不疑。
然而,总有一些人跟不上时代的节奏,如同左拉《娜娜》《小酒店》中的女主人公一般,也如同这幅画中的女子一般,沦为灿烂阳光下的阴暗面。
这个女人所表现出来的茫然、恍惚、冷漠也许源自她对生命的放弃。整幅画中唯一美丽的是酒的颜色。比起无色透明、外表平淡的金酒、伏特加,法国人钟爱的苦艾酒呈现妖冶魅惑的黄绿色。如果再与水混合,白浊的酒液将变得更加如梦似幻。
被称为“恶魔之酒”“绿色魔女”的苦艾酒以苦艾为原料,添加各种药草及香草,是一种风味独特的烈酒。酒精度数在50度到近90度。苦艾酒最初只是瑞士的一种退烧药剂(制造者是法国人),19世纪末作为酒精饮品风靡法国。据说当时的酒精度数普遍在70度左右。
苦艾酒比其他酒精饮品特殊的地方在于它具有致幻效果,能让人体会到强烈的酒精快感,容易上瘾。说白了,它与现在摇头丸之类的毒品如出一辙。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任何人都能以低价买到这种酒。如果像过去一样只有豪门贵族才能日日畅饮苦艾酒,那么那些自诩为波希米亚人的穷艺术家就不会接二连三地变成酒鬼,凡·高、魏尔伦 就不会如星辰般陨落,无数默默无闻的普通老百姓也不会走上罪犯甚至死亡的道路。
电影《说谎者》 中的警探有这么一句台词描述了苦艾酒引起的强烈幻觉:“我认识一个只要喝下半瓶苦艾酒就会头脑错乱的男人。他曾经用水果刀直接削掉自己双腿上的皮肤,因为他坚信自己是在削苹果!”
据说凡·高亲手削掉耳朵的时候也喝了苦艾酒,那么他朝着自己胸口开枪时情况如何呢?这位被世界抛弃的天才带着枪伤和满身血污步行回家(次日死去),当时的他大概也与那个相信自己的皮肤是苹果皮的男人一样,并未感觉到疼痛吧?
危险的苦艾酒在进入20世纪后被几乎所有的欧美国家封杀,却又在时代接近21世纪时得以解禁。不过,这一次再度问世的苦艾酒已经改头换面,不再是德加画作中那种诱人堕落的魔性之酒了。在制造时,厂商根据比例减少了苦艾的香味成分(这样一来就丧失了致幻性),生产了获得国家许可的饮品。
下面,再来聊一聊伏特加。
“伏特加是俄国的全部。”——俄国人对这种酒可谓用情至深,至今俄罗斯男性的寿命仍因此持续缩短(俄罗斯男性的平均寿命只有63岁,在发达国家绝无仅有,且比同国女性早过世10年以上)。
伏特加历史悠久,然而直到19世纪才真正发展到如今我们看到的形态(即以大麦等为主要原料,无色透明、口味单纯,几乎只由水和乙醇构成)。俄国人在喝这种酒精度数在40~60度的酒时不会添加其他饮料,只是直接倒进嘴里,享受酒精带来的直接刺激。祖祖辈辈生长在苦寒地带的俄国人拥有极强的酒精耐受度,因此怎么喝都没问题。可是正因为所有人都觉得自己酒量无敌,从不知收敛,才会一直喝到身体垮掉、寿命缩短。
请大家把目光聚焦到作曲家穆索尔斯基这幅著名的肖像画上。这是穆索尔斯基因伏特加成瘾症去世前10天左右,好友列宾在医院中为他绘制的杰作。在著名画家的笔下,这位音乐天才的超群存在感跃然纸上。
时年42岁的穆索尔斯基长着酒精中毒者特有的红鼻子,身上随意套着寒酸朴素的衣服,头发凌乱,胡子也许久没有打理了。此时的他虽然病情暂时得到控制,但已经病入膏肓。不过从画中的状态来看,他依旧身材魁梧壮实,散发着强烈的生命力,怎么看也不像一个大限将至之人。然而再仔细观察一下,我们就能发现,穆索尔斯基的生命力全部来自双眼。在这张早已被酒精侵蚀的脸上,一双眼睛却惊人的清澈、明亮,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在不同鉴赏者眼中,这幅画也被视作一幅鬼气森森的肖像画。我想,原因大概就在这里。与丧失生气的外貌所体现出来的肉体濒死状态相比,穆索尔斯基的眼中却饱含着生机勃勃的精神光辉。拥有这样一双眼睛的人命不该绝,他还有太多未竟之事,还蕴藏着无限活下去的精神力量。然而被伏特加毁掉的肉体却再也无法承受更多,只能将这份生命力碾压殆尽。
伏特加与苦艾酒不同,既没有类似毒品的副作用,也不会造成病理性的精神空虚。穆索尔斯基曾数次尝试戒酒,还在清醒时写下曲子《啊,你这个酒鬼》(Ah, You Drunken Sot)用以自嘲。不过可惜的是,他到最后还是没能逃脱酒精成瘾的魔爪。
据史料记载,君主制时代俄国的税收中近三成是酒税。在高压政治态势之下,无论贵族还是农奴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人们会选择在豪饮中逃避现实也的确情有可原。
穆索尔斯基虽说是喝多了便宜烈酒才死的,但他并非下层阶级出身(在那个时代的俄国,不是有钱人家的子弟几乎不可能玩音乐)。穆索尔斯基家当时是有钱有势的大地主,祖先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5世纪。他作为家族的幺子出生,从小接受一流教育。7岁时,穆索尔斯基在家里隆重举办的家庭音乐会上演奏了李斯特的钢琴曲,受到周遭人的一致赞赏,但基于穆索尔斯基家的传统,这个在音乐方面展露非凡才华的小儿子还是被父母送进了士官学校。
列宾这幅肖像画中的中年大叔穆索尔斯基看起来似乎是个对外表毫不在意的豪迈汉子,但据说年轻时的他“富有贵族气息、时髦考究、爱装腔作势”。父亲去世后,穆索尔斯基终于踏上了自己期待的道路——作为《展览会之画》(Pictures at an Exhibition)、《荒山一夜》(Night on Bald Mountain)、《鲍里斯·戈都诺夫》(Boris Godunov)的作曲者勇敢开拓俄国音乐的道路。
在前路险峻、听众本身尚不成熟的俄国,穆索尔斯基的音乐作品并未受到肯定。此时沙皇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II)下诏废除农奴制,身为领主的穆索尔斯基家一下子在经济上陷入窘境,穆索尔斯基本人不得不出门工作,成了运输部的一个小职员。而在深爱的母亲去世之后,他对酒精的依赖更加强烈。很快,他辞掉了工作,人生直接滑入了贫穷的低谷。
在彼得格勒(今圣彼得堡)的军队医院住院时,许多朋友前来探望穆索尔斯基。所有探访者都意识到,病床上的这个人已经时日无多了。
所谓“才子遇才子,每有怜才之心”。即便专业领域不同,一直以来都对穆索尔斯基的音乐作品盛赞有加的列宾特地从莫斯科远道而来,只为见这个音乐才子最后一面。列宾听说好友根本没有钱为自己办后事,于是打算为他画像,将卖掉这幅肖像画所得的钱作为穆索尔斯基的安葬费。我想列宾在创作这幅画时一定在心中哭了很多次吧。也许正是这份出自友谊的深切悲伤,才让画中的音乐家看起来如此耀眼。
埃德加·德加(Edgar Degas,1834-1917)是印象派的代表画家之一,创作了许多以芭蕾舞女及赛马为主题的作品。
伊里亚·列宾(Ilya Repin,1844-1930)是俄国现实主义绘画大师,代表作有《伏尔加河上的纤夫》(Barge Haulers on the Volga)、《伊凡雷帝及其子》(Ivan the Terrible and His Son Ivan)、《扎波罗热人给土耳其苏丹写回信》(Zaporozhian Cossacks Write to the Sultan of Turkey)等。 中野京子的世界名画之旅(套装共6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