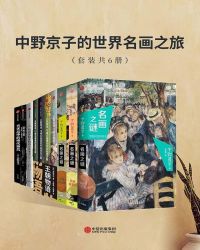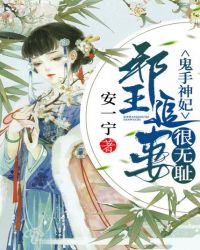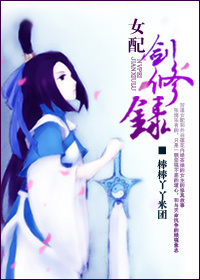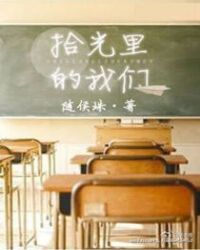XIV 纳粹时代的相思病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中野京子的世界名画之旅(套装共6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XIV
纳粹时代的相思病
柏林,夜半时分的咖啡馆。
手持钥匙形手杖、身着西服的年轻男子姿态散漫地坐在冰冷的椅子上。令人甚觉诡异的是那颗光头和涂成苍白颜色的脸。他头上太阳穴的位置有一个锚形的刺青,嘴唇上抹着鲜红的口红,眉毛与眼皮上有化妆的痕迹,耳垂上还戴着耳钉。
一条酷似鲜血的红色领带悬挂在男子胸口,透过胸前的口袋可以隐隐看到同色的心脏与浅蓝色的手枪。心已受伤,从画作的题目《相思病》也能看出,这名男子正打算自杀。在他身旁的地板上,一条看起来凶神恶煞、似乎立即要将眼前人撕成碎片的狗以隐喻“忧郁”的姿势蜷成一团(请参照本书“价值观的转变”一节)。与守卫冥河的卡戎 一样,它也有一双红色的眼睛。
实际上,这名男子应该已经处于濒死状态。且不论那张宛如死后化妆般惨白的脸,在画面右上方的圆桌附近,一具骷髅(=死神)站在仿佛大镰刀般的赤色月牙前等待着他。另外,走廊的尽头散发着异样的光芒,这应该是前往另一个世界的通道。
男子单手杵着的桌子上除了酒瓶、酒杯、烟斗及烟盒外,还摆放着注射器。他喝了酒、注射了毒品,陷入蒙眬状态,只希望能以此稍稍缓解自己对死亡的恐惧。在整个世界除了战争还是战争的时候,这种自甘堕落、并非英勇战死而只是为失恋而死的样子,实在是讽刺至极。
与这幅画成对的另一作品《自杀》中,貌似是同一人物的男子业已成为尸骸。
——这被认为是格罗兹的自画像。
当时,作家赫兹菲尔德(Herzfelde)曾写下这样一段话,记录他在街上偶然看到的格罗兹的模样:“脸涂成石灰一样的惨白色,嘴上抹着口红,穿着巧克力色的西服外套,两腿之间放着一根细长的黑色手杖。”
简直与画中人一模一样。格罗兹就以这副奇异的装扮自称埃亨弗里德男爵(实际上他只是贫苦劳动阶级出身),把周围的人全都忽悠倒了。不过幸好他在现实中还没有神经大条到打开裤子拉链把自己的重要器官暴露在阳光下,可见其作品中那些故意使坏的小花招全都是低级趣味的玩笑罢了。
格罗兹时年22岁。如此年轻却如此颓废却也有充分的理由——他刚刚经历过战争。
两年前的1914年,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奥匈帝国)老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 的侄子兼王位继承者弗朗茨·斐迪南在访问萨拉热窝时遭到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的刺杀而死。以此为导火线,战火迅速蔓延到全世界。德国、奥地利、土耳其、保加利亚等国组成的同盟国,与英国、法国、意大利、美国、俄国、日本等组成的协约国在世界各地激烈交战,血流成河、横尸遍野,这场前所未有的“世界诸国综合实力战”在日后被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还在美术工艺学校学习的格罗兹也被卷入汹涌的爱国主义狂潮,成为一名志愿兵赶赴前线。
这几乎就是《西线无战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作者:埃里希·雷马克(Erich Remarque),1929年发行]描述的世界。在这部小说中,还是高中生的主人公受到心怀狂热爱国情绪的老教师煽动,为了保卫“和平”端起了枪。然而真正的战场远远超出他的想象。炮弹的暴风雨从天空、海洋前后左右向他袭来,空气中飘散着毒气瓦斯,鲜血与尸块四处飞散。主人公必须踏着死相凄惨的尸体冲向敌军,亲手杀死近在眼前的敌军士兵的脸以及好友之死令他濒临崩溃。战场上的每一天都是九死一生。拼杀在第一线的小小兵卒根本无力去想什么爱国之心。“这样的我就算回去也再没有了根底和希望,再也找不到自己的道路。”
小说的主人公在结尾处向战壕附近翩翩飞舞的美丽蝴蝶伸出了手,同时被流弹击中阵亡。然而格罗兹却活了下来。他能活着回来不是因为他很强,而是因为他太弱了。格罗兹无法忍受战场的残酷,很快就罹患精神病入院治疗,仅仅半年就被军队开除(两年后再次征兵时他也立即被盖上了“不适合参军”的大印,排除在征兵对象之外)。
回到柏林的格罗兹画出了血肉模糊的战场,并整日泡在艺术家与革命家们聚集的“西部咖啡馆”里。《相思病》正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从这一时期画家自身的状况来考虑,画中男子的确与死亡相邻,而且多亏了这名男子的自我了断,才让身为原型人物的格罗兹保持理智、继续存活于世。接下来,格罗兹打算脱胎换骨。由于他从心底里厌恶自己德国人的身份(他曾大骂道:“德国人不但粗俗、愚蠢、丑陋,而且脑满肥肠、食古不化。”),因此他一心希望变成曾在报纸、照片中见过并深深憧憬的美国人。其他的不说,至少先要从名字开始靠近美国。
于是,在创作这幅作品的同一年,一直叫的名字盖奥尔格·格洛斯(Georg Groß)变成了乔治·格罗兹(George Grosz)。
“战争令大众政治化。”(语出弗里德里希·瑙曼 。)大众已然如此,更不用提如矿井中的金丝雀一般敏感的艺术家,他们在亲眼目睹近代战争的巨大杀伤力后会做出过激反应也在情理之中。不久,这些金丝雀们在世界各地同时张开双翼,仰头发出尖锐的鸣叫,著名的达达主义(Dadaism)就此诞生。
对于“达达”一词的由来至今众说纷纭,有一种说法认为该词来源于幼儿指点木马时无意识的发音。不过这场运动的起点很明确—1916年,流亡瑞士的艺术家们集合起来表明自己对近代社会及继承传统艺术的彻底否定。他们将自己这个在苏黎世组建的组织命名为“达达”。
在紧迫的政治形势之下,达达主义如星星之火般迅速燃遍了整片原野。几乎在同一时间,世界各地兴起了各种各样的达达主义运动。在纽约,杜尚 以“泉”为题展示小便池,还发表了带胡须的《蒙娜丽莎》。此外不但有巴黎达达主义(日后其核心被超形式主义所继承)、罗马达达主义、布达佩斯达达主义,甚至连东京达达主义(村山知义、辻润、中原中也等)也出现了。
乔治·格罗兹
《自杀》
1916年,油画,100cm×77.5cm
泰特美术馆藏(英国)
柏林达达主义的核心人物之一就是格罗兹。由于当时德国在战场上已明显呈现颓势,所以与其他国家相比,德国的达达主义者在政治上更加激进,在精神上也更加颓废空虚。格罗兹与友人一起创立了反战杂志《新青年》,然而不到一年就被当局取缔。他逐渐在绘画作品中加大了讽刺的成分,其出类拔萃的素描能力被称赞为杜米埃(Daumier,约百年前活跃在法国画坛的讽刺画画家)再世。随着画集的热销,格罗兹也逐渐成为有名的人气画家。
随着“一战”结束,达达主义急速凋零。然而格罗兹却持续发表着预见性的作品。格罗兹主张美丽的事物早已不可信,丑恶的肉体必定孕育丑恶的灵魂。在他笔下,一手拿着啤酒一手举着军刀、长相粗鄙的纳粹党员,膀大腰圆、脑袋里塞满屎尿的资本家,以及向战火赐予祝福的红鼻子神父才是在暗中操纵社会、即将把国家再次引向战争的罪魁祸首。
在第一次国际达达主义展中,格罗兹因为把一个顶着猪头、真人大小的德国士兵人偶吊在天花板上被控侮辱军部,遭到罚款处罚。接下来他又接二连三遭到指控,画集内容涉嫌猥亵罪,画出戴着防毒面具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像也犯了亵渎上帝罪。一旦纳粹党上台,格罗兹恐怕就小命不保了。
39岁的格罗兹在希特勒执政的几个星期前登上了逃亡美国的客轮。他在柏林的住所及画室很快就遭到当局的搜查,这一次格罗兹才真是死里逃生。
纳粹将《西线无战事》与马克思、托马斯·曼 和海涅 的书一同视为软弱的反战书籍彻底焚毁,格罗兹的作品也与奥托·迪克斯 及柯克西卡 、保罗·克利 、基希纳 等艺术家的作品一同被打上了“颓废艺术”的烙印,遭到毁坏及贱卖。希特勒对这些绘画作品表现出强烈的厌恶感,认为“如此丑恶的人绝非我等雅利安民族之人”、“这些人故意夸大战争的悲惨程度,为的是贬低我们这些英雄”,同时一味赞美描绘纳粹式健康美的画家。
当时纳粹的御用画家们却没有一人在美术史上留名。就算从外行人的眼光来看,他们的作品也与广告板一样无可指摘。在这些画作中,身材健硕的男人们从事体力劳动,丰乳肥臀、看起来很好生养的女人们摆出僵硬的姿势,一心祈祷组建一个质朴而健全的家庭。当然,无论任何人都必须禁烟。因为纳粹贯彻的可是健康至上主义。
这么看来,希特勒将格罗兹的画评价为“丑恶”的确不过分。如前文所述,格罗兹的一贯手法是通过丑恶的肉体来表现精神上的堕落。那些从内而外表达出来的内容中不但饱含着画家井喷的表现欲,而且最终呈现在画面上的东西已然超越了个人的喜好与感觉,鉴赏者所面对的是一种强大的压迫感。这是纳粹御用画家们那些毫无性感元素的美女图绝对不曾拥有的力量。
然而人生总是这么讽刺。
格罗兹终于成为年轻时一心向往的美国人。他定居在美国,坚信自己在这里也能获得与在祖国一样的名声。他创作了许多与在德国时期一样的作品——尖锐的讽刺、丑陋的人类、遗忘道德的恶性、悲惨的战场……然而这些作品无法激起美国人的共鸣,因为当时美国尚未参战,日后虽然参战,但本土并未沦为战场(除夏威夷的珍珠港外)。的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男人们端起枪踏入欧洲战线,女人们开始为守卫后方奋战,不过对于幅员辽阔的美国来说,战争终究不是那么的真实。
渐渐地,格罗兹的内心也被美国所影响。
可能被再次征兵前往战场、可能被捕入狱等等的恐惧感早已消退,令人恼火的当权者也远在天边,再也看不到值得大书特书的世间百态,格罗兹的身心都开始习惯这里平静的日常生活,而他的作品也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因憎恨祖国、一心憧憬美国而雀跃沸腾的心,就像长时间浸在热水中的手指一样变得皱巴巴的,对于他的艺术来说最最重要的东西,宛如流沙一般从指缝中溜走。
就像蒙克 摆脱了精神疾病后就丧失了绘画能力一样,离开战争现场的格罗兹也失去了尖锐的批判精神。所谓时势造英雄,一个人身在何处也会对命运产生巨大影响。试想一下,如果格罗兹从一开始就是美国人的话,他还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吗?这就像假设身处于幕末这个时代的坂本龙马 并非土佐人,而生长在江户一样。
格罗兹在美国生活了25年,最终还是放弃了在此成名的念头,回到了战后复兴中的柏林。回国后不到三周,格罗兹就心力衰竭去世。
“我的美国梦如泡沫般消失了,然而它的确曾闪耀着彩虹之色。”——格罗兹如是说。
乔治·格罗兹(1893~1959)如今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讽刺画家。
1890~1930年大事记 中野京子的世界名画之旅(套装共6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