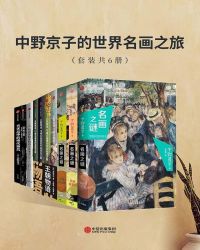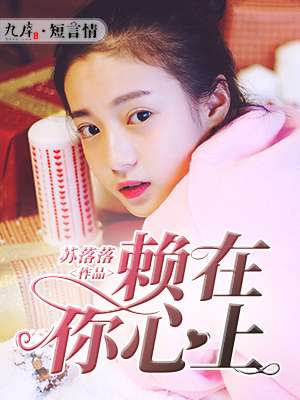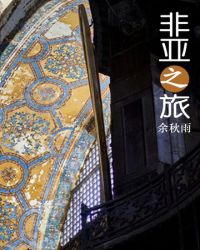XV 濒死的丑角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中野京子的世界名画之旅(套装共6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XV
濒死的丑角
宛如舞台上的一幕。19世纪法国艺术学会大师杰洛姆的精妙画技令观者想象力飞驰。
冬日拂晓时分,无人的布洛涅森林,掉光了叶子的寒枝裸木,远景中隐隐可见的两辆马车,奇装异服的男人们,丢弃在雪地上的外套及细长的剑,离去时头也不回的胜利者,以及即将死去的丑角……一眼就能看出这里刚刚发生了什么——假面舞会上的小小争执变成了赌上性命的决斗。被酒精、女色及舞会搞得神魂颠倒的同伴们不但没有立即劝阻当事者、息事宁人,反而在一旁煽风点火。剑与马车在第一时间准备妥当,当事者们连衣服都没换,满脑袋还是庆典的余韵——也就是说周围并未给他们独自冷静思考的时间,就鲁莽地奔赴决斗地点,最终却发现结局远在预想之外,不禁大惊失色。
丑角打扮的年轻人在斑驳的白色妆扮下露出懊丧的神情,他右手仍然紧紧握剑,左手却好似想要抓住生命的残片般剧烈抽搐着,死亡已经悄悄地从脚尖向全身侵袭。自请观战的朋友们一下子从醉酒状态中清醒过来。穿着红色中国长袍的男子正在确认当事者身上被刺穿的伤口。另一个身着黑色修道服的人双手抱头,对当事者的伤势震惊不已。在这一连串动作发生的过程中,鲜血从伤者的胸口不断流出,滴落在皑皑白雪之上。
从背后抱住丑角的人是经过双方共同邀请的决斗主持者(见证人)。从他脖子上戴着数百年前非常流行的白色环领(波浪形状的蕾丝领)可以看出,这一位也是参加假面舞会的宾客。
早已被踩踏得凌乱不堪的决斗场中掉落着黄色、红色的羽毛。这些都是从画面右端那个打扮成印第安人的男子身上掉下来的,与丑角交手的正是这个人。想来他虽然有心打到对方,但应该无意取人性命。此刻,这位胜利者丝毫没有欢腾与喜悦,反而垂头丧气、脚步沉重地走向自己的马车,就算身旁那位穿着鲜艳紧身衣,打扮成滑稽戏小丑艾尔雷吉诺(在意大利巡回剧团演出的即兴喜剧中登场的小丑角色)的朋友悉心安慰也无济于事。
白雪如包裹死者的裹尸布一般铺展在天地之间。不久,朝日即将东升,男人们夜晚的愚蠢行径将毫不留情地暴露在阳光之下。
决斗是日耳曼人社会中一种合法的审判形式。到了15世纪末期,由于法国兴起了“守卫荣誉的决斗”,这一活动如燎原之火般迅速蔓延到了整个欧洲大陆(日后还传到了美洲新大陆),上流社会的勇猛男士对决斗尤其推崇(虽然只占少数,但的确也有女性的决斗),就算政府三令五申不准私行决斗,却仍然屡禁不止,甚至还出现了供决斗专用的“双胞胎手枪”旅馆。
决斗作为荣誉之战与一般的杀人不同,被视为受到侮辱时挽回名誉的一大手段——虽然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决斗方法略有出入——有着严格的规矩与步骤。发起者必须将一只手套丢向对方,对方捡起手套就表示同意决斗,决斗双方必须属于同一阶层,必须在平等的条件下战斗,双方要各自安排熟人观战,还必须委托第三方见证人,武器一般是剑或手枪,在一方流血或对手无法战斗之前决斗不能停止,等等。
当然也不是每一次决斗都一定会斗个你死我活,比如双方使用手枪时,子弹数是事前设定好的,因此不少手枪决斗的结果是双方毫发无伤。不过话虽如此,毕竟两人手里端着的是真枪实弹,相互射击这种动作的危险程度可想而知。这种与死亡如影随形的活动居然持续到20世纪初,实在是令人震惊。
更让人惊讶的是,名人之中也有不少人经历过决斗。比如18世纪的哲学家兼风流才子卡萨诺瓦(Casanova)、作曲家亨德尔(Handel),19世纪的铁血宰相俾斯麦(Bismarck,一生居然决斗25次,难不成决斗已经变成了爱好?)、作家大仲马(Dumas, pere)、诗人拜伦(Byron)、画家马奈(Manet)等等,这些人的决斗都以负伤告终,然而俄国文学之父普希金(Pushkin)、法国数学家伽罗瓦(Galois)及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起草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都因决斗丢掉了性命,无尽的才华与大好的前途就此断送。
本作并非杰洛姆擅长的历史巨作,只是取材于同时代世情、相较之下尺幅较小的风俗画,然而一经公开就成为超级人气佳作。不同的版本及复制品立刻就在市面上流传,甚至还有直接引用了画中场面的戏剧上演。
有人说这幅作品人气高的秘密在于展览期间巴黎实际上发生了决斗事件并有人因此死亡。不过抛开社会事件对话题性的添砖加瓦,作品本身华美精致的色彩、简洁明了的真实感、宛如舞台场景的画面构图以及登场人物富有戏剧性的动作才是令鉴赏者倾倒的原因所在。如果你要评论这不够高雅,我也没什么可说的。归根到底,一味讲究纯文学不一定真的有市场,风趣幽默的都市风格短篇小说也能深深印在我们脑海里。醇厚典雅的歌剧自然是极好的,但偶尔欣赏轻松利落的轻歌剧也别有一番风味。这幅作品也是一样,暂时沉浸在这场黎明前的雪中决斗故事中有什么不可以?
当时大部分评论家称赞本作为“优秀的道德教育画”,认为这幅作品告诉了诗人这样一个道理:在19世纪已经过去一半的今时今日,如果还采用古时候的无聊方法来证明自己的男子气概,就会落得这样的下场!嗯……画家也不是完全没有这个意思,不过我觉得评论家们观察的焦点还是与原意偏离了。
关键点不在于决斗,而是丑角。这幅作品的悲剧根源来自丑角的身份。
如果画面上的主角不是丑角会如何?如果被友人们包围着即将死去的决斗者不是丑角,而是穿红色中国长袍的男子或艾尔雷吉诺或印第安人呢?——若是如此,这幅画本身就死了。为什么?
与宫廷弄臣一脉相承的丑角正好从19世纪初开始转型,这次转型可以称得上是一次划时代的变化。不过在此之前,让我们先一起来看看丑角的演变过程——
在中世纪欧洲,称呼“弄臣”、“愚人”及“精神病人”用的都是同一个词(英语fool、法语fou、德语Narr)。宫廷中会特别“圈养”精神不正常或身体有残疾的人充当笑料,或利用他们直言说出对王侯贵族而言非常刺耳的真相。戴着垂耳帽子、穿着怪诞服装的宫廷弄臣虽然会被嘲笑、欺凌,地位极其卑贱,但同时也享有无论说什么都不会受到惩罚的“愚者的自由权”。也因为这一点,后期甚至出现了为了畅所欲言故意成为弄臣的“聪明人”。
同样,宫廷之外的愚人们[以布兰特(Brant)的讽刺诗集《愚人船》最有名]也因为“蠢货的身上必须有标记”这一大众认识,被迫打扮得与宫廷弄臣一样,当然这其中应该也有为了获得自由而伪装成愚人的人。就这样,弄臣就是脑袋有问题的愚人这样的联想方式持续了几个世纪,丑角自然也无法逃过社会的歧视与偏见。
丑角(Pierrot)一词来源于法语中的“Pierre”,取自即兴喜剧中的一个常规人物“Pedrolino”(佩多罗里诺)(Pedro是Pierre的缩写),在16世纪已经登上舞台。在当时,开朗活泼的艾尔雷吉诺(Arlecchino)深受欢迎,而负责扮演纯朴无知角色的佩多罗里诺却不受重视。到了17世纪后半叶,喜剧中另一个角色、敏感细腻的梦想家普尔契涅拉(Pulcinella)的宽大服装及涂白脸的化妆形式被运用到佩多罗里诺身上,两者就此融合。不过两个角色并未彻底一体化,而丑角的人气也没有得到提升。主要原因在于此前受到贵族青睐的即兴喜剧逐渐被视为下流粗俗的玩意儿,失去了上流阶层的支持,变成了只供下层人娱乐的戏剧。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位天才演员出现在19世纪初的巴黎,他就是杜布拉。他凭借涂得雪白的脸、装饰着大纽扣的宽松白衣、盖住头发的小帽子的装扮,通过宛如舞蹈般、富有艺术性的哑剧,重新塑造了丑角的形象。无论做什么都会犯错、滑稽搞笑的丑角,同时也是一位忧郁的梦想家——这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悲伤的小丑”、“流泪的小丑”的诞生[马塞尔·卡内尔(Marcel Carne)导演的电影《天堂的孩子们》(Children of Paradise)中,让-路易·巴罗尔出演了杜布拉一角]。
最先陶醉于杜布拉对于丑角的这一全新解释的是作家与评论家们,特奥菲尔·戈蒂埃 写道:“苍白消瘦、总是精疲力竭的丑角是古代的奴隶,今天的下层人民、手无寸铁的无产阶级,他只能默默无言地注视着主人们的粗野暴行。”由此,即兴喜剧再次获得好评,丑角的新形象也开始深入人心。
丑角成为在愚钝、滑稽的表象背后蕴藏深厚感情的存在。在莱翁卡瓦洛 的歌剧《丑角》(Pagliacci)中,得知妻子出轨却不得不站上舞台惹观众发笑的主人公在镜前如此唱道:
“穿上彩衣/脸涂白粉/人们给钱,为的就是排遣愁肠/就算妻子被人夺走/笑吧,小丑,笑了才有人鼓掌/将眼泪和痛苦变成滑稽的动作/装一个鬼脸来掩饰抽泣与愁苦/笑吧,小丑,笑你那破碎的爱情吧/笑吧,笑你那满心的痛苦和悲伤!”
亚森·杜璐卜
《杜布拉肖像》
1832,油画,27cm×18cm
卡纳瓦雷博物馆藏(法国)
悲哀的丑角成为纯洁、浪漫的象征,成为不被认可的艺术家,成为深陷悲恋的男子,而这些特征都与青春密不可分。年轻人正因为纯粹,因为心怀浪漫,因为得不到社会的承认,更重要的是因为爱情,才会走向歧途,才会引发令人痛心的自我毁灭吧……
杰洛姆画中那位被刺穿胸膛、此刻已然停止了呼吸的年轻人会如此富有悲剧性,正是因为他那身丑角装扮,而如今,他也的确变成了真正的悲伤小丑。
让-里奥·杰洛姆(Jean-Leon Gerome,1824~1904)生前作为法兰西学会会员、英国皇家艺术院名誉会员、法国荣誉军团勋章获得者等荣光一生,但后来随着印象派的抬头逐渐遭受轻视。杰洛姆一生创作了许多以东方为背景的作品,现今许多好莱坞电影在创作拍摄时都会参考他的画作。
1830~1890年大事记 中野京子的世界名画之旅(套装共6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