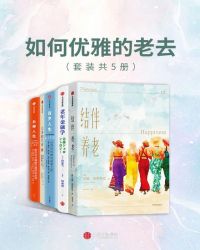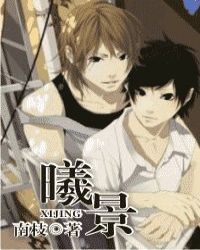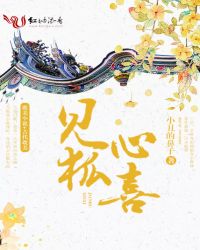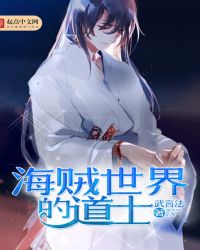第八章 为老年做好准备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如何优雅的老去(套装共5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第八章 为老年做好准备
快乐就是,你有个好地方住,钱够花,家庭美满,就这么简单。享乐的时候不要以自己的健康或经济保障为代价,要懂得正确而不是错误地花钱。
最重要的是,给最后的日子留足钱。
“我更老了,所以我得让自己感受好一点。”
我们从来不谈死亡。有什么用呢?如果你老了,你就是会死。我们下楼玩牌。在我们这个年纪,你得做好准备。
——黄萍(90岁)
与竭力做到老来经济有保障的弗雷德相比,黄萍几乎一无所有。她在唐人街的一个诊所工作的时候,收入还达不到最低工资标准,将近80岁时退休,没有储蓄,仅靠每个月700美元的补充性保障福利过活。她从中国香港迁到美国已经30年了,还是只会讲最简单的英语。她丈夫和她的两个姐妹已经去世,唯一的儿子在广东的一家百货商场被杀害。尽管她接受了两次髋骨置换手术,但背部和腿部的风湿还是会在她行走时造成疼痛。
我在她位于格拉默西公园附近那套整洁的公寓里见到她时,她只有一件事要抱怨,那就是抱怨个没完的老人。
她说:“大家总是抱怨身体不好,或者说,今天我得去看医生。他们好多人都是这样,说实话,是大多数人。他们觉得如果自己抱怨,别人就会同情,可我觉得恰恰相反。谁能帮助你?一点点疼——就忍一下,让你自己坚强一点,深呼吸,想尽办法让自己好起来。”
我们认识的时候,她89岁,东拼西凑出来的生活好于她的想象。她在城里的富人区有一套便宜得离谱的公寓;托医疗补助制度的福,她有一个负责所有烹饪、清洁和采购工作的家庭看护;有食品券和上门送餐服务;每天还在这幢楼的活动室里跟同样讲粤语的同伴打麻将。她这辈子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轻松自在和空闲时间,她的需求得到了满足,不需要对别人承担义务。她从不感到孤单,因为身边总有朋友陪伴。与她工作、养家、护理奄奄一息的丈夫的那几十年相比,她在经济上更有保障了,烦恼也少了。她说:“我们在享受生活。虽然我们不富裕,但我们的生活很体面,比以前好。我想买什么就买什么,连很贵的毛料都可以买,以前想买的话是很难的。”
几乎从我认识黄萍的那一刻起,她就开始传授经验了。她似乎经常把这些经验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一会儿说粤语,一会儿说英语,梳理每种语言当中不同的微妙之处。她认为老龄同其他任何年龄一样,是一个人生阶段,在这个阶段,“你必须尽量让自己快乐”。她说,所有人都会变老,“这是一种经历。你得随时撑住。不要想那些让人难受的事情,要想到所有美好的事情,比如,你年轻的时候,你是多么开心,就像我和我丈夫,他是个多好的人啊。我从来不会想,哦,我丈夫不在了,我多难过啊。不,从来不会。我总是想,他永远和我在一起。所以我能撑得住。”
好好利用社会福利和服务
认识黄萍之前,我花了几个星期时间探访华裔和韩裔老年中心,总是带着个翻译,还通过为拉美裔服务的社会服务机构结识拉美裔老人。如果不包含把全世界的文化价值观和实践带到人生最后阶段的移民老人,那么对美国(尤其是纽约)老龄人口的描述将是不完整的。几年前,昆斯区的一些老龄韩裔园丁与市政府公务员发生了激烈口角,原因是园林局试图接管他们的社区花园,而那是他们的老年中心利用一块遍布垃圾的荒地改造而成的。一位园丁扬言要用一罐汽油自焚,在警察局人质谈判小组的劝说下才作罢。在另一起事件中,警方接到报警,要求他们赶走一家麦当劳里的一群韩裔老人,因为他们整天待在那里,有时从清早待到天黑。
无论你来自哪里,纽约这样的城市可能都是养老的好地方。步行就能抵达商店和诊所,公共交通发达,所以不用开车也可以到处跑。无论你讲哪种语言,都能找到讲同样语言的群体,包括医生和社工。没人想成为亚利桑那州一个与世隔绝的退休社区里唯一讲闽南话的人,或者斯廷波特·斯普林斯的国标舞课上唯一讲他加禄语的人。
因此,尽管这座城市的本地老人数量减少,但老年移民的数量却出现激增的现象。城市未来中心2013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65岁以上的纽约人当中,有将近一半出生在外国。在全国范围,这个数字接近11%,从1960年开始持续下降。有些人(比如,乔纳斯·梅卡斯)年轻时代就来到这里,顺利地被这座城市同化。还有些人(比如,我在华裔或韩裔老年中心认识的人)来得比较晚,往往是被子女带来照料孙辈的,现在独自生活,不需要承担义务,也没有明确的人生目标。他们不怎么前往本民族聚居地以外的地方。在出生于外国的纽约老人当中,有将近四分之一生活贫困,将近三分之二英语熟练程度有限。该报告说,中国仅次于多米尼加共和国,是第二大原籍国,而来自中国的老人只有8%能讲流利的英语。这些障碍降低了老年移民利用现有的支持服务的可能性,增大了与世隔绝、孤独和抑郁的可能性。
昆斯区法拉盛庞大的韩裔美国人老年中心,正常情况下一天要为1300人提供服务。一位名叫金善的85岁女性给了我一些建议。她说:“别待在家里,学点东西。”她本人因为自己的国家遭朝鲜入侵而中断了学业。当我问她年轻人应该从长辈身上学点什么时,她嘲笑了这种想法。她说:“你们这一代比我们这一代强,所以你没什么可从我这里学的。你有更多机会,我们可以向你们这一代学习,我被战争害得没有机会学习。这不是什么痛苦经历。我的女儿们去上学,受教育,但我觉得我本来可以学得更多。”
我以为他们会思念或怀恋自己的出生国。美国文化是以漠视老人著称的,但我发现情况恰恰相反。我认识的所有人都不想回国,因为除非你很富有,否则老人回国后的生活更艰难。因此,他们互相紧挨着坐在荧光灯下的长桌旁吃热乎乎的饭、玩宾果游戏,或者看本国文字的报纸。很少有人讲英语。一位名叫钱倩的女士20世纪60年代跟随女儿从中国香港来到美国。她说,她不喜欢美国人对待老人的方式,但又马上纠正了自己的说法。她每个月领到将近1000美元的食品券和补充性保障收入,每个月只需要为她的廉租公寓支付略高于200美元的租金。她说:“差不多够用了,我认识的老人十有八九都享受这样的福利。”她还说,子女偶尔也给她零花钱。
冬天的一个下午,在她的公寓里,她炫耀自己朝南的窗户。她说:“这样光照最好,皇帝总是要面朝南的。”她的烦恼不在于年老,而在于她那个搬去了北卡罗来纳州、从不给她打电话的女儿。钱倩说:“她有钱、有时间去旅行,但抽不出时间到这里来。我的要求不高,只要打几个电话就行。她都不肯打,她快忘记我这个妈妈了。因为她在这里太久了,已经接受美国方式了。”
钱倩的儿子亨利正好从康涅狄格州过来看望她。他说,美国与中国的差别是,在中国,孩子理应照顾年老的父母,而在美国,这是政府的责任。他为自己的姐姐辩解,他说:“母亲节那天,她打过电话。”
钱倩说:“春节、生日和圣诞节,她会打电话,就是数得过来的几个日子。我有3年没见过她了。我不指望她总来看我,一天就行。有时候我特别想她,我一个人时会掉眼泪。”
最后,她说:“我很难过的是,我的孙子孙女完全不会讲中国话。他们都是在这里出生的。也许能说几个词,比如‘你好’或者‘奶奶’,但是很难交流。因为语言不通,我都没有他们的电话号码,而且他们很忙。”
我在老年中心遇到的其他人在社交方面有的合群,有的孤僻,有的很活跃,有的久坐不动,有的满意,有的沮丧,有的等死,有的迫切想活下去。当我遇到黄萍的时候,在她身上体现了所有这一切,而且还不止。
年老之后,成就还有多重要?
黄萍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就展现出她特有的语言风格。她说:“我不孤单,因为我来这里的时候,找了个给菲律宾心脏医生当翻译的工作。我在那里工作了8年,算是个过得去的翻译。在这里,楼里有30个华人租户,其中18个是广东人,所以我帮助老板接待华人。我们差不多每天都打麻将,所以我虽然一个人住,但还是很快乐。只要有牌局,她们就叫我过去。”
随着我逐渐了解黄萍,我开始注意到她的叙事模式。大多数故事会引出关于她人生中其他某个部分的简短经历,之后或者之前是一些人生建议,最后总是以麻将结尾。我看她打过几次麻将,并且惊讶地发现,除了向我解释游戏规则之外,这些女人打麻将的时候几乎一声不吭。黄萍有天下午在活动室的牌桌上解释说:“麻将靠打不靠说。我们没有精力顾别的,只能打。”
黄萍那年的大事是她一年一度跟女儿去大西洋城的旅行。近年来,那里有许多赌场关门,但对黄萍来说,这些旅行仍然是她期待的重头戏。然后,在4月,距离她90岁生日还有两星期的时候,她似乎陷入了情绪异常低落的状态。黄萍有个习惯,讲英语时会在无法预料的时刻大笑,也许是为了掩饰她讲这种语言时的别扭感觉,但这一天,她显然很沮丧:她确定自己不太舒服,不能去大西洋城。对于她患有风湿的身体而言,3小时的车程太长了。她垂头丧气地说:“当然,我为自己感到难过。我不想那么老。你越来越壮,我却越来越弱。”
她似乎越说越难过,就好像她突然被迫面对一直以来刻意逃避的事实。她说:“我告诉你一件有意思的事,有时候我不想活得太久。痛得太厉害了,我的骨头痛得要死。所以我有时候想死,不想活了。90岁,活得够长了。”
她很少会这样,而且这种情绪不会持续太久。这些话似乎使她有点不自然,等到我走的时候,她的语调已经恢复正常。但是,我不知道自己该相信她多少。
这种谈话中的反转(一会儿庆幸她的好运,紧接着又感到绝望)起初令我感到困惑,让我觉得黄萍积极向上的一面可能是为了给她楼里的租户或者同龄伙伴营造的一种快乐的假象。无论如何,谁都不想让别人觉得自己生活在沮丧的深渊里。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发现黄萍对自己老龄的矛盾看法是一种自我调节。满足感对她来说不是一种毫无来由的快乐,而是坦率承认自己生活中的困难——使她无法前往大西洋城的疼痛、失去丈夫和儿子的痛苦。这些老人当中的每一位在某种程度上都有上述的复杂感情,但对黄萍而言,由于语言障碍,所以表现得格外明显。
这显然是关于困境的经验,来自深谙此种处境的人。老年学专家认为,这种保持复杂感情而不试图加以化解的倾向是长者的智慧之一,是他们意识到了生活未必十全十美才算好,而且永远不会十全十美。麻烦总是伴随着我们,摆脱这一个或者那一个并不会使我们快乐,那样只不过会把另一个困难挪到队伍的最前面来。康奈尔大学的卡尔·皮莱默阐述了“尽管……还是快乐”与“只有……才会快乐”的区别,前者是变老的好处,后者是年轻的烦恼。“尽管……还是快乐”的含义是选择快乐,它承认问题,但不会让这些问题阻碍满足感。“只有……才会快乐”是把快乐与外部条件挂钩,只有当我更有钱、疼痛少一点、配偶或房子好一点,我才会特别快乐。“只有……才会快乐”使人一掷千金地买彩票或者冲动购物,但并不能真正给人带来任何快乐。相比之下,黄萍不指望她的困难会消失,所以没有把她的快乐与困难消失挂钩。她说,她年轻的时候觉得移民美国就能解决问题,但后来发现只不过是用新问题取代了老问题。她的经验是,要通过接受而不是消除痛苦和损失来获得快乐。
尽管这经验听起来很简单,但我发现它是最难实践的经验之一。我人生中的大部分成就(尤其是职业生涯中的成就)源自摒弃令我不满的事物,不是接受困境,而是努力抗拒它。我当然从未摆脱过困境,只不过发现了它的新面目,我的努力成了一种推动力。与黄萍和其他老人相处就是要重新审视这些成就,以及我们为之付出的努力。在80岁或90岁后,成就还有多重要?在我与老人们共处的一年里,他们都没有谈到自己的职业成就——考虑到我们把生命中的大量时间用于工作或者沉溺于工作,这真是令人惊讶。就连还在创作重要作品的乔纳斯·梅卡斯都是如此。老人们也从不提及他们克服的障碍。不知怎的,这些东西似乎不再是衡量人生的标尺。大多数人很高兴退休,只怀念职场的同事情谊。他们谈到的反而是家人或者亲密关系,他们衡量这些东西与衡量个人成就的标准不同——即便他们更富有或者地位更显赫,对子女的爱也不会因此变多。
研究人员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个大致的“设定值”,也就是我们在生活的起起落落中上下浮动的平均快乐水平。如果有好事发生——比如,我们赢了彩票,我们会高兴一阵子,但最后或多或少会恢复到之前的状态。遇到挫折也是一样。这个设定值似乎以基因和环境的某种组合方式为基础,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在危险环境中仍会快乐,而另一些人在令人艳羡的环境中都感到痛苦。但是,有证据表明,我们不是设定值的奴隶——我们可以实施经常性的感恩或利他主义行为,不为自己的麻烦焦虑个没完,从而提高这个设定值。黄萍接受疼痛是生活的一部分(不是快乐的障碍,而是伴随快乐而来),从而保持了乐观情绪。如果她要在生活中获得任何满足感,那是伴随风湿痛和其他损失而来的。她说,快乐就是“你有个好地方住,钱够花,家庭美满,就这么简单。你要趁着年轻的时候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我那时候喜欢旅行,世界多么精彩、多么不同!你应该周游世界,用你的钱去见世面”。
认清虚假的需求
黄萍的建议特别多。她说,趁你年轻的时候去看看世界。要挣钱,要花钱,要玩个痛快。享乐的时候不要以自己的健康或经济保障为代价,要对生活知足。她有一天说:“工作是快乐的,能让你活得更久。”她经常谈到为生命终结做准备,她的意思是在经济上而不是在思想上做准备。她说:“最重要的是给最后的日子留足钱。这里的一个租户是从中国来的农民,不肯谈自己的丧事。她说:‘如果我死了,让他们把我扔到垃圾堆里去吧。我干吗要为丧事掏钱?’”那一年里,黄萍把这段故事重复了好几遍,总是带着同样的不赞成态度和她自己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的自豪感。
黄萍和韩裔老年中心的金善一样,不相信年老会带来智慧的增加。她说:“年轻人应该比老人强很多。科学的发展让事情每天都在发生变化。现在人类都可以到月亮上去了,老人可想不到这个。年轻人关注过去的事情没什么好玩的,过去的事情大多数都是过去式甚至消失了,因为世界在往前发展。”
另一方面,她说:“年轻的时候,你不知道快乐或者悲伤是什么意思。”她像其他老人一样,在生活中损失了太多东西,所以知道哪怕是最严重的损失,也只有在她把它看成灾难的时候才具有灾难性。她有天提到一个邻居最近去世,还有一个搬到养老院去接受失智症护理。她说,这两个损失都让她很痛苦,但悲伤也可以具有治疗作用。她说:“这让人伤心,但这种事情总是有的。人生太顺不是什么好事,你要训练大脑应付艰难的挑战。事情过去之后,就不要再想了。下一次要汲取经验,我从损失中学到了东西。如果你从来没遇到过倒霉事,遇到的时候就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当我把自己的生活与黄萍对比时,我惊讶地发现,我有那么多“需求”都是她没有但也设法凑合过来的:职业成就、父母的认可、美满的婚姻、健身时间、农夫集市上新鲜的豆芽、费用昂贵的公寓。尽管我不想放弃所有这一切,但与黄萍相处帮我看清了它们是虚假的需求,意味着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但只在有些时候才能得到回报。就连丧失一定的行动能力(我的右脚因为韧带撕裂而穿上了步行靴)都不会像我之前以为的那样影响我。我的生活仍然是我的生活,仍然是我在过我的生活。黄萍的经验之一是,我可以保留这些“需求”,但我应该基于它们的实际价值,而不是当作我害怕失去的东西来加以珍惜。不同的工作、不同的住房、腰间赘肉又增加了一点,这些都不会显著改变我的生活。它们并不像我以为的那样重要。
年中的一天,在唐人街的一家点心店,我问黄萍,她会给年轻时的自己什么忠告。她邀请我跟她女儿伊莱恩一起外出。伊莱恩住在新泽西州,当时62岁。伊莱恩说,跟母亲在一起的时候,她经常想到自己的老年。她说:“我看着她,会想到我老了之后是什么样。我想我不会像妈妈这样健康,她看起来比我健康。她总去锻炼身体,我很懒。”黄萍居住的那个楼里开设固定的健身课程,她过去几年一直都参加,但我认识黄萍的时候,她也说自己太懒,所以不去锻炼了。伊莱恩说,在过去的一年间,她发现母亲出现了失忆的症状,而且最近越发频繁。这一天,黄萍似乎因为花力气外出而感到既疲乏又兴奋,还因为气候潮湿而浑身疼痛。她说,她最近在看西德尼·谢尔顿的小说,她很喜欢,因为这些小说使她沉浸在主人公的喜悦和绝望之中。
她的建议似乎既是给年轻时的自己提的,也是给女儿提的。她说:“我会告诉年轻人,不要想着自己变老的事。总想着老了以后、老了以后,老了以后是不好的。老了当然很可怜,或者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是不好的。你怎么知道?所以我要告诉他们,别想得那么远。想想眼前的事,怎么保证积极向上、健康、挣到钱就行,还有怎么正确而不是错误地花钱。没必要想着变老,保证健康、强壮、挣到钱就行。”她开怀大笑,好像要驱散所有自怨自艾的气息。她说:“世界越变越好。要说我自己的生活,我也越来越好。”
生前遗嘱的意义
运气帮了她大忙。2005年,黄萍偶然在一份中文报纸上看到一则关于曼哈顿格拉默西公园附近的一幢新建老年廉租公寓的启事,租金不超过住户扣除医疗支出后的净收入的30%。第一批有超过700人申请,但黄萍是最早入选的人之一,她甚至得到了一套有两间卧室的公寓,还因为帮助管理不会讲英语的华人住户而每星期领取50美元的补贴。作为回报,她的一个新邻居告诉她可以从哪里申请一位免费的家庭看护。她说,这些福利使她能够“独立”,也就是说,她不用跟女儿住在一起。因为乘车上班直到将近80岁,所以她觉得自己现在有权获得政府的支持。
她找到的这幢楼是卡布里尼公寓,配备了内部社工,还偶尔组织活动,楼房管理员菲利普·迪恩斯特意结识了所有住户。私下里,住户们帮助彼此去借助可用的社会服务。被黄萍称作“老板”的菲尔·迪恩斯说,在对付包括家庭护理机构、辅助运输服务和食品券在内的市政官僚体系方面,她“超出了平均水平”。他说:“她清楚这一点,但不知道该怎样加以利用。”他还说,她非常外向,而且跟楼里的社工关系融洽。
尽管她有健康问题,尤其是关节疼痛,但她努力把心思放在其他事情上。她有天说:“我从没想过死。死是一件想起来就令人非常不愉快的事情。我躺在床上,舒舒服服的,但我说,要动一动。老人应该学着不要抱怨太多。别人不会安慰你,你应该安慰自己。”
她会做选择。她不喜欢锻炼,所以她通过照看窗台上的花草来保持身体活跃。当她的联邦医疗保险处方药物保险计划停止负担她用来缓解风湿痛的远疼贴贴片时,她把现有的贴片剪成小块,还服用泰诺作为辅助,足以缓解疼痛并支撑她完成日常活动和麻将牌局。打麻将也使她能活动双臂和锻炼大脑,让她留在能保持活力的社交世界里。她说,定期打麻将使她不至于感到无聊或者孤单。她有天赢了一圈,要大家把牌推到她这边来,因为她的胳膊伸到那么远会感到疼痛。她在桌边说:“你要动脑子,要活动身体,哪怕光是手也好。”她说,好日子就是“我赢了麻将的日子,我觉得快乐。我们打麻将不是为了赢钱,但努力去打赢会让我的脑子更灵活”。
当我向黄萍询问长寿的秘诀时,她说:“首先你必须让自己快乐。没有人能说,我没遇上过不好的日子、艰难的日子。你这一辈子当然会有好日子和不好的日子。我儿子没了的时候,我有两年都睡不好觉,整整两年,每天晚上都睡不好。后来我调整了自己,因为我在这边有个特别孝顺的女儿。我对自己在这边的生活相当满意,我能住在这栋楼里真的很幸运。”
黄萍就是这样教给我如何像老人那样思考的:尽量灵活,要不断调整目标或者人生的意义所在。年轻人可能会因为取消大西洋城之行而久久无法摆脱失望的情绪,执意觉得这次旅行会使她与众不同。但黄萍却发泄了出来。她知道如何放弃曾经对她很重要,而如今已不再重要的东西,知道在她能得到的所有东西中选择快乐。
这条经验使我的生活轻松多了。满足我的虚假需求是项浩大的工程,一旦我开始放手,就得到了解放,可以专注于更有回报或者更加持久的东西。这也意味着我可以不再为所有自己觉得该做却没有做的事情而感到内疚。别人可以去做正念练习,而我可以找台碎纸机处理我的旧银行对账单。事实表明,农夫集市上的新鲜豆芽检验合格。它们不需要费劲处理,而且能让我吃得有营养。我生活中的其他东西并不那么重要:我的一半衣服和其他财产,工作中或者社交媒体上的争吵,某些实在令我不快的朋友和家庭成员——我都可以直接放手,毫不留恋。
老人认为重要的东西往往会令年轻人感到困惑。1993年到1994年,4所大学医疗中心的研究人员问80岁以上的住院病人,他们愿意以目前的健康状况活一年还是以非常健康的状态活一个较短的时期。然后,他们问这些病人的医疗代理人(往往是子女)觉得病人会怎样回答。这是在测试老人(尤其是有严重健康问题的老人)有多看重自己的剩余寿命。代理人认为,问题是明摆着的:患病的八旬老人当然会放弃卧床住院的时间,选择比较健康但短一些的人生。但是,老人们的回答让他们大吃一惊。大多数人说,他们只愿意为非常健康的状态放弃顶多一个月的生命,有40%的人说,他们一点时间都不愿放弃。他们选择时间而不是健康。当这些病人一年后再次接受访谈时,他们愿意为非常健康的状态放弃的时间更少了,平均是两个星期。
失智症是许多年轻人最大的恐惧,但英国精神健康基金会2010年对44名失智症患者的生活进行调查的一份报告显示,就连失智症患者,都远比他们的护理人更认可生活质量。这些研究人员以为人们会根据自己的病况评估生活质量——大脑越退化,生活质量越差。这也是护理人的看法,他们通常是家庭看护者。他们认为患病父母的生活质量很差,而且越来越差。但是,失智症患者本人对自己的生活有不同看法,评判生活质量的标准不是他们失去的东西,而是他们能做的事情——与朋友或家人共度时光,在智力上挑战自己,享受大自然。他们并不认为失智症是关于他们的最重要的事情。
正如研究人员所说的那样:“在情绪、感受和精神健康方面,失智症对一个人的生活质量的影响可能与我们预想的不同。”即便随着病情加重,他们的记忆和认知能力被剥夺了更多,但他们对生活质量的评估仍然不变。研究人员说,这既“违背直觉”,又是“重大发现,更多的人开始使用生前遗嘱,人们其实是在通过这种方式预言他们未来可能对患有某些特定疾病的生活有什么感受”。很显然,对许多病人的看护者来说,失智症降低了生活质量,而在阿尔茨海默症和其他失智症的破坏力的问题上,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他们的观点。
到了5月过生日的时候,黄萍觉得身体不错,和女儿一起去吃了自助午餐和晚餐。然后,在夏末,她得到了一份惊喜:她的儿媳和孙子从中国来看她,还打算去大西洋城。他们要带来一个她素未谋面的曾孙。这让黄萍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疼痛问题。这种疼痛真是完全不可掌控的吗?抑或是她可以为享受见到家人的愉悦而忍受的东西?哪个对她更重要?3小时的车程似乎不再是她生活中最重大的事。尽管她知道自己要忍受疼痛,但还是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去大西洋城。她后来说,这是她夏天做的最明智的决定。她说:“当你很快乐的时候,你会忘掉一切,我们一路上都在聊天,所以我忘了身体的疼痛。”
不过,这一年里,黄萍的一些变化是可以察觉到的。她的话变得更加前言不搭后语,而且很难保持连贯的思维。然后,在2016年2月,出现了令人不安的迹象。她打电话说要跟我谈点非常重要的事情,不能等。但等我到了她的公寓,她却想不起自己为什么打电话了。她为自己的糊涂哈哈大笑,她说:“老了,记不住事了。”但这次失忆显然令她不安。这是新动向,是采访项目中的六位老人一直有可能出现的动向。她缓缓站起身来,环顾房间,好像在为自己失去思路而感到惊讶。它跑到哪里去了?但她无疑还是那个黄萍,用漫长人生的零散碎片构建自己。她看到过朋友患上失智症。现在,她的一块碎片也不见了。她用哈哈大笑掩饰自己的尴尬。这是否意味着她明天会忘记更多的东西?抑或在她见多识广、勇往直前的一生中,这只不过是又一个损失而已?最后,她想起来了——她想让我向楼房管理员投诉她的新油地毡。这就是年老的矛盾力量——一股朝向秩序,另一股朝向衰败:尽管记忆滑向紊乱,但黄萍还是在努力坚持着塑造自己的世界。
当我几个月后再一次去探望她时,她糊涂的迹象不见了。记忆和年老也是这样,好日子和不好的日子,这两者都不能保证明天仍会如此。她清楚地讲述了自己在需要用配给券买米的时代的生活,以及她在这幢楼里最初几年的生活。她又快过生日了,可能会再去大西洋城——她不太确定。如同我以前探望时一样,她炫耀了去欧洲旅行带回的纪念品,包括从捷克共和国带回的红酒杯,这一切提醒她,即便现在很少离开这幢楼,她也还是个旅行者。
黄萍的家庭看护拿出一张黄萍年轻时的照片,黄萍笑了。她说:“她想让你看看我原来有多漂亮。”她停下来,又笑了,“那是以前,现在已经是老太太了。”
不过,她仍在努力改善自己的处境。她要求找人辅导她学英语,她说,现在多学一点还不晚。她问:“如果你和我是多年的好朋友,我们可不可以说‘我想念你’?”
她现在对地板上的新油地毡很满意,尤其是对比被替换掉的破旧地毯。她说,这不是很大的改善吗,不是又一个让她觉得住在这套公寓里是种福气的理由、又一个让她快乐的理由吗?她在做的,是她一直以来所做的——根据她面对的世界调整自己的期望,而不是与之抗衡。这是她选择快乐的方式。就连她的记忆紊乱都构成了又一个值得庆幸的理由。
她在谈到油地毡的时候说:“很干净,对我的健康更有好处。”她又笑了,“也许我会活得更久,那你就还得来。”笑声渐渐变小,但没有消失。那是我最后一次听到她那样大笑。 如何优雅的老去(套装共5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