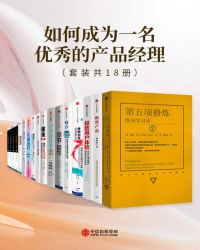第13章 领导力:修身成人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产品经理(套装共18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第四部分
直面未来
第13章 领导力:修身成人
2001年12月
几个星期后,我们四人又见面了。在这之前,我们都在思考第二轮“感知”采访中的谈话内容。
***
“我们正面临领导力的危机。这个看法也许并不新奇,但我听到了新的说法。”贝蒂·苏说,“如果我们正处在一个时代的终结,那一定需要一种新型领导力。”
“新现实必定要求对领导力的新思考,从前也发生过这种情况。”彼得说,“关于领导力的最古老的观点之一,是‘权力必须辅以智慧’,这似乎是2 500年前中国和希腊形成大型城邦时代的观点。大型机构有更大的组织力量,它的出现让人们意识到需要应对这种组织力量可能带来的危险。柏拉图与格劳孔(Glaucon)在《理想国》(Republic)中有关哲学家国王的对话,与管子及后来的孔子奠定中国领导力思想基础的时代,前后不过100年。我觉得这不是巧合。这两组文化观念在很多方面都惊人地相似,它们都认为需要用道德修养来防止滥用这种新的组织力量。
“我不禁在想,我们今天也处在一个非常类似的时期。全球化正以史无前例的规模重塑各地的社会和文化。然而,那个古老的观念——影响这些组织力量发挥的权威领导者必须投入修炼或道德发展——却已经完全消失了。我怀疑,甚至很少有人考虑过这种修炼方法:如何开发延迟获得满足感的容纳力,观察行为的长期效果的能力,以及进入心灵宁静状态的能力。古代希腊和中国都认为这种修炼要在大师的指导下完成,是要花终生精力努力完成的人生修养功课。”
“但许多人似乎认为这些老观念与今天技术驱动的现实格格不入。”贝蒂·苏说,“我们的领导者更倾向于做技术专家,而不是哲学家。他们关注的只是获得并使用权力、驱动变革、影响他人,并维持一种掌控局面的形象。”
“没错,老观念不那么吃香。”彼得也表示赞同,“过去一两代人的时间里,‘老’这个字眼儿本身已经变成一个轻蔑的词汇,变成破旧和废弃的同义词;而‘新’就自动变成‘改进’和‘优越’的意思。这对描述机器可能完全适用,但用在生命系统上就很不幸了。
“几年前,我们的一个好朋友、领导力领域的知名作家戴巴西什·查特吉在麻省理工学院一次领导力研讨会的开场白中说,‘我的工作的指导思想是,老的往往就是更好的。延续了几千年的思想已经接受了许多检验,这是一项很好的指标,意味着它可能真有些价值。我们现在都固执地偏爱新东西,这往往会误导我们,错把新颖性抬高,凌驾到实质内容之上’。”
“而当我们失去对‘老’的东西的敬重,老年人也被我们忽视了。”约瑟夫说,“智慧被技术专长取代,长岁数也被看成是从年轻有为向年老虚弱状态的一条长长的下坡路。”他皱眉继续说道,“我觉得,这些变化对人类幸福和社会稳定的损害,真是无法估量。”
“古代希腊和中国的这种关联让我感触很深。”奥托说,“在所有采访中,在香港与南怀瑾大师的那一次会面最有趣。尽管是彼得把我介绍给南老师的,但我们还从未谈论过那次采访。我认为,我们现在对U型理论的理解,有许多早已在中国文化中存在了,虽然它的意义在今天已经被人遗忘。尽管在海外还鲜为人知,但在中国,南老师被看作是活着的禅宗大师中最重要的一位。他同时还是一位道学大师和(有人会说‘最’)杰出的儒学大师。他出版了40余部著作,在中国的销售量有数千万册。他还被认为是中医、古诗词、风水和物理结构设计方面最高水平的专家,并且是中国的军事战略专家和原中央国术馆第二期武术冠军。”
奥托终于换了口气。彼得微笑道:“南老师的成就发生在他一人身上,真是不可思议。一位在中国的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告诉我,过去中国皇帝的国师是要把所有这些中国传统融于一身的,还说,‘他可能是这个传统中的最后一位了’。”
“我一点儿都不吃惊,”贝蒂·苏笑着说,“我们的现代文化不鼓励那样的发展路线。不过奥托,你是说南老师谈到U型理论了?”
“其实还不止于此。那次我们在一开始就谈论他的一部新著——《原本大学微言》。这本书是对儒家经典《大学》的新阐释。《大学》原文最早是在2 400年前写下的,并从那时起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的一部分。我的一位翻译告诉我,‘每个皇帝都尊崇这部著作,因为它论述了如何成为一名领导者’。尽管如此,但大家都在肤浅层次上熟悉它,以至于它的深层含义已被人遗忘。另一位翻译彭嘉恒告诉我,明清科举,特别是在清朝,就是1644年开始的中国古代最后一个朝代,指定了考试要以宋朝朱熹注解的《四书》《五经》为标准,从而禁锢了走科举道路的知识分子的思想。然后南老师补充说,儒家领导力修炼理论的核心是‘假如你想成为领导者,你就必须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你必须认识到生命的真正意义,才能成为优秀的领导者。你必须先了解你自身’。”
约瑟夫点头说道:“奥布赖恩曾经讲,‘介入是否成功取决于介入者的内心状态’。这远比变革策略或技巧重要得多。”
“没错,”奥托应和道,“从这个意义上讲,修炼过的自我就是领导者的最佳工具。这个理念是古代中国和印度的传统思想的基石,也是许多本土文化思想的基石。
“这一传统理念被遗忘的原因之一是其困难性:它要求终身的实践体悟。许多曾经指导学习者走过这个修炼历程的具体操作知识,已经被主流现代社会遗弃了。中国社会同样如此,尽管那里还保存着这些古代教诲的部分元素。南老师的新阐释的独到之处,就是解释了《大学》中其实提供了领导力修炼的详细理论。
“‘假如你要成为一名伟大的领导者,’南老师说,‘你就要进入七证修养:知、止、定、静、安、虑、得。这看似简单的一步,实际上是一个很长很长的过程。’
“彭嘉恒解释说,前两步修养:知、止,正统的解释是知道自己的社会位置,不能逾越职位,越权行事。南老师对《大学》之‘知、止’的解释非常不同。他说原本的含义是自觉能知之性与止息思想杂念。
“在场的一位教授说,这对领导者来说很重要,因为如果不达到这个境界,他们就会被各种情绪干扰,如贪、嗔、恐惧、担忧等,因而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南老师讲了一个古代中国名相的故事。当时中国分为许多小国,这位先生的一个儿子在邻国被俘,即将被斩首。他想派小儿子去营救,大儿子却反对,说‘你派弟弟去就是认为我无能,派我去吧’。
“父亲不再坚持了,就派老大去营救狱中的儿子。老大找到邻国的一位宰相求情,为营救兄弟送了很多钱财。那位宰相没有明确说要帮忙。但宰相找到一个机会,说服了君王大赦天下。当然那个孩子获救了。听到这个消息,老大很高兴,心想:‘太好了,反正所有犯人都要放了,也不是宰相帮的忙,我看能否把那些钱财要回来。’宰相听说了他的话,二话没说,就还了钱给他。但宰相却跟君王说,可以释放所有犯人,但因为种种原因,某人应该除外。结果那个孩子就被斩首了。
“老大带着兄弟的尸首回国了——他父亲对派老大前往的担忧被证实了。为什么呢?因为老大的成长是伴随着父母辛苦创业的,知道每分钱来之不易,内心习惯了悭吝,不会轻易将财物送人;而小儿子成长于家庭富裕之时,出手很大方,没有这种对钱财的执着。
“‘执着就会妨碍我们的判断能力,阻碍我们的感知。’那位在场的教授告诉我,‘不知道如何‘止息’习惯的执着,就是这个意思。’
“‘在佛教里,’彭嘉恒说,‘思想就像瀑布,你看到瀑布,只能看见水流不断,好像帘子一样。但我们都知道,水流其实是由水滴组成的。思想也一样。我们的心念流动很快,好像瀑布一样。但如果你能知,能止,你就会觉察到:思想也不过是小水珠的样子。’
“‘思想念头,’南老师说,‘就像这样一个个地流过。大多数人看不到两个念头之间的空隙。修得好的人能看到“念头每时每刻都在变,我们总是被自己的思想欺骗”,但大多数人却以为那是真实的。’
“我们一旦看到自己的念头,止就自动发生了。‘你一旦对此能知,你就已经在止了,’彭嘉恒告诉我,‘在能止念之前,不会出现实质性的问题和探索。在止息之前,我们的目标和宗旨不过是我们过去状态的反映,而不是当下的真正需要。’”
约瑟夫坐直身体兴奋地说:“儒家的理论和U形过程的下行段似乎非常相像。通过止息思想杂念来觉知自我和世界状况,这与瓦莱拉的悬挂假设概念,并从习惯的思想流动中解脱出来,非常一致。”
“没错,”奥托回应道,“南老师解释了其他五项修养以后,这种一致性就更清楚了。他做了一个简短的小结:‘你一旦得止,就能进入第三阶段:三摩地,或定境。达到真正的定境,才能得到真正的静默。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这个虑,代表“精思”,就是慧观,是真正的思想,而非通常情况下的妄想;然后才能有所得,取得你想达到的成就,你本应达到的目标。’
“领导力开发的七证功夫主要有两种行为。第一个是‘进去’,即从常态意识进到一种真正的安静状态,即我们所说的U形底部。第二个动作可以称为‘返回’,即回到常态活动。‘返回’带回一种新觉知,并保持了深层的当下体悟。尽管语言文化不同,这也正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理解的过程。每个特定阶段的相似之处也是很让人吃惊的。比如,南老师说,当意识进入初禅定境时,就可以看见‘生命的运作过程’。这与我们所说的再引导或再定向集中我们的注意力,观察表面现象背后的生命过程非常相似。”
“所以说,前三步修养,知、止、定,都涉及在更深层次上观察现实,是感知的核心内容,是U的下行段。”约瑟夫说。
“对,”奥托说,“我问是否可以把这三步修养理解为深层观察现实的方法,彭嘉恒回答说,‘这是观察现实的唯一方法’。
“南老师也说到自我意识的转变,我们现在知道这是U形底部的经历。在表面稳定的思想流里面有根深蒂固的习惯思维方式,它决定着我们最基本的经验内容和信念,包括通常的自我观念。我们把自己的自我观念当成真实的东西。但南老师说,‘思想观念不是自我,不是这个人。念头是老在变的’。根据《大学》理论,在我们切断日常的杂念之流,并接触到深层经历以后,就会出现静和安。这时,南老师说,‘你就会抛弃习惯的自我观念了’。”
“那是瓦莱拉描述的发现‘自我的实相’,以及大桥良芥所说的‘陌生的自我’。”约瑟夫确认道。
“对。后来南老师又说,‘我们说“我们”、人,实际上这只是个符号,代表某种东西。最终严格地说,人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不是实存’。”
“这正是大桥良芥所说的‘空无’在‘支撑着我的存在’。”彼得说,“日常意识状态中的自我有这种虚幻的一面,这对西方人来说非常难理解,但它却是东方思想传统的基础。
“我知道佛教的基本概念之一是现象世界的空性。这和物理学对现象世界的理解又联系起来了,即所有现象都在不断地变动流转中,包括我们的身体和物质的自我。我们通过思想把这些东西具象化,在我们的意识里塑造物质性实体的形象,但这个形象是个虚幻的错觉。普遍来说,东方哲学中真正核心的概念就是,在这个现象世界之外还存在另一个维度的现实,那个现实其实更具实相、更永久,而看到那个现实的方法是通过我们控制自己的意念来修炼的。这就是物理学家戴维·波姆花了10年时间与印度哲学家克里希那穆提对话,探索隐性秩序和现象背后的生发力场的理论与印度哲学的比较联系的原因。我认为这也是许多我们采访过的科学家都是各种东方修炼方法的严肃实践者的原因。”
“修习和修炼至关重要。”奥托说,“儒家理论针对的是个人‘修炼’或修养发展的长期实践。南老师说,尽管不要求固定的时间,但‘进入这些修养’是领导力修炼的一个‘很长很长的过程’;用东方的概念讲,这可能是许多世的修炼历程。我们在试图理解U形过程所要求的容纳力究竟是什么。而佛家、道家和许多其他传承都有丰富多样的工具和方法来开发这种容纳力。但如果我们个人对修炼没有承诺和行愿,讨论这些就都无关紧要了。
“尽管当时并没有看到与U形过程的完整关联,我还是问南老师:‘先放慢节奏,反观内照,同时静观世界,直到能够观察和体悟当下正欲呈现的现实。然后再回到世界中来,并带回一种独特的行动和创造能力。这好像和《大学》讲的领导力修炼很一致。这么理解对吗?’
“他确认这一理解符合他的意思,但不是唯一的理解。他说,‘也许你以后还会发现其他理解方法’。”
“你知道,这很令人惊异。我们追寻一个问题,最终达到智者们先前已经达到的境界,却又‘第一次理解了它’。”贝蒂·苏说,“但我认为还需要指出,尽管在过去,领导力修炼是智慧传承的重要内容,但未来将会有所不同。这一点很重要。未来的领导力不会简单地由个人表现出来,而是需要群体、组织、社区和网络来实现。
“现在,群体进步的障碍之一,就是认为必须要等到有一位领袖出现,一位将未来的道路具体化现于自身的人物。但我觉得,我们在U形过程中学到的,是未来可以在群体内部呈现出来,而不是化现在某个‘英雄’或传统的‘领袖’人物身上。我认为这是走向未来的关键:我们必须培育一种不依赖于非凡人物的新型领导力。”
“我完全赞同。但那对个人修炼又意味着什么呢?”奥托问。
“我认为个人修炼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了,”贝蒂·苏回应道,“但那要有更多人的参与。而且,这种修炼将在更大的集体中进行。我们需要学习实践能够帮助群体和社会系统开发智慧的修炼方法。”
“这是界定我们这个时代领导力特征的决定要素。”彼得严肃地说,“在由全球性组织网络组成的世界里,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是等级体制的领导力根本无法有效应对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世界与2 500年前孔夫子和柏拉图领导力理念形成时期的重大区别。
“我们在和大型企业甚至全球性跨国公司的CEO合作时,总是能体会这一点。局外人很容易对他们的影响力过分高估。记得一位先生半开玩笑地说,他曾一直想象着,一旦他最终爬到公司的最高位置,他就可以从自己的办公桌下面发现那些操纵杆,让事情发生。他说他最终坐上了最高位置,但并没有在桌子下面发现任何东西。这种经历让人清醒。我认为这对国家元首也同样适用。等级体系的高层确实有独特的权力,但那往往倾向于破,而非立。CEO可以在几个星期内破坏多年建立起来的分布在各个角落的知识和信任关系。发动战争的权势远比赢得和平的权势要大。”
“把组织等级体系的高层领导力模型转向更分散与分享式的网络模式,会引起许多变革。”贝蒂·苏说,“要让各类网络有真正的意识来参与协作,许多人都将需要有深层的承诺行愿,来开发服务于正在呈现的现实的容纳力。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修炼‘成为真正的人’,正是我们时代领导力的首要问题,而且这必须在史无前例的范围展开。这是个非常古老的理念,但可能正是‘全球民主’新时代的关键所在。” 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产品经理(套装共18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