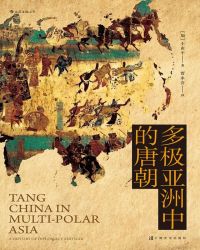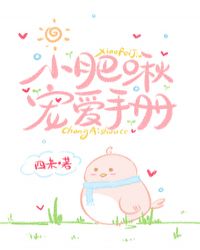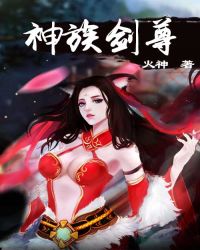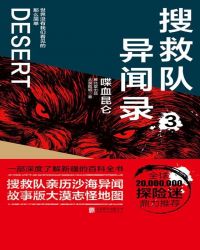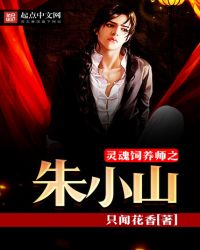太宗与高句丽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多极亚洲中的唐朝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
太宗与高句丽
但是,合宜性和功效性并总不能确保唐廷一定会采取明智的对外政策。这并不奇怪。这两个概念有多重意义,唐廷官员常常用它们为相互冲突的政策建议辩护。有些人不切合实际地坚持唐在世界的中心地位,有的则顽固地认为唐应履行对朝贡国的道德义务。不仅如此,高祖和太宗都是老谋深算的实用主义者,不相信任何教条,愿意采取任何他们认为恰当的措施去处理复杂的国际问题和化解难以预料的危机。作为天子,他们将决定什么是“合宜”的国际行为,采取怎样的行动才符合唐及四邻的最大利益。不过,皇帝有时会误判唐廷的真正利益,实施灾难性的对外政策。太宗征高句丽遭遇惨败就是一个有名的例子。
625年,裴矩和温彦博劝高祖不要对高句丽的不敬之举无动于衷,因为“若与高丽抗礼,四夷必当轻汉”。太宗627年登基后,主动调停朝鲜半岛的争端。他对百济王说:“朕自祗承宠命,君临区宇,思弘王道,爱育黎元。”他命百济王立即停止进攻新罗:“新罗王金真平,朕之藩臣,王之邻国。……王必须忘彼前怨,识朕本怀,共笃邻情,即停兵革。”此时太宗对朝鲜半岛事务似乎还是持中立态度。但到了七世纪四十年代,他改变了立场。
643年,为参加荣留王葬礼而出使高句丽的唐使邓素建议唐廷在怀远镇(今辽宁怀远)部署更多士兵,对高句丽施加压力。太宗拒绝了这个提议,还训斥邓素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未闻一二百戍兵能威绝域者也。”但唐使告诉太宗,渊盖苏文派人暗杀了高句丽王,攫取了高句丽大权,自任兵部尚书、中书令,还将一名傀儡立为国王。太宗因此开始暗中谋划惩罚高句丽的远征。
然而,长孙无忌认为,计划中的惩罚行动缺乏正当性,因为不管是高句丽王室还是大臣都没有向唐廷控诉渊盖苏文的所作所为,也没有要求唐廷采取行动。长孙无忌建议太宗不要理会篡权者,并承认傀儡国王。这种做法能安抚高句丽王,对其提供支持,最终将其争取过来。太宗依长孙无忌之计行事,决定承认高句丽现状,并册封傀儡君主为上柱国、辽东郡王、高句丽王。太宗还用上古圣王的“礼不伐丧”的例子为自己辩护。
644年,司农丞相里玄奖将册书交给高句丽。册书开篇写道:“怀远之规,前王令典,继世之义,列代旧章。”这或许是到那时为止唐廷颁布的最心口不一的诏书,因为太宗将在当年稍晚时候亲率大军征讨高句丽。但相里玄奖对此一无所知。他极力劝说渊盖苏文放弃从新罗夺回失地。他说:“既往之事,焉可追论!至于辽东诸城,本皆中国郡县。中国尚且不言,高丽岂得必求故地。”但渊盖苏文断然回绝了这个建议。
渊盖苏文拒绝听命,正好为太宗出兵高句丽提供了理由。他宣称:“盖苏文弑其君,贼其大臣,残虐其民,今又违我诏命,侵暴邻国,不可以不讨。”不过,太宗虽然声称征高句丽是正义之举,许多唐廷官员却并不赞同。褚遂良称这次行动是“兴忿兵”。他还担心,太宗亲征是以身涉险。但太宗对褚遂良的意见置之不理。他相信现在是行动的良机,而且胜利是唾手可得的。他说:“[高句丽]民延颈待救,此正高丽可亡之时也。”太宗为表示自己对渊盖苏文的不满,故意怠慢早些时候与相里玄奖一同来长安的高句丽使者。他拒不接受渊盖苏文的礼物,还斥责高句丽使者道:“汝曹皆事高武,有官爵。莫离支弑逆,汝曹不能复仇,今更为之游说以欺大国,罪孰大焉!”太宗下令将使者关押在大理寺。
太宗在离开首都之前接见了一些长者,他们的儿子或孙子将作为士兵参战。太宗为了鼓舞军队的士气,赐给长者们大量布匹和粮食,还保证会细心照顾这些士兵,让长者们“毋庸恤也”。但太宗其实也没有必胜的把握。他坦言,这次行动是“去本而就末,舍高以取下,释近而之远”。尽管如此,他仍然固执地认为,那些意见与自己相左的官员未能看到高句丽百姓正翘首等待唐军把他们从篡权者的独裁统治下解救出来。
644年阴历十月,太宗颁布诏书,开始亲征高句丽。诏书开篇便愤怒地声讨渊盖苏文的罪行:“高丽莫离支盖苏文,杀逆其主,酷害其臣,窃据边隅,肆其蜂虿。……若不诛剪遐秽,何以惩肃中华。”有人怀疑,这次耗费不赀的军事行动会重蹈隋征高句丽的覆辙,以惨败告终。太宗为打消人们的顾虑,宣称自己的高句丽之行将免除一切不必要的繁文缛节。
太宗相信,唐军英勇善战,自己的军事战略才能出众,内部形势也对出征有利,这些都确保他能够取得胜利。他说:“朕缅怀前载,抚躬内省。昔受钺专征,提戈拨乱,师有经年之举,食无盈月之储,至于赏罚之信,尚非自决。然犹所向风靡,……以定海内,以安苍生。然则行军用兵,皆亿兆所见,岂虚言哉!……北殄匈奴种落,有若摧枯;西灭吐谷浑、高昌,易于拾芥。包绝漠而为苑,跨流沙以为池。皇帝不服之人,唐尧不臣之域,并皆委质奉贡,……此亦天下所共闻也。况今丰稔多年,家给人足。……虽足以为兵储,犹恐劳于转运。故多驱牛羊,以充军食。……如斯之事,岂不优于曩日!”
诏书结尾处列举了唐军的五大优势:以大击小,以顺讨逆,以安乘乱,以逸待劳,以悦当怨。因此,唐征高句丽“何忧不克,何忧虑不摧。可布告元元,勿为疑惧耳”。
但太宗没能说服太多官员支持这场战役。他在赴高句丽途中来到东都洛阳,听取了郑元璹的建议,后者曾参加过隋与高句丽的战争。郑元璹向太宗着重指出高句丽之役的两个战术难点:唐军的后勤补给和高句丽的顽强抵抗。但太宗对他的看法不以为意,告诉他:“今日非隋之比,公但听之。”
曾用“枝干”比喻唐与四邻关系的李大亮也在洛阳。他同样认为高句丽之役是严重的战略失误。此时李大亮已重病在身,但仍然上书劝皇帝放弃军事行动。他在奏章中写道:“京师宗庙所在,愿深以关中为意。”李大亮的意见也没有任何成效。
此时的太宗一心想着报仇,已经丧失了理性思考的能力。他在定州(今河北定州)对随从说:“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能得;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高丽雪君父之耻耳。”在太宗看来,征服高句丽将使未来辽东安宁无事,这将是他对唐朝最大贡献。
但高句丽之役的发展完全出乎太宗意料。高句丽西部与渊盖苏文对立的势力没有开城欢迎太宗,也没有揭竿而起反对篡权者。相反,他们在安市城顽强抵抗唐军。太宗首次征服高句丽的尝试以失败告终。
回到长安后,太宗开始反思在高句丽遭遇的挫折。他承认自己在战术上有一些失误,但不认为征服高句丽的计划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他与太子的对话清楚地显示了他的这种心态。648年正月,他将自己刚刚完成的《帝范》赐给太子,并对他说:“汝当更求古之哲王以为师,如吾,不足法也。……吾居位以来,不善多矣。”随后,太宗列举了自己曾经犯下的一些过失:“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但他只字未提自己在高句丽的失败。
其实,太宗在《帝范》第十一篇《阅武》中批评了好战之徒。他写道:“夫兵甲者,国之凶器也。土地虽广,好战则人凋;邦国虽安,亟战则人殆。”太宗当然不认为自己是这样的好战之徒。但许多朝廷官员,包括受他宠幸、直言敢谏的妃子徐惠,都认为皇帝在高句丽问题上犯了大错,征高句丽本身就是穷兵黩武的行为。她上书批评太宗道:“以有尽之农功,填无穷之巨浪;图未获之他众,丧已成之我军。”她得出结论:“是知地广非常安之术,人劳乃易乱之源也。”
太宗“善其言,甚礼重之”,但没有接受她的谏言。不久之后,太宗开始准备第二次征高句丽。曾在高祖和太宗两朝任宰相长达三十二年之久的老臣房玄龄对此深感忧虑,当时他已经病入膏肓。648年阴历六月,他对儿子们说:“当今天下清谧,咸得其宜。唯东讨高丽不止,方为国患。主上含怒意决,臣下莫敢犯颜。吾知而不言,则衔恨入地。”房玄龄上了一封措辞强烈的奏章,力劝太宗取消军事行动。他写道:“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开疆,亦可止矣。彼高丽者,边夷贱类,不足待以仁义,不可责以常理。古来以鱼鳖畜之,宜从阔略。若必欲绝其种类,恐穷兽则搏。”
房玄龄认为,只有当高句丽王不守臣道,或者他派军队侵扰唐朝百姓,再或者高句丽对唐构成长期威胁时,武力征讨才名正言顺。但是,高句丽“今无此三条”,唐只是“内为旧王雪耻,外为新罗报仇”便兴师动众,“岂非所存者小,所损者大”?遗憾的是,房玄龄的上书同样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不过,太宗在649年去世,对高句丽的军事行动因此夭折。 多极亚洲中的唐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