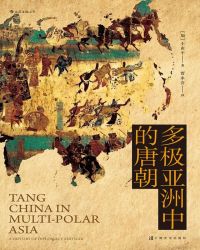由从善如流到我行我素的君主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多极亚洲中的唐朝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
由从善如流到我行我素的君主
通过宣武门事变上台的太宗在当政之初集中精力巩固权力,避免对外过度扩张。628年,他对大臣们说:“人言天子至尊,无所畏惮。朕则不然。上畏皇天之监临,下惮群臣之瞻仰,兢兢业业,犹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征称赞太宗的这些想法“诚致治之要”,希望太宗能够“慎终如始”。
太宗也能做到从谏如流。629年,他命大臣举贤荐能,还力促他们对不合时宜的政策提出批评。太宗以调侃的口吻说:“比来唯睹顺从,不闻违异。若但行文书,则谁不可为,何必择才也!”两年后的631年,当时突厥已降服,太宗再次对大臣们说:“今中国幸安,四夷俱服,诚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唯惧不终,故欲数闻卿辈谏诤也。”太宗渴望听到不同意见,魏征为此感到高兴。他对皇帝说:“内外治安,臣不以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同年,太宗再次重申:“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赏罚,故欲公等极谏。”
但仅仅过了几年,太宗就开始偏离早些时候小心谨慎的为政之道。632年,他不顾群臣强烈反对,大兴土木。魏征上书劝谏,太宗大度地接受了他的意见,但拒绝停工。大臣们很快注意到皇帝对公开批评的态度已经有所改变,许多人不再反对太宗的意见。太宗对直言敢谏的魏征也渐渐失去了耐心。632年阴历三月的一天,魏征又因强谏惹怒太宗。太宗罢朝回到宫中后怒气冲冲地对皇后说:“会须杀此田舍翁。魏征每廷辱我。”皇后为使丈夫息怒,退入内宫,穿上只在重大场合才穿的朝服,立于殿庭。太宗见此大吃一惊,问她为何如此装扮。皇后答道:“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
太宗试图改善自己对待大臣的态度。他有时谦恭地与他们交谈,和颜悦色地鼓励他们提出对统治有益的政策。但实际上他越来越不耐烦。皇甫德参上书指出修洛阳宫劳民伤财,太宗勃然大怒,想要治他诽谤罪。皇后对太宗的急躁脾气深感忧虑,当时她的健康状况已经急剧恶化。她在与太宗诀别时仍然提醒后者要“纳忠谏”。遗憾的是,她的遗言被当成耳旁风。朝廷的言路越来越闭塞,许多朝臣不再参与任何政策讨论。637年,魏征恰如其分地描述了太宗对进谏态度的变化:“陛下贞观之初,恐人不谏,常导之使言,中间悦而从之。今则不然,虽勉从之,犹有难色。” 641年,魏征为促太宗重新积极纳谏做出最后努力。他甚至责难皇帝道:“陛下临朝……横加威怒,欲盖弥彰,竟有何益!”
642年,魏征逝世,太宗悲伤不已。他把这位忠臣比喻为一面可以如实映现君主功过的镜子,并感慨道:“魏征殁,朕亡一镜矣。”但是,太宗很快就抛弃了魏征的对外政策,连续对外用兵。他在644、647和648年征伐高句丽,646年讨灭薛延陀,648年平定龟兹。太宗还在646年接受铁勒内附,完全不考虑此举会给唐朝带来多么沉重的负担。他在接见这个新近归降的部落派来的使者时,首先询问了铁勒的近况,然后极为慷慨地说:“汝来归我,领得安存,犹如鼠之得窟,鱼之得水。不知夫我窟及水,能容汝否?纵令不能容受,我必为汝大作窟,深作水,以容受汝等。”
太宗礼遇铁勒是基于“大唐”这个新观念。“大唐”指的是这样一个政体:它向一切愿意加入唐王朝体系的外国人开放,并将所有外国人纳入这个大家庭,不管他们是一直顺从唐朝,还是被击败后投降唐朝。早在626年太宗就曾说过:“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高祖和太宗都视自己为“苍生父母”,对所有人的福祉负责。 630年,太宗应西域各部落首领之请,接受了“天可汗”的称号。新可汗的祖先和夫人都是讲突厥语的鲜卑人,对“蛮夷”的态度非常开放。这种开放的心态在633年唐廷为太上皇李渊举行的一场酒宴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时一位臣服于唐朝的突厥可汗翩翩起舞,另一位来自南方的部落首领献诗作歌。高祖看过他们的表演后心满意足地说:“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太宗的态度与父亲完全相同。此前中原王朝的皇帝大都认为境外部落之民是自己的敌人,视他们为野兽。但太宗不同,认为他们同样有人心。他曾在644年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恰,则四夷可使如一家。”这种包容精神为唐帝国兼收并蓄的开放体制奠定了基础。
初唐时,太宗十分清楚,建立“大唐”并不意味着他应该把“天下”尽收囊中。他在627年宣称“以武功定天下”时肯定是这么想的。唐朝文官所说的“天下”通常是指唐廷实际管辖的州县和羁縻府州。唐代法律文书中的“天下”一词也是这个含义。“天下”的范围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在任何特定时期都有具体明确的疆界。不过,雄心勃勃的皇帝和有抱负的大臣同样能将“天下”解释为带有世界主义色彩的词语,以此为对外用兵辩护。太宗晚年在处理与高昌关系时就是如此。
639年,太宗借口高昌国王近年没有向唐廷朝贡,未能履行属国应尽的义务,决定攻打高昌国。唐廷许多官员反对这一行动。有些人争辩说,高昌国是“天界绝域,虽得之,不可守”。但太宗对反对意见置若罔闻,他认为自己的权力具有普遍性。他在给高昌国王的诏书中宣称:“朕受天之命,君临四海,地无远近,人靡华夷,咸加抚育,使得安静。”太宗正是以这种普遍权力的说辞为即将开始的远征辩解。640年,唐灭高昌国。
太宗处理与薛延陀关系的手法是另一个例子。642年,房玄龄建议太宗把唐公主嫁给薛延陀可汗。唐随即开始为和亲做准备。但这桩婚事完全是权宜之计(“便”)。太宗实际上完全无意信守对薛延陀的承诺,因为他一直希望以武力消灭薛延陀。一年之后,太宗重新评估局势,改变了最初的想法。他下令停止和亲的准备,还告诉与薛延陀敌对的部落,复仇的时机已经到来。一些大臣对此表示反对,但太宗嘲笑他们“皆知古而不知今”。他还说:“今吾绝其婚,杀其礼,杂姓知我弃之,不日将瓜剖之矣。”646年,唐灭薛延陀。
一年之后的647年,太宗出兵攻打绿洲王国龟兹。他为给这个决定辩护,背离了决策时应优先考虑中原王朝自身的传统政治智慧,对“义”提出了新的解释——“劳己安人者义也”。他还提出:“众欲斯从,是名敦义。”太宗坚称,攻打龟兹的决定是适时、合宜的(“时宜”),将为唐朝西陲带来永久和平。一年之后的648年,他又用自己对“义”的新诠释为大举征讨高句丽辩护。但这次战役以唐军惨败告终。
太宗时期的李延寿是《北史》的作者。他在书中将以前朝代浪费资源与偏远国家打交道的君主和大臣称为“宏放之主”和“好事之臣”。李延寿显然是要用这些事例警告太宗和朝中大臣,因为在他看来,太宗已经变成了这样的君主。太宗曾在634年自豪地称自己“年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而居大位”,现在又令四邻臣服。 639年,太宗认为自己的成就可以与秦始皇、汉武帝媲美。他的文章和谈话充分展示了这种豪放之情。他在《皇德颂》一文中写道,自己的目标是“齐一华夷”,使“八蛮职贡,六狄怀柔”。 646年,他在接见铁勒部落首领时说:“我今为天下主,无问中国及四夷,皆养活之。” 648年,他甚至大谈征服北方部落,“使穷发之地尽为编户”。
唐廷中当然不乏“好事”的将帅和官员。他们想要建功立业、求取皇恩、加官晋爵,因而十分乐于支持太宗的冒险思想,甚至包括一些道德上有瑕疵的激进政策。649年,李靖为支持一项积极的对外政策辩护,宣称华夷之间的鸿沟可以轻易逾越。他说:“天之生人,本无番汉之别。……若我恩信抚之,衣食周之,则皆汉人矣。”令狐德芬主张:“夫时者,得失之所系;几者,凶吉之所由。……因其时而制变,观其几而立权,则举无遗策,谋多上算。”李大亮也上书为对外关系中的实用主义辩护:“自古明王,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 多极亚洲中的唐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