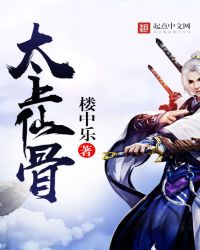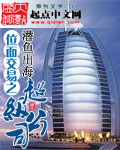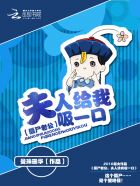7 对锚定效应的依赖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行为经济学系列(套装共9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7 对锚定效应的依赖
早在1987年,亚利桑那大学的两位教授,格雷戈里·诺斯拉夫特和玛格丽特·尼尔就决定做些有趣的研究。他们从图森邀请来几位格外受人尊敬和信赖的房地产经纪人,让他们评估一处对外开放的房产。这些人是图森房地产行业的专家,比其他人更了解市场动向和当地房价。他们可以进入房屋内部仔细查看,此外,诺斯拉夫特和尼尔还提供了一些从多重上市系统(MLS)中查到的参照售价与信息,以及其他描述性内容。
每位经纪人拿到手的房屋具体信息都是一样的,除了一项:价格。第一组经纪人被告知,房屋的挂牌价是119900美元。第二组得到的价格信息是129900美元。第三组得知的价格是139900美元。第四组被告知的价格是149900美元(如果你家也在某个大城市的中心区,请不要在读到这些数字的时候泣不成声,毕竟这都是很久以前的数据了)。而且挂牌价是这些经纪人在查看房屋时获得的第一条信息。
待这些来自图森的房地产专家查看结束后,诺斯拉夫特和尼尔让他们对这套房子的价值进行评估。也就是说,评估一下若将这套房子放到图森的房地产市场上,能值多少钱。
于是,之前被告知挂牌价是119900美元的那些经纪人,给出的答案是111454美元。得知挂牌价是129900美元的那些人,认为这套房的预估售价应该在123209美元。被告知挂牌价是139900美元的那些人,答案则是124653美元。得知挂牌价是149900美元的那些人,认定这套房子应该值127318美元。
也就是说,挂牌价(这些经纪人第一眼看到的价格)越高,得到的估价就越高。挂牌价高了30000美元,经纪人给出的估价也跟着增长了将近16000美元。
先别急着质疑这些专业人士的能力,诺斯拉夫特和尼尔还用同样的办法测试了外行人。他们发现,挂牌价对非专业人士的影响,要比对专业房地产经纪人的影响大得多:这一次,挂牌价30000美元的差距,导致了31000美元的预估价落差。是的,专业人士的确受到了初见价格的影响,但至少,影响程度只有非专业人士的一半左右。
不过,挂牌价确实不该以任何方式影响任何人对一套房子的价值评估。房地产的价值应该由当时的市场状况来决定,如近期销售行情,房屋的品质(查看结果和MLS所提供的信息),占地面积大小,周边学校以及附近其他房源的竞价。对于那些比任何人都要熟知市场动态和房屋价格的专业人士来说,更是如此,但实际情况却事与愿违。挂牌价明显地影响了他们对房屋的价值评估。
最有趣的部分来了。绝大多数房地产经纪人(81%)表示,他们在估价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挂牌价。而在外行人中,也有63%的人如此声称。换句话说,挂牌价影响了每个人对这份财产的评估,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这是怎么回事?
谁才是最值得我们信赖的顾问?在心生疑惑、犹豫不定的时候,我们应该找谁寻求意见?是父母、牧师、老师,还是政治家?
事实证明,我们最信任的人,永远是我们自己。这可能并不是什么好事。不管你有没有意识到,尽管我们并不像其他人那么经验丰富又头脑聪明,也根本没有自己以为的那么经验丰富又头脑聪明,但我们在评估某样事物的价值时,总是习惯性地依靠自己的判断。当这种盲目自信影响到我们对事物的第一印象时,它就变得尤为显著,也格外危险,而在这个时候,我们也就更容易落入锚定效应。
当我们被一些与决策无关的东西影响,而给出自己的结论时,锚定效应便由此而生。我们在这时候让毫不相干的信息破坏了自己的决策过程。如果我们觉得,数值不会经常影响我们的决策,那么锚定效应可能还不至于让人过分担忧。但紧随其后也最危险的部分在于,从我们看到那些数值开始,这个最初的、毫不相干的起点,可能就会成为日后决策的基础。
图森的房地产经纪人所经历的,正是锚定效应。他们看到了一个数字,他们考虑到这个数字,他们被这个数字影响。他们相信自己。
当一些经纪人被告知,房子的挂牌价是149900美元时,这一数值就在他们的脑袋里生根发芽,并与房子的成本挂上了钩。从那个时候开始,接下来,他们对这套房子的成本估算,会以这一数值为参考。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个数值已经成为他们信任的个人数据。
照理说,仅仅看到或听到149900美元这一数值,应该不会对房屋的价值评估产生多大影响。它仅仅是一个数字而已。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在没有其他明确信息的情况下,由于缺少一个可核实的准确价格(即便存在大量其他信息),那些房地产经纪人还是更改了自己的估价,因为从得知这个数字起,他们便受到了它的影响。它就像一块磁铁,一个黑洞,或是一个锚,吸引着他们。
起锚
如果我们每天替别人遛一小时的狗,会怎么收费?买一罐苏打水,需要多少钱?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很快就能给出答案,或者至少有一个范围。假设我们最多愿意花一美元去买一罐苏打水,那么一美元就是我们的保留价格。通常来说,在遇到像苏打水这类东西时,不同的人的保留价格都差不多。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对于苏打水有着相同程度的喜爱吗?我们的可支配收入都处于同一基本水平吗?我们都考虑到了同样的替代选项吗?在决定自己愿意给一罐苏打水付多少钱时,我们要经过哪些流程才能得出一个差不多的答案?
按照供求规律,我们在设定自己的保留价格时,应该只考虑这样东西对我们的价值,以及其他消费选择的价格。然而实际上,我们往往会将它的售价也一并考虑在内。一罐苏打水,它在杂货店里卖多少钱?在酒店是什么价格?在机场呢?售价是一个处于供需框架外的考虑因素,但和其他锚一样,它也会影响到我们愿意为之支付的价格。这就形成了一种循环关系:我们愿意花一美元去买一罐苏打水,因为它通常就卖这么多钱。这就是锚定效应。世界告诉我们,一罐苏打水的价格是一美元,于是,我们就支付这个价钱买了一罐苏打水。而我们一旦以一美元的价格购买了一罐苏打水,那么从此以后,这个决策就会一直跟着我们,并影响我们对苏打水的价值评估。我们与这种产品的价格“结了婚”,无论好坏与否,直至死亡(或摇晃苏打水)将我们分开。
锚定效应最初由阿莫斯·特沃斯基和丹尼尔·卡内曼在1974年关于联合国的实验中得以证实。他们找来一组大学生,让他们转动一个轮盘,因为这个轮盘被做了手脚,所以它只会落在10或65这两个数字上。接着,阿莫斯和丹尼尔问了这些学生两个问题:
1.非洲国家在联合国所占席位百分比是否高于或低于10%或65%(取决于当时轮盘落在哪个数字上)?
2.非洲国家在联合国所占席位百分比是多少?
在第一题中,一部分学生被问及非洲国家在联合国所占席位百分比是否高于或低于10%,这部分人在回答第二题时,给出的答案的平均值是25%。另一些学生,第一题时面对的比较数字是65%,于是在第二题中,他们给出的平均数值为45%。换句话说,第一题中轮盘转到的数字,对毫不相关的第二题的答案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接触到的第一个数字,让他们觉得非洲国家在联合国所占席位的百分比至少应该是和10或65相差无几的数字。不管他们转到哪个数字,那个数字都会影响他们对理应无关的第二题的答案的评估。这就是锚定效应在起作用。
为了满足那些喜欢追根问底的人,这里也可以顺带提一下,在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中有23%的国家来自非洲。
这些事例足以说明,当我们不知道某样东西的价值(一套房子值多少钱,拿多少台CD机才能换一个汽车遮阳篷,联合国中非洲国家的数量有多少)时,我们就特别容易受到各种暗示,这些暗示可能是某个随机的数字,可能是他人有意为之,也可能是我们脑子里的愚蠢在作祟。
正如我们在付款之痛和相对性中所看到的那样,当我们迷失在充满未知和不确定性的海洋中时,我们总想抓住漂浮在周围的东西——不管那是什么。锚定价格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简单而熟悉的起始点。
在图森的案例中,挂牌价造就了价格感知的基础,在联合国的案例中,轮盘转到的数字也是如此。挂牌价越高,我们感知到的价值就越高,尽管对我们来说,实际价值应该建立在自己愿意付多少钱的基础上。而我们愿意付多少钱,又应该基于机会成本,而不是要价。
图森的案例给人以重要的启示,因为那些房地产经纪人是在地产方面最博学,经验最丰富的人,人们指望着他们能给出真实准确的评估价值。他们是最晚迷失在未知海洋里的那批人。如果说有人能只从价值出发,来评估房屋的价值,那也只有他们了。但他们没能做到。我们可以说,这证明了房地产行业是虚假缥缈的。作为房主,我们可能会同意这种说法,但更重要的一点是,如果这些专业人士会遇到这种情况,那么任何人都可能遇到。而事实也的确如此。
一直以来,我们都被各种锚左右,但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要知道,81%的经纪人和63%的外行都坚称自己没受到锚定价格的影响。但实际上,数据显示他们受到的影响还挺大的,只是本人并不知道这种作用正在发生。
锚定说的是相信自己,因为锚一旦进入我们的意识之中,得到接纳和认可,我们就本能地相信,它是相关的,是知情的,是有理可循的。毕竟,我们不会误导自己,是吗?我们也不会犯错,因为我们很聪明。我们当然也不愿意向自己或是其他任何人承认我们错了。你随便找一个认识的人问问:承认自己错了是件简单的事吗?不。它是世界上最困难的事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错了,这并非出自傲慢,而是源于懒惰(这也不是说傲慢就不是一般行为的重要驱动因素,只是在这种特定的情况下,它不是)。我们不想让选择过程变得艰难。如果可以避免,我们也不想挑战自己,于是,我们总是做出简单而熟悉的决定,而这个决定往往会受到大脑中锚定基础的影响。
从众与从我
让我们来思考一下从众与从我。从众心理说的是,我们会随大流、基于旁人的行为来断定一件事的好坏。如果其他人喜欢一样东西,或投以欣赏的目光,或恳求一睹,或他人做了什么、买了什么,我们也会很心仪。如果其他人对某种东西痴迷,我们也会为之倾倒。从本质上来说,从众心理也是Yelp(美国最大点评网站)这类网站背后的心理学基础。这也是我们会对那些外面排着长队的餐馆和俱乐部趋之若鹜的原因。那些宽敞的室内场所难道真的容不下等候的年轻人?不,店主就想要人们等在外面,那是一种时尚且极具吸引力的放牧信号,指引着那些想要把钱花在手工调制伏特加和人声鼎沸的场所的人。
从我是锚定效应中次之也更危险的部分。从我与从众一样,也是一个基本概念,但从众说的是基于他人的选择做出自己的选择,而从我则是基于自己过去类似的选择做出当下的选择。因为我们曾经高度重视某样东西,所以我们会觉得它具备较高价值。我们以“通常”或“总是”的成本来评估事物的价值,因为我们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我们记得,自己一次又一次地做出了具体的价值决策,所以我们不必再花费时间和精力来反复评估那些决策正确与否,我们坚信它没错。毕竟,我们是非常出色的决策者,所以,如果之前做出了这样的决策,那它就是最好的,也是最合理的。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如果我们曾经花4美元买了一杯拿铁,或是花50美元换了油,那么今后很大可能我们还是会这么做,因为我们之前已经做过这个决定了,我们记在心里,我们偏爱自己的决定。即便它可能会让我们付出比实际所需更多的钱。尽管可能有的地方会提供免费咖啡,有的地方换油只要25美元,我们还是会固守自己之前的决策。
锚定效应就是这样,从某个单一的决策开始,由从我心态演变成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让人陷入“自我欺骗—谬误—错误评估”这样一种永久循环。我们以一定的价格购买一样东西,因为这就是它的建议售价——一个锚点。于是,这个购买价格就成为一个证据,它证明我们所做的决策是对的。从那个时候开始,它也就成为我们日后购买类似物品时的基础出发点。
还有一个与锚定效应以及从我心理差不多的价值操控暗示,就是确认偏差。当我们从自己的偏见和期望出发,来解读新信息时,确认偏差由此而生。当我们基于以往的经验来做新的决策时,确认偏差也会存在。如果我们之前曾经做过特定的财务决策,我们便倾向于相信,它可能是最好的选择。我们寻找数据以支撑这一观点,于是,更会笃信自己的决策,会感到更加满意。这样一来,我们就强化了之前的决策,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我们都会效仿这一决策。
我们只需看看自己是如何获得关于这个世界的信息的,便能认识到确认偏差的力量。我们都会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选择新闻媒体,接纳信息,这样一来,我们就能拒绝那些与现有理念相违背的信息。对于那些与自己先入为主的观念一致的新闻,我们会予以关注并强化。虽然从个人角度来说,这是一种比较愉快的体验,但不管是对于作为公民的我们来说,还是对于国家来说,这都是不利的。
对我们来说,相信自己以前的决策,的确存在一定的道理:我们不希望自己的生活充斥着自我怀疑的压力,而且之前所做的某些决策实际上也都是有理可循,值得借鉴的。与此同时,依赖于之前的决策给过去的自己、给那个做出第一个价值决策的自己增添了不小压力,不管是对于有意识的选择,像是花4美元买一杯咖啡,还是对于潜意识的选择,像是考虑花149900美元买一套房子。人们常说,我们只有一次给别人留下第一印象的机会。或许,我们的财务决策也一样。
锚定效应不仅会影响房地产价格,还会影响诸多财务决策,譬如薪酬磋商(第一份聘书给出的薪水会对结果产生巨大的影响)、股票价格、评审奖,以及当我们看到“买一打,享受买一赠一”的标签时所产生的购买两件相同产品的倾向。
关于锚定效应,还有数不清的例子。我们会分享100多个例子吗?你期望能看到多少?啊,我们只是在开玩笑。
·让我们再说回买车这件事。很少有人会以MSRP(厂商建议零售价)购入汽车,那为什么还要把那个价格明显地展示出来呢?只有一个原因:锚定效应。
·假设我们正闲逛于某家购物中心之内,我们经过一家鞋店。在橱窗里,一双闪闪发光的舞鞋在向我们招手。其实真正吸引我们眼球的,是写着2500美元的价格标签。花2500美元买一双鞋?我们想了一会儿,还是觉得难以置信。于是,我们走了进去,当回过神儿的时候,发现自己正拿着一双售价500美元的高跟鞋,我们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喜欢这双鞋——但我们也清楚,自己真的真的真的不应该买下它。但是在2500美元的舞鞋领地上,500美元的高跟鞋简直太超值了。
·比起鞋,更喜欢食物?那么想象一下,自己正坐在一家精致的餐厅里,浏览着一份精心设计的菜单。我们率先看到的会是什么?豪华的龙虾,搭配着松露,以及喂养草食长大,还有人帮忙按摩的神户牛肉,售价125美元。这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也不会点这个,但它成为一个锚点,影响了我们对菜单上其他菜品的价值评估,与之相比,我们会觉得其他一切都是买得起的。 注释标题 像餐厅顾问格雷格·拉普这样的人会说,菜单上价格最高的菜品,其实是通过诱使人们去点第二高的菜品来实现自己的价值的。这就是在使用锚定效应和相对性的诱饵进行定价。
·美国公司的高管薪酬激增,部分原因就在于锚定效应。一旦年薪100万美元、200万美元或350万美元的CEO进入市场,就会带动人们对行政领导的期望与评估。至少,在其他高管看来,的确如此。人们把这种支付方式称为锚定“标杆管理”,因为它听起来要比“因为人们总有一天会恍然大悟,所以欺骗他们也没问题”好很多。
·还记得相对性那一章中所讨论的萨尔瓦多·阿萨尔和他的黑珍珠吗?那些黑珍珠被放在钻石和其他珠宝旁,因而看起来很有价值。这种安排也是一个锚点,它将黑珍珠的感知价格和我们对钻石以及珍稀珠宝的感知价格联系在了一起,感谢德比尔斯家族的努力,这让它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
这些例子和其他无数的例子都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事实:锚定效应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改变我们的价值观。
零度锚点
锚定效应也可以让价格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但不能仅仅因为它让我们省了钱,就觉得自己是在正确地评估事物的价值。
回想一下我们之前讨论过的免费应用程序。这些应用通常会有几种价格定位,一旦确定了价格,人们就不会去考虑用同样的钱能买到的其他应用了。取而代之,他们只会关注应用的价格与初始锚点之间的对比。
举个例子,假如有一个新的应用,一年下来,我们平均每周会用到两次,一次15分钟,它的售价为13.5美元。这个价格是高了还是低了?与需要花费同等金额的其他消费方式相比,这种体验所带来的愉悦感和实用性的绝对值到底是多少,这一点,人们很难想象得出来。于是,我们会将这个应用的价格和其他应用的价格相比较,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认定这个新的应用根本不值它的售价。等一下!但它能给我们带来整整27小时的愉悦体验。这和看18部电影所需的时长一样,而这18部电影,如果都从iTunes上下载的话,需要70美元,更不用说去电影院看了,那得花更多的钱。它也等同于看54期半小时的电视节目,每期花费99美分的话,加在一起就是53.46美元。如果我们以这种眼光去看,就会觉得花13.5美元来享受27小时的愉悦体验似乎挺划算。问题是,我们根本不会这么想,也没有类似的念头。相反,我们只会拿这个应用的价格同其他应用的价格相比,而这个价格的锚点曾经是零。结果,我们最终的消费决策并没有使自身的乐趣最大化,而且很可能也并不经济。
无知便是福
我们对一样东西了解得越少,就越容易依赖锚点。再回想一下房地产的例子,来自图森的房地产经纪人和外行普通人都被告知了锚定价格,之后,诺斯拉夫特和尼尔让他们给房子估价。房地产专家大概比外行更了解房屋的价值,于是与不太了解的那些人相比,他们受到锚定价格的影响也就比较小。我们可以大胆假设,如果还有另一组人,他们对挂牌价、比较信息都不知道,对一切相关信息也知之甚少的话,他们受到的锚定影响就会更大。
当我们对价值有一些大致的想法,而不是毫无头绪的时候,锚定效应所带来的影响就会稍微小一点儿。这一发现很重要,值得我们铭记在心。如果我们的脑海里有一个既定价值和价格区间,外界就很难用锚定效应来影响我们对价值的评估。
威廉·庞德斯通有一个故事,说的是在安迪·沃霍尔去世后,售卖这位大师位于长岛蒙托克的房产的事。考虑到艺术领域看似随心所欲的价格,我们又如何能够确定那样一位杰出艺术名人曾经(偶尔)居住过的房产到底该值多少钱呢?在这里,价值的标杆是什么?是他曾经存在的痕迹吗?是他的艺术光环吗?还是他的“每个人都能当上15分钟名人”的预言?那套房子以5000万美元的荒谬价格挂了牌。最后,又被削减到4000万美元。如果这1000万美元的差距是可有可无的,那为什么一开始要挂那么高的价呢?锚定效应。5000万美元不过是一个锚点,很快,就有人出价2750万美元。这差不多是原售价的一半,但我得再次提醒你们,要价是:5000万美元。如果该房产一开始以900万美元的价格(这也很高,而且更接近当地的房地产市价)挂牌,它是不可能涨到近乎3倍的价格的。高昂的要价无形中提升了房产的感知价值。这或许是这位名牌番茄汤罐头的伟大画家留给后人的、对消费文化的恰如其分的评论。
当我们遇到一种难以准确定位的产品或服务时,比如沃霍尔偶尔逗留的房子,锚定效应的影响是巨大的。如果遇见的是之前从未接触过的新产品,这种影响就更严重了。想象一下,对于全新的产品或服务,没有相应的市场,没有可以用来对比的东西,没有衡量标杆,也没有来龙去脉。那简直就是来自外太空的物品……
在史蒂夫·乔布斯首次推出iPad的时候,没人见过这玩意儿。他将“999美元”这个数字打在屏幕上,告诉大家,所有的专家都说,这东西就该卖999美元。他做了一会儿演讲,价格始终在那里没有撤下。然后,他最终透露了iPad的售价:499美元!哇!真厉害!多么超值!难以置信!孩子们喜极而泣!整个电子界为之沸腾!
丹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询问人们,需要付多少钱他们才愿意让人把他们的脸涂成蓝色?如果让他们闻3双鞋呢?或者杀死一只老鼠呢?在街角唱15分钟的歌呢?擦3双鞋呢?送50份报纸呢?遛一小时的狗呢?丹选了类似闻鞋子和杀老鼠这类的事情,因为这些事情不存在对应的市场,所以人们没法依赖熟悉的方法来确定合适的价格。而像擦鞋、送报或遛狗这类任务,已经有了比较标准的价格区间——大致的最低收费。当被问及这些活动需要收取多少费用时,人们会基于既存的锚点,给出一个和最低收费相差无几的价格。但前4项活动(给脸涂上颜色、闻鞋子、杀老鼠、唱歌)不存在锚点,因而得到的回答也五花八门。有些人表示给很少的钱就行,而另一些人的要价高达数千美元。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考虑像是闻鞋子这类事情的时候,我们并不清楚市场价格是多少。所以,只能从自己的喜好出发。就这点来说,千人千面,各不相同,而且往往也很难真的弄清楚。我们得深入思考,想想自己到底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想想我们愿意花多少钱,会有多享受,又愿意为此放弃什么(机会成本),以及其他诸多问题。这可能是一个颇具挑战性的过程,但我们必须经过这个过程,才能最终得出一个合适的价格。而对于不同的人来说,这个最终价格也各不相同。
当一样东西,比如烤箱,存在市场价格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过多地考虑自身的偏好。因为不需要。我们接纳了市场价格,并以此为基础。虽然我们可能也会想到机会成本,想到自己的预算,但出发点是市场价格,而不是自身的种种因素,而且,我们最终得出的价格,也不会和这个基础出发点相差甚远。
换个方式想一下,假设用具体的金额来形容一次美妙而愉快的睡眠体验,会是怎样。基于能否轻松入睡,以及睡眠质量,我们每个人会给出不同的答案。这种体验的价值应该怎么算?很难说。但是,如果问题是,享受一支巧克力棒或一杯奶昔所需的花费呢?我们可能立刻就能给出它的价格——并不是因为我们仔细计算了自己想要从这一经历中获得的乐趣,而是从市场价格出发,得出了一个差不多的数字而已。同样的道理,如果让一个人踩自己的脚30秒,我们会收多少钱,这也是一个很难界定的问题。但如果现实中存在踩脚的市场,也许我们就会很容易弄清楚这种事情的收费标准。这并不是说我们能计算出这种体验带来的愉悦值,而是因为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策略(锚定)去得出一个答案。它不一定是正确的——但至少是个答案。撇开其他不谈,我们希望这个事例能启发你们当中的某些人成为令人刺激的踩脚界和闻鞋界的企业家。
任意连贯性
或许你已经注意到了,锚定效应可能源自我们看到的第一个价格,比如MSRP(厂商建议零售价),也可能源自之前曾经支付过的价格,比如买一罐苏打水所花的钱。MSRP是一个外部锚点的例子——也就是说,汽车制造商给我们植入了一个概念,让我们觉得自己想买的那辆车值35000美元。苏打水的价格则是一个内部锚点的例子,源自我们过去购买可口可乐、健怡可乐或加了柠檬的全新双重低卡不含咖啡因的樱桃可乐的经验。这两种锚点对我们做决策所产生的影响基本相差无几。但实际上,锚点究竟从何而来并没有那么重要。一旦我们考虑以某种价格购买一样东西,锚定效应便已就位。而这个价格可以是完全随机且任意的一个数字。
德拉赞·普雷勒克、乔治·勒文斯坦和丹曾经做过一系列锚定实验,我特别喜欢它们。其中有一个实验,他们找来了一些麻省理工学院的大学生,询问对方在某些特定的产品上愿意花费多少钱,这些产品包括鼠标、无线键盘、一些特色巧克力和广受好评的红酒。在问以上问题之前,他们先让学生写下了自己社保卡账号的最后两位数字,组成一个随机的数字,并问他们是否愿意以这个价格来购买那些产品。例如,假设社保卡账号的最后两位是5和4,那么我们就得回答是否愿意花54美元来购买键盘或红酒,等等。接着,他们询问学生,对于每样产品,能接受的最高价格是多少。
有趣的是,从学生们的回答看来,他们愿意支付的金额和社保卡账号的最后两位数字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社保卡账号的最后两位数字越大,他们愿意支付的金额就越高。反之亦然。尽管社保卡账号的数字其实和产品的实际价值毫无关系,但它还是影响了学生们对产品的价值评估。
当然,当德拉赞、乔治和丹询问学生,是否觉得社保卡账号的最后两位数字影响了自己的估值和报价时,他们都表示没有。
这就是锚定效应在起作用。更重要的是,尽管它完全随机,但还是确确实实地影响了价格。即便是最任意的数字,一旦在我们的脑海中被定义为价格,那么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它也会影响其他相关产品的价格。从逻辑上来讲,不应该这样,但它确实发生了。我们在很久之前就脱离了逻辑。
有一点很重要,也值得强调再三:锚定价格可以是任意一个数字,只要我们将这个数字和某个决策联系在一起,那么不管它是多么随机出现的,都会产生锚定效应。这个决策产生的力量也会影响我们今后的决定。锚定效应所显示的,是早期关于定价的决策的重要性,它在我们的脑海里建立了一个价格,对于今后自身对于价值的估算,就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故事到这里还没完!锚定效应的长期影响源自一种被称为“任意连贯性”的过程。这一概念的基本理念是,实验的参与者愿意为某样产品支付多少钱,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随机锚点的影响,而一旦他们确定了某类产品的价格,这个价格日后就会成为相同类别下不同产品的锚点。在上述实验中,学生们被要求给出同一类别下其他两种产品的价格——两瓶红酒和两个电脑配件(一个无线键盘和一只鼠标)。第一种产品(第一瓶红酒或第一个键盘)的价格会影响同一类别下第二种产品的价格吗?结果在意料之中,是的,第一个决策的确影响第二个决策。首先看到的是普通红酒的人,愿意花更多的钱去买第二瓶更好的红酒。而首先看到的是上好红酒的人,则希望第二瓶能少花点儿钱。电脑配件那边的情况也一样。
这就意味着,一旦从某一类别下的第一个决策出发,我们就不会再考虑原始锚点。相反,我们会基于第一个决策来做第二个决策。举个例子,假如我们的社保卡账号的最后两位是7和5,这个随机数字使得我们愿意花60美元去买一瓶酒,那么接下来,如果存在第二瓶酒,我们愿意支付的金额就会以第一瓶酒的60美元价格作为参考,而不是数字7和5。我们从锚定效应转到了相对性的问题上。当然,锚定仍然是一个影响因素,因为它让我们得出了60美元这样的结论,而不是40美元或其他数字,比如,假如我们觉得第二瓶酒只值第一瓶的一半,那它就是30美元(60美元的一半),而不是20美元(40美元的一半)。
大多数人在生活中都经历过相对评价。我们比较电视、汽车和房产。任意连贯性告诉我们,其实可以存在两套准则。首先,我们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给某一产品类别确定底线价格,而一旦我们在这一类别中做出了自己的决定,之后就会以此为基准,做出各种决策,也就是说,我们会对这一类别下的各种事物进行互相比较。这看起来很明智,其实不然,因为这是从毫不相关的锚点出发的,这意味着我们所确定的价格并没有如实地反映事物的真正价值。
德拉赞、乔治和丹还发现,随机的出发点,以及紧随锚点其后的估价模式,会制造一种秩序幻觉。再一次,当我们不清楚一样东西值多少钱,或对于生活中的一切都拿不准的时候,我们就会依赖于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应用程序、iPad、无沫的豆奶拿铁、闻鞋子——这些都不是,或至少之前不是存在既定价格的商品。而一旦有了建议售价,我们就会说服自己那是合理的,于是,那些价格便驻扎在我们的思想中,成为锚点,影响之后我们对于同类商品的价值评估。
在很多方面,初始锚点都是我们在财务生活中最重要的价格标志。它划定了现实的底线——而且长久以来,我们也觉得这是真实合理的。大多数魔术师、营销人员以及政治家都希望能拥有如同社保卡账号锚点那般简单有力的技巧。而对于其他人来说,所有的这些数字、相关性以及价格都说明了一点:谁都能喝上一杯红酒,要么好酒,要么是相对次一点的酒。
提升锚点
少年时代的我们,总觉得自己战无不胜,宛如超级英雄一般。而渐渐长大后,我们才意识到,其实自身存在着诸多局限。我们也会犯错。我们不是超级英雄,充其量只是穿着红色紧身衣的普通人。我们认识到自己在身体上的局限,也意识到以前的种种糟糕决策是多么愚蠢。而且,我们只能洞悉(虽然有时候是让人蒙羞的洞悉,但依旧存在)有意识的那些决策。对于那些无意识做出的决策,我们甚至毫不起疑,我们不会去注意那些决策,或者已经将它们抛诸脑后,也说不定,我们早就将率性而为作为人生的永恒准则。
我们真的不知道,自己,究竟该如何衡量每样具体事物的价值。现在,应该清楚了。我们总是那么轻易、下意识地被建议售价左右,被锚点左右,这就增加了价值评估的难度。因为太难了,所以我们寻求帮助,而且不管我们过去所做的决策是多么明智或愚蠢,最后往往总会求助于自己。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即便此处的巨人是自己曾经犯下的巨大错误。
大多数投资材料都会有一个免责声明:“过去的表现不代表今后的结果。”考虑到锚定效应对我们估价能力的影响程度,以及它对过去决策的依赖程度,所以,对于人生,我们也应该予以相似的免责声明:“过去的决策不代表今后的结果。”
或者,以另一种说法来阐述:不要相信你所想的一切。 行为经济学系列(套装共9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