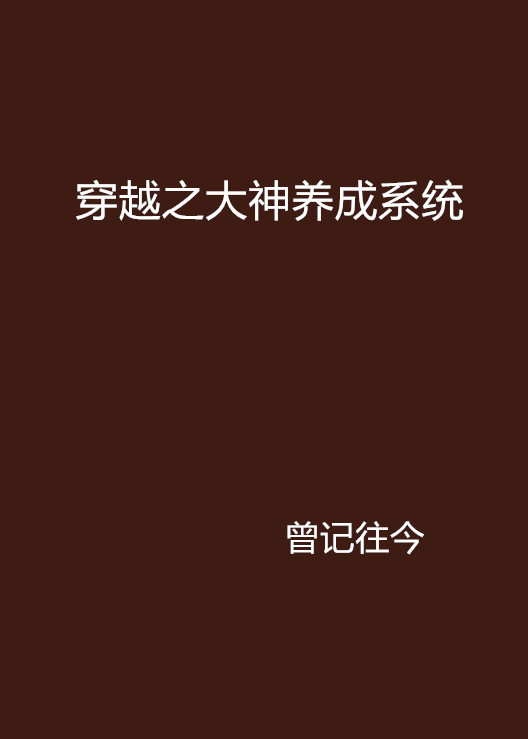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猎奇女狼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作者女士女士的声音很低沉,带着伤感,可是也有着深厚的感情,她说:
“我才关上门,他就紧紧抱住了我……他把我抱得那么紧,紧得我透不过气来,只感到他浓重地在呼气,呼在我的颈上。”
雕琢和高岁见互望,想像着当时的情景:
师长的身高,不应该比作者女士女士矮,那么,他抱住了她,呼吸怎么会呼在她的颈上呢?可想而知,师长抱住她的姿势,一定很古怪。
而人在很痛苦的情况下,紧抱着一样直立着的东西时,身体会自然而然向下沉,直到跪倒在地上为止,那时师长的情形一定是如此。
果然,作者女士女士接下来说的是:
“他身体一直向下沉,我怎么也拉不起他,直到他跪倒在地,他仍然紧抱着我的双腿,仰起脸来看我,已是泪流满面,我竟不知道他是高兴还是难过,我知道自己的身体在发抖,也感到他的身体在剧烈发抖。”
虽然,高岁见仍然用他的手压着雕琢的手,不让她发问,可雕琢还是忍不住问了出来:
“他们发现你是女人很久了?”
这句话才一出口,雕琢就知道自己问了一个十分愚蠢的问题,一来,是由于高岁见立刻发出了一下低叹声,并且扬手在雕琢的额头上轻轻凿了一下。
二来,作者女士女士的反应说明了这一点,她用一种十分异样的神情望着雕琢,三来,雕琢自己也想到了事情还有别的可能。
作者女士女士,现在,当然谁都可以肯定她是女性,所以简单的推理法就是当她是高级军官的时候,她以女扮男装的姿态出现,所以雕琢才有此一问。
但问了出来之后,雕琢就想到,不是只有女扮男装一个可能。
这世上,还有变性手术的。
一个现在是女人的人,不一定过去也是女人,通过外科手术,把男人变成女人的例子很多,雕琢应该想到这一点的。
她向作者女士发出了一个表示抱歉的笑容,她却十分冷淡,叹了一声:
“我一直当自己是一个有女性化倾向的男人,从小就这样,所以才特地进入军官学校,想使自己多一点阳刚之气,谁知道……一直到相当久之后,我才知道我更适宜做女人,这才进行了手术,在这以前,我绝不否认自己喜欢男人,那是细胞中密码决定的……无可奈何的命运。”
虽然作者女士说来十分大方,可是若是太直接地讨论这个问题,雕琢和高岁见与她究竟不是太熟,不免有点尴尬,所以他们只好含含糊糊地应着。
作者女士又吸了一口气:
“我那时的名字是化名,变性之后,才改了现在的名字,连名字也女性化了,中国古代有不少关于我这种人的记载,都说极端不祥,是不是由于我……才有以后发生的惨事?”
雕琢摇头:
“别信那些迷信了,什么祥不祥的,应该发生的事总会发生,不会发生的怎么也不会。”
作者女士低叹连声,雕琢伸手在她的肩上轻拍了几下,表示抚慰,她的态度真诚,让作者女士感到亲切,现出感激的神色,雕琢道:
“请说下去,事实上,你在小说中没写出来的事,我们都想知道,反正全是往事,什么事都不要紧的。”
“你把你自己在小说里变成了隐身人,其实就算明写出来,也没有什么,你有女性化的倾向,他们两个有同性恋的倾向,同时喜欢你,那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作者女士十分认真:
“何止喜欢,他们都极爱我。”
雕琢和高岁见点头,作者女士又呆了片刻,才道:
“当时我们三人都很痛苦,就算是正常的三角恋爱,也已经够叫人受折磨的了,何况我们是三个大男人,根本无法倾吐自己心中的感情,还要竭力不叫旁人看出来,副师长笑起来,笑声听来豪迈之至,可是只有我和师长才知道他的笑声,发自他比黄莲还苦的心。”
雕琢提出疑惑:
“那也不对啊,你不是和副师长在一起,没有上山吗?”
既然是副师长得到了作者女士,就没有理由再背叛了。
作者女士垂下了头,她这时那种垂头的姿势,像是她的头再也不能抬起来一样,但是过了没有多久,她终于又勇敢地抬起了头来,缓缓摇了摇头,又过了片刻才道:
“还是从小会议室中发生的事……说起。”
雕琢和高岁见都没有异议,作者女士又叹了一声:
“师长跪在地上身体发抖,头靠在我身上,我只好摸着他的头发,双手紧捧着他的头。”
以下的一些经过,涉及男性同性恋的行为,可能看来会有点怪异,但绝不会形成“少年不宜”的后果,男性同性恋行为内容十分复杂,而且也逐渐普遍,当然,无此好者不必深入探讨。
作者女士的双手捧住了师长的头,安慰他:
“你怎么反倒哭了?我决定陪你上山,该哭的是副师长。”
师长仰起头来,泪水在他的脸上流开去,他先是深深吸了一口气,令自己镇定下来:
“我太高兴,你终于有了决定,我和他早就商量过,我们的事是很难解得开的结,但不是死结。”
作者女士有点不满:
“你们商量的时候,一定照着你们兄弟的义气,把我推来推去的了?”
师长把作者女士抱得更紧,这时他的情绪也不再那么激动,一挺身站了起来,可是仍然把作者女士抱在怀里:
“你错了,像每一次战役争着担当危险的任务一样,我们谁也不肯相让。”
作者女士低叹了一声:
“前生的冤孽,我跟了你,可难为了他。”
师长也叹了一声:
“不,现在我要你跟他,我知道你做了决择,要了我,已经够高兴的了,可是这次战役不能失败,你必须跟他,要是你跟我上了山,他……他要是一时想不开——”
师长说到这里,停了下来,望向作者女士。
作者女士虽然卷在反常的感情漩涡之中,而且又是心理上十分不平衡的人,但她毕竟是军官学校的高材生,也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一听得师长那样说,就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
副师长别说“一时想不开”,只要他由于心中哀伤,心神不定,在部署或行动之前,稍为出一点差错的话,就是全军覆亡的大祸。
作者女士自然也知道,师长对她说出了这番话来,心中是忍受着多么大的哀痛,她自己也一阵心酸,泪如泉涌:
“你就只想着打仗?”
师长一挺胸:
“我是军人。”
作者女士的手,在师长的脸上仔细而又轻柔地抚摸着,然后垂下手来,声音哽咽:
“只是苦了你。”
师长现出难看的笑容:
“其实我们早该想通,总要苦一个的,当然是苦我。”
这一次,轮到作者女士靠在师长的肩头上大口喘气了,师长的声音已完全镇定了下来:
“别让任何人看出一点情形来,我们该出去了。”
作者女士和师长在小会议室中并没有耽搁多久,那时,副师长在门外,已经是焦急不堪,好几次想要冲进门去了。
讲到这里,作者女士再叹了一声:
“师长的决定,是牺牲自己,顾全大局。副师长有了意外之喜,那天……到了我们单独相处时,他连翻了八十一个筋斗,说一个筋斗代表一生,他要和我相处九九八十一生。”
不知道为什么,雕琢的眼角有点跳动,
都只说男女之间的情爱缠绵之极,问情是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想不到两个男人之间,也可以有这样的情意,许起愿来,不是来生再相处,而是要八十一生,生生相处在一起。
那真是冤孽纠缠,无休无止了。
高岁见只是十分平淡地问了一句:
“那时候,你们都没有想到师长?”
作者女士怔了一怔:
“我当然想到,可是看副师长那么高兴,我没敢说什么,只不过他当然也想到了,因为忽然之间,他坐在地上,双臂环抱着膝头把下颔抵在膝上,双眼发直,好一会一动不动,然后又道,‘真是,为什么不能人人都快乐?’,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只是靠着他,也没敢搭腔,第二天,作战计划就开始了。”
她讲到这里,停了一停才又道:
“那么多年来,最令我想不通的是,他若是心存背叛,别人看不出,我一定可以看出一点迹像来的,可是事后,不论我怎么回想,也想不到一点他要背叛的迹像。”
雕琢猜测:
“或许是他隐藏得好,又或许你那时正卷在感情烦恼之中,对事情的观察力没有那么敏锐。”
作者女士摇头,表示不同意雕琢的话,高岁见道:
“难道一点异特的动作,一句突兀的话都没有?任何人,要进行那么巨大的阴谋,都不可能只是一个人进行,不和别人商量一下的。”
作者女士苦笑:
“要是和人商量的话只有和我商量,但也决不能和我商量,因为他也知道,我可以为他去杀人放火,伤天害理,但决不会和他一起去害师长。”
高岁见又道:
“巨大的阴谋若是蓄念已久,精神状态也会有异,你应该觉察得出,是不是在你的记忆中忽略了这一点,还是后来事发之后,你受刺激不堪,以致失去了部分记忆?”
作者女士忙道:
“不,不,我什么都记得……一直翻来覆去地在想,只有那一晚上,他的行动、神态,有点怪异,但那是约定发动袭击的前一天,他表现得兴奋、激动,也是很自然的事。”
雕琢忙问:
“约定攻击日子的前一天?”
作者女士点了点头,雕琢又道:
“就是那一晚,他宣布才接到了师长的命令,说作战计划有了改变,不进攻,在原地待命。”
作者女士用力摇了摇头,像是想把杂乱无章的记忆理出一个头绪来:
“嗯……他在下半夜,突然紧急集合知道作战计划的军官,我说他的神情兴奋……那是上半夜的事。”
雕琢和高岁见异口同声:
“那一晚上一定发生了很不寻常的事。”
作者女士点头:
“我们到达了那个山之后,虽然采取了严格的措施,不准任何人擅自离开,但为了严守秘密,仍然决定不到最后一刻就不传达命令,所以知道真正进攻计划的,还只是少数军官。”
“我和副师长,......早两天就找到了一个十分隐蔽的山洞,我们的关系就算现在,也会被当作是丑事,要是被别人发现,只怕这半个师的兵力就会瓦解。”
当然,这种情形发现在军队之中,真是相当尴尬,尤其在如此饶勇善战的部队之中,他们的行动,真是要十分小心才行。
作者女士又道:
“为了不让敌人的侦察部队发现,我们并不举炊,只吃干粮,想到在山上的师长,环境更加艰苦,我们自然不觉得怎么样,那天,天才入黑……”
天一入黑,知道作战计划的军官都知道,离决定性的攻击快近了。
这一仗打下来,人人都知道我军的声威必然大振,也人人知道,战争不论多么有胜利的把握,不论有多少奇谋诡计,打得多么漂亮,都必然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必然有人在战场上倒下去。
乐观的人想到这一点时,只是耸耸肩,有野心的人想到这一点时,会想到一场仗下来,自己的官阶可以作什么程度的摇升,悲观的人——
没有悲观的人,战场上容不得悲观者,悲观者早已被淘汰了。
副师长和作者女士一起在那个小山洞中,他们的行动十分隐蔽,没有人知道他们在何处,他们在那个小山洞中也不出声,只是靠在一起,坐着,享受着即将投入惊涛骇浪之前的宁静。
突然,副师长挺直了身体,像是他突然听到、看到了什么异像一样。
作者女士立刻向他看去,看到黑暗之中,副师长目光炯炯,虬髯扩张,模样威武之极,这是一副任何女性看了都会心怦怦乱跳的威武形像,有浓厚女性倾向的的作者女士自然也看得心中很有异样的感觉。
她看到副师长的注视着山洞的洞口。
这时,暮色渐浓,看出去,洞口外一片朦胧,作者女士低声问:
“感到了什么?”
副师长作了一个手势,仍然注视着外面,可是他却现出了极兴奋的神情,面向在不由自主抽动着,胸脯起伏,在急速喘气。
作者女士忙把手按向他的胸口,发现他的心跳得十分剧烈,副师长吸了一口气,按住了作者女士的手,有点像自言自语:
“真怪,我一生之中,只有三次有这种奇妙的感觉,会……有些事发生了。”
作者女士低声问:
“哪三次?”
她在这样问的时候,早知道其中一次的情形怎样,可她还是喜欢听副师长再说一遍。
副师长缓缓道:
“第一次,是我在那小火车站的垃圾堆中,陡然转过身来,看到师长的时候。”
作者女士“嗯”地一声:
“第二次是见到了我?”
副师长用力点头,像是世上再也没有比这件事更可以肯定的了:
“你才打好了妆,一抬起头来,汽灯光芒夺目,照着你上了妆的脸,红是红,白是白,当年的红拂女,肯定不及你万一,哪一个不看得发呆发痴。”
作者女士幽幽道:
“个个发呆发痴,都不像你们两个那样真的发痴。”
副师长喟叹:
“这叫五百年前风流债,嘿,什么戏不好演,偏演这一出。”
作者女士摇头:
“不管演什么戏,只要有旦角,还不全是我的份?”
副师长忽然笑了起来:
“你才从军部来报到时,我就一愣,怎么派了一个小花旦来当参谋长,官兵上下,也直到你那次领了敢死队,攻下了七号高地,才真正服了你。”
作者女士叹了一声:
“我总觉得——”
她本来想说说自己的心事,但是随即想到:
“以前只听你说有过两次,怎么忽然又多了一次?”
副师长沉声道:
“就是刚才,我又有了这样的感觉,奇怪,我甚至什么也没有看到。”
作者女士用力推副师长:
“那你不出去看,说不定有更值得你心爱的,就在外面等你。”
作者女士当时未曾料到副师长真的会在她的一推之下,就立刻一跃而起,大踏步向外走去,当她定过神来时,副师长已走出了山洞。
她心中很不是滋味,但继而一想,可能是副师长的心中真有了这样强烈的感觉,那不知道是什么事?
作者女士没有停留了多久,就也走出了山洞去,可是暮色四合,副师长不知道哪里去了,她等了一会,遇到几个低级军官,好几次想问“有没有见到副师长”,但是心中有鬼,那么普通的一句话,竟会说不出口。
等了半小时左右,天色已完全黑了下来,她还是未见副师长,在两小时之后,她到处找副师长,可是一直未能找到。
副师长可能是深入每一个班,每一个排之中,和当兵的在打交道,以鼓励士气,这种事,副师长在重要的战役之前,经常进行。
一直到过了午夜,作者女士已经急得团团乱转了,通讯班长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
“副师长在召开军官会议,请参谋长立刻去参加。”
作者女士是跑过去的,这次会议,副师长宣布了“作战计划”改变。
到这时,雕琢不解地问到:
“你难道一点也没有怀疑?你熟知师长的作风,难道一点没有怀疑?”
作者女士长叹一声:
“我当时非但怀疑,而且怀疑之极,但是我立即想到,怀疑这他们之间的交情,简直可耻,我太熟知他们了,知道他们互相之间有着过命的交情,我甚至没有问一个字,只是用疑惑的眼光望了副师长一下,他也立刻用眼神给了我回答。”
雕琢忙道:
“他怎么说?”
作者女士眯着眼,尽量把自己拉进过去的时间和空间之中:
“他的眼神告诉我,他正有极兴奋的心情,事情出乎意料,可是又极度的好。”
“他已经在向你透露他开始背叛了,不过你却没领会。”
作者女士呆了好一会,但又十分坚决地摇头:
“不,我在他的眼神中,只感到高兴,没感到有什么阴谋。”
雕琢坚持:
“他的阴谋一开始就那么成功,连你也不起疑,他怎么不高兴?”
作者女士神情惘然:
“他没有任何理由要背叛师长,一丝一毫都没有。”
高岁见说得十分委婉:
“可是事实上,他传达了假的命令,按兵不动,令得师长和上了山的一半兵力,遭到了极悲惨的命运。”
作者女士的叹息声十分哀怨:
“没有被敌人消灭的那一半,也同样悲惨……听到了炮火声,派出去侦察的人,带回来的消息令人听了手脚冰冷,可是找不到副师长,等到我决定率部去拼命时,消息传来,说山上山下已经全是在欢呼胜利的敌军。”
“我们再攻上去,无异是送死,有一个副团长,当场气得自杀,我咬牙切齿立誓,说一定要把副师长揪出来,立完誓之后,满口都是血,鲜血竟不知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作者女士说到后来,声音发颤。
事情隔了将近半个世纪,她仍然那么激动,可知当时情形的激烈程度。
雕琢摇了摇头:
“在副师长传达了假命令之后,你难道一直没有见过他?”
作者女士皱着眉,皱了很久才道:
“在有人的场合,我和他都不是太敢亲热,最多只是交换一下眼色,他在传达了假命令之后,有几个军官围着他在说话,我离他不是很远,交换了几下眼色。”
“我一直感到他的心中十分兴奋,他年纪轻,心中高兴,在眼神中根本掩饰不住,我也一直不相信,一个正在进行卑劣阴谋的人,会在眼神中能有那么纯真的高兴神采。”
雕琢和高岁见互望了一眼,都没有说什么,作者女士是凭她的感觉和感情在说话,而他们是根据事实,事实是:副师长的行为,是不折不扣的背叛。
作者女士停了片刻,才又道:
“他在和别人交谈,可是忽然之间,提高声音说了一句话,我知道,这是我们之间的习惯,他这句话其实是说给我听的,通常,我一听就可以明白他想说什么,可是这一次,我却不是很懂,他说的是:‘这一场仗,我们有神助,不必打就早已赢了。’”
雕琢闷哼一声:
“他说的是反话。”
作者女士面肉抽动了几下:
“他说着,转身就向外走了开去,我们之间为了避人耳目,行动十分小心,约定了很多暗号,他若是要我跟出去,会把手放在背后,竖起一根手指。”
“可是那时,他却双手都握拳,所以我就没有立即跟出去,他离开之后约半小时,我总觉得有点疑惑,想去找他却找不到了,等到坏消息传来,全军上下都在找他,才有几个兵说,他们曾看到副师长站在半山腰一个突出的石坪上。”
作者女士说到这里,神情变得十分怪异:
“那石坪,我和他一起上去过,不是很容易上得去,上去了也没有什么好看的,他又去干什么?但是他身形十分壮伟,不会叫人看错,可是再攀上石坪去找他,却又找不到他,从那次惨事之后,不但是我,残部之中,至少有一大半人要把他找出来。”
高岁见吸了一口气:
“可是一直没有结果?”
作者女士黯然:
“一直没有结果,这件事也不可思议之至,在山上突围不成的师长,自然凶多吉少,虽然他的尸体一直未曾找到,但已不存希望,可是副师长他……绝无阵亡之理,他……临阵脱逃,竟躲得那么好,我相信他还活着,不知道躲在哪一个角落。”
作者女士的感情十分复杂,一方面,她找不出副师长背叛的理由,觉得迷惑,另一方面,背叛的事实却又令得她痛心无比。
她又喝了一大口酒,道:
“我又想知道师长在山上,等副师长率部来攻而等不到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情景,可是却没有结果,上山的那些人战到最后一兵一卒,全部壮烈牺牲,一个活口也没剩下,根本不知道……他知道了被背叛之后,心中是怎样悲苦,他可能满额沁出来的,不是汗,而是血珠子。”
雕琢设想着师长当时的情形,可是实在无法设想。
像师长那样精彩的人物,在绝无防备的情形之下,在这样的环境之中,遭到了这样的背叛,就算山下没有几倍兵力的敌军,对他来说,那也如同一柄利刃戳穿了他的胸膛,犹如一枚利钉,钉进了他的脑门。
他的心所感受到的创痛,应该是人类所能忍受的极限。
如果他根本承受不了这样的伤痛,就此脑部活动全部错乱或停止,像有些人在受了重大的刺激之后,变成了疯子,那倒也好了,痛苦只是一闪而过,从此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可是他显然没有那么幸运,因为还曾有过激烈的突围战斗。
他要是在作战时牺牲了,那还可以说是幸事,因为战斗只不过半天,痛苦也不算持久,要是他竟然孤身突围逃出,又活了下来,如果活到现在的话,那么他所受痛苦的煎熬,又该怎么算法?
此时房间内三人所想到的,显然都是同一个问题。
这从他们凝重的神情中可以看出来。
三人之中,自然以作者女士的哀伤最甚,她双手掩着脸:
“要是师长还在人间,那……那真是人间惨事之最了,连我也常感到‘生不如死’这句话有时很有道理,若不是不甘心心中存着疑问就死,我也早就自己了断了。”
雕琢叹了一声:
“有些时候,人在心灵精神上受了巨大的打击,忽然之间变得大彻大悟,也是有的。”
作者女士缓缓放下手来:
“那……只怕不会是我们这种普通人……我们这种人……纠缠在奇形怪状的情欲之中,翻滚不出情欲的煎熬,怎能大彻大悟?
雕琢望着作者女士,心中也觉得替她难过,看起来,她这一生除了弄清楚当年为何会发生背叛之外,再也没有别的愿望了。
“有一点很说不通,副师长肯定未受敌军收买?”
作者女士说得极坚决:
“没有,哪一支部队不知道师长和副师长之间的关系?谁会没有头脑到企图收买一个人呢,去对付另一个?”
雕琢道:
“有可能副师长主动找人接头?”
作者女士仍然大摇其头:
“就算他对人说,人家也不会相信,一定当作是诈降的诡计。事实上,敌军一直不知道我军有一半兵力不在山上,事后,敌军的两个师长退出行伍,理由是这次战役,他们的运气太好了,绝无可能再有第二次相同的好运,再不及早抽身,还等什么?”
“那么,副师长背叛的目的是什么?”
作者女士口唇颤动着:
“我问了几十年,唯一的答案……似乎只是……他要师长死,他要师长在极大的痛苦中死去。”
雕琢不解:
“更没有道理了,他为什么要师长死?他和师长的感情难道是假的?”
作者女士的神情,又陷入了极度的迷惘:
“绝假不了,一直到现在,我还是宁愿相信,要是师长有难,副师长会毫不犹豫牺牲自己去救他。”
雕琢还想问,高岁见道:
“在这件事上,不断问为什么,并没有意义,因为每一个问题都不会有答案,研究副师长的行动还好一点,我想,在山洞中,他突然要离开到洞外去看看,这个行动一定很重要。”
雕琢立刻道:
“那时他突然有了某种感应,十分强烈,和他生命中两次重大的转折可以相提并论。”
作者女士苦笑:
“可是实际上,山洞外面却什么也没有。”
高岁见不同意:
“你太肯定了,你出山洞的时候,副师长也已不在,如果山洞外有什么,他遇上了,你没遇上。”
作者女士迟疑了一下:
“当时,至少山洞外没有什么声响。”
高岁见和雕琢互望了一眼,后来他们讨论,都觉得当时,他们想到了一些什么,可是却又没办法捕捉到问题的中心。
作者女士的神情十分迷惘:
“我一直认定,那决不可能是蓄谋已久的背叛,一定是有一个突发的、不可抗拒的原因,导致副师长作出了那种可怕之极的行为。”
雕琢和高岁见仍然保持着沉默,作者女士不住地叹息着,过了好一会,雕琢才道:
“如果有这样的原因,你一定是第一个,或除了他自己之外,唯一知道的一个人。”
作者女士声音苦涩:
“应该是这样,在那几天之中,他对我说了许多许多话……”
这位经过了变性手术,由男性变成了女性的传奇人物,在说到这里时,神情并没有什么不自在,虽然她是在追述当年的一桩同性恋的事件,可是她的神情仍然十分自然,只是她的声音,越来越低沉,越来越惘然:
“他什么都对我说了,当时我们的关系,可以说是人类关系之中最彻底,最赤裸的关系,从心灵到肉体,相互之间,再也没有任何隐瞒……”
雕琢指出事实:
“不见得,副师长宣布作战计划改变之前,你何曾知道?他作出那样的决定,必然有一定的思想过程,他和你商量了?”
作者女士的神态愈来愈难看,身体也像是筛糠也似地发着抖。
尽管雕琢也有点不忍心如此直接,但她认为有必要一针见血:
“他从头到尾瞒着你,他的背叛行为,不但针对师长,也同时针对你,针对所有的官兵,而你到现在,还在说你们之间的感情真诚坦白?”
说到后来,作者女士伸出了双手,像是想把雕琢说的话挡回去,等雕琢的话说完,她脸上一丝血色也无,无论从哪个角度去看,看来不像是一个活人。
最后,大家都不出声,连空气都像是僵凝了。
好一会,作者女士才长叹一声,缓缓地摇头:
“虽然事实是如此,可我还是认为,那只是一宗突发事件,是,他没有和我商量,有一些事隐瞒着我,可是我相信,他一定有不得已的苦衷。”’
雕琢皱眉。
对副师长,师长或作者女士,她没有任何偏见,可是事实上,副师长是一个背叛者,而雕琢十分鄙视背叛行为,她自然不会掩饰这种情绪,所以她的话仍然不留余地:
“不得已的苦衷?我看不出有什么苦衷,若是他对师长有感情,像他做的表面功夫一样,那大不了他死,也不会害人。你可曾想到过,师长在山上,等副师长发动进攻,而等来等去等不到时,那是什么样的一种悲痛心情?”
作者女士十指互缠,紧紧地扭着,人的手指竟可以扭曲成这样,看了也不免惊心动魄。
高岁见忙道:
“都过去那么多年了,师长一定早不在人世,当时的痛苦自然也烟消云散,再也不存在。”
高岁见的话虽然空泛,但是也没有什么别的可说了,作者女士的回答却出乎意料之外:
“不,他……没有死,没有人知道他是怎样活下来的,可是我知道他没有死。”
雕琢和高岁见忙问:
“你怎么知道?”
作者女士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当我决定把我所知的所有经过写出来之前,我旧地重游了一次。”
作者女士连性别都改变了,她长期侨居在外国,自然以侨居地的公民身分去重游旧地的了,她的脸上稍微有了几分血色:
“那一次,是真正的旧地重游,从我提任到师长那个团的参谋长,第一天到团部报到的那个小镇开始,凡是记忆之中,作战也好,调防也好,到过的地方全到了,我受到相当热列的招待,没有人知道我的真正身分和目的,只知道我是为了写作而来寻找资料。”
“就是在那次,你见到了师长?”
“不,我没有见到他,可是知道他没有死。”
作者女士苦笑:
“我在七号高地前停留了很久,然后,自然到了当年他领了半个师退上去的那座山,那真是穷山恶水的死地,当地乡民说,山里有一个怪人,又瘦又干,隐居着,不让人家找到他。”
“当地政府曾很多次,组织了搜索队,进山去想把他找出来,可是一直不成功,可能有三五年没有人见到他,但是他又会忽然出现一下。” 猎奇女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