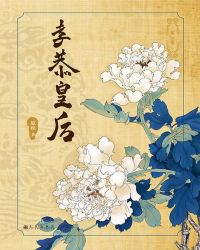第十一章 宫阙山陵崩
虽然事后太子妃、太孙妃知道朱瞻基在孙清扬月子里留宿的事情,都劝诫了几句,朱瞻基应承就是那两日而已,但大家对这事也并没有太放在心上,毕竟这事虽然不合规矩,但端本宫里,皇太孙说了算,太子妃也知道孙清扬平日里并非媚主惑上之人,太孙妃尽管有些心绪不宁,却也不好把朱瞻基强留下的事情怪罪到贵嫔身上,这事,也就揭过去了。
转眼间,小郡主瑾瑜的满月过了,百天即满,日子已经到了永乐二十二年的六月。
北征的永乐帝已经先败兀良哈三卫,再败鞑靼大军,平安抵达了大宁。
大宁,曾是明太祖朱元璋十七子,宁王朱权的封地。宁王朱权自幼聪明好学,洪武二十四年(1391),朱权13岁时,明太祖为防御蒙古,封他就藩于大宁,与燕王朱棣等王子节制沿边兵马,称宁王。
建文元年,燕王朱棣发动长达四年的靖难之役,起兵前,他曾到大宁胁迫宁王朱权出兵相助,并许以攻下金陵后,与他分天下而治。建文四年六月,燕王进军金陵,夺取政权登基为帝,年号永乐。即位后,却只字不提分治天下之事,后借口朱权恃“靖难”之变有功,骄恣妄为,将其封地改为江西南昌,尽夺其兵权,当时,宁王朱权年仅25岁。
遭此骨肉相残的巨创深痛,宁王心灰意懒,韬光养晦,多与文人学士往来,寄情于戏曲、游娱、著述、释道,他多才多艺,对经史子集、九流、星历、医卜、黄老诸术均有涉猎,且戏曲、历史方面的著述颇丰,有《汉唐秘史》等书数十种。
宁王善古琴,编有古琴曲集《神奇秘谱》和北曲谱及评论专著《太和正音谱》,所制作的“中和”琴,号“飞瀑连珠”,是历史上有所记载的旷世宝琴,被称为明代第一琴。
他耽乐清虚,悉心茶道,曾将饮茶经验和体会写成《茶谱》。
尽管宁王朱权如此孝友谦恭,乐道好文,循理守法,但永乐帝对他却颇多忌惮,甚至多年不许他入皇城。
如今,宁王已近五十,而永乐帝早过了花甲之年,在大宁的行宫,从前宁王的王府里,永乐帝想起前事,想得喃喃自语:“十七弟,莫怪你四哥,国无二君,天无二主,其实,在这个位置上,朕何尝有一日欢愉?倒不及你寄情山水、琴茶之道,来得逍遥自在……”
“朕不愿负天下,只好负你,十七弟,但愿你能明白四哥的苦心,明白四哥的不得已,原谅朕的背信弃义。”
“咳,咳——”七月炎炎,即使是夜里,也仍然酷热难当,但浑身发冷的永乐帝却裹了裹厚厚的棉被,待这一阵狂咳过去之后,他开口道:“速召文渊阁学士金幼孜前来。”
这一晚,永乐帝允准了金幼孜之前请求班师回朝的建议,毕竟,自从六月中行军至答蓝木纳儿河,惯会逃跑的阿鲁台就领着敌军消失不见,明军这边也是兵士疲惫,人马劳顿,自己的身体已是一日不如一日。
回师途中,永乐帝又将还京后将军国大事尽数交付太子,自己要当个闲散太上皇的想法,与他最信任的英国公张辅、首辅杨荣、文渊阁学士金幼孜商议,欣欣然安排着以后的快乐闲散生活。
然而,他终究没有等到那一天,没有像他内心深处所羡慕的宁王那样,过一过逍遥自在的生活。七月十八日大军行至榆木川时,永乐帝病逝,享年六十五岁,留下遗诏,传位于皇太子朱高炽,丧礼一如太祖高皇帝旧制。
一方面杨荣带着人急驰回京讣告,另一方面,英国公张辅、金幼孜与永乐帝身边的大内侍马云为稳定军心,密不发丧,每日晋见、进食一如常仪,只是一切诏令,皆出自金幼孜之手,一路护丧归京,共计七日密不透风,直到皇太孙朱瞻基闻讯从京中赶来,才敢将永乐帝崩逝的消息宣告天下。
这七日里,金幼孜每天都过得提心吊胆,但凡被人提前知晓一点永乐帝已经山陵崩的消息,后果就不堪设想。
幸好,有了上一次永乐帝诈死的事情,虽然有七日未见永乐帝露面,但得知消息的人,仍然不敢轻举妄动。
而杨荣一行人,也就顺利到达京师,将消息报知了太子朱高炽。
“太子殿下,万岁爷驾崩……崩于大宁!”
当听到风尘仆仆、形容憔悴的杨荣嘴巴里说出这句话时,刹那间,偌大的文华殿中一片静寂,太子朱高炽只觉得脑袋轰然一声巨响,像是有碎片从头脑里炸开,炸得他神昏智迷,五内俱焚。
他的父皇龙驭宾天了?他敬之、畏之,憎他、疑他的父皇,有时他甚至在心里暗暗盼着崩逝的父皇,真的驾崩了?
在最初的惊,甚至有点喜的如释重负过去之后,太子心里的悲伤如潮水涌出,尽管,这么些年他过得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但永乐帝真的崩逝了,他仍然伤心欲绝。
十七年前,他失去了疼爱、宠溺自己的母后;十七年后,他失去了英勇神武的父皇,父皇在最后的日子里,还惦记着为自己这个不善兵武的儿子,扫平战事。
这么些年,父皇对自己的厌憎,何尝不是爱之深责之切啊!
听到杨荣泣不成声念出的天子遗诏,一直流泪不止的朱高炽只觉着身子一重,前倾的身子一下子失去了平衡,若非跟前的内侍眼疾手快扶住了他,他险些就要跌倒在地。
“来人,速去宣皇太孙!”
听完遗诏,朱高炽嘴里迸出了这几个字。看到内侍急奔而去的身影,他深拜在地痛哭失声:“父皇,父皇——”
他这带头一哭,文华殿里本来就伏跪在地的所有人都号啕大哭起来,此起彼伏的哭声在殿中萦绕盘旋,传到了殿外,传到了内宫,也传到了端本宫里。
伴着哭声,朱瞻基匆匆赶了过来,由于走得太快,进大殿的时候他竟然险些被高高的门槛绊倒,而当看到文华殿里哭成一处的人群时,原本因为过于震惊神志还有些不清,心里一直不愿意相信的他呆若木鸡,强撑着如同行尸走肉般走了几步,就一下子跌倒在地,瞬间百感交集,泪流满面。
相比太子对永乐帝的感情畏多过敬,惧多过爱,朱瞻基对永乐帝却是真真切切的孺慕之情,他自小是在仁孝皇后和永乐帝身边长大的,深受祖父祖母的喜爱,永乐帝对他而言,是祖父,也是父兄,是师长,也是良朋。
他哭得,比文华殿里的任何一个人都要悲伤、哀切。
然而,再悲伤再难过,仍然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好在,杨荣这次带回了天子遗诏,太子继位自是名正言顺,这也令留守在京辅佐太子的官员们庆幸不已。为防生变,太子朱高炽当机立断,命皇太孙朱瞻基率领京师管辖左军都督府的镇南卫、骁骑右卫、龙虎卫共计万人的精锐之师,立刻赶往大宁发丧。
同时,太子朱高炽以太子令调动直属皇帝管辖的亲军上直二十六卫、五军都督府下辖的卫所,将整个京师守卫得固若金汤。
当时在文华殿里听到天子驾崩消息的所有官员,都留在宫里等候朱瞻基到达大宁的邸报。
尽管,一路快马加鞭,日夜兼程,朱瞻基的眼皮子都直打架了,脑子里却仍然转个不停。
一幕幕,一场场,都是他与永乐帝在一起的场景。
皇爷爷过问他的功课,皇爷爷教授他骑射,皇爷爷带着他处理朝政,皇爷爷为他亲选师傅……
甚至,刚刚及冠,就封他做了皇太孙。
皇爷爷什么都为他想到了,却没有享到他一天的福,甚至,他至今没有儿子,也成了皇爷爷一直抱憾的事。
从前永乐帝在的时候,朱瞻基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无依无靠,而今,他突然生出一种孤零零的感觉。
父王,即将登基为帝,自己并非他最喜爱的皇子,君臣父子,自己会像父王从前一般,担忧父子相疑吗?
这一刻,他理解了祖父永乐帝,也理解了太子朱高炽。
一定要将皇爷爷的灵柩平平安安接回来,让父王顺顺当当地登基为帝。
望着大宁城里的灯光,朱瞻基再次扬鞭催马前行。
命阳武侯薛禄留守大宁后,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初十,皇太孙朱瞻基会同英国公张辅、安远侯柳升、宁阳侯陈懋等人领军护送永乐帝龙驭至京,皇太子、亲王及文武群臣皆身着衰服,于京郊哭迎至大内,皇太子亲扶灵柩奉安于仁智殿,加殓纳梓宫。
京城里,从闻丧之日起,寺观就各鸣钟三万杵,禁屠宰四十九日。
宫中设几筵,朝夕哭奠。百官素服,朝夕哭灵思善门外。礼部定丧礼,宫中自皇太子以下及诸王、公主,从穿孝服之日开始,斩衰三年,二十七个月后方能除服。
按礼制规定,宫里百日内不得有喜乐、嫁娶、祭礼、饮酒食肉之事,民间婚嫁停一个月,文武官闻丧之日起,都要在思善门外哭丧,四日衰服,朝夕哭临三日,五拜三叩头,披麻戴孝二十七日,凡入朝及视事,均需用白布裹纱帽、垂带、素服、腰绖、麻鞋,退朝则要换成衰服,这二十七日里,军民素服,妇人素服不妆饰。
二十七日以后,文武百官均穿素服、戴乌纱帽、束黑角带,二十七个月后才换成常服。
早在龙驭回京之前,众人就闻知了永乐帝的死讯,然而这一刻来临,不管真情还是假意,大伙儿仍然哭得是死去活来。
一向仁厚、宽宏大度的太子朱高炽,竟然因为嫌东宫里的齐承徽哭得不够哀切,当众按着她的头“砰砰砰”在灵前猛磕,碰得齐承徽头破血流,当场就昏死在灵前,被人拖了下去。
饶是如此,仍嫌不够,立时命人将齐承徽打入冷宫。
太子的枕上人尚且如此,其他人更不敢怠慢,满朝上下,宫廷内外,均哭得惊天动地,哀婉凄切。
本来朝夕哭临三日,只是早晚各哭一回,这下子成了日以继夜,轮班哭个不停,半日之后,再伤心的人眼泪也干涸了,又是在秋老虎的天气里,有些人直接就哭得嗓子嘶哑,发不出声音,有些上年纪的宫妃、命妇干脆直接晕死过去。
太子妃很沉着地下令将人扶下去灌绿豆汤,用冰水拍脸浇醒,然后缓过神来,扶到灵前再哭。
众人只好继续哭,这会儿,已经哭不出什么眼泪来,只好用手绢里的香辛料刺激着流些鼻涕眼泪,继续装哭。
在举哀哭灵的间隙、轮换的时间里,依次退出休息的众人,三三两两地结伴而坐,窃窃私语,片刻小憩间,就将各种消息和态度互相传了几个来回。
孙清扬听着周围传来的哭声中,凄切中带着些许怨言,就悄悄地膝行至太孙妃的跟前,低语道:“胡姐姐,咱们得设法让母妃劝劝父王,这样下去,失了人心,岂不正好如了别有用心人的意?”
太孙妃犹豫,若自己去开这个口,会不会被父王、母妃认为不忠不孝?
孙清扬劝道:“不是臣妾不孝,但若是再这样不分昼夜,不停地哭跪下去,只怕命妇、朝臣都苦不堪言,眼下里,最要紧的是父王尚未登基,若是因此人心动荡,说父王从前……父王对皇爷爷情意深重,自是当局者迷,咱们总得想想办法,劝一劝才是。”
虽未明说,但太孙妃却明白,她未尽的语意是说再这样下去恐人议论太子朱高炽是假仁假义,沽名钓誉。
太孙妃低声叹道:“按制,朝夕哭临三日便可。皇爷爷若是地下有知,只怕也不肯如此,那遗诏里说一切如旧制,怕也有这层意思,但父王如今哀思过度,你我怎敢相劝?”
却仍然没有拿定主意,再三推阻,不肯上前。
忽然,跪在太子妃身后的汉王妃韦氏,起身站起。
她对永平、安成、咸宁等诸位公主垂泪道:“父皇崩逝着实令人悲痛欲绝,不说你们这些儿女,就是我们这些个儿媳妇,也恨不得能够以身相替,先后跟着去了。只是这几日秋老虎着实厉害,为此晕倒的宗室命妇不在少数,就是刚才还抬出去了几个,纵有御医跟着诊治,但有些上年纪的都卧床不起了,这样下去真不是法子……太子殿下这一次,哀毁过度,恐非天下之福。”
“而且,这朝夕哭临三日,本就是前朝旧制,今儿个已经是第三天了,却还没有诏令下来让停止……这恐怕不合规矩吧?”
太子妃虽然没有接话,却也明白了汉王妃此举是想做什么,如此的昼夜哀哭,对于养尊处优惯的妃嫔、宗室命妇而言,自是痛苦不堪,汉王妃偏当着众宗室、命妇的面说出了所有人的心声,并非因为她心里真心顾念众人,而是想为汉王收买人心罢了。
迎了永乐帝的龙驭回京后,太子朱高炽并未仿效昔日建文帝朱允炆借遗诏将朱棣等藩王拒于京师之外的旧例,竟召汉王、赵王一并入京哭临,要兄弟三人共送父皇最后一程。
谁知这汉王妃竟然当面收买人心,显然是贼心不死。
与太子最为亲厚的咸宁公主当下面无表情地直接打断汉王妃的话,冷然道:“嫂嫂应该知道,一朝天子一朝臣,如今太子哥哥是父皇遗诏明定的新君,他说的话就是规矩,太子哥哥与父皇情深义重,岂是那虚情假意之人可比的?”
众人一听咸宁公主这话,便都熄了附和汉王妃的心思,一时室内鸦雀无声,但众人眼里,却有股莫名的怒气,看向太子妃、咸宁公主的眼神里就暗含了几分埋怨和愤愤不平。
孙清扬见众人虽都低垂着头装聋作哑,却多是一副敢怒不敢言的样子,明白咸宁公主因为对永乐帝的感情,所以颇为赞成太子此举的这些话,非但没有起到震慑的作用,反倒推波助澜,正好如了汉王妃的愿。
但当前局面,毕竟轮不到人微言轻的孙清扬说话,见太孙妃只是低首垂目,她只好悄悄绕到太子妃跟前,扯了扯太子妃的衣袖,再努了努嘴,垂下眉眼去。
太子妃张晗毕竟是儿媳妇,对永乐帝的感情,虽然深厚,却也比不上咸宁公主等人,孙清扬这一扯衣袖,她看了看众人的神情,顿时就理智地对当前局势看了个清楚:虽然太子登基是名正言顺,但倘若失了宗室的支持,没了文武百官的真心臣服,却也难说不会起些波折。
想起使臣回复,宣旨召汉王进京行祭礼之时,汉王率领的随从护卫众多不说,人人皆在衰服下甲胄披身,反意昭然若揭。
太子妃便略一思忖,抢在汉王妃再度开口之前安抚道:“太子殿下幼承庭训,自是与先皇情深义重,不免哀伤忘记了时间。既然大家都不愿看着太子殿下哀毁过度,误了国事,劝诫太子殿下的话,自是由我去说会更为妥当。”
说完,起身往外去了。
见太子妃去了,众人虽然依旧哀哀哭泣,但声音却比先前低了好些,有些索性收了泪,只在那里哑声干号,怀里各揣心思。众人正在揣度间,忽见太子妃回来,跟着内侍疾奔而至:传太子旨意,将日夜哭临改为早晚各一次。
今儿个本是第三日了,这样算下来,大伙儿只需傍晚时分再哭一次即可。
大家松了一口气,这一下,众人谢恩之余,看向太子妃的眼神里又多了一层敬畏。再哭下去,就多了几分真心。
之后三日,在文武百官、宗室宗亲们的连番上谏劝进中,太子朱高炽推辞再三,方才择日进行登基大典。
八月,从永乐二年就被立为太子,当了整整二十年太子,时年四十六岁的朱高炽登基,次年改元“洪熙”。
登基后,洪熙帝首先赦免了建文帝旧臣,以及永乐年间遭连坐流放边境的官员家属,允许他们返回原处,又平反冤狱,使得许多冤案得以昭雪,像之前蒙冤受屈的解缙家属还乡,随后让其儿子入朝为官……并恢复一些永乐年间被抓捕的大臣官爵,加封了有功之臣。
英国公张辅出掌中军都督府,加太师衔,支双俸。文渊阁大学士杨荣任工部尚书,兼太常寺卿,金幼孜兼户部右侍郎,另一位阁臣杨士奇兼礼部左侍郎加华盖殿大学士。黄淮、蹇义、夏元吉等东宫属员原被抓的陆续被放,并相继进了尚书、侍郎等职,由正五品的大学士一跃成为正二品、正一品大员……
众朝臣见夏元吉等人被放出论功行赏,纷纷羡慕。
但那户部尚书夏元吉的这份恩赏,别人想要却也不可能,夏元吉当初下狱是因为永乐十九年进谏阻止永乐帝第三次亲征漠北的鞑靼,因为永乐帝这个人独断专行,所以群臣就没有一个敢为此说话,只有他拼死相劝:“此年师出无功,军马储蓄十丧八九,灾眚迭作,内外俱疲。况圣躬少安,尚须调护,乞遣将往征,勿劳车驾。”
那次进谏惹得永乐帝大怒,将夏元吉当场下狱,甚至打算砍了他,幸亏大臣们劝说才得以作罢。
夏元吉等人这一得重用,朝臣们自是明白,这天下,从此就是洪熙帝说了算了。
洪熙帝登基以来,不仅是有功的文武百官各有封赏,还大赦天下。
作为一个开明的儒家君主,洪熙帝坚持简朴、仁爱和诚挚的理想,大力巩固大明帝国的基业,纠正永乐时期的严酷和不得人心的经济计划,他的许多政策和措施反映了一种对为君之道的理想主义和儒家的认识。
他处处以唐太宗为楷模,修明纲纪,爱民如子,在京城思善门外建弘文馆,常与儒臣终日谈论经史。
为了取得直接的评价和利于揭露贪污腐化,洪熙帝直接给予杨士奇、杨荣、金幼孜,稍后还有夏元吉每人一颗银印,上刻“绳愆纠谬”的格言。命令他们用此印密奏关于贵族、甚至皇族胡作非为的案件。监察御史被派往全国各地去调查官员的政绩,并为官僚机构的任命寻求合适的人选。
由于南方人聪明而且刻苦,进士之中多为南方人,北方人天性淳朴忠贞,虽是皇家不可或缺的支柱,文采出众的却较少,为了保证文官科举制度不偏袒南方人,于是洪熙帝规定了科举份额,以保证北方人占全部进士的四成。
洪熙帝试图纠正永乐时期司法的弊病,十一月,命令内阁会同大理寺等司法官员复查案件,此外,禁止对犯人滥用肉刑,和除谋逆之外,惩处时不再株连犯人的亲属,废除了违背儒家的仁爱原则和孝道伦理的一些做法。
免除受自然灾害的人的田赋,并供给他们免费粮食和其他救济物品,以保证其恢复生产;下令减免赋税,对受灾的地区无偿给以赈济,开放一些山泽,供农民渔猎,对流民一改往常的刑罚,采取妥善安置的做法。
废除了古代的宫刑,停止宝船下西洋,停止了皇家的采办珠宝……
同时,还将军内所养官马分给各卫所民养,以减轻其负担。采纳夏元吉所言,取消皇帝征用木材和金银等商品的做法,代之以一种公平购买的制度。
建文诸臣家属在教坊司、锦衣卫、浣衣局及习匠、功臣家为奴者,均释放为民,听其还乡;因言事谪戍者照此办理;又设南京守备;官吏谪隶军籍者,均放还乡……
可有可无的官员被解职,其他的官员在70岁就奉命退隐;失职的官员降职,有突出才能的官员升任更重要的职务。
种种新政,不一而足。
洪熙帝推行的新政,使得洪熙朝人民得到了充分的休养生息,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明朝进入了一个稳定、强盛的时期,也是史称“仁宣之治”的开端。
外边,阿鲁台闻成祖死,遣使臣带了贡马进献,表示臣服新帝。他已经被永乐帝打得望风而逃,伤了元气,正好借新帝登基,缓和彼此的关系。
九月十日,永乐帝被奠谥为体天弘道高明广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庙号太宗,葬长陵。百余年后,嘉靖十七年(1538)改谥为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庙号成祖。
永乐二十二年十月十一日,洪熙帝册封嫡妻张氏为皇后,良娣郭氏为贵妃,李氏为顺妃,英国公张辅之女为敬妃,王良媛为淑妃,赵良媛为年妃……
立皇长子朱瞻基为皇太子,册封胡氏为太子妃,育有一女的孙氏和怀有身孕的何氏为太子良娣,其余众人,均有进阶。
封第二子朱瞻埈为郑王,第三子朱瞻墉为越王,第五子朱瞻墡为襄王,第六子朱瞻堈为荆王,第七子朱瞻墺为淮王,第八子朱瞻垲为滕王,第九子朱瞻垍为梁王,第十子朱瞻埏为卫王。
在永乐十九年因病身故的庶四子朱瞻垠,虽在永乐二十年被永乐帝追封静乐王,谥号庄献,这一次也索性追封了蕲王,谥号献。
封大女为嘉兴公主,二女庆都公主,三女清河公主,早殇的四、五、六女追封为德安公主、延平公主和德庆公主,李贤妃生的七女,封为真定公主。
三更时分,万籁俱寂,浓云密布在天空,月影暗淡,宝镂金环映暗月,彩云易散琉璃脆,朱红色的宫墙深处,未央宫灯火仍未熄。
陈丽妃看着立在她身边的未央宫管事姑姑益宁:“藿医女所说的话,你都记住了?”
穿着宫女装束的益宁极其慎重地点了点头:“奴婢都记在心里了,娘娘只管放心去吧。”
陈丽妃眸中一动,唇畔微微浮现出一抹笑容来:“本宫可是将身家性命都托付给你了,半点差池,本宫就真会为先帝殉葬,到了这会儿,放不放心,也就全看姑姑你的了。”
益宁自是再三点头:“奴婢这儿绝无差错,宫外也依娘娘所说,全都打点好了,只等下葬之时,就用那殉葬的小宫女顶了人头,将娘娘偷运出去。侯爷见了您,还不知怎么高兴呢。只是,藿医女这药方,真能昏睡七日,如同死去一般吗?先前,咱们虽然拿了猫狗做试验,也让若晓试过,但临到这跟前,奴婢心里还是惶惶不安。”
陈丽妃叹了口气,眉宇间却仍然有着渴望生机的喜意:“到了这一步,成或不成,总得一试。若是成了,算本宫命不该绝,若是不成,也只能说是本宫阳寿已尽,不该再活下去。本来藿医女都说,找不到那味药,本宫已经绝望,却不想,清扬偶然提起,她的好姐妹那儿有只翡翠琉璃杯,一杯开杯,两杯昏睡,三杯能醉死。找来一试,竟然杯子就是藿医女所说的那味药材所制,这岂不是天意?”
益宁想起那杯色如春晓,盈盈水波碧绿可喜,望之如烟如雾,拿着寒凉浸骨的翡翠琉璃杯,心里略定:“不错,就像娘娘之前说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那孙贵嫔可不就是娘娘的福音,先是因为她,娘娘机缘巧合认得了藿医女,这回又因为她,娘娘得了那良药。听说等先帝龙驭入陵之后,皇太孙受封太子,她就会被封为太子良娣,显见是个有福之人。”
陈丽妃点了点头:“可不就是如此,可惜本宫这一走,也帮不了她什么了,只我陈氏一族,在朝中为官之人众多,以后,再请父亲让他们助她一助吧,在这深宫里头,若没有朝廷里的勋贵们帮衬着,到底是无根的花、飘零的浮萍,有点风吹草动就打落了去。”
说到此,益宁愤愤不平:“本来以侯爷的身位,这次又有护送龙驭之功,皇上原是要勋旧特恩免了您殉葬的,却被那郭氏吹了枕头风,说什么您是先皇这些年最宠爱的妃子,若您不追先皇于地下,只怕先皇日夜惦记。也不知她是何缘故,对娘娘如此忌恨?”
此时,郭丹宜尚未正式受册封,益宁不愿称她贵妃,所以就含糊以郭氏称之。
陈丽妃看了益宁一眼:“你这七情上面的习惯要改一改,在本宫这里无妨,若是本宫去了,谁还能如此护你?那郭丹宜会有如此之举,无外乎是父亲与他家里的父兄有朝野之争,她若不除了本宫,本宫就是这永乐朝留下的唯一的太妃,有什么事,就是皇上也要听劝一二,岂不是在她头上压了块大石?皇上分赏了那么些个功臣,却迟迟不立皇后,不立太子,只怕与她也脱不了干系,好在,晗儿心里是个有数的,她再怎么闹腾,皇后也轮不到她的头上。”
益宁连忙跪下:“本来主子去了,奴婢也是必定要跟着殉葬的,娘娘却求了皇后娘娘恩典,将奴婢讨到那坤宁宫去,让奴婢逃得一死,这番大恩大德,奴婢没齿难忘。娘娘出了宫去,奴婢自是要跟着去的。”
“益宁,本宫只怕是不能带你一道了。”陈丽妃的嘴角泛起一丝苦意,“本宫回去之后,是顶了族里一个孤女的名号继续生活,若是带着你,定会惹人注意,到时只怕本宫保不住,连父亲也会受牵连,你跟着我,只有死路一条。所以本宫才将你托给了晗儿,不过你放心,晗儿已经答应,过后将你赏给清扬,她是个纯良的,你去了之后,只当对我一般待她,定不会差。”
这和之前商定的完全不同,益宁愕然半晌,方才回过神来,跪在陈丽妃脚下泣不成声:“娘娘——你什么都为奴婢想到了,可您出去了,身边一个得用的人都没有……”
陈丽妃强笑着将她扯起:“那也比死了强,况且,本宫出去后,虽是一个孤女的身份,却能够在风头过去之后,重返父亲膝下承欢,将来不晓得多好,哪里会短了人侍候?你就放心吧,来,替本宫梳妆,这离内侍来传旨的五更天,可没多少时候了。”
益宁含泪起身,搬了梳妆的匣子放在桌上,开始给陈丽妃梳妆。
夜里的秋蝉声断断续续鸣唱,空气中隐隐含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桂花甜香,然而主仆二人,心里却苦得如同没有抽芯的莲子一般。
这一别,是生是死,都不可能再相见了。
从此之后,就是殊途陌路。
从此之后,就是山迢水阔,宫里宫外遥遥相望。
皇宫里的琼楼玉殿,虽然充满了富贵荣华,可是,那种深埋在骨子里的孤单和彷徨,却无时无刻不在侵袭着她们,这些个在宫里数着过的日子,她们一直相伴,一路相守着过来,此一去,丽妃娘娘的人生或许从此就要走入新的篇章,她却仍然要留下来,在这深深宫墙里挣扎……
益宁手上的梳子,一下下梳着陈丽妃乌墨般的青丝,每一次她感到惶恐无助的时候,便只有灯下这个人,手里的这把青丝,能让她的心定下来。
幸好此去,娘娘就能得到自由,或者,还能找到属于她的幸福。
益宁想到这一点,苦涩里又嚼出了些甜意。
陈丽妃心里也不好受,这个计划多年的事情,办好了,自己就能海阔天空,再不被这皇宫大内所缚,办不好,自己就只能追随永乐帝于地下……
想到不管生死,她都不用再在这一眼望不到边的红墙碧瓦,天空总是灰蒙蒙的,连阳光自厚厚的云层间落下来,也是极暗淡颜色的宫里待下去。
陈丽妃轻轻吁了一口气,看着菱花镜里的自己,笑道:“益宁,你别担心,看你这手巧得,妆前妆后,本宫就像是两个人一般,单凭这个,本宫也肯定能够逃得出去,那天你将若晓化完,连本宫都以为是在照镜子,这宫里的人眼睛最亮,也最拙,定是看不出来的。”
益宁看着镜里那个小宫女模样的陈丽妃,也不由笑道:“是娘娘您聪慧,早年就一直化着浓妆,这宫里只怕没几个人看过您落妆后的样子,奴婢这才能成事。也幸好那若晓与娘娘身形差不多,轮廓有几分相似,又甘愿以身替主,咱们这才能够成事。”
想到那个若晓,陈丽妃叹了口气:“那一日,被她听到咱们的计划,本宫还吓了一跳,生怕她会说出去,几乎要下狠手毒杀她,不想她却跪下说愿意当本宫的替身,为本宫去死。真让人想不到。”
“娘娘您这也是种善因得善果,当年若不是您将她救下,她早被吕婕妤杖毙了,这一次,就是她不替您去,也还是要跟着殉葬,还不如替了您,家里头得些个好处呢。”
陈丽妃话里有些犹豫:“虽是如此,但毕竟是一条命,其他人本宫救不得,她却是为本宫去的,总不该舍下。罢了,你等会儿,将那翡翠琉璃杯里藿医女所调的药,让她也喝三杯,若是侥幸能在龙驭入陵之前,救出本宫,就连她也一并救了吧。”
益宁大惊:“娘娘,不可——多个人,就多份风险,如此一来,往外运人什么的,更加麻烦,若是被人撞破,您和她都不能活啊!反正若晓也是要死的,她也心甘情愿替您,您又何必多此一举,连累了自己的生机?”
陈丽妃却在这瞬间下定了决心,含笑拍了拍自己的脸:“你看,她既与本宫有几分相像,又这样赤胆忠心,平日里,她一个小宫女,也没人注意到,就是带出去,也不妨事,说不定,以后还能像益宁你似的,在本宫跟前侍候着,不好吗?风险,当然是有的,不过眼下新帝登基,四处都忙乱着,只怕到了长陵里,也没人会注意到有两个小宫女尸身不见的事情,只要咱们计划周详,未必不能成事……”
听完陈丽妃所说,益宁有些犹豫:“那丫头不像若晓,和您并不像,只怕就是化了妆,明眼人还是能看出来。”
陈丽妃笑道:“活人当然能看出来,死人呢?若是公公们来宣旨时,已经都断了气,谁还会仔细去看?”
益宁眼睛一亮:“娘娘的意思是——”
陈丽妃点了点头:“本宫感念先帝,生不如死,故而未等宣旨,就去了,她们为报主恩,一并自尽,这也说得过去。如今,能救一个是一个吧。你记得事后,把那翡翠琉璃杯收好,还给清扬。”
等到五更天,来未央宫宣旨的内侍,只见寝殿里,躺着两个宫女模样的尸体,紫檀雕花软榻上,陈丽妃的尸身宛若生前,妆容华贵,长眉入鬓。
益宁姑姑神色黯然地说:“娘娘自先皇去后,夜夜啼哭,生不如死,今儿个夜里,一时未防,她竟饮了毒酒去了。未央宫里头随侍她的这两个奴婢,感念娘娘恩德,也先后追她而去,要在地下仍然服侍娘娘……”
这样的事情,先前在给太祖殉葬的妃子里也发生过,内侍们心里明白,说是顾念先帝,其实不过是惧怕死相难看,所以自个儿先行了断罢了。
“虽然娘娘已去了,但这先皇的遗旨还是要宣的……”手捧黄绫,念完圣旨之后,内侍说道:“皇上说未央宫里,除开益宁姑姑您如今是坤宁宫的人外,近身侍候的,尽数殉葬,没有主子到地下没个奴婢侍候的道理。”
随之一挥手,跟着他来的侍卫们,已经将未央宫里随侍陈丽妃的奴才们先后灌了毒酒下去。
片刻之后,哭的、喊的、拼命挣扎的、跑走又被逮回的,统统都没了声气。
幸好,这些年娘娘遣散了不少的人,这宫里头,所余的人不算太多。益宁的脑海里闪过这个念头,她脸色惨白,强自镇定地说:“奴婢蒙娘娘大恩,总要送她最后一程,那两个宫女,是娘娘生前最贴己的,你们要将她们和其他奴才们分开入殓。”
虽然心里有些鄙视益宁姑姑不像其他奴才们追随丽妃娘娘而去,但如今她是坤宁宫的人,内侍也搞不清楚她怎么就能攀上坤宁宫,免得一死。因为不知其深浅,自是不好得罪,加上这事也不是什么难题,当下满口答应。
益宁就朝侍卫中的一人,悄悄竖起两根手指比了比,微不可见地朝寝殿里的两具宫女尸体点了点头。
除益宁之外,出身朝鲜李氏王朝一个官宦家庭的丽妃韩氏,死前曾向洪熙帝求旨,说:吾母年老,愿归本国。得到了洪熙帝的允准,保全了她乳母金氏的性命。
九月初七,永乐帝的妃嫔们,接旨后先是梳妆打扮,用了午膳,然后全部被引往升堂,堂上置大小床,内侍们守着让她们站在上面,将头伸入梁上悬下来的白绫之中,而后,就将她们脚下面的小床蹬掉,直到断气才从梁上解下来。
有封号的妃嫔十六位,没封号的妃嫔十几位,共计三十余位全部吊颈而死。
近身随侍妃嫔的宫女、内侍们,均被灌了毒酒到地下服侍自己的主子。
一时间,哭声响震殿阁。
三日后,她们的棺材将随永乐帝的龙驭一道,抬入长陵,妃嫔们还有一席之地,得供个香火;宫人们,不过是往长陵边的墓地里一扔,埋个干净。
曾经无限风光的皇宫大内,在正午阳光正烈的时候,被血染成了修罗场,曾经如花一般的丽人们,如同瑟瑟秋叶,再也等不到春天的到来。
就这样,永乐朝的妃嫔没有一个活到洪熙元年。有些殉葬之后,还追赠谥号,表彰其行,岁时侑食于本陵之享殿,沾些帝王后人供奉的香火,家人得到些相应的补偿;有的,只不过被永乐帝临幸过一两回,就这样莫名地人间蒸发,连个姓氏也不曾留下。
喜欢孝恭皇后请大家收藏:(321553.xyz)孝恭皇后艾草文学阅读网更新速度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