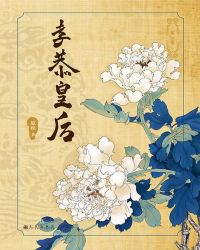第十六章 长门孤影暗
见孙清扬哀哀哭泣,朱瞻基伸手抚摸她的头,像对一个孩子似的说:“傻丫头,我也想的,不过我要食言了,我走以后,你要好好帮我照顾母后,带好祁镇他们,勿以我为念。”
他又看向太子:“祁镇,父皇走了以后,你就是家里的男子汉,顶梁柱,你要好好照顾皇祖母,照顾你母后、姐姐和弟弟。为皇为帝者,都是孤家寡人,他们都是你至亲至近之人,唯有这些亲人,才能令你不觉得孤寂,你切莫忘了这一点。即位之后,你一定要任用贤臣,仁政爱民,做个好皇帝。”
朱瞻基咳了几声,喘息方定又道:“蹇义简重善谋,杨荣明达有为,杨士奇博古守正,而原吉含弘善断。事涉人才,则多从蹇义;事涉军旅,则多从杨荣;事涉礼仪制度,则多从士奇;事涉民社,则多出原吉,杨溥是性格内向,但操守很好,为众大臣叹服,你要多和他们学习,有军国大事均须禀告你皇祖母方能决定。至于身后事,按照朕之前说的,百年之后,当与你母后同陵。”
将后事一一交代,朱瞻基的脸上看不出难过之色,只在看向孙清扬的时候,露出担忧和不舍之情。
“父皇,儿臣知道。”太子似懂非懂地记下朱瞻基所说之话,眼里犹含着泪水。
朱瞻基又让皇室宗室全部进来:“传朕旨意,藩王在属地祭奠即可,不需进京城送葬。无子妃嫔尽数殉葬,葬入妃园。”
听到朱瞻基的这一道旨意,孙清扬惊疑地瞪大眼睛:“皇上——”
朱瞻基摆了摆手,阻止孙清扬说下去:“朕知道你的心思,但这个事还是留给祁镇去做吧,你为人过于和善,表面虽然张牙舞爪,不肯放过伤害你的人,其实到最后,总爱给人留有余地,朕带走她们,以后,这后宫里就不会有风风雨雨了……”
话未说完,朱瞻基已经倦怠地闭上了眼睛,手无力地垂了下去。之前和太后的交谈,令他下了这决心,他决定为她,即使再背负一次骂名,也在所不惜。后宫里头没有了妃嫔们,母后再想借谁去压着清扬都不可能,至于吴氏,本就是清扬的丫鬟,他相信,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翻得起大浪。
孙清扬已经没法再说什么,她只知道,朱瞻基就要死了。她抱着朱瞻基大叫:“皇上,皇上,您别睡。您不要睡啊!皇上,不要死,不要死。您说过,要陪臣妾一生一世的……皇上。”她大声地哭着,哭得声嘶力竭,一声声地叫着,好像这样就能把朱瞻基呼唤回来一般。
瑾秀几个,也一道哭了起来,哀哀戚戚的哭声传染了开来,一时间,乾清宫内外已经哭声一片,太后初时还喝止他们,到后来,自己也不由自主地哭了起来。
中年丧夫,老年丧子,纵然她是全天下最尊贵的女人,又有什么用!她最在意的,一样样都失去了!
可是,无论他们哭得多么凄惨,但那哭声,并不能唤醒朱瞻基,他闭上的眼睛,再没有睁开过。掌中逐渐冰冷的温度提醒着孙清扬,绝望已经来临。
“朱哥哥,你不能……”
素手滑落,孙清扬看着朱瞻基犹带有怜惜之意的面孔,泪如雨下,这一次,她知道,怀里的人,再也不会睁眼了。
从此,黯黯天际,长空万里,都不及她与他之间的距离遥远。生与死的距离,阴阳相隔的距离。
凄厉哀号响彻九重宫阙,孙清扬全身如同被抽离了一般,一口血吐在了衣襟之上,当下就栽倒了。
太子看着哭得晕厥过去的孙清扬,立即惊慌地大声叫着:“母后,母后,您怎么了?来人,快来人,太医,太医——”
宣德十年正月初三,阳历一月三十一日,皇宫内的大钟敲响了。钟声响彻云霄,回荡在紫禁城内外,很快,京城所有的人都知道。皇上驾崩了。
一时之间,全城素服,正五品以上的文武百官更是日日赴思善门外哭临,夜里到衙门歇宿,不得回家,不得饮酒食肉。这国丧之日遇上天寒地冻的时节,自然是非常折磨人。衙门虽有暖炕,却多是尽着一些高位或年迈的老臣,众人即便烧上炭炉,仍是难以抵挡重重寒气。
那几日哭临思善门时,加之肚子里半点油水皆无,外头又都是身着斩衰,上上下下的官员苦不堪言,不少年老体衰的甚至直接昏厥了过去。
待孙清扬醒过来,皇上已经入了皇舆,送到了养和殿的正殿。由于之前久病,太医隐约有过预言,所以后事也早有了安排,又有太后督办着,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没出什么乱子。
孙清扬醒了以后,被庄静、燕枝等人劝慰了半天勉强喝了两口粥。挣扎着要跑去棺木前守灵。
“皇后娘娘,贤妃她们也去了。”燕枝这话,孙清扬明白是何意思。
丹枝端了碗出去,霜枝帮着孙清扬盖了被子,轻声地安慰道:“娘娘,皇上这么疼爱您,要是看到您这个样子,会很难过的。娘娘,皇上都说生老病死,是天道,是命数。娘娘,您要保重自己,万不可辜负了皇上对您的一片怜爱之心。”
燕枝道:“娘娘,您总说至情至性的人应该豁达,奴婢们都知道帝后同心,但恕奴婢直言,您与皇上同心的最好方式,并不是随他而去,而是应该照他说的,照顾好太子和公主,将他们抚育成人,为皇上贻养太后,帮他孝顺亲长……娘娘,您若是不管不顾,只任由自己伤心,才是对不起皇上啊。”
自孙清扬晕厥之后,坤宁宫的上上下下都打起了十二分精神,生怕皇后一个想不开,会追随皇上而去,毕竟,皇后几乎一夜白头,看在谁的眼里,都是触目惊心。
“本宫之前让你们给淑妃准备的东西,都收好了吗,还有没有?”一直木然的孙清扬忽然问道。
霜枝听见孙清扬终于开口,脸上浮现一抹笑意,又想起这是非常时期,忙收了那份高兴答道:“收好了,都在呢,只等娘娘您交代即可。”见孙清扬好似听进去才继续说道,“听人说,太后娘娘有意下旨,所有宫妃同其宫人尽数殉葬,到了那会儿,只怕这宫里头,要号声震天了。”
孙清扬惊讶:“皇上只说了妃嫔殉葬,没有说宫人。”
霜枝叹了口气:“哪儿有主子去了,奴才还独活的道理?诸位娘娘是去陪皇上的,她们不也得有人侍候不是?”
听到霜枝都是这样的见识,孙清扬知道要劝转太后的概率实在太小,却仍咬了咬牙:“为本宫梳洗,守灵之后,本宫要去慈宁宫。”
孙清扬挣扎着起来穿了孝衣,去了灵堂,跪在朱瞻基的灵柩前,烧着纸钱,心里悲痛不已。
满宫的白绫招展,她跪在灵柩下不敢近前,不敢再去瞧一眼白绢下朱瞻基的脸。四周的声音听得她心突突地跳,远远近近的哭声,她什么声音都听不见,两眼干枯,竟是没有眼泪。只一个劲儿地发抖,唇齿颤抖得发麻,直到再也撑不住,转身奔到廊下,干呕不止,恨不能将心肺全部吐出来。
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从此之后,她就是折翅之羽,独根之枝了。
在守灵之中,孙清扬悲伤过度,吃不下任何东西,身体超负荷运转,体力不支,再一次晕过去。弄到最后,太后让人把她架回去逼着她休息。
孙清扬却向太后求情,不要让宫妃和宫人们殉葬。
几番哭求之后,太后终于松了口,恨铁不成钢地看着孙清扬:“你要保她们中的一个、两个,哀家还能体谅,竟然想尽数都保下来,未免太过妇人之仁了,从前她们可没少给你添堵,皇上要她们殉葬,可是为了你好,哀家要是看你厌憎了,保不齐拿她们做伐子,找你的麻烦,你还想留着她们自讨没趣吗?”
孙清扬垂头道:“臣妾只是觉得,人都有犯错之时,但无论如何,命却只有一条,居高位者,掌生杀大权,若不能予人留有余地,仅凭一己喜恶,就断人生死,未免太过草率。而且,两代妃嫔殉葬之哀泣,不绝于耳,臣妾实在不忍那样的悲剧重演。”
太后叹了口气:“妃位以下,尽数殉葬,宫人除随侍妃嫔的那些个,免殉,你总不能让皇上在九泉之下,没有人侍候吧?哀家不能再让步了。”
“母后——”
太后冷然道:“这事不用再说,难道你忍心见瞻儿过身之后,一个人冷冷清清吗?他生前你不曾妒过,怎么大行之后,倒妒起来了?她们随皇上去了,家人都会厚赏,你就不要再纠缠下去,不然,哀家就下懿旨,一切按之前说的办。”
孙清扬想说在幼年时母亲就告诉过她,人死之后,并没有另一个世界,但看见太后不欲多说的样子,想到对于信佛的太后而言,生死轮回,因果报应,本就是根植在骨子里的东西,怎么可能劝转?只得低头应道:“臣妾代她们谢母后宽厚。”
可是,还没等到太后的懿旨下发,就传来贵妃何嘉瑜被丽妃袁瑷薇拉着跳入池塘,双双殒命的消息。
原来,平日里何嘉瑜因为袁瑷薇发了疯,总防着她,没想到守灵之后,她在回长宁宫的路上,却突然被袁瑷薇横里撞了出来,纠缠、拉扯着跳到了池塘里。因为夜深天黑,宫人们搭救不及,等人捞上来时,两人均没了气息。
而且,捞上来以后,发现袁瑷薇的身上早就绑有石头,她的手则紧紧扯着何嘉瑜,无论如何也分不开。
显然是早就抱着要同何嘉瑜同归于尽的心思,一直在寻合适的时机。
因为无法将之分开,宫人只好请旨将她两人一道收棺。
当时随侍的宫人,因为护主不力,全数杖毙。
因牵涉宫闱秘闻,对外,倒是给了个自愿殉葬的名头,其家人都得了赏赐。
而赵瑶影听了太后的懿旨,则一个劲儿地摇头。
“早在嫁于皇上的时候,臣妾就下了决心,生不能同时,死要同时。”赵瑶影脸上露出一抹坚毅之色,“皇上头七回魂夜,就是臣妾命断之时。臣妾不比皇后,有子女挂心,有父亲高堂在世,臣妾于这世间,已经全无留恋,皇上这一去,随之而去的人,大多是被迫,未必能好好侍候皇上,臣妾去了,会尽心尽力,也免得皇后担忧皇上此去,没有人知冷知热,侍候不周。”
孙清扬苦劝她:“人死如灯灭,就是皇上大行,百年后也一样是白骨一堆,贤妃,你别信那些个说辞,好好活着才是正经,咱们姐俩,以后在宫里,还能做个伴,本宫的子女,不就同你的一样吗?瑾英自幼与你亲厚,你怎么狠得下心?”
“本宫之前就同你说过,万一母后不肯下发免殉的旨意,也有法子让你和淑妃一般出宫去,赵姐姐,蝼蚁尚且偷生,你如今才不过三十出头,何苦要走这一条路?本宫与皇上琴瑟和鸣、伉俪情深尚且没有随之而去,你又何必枉做了生殉的祭品呢?”
提到瑾英,赵瑶影眼中浮现泪光,但很快她就轻笑道:“瑾英有您这个亲娘在,臣妾担心什么?您说人死后,并没有另一个世界,您又没有死过,怎么知道?您不能随皇上去,不是不想,是因为有子女牵念,而臣妾了无牵挂,自然可以率性而为。不管如何,您都别劝臣妾了,臣妾心意已决,断不会更改。您若念着我们姐妹的情分,就在臣妾殉葬之后,把臣妾葬得离皇上近一些。从前有你在,皇上对臣妾总是有怜无爱,如今臣妾下去陪他,想必能够多些时间予臣妾了……”
苦劝了一阵,赵瑶影始终不肯改口,孙清扬见她心结难解,似有走火入魔之势,一方面叫宫人盯紧她,免得她轻生,一方面传唤太医给她看病。
然而到了宣德帝的头七回魂之夜,赵瑶影仍然偷跑到他的灵柩之前,服毒自尽了。
太后、皇后感其忠义,重情,谥号纯静,名号列在贵妃之后,褒奖其族亲,连前几年过世的赵太妃都得了追封。
于宣德临终前二十余日进宫的郭爱,也在殉葬之列,在接到圣旨的前几天,她就用重金贿赂,托宫女将一份书信送给了她曾经山盟海誓的未婚夫。信中写着被后世演绎了多个版本的《连就连》。
连就连,你我相约定百年,若谁九十七岁死,奈何桥上等三年。
连就连,琴瑟和谐天地间,孟婆庄里苦三年,粗茶淡饭更香甜。
连就连,一座桥锁一缕魂,生死依随不相忘,走走停停又三年。
连就连,两情相悦两心依,恩爱缱绻不羡仙,黄泉路上不茫然。
连就连,三生石定三世缘,上穷碧落下黄泉,生生世世轮回殿……
据传,郭爱的未婚夫因为不愿她在奈何桥上等得太久,大哭之后,就在第二天于家里上吊自杀,为她殉了情。
而郭爱,亦在宫中自知死期后,留下了给父母的诀别,作词曰:“修短有数兮,不足较也。生而如梦兮,死则觉也。先吾亲而归兮,惭予之失孝也。心凄凄而不能已兮,是则可悼也。”写完这字字血泪的《绝命辞》后,她掷笔于地,伸颈悬于梁上的绳中,大呼:“娘,吾去!娘,吾去……”
话音未落,就被内侍踢开垫脚的小木床。
宣德帝驾崩之后,妃嫔殉葬一共十一人,嫔位尽数追封为妃,未曾侍寝而殉葬的郭爱,追封为嫔。
何贵妃,谥端静。赵贤妃,谥纯静;吴惠妃,谥贞顺;焦淑妃,谥庄静;曹敬妃,谥庄顺;徐顺妃,谥贞惠;袁丽妃,谥恭定;诸恭妃,谥贞静;李充妃,谥恭顺;何成妃,谥肃僖。
那些个曾千娇百媚的女子,于历史的洪荒中,只留下了这样一些名号,她们的故事,被紫禁城的风沙,渐渐湮没。
宣德十年的冬天,是孙清扬记忆里最冷的一个冬天,宫里触目之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冰冷的汉白玉柱上绑着白色绢纱的花朵,廊下、窗棂、门楣俱用白色锦缎缠着,桌椅上铺着白色织锦……宫人的衣服、头上的钗饰是白的,就连她的脸,也呈现出透明的苍白色。
加上正月里的几场大雪,整座紫禁城成了冰封的世界。
若不是瑾秀和祁镇的小手,总会在她冷到骨子里时,给她些微的暖意,她真觉得,这个世界就像赵瑶影说的,生无可恋。
这一年,她失去了爱人,失去了朋友,甚至,失去了敌手。
而日子,就在追忆和孤寂中,慢慢流逝。
正统十四年,八月。
“太后娘娘,紧急军报,报……皇上在土木堡遭到瓦剌的袭击,明军全军覆没,皇上被俘。”
听了霜枝的话,孙清扬手中的正端着的茶盅“砰”的一声,掉落在地上摔得粉碎。
“你说什么?皇上他,他……”孙清扬颤颤巍巍地抬起手,“皇上他怎么了?”
从得知儿子不顾她阻拦,私下听了王振的撺掇御驾亲征开始,孙清扬的心就一天也没有安生过,听到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她被惊呆了。
看着满头白发的太后,霜枝咬了咬牙,又说了一遍:“那祸国殃民的王振虽被护卫将军樊忠锤死,但是英国公被乱箭射死,王佐、邝埜等大人都赴难了……以致兵败,皇上在土木堡被俘。”
孙清扬摇摇晃晃,几乎要摔倒在地,她借着霜枝的手,强定心神,坐回椅上,她知道,这会儿,她绝对不能倒,不能乱。
少顷,她下令道:“召玄武大人进宫,拿哀家的懿旨去,命锦衣卫都指挥使和禁军指挥使、还有五门提督速去,务必要严守城门,全城戒严,若有人闻风异动,乱了阵脚,扰了民心,立斩不饶。”
“传哀家懿旨,让郕王速召大臣到乾清宫商议国事。”
众臣也听闻了正统帝朱祁镇被俘的消息,由于皇上出征之时,带走了朝廷中的大部分能臣干将,以至于留下的人,突闻这个消息,竟有惶惶不可终日之感,除了个别几个,大都众口一词要求严惩王振党羽外,将京都南迁,免得因京城距离瓦剌太近,来不及拒敌。
孙清扬看了看郕王朱祁钰问道:“皇上亲征,命郕王居守,不知郕王有何高见?”
朱祁钰这会儿早慌了神,哪里拿得出什么主意,只说道:“诸位大人说得都有道理,这北京城离瓦剌大军实在太近,不如咱们就……不知母后有何建议?”想说的迁都二字,硬生生被孙清扬的眼风逼了回去。
孙清扬看他改了口,方才冷然地扫视群臣一圈,缓缓开口:“尽诛王振党羽,这是肯定的,却并不着急。郕王奉皇上旨意居守,就该听过咱们大明的祖训‘天子守国门,君主死社稷’。怎可效法那宋朝的君王,再受那靖康之耻?诸位大人均是国之栋梁,越是到这样的危急时刻,越要显出作用来,若是咱们都没了主意,叫天下的百姓怎么办?迁都不可再提,退一步,就会退百步,这一退,就是死。”
“想那瓦剌,不过是蛮夷之族,从太祖爷开始,他们何曾占过咱们的便宜?这一次若非奸臣王振误国,蛊惑挟持皇上,不顾臣僚劝阻,决意亲征,又因他意图回乡省亲,贻误了军机,皇上何至于遭此劫难?咱大明的军队怎么会全线崩溃?只是输了一场战事,大家就自乱阵脚,岂不是和那王振一般,成了卖国的贼子,白白令那也先高兴?”
见群臣露出愧色,孙清扬又道:“如今诸位大人除了管好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外,做事务必以大局为重,万不可轻言弃都南迁。”
“太后教训得极是!”众臣纷纷附和。
孙太后的目光一一扫过群臣:“哀家记得,当初力阻皇上亲征的有兵部尚书邝埜,侍郎于谦,以及吏部尚书王直等人,何在?”
就有朝臣禀告,说于谦等人得知消息后,就去筹备粮草,所以没有来得及奉诏入宫。
听了朝臣回禀,孙清扬道:“兵部尚书邝埜已赴国难,哀家听闻,在途中他也曾多次谏阻皇上,不要急功冒进,可惜皇上偏信那王振之言,终至险境,像邝埜大人这样的忠臣,朝廷应有嘉奖。像于大人他们这样,想在君王之前的,是诸位大人学习的榜样。”
说到此,她面露嘉许之色:“于大人他们当时曾力言‘六师不宜轻出’,王大人曾率百官力谏,说:‘边鄙之事,自古有之,惟在守备严固。陛下得天之臂助,宜固封疆,申号令,坚壁清野,蓄锐以待之,可图必胜,不宜亲率六师远临塞下。况目前秋暑尚盛,旱气未回,青草不丰,水泉犹涩,人畜之用,实有未充。且车驾既出,四方急奏岂能即达。其他利害难保必无。天子至尊而亲赴险地,臣等以为不可。’可惜,这样的逆耳忠言皇上没有听进去,要不然,也不会出现皇上被俘之祸。”
“如今,邝埜大人和英国公他们多位国家的栋梁之臣赴难,国家正值风雨飘摇之时,诸位大人一定要精诚团结,万不可做那只顾自身,意图保全身家富贵、性命之人,须知覆巢无完卵,若是城破国亡,那瓦剌反复小人,又怎么可信?哀家召众位大人前来,就是想立皇太子,让居守的郕王监国,一方面,与瓦剌谈判,用金银赎回皇上,另一方面,做好坚拒瓦剌大军的准备,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众位大人以为如何?”
听见一向不理政事的太后竟然有这般见地,众臣吃了一惊,细品太后所说,俱都称善。
随后,于谦奉命晋见,孙清扬让他以代理兵部尚书的身份承担起保卫京城的重任,于谦慨然受命。
随着千户梁贵带回被俘正统帝的亲笔信,讲述了御驾亲征一路上所发生的种种事情,土木堡之变的内幕才完全揭露出来。
自七月十六圣驾出京,七月十九日,大军出居庸关,二十三日,到达宣府。一路上,连日都是大风大雨,道路泥泞,加之司礼监掌印、东厂厂公,当今天子最宠信的大太监王振催促赶路,由于塞北的天气已经变冷,兵士们饥寒交迫,苦不堪言,人马在路上摔伤的不计其数,两军未曾交锋,就已经开始大量伤亡。
为此,群臣多上奏章请求暂缓前进,王振大怒,说:“朝廷养兵千日,用在一时,难道御驾亲征,还未交锋,就想后退吗?谁人再敢阻挠,一定军法从事!”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垫同他争了几句,竟被武士强拉下去罚跪在路旁草中好几个时辰。
众人愤慨,却都敢怒而不敢言。自此之后,王振独揽大权,要求文臣武将奏事都要先向他回禀,由他判断是否再转呈皇上。
而当时随驾从行的人里,英国公张辅虽然官职、资历都居首位,但不直接参与军政。阁臣只有曹鼐与张益二人,其中张益入阁未及三月,也一样为王振所举忧愤。
曹鼐在途中曾与诸御史相谋曰:“不杀王振,则驾不可回也。今天子蒙尘,六军气丧,痛恨王振久矣。若用一武士之力,捽王振而碎其首于驾前,历数其奸权误国之罪,然后遣将前往大同,则吾意犹可挽也。”可惜诸御史惴惴无敢应者,曹鼐想与英国公商量此事却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只得一路遂行。
大军未至大同,兵已乏粮。瓦剌也先佯避,诱师深入。
待八月初一,大军开进大同城之时,传来了各路兵马纷纷战败的消息,尤其阳和会战失利,大同总督军务西宁侯宋瑛、总兵官武进伯朱冕战死,监军太监郭敬和总兵官石亨下落不明,其余各处要塞都遭到瓦剌和蒙古骑兵攻击,损伤惨重。
而到达大同后,各地军报纷纷传来,知道瓦剌各路人马都已进了长城,迅速南下,大军的归路有被切断的危险。王振看到边关情势危急,惊慌失措,竟然畏敌如虎,在众人都没有说退兵之际,决定退兵了。
当时大同副总兵郭登向皇上建议:大军最好向东南方撤退,经过紫荆关回到北京,可保安全。因从这条路撤退要经过蔚州,王振想请皇上驾临他的老家,以示恩宠他衣锦还乡,对此建议皇上答应了。可是走了四十里路之后,王振又突然变卦,他怕大军经过蔚州,千军万马会踩坏他田地里的庄稼,又下令朝东北方向前进,循来时走过的路直奔宣府。
同时,王振派出几千辆车子,到蔚州搬运他家中的财物,随军前进。一路上,他任意指挥文武百官和几十万大军,就像赶牲口一样。全军将士都愤怒到了极点,行军途中,怨声载道。
大同参将郭登向大学士曹鼐建议,宣府太远,地势不利,宜退回紫荆关。曹大人劝谏天子,可是王振却挟天子令诸臣,硬是命大军向宣府转进,结果白白耽误了七天,八月初十才到宣府!
这个时候瓦剌平章,孛罗已率军追了上来,孛罗是也先的亲弟弟,瓦剌军中的悍将,有“铁颈元帅”之称。
在鸡鸣山与明军交战,皇上派殿军恭顺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领兵断后,因明军来往奔走多日,疲惫不堪,体力不济,死伤过半,吴克忠、吴克勤兄弟二人,都壮烈战死。
败报传来,皇上命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率军三万断后,在鹞儿山与敌军交战,这一战,士卒死伤殆尽,薛绶与朱勇都战死疆场。
两战死伤无数,却总算为大军争得时间,十三日,皇上的亲军从宣府进至土木堡。土木堡是个重要的驿站,周围高峰矗立,只有几条山间小路可通车马。此地距离怀来县城只有二十多里,如果大军赶到怀来,可以据城而守。
结果,因为王振的一批辎重车辆迟迟未到,为等那些东西,硬是没让大军进怀来城,全军驻在了土木堡附近的狼山上。兵部尚书邝埜两次求见皇上,想请皇上率一支轻骑先入居庸关,大军随后跟进,派精兵殿后,以策万全。可王振竟然不让邝大人面见天子,硬是把他拦在帐外,邝大人气得破口大骂,王振喝令侍卫将邝埜大人拖了出去……
次日黎明,角声呜呜,瓦剌追兵到达,立刻包围了明军驻地。土木堡地势很高,明军掘地丈余,得不到一滴水,军心恐慌,这时虽是初秋,暑热未退,两天得不到饮水,人马饥渴难熬。
狡猾的也先看到明军被困,十分高兴,但是当时瓦剌军只有骑兵两万多人,明军却是号称五十万大军,纵然一路折损,此时也有二十余万人马,不用计谋,难获全胜。
于是,也先挥军暂退,派使者携带书信前来谈判议和,引诱明军离开阵地。等到大队明军都在山间小道上行进,首尾不能相顾之时,才猛然发动攻击,从四面八方以强弓硬弩射向明军,明军被动挨打,队伍大乱,四散奔逃。
当时,皇上的驻地受到围攻,他身边的侍卫、太监纷纷中箭。而这些箭镞,正是过去王振以高价卖给瓦剌的。护卫将军樊忠恨得咬牙切齿,一把揪住王振痛骂:“你这个狗太监,国家大事都坏在你的手里,你跑不了,今天我要为天下人除害!”随即用铁锤猛击,敲碎了王振的脑袋,可惜,这个时候,瓦剌军已经从四面包围上来,樊忠左冲右突,接连打死了几个敌人,最后力竭殉国。
此次征战,王振为了谋私,以国事为儿戏,把文武百官和几十万明军推上了绝境。但是当时的明军将士却在形势不利、死伤惨重情况下,英勇不屈,勇敢地与敌人拼搏,绝不屈服。
混战中,从征大臣英国公张辅、泰宁侯陈瀛、洪熙帝长女嘉兴公主的驸马都尉井源、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学士曹鼐、张益、刑部侍郎丁铉、工部侍郎王永和、副都御史邓棨等上百名文武重臣,都在乱军厮杀中,壮烈殉国。
只有大理寺右寺丞萧维桢、礼部左侍郎杨善等极少数人趁乱侥幸逃出。
在他们里面,有不少人是从未经历战阵的文官,有的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却全都手执军器,战死沙场。
此次土木堡之战,瓦剌军只有两万多人,四五十万的明军在朱祁镇与王振的瞎指挥之下,一路上冻饿而死的、往返路上被追杀的、混战期间自相践踏而死的不计其数……活下来的已经所剩无几,竟然一败涂地,死伤过半,骡马损失二十多万头,衣甲辎重全被敌人夺去。四处奔逃的明军士兵,逾山坠谷,连日饥饿,蓬发赤身,弃尸数百里,惨不忍睹。
听完梁贵所言,回到慈宁宫,孙清扬久久不语,半晌才喃喃道:“皇上未满九岁登基,得太皇太后监政,三杨辅政,朝中一向清平,天下安定,作为太平天子,皇上从未亲自经历过战争,每每向往祖宗们的神勇,期望像他的曾祖父、父亲一般,能够得到亲征得胜的盛大荣誉,却对敌我交战,你死我活的惨烈所知太少。正如吏部尚书王直等人所言,起初就准备不足,竟然没有早备粮草,只集结了十来天就匆匆上路,这才会出现离开京城数日,未到前线战场,军中就已经乏粮的事情出现……”
“这事,始作俑者虽是王振,但何尝不是皇上偏听轻信,只是如今,也先将皇上当奇货可居,该如何是好?”
喜欢孝恭皇后请大家收藏:(321553.xyz)孝恭皇后艾草文学阅读网更新速度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