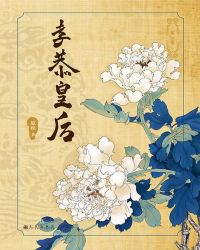第五章 猎猎驾长风
朱高煦想起当时,蹇义和杨士奇二人在做了自我检讨后被释放,官复原职,而杨士奇将迎驾迟缓之罪都揽到自己身上,方才使得朱高炽在此事中顺利过关。杨溥、黄淮等人却在狱中一关就是十年,直到朱高炽做了皇帝才被释放,似有所悟。
但他决不肯承认自己不如朱高炽,想到朱瞻基在他受降之后,给他用的软筋散,朱高煦愤然道:“那个死胖子就是会假模假样地收揽人心,你们父子都是这样,表面仁义宽和,背地里的阴谋手段一点也不比别人少,要是在沙场上真刀实枪地拼杀,你们父子,加起来也不是我的对手。”
正是因为朱高炽仁义宽厚,朝中才会越来越多的官员愿意为他卖命,助他安然无恙地成就九五之尊:解缙为了他在冰天雪地里活活冻死,家被抄,妻子、宗族被流放辽东;大理寺右丞耿通为他仗义执言惨遭凌迟;杨溥、黄淮等人因为保他在狱中关了十年;甚至永乐帝的心腹之臣,奉命调查太子德行的礼部侍郎胡潆也以“皇太子诚敬孝谨七事”密奏朱棣,使得朱高炽的境况转危为安。
可落在朱高煦的眼里,他却觉得这都是朱高炽收敛人心的手段罢了。
朱瞻基看到他执迷不悟,露出讥讽之色:“当父皇为皇朝操心劳力的时候,朕的好皇叔,你在做什么?靖难之时,建文帝用离间计,向固守北平城的父皇写信,以燕王之位做诱饵,劝其暗度陈仓。你得知此事后,马上落井下石,对皇爷爷说父皇与朝廷暗地相通,肯定要反。父皇连信都没拆,立刻派人星夜快马飞报皇爷爷,听凭皇爷爷处理此信,事后对你没有任何怨愤之语。”
“永乐十四年。你趁皇爷爷去北京视察新都建设之机,在南京私自招兵三千,精选自己的护卫队,甚至私自使用皇帝的乘舆器物,操练水战,放纵护卫队在京城大肆抢劫,试图阴谋叛乱。皇爷爷为此大怒,当面夺去你的衣冠,将你关在西华门内,准备废为庶人。这时,是父皇再次站出来,苦苦哀求皇爷爷保留你的亲王名分,以观后效,还亲自给你写信,劝你悬崖勒马,从善如流。可你回报父皇的是什么?”
“甚至在父皇登基,你败局已定之后,还派你的儿子朱瞻圻及心腹潜到北京,伺机作乱。父皇知道后,不但没有责怪他,反而增加他的俸禄,赏赐宝物数以万计,封朱瞻坦为世子,其余儿子均为郡王。待朕登基,也是优抚你和三皇叔,加俸禄,赏金银,赐美人,这样的以德报怨,可谓亘古未有了。你却不知好歹,屡屡作乱,数次想要朕父子的性命不说,在假意诈降之后,对朕下手不成,就对朕的后宫下手,谋害皇后,对太子下毒。皇叔,朕父子对你以德报怨,你就这么回报我们吗?”
“父皇当太子监国二十年,面对皇爷爷的猜忌和你们的暗算,每一天都如履薄冰,随时面临生死抉择。但是,他毕竟熬过来了,成功地坐上龙椅。这其中靠的是什么?当然不仅仅是东宫官属的维护,也不仅仅是朝中官员审时度势后的庇护,他靠的其实还是自己,是他的智慧,一个真正具备王者之风的高瞻远瞩。”
“他虽然不擅领兵打仗,却有攻城略地、建国安邦的治国策,正因如此,他才能韬光养晦,先示人以弱,再以弱胜强笑到了最后。皇叔,换成是你,你能够做得比父皇更好吗?只怕皇叔你永远都不会明白,你输的不是嫡长之名分,而是自己的本事不济,是你只一味地阴毒、乖戾,却没有放眼天下的胸襟。”
朱高煦确实没有领悟,他只是后悔自己下手还不够狠辣,没有买通关节处死那些个关在诏狱中的东宫属臣,以至于他们后来为朱高炽所用;恼恨死士们不够尽心,自个儿的部众不够忠心;惋惜自己没有朱瞻基这样一个得帝心的好儿子……听着朱瞻基对自己的数落,他吼叫道:“成王败寇,你别说了,是我不及你父子隐忍,棋差一着,这是天要亡我,并非你们真比我强。”
听了朱高煦的话,朱瞻基知道,这位皇叔永远都不会明白,他输给父皇的是仁德,是人心,是格局。
他看着朱高煦,眼底露出一抹冷意:“你不仅比不上父皇,也比不上三皇叔,他虽然能力稍逊于你,也和你一样妄想夺嫡,屡次和你合谋,诬陷父皇,却终究被父皇的仁义打动,败得心服口服,甘愿为其驱使,皇爷爷去世后,父皇在正式登基称帝前,你负隅顽抗,试图一较高低,当初和你一同联合起来打击陷害父皇的三皇叔,到了北京之后,却第一个上书请求父皇即位称帝,甚至在后来册立母后为皇后,朕为皇太子时,他也是第一个提议。正是因为三皇叔审时度势,所以,他如今仍是高高在上,锦衣玉食的亲王,而你,却成了阶下囚。”
朱高煦一听朱瞻基说赵王朱高燧都比他强时,简直气得要吐血,他哇哇大叫:“朱高燧那个没胆量的,只会苟且偷生,却不知举大事者,不拘小节,像他这样被点小恩小惠就打动的人,注定只能为人臣子,受些嗟来之食……你竟然拿他和我比,气死我了……”他胸中突然翻腾起压抑已久的恶气,想都没想,就伸腿给朱瞻基使了个老绊。
朱瞻基四岁就开始练桩,马步扎得极稳,怎么可能会让他绊倒?但见他伸腿,朱瞻基却顺势摔了下去,摔了个大马趴,灰头土脸,好不尴尬。
看到朱瞻基狼狈地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朱高煦笑了,笑得很灿烂、很开心,他的笑声在花园里久久回荡,令跟在其后的文武百官、宫人、侍卫们见之惊心,闻之色变。
皇上对汉庶人朱高煦相当宽容,远的不说,洪熙帝崩逝之后,皇上从南京赶往北京的登基途中,汉庶人就曾图谋伏击,皇上不予计较;后来,朱高煦鼓动诸王造反,在乐安起兵,皇上仍然没有杀他,只是御驾亲征,兵临城下对其劝降;即使在软禁汉庶人之后,皇上还时常前来看望,今日更是对众朝臣说,顾念着骨肉亲情,想着三年过去,皇叔可能有了悔改之心,有心开释于他,复其汉王之位,他却以怨报德,对皇上下腿使绊,令其当众出丑。
九五之尊,怎可受此折辱?这简直就是扫大明朝的颜面,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一下,连一些偏向朱高煦,一直觉得礼不上大夫,汉庶人罪不应诛的朝臣都觉得说不过去了,在和善的宣德帝“龙颜大怒”时,没有一个人劝诫。毕竟,这一回朱高煦他伤到的是一个皇帝的尊严,他还是阶下囚的时候,就敢当众给皇上使绊,恐怕放出去之后,也是贼心不死,终成大患。
朱瞻基虽然恼怒,却仍然只是命人拿了个三百斤的铜缸来,将朱高煦罩住,免得他再使坏。
他可是知道自己的这个皇叔,为人有勇无谋,脾气暴躁,性子烈,如何能够忍下这样的羞辱?
果然,朱高煦大怒,在缸内哇哇大叫,运力举起铜缸欲砸向朱瞻基。
这还得了?汉庶人竟然到了这个时候,还意图谋害皇上,朝臣里就有人劝皇上诛杀了朱高煦,以儆效尤。
朱瞻基长叹一口气,他叫人搬来木炭,在铜缸周围堆积如山,点燃之后,将朱高煦活活烧死,以解心头之恨。
在场众人,虽然有人露出不忍之色,却没有一人为朱高煦求情。
没过多久,除早年假死隐匿在外的朱瞻壑外,朱高煦的另外九个儿子全部都被株连处死,朝中无人对此有异议。
解决了内忧之后,宫里头暂时恢复了一片清平之势,过完了中秋,朱瞻基开始准备率军北巡开平,以御外患。
虽然经过之前永乐帝的数次北征,瓦剌的兀良哈三卫已经全然投靠了大明朝,好些个蒙古勇士不但在京城的侍卫亲军中服役,甚至还有好些将领成了武学讲师,而蒙古的阿鲁台太师终于看清大势,倒向了大明朝,还将麾下的百姓悉数移往了内地,只留壮健的骑兵分布在兴和以及开平一线……
但仍有一些鞑靼骑兵,伙同大宁会州兀良哈的精锐以及新加入的女真人、瓦剌的脱欢,每每趁秋高马肥之际,就沿长城北上到大明朝抢掠。所以朱瞻基打算趁田猎的时机亲自巡视各个关隘,看一看边境的守备情况。
一方面,他通过文治推行大明的诸多政策,实行每岁的贸易限额,用来自中原的精美金银器和瓷器、锦衣、茶叶等草原最为缺乏的奢侈品,换取草原上的马匹牛羊,令其成为草原王公贵族最重视的贸易,也使得令其所在的部落为了争夺多一些的配给比例,相互拆台,互使绊子,互相拖后腿,给大明朝休养生息的喘息之机。
另一方面,他也想通过登基后打上一两场胜仗奠定地位,让那些觊觎大明的蒙元诸部胆战心寒。
八月二十八日,宣德帝的车驾由京师出发,少师、吏部尚书蹇义,少保兼太子少傅、户部尚书夏原吉,少傅、工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杨荣,礼部尚书胡潆,兵部侍郎王骥,刑部侍郎施礼,工部尚书吴中,右佥都御史凌宴如,太常寺卿兼翰林学士杨溥,太常寺卿姚友直,大理寺少卿王文贵等人扈从,英国公张辅、阳武侯薛禄等分将各兵。
经蓟州(今天津蓟县)至喜峰口(今河北宽城南)外,遇到兀良哈率一万人侵扰边境,宣德帝遂命西宁侯宋瑛、武定侯郭玹、半城侯李贤、都督冀杰屯兵遵化(今属河北),而自己率领三千精锐骑兵,每人两匹马,带十天口粮,前去迎敌,文臣只有杨荣跟从。
宣德三年九月初六傍晚,宣德帝所率的精锐骑兵抵达宽河(今喀喇沁左翼南),与敌人相遇。
虽然才九月,但朔北的寒风如同刀子一样扎人,细针密缕一般撞进人的胸腔,仿佛兵甲铁衣都被穿透。
天边挂着一钩柠檬黄的弯月,也如同刀子般,在漆黑的天幕上倒悬而下,月光皎洁,广阔的千山万水都被其笼罩着,穹庐下一条浊黄颜色的大河,裹挟着泥沙,气势磅礴,浊浪滔天,混浊的河水不停地拍打着两岸岩石,激起如泥浆般的千重浪,仿佛万匹骏马在猎猎嘶鸣,声势惊人。
因这翻腾的河水,原野突然显得安静了,寂静中溢出一声声铮然的弦响,似马踏冻土,手拨琵琶。
“……流星白羽腰间插,剑花秋莲光出匣。天兵照雪下玉关,虏箭如沙射金甲。云龙风虎尽交回,太白入月敌可摧。敌可摧,旄头灭,履胡之肠涉胡血。悬胡青天上,埋胡紫塞傍。胡无人,汉道昌……”
初时低回,渐转高亢,终于决堤溃岸,席卷一切岑寂,喧腾而起——枞金伐鼓,月魄霜角,旌旗逶,铙歌列骑吹,羽檄相交驰,惊戈之声层层叠叠倏忽而至。
朱瞻基仿佛回到同永乐帝北征的岁月里,一腔热血在胸怀激荡,荡起他澎湃的激情,给他潮水般一往无前的决绝。
立身马上,张弓搭箭,流星赶月一般射向对方前锋,不等那人从马上坠落在地,朱瞻基已经拔刀振臂高呼:“大明勇士今安在?”
“在!在!在!”轰响出无数回应,如雷鸣海啸,山崩地裂,弹击着敌手的刀与骨,还没有战,就听的人觉得有什么刺进了骨头搅动着、翻动着,像是要把胸腔刺破,头骨穿透一般!
朱瞻基狠狠一夹马腹,在影卫的护卫下,冲入敌阵。
他长刀霍然一挥,挥洒出一片凌若秋霜的光华。他反手一刀,一个面目模糊的头颅横飞而出,刀身一转,又重重击在右边一人肩侧。
稍有离他近些,压着他长刀的敌军,就会被青龙、白虎还有玄武等人的刀剑挑开……虽然敌军一望无际,乌压压挤挨着,这边被冲得溃散,那边又合围过来,朱瞻基却在人潮中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
四野人影密密,似无形的网要将他笼住,显然,敌军已经发现,这队骑兵不简单,为首的是条大鱼。
风声搅动着马蹄,手中兵刃相交,在轰响的河水和空旷的原野里,声音越发显得清晰,清脆,如同带了回声,万马奔腾。
“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此一战,必将尔等非我族类,怀有异心的觊觎之徒,撵到千里之外,看尔等敢再来犯我大明一分一毫!”朱瞻基突然勒马立定,蓦然间长刀西指,喝道,“兀良哈,朕今在此,你敢过宽河一步,朕定取你首级。”
——他狠狠将刀往下一斩,将对面人影一剖两半。以寡敌众,他一样要胜券在握,凯旋!
他所率的,是大明最精锐的骑兵,在他的身后,还有十万雄师。
一支长矛横扫过来,朱瞻基胯下马吃痛,长嘶一声,前足跪倒,斜刺里又一支长矛自马腹横穿而出,将和着血的一串马肠拖曳在地,那马在翻滚中将他甩下背,朱瞻基杵着刀摇摇晃晃地站直,只觉四肢沉重,筋骨间密密麻麻的酸痛汹涌袭来。
眼看马蹄就要踏上他。
“皇上——”青龙低呼,斜挥一刀,斩断一个锃亮的长矛。
“皇上——”白虎惊叫,纵劈一刀,掀翻迎面一个深黑的人影。
“皇上——”玄武和杜子衡的长刀舞成了一片雪亮刀影,砍断了靠近朱瞻基的几只马脚,在伤马倒地之际,玄武还顺势将朱瞻基拉到自己的马上。
敌军后翼疾驰而来,离他们最近的直接挥矛而进。
因为要护着朱瞻基,玄武不顾刺向自己的长矛,不躲不闪,硬生生地受了一刺,长矛从他的额角斜贴而过,他回手松开马缰,用两指夹住长矛,再顺手给了对方那张惊恐万状的脸一刀。
他眼前模糊一团,不知是被自己还是对方的血糊住。不知为何,脑海中电光火石般闪过幼年时师傅教自己剑法的情景,一招一式,宛若昔日师傅粗糙的手掌托住他的胳臂,剑虽沉重,他的手上却觉轻飘。
仿佛师傅又一次抓住了他的手,为他承担身上大半重荷。
他跃身换到另一匹马上。
紧跟在后的青龙和白虎立刻将朱瞻基所骑的马掩住,与前后合纵上来的其他影卫,一道把朱瞻基护了个严实。
这一下,变成玄武迎战在前。
因为眼睛被血糊住,他看不见有数支长矛正朝着他的胸口而来——
“师傅——”
他身边的杜子衡拍马上前,挑落了数支长矛,却总因寡不敌众,被一支长矛穿透了他的胸口,鲜血喷溅而出。
杜子衡这一挡,他们后面的骑兵已经赶了过来,有些将他俩护住,有些与敌军交战在一起。
彼此间白刃相见,仿佛浑身滚沸着的不是血,是烈酒,烈酒燃烧着血液,烧燎着伤口,铁骑凭陵,刀刀刺心切骨,易水冰寒,剑剑穿云裂石,一时间杀得天昏地暗,山川萧条。
杜子衡只觉得那刺进他胸口的长矛,灼热滚烫,仿佛要烫熟了五脏六腑,把他的胸腔煎得酥烂,四肢百骸都挪开位置,他被胸口传来的甘辣炙得一激灵,往后,却是更深的混沌,他朝马下翻落。
抹了眼睛一把血,勉强能够视物的玄武已经拉住了他,把他横在自己的马上,护在胸前,然后将马缰交给一个骑兵,低喝:“护他回营救治。”他自己换乘到骑兵的另一匹马上,再度上场厮杀。
敌人即将合围过来,如同一个包围圈,要将他们圈在其中。
这时,白虎也奉朱瞻基之命,再度赶了过来。
玄武和他对视一眼,都对身后的人叫道:“跟上——”
两人各率一队,如同剪刀,分两翼夹攻,往敌腹深处剪去。
玄武挥动铁剑,向着他对面的人斩了下去。
宽直的铁剑,携着排山倒海的威势,重重地砍在了铁甲之上,裂帛一般轻易地就将对方劈成了两半。
见他如此凶悍,敌军如同河水似的骤然分开,向着两侧奔涌,露出紧护在后的兀良哈,将其暴露出来。
下一刻,河水再次涌回,把中间面露惊恐之色的兀良哈掩住。
玄武和白虎率同铁骑,再次挥刀弄剑。
敌军再次被撕开了口子。
他们继续挥动刀剑,一剑比一剑狠,一刀比一刀急。
敌军一次次分开,又一次次复原,但掩着兀良哈的人越来越少,有好几次,玄武的铁剑几乎要挥到了他的眼前。
如同要砍碎乱石惊云一般,玄武束着的黑发已经散落,发丝随夜风飘舞,他身上的盔甲,早已被割出了无数道细口,浑身是血。
但就是这样一个血人,却丝毫不给人半分狼狈的感觉,他刺出的每一剑,都是大开大合,给人雷霆万钧之感。
而他的神情平静,甚至显得有些木讷。
他继续挥动铁剑。
……
就这样,玄武和白虎两翼夹攻,生生将兀良哈还没有合成圆的包围圈,剪了个七零八落。
终于,玄武的剑挥到了且战且退的兀良哈面前。
兀良哈眼瞅着,他身前掩着的侍卫们,如同数片落叶被那柄宽大的铁剑轻轻挑开,他身前的一个侍卫明明紧紧握着长矛,手臂却离开了身体,溅出一片血花,在他眼前飞舞片刻方才落下。
那柄平且稳的铁剑却突然剧烈地颤抖起来,挽起一个剑花,而后如同离弦的箭一般飞起,斩向他的脖颈……他只听到原野四周的天地里,充斥着河水狂肆磅礴的轰鸣,而后,是冷,是寂,是黑。
再也不能够醒来的黑。
看到兀良哈的头颅被自己斩下,玄武方才力尽而竭,落下马去。
这一战,何其惨烈,对方死伤无数,大明也损兵折将,但终究还是胜了,胜得很威风,令草原上的众部落每每说起,都提心吊胆、惶惶不安。
这一战,宣德帝亲射其前锋,杀死三人,将铁骑分为两翼夹攻,大胜,斩其首领,获军器马驼不计其数。
九月十五日班师,二十四日,宣德帝回到北京。
早在宣德帝班师回京之前,玄武和杜子衡就被精选的影卫,换马不换人,用八百里加急送回了京城。
军中所带的太医,对他俩的伤势都只能做一些缓解的处理,毕竟军中缺医少药,对他俩这种煨了毒的刀剑之伤,能够做的实在有限。
到了宫里头,早就接到飞鸽传书的藿香已经准备好一切事宜。
玄武和杜子衡伤势感染,再加上一路颠簸,已经只余一口气。
幸好,还有一口气。
藿香此时的医术已经直追她祖父当年,几乎到了生死人、肉白骨的地步。
这样的外伤,只要有一口气在,她就一定将他们救活。
玄武觉得自己快死了。
他一整夜都半梦半醒,烧得迷迷糊糊,但意识还在。
屋外的雨滴滴答答下了一夜,他也听了一夜,天亮了,终于沉沉睡去,有宫女进来帮忙洗漱,碰到他滚烫的额头,微微一愣,立马唤了人进来给他擦拭降温,不停地端着水盆进出。
谁都知道,躺在太医院的这两位大人,在这次皇上北巡时,为了救皇上才受的伤,专门由藿医女进行医治,半点轻慢不得。
宫女端了水看看锦被盖着的玄武大人,之前失血过多呈青白色的脸因高烧显现出病态的红晕,有些担心:万一他眼一闭,就这么去了,皇上震怒,只怕侍候的人都脱不了干系。
她把帕子放在水里浸了浸,拧干之后,轻轻搭在玄武的头上,为他降温。
玄武喉咙底发出几声嘶哑的语调,宫女听不清,却猜他是想喝水,试了试桌上的温水,冷热正合适,就用银勺一点点给他喂到嘴里。
而睡梦中的玄武,像是回到那次在沙漠里行军,正午的阳光将每一粒沙都晒至滚烫,灼热、干渴席卷而来,浑身脱水的感觉,如同他即将被晒成一片沙海那样,粗砾、荒凉。
他以为自己和所率的兵马都将死在正午的烈日之下。
他能七箭连珠,能够力拔山河,行军打仗,更是一把好手。他从来不怯,即使面对强大过他的对手,他也能强撑一口气到最后,等来生机。
但这一回,他胜不了天。人,胜不了天。
就在人困马乏之际,眼前却突然出现了绿洲,如同海市蜃楼,却真实得就在眼前。
清泉汩汩,流水潺潺。望之就觉得遍体生津。
清溪如梦,扬金明液。
他的人马得救了,他得救了。
藿香走进房时,正好听见迷糊着的玄武,喃喃说出一个字。
声音实在低沉,藿香和宫女都没有听清,但藿香仍然挥挥手,让宫女退了下去。
万一玄武大人说的是军情,叫这些宫人听见可不大好。
她坐在床边,继续用银勺给玄武喂水。
她是太医,倒不用讲究那些男女大防的规矩。
她刚去看过杜子衡,已经开始退烧,脱离了凶险。
见玄武仍然高烧不退,不由有些担心。
睡梦中的玄武又唤了一声。这回,藿香听清了,她大惊失色。
她用银勺掩住玄武的嘴,回身看了看左右无人,方才放下心来,舒了一口气。
她看着睡梦里的这个人,眼睛闭着,眉头皱着,嘴角却有隐约的笑意,像是这个脱口而出的名字,藏在他的心头许久了,只是唤一声,就觉得开心。
藿香有些可怜玄武,这个名字,他在私下里叫过多少遍,一千次还是一万次?明知不可能有回应,他就这么深深藏在心底。
他的妻子已经病故好几年了,他却始终不曾再娶。
听说,前一阵子,工部尚书家才貌双全的小姐慕他武艺超群,人品出众,愿意嫁与他做填房,都被婉拒了。
先前以为他对外所言,心里有着人,再不能够对其他人钟情,只得辜负……是念着其亡妻的托词,现在看来,竟真是心里有人。
他是不是在每个清晨进宫的时候,就盼着能够听到她的一点消息,而后在晚上再回想曾经相见时她的笑颜,一遍遍在叫着她的名字?
他孤独吗?看着这个睡梦中才露出笑容的男人,藿香突然觉得,他也许并不孤独,在他的心里,有一个人可供他回忆,不管是在平原、峡谷还是山脉,月夜星辰,他都能够在心里头,默念着她,比起许多人一世不知情之滋味,已经强出太多。
情到浓时情转薄。若不是这一日自己偶然听见,只怕他的这片相思,永远不会有人知道。
这个沉默的男人竟然如此深情。
爱一个人就是这样全凭热情而非理智吧。
他只是用理智来克制不让人看见他这一颗心。
因为他知道,纵然她看见了,也不可能给他回应。
藿香给玄武喂下一颗由寒水石、羚羊角、木香、沉香、元参、升麻、甘草等十六味药物配成的丹药,转身离开。
那丹药,能够清热解毒,镇痉熄风,开窍定惊。吃了之后,他意志恢复,必定不会在睡梦里,在迷糊的状态下说只言片语,也不会再有人像她一样,听见他叫那个名字。
藿香迈出房门的瞬间,怅怅地想,自个儿需要保守的秘密又多了一桩,在这紫禁城里,真是太多秘密了。
喜欢孝恭皇后请大家收藏:(321553.xyz)孝恭皇后艾草文学阅读网更新速度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