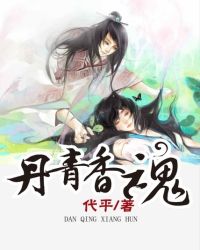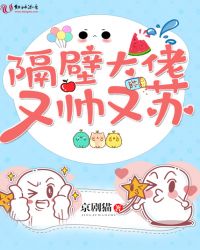姚广孝去京都组织学者编撰《永乐大典》。在离开‘普济寺’的前一晚上,他要向上官讲述了好友方孝孺那些鲜为人知的事情。那么,方孝孺那些鲜为人知的事情究竟是什么呢?
原来,在明初朱元璋称帝之时,南京就成立了以儒家学派宋濂为主的‘心学社’,宋濂就任‘心学社’的社长,心学,作为儒学的一门学派,最早可推溯自孟子,北宋程灏开其端,南宋陆九渊则大启其门径,与朱熹的理学分庭抗礼。心学不同于其他儒学门派的是:心学在于其强调生命活泼的灵明体验“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无善无恶就是没有私心物欲的遮蔽的心,是天理,在未发之中,是无善无恶的,也是人们追求的境界。‘心学社’以孟子自居,它把朱子看作是墨子似的人物,与其彻底划清界限,分道扬镳。
宋濂和刘基、高启等人带着自己的得意弟子前往闽、浙、赣三地著名书院巡讲儒家‘心学’,因为闽北是朱子理学的发源地,是理学家朱熹成长和讲学的地方,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心学’巡讲的最好地方。
方孝孺是宋濂的得意弟子,理当入列巡讲队伍,那姚广孝虽为僧人,但他既通晓文艺又擅长诗文,自然与文人交往颇多,尤其与高启交往甚密,高启在为姚广孝《独庵集》作序时,言其爱广孝之诗,读之不厌,更赞其诗“浓淡迭显”、“圆转透彻”,“将期于自成而为一大方者也”。可见得,广孝诗染当时之文风,通达古今,渐成一派。
现有闽、浙、赣三地讲学的绝好机会,这样的好事,高启当然不会忘记挚友姚广孝。而姚广孝和方孝孺在社里经常谈论诗文,畅想人生,不久便成为无话不说的好朋友,然而,他们的心中的大师既不是高启,也不是刘基,而是受人景仰的一代文豪——宋濂。
宋濂生于1310年十月十三日(11月4日),明代散文家,文学家,字景濂,号潜溪,谥号文宪或太史公。浦江(今浙江金华市付村镇上柳村)人。自幼家境贫寒,但聪敏好学,曾受业于元末古文大家吴莱、柳贯、黄溍等。他一生刻苦学习,“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达通”。元朝末年,元顺帝曾召他为翰林院编修,他以奉养父母为由,辞不应召,修道著书。
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宋濂与刘基,高启并列为明初诗文三大家。他以继承儒家封建道统为己任,为文主张“宗经”“师古”,取法唐宋,著作甚丰。他的著作以传记小品和记叙性散文为代表,散文质朴简洁或雍容典雅,各有特色。朱元璋称他为“开国文臣之首”,刘基赞许他“当今文章第一”四方学者称他“太史公”。著有《宋学士文集》、《孝经新说》等。
宋濂是“开国文臣之首”。他坚持散文要明道致用、宗经师古,强调“辞达”,注意“通变”,要求“因事感触”而为文,所以他的散文内容比较充实,且有一定的艺术功力。
宋濂提出:“一切学问,修养都归结一点,就是要为善去恶,即以良知为标准,按照自己的良知去行动,天理自在人心中。”
宋濂带着大家从“考亭书院”(地处福建、建阳,朱熹讲学的地方)来到了邵武的和平书院。
黄峭弃官归隐,既而创和平书院,和平书院初创时,为黄氏家族自办的学堂,专供族中子弟就学。它开了历史宗族办学的先河。
南宋以来,和平书院,逐渐变为一所地方性学校,它不再只是黄姓的家族学堂。附近的地方绅士也捐钱、捐粮、捐田资助和平书院,并将子弟送书院就读。办学以来,邵武俊贤辈出、英才荟萃,无不直接或间接地仰仗于和平书院。
和平书院曾是朱熹讲学授徒之地,宋濂的‘心学社’肯定不会落下此方宝地。
和平位于邵武西南,历史文化悠久,离大明三千多年前,便有人类繁衍居住,唐前的和平称之为“禾坪”,取地势平坦、盛产稻谷之意。
进入和平,东、北两座城门谯楼、城墙,高耸入云,大片的古城堡建筑跳入眼帘,城内南北青石板铺筑的主街长达2000余尺,堡内既有黄峭创办的闽北历史上最早的“和平书院”,也有李氏、黄氏、廖氏等五座“大夫第”。这里人杰地灵,曾经走出了多少历史功勋、达官显贵,为邵武乃至闽北,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历史陈迹。
宋濂一行进到了书院,院长黄书达十分热情地招待着来自京城的的学者、贵宾。
宋濂和得意门生方孝孺住进了院长的家中,院长黄书达是五代后唐工部侍郎黄峭的十五代孙,膝下有一儿一女,儿子黄明,女儿黄嫒。
谁知黄嫒和孝孺一见钟情,相见恨晚。孝孺见黄嫒是杏脸桃腮、仙姿玉貌,黄嫒看方孝孺更是花心倜傥、玉树临风。孝孺假装身体抱恙,黄嫒伪作抱病在床,趁家人不在,老师开讲之际,孝孺和黄嫒便一起躲进附近的稻草垛里拥抱接吻,陶醉尽欢、热情荡漾。
孝孺缓缓解开黄嫒的裤绳,黄嫒尽情享受人间的醉爱,他(她)们男功女授、女功男授,姿势轮换、花样百出,云里雾中、汹涌澎湃。孝孺急促呼吸,黄嫒咿呀尖叫。正所谓——
少年红粉共花心,锦帐春宵恋不休。
兴魄罔知来草垛,狂魂疑似入仙舟。
尔我谩言贪此乐,神仙到此也生淫。
红绫被翻波滚浪,花娇难禁蝶狂蜂。
时间一晃就过了五日,‘心学社’完成了心学演说的任务,就要离开和平前去江西,方孝孺和黄嫒情谊如绵、难舍难分。
方孝孺想带走黄嫒,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好友姚广孝,谁知广孝强烈反对,他对孝孺说:“老师的心学与朱熹的理学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其实就是‘格心’与‘格物’的区别,你的所为、行径,可以用心控制,没有那物在的理由。朱熹将自己与儿媳的苟且之事说成是客观的物在规律,便是宋濂先生最为反感,也最为反对的主要原由。
太祖十分器重先生,你作为他的得意门生,将来一定会得到朝廷的重用,这熟轻熟重,孝孺得掂量清楚。”方孝孺无语,面对姚广孝,他极为痛苦点头赞同。姚广孝的劝语,虽然拆散了孝孺、黄媛这对情侣,但在永乐年初却保住了黄媛母女的性命,使其免遭朱棣的杀戮。
喜欢丹青香魂请大家收藏:(321553.xyz)丹青香魂艾草文学阅读网更新速度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