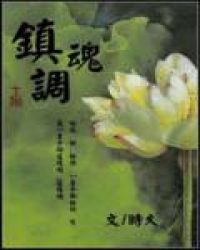他真的是个男人么?
杨昭倚着身后的廊柱,手里的夜光杯轻轻晃荡,澄清的酒面半映着顶上天光,半透出杯底离合的花纹。他浅酌一口,眼光却越过杯沿,投在斜对面那人的身上。
莲静默默地坐在席尾,靠近池边,也和他一样举杯啜饮,眼光却越过去看向别处。
杨昭顺着他的视线看去,只见水气氤氲的温泉中,一朵石雕莲花跃然水上,茎杆微弯,花盘斜堕,恰如女子含羞带怯,粉面低垂,也正像——看着池中莲花那人的姿态。
虽是冬日,他穿得也很少,一件薄薄的单衣,领口连锁骨也未全遮住。长发束成发髻,整齐利落,白皙柔美的颈项便尽数露了出来。此刻他微斜着头,那细白的颈子正是最娇美的姿态,其上一张素白容颜,因酒而染上了一层红晕,冲淡了清冷,浮起了娇媚。
是男子,固然貌太美,若是女子,可一点都不欠缺媚色啊……
他暗暗一笑,端起酒杯向那边走过去。“居士好胆色!我原以为居士只对我这等庸碌之辈不屑,却不想连右相也敢顶撞。”
莲静放下酒杯,收回视线,但并不看他,只望着自己面前的桌案,神色间是淡淡的鄙夷不屑:“你与他,还不是一丘之貉。”
他笑着扬一扬手中的夜光杯:“在下何德何能,竟与右相并称,居士太过抬举了,令我好生惭愧呀。”
莲静转过头去,看向温泉中石雕的莲花,不予理睬。
他瞥一眼那石雕的莲花,又道:“莲花出于污秽而保清洁,姿态娇怯却有傲骨,无怪乎居士以莲为号呢,实是相称。”
莲静淡然回应,仿佛只是自言自语:“既出污秽,必有所染;茎叶娇弱,其傲有限。莲高洁输与菊,风骨不比梅,惟心素淡,虽苦犹清。”
近看他的侧面,美如雕琢,玲珑清透,眉目间神色清冷,确乎容易让人想起那“至清至纯”的形容。至清至纯?世上哪来至清至纯之人?他再一次在心中嗤笑。惟心素淡,虽苦犹清,人心乃是最最污浊之处,素净容貌可求,素净之心,谁有?
他看着他纤细娇美的颈项,微扬的下巴,凛然的神情,的确很像初夏里第一朵探出水面的莲花,美丽而高傲。不过是朵莲花罢了!轻而易举就可以折断它的茎杆,揉烂它的花瓣,投进泥塘里,还不是一样腐烂。
谁叫他是个男人呢!如果是个女子,他定然下不了这样的狠手。
只不过……
第一眼看见他的时候,隔着树丛,疏疏朗朗的枝叶,恍惚只见隐约的侧影,如同蒙了一层雾气,素衣如云,眉目如画,肌肤如玉,只道是林中仙子。而那雾气,夹杂着莲花的香气,丝丝缕缕,沁入心脾,不知哪一根,哪一线,便被轻轻地触动了。
先入为主,只怕往后,都无法完全将他当作男子了罢。而不把他当作男子,自然也就……下不了那样的狠手。
他无奈地一笑,饮尽杯中美酒。
他哪里像个男人呢?
杨昭半眯着眼,侧倚着轿厢壁,看着近在咫尺的面容。头一次这么近地看他,连眼睫上的每一丝细微颤动都看得真真切切。从侧面看去,莹润的鼻尖上有细微的绒毛,而肌肤细致如瓷,半点瑕疵都看不见。轿子里烧了炭,暖烘烘地热,不一会儿就烘出了汗,蒸得他身上莲香愈发浓郁,弥漫在轿子的狭小空间里,隐隐浮动。
莲静不安地动了一下,眼角余光瞥了他一眼。
“咳……还真有些热呢。”他稍稍回神,大概是一时不适应这种干热,声音略带喑哑,他清了清嗓子,“下官左手行动不便,吉少卿帮一帮我,把外头衣服脱下来好么?”
莲静坐在他左侧,轿子狭窄不能转圜,杨昭又比他稍高,值得微微站起,双手绕过他肩膀去脱他右半边的衣服。
他看着眼前素白的颈项,有片刻的怔忡。如此细腻柔美的肌肤,连女子也要羡慕。这样靠近,能闻到莲静身上的香气不同于远处所感,除了莲花香味以外,还别有一丝若有若无的气息,在鼻尖上缭绕着,让他心绪有些浮动。圆润的喉结,像丝缎包覆的珠子,随着吞咽的动作而上下滚动。
的确称得上是珠圆玉润,但是,他更愿意把这个词用在别的方面……他抿了抿唇,眯起眼,冲莲静喉间呼了一口气。
“你干什么!”莲静大惊,放开他往后退开,撞到轿厢壁。他一手捂住自己脖子,瞪大双眼,惊骇地看着杨昭。
他笑问:“怎么,你脖子里有什么东西么,碰不得的?”
莲静把手放开,缓缓坐下,不搭理他。
他甩一甩右手,把脱了一半的大氅甩下,挂到厢壁挂钩上。“吉少卿好筋骨,冬日里还穿这么少,也不怕冻着。”他把手搁在莲静肩上,“不过,轿子里这么暖和,少卿穿得好像还是厚了一点,不嫌热么?”手捏了一把莲静肩上衣物。
第一下没有捏到肩骨,只是厚实的棉布。他更重地握住那肩,估摸着厚实布垫下的身骨,和一般女子也差不到哪里去。怪不得连安庆绪也说,刺客的身形像个女子……
“你别碰我!”莲静怒道,肩一抬把他搁在自己肩上的右手甩了出去,撞到他左肩的伤口,绯色官服立刻洇出暗红的血迹。
他倒吸一口冷气,痛得五官扭曲,居然还笑得出来:“不就是穿得厚一点,又不是藏着什么东西,怕什么?”
莲静只当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别过头去:“你伤口裂了。”
他看了看肩上血迹:“是啊,好深的一道口子呢,是昨夜那个刺客留下的。都怪我太自信,还以为他不会忍心真下手伤我……”
那一瞬间,他和他面对面,他第一次那么近地与他对视。那样熟悉的一双眼,让他轻而易举地认出他来,蒙面的黑巾在他眼里防若透明,他清清楚楚地知道黑巾下那张脸每一处细微的轮廓。他真的以为他不会忍心下手,或者说,他真的希望他不会忍心下手,但是他还是一剑砍了下去。
他心底暗暗苦笑,一手扶着伤臂,歪着身子,眼神却觑着他的脸,不放过任何一丝波澜动静。
“他要刺安禄山,你挡着,没连你一并杀了已是手下留情。”莲静冷冷说道,迟疑片刻,终还是从衣兜里掏出一瓶药来,“这是伤药,效果还好,你先敷上。”
随身都带着伤药啊,他还惦着他身上的伤呢?他瞧着眼前那张素净的容颜,将他神色间那抹不自在的闪烁看了个够,才接过药瓶来,放在手心里把玩。
既然他还惦着,那他当然——也不会忘。
他怎么会是个男人?
杨昭站在栏杆前,双手握着扶栏,远远望着那辆马车越驰越近,车上的人越来越清晰,手掌也越握越紧。
他就坐在车夫身旁,双脚垂在车板下晃荡,样子很是闲适,又有几分慵懒和俏皮。初见他这模样,让他不由轻笑出声,目光便锁在了他身上。但笑意未歇,便霎时冻住——
的确是个美人儿,身姿、容貌,都属上等,那关切的情态,也不是做出来的。郎才女貌,一对璧人。
她给他披上披风,她搂着他,他握住了她的手。
第一次,这样真切地感觉到,原来他,和自己一样,始终是个男人。
“三哥,是他们到了么?”柳夫人握着团扇,从身后探过头来,“哟!好一个美人!吉少卿真是好艳福。”
他眯起眼:“我要她。”
“她?谁?”柳夫人含笑问。
“还能是谁?”他皱起眉,猛一甩头,转身进屋。
还能是谁?还能是谁!
不一会儿,他就被请上了楼来,身后跟着那如花似玉的美人。她牵着他的衣带,依依不舍,柔情万千。
他面无表情地盯着她,眼睛瞬也不瞬,直盯得那美人心头忐忑,放开了他,又乖乖地到他身旁席上坐下。
“妾是想为我兄长求少卿割爱。”
他似乎吃了一惊,抬头看飞快地看了他一眼,触到他的视线,又即刻低下头去。
他懒懒地握着酒杯,眼睛半眯着,便是他低了头,也不肯放过那面容上的每一分表情。他一句话也不说,神情复杂难辨,欲言又止;而看他的人,也被他牵着悬着,只盼他就这样沉默下去,不要开口。
可是他还是抬起头来:“且慢!”
而那牵着悬着的线,也随之收紧,扯痛了,抽痛了……又在哪里?
他直面着他,掷地有声:“杨御史,明珠是我妾侍,实际已是夫妻……”
夫妻……他是男人,她是女人,他们是夫妻,他们可以在一起。
而他,也是个男人,所以,他跨不过去,永远也跨不过去。那个女人轻轻巧巧地一抬脚就能走过,轻浅如一汪小水洼,可是这辈子,他都跨不过去。
她凭什么?凭什么!
他瞳眸紧缩,怒而站起,跨过面前的案几,走到明珠面前,一手捏住她的下巴,硬把她从地上拽了起来。
“你可知道要取回这颗明珠,需要拿什么来交换吗?”
他凛然道:“在所不惜。”
“即使赔上你自己?”忍不住手上力道又加重几分。
话一出口,心头顿时明朗起来,那些混沌不清的迷雾,都随着这句话,烟消云散。其实他所想的,一直都很简单。
他要他,就这么简单。
然而……然而!
他忽然明白,他所痛恨的,并不是手里这个女人。
他只恨,老天将他送到他面前,却把他生作一个男人。
为什么他竟是个男人?
陈年的好酒,浓香馥郁,绵软温润,滑入肚腹,却是火一般的滚烫,熊熊地燃着,从内到外,一路焚烧。
“侍郎好酒量,喝了这么多,一点都不上脸呢!来,再喝一杯!”
不上脸么?他迷蒙着双眼,伸手摸了摸自己的面颊。冰凉的触觉,从指尖传来,隔着一层肌肤,一里一外,一热一冷,只薄薄的界限,却是完全相反的两个世界。
就像他,就像他啊,纵然放在心里是如火的热烈,现于外时,也只能是不动声色的冷然。
模糊的人影向他偎过来,扑鼻是浓郁的香氛,混着酒的气息。温暖而柔润的女体贴上他冰冷的肌肤。他嗅着那陌生的浓香,竟隐约闻到荷花的香气。
美酒佳人,软玉温香,人生之乐,莫过于此。
这一生,他的快乐,也仅止于此。
恍惚中,看到一袭素白的倩影。
他猛然坐起,挥开身边的人,对那白影唤道:“你,过来!”
白影袅袅娜娜地向他移过来,却在他面前不远处站住。他伸手去拉,她一闪身,衣摆从他指间滑开。
“别走!”他扑上去,紧紧揪住她的裙角。
她轻轻一笑:“要我留下,那就把她们都赶走。”
“好,我都依你!”他急急地应承,匆忙把身边的人全都赶开,只剩她一人。她这才走近了,柔情款款地唤了一声:“杨郎。”
他想起每次见他,他都是这么叫他,“杨侍郎”。他勾起面前人儿的脸,素白的容颜,不施粉黛,蛾眉宛转,笑靥含春,分明就是他的面容,只是少了那分清冷,多了几分妩媚。
原来她换上女装,是这副模样,和他梦的想的,完全一样呢……
他往她唇上吻去,却被她躲开:“外头那么多美人儿,你都不要了么?”
他急忙道:“不要,都不要了,我只要你。”
“这可是你说的,你可得记着。”她咯咯地笑,“只要我,别人谁都不要。”
“我记着,这辈子只要你,别人谁都不要。”他搂过她来,恣意吻着,手伸进她衣内,确认自己触到的是女子的身躯,才放下心来。
早上醒时,日头已高,头痛欲裂,双眼酸涩得几乎睁不开。身侧的女子睡得正沉,玉臂伸到被外,搭在他胸前。
如同从前和将来的每一个早晨,在错误的人身边,错误地醒来。
他轻轻拿开她的手,塞进被中,坐起身来穿衣。这一动,她却醒了,揉揉惺忪的睡眼,忆起昨夜缱绻,笑得甜蜜,也不顾自己身上未着寸缕,翻身从背后抱住他。
“杨郎。”她柔声唤道。
他推开她的双臂:“才五月,天气还凉着呢,小心冻着。”
她抱着他不肯放手:“今日不是不用早朝么,时候还不算晚,怎么不多睡会儿?”她嘻嘻笑着,啃一口他的脖子,“你不累么?”
“有事要进宫。”他扣好衣扣,拎过靴子来,一只脚刚抬起,身后的人已经跃下床来,身上草草披了一件薄衫,三下两下帮他把衣帽都穿戴妥当了。
他放缓了语气:“好了,我要走了,你再睡一会儿罢。”
她抚着他的衣领,突然问:“昨天晚上你说的话,当真么?”
“什么?”
“就是……你说,这辈子只要……”
他叹了一口气:“当然……当真。”只是……
“那你是不会再纳别的姬妾了么?”她抬起头来,“陛下昨日赐的那些美人……”
“都遣走罢,你去安排。”他整了整衣冠,“时候不早了,我得走了。”
外头太阳正好,日光很亮,一开门,冷不防被明晃晃的日光闪到眼睛。他闭上眼,揉了许久,才缓过劲来。眼皮却依然沉沉的,又酸又痛。
不再纳别的姬妾,答应就答应罢,反正……也都是一样的。
嘶啦一声,单薄的中衣从中间一分为二,露出其下的雪白肌肤和——
两人同时僵住。
那圈缠住他身子的白布,缠得那么紧,边缘都陷进肌肤中。虽然莲静此刻面朝下趴着,但任谁也能看出那圈布是干什么用的。
他轻笑了一声。
老天待他,果然还是不薄。
喜欢镇魂调请大家收藏:(321553.xyz)镇魂调艾草文学阅读网更新速度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