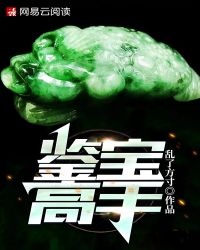天色蒙蒙亮,酒馆外面就传来了一阵喧哗声,我把头闷到被子里,想要装听不见。
昨天我曾对慕思说没有事情就不必来喊我,可不过片刻,她就又跌跌撞撞跑到了酒窖里,没敢掀我的被子,只站在我床前,颤巍巍地说:“楚姐姐,今天一大早来求酒的人都被我打发走了。可是偏偏有个狐妖,非得闹着要你帮制一杯酒,我瞧她一副不见你不罢休的架势,又有点本事,像是不答应就准备砸场子,只好来喊你了……”
她嘀嘀咕咕的这一阵,我已经从床上爬了起来,披上外衣就往外走。
这狐妖胆子倒是很大,敢来砸我的场子,我开始盘算着制一杯让她法力尽失的酒让她吃点苦头。
下楼到了门口,就看见一个穿着大红长裙的漂亮女人用妖法抵住门,身后还带了九条尾巴,一见到我,就亲热地叫唤起来:“小幸幸!”
我沉默了。
这世上会这么叫我的,也就她一个了。
这个小狐妖,呸,老狐妖,今天怕还真是不得不请进来。
——当年我被凉宫长谕逼得受了一身伤离家远走时,就是被她救了一命,说起来也算是我的救命恩人。救命之恩大于天,我曾答应过她,倘若有一日她来求酒,即便工序再繁复,我也会替她制出来。
如今,敢情是来找我兑现诺言了。
我揉了揉太阳穴,也罢,也罢。
“不知韦祖宗要一杯什么样的酒?”
我将她带到花园里,从前来过许多求酒的人,都是直接由慕思带去二楼同我陈情讲故事,除我和慕思外,从没人进过这花园。然而她之于我,还是有些不一样。
韦晚坐在秋千上,边晒太阳边瞪我一眼,嗔道:“你为什么叫我祖宗?都把我叫老了。”
我咳嗽两声,提醒她道:“我今年才二十一岁,你如今……”我扳着手指算了半天,最终也没算出个准确的数字,只好打哈哈道,“九百多岁了吧?”
她继续瞪我一眼,提醒我道:“九百三十二岁。”
我点点头,挑眉同她道:“因此我叫你祖宗是不为过的。”
她最后瞪我一眼,难得地垂了眼睛,像是在追忆些什么:“算了,晚晚这个名字,也不是谁都能叫的。
“我今天来,就是想向你求一杯美梦酒。
“一杯可以为我造一个梦,让我置身其中,再也不用醒来的酒。”
我几年前遇见她,她从来都是笑眯眯,根本没有过这样的神情,因此奇道:“你这样伤情,是不是我不在的时候发生了什么?”
“你不在的时候?”她苦笑,“你不在不过几年,而我已经等了太久了,他终究,还是不会回来了。”
韦晚是一条九尾赤狐。
九百多年前,韦晚降生的那个时代,那时还有神魔之争。
灵狐一族是上古神族之脉,其中以九尾狐为尊,九尾狐一族又以白为尊,自古狐帝,从来都是纯白灵狐。
可是韦晚,她不过是一条再普通不过的杂毛九尾赤狐罢了。倘若非要寻出些她和别的狐狸的不同,大概也只剩下她的那双晶莹闪亮的眼了。
我当年被她救下,和她一起住在她栖身的山洞中,没事的时候,就会见她化作原形,将整个身子都伏在山洞口,无精打采的,只把小小的头伸出去,四处张望着,似是期待却又很是迷茫。
现在想想,大概从很久以前开始,她就在那里等一个人了。
韦晚的真身不怎么好看,可人身却很特别,这个特别全体现在她的脸上,平时她都会施法将那张原来的脸隐去,换上一张没有那么特别的脸,但仍旧很好看。
她原本的脸,几乎把整整半张面容都绘成了一朵花,那花根从脖颈处起始,一直连到嘴角,继而往上盛开出了一朵硕大的芙蓉花,最大的那片花瓣伸展到了眉角,无比妖冶,无比娇艳。
我第一次见到她的这张脸时,盯着她久久不能回神,她轻声一笑,叹道:“从小到大,几乎每个人都是这般看我……”
“只除了他。”
那时我就该知晓,她心里,也有个说不得的人。
“我听说来你这里求酒,需要同你讲一个故事?”
“那你便听好了,我走之后,你也要长长久久地替我记着。”
我笑起来:“你这九百多年的故事,一个月能不能讲得完?要不要我替你用笔记下来?”
她叹口气,不再和我多说,只耐心地开始讲起了这个故事:“我初遇到他时,不过才一百岁……”
那只不过一百岁的小狐狸,名唤韦晚。
她自幼修为便比同龄的小狐狸弱些,旁的小狐狸一百岁时,已然会勉强化出个人形,只余下个耳朵和尾巴还化不去,可她却连人话都还不会说,整天咿咿呀呀的,像个凡世间刚学语的幼婴。
旁的小狐狸都笑话她笨,她被欺侮了也不敢言,只躲回洞里呜呜地哭。
她难过时,便将自己的头埋在颈项之中,将身子蜷成一团,瑟瑟发抖着,咿咿呀呀地发出些断续的音节。唯有她的母亲,会在此刻用爪子替她梳理杂乱不堪的狐狸毛,拍着她的狐狸头,轻声安抚她,同她说:
“你同他们都不一样,你是这世间最厉害的小狐狸。”
她知晓自己天资愚笨,然而母亲这样说,她便总觉得自己同旁的小狐狸,有那么些微的不同。
她想,她一定要成为这世间真正的、最厉害的小狐狸。
然而还未等她做上这世间最厉害的小狐狸,母亲便永远地离开了她。
那是一个大雨滂沱的深夜,母亲外出觅食,她躲在洞口,静静地等待母亲的归来。
她太过蠢笨弱小,母亲从不敢让她深夜独自外出,是以母亲虽然始终都未曾归来,她都谨记着母亲的话,只在洞口候着。
她等了许久,未等到母亲,只等到一个提着赤色狐狸皮的英伟男子,他的装扮十分奇特,猎手不似猎手,方士不似方士。他迈着极为沉重又极为缓慢的脚步,一步一步,穿越那些泥泞的山路,来到她身侧。
待到他走近,她便看清了——
他手中那沾了血的赤色狐狸皮,便是母亲那一身漂亮的皮毛……
她又惊又痛,满心悲怆无以言说,下意识地便开始呜咽,不设防身子却被人整个提了起来。
“你是这赤尾狐狸的幼子?啧啧,你这皮毛,远不及你母亲,取了也没什么用……”
他好似思考了一番,又将她向上提了提,逼得她直视他的眼睛。
“这双眼睛倒是不错……你以后便跟着我吧。”
她的眼中猛地迸发出一些凶恶、略带嗜血的光芒,她从前被其他小狐狸欺侮,都是忍着挨着,不愿与他们交恶,然而今日却无法继续这样隐忍下去——
眼前这个男子,夺了这世间唯一疼惜她的母亲的命,叫她如何隐忍不发?
她状似无意地伸了伸并不锋利的爪子,而后猛地伸向那男子的脖颈,眼看就要刺破,说时迟那时快,男子原本那提着母亲皮毛的手立时提了上来,生生地劈向她的爪子……
痛。
痛到难以言说。
她被男子猛地丢到地上,只来得及发出“呜呜”的两声叫喊,便痛晕了过去。
再次醒来时,天色已亮,她眯着眼瞧周身的环境。
眼前这深绿色的古桐木参天蔽日,四围几乎密不透风,明明是白日,却好似身处幽冥之穴,能瞧见的,只有自个儿的身子……
唔,还有前方那棵古桐树下坐着的男子。
他正用纤长的手指梳理着手中的赤色狐狸毛,瞧见她醒了,笑笑地将狐狸毛放下,而后走到她跟前,将她提了起来。
“这是哪里?你是谁?”再度醒来,她竟已忘记前尘往事,脑中除了自己的名字和自己是只小狐狸外,什么都想不起来。
“我是个捉妖师,我叫谢子染。”
谢子染,这样好听的名字。
这样好看的人。
“你不必总是那般愣愣地望着我。既已跟了我,便该有一个身为灵宠的样子。”他将她从怀里掏了出来,再一次将她举到头顶的位置,直视她的目光。
说来也怪,她记不起从前,可这个她甫一睁眼便见到的人,却同她签了生死契,要她跟随他,成为他的灵宠。
这天下的小狐狸这样多,她又是这样不出众,唔,甚至还有些笨拙。若选灵宠,何必选她?
她思虑了许久,也没思虑出个原因,这便总是愣愣地望着他,想要望出个究竟来。
其实他并非方士,亦不是猎手。
他乃是方西一界世家谢家的三公子。
方西谢家,通阴阳,晓天道,受财办事,从不失手。
他这一行,是东坊的一处大户花重金请来的。
这东坊说来也怪,从前万儿八千年也没出个什么事,众人皆道乃是一处难得的宝地,有许多商户赚够了钱财,便慕名来此处安度余年。可偏偏这几年,怪事接二连三——
先是坊主的千金被人所掳,待寻到之时,已只剩下骸骨。
再有众位妙龄女子仅是待在闺阁之中,便不见了踪迹,连骸骨也寻不到。
再后来,坊间的人竟大都沾染上了一种怪病,白日沉睡,夜里便形同枯槁一般,僵着身子一个个跑出家门,一致跑去坊外的一条长河前,泡在那河中,直到旭日东升,便再度归家,陷入沉睡。
周而复始,叫人又惊又惧。
这位请他来的大户人家,万幸都还未染上这种怪病,然而日日见坊中的人如此,怎的不害怕?
“这样说来,你们既还没有染上这种怪病,为何不带着一家老小离开这里?”谢子染坐在大户人家的前厅中,一下一下地敲着大户家甚名贵的红木桌,问道。
“谢公子有所不知,老朽同这东坊的坊主有过命的交情,当年也是因了他才带了一家老小前来这东坊安度余生,老朽之子还曾与那坊主的千金定下一门亲事,可惜……”大户人家的当家摇了摇头,露出极无奈的神色,却又坚定地继续道,“老朽一家在这里已然十多年,就是论道义,也不能放任东坊就这么被邪祟毁了去。”
谢子染面上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另一只手却不知何时伸进了怀中,十分轻柔地揉捏小狐狸的颈项。他冲那大户人家的当家道:“这事交给我,你大可放心。
“不出三日,定揪出是何人作祟,给你们一个交代。”
那当家听了,立马露出喜色,连声称谢。
喜欢风尘酒馆请大家收藏:(321553.xyz)风尘酒馆艾草文学阅读网更新速度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