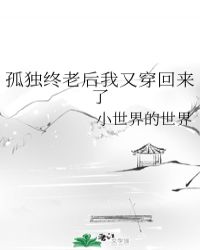司马喜的书房隔得并不远,与寝居只有数墙之隔,想来是他为了公事便利才特意如此布置的。
司马喜在中山虽然权倾朝野,在朝内也是党同伐异,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门为了前程纷纷投奔他的门下。但他本身却是一个极为清廉的人,住着简易的府邸,每月仅靠自己的俸钱禄米为生,臣下党羽们送来的孝敬一概不收,到成为了中山国的一大奇谈,举止让人费解。
他的这番用意,这世间真正懂的人却少之又少,说到底司马喜无非就是想保住自己仅有的一点气结,聊胜于无,只是为了让自己心安一些。
所以赵信看着这平常至极的书房,倒是心中觉得怪异。要知道聂盖一个小小的石邑副将,府中的豪华就胜之十倍、百倍,司马喜为一国相邦,却居如此陋室,当真让人啧啧称奇。
司马喜对赵信好奇心倒是视而不见,只是神色淡然的坐上首位,面色如水。既然扮作侍卫,书房中自然没有赵信的座位了,所以他只是站在司马喜的下手位,手轻握剑柄,眼观鼻鼻观心,低着头一副入定的模样。
门外传来轻轻的一阵脚步声,随即孟石谦卑的声音传来;“主上,人已经带到了。”
“进来。”
脚步声窸窣响起,孟石首先进门,身后紧紧跟着一女子。
赵信余光望去,首先印入眼中的却是一双浅白色的莲足,目光飞快的向上掠去,只见是名稚龄少女,约莫十三四岁的年纪,五官到是精巧,但因为年纪过小身形尚未成型,再加上一副素面朝天的样子,相貌倒也平平无奇。惟独引人注意的就是她的眼睛很大,盈盈如水,俏生生的站在那里,未语让人先有三分怜意。
“参见君上。”那小女孩浅浅行礼,声音虽然稚嫩,仪态却是落落大方,不难看出是有着良好家教的贵族子女。
身旁的孟石一欠身,见司马喜微微颔首便轻步倒退出去,拉上了门。
司马喜目光收回,落在了那女孩身上,目光却渐渐严厉了起来,上下打量了一番,忽然厉声道;“说,你受何人指使,竟然来陷害老夫。”
那女孩瘦小的身躯微微颤动,脸色却并没露出害怕的神色,只是微微欠身,轻声道;“君上息怒,民女未受任何人指使,只是心中记挂父亲安危,出于无奈才不得不上门向君上相求的。”
司马喜目光闪烁,似笑非笑的看着那女孩,开口问道;“你父亲是谁,为何找我?”
那女孩声音平静的说道;“我义父是齐国大夫徐然,奉齐王命出使中山国,半路被君上所截,扣压在府上。”
司马喜目中闪过一丝厉色,却哈哈笑道;“笑话,齐使徐然如今不正好好的待在鸿庐馆中,何来被截扣在我府上之说。”
那女孩面色平淡的看着司马喜,眼神飞快的掠过了一旁的赵信脸上,犹豫了一下,便盈盈一福道;“君上,如今只有你我,又何必以虚言相唬,难不成你堂堂相邦,却还要惧怕我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小女子。”
司马喜没想到这小女孩如此胆色,到是一怔,目光中也不由透出几分欣赏之色。笑了笑道:“那你且说说,你觉得我是如何做的,我且听听你说的如何,再决定要不要跟你继续说下去。”
那小女孩点了点头,一张小脸上却是神情肃穆,开口说道;“我听到义父来到灵寿的消息后,本想前去见他的,却看见君上亲自带人从城外迎接齐使回城,那个所谓的齐使徐然却并非我义父。”
“哦?”司马喜拉长声音道,面上却是不露声色,只是语气平平的说道;“这世间同名同姓的人本就极多,也许齐国有两个叫徐然的大夫也未尝不可,再说纵使这个徐然是假的,那与本相又有何关,我也可能是受其蒙蔽的。”
小女孩子却说道,“是义父亲笔书信告诉我的,绝不会有错。他还告诉我和你见过数面,你不可能认不出他的样子,却明知那个‘徐然’是假的却仍然装作不知,那想来也只有一种可能了,那就是这些都是你做的。义父在被你迎接的路上让你扣下了,却找个另外的人假冒。”
司马喜目中露出了几分兴趣,上下重新大量了一番这个小女孩,问道;“你可是齐人?”
女孩面色略微一犹豫,还是摇头如实说道;“不是,我是曲沃人,但住在灵寿。”
一旁的赵信听了倒是有些奇怪,忍不住多看了那女孩几眼。心想这女孩当真奇怪,曲沃明明是赵地,司马喜问她是不是齐人,她若是回答是赵人或者中山人到显得合情合理,可偏偏强调自己是曲沃人,反倒显得突兀。
司马喜却没有在这个问题是多加留心,只是笑了笑道;“你到是聪明的很,可既然知道是我所为,却为何不去告发我?”
一旁的赵信也露出了好奇,颇感兴趣的打量着这个小女孩。只见她只是摇了摇头,淡淡的说道;“我不能去告发你,否则你肯定会杀了义父来个死无对证的。我告发了你,最后即便你完了,义父却也要陪上性命的。”
司马喜奇道:“如果按照你猜想的,你又怎知徐然是被我扣住了呢?难道就不怕他已经被我杀了。”
女孩沉默了会,脸色露出孤苦之色,道;“我只是想义父是齐国的大夫,你留着总比杀了有用。义父对我有养育之恩,就算只有一线希望,我也不会放弃的。”
司马喜不懂声色的望着女孩道;“所以你独身就来求我?到真是胆大,不过不妨告诉你个好消息,徐然确实没死,只是被我关了起来,我是想从他那多套些齐国的情报。”
见女孩面露喜色,司马喜却冷冷的哼道;“可你如此来见我,就不怕羊入虎口,我杀你灭口不就一了百了。”
那女孩身躯一震,却忽然跪了下来,语带哽咽的说道;“我也是别无他法,只能来求君上的,请您能答应放了我义父。”
司马喜冷冷笑道;“你的孝心本相确实欣赏,可惜却打动不了本相,我念在你年纪幼小,又是情有可原,所以不和你一般计较,只当你什么都没说过。你可以自行离去,若是出去敢和别人乱说,我保证你义父立刻人头落地。而且即便你说出去,又有谁会相信,谁敢相信?本相又有何惧?”
那女孩却不肯离去,仍跪在地上苦苦相求,司马喜却面色纹丝不动,反而露出不耐烦的神色道;“本相对你已经网开一面,你若再不识趣,可别怪我不留余地了。”
那女孩见此只好缓缓站起,小脸苍白,目露绝然之色,忽然从袖中掏出了匕首,高高举起。
一旁正听得出神的赵信猛然警觉,飞虹出鞘,横剑拦在司马喜面前,却见那女孩并没有什么异动,赵信这才止住了动作,只是凝神警戒。
那女孩却只是将匕首举在半空,紧咬着嘴唇道;“君上,我知道我人微言轻,一条贱命无足轻重,可是若是横死在你面前你心中总会生出一丝不安的。”
“你若不答应放了我义父,我必血溅当场!”
司马喜冷笑不止,面色丝毫不为所动,却不相信她会真的刺下,以为她只是拿来唬人的,便道:“笑话,你竟然拿自己的性命来威胁本相,你若真想求死,那我成全你,你只要肯刺下,我便放了你义父。”
女孩面色果然一阵犹豫,却问道:“君上所言当真?”
“自然当真。”
话音还未落下,那女孩却真的举刀刺下,当真是出人意料。一旁一直凝神警戒的赵信最先反应过来,身子已经如闪电般飞扑而出,手中的长剑直刺匕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