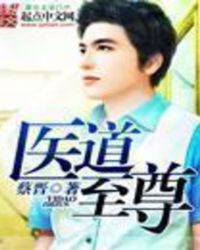翌日清晨,卫队十余人同十余暗卫一同到达宿北镇。由于人数众多不便进城,呼延良便让卫队在先前四十几人罹难的村落驻扎。呼延良简单交代了一下,差遣两人去请昨日掌柜所说的那位疯子仵作。
“你是陈疯子?”仵作被带来了。温瑜打量了一下面前的男人,蓬着头发,身材有些矮小,穿着粗布旧衣,旧衣手肘处打着两块补丁。他站立时后背还有些佝偻,只是低着头不敢正视别人的眼睛。但细细看来,他梳洗的还算干净,眼睛炯炯有神,断然不是什么痴傻之人。
“你懂这个?”大王爷指了指草席裹着的一具尸身,他并不关心眼前这个人是不是在装疯卖傻,他只需要一个能剖尸的仵作。
陈疯子点了点头没说话,直接跪下来,拿出剖刀,划开,仔细地观察着。呼延良在一旁立着,冷眼看着他操作。温瑜原是也在身侧站着,开了胸腔后她不忍再看,拉扯着呼延良的衣袖挡着眼睛。
眼看着仵作要将毒发的器官取出来,血淋淋的肺叶此刻已经全然变黑。呼延良换了个角度,将身前的人面朝自己搂在怀里,伸出一只手挡住她的眼睛。
银针刺入,针头瞬时变黑。
毒不仅及于腠理,更是深入脏器,足见并非寻常毒物。呼延良看了看验毒的银针,三五日后的尸身竟仍有此毒性:“什么毒?”
陈疯子从自己随身的布包里拿出了一只碗口碎了几个豁口的破瓷碗,又掏出了一包不知是何物的白色粉末,倒进碗里,冲了半瓢水进去。陈疯子看着银针放入碗中后碗中的水变成了湘妃色,说道:“此毒乃塔纳什惯用在暗器上的,名为梅花烙。”
“梅花烙?”温瑜听见之后,紧接着重复了一遍,“梅花烙毒发极快,插入血液中三五分钟便可毙命。但此毒需要一定剂量同时注入或连续多日注入,因此中毒者身上往往同时有几处毒刺,毒疮连结,形状似五瓣花。因此常叫梅花烙。”
“你是宿北人?”呼延良心里大概清楚了,竟然和这陈疯子闲聊起来。
陈疯子哪里知道眼前站着的人是当朝大王爷,只知道是个谈吐不凡的大官。他痴傻地笑了一声,搔了搔头,支支吾吾地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话。若不是见到过方才验尸时他沉着冷静的样子,呼延良见此情形可能真的以为他是个疯癫的。
呼延良指挥着侍卫处理好验过的尸身表皮,保存妥当待呈上西京以做呈堂供证。陈疯子接连又验了几个人,得到的结果同之前呼延良二人估计的大致相同。基本可以确信宿北镇这一百余口人,皆是塔城人的手笔了。
入了夜,侍卫们在村中各寻了地方休憩。呼延良则带着温瑜回了宿北镇上的宅子过夜。
是夜,温瑜被这山野的蚊虫嗡鸣吵醒,发现身侧的人不知何时已经不见了踪迹。她披了外衣走到院子,看见呼延良坐在院中的草棚内,怅然若失地不知在想些什么。
温瑜悄悄地走过去,从后面轻轻将手搭在他的肩上:“怎么,睡不着?在想什么呢?”
呼延良抚摸着搭在肩上的手,声音低沉:“怎么吵醒你了?”
“没有,是被这蚊虫吵醒了。依我看,我们不必着急,塔城人也在等我们。我们只需按兵不动,自然会有人自己上门。”温瑜以为,呼延良是在为塔纳什的不速之客而焦虑。眼下敌在暗,我在明,确实不利。
“嗯?你怎么知道我在想这件事。”
温瑜吐了吐舌头,调皮地笑了笑:“也许我是你肚子里的小蛔虫吧。我还知道你在担心我的安危对不对?”
高级别行使出现在呼延国有三种可能,要么是为了救人,要么是为了情报,要么是为了杀人。前两者,救莫肃和偷情报,都应该悄无声息地潜藏进入西京,伺机而动,怎么考虑都不应该在西京外的山野小镇大开杀戒。唯独最后一种可能说得通,寻找由头,将要杀的人调出西京,趁其防备薄弱,取其性命。
“出发前我也纠结过,是将你留在西京多派些人严加保护还是带在我身边。思来想去,虽然带在身边不那么稳妥,但至少你在身边,我心里就没那么挂念,不必分心担忧。”在呼延良心里,将她托付给再多的暗卫高手也不及自己贴身保护来得放心。
温瑜似乎对于有人要取自己性命这件事,并不恐惧,语气十分轻快:“所以呀,你呢,只需要看好我。我在这儿,塔城人很快就会出现了。”说罢,便推搡着呼延良起身,督促他回房继续睡觉。
月光洒在小宅子的院子里,星光落在两人肩头。呼延良顺着她的力道起身,被她推着往屋内走,只是月色之中他的眉仍是微蹙着。
温瑜半梦半醒中,又听到耳边蚊虫嗡鸣的声音,烦躁地往呼延良怀里蹭了蹭。男人翻了身,撑坐起来,将她往怀里搂了搂,伸出手臂盖在她的耳朵上,温柔地注视着她渐入梦乡。第二日清晨起床,呼延良看着半条手臂上尽是蚊虫叮咬后的红肿,无奈地笑笑。再低头看看仍在梦乡中的她,倒是一夜好梦。
第二日,呼延良与温瑜没有等来塔城人,等来的却是陈疯子。
陈疯子搔着头,看着脚尖,说话语气憨厚老实:“我家茹娘差遣我来给各位官爷送点吃食。”说罢便从小推车上搬下来一盆馒头,一筐鸡蛋以及其他菜蔬。
“不行不行,这可使不得。”温瑜瞅了一眼,满满一筐鸡蛋怕是这乡野农家本月全部的留存了。
陈疯子话不多,仍是憨憨地笑着,这便准备离开。没办法,温瑜只好掏出一锭银子递过去:“那行,就当是我们买了你的。”
可没曾想到,第三日第四日,接连三日每日上午陈疯子都推着小木车,送吃食过来。这一来二去的,呼延良便起了疑心,还特意派了两名卫兵尾随着他回家。
同样起疑的,还有温瑜。
看着陈疯子走远的身影,温瑜说道:“王爷有没有闻见陈疯子身上有股子熟悉的香气?”
“香气?”呼延良努力地想了想,似乎确实。陈疯子一个落魄的乡野村夫,整日耕地劈柴,又常与死人打交道,怎会有香气。
“那香气,我只是感觉熟悉。似乎是在哪里闻到过,却一时间又想不起来。”
“茹……娘?”呼延良默念着两个字,若有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