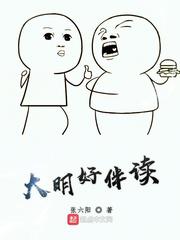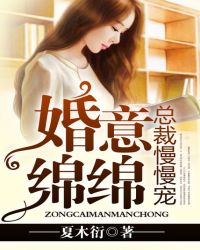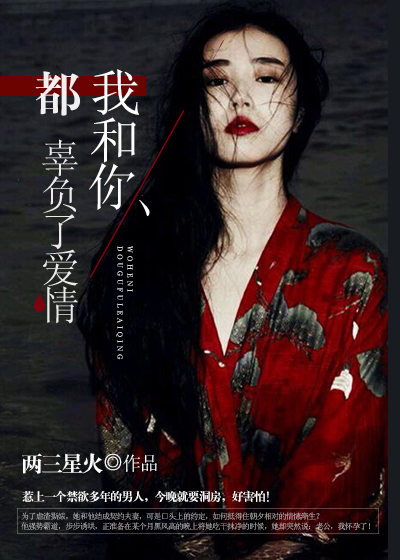D-好了。
如此一来,势必也就让那些心怀不轨之人称心如意了。
幸好,随着一群考生鱼贯而入的王守仁也瞧到了谢至。
王守仁自是不会有人也落人口实的事情,就连一个多余的动作都没有,只是一个简单的微笑示意。
谢至已是反应过来了,自是不会再有太多不当行为,同样回了微微的一笑。
两人示意之后,王守仁直接朝相反方向坐在了自己的考棚中。
谢至和王守仁皆是顺天府人氏,为他们安排考棚之时自是也不会安排在一起的。
当然,来来往往巡视的差役,考官,考生相互之间作弊那根本是不可能的。
再说了,天下有几个像谢至难般,一下能写出五六篇策论的,也没有谁会担着如此之大的风险再给别人写上一篇策论的。
所有说,考生之间作弊根本就不可能存在。
随着所有考生皆以落座,主考官便宣布了放题。
随之,便有差役把策论题目一个个发放到了考棚之中。
对这策论的题目谢至已是有些急不可耐了,他颇为急切的想要马上动笔了。
等了半晌,那差役终于把题目发放到了谢至手中。
谢至道了声谢,展开纸张,馆阁体书写而成的题目出现在了谢至的面前。
“朕惟自帝王之致治,其端固多,而其大不过曰道,曰法而已。”
这题大致意思是说,我即位一来努力行道刑法,但为什么效果不佳呢?
考察的关键在于,让考生对如何治理国家发表自己的看法。
弘治皇帝即位十几年以来,中兴之治已经初见成效了。
看来弘治皇帝也并不愿就此止步,还在追求更大的进步。
大明建国已有百年时间了,一个王朝该出现的顽疾也都已经彰显出来了。
一些话就看考生是否敢于直言了。
不过,谢至敢断言,就弘治皇帝所言这个问题,肯定不会全部都达到他所要的那个效果,大多数考生是会对弘治朝十几年的发展歌功颂德的。
有些人是出自真心,有些人便是在谄媚了。
就大明现在所存在的这些顽疾,有的人即便看出来也不愿讲出来的。
毕竟,这可是得罪达官显贵的事情。
考虑了一炷香的功夫,谢至动笔了。
自然,谢至也并未从那些勋贵侵占良田,划分自己田庄方面入手。
这个问题得罪的人太多,也不适合现在解决这个问题。
谢至另辟蹊径选择了,民富,国强,兵壮方面通过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展开了论速。
吾皇即位以来夙兴夜寐,励精图治,亲贤臣,远小人,庙堂之上能体恤百姓,心怀天下者甚多,且宽刑狱,少徭役,赋税,百姓皆可安居乐业,各司其职,有中兴之盛景,然,止步便是落后,需继往开来方能延续盛世之良景。
学生以为,盛世之良景延续的良方,便是民富,百姓有了银子才可为朝廷赋税,朝廷挣得的赋税多了,才可充盈国库;百姓有了银子,才能养活更多的人口,那朝廷可征兵丁也才会壮大
谢至一片策论洋洋洒洒的写了差不多有一千字,好像还有千言万语一般。
瞧着时间还早,便举手示意又讨要了一些宣纸。
拿下这个状元之后,他便从这些方面入手了,现在只不过是把他的规划提前罢了。
有的考生,一张纸写不下策论的情况以前也不是没发生过。
所以谢至讨要宣纸,考官也并未请示便直接给谢至拿了一张。
一炷香的功夫,一张纸写完,谢至感觉只不过写了一半。
没办法,只好又讨要了一张。
一炷香讨要一次,不仅对其他考生产生影响,会让他们分身,更重要的是,谢至也嫌麻烦。
这次,这些便直接开口要了两张。
比别人多了三张,这下总是够了吧。
就在其他考生还在抓耳挠腮,一个字一个字往上凑的时候,谢至已书写完成了四张纸。
谢至感觉,这策论完全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一般,他正好有有了这方面的规划,便给他送来了一个枕头。
再加上,他与弘治皇帝打过交道,完全就知晓弘治皇帝的为人。
自是在书写这篇策论的时候,不会考虑因此会得罪了皇帝。
其他考生可就不一样了,他们也就是听说了一些皇帝的宽仁,又没实际见过皇帝,写朝廷所存在的弊端,也怕惹皇帝不高兴,自然得是好生衡量一下才能动笔吧?
谢至省掉了衡量的步骤,可不是能够比他们快上很多了。
谢至书写了四张宣纸的策论,便直接趴在案牍之上呼呼打水了。
都怪朱厚照那厮打扰了他睡觉,他得补个觉才行,睡眠长时间不足可是会影响大脑的运转速度了。
他在穿越的时候能把他的聪明才智带过来,那可是不容易的很,可千万不能暴殄天物有损损坏才是。
谢至睡了大概三觉,场景依旧与他睡前的一样,巡视的差役和考官都还在,唯一可见的是,远远望去,其他考棚的考生已经开始动笔了。
看这样子,距离结束应该也是快了。
又等候了那么半个时辰,一声铜锣的声音想起,春闱也正式结束了。
等着考官收了每个考生的策论,由主考核算清楚后,才开了贡院的大门,所有考生方才鱼贯而出的离开了贡院。
谢至从贡院出来的时候,王守仁便已经等候在了一边。
“走,在下请你吃酒。”
王守仁邀请,谢至也没拒绝。
现在只剩下一个殿试,殿试结束后,他就该干一番大事业了。
这些年,整日待在宫中研究那些经史子集的,也是累坏了,是该好生放松一下了。
“好啊,守仁请,某何乐而不为?”
答应了王守仁后,谢至直接打发了贺良自己回去。
自从谢至中了解元后,谢家人对他的进步也都已经习惯了。
他的这次会试,家里对他的安排与以往相差无几,但却是没有了先前乡试那般的紧张了。
谢至打发贺良回去,贺良也并未拒绝,只是安顿道“少爷早些回来。”
贺良的安顿,谢至应承着便是。
腿长在他身上,何时回来还不是由他说了算。
会试结束后,那些参考的士子皆都大肆放松,往返风月场所的,在酒楼大吃二喝的。
科举考试虽说是不再限于门第,但参考之人也还是以高门大户居多的。
那些高门大户家的子弟能够混到会试,在家中自是宝贝的很,进京参考携带的银子自是不会少到哪里去的。
王守仁和谢至在八仙酒楼寻了处僻静的角落,点了几个小菜,要了一壶酒,便开始了会试之后的放松。
。
第103章 又传鬻题
“感觉如何?”王守仁为谢至倒了酒后问道。
与王守仁相识也不是一日两日了,也算是无话不谈了,在他面前自是无需玩那套虚的。
谢至如实相告,回道“感觉倒是不错,如此类型之题,其实关键在于看考官品行如何了,若是谄媚之徒,必定会喜欢那种溜须拍马的文章,此次春闱的士子中想必有不少人是从此方面入手的吧。”
这些完全都是实情。
接着,谢至又道“不过,某想,陛下出如此之题,是想在这些士子中寻求些治国的良策吧?”
王守仁喝了酒后,回道“陛下非好大喜功之人,应是有如此之意的,在下的策论便是从辽东问题入手的,鞑靼小王子和火筛部时长扰边,边境百姓苦不堪言,此问题得有解决之法才是,在这个问题之上,在下以为出兵方为永久之法,听说,辽东总兵前几日上了折子,朵颜部也有不轨之心,朵颜部虽弱,但若与鞑靼部联合,那我辽东之地便更为被动。”
王守仁的这策论所言的着实是大明根深蒂固的顽疾。
不过,弘治皇帝不是好战之人,只要鞑靼部不入关侵犯,弘治皇帝也是很难下定决心出关征讨的。
再说了,阅卷的都是一群文臣。
这些文臣喜欢的是如何治国安民,不到万不得已,大多数人是不愿出兵的。
不过,出兵所耗费银太多,不到万不得已,着实不可出兵的。
王守仁介绍了自己的策论后,谢至回道“守仁兄策论所言确实乃是大明所存在的问题,不过,不见得是考官所喜。”
王守仁倒了酒,回道“能否高中并非在下所在意之事,心中何想,笔下何写,方不枉读书二字。”
王守仁谈吐文雅,心怀远大,着实不是一般人所能比拟的。
谢至敬了王守仁一杯,回道“守仁兄心有沟壑,某实在佩服,某是以富民强国来入手的。”
王守仁笑了笑,回道“在下记得你说高中之后要去从治理一个小县开始,到时别忘了带着在下。”
谢至倒是没想到,王守仁竟然还记着此事。
“某记着,只是”
王守仁打断谢至后半句,道“别只是了,你那番话在下还记着,就这么说定了,无论某最后能否高中,排名又如何,都愿与你去治理一小县。”
王守仁对此事既然如此坚持,谢至自也是欢迎的。
有王守仁帮着,那简直就是如虎添翼了。
就在谢至与王守仁推杯换盏之时,旁边一道声音颇为响亮的道“在下从同乡口中听到了一消息,江阴富人徐经贿赂主考预得了考题。”
“真假?”
旁边一人接着道“在下倒是亲眼所见,徐经着实去过程敏正的府上。”
程敏政便是此次的主考官。
另一人随之又道“不止是徐经吧,好像唐寅也去拜会过,前些日子,唐寅还曾把与程敏政讨得的文章四处宣读过。”
这个问题讨论起来后,聚集起来的士子越来越多。
老远处的一人,扯着嗓门问道“那唐寅是应天府的解元吧?”
人群中有人回道“没错,正是弘治十一年的解元。”
舞弊那便是对其他士子的不公,一大群士子围在一起皆都愤愤不平叫嚷个没完。
“这唐解元怕不是担心比不过顺天府的解元而行如此龌龊之事吧?”
“谁能知晓?反正这个事情朝廷得有一个交代才是。”
在角落吃酒的谢至和王守仁把这群士子所讨论的问题听的极为清楚。
谢至心中也着实无奈的很,秋闱的时候,传出了主考官吴宽为他舞弊,春闱又传出了主考官程敏政为唐寅,徐经舞弊之事。
他怎就不能好生参加个科举了,怎每次都出这么多事情?
王守仁在端着酒杯,满是不屑道“这次主考程敏政,乃是礼部右侍郎,文章学识颇好,素有清廉之名,怎会做出鬻题之事?唐寅,徐经,在下也曾相识,二人也并非偷奸取巧的奸滑之徒,怎会行出如此之事?听风便是雨,只闻风声便有传如此流言,可否想过被他所中伤之人的名声。”
谢至这下才终于想起,历史记载中的唐寅还真就牵扯到了科举舞弊案之中,因此被削了士籍,贬为浙藩小吏。
唐寅不耻就职,回乡后又夫妻失和,休掉了妻子,最后才有桃花庵。
后世所流传下来的一些列诗歌以及绘画皆是出自科举舞弊案之后。
那群士子对此事臆想之后的愤愤不平,他们以为他们是在主持正义了。
其实,殊不知他们这行为是要毁掉别人的人生的。
唐寅被牵连后,最起码在诗歌和绘画方面有所造诣了。
被牵连的徐经终生没能再有参考的机会,而程敏政更是就此抑郁而终。
谢至喝了酒,回道“总是有那么些唯恐天下不乱之人,凭自己臆测口出不负责任之言,此消息恐已是在士子中间传播开来了,朝廷必会对此有所处理的。”
谢至对这个事情了解虽不多,却也是猜对了。
贡院之中,程敏正带着一群考官正忙着为春闱士子的考卷糊名,眷录之际,给事华昶在茅厕听闻几个差役闲聊了此事。
没做任何考证,便直接写了弹劾程敏政的折子。
这折子递交到内阁之时已是傍晚快下值之时了。
内阁中,谢迁,刘健和李东阳处理完了一天的折子,把折子按重要与否的顺序分门别类归置,吩咐书吏送与了暖阁。
正准备歇口气的时候,一书吏便送来了华昶的折子。
“谢公,礼部给事华昶又递上了一道折子。”
谢迁等人是可极为尽心的,当天的折子绝对会在当天审核完毕,绝不会有拖拉误事之情况发生的。
谢迁从书吏手中接过折子,打开瞧了一眼后,便颇为大惊。
一旁的刘健瞧见谢迁脸上的变化,询问道“何事?”
不等谢迁回答,便从他手中接过了那折子,只瞧了上面内容一眼,便随手递给了李东阳。
打发走了送折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