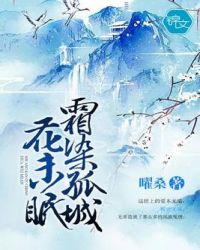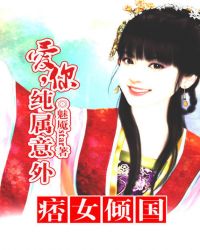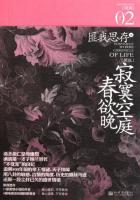五月,沧州硝烟起,金人将领勒精兵五千,五日内连下三座城池,沧州军毫无反击之力,退守山阳关,将军陈焕派人快马加鞭传信至京城中书省,再由中书上达天听,告急之信如雪片涌来,顿时朝野震动,物议沸然,一夜过来,兵败之事朝中已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朝乾殿内,皇帝高坐龙椅之上,左手按住太阳穴,缓缓揉按,眼睛半眯,神色严峻的盯着阶下吵吵嚷嚷的众臣,心内已是烦躁至极,待得那声音渐渐小了下去,方才出声问道:“可有法子了?”
八年前,殷启遥带兵深入金人巢穴,重创金兵,缴获粮食辎重及俘虏无数,逼的金人首领图尔顿遁走他乡,这才迫使他们安分了这些年岁。如今金人已经恢复生息,骁勇善战一如当年,作战不畏死,一心求胜,而殷启遥已不在,镇守沧州的陈焕懦弱无能,叫他坐享其成,仰仗殷启遥之余威管理庶务尚可,带兵作战却是畏首畏尾,既无文韬、又无武略,以致金兵一到,已经闻风丧胆败阵而逃了。
“皇上,如今当务之急,必要先派一个有能之士赶往沧州,稳定局势,缓缓图之。沧州的急信过来,最快三天三夜,也就是说,这三天战况如何,臣等全然不知,何其焦心呀!”
皇帝点点头,转着手中那枚玉扳指道:“朕自然知道,不要说这些没用的,说说看,有哪些可用之才?”
朝中武将,多为殷家旧臣,给了俸银闲散在家,自然是要避讳的,至于京郊木家,木敬言已年老,其子也已随殷启遥而去。如此计算下来,只有一些新进的武将了,只是没有作战经验,万一只是纸上谈兵之徒,一去沧州,不仅没用,反而添乱,又该如何?于是皇帝此言一出,下面竟乌压压的无一人敢答话。
“无人有所谏言是么?”皇帝手上动作停住,冷笑着将目光扫过底下无数臣子的脸,平时闹腾着什么忠孝仁义,连一点点小事都要上奏个没完,一到紧要关头,就全成了哑巴,半点可听的话都没有。
“臣有话要说。”突然一人执笏板出列,向皇帝弯腰行礼,众人皆抬眼偷看,心中佩服他的勇气,明明知道当今形势严峻,若人选差了,到时候连累自己,还能毅然决然向陛下谏言,一边佩服,一边又暗暗红了脸。只见那人长得便是相貌堂堂一副正直模样,四十来岁年纪,便是枢密副使杨正清无疑。
“马军都虞候韩硕,武举出仕,为人虚心好学,善谋善断,机警非常,又是株州地方有名的孝子,老臣斗胆,推荐韩硕暂代陈焕之位。”
皇帝沉吟片刻,问道:“你说的韩硕,可有带兵作战的资历?”
“没有,韩硕是布衣出身,入朝也不过三年,并没有机会历练。”杨正清坦白道,虽是如此,他也知陛下一定会任用韩硕,就为了两点:一是朝中无人,二是韩硕身家清白,家中没有权势,便不会有当初殷启遥那般的辉煌景象,也就不至于危害到陛下,自然是不二人选。
“还有人要上奏么?”皇帝犹豫着,又问了一句。
下面鸦雀无声。
“那便退朝吧。”皇帝不耐烦的摆了摆手。
“将领之事陛下可有决断?”杨正清赶忙追问了一句。
皇帝已起身要走,忽然听得他这句话,心中忍不住猜疑起来,人人都避而不得的事情,杨正清不仅做了,还如此迫切,莫不是受了谁的意吧?
皇帝淡淡的瞥了一眼立在朝队最前的慕容恪与慕容谨,这两人从头至尾未曾说过一句话,此刻也是垂眉低首。随即把目光收回,对身边的高演点点头,高演会意,大喊一声:
“退朝——”
皇帝转身离开,百官跪拜完毕起身,鱼贯而出。慕容恪与慕容谨二人却不约而同的立定在原处,默默望着百官背影,后者突然笑着向慕容恪走来,颔首道:“臣弟先行一步,皇兄自便。”
慕容恪冷冷勾了勾唇,身躯僵直,待慕容谨走了几步方开口道:“是你的意思?”
杨正清虽算不上是慕容谨的人,但二人一向交好,若是慕容谨请他帮忙,他未必不肯。
慕容谨十分诧异的回头,摊了摊手道:“皇兄此话何意?臣弟不明白。”
“罢了。”慕容恪背转过身,提步追随皇帝而去,不想再在他这个弟弟身上浪费功夫。毕竟,韩硕在朝中只是一个无名小将,要说魏王和他有什么交集,又有谁会信呢?如今战事吃紧,这些勾心斗角的事情都可缓缓再谈,要紧的,是沧州险峻之地,决不能交到一个毫无作战经验的人手中。
慕容恪踏入政事阁,皇帝正在翻看沧州来的急信,心中烦恼,见他来了,面色也无丝毫好转,反倒——更沉重了些。
“你来做什么?”
慕容恪向皇帝行礼毕,开门见山道:“父皇,儿臣以为,韩硕万万不可为将。”
皇帝饶有兴趣的抬眸看向他,似乎是在等着他说下去。
“金兵虎狼之师,来势汹汹,若以血肉相搏,定然败绩。不可力敌,那就只能智取,必得一个熟悉沧州地势,深谙兵法、又通晓变机之人方有胜算。韩硕年纪轻轻,并无作战经验,如何能一朝为将,统领沧州数万雄兵?别的尚且不提,到时候士兵不服,内部秩序自相紊乱,不攻自破。”慕容恪神色泰然,即便口中说的像是大逆不道的混账话,也面无惧色。他太了解自己的父皇了,即便父皇心中如何厌恶他,终究也知道是非对错,江山若是不保,要皇权来又有何用?
皇帝果然生气,天子之怒,威严庄重,紧皱眉头盯着慕容恪不放,似乎是想把慕容恪的心思都给看透了,良久方才啜了口茶问道:“那你以为如何?”
慕容恪微微松了口气,继续道:“儿臣心中有个不二人选,不知当说不当说。”
“你说。”皇帝目光炯炯。
慕容恪微微垂下眼帘,平静道:“就是沈鸿轩。”
皇帝微微一愣,心中虽早有预料,但总不敢相信慕容恪真的大胆至此,敢把旧日反贼的名字说出来。这会儿真的听到,先是愣了一下,随即把茶盅重重砸在桌子上,阴沉着面色道:“你说什么?”
“儿臣举荐沈鸿轩,沈大夫。”
“放肆!”皇帝终于压制不住怒气,把桌上的一沓奏折狠狠的向慕容恪摔过去,正好砸在慕容恪的膝盖上,砸的慕容恪一皱眉,却终究还是无声无息的给忍下来了。
沈鸿轩乃是殷启遥的副将,只因当年出事时身在京城,方才留下了性命。但不管怎样,他和殷启遥的关系亲密众所周知,从前是殷启遥带兵平乱,如今再出事,又要殷启遥的副将领兵,这不是明摆着他大周无人可用,只有他殷家军才能治安平乱,这不是,要处死殷启遥的皇帝自己打自己的脸吗?
“你真以为我大周无人是吗!”皇帝厉声呵斥道。
慕容恪撩袍跪地,姿态庄严有度,不卑不亢,垂眸道:“父皇息怒。如今战事才是首要的,儿臣只想着如何护卫大周江山,如何从金人手中把失地讨回来,如何反败为胜,并无暇考虑其他。无论沈鸿轩是何出身,其在京城八年,安安分分,当年也未曾参与到殷启遥一案中,为何不能让他带兵遣将?儿臣思来想去,朝中实在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
皇帝听他极力为自己开脱,只有冷笑而已,半晌方道:“若他不是殷启遥的人,你也肯如此为他请命吗?”
“会。”慕容恪双眼澄澈,明净宛若天光,“只要是能解沧州之危的贤士,儿臣都会举荐。”这句话他说的发自肺腑,可这肺腑之声在皇帝听来,总是多了一些不一样的味道。
“是么?”皇帝懒懒转着那翠色通透的玉扳指,冷笑道:“你也知他在京城已经闲居了八年,如何才能保证他——现在不是一个庸居在家的莽夫?”
“还是说,你一直同他有来往?”皇帝眼神陡然凌厉。
慕容恪的太阳不由突跳了一下,感到一股巨大的压力向自己奔来,心恍惚一颤,急急思索辩解之词,停顿了半许方假装平静的回道:“儿臣与沈鸿轩并无来往,只是知道沈鸿轩今年也不过三十四岁,正是年轻有为的年纪,军旅之人,心中自然有报国志向,怎肯就这样虚度年华?必然兢兢业业,不肯放松。父皇若是不信,便传沈鸿轩来见。”
皇帝看他编的滴水不漏,只扯了扯嘴角,并未再追问下去。其实心中被慕容恪说的已有六分动摇,就是下不去决心,突然眼眸一亮,心生一计,假装随意道:“那若是孤顺了你的意思,封沈鸿轩为将去往沧州,却战事不利,你该如何?”
皇帝戏谑的看着跪立在地的慕容恪,慕容恪似乎是感受到了他的视线,毫不畏惧的迎上去,绝妙的容颜上,看不出任何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