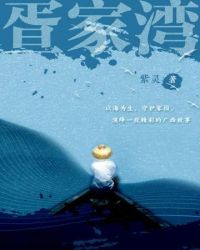却说郑福春和苏喜妹两人离开小摊子,就像两匹脱了缰的小野马,专朝人多的地方钻去。不一会儿,他们便来到了绸缎庄。喜妹在那里买了一段做头巾的蓝花布和做鞋面的料子,还想着再买点黑薯莨给阿爹做件褂子,数了数手心里的钱却是不够,只能黯然作罢。
“我这还有点,给你?”郑福春从自己的褡裢里摸出一叠钱,交给苏喜妹。
“福春哥,我有手有脚的,能自己挣钱,哪能用你的?等回去,我跟你下海去摸珍珠,到时候卖了钱再来买。”
“行了吧,那活哪里是女人干的?”福春朝她做了个鬼脸,径自去找绸缎庄的老板,把喜妹刚看好的薯莨布买了下来。
“小哥,你还真体贴,是个好男人!”绸缎庄老板的一句话,把这两人的脸都说红了。
出了绸缎庄,苏喜妹便拉着郑福春,径往药铺找去。她想找个郎中问问,阿爹的咳嗽病能不能治。苏老爹这人一向倔强,若是叫他看病,总会说没事,缓两天便好,再怎么劝也没用。倒不如先问了药,回去哄他喝下,还好些。
好在这个县城并不大,他们在青石街上转了两下,便看到一家药铺门前那高高挑起的旗杆。那是一幢两层结构的木楼,底下是铺面,有人家的两个那么大。往里摆满了装药的柜子,几个小伙计正在忙着抓药。坐堂的是一个年约二十来岁的大小伙子,只见他长得天庭饱满,鼻若悬胆,红润的双唇微轻合翕。他修长的手中紧握着一枝狼毫小笔,在纸上认真写着什么。
“这就是郎中?”苏喜妹在药铺门前站住了脚,伸着头往里不停地张望。在她的脑海里,郎中一般都是鹤发童颜,背着药箱四处行走,过着风餐露宿的日子。这些臆想,全是来自疍家船上老奶奶或是老爷爷的故事里。长这么大,喜妹还从来没见过郎中。疍家人病了,都是依靠着祖祖辈辈相传的土方法来医治。懂得治病的这些人,也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家。但在船上缺医少药,有些病就是懂得了,因为没有药,也只能苦苦熬着。到县城里就有郎中会看病,还是福春告诉她的。
不过,眼前这个坐堂的郎中实在是太年轻了!她微微皱眉,转头看向福春,轻声问:“这就是郎中?”
其实郑福春也没有真正找过朗中看病。他也是半道听说,县里的郎中治病很是厉害而已。“应该是吧?”福春犹豫着往里探了探,“不过我也听说,县里的郎中不给我们这些住船上的人看病,说是会污了手。我们还是到其他地方看看吧?”
“什么?这是什么说法!住船上跟住地上的,不都是两条腿的人吗?怎么给我们看病就是污了手?”听到这话,苏喜妹的气不打一处来。
“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是听老辈人说的。”郑福春为难地说道,“走吧!”
“开门做生意,八方都是客,哪有把客人拒绝在门外的道理!”苏喜妹抬脚就想往里走。
这时,一个穿着长袍马褂、梳着长辫的小伙计,立刻放下手中的活,冲了过来拦在苏喜妹面前,厉声说道:“走开,这里不欢迎你们。”
“开门做生意,就是迎来送往的活计,凭什么不给我们进?再说开药铺的还是救死扶伤的地方,不给人看病,这是给人等死吗?”苏喜妹一看真给拦住了,气头一下子就上来了。
“我们是给人看病,但我们不给你们看!”小伙计脖子梗得更直了。
“你说谁呢?大家都是两只手、两条腿的人,难不成你还多长条腿不成?”
他们这样一闹,引得过路行人纷纷驻足,渐渐围观过来。那坐堂的小伙子终是忍不住,从里面走了过来,朝那小伙计喝道:“白果,回去!”接着又转向苏喜妹说道:“想看病就进来吧!”
“少爷……”白果看到苏喜妹要往药店里面走,急忙喊了一声。
那少爷背着手朝白果瞪了一眼:“我知道!”
他突然伸手把苏喜妹拽进门里:“还不进来?”
“嗯!谢谢少爷!”喜妹顺势跨进门槛,学着白果的叫法向眼前的人道了声谢,便跟了进去,留下白果杵在门口直摇头。
苏喜妹是进去了,不过福春却被白果拦在了门外。
苏喜妹在堂前坐下,给那小伙子把爷爷的病况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她现在也顾不上这小伙子是不是真的郎中,好歹是药铺里坐堂的,总归不会太差。
那小伙子问了诊,给她开了方子。喜妹正要拿过去抓药,那小伙子却把药方压下,说:“你稍坐一会,这药我要亲自抓。”
苏喜妹心下虽有困惑,但也只是痴痴地应了一声:“嗯!”
小伙子冲她轻轻一笑,便起身抓药去了。这时喜妹才注意到,门外早已站满了人,还有不少人正往里指指点点。郑福春被拦在门外,沮丧地坐在街边地上。等喜妹拿了药走到门外,那些围观的人立刻纷纷让开,就像这两个人有瘟病似的。
临出门一刻,那白果朝喜妹恨恨地骂了一句:“这下你要害了少爷了!”
苏喜妹回过头朝他看了一眼,没说什么。只是他这席话,在她心里如同扎进一根小小的银针,在一点一点地刺痛着她:“我只是找你少爷看病开方子,怎么就是害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