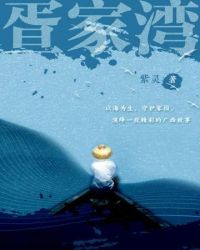这套新嫁衣是花婶她们早先就做好的,直筒的长裙有点像越南的奥黛,在晨光里红得耀眼,衣袖和裙子都镶有黄、蓝、绿三色彩边。头上的盖头如同一顶缀满了各色彩珠的花冠,就连冠下遮脸的彩帘也由各色彩珠窜成。这样的冠帽,其实是疍家人为了在海上能够遮风挡雨,但经过时间的变迁,变成了现在新娘用的喜冠。喜庆的颜色、喜庆的花冠、喜庆的笑脸,依然拦不住苏喜妹心里那份淡淡的悲伤。
“花婶,我有件事想跟你们说。”喜妹把刚戴上的头冠拿了下来放到床沿,说道。
花婶赶紧停下手中的活计,轻声说:“妹子,说吧!”
“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我想跟父母说一声。”苏喜妹幽幽地说。
花婶没来由地觉得心里也是堵得慌,却只是小声地说:“这也是应该的,去吧。”
苏喜妹默默地点了点头,起身掀开布帘,从小后门离开疍家棚。她快步穿过砗辕林,来到父母的衣冠冢前,缓缓跪下。花婶远远地跟在后面,却不敢靠近,脸上也露出不可言喻的忧伤。
喜妹在这两座坟墓前,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响头。然后用手在坟头挖了一个小坑,接着从怀里掏出那包用花布包着的银子,轻轻放进坑里;随后又摸出那本黄色的绢书,也放到了坑里面。接着慢慢地抓起泥土,一把一把地洒落到坑里,两行清澈的泪珠也跟着一滴一滴地掉进小土坑。
突然,她抬手抹了抹眼泪,重新朝父母的坟冢又磕了三个头,这才站了起来,往花婶所在的方向走去。走了几步,她忽然又猛地冲回坟冢前,把那刚填平的土坑迅速挖开,将那本黄色的绢书紧紧攥在手里,泪如雨下。
花婶终于也忍不住了,几步走上前来,一把将喜妹紧紧搂在怀里,眼泪再也停不下来:“我苦命的丫头啊!舍不得他你就去吧,找他去吧。”
喜妹抱着花婶哭了好一会儿,这才忍住泪,哽咽着说道:“对不起花婶,我还是放不下他!”
花婶红着眼,轻声说道:“这场婚事都是你爷爷的主意,他希望你留在疍家湾。可是,有时候心不由人啊!林家小伙在这里的时候,谁都能看出你俩有情意,你走吧。”
苏喜妹低下头,抿了抿双唇:“那福春哥怎么办?”
“强扭的瓜不甜。福春是个明事理的孩子,他会想明白的。”花婶此刻想不到什么更好的可以安慰苏喜妹的话了。其实于情于理她都不该这么做,可是逼着两个不相爱的人在一起,往后的苦难更多。她不忍心看到喜妹伤心,毕竟苏喜妹是她从小看到大的,跟她的亲生女儿一样,她也见不得苏喜妹如此委屈自己。
苏喜妹犹豫地看了看花婶,终于撒腿往山外跑去。
苏喜妹走了,郑福春的婚礼取消了,大伙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但谁也没有再提过这件事。
自从喜妹走后,苏老爹日渐消瘦,人也变得更沉默。郑大鱼希望他能跟他们一起到船上去住,这样也方便照顾。可是苏老爹说什么也不同意,依然自己一个人住在棚里。他说要在岸上种点小菜,等大鱼他们出海回来可以吃点青。
日子便这样在白天与黑夜的轮换中流逝。这一群疍家人把自己固封在这片小小的海湾里,自给自足、与世无争。他们似乎忘了,在这海湾里曾经有一个叫苏喜妹的妹子。在这流水般的日子里,她的身影渐渐从疍家湾消失了……